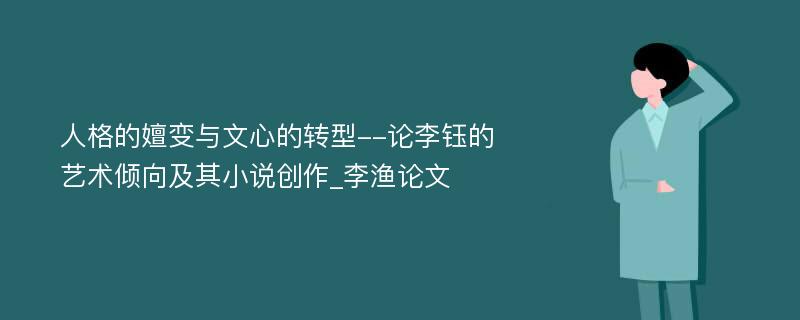
人格的嬗变与文心的转迁——论李渔及其小说戏剧创作之艺术偏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李渔论文,戏剧论文,人格论文,艺术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人格在文学作品的诞生过程中显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正如歌德所说:“总的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艾克曼39)他甚至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艾克曼229)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李渔,雅擅众艺,文备诸体,其诗、词、散文、小说、戏剧无不打上其人格心理的深深印记,本文即着重探讨李渔的人格嬗变与其小说、戏剧创作之关系。
一、从“愤世”走向“谐俗”
李渔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人格极其复杂的作家,日本学者浦部依子曾说李渔是“变色体质”的文人,①可见其人格之丰富性与多样性。如果纵向地看,李渔一生人格之发展确乎反复多变,决非直线式行进,然就其荦荦大端而言,乃是从“愤世”走向“谐俗”。大致说来,李渔入清后开始发生此种人格转向,而此后从故乡兰溪迁徙到杭州后立志从事小说、戏剧创作,则标志着此种人格转向的基本完成。其主要依据在于,入清前包括入清后开头几年的李渔,是一个比较关注时势与社会的诗人与社会批判者,此后的李渔迫于日趋严峻的政治环境,则逐渐成为一个在整体上疏离社会现实而用心以小说、戏剧创作谋生的通俗文学作家。但这并不是说他人格中的“愤世”特质已荡然无存,而是被险恶的现实生存环境所深深压抑,因此若谈论与现实不发生明显关联的历史事件等时,他“愤世”的个性就会时而显露。
简括而言,李渔人格中的“愤世”,是指他个性中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小说丛话》载浴血生语云:“笠翁殆亦愤世者也。”(《李渔全集》19:317)②浴血生所云李渔之“愤世”,当是指他的某些小说、戏剧作品中有“孔方一送,便上青霄”一类的借题发挥。客观全面地说,李渔的“愤世”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诗文中,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对愚昧风俗的痛彻批判,对现实社会的强烈谴责,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重新评价。
李渔对愚昧的社会风俗常常给以痛彻的批判。最典型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父亲去世时他写的《回煞辩》一文,文中强烈斥责“回煞”之说的不可信。所谓“回煞”,是指人死之后化作凶神恶煞于某日回家,家人当举家徙宅以避,否则必有不祥。这本是当时兰溪人据“殷俗尚鬼”而形成的一种迷信,乡民百姓奉之惟谨。李渔对此则不屑一顾,他曾颇为愤慨地写道:“甚矣,小民之愚,而传说者之过也!”(《李渔全集》1:121)强烈地表达了他富于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另如他所撰《乌鹊吉凶辩》及《不登高赋》亦然,前者对世俗想当然所认为的乌之声系凶灾、鹊之声系吉祥,痛加挞伐;而在后文中,李渔对当时人认为重阳登高能够避祸此种“无人弗信”、“举国若狂”的愚昧风俗极表愤懑:“怪善俗之无人,听举世之迷津!”(《李渔全集》1:16)
诗文中,李渔对现实社会的强烈谴责也显而易见。如果说早年《榜后柬同时下第者》一诗中的“愤多姑缓读《离骚》”(《李渔全集》2:150),表达的是对科举考试不公平的愤怒,那么,当甲申、乙酉之变时,他更写下了许多令人感愤的诗篇,如《甲申纪乱》、《避兵行》等诗,就无比激愤地控诉了战乱中明朝官兵与流贼在浙东的强盗行径与当地百姓所遭受的空前劫难。而他在1646年所写的《丙戌除夜》与在1647年写的《丁亥守岁》中分别有“秃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骨立先成鹤,头髡已类僧”等(《李渔全集》2:98,103)诗句,则极其强烈地表达了对清政府“剃发令”的一腔愤懑。李渔之所以敢于在清初如此直率地发泄对统治者的不满,乃在于当时社会还处于动荡中,掌权者尚无力严密控制文人士大夫的思想(陈大康637)。此后,李渔就再也没有写过如此充满“愤世”精神的诗作。
在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重新评价方面,李渔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愤世”者。他有一部从早年就开始写作并问世于1664年的读二十一史的笔记《笠翁别集》,亦称《笠翁论古》。此书所论与当时社会现实不发生直接冲突,他的“愤世”情绪因此几乎可以说如日初升般喷薄而出。李渔有一首题曰《读史志愤》的诗,其小序有云:“此予《论古》一书所由作也。”(《李渔全集》2:18)在他看来,一部二十一史,对许多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评价都错了:“一部廿一史,谤声如鼎沸。不特毁者怨,誉者亦滋愧。”(《李渔全集》2:19)其《笠翁别集》之《弁言》则云:“予独谓二十一史,大半皆传疑之书也。”(《李渔全集》1:307)《笠翁别集》简言之就是一部据理替古人翻案的书,而对宋儒的“工于信史”尤为鄙视。这包括对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的批评。③他在《笠翁别集》卷二《论刘知远先正位后兴师》一文中说:“《纲目》之文,亦有可以为法而实不可以为法者,要当识其苦心而已矣。”(《李渔全集》1:482)张安茂因此在此文后评李渔说:“其于朱子《纲目》,尚多谔谔之词,况其他乎?”(《李渔全集》1:482)总之,李渔读史独具只眼,而忧愤深广。
朱琰《金华诗录》指出明之中晚有李贽、陈继儒、李渔三人名声最噪,说“近雅则仲醇庶几,谐俗则笠翁为甚”(《李渔全集》19:313)。朱琰所说的“谐俗”,其实正道出了李渔人格发展的总体趋向。按李渔人格之“谐俗”,不是一般地指他所具有的诙谐个性得到世俗社会的欣赏,更主要的是指他入清后逐渐放弃以“愤世”面目出现的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而在总体上转向对当时社会的妥协、逢迎乃至谄媚。简言之,李渔人格之“谐俗”,其实质就是“媚俗”。李渔人格之所以会发生从“愤世”到“谐俗”的嬗变,究其根本,乃在于他在本质上绝不是传统意义上恪守气节的士人,而是扮演着士人与市井游民之间的一种社会角色。因此,在没有受到现实生活环境的威胁时,李渔可以睥睨世俗,坐而论道,不乏士人的正义感与“愤世”精神,但入清后,由于承受政治高压,兼之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等原因,为着生存与他所崇尚的享乐,李渔就缺乏真正士人所拥有的不屈服于世俗的大勇精神,而更倾向于奉行趋时善变的市井实用主义人生哲学,基本放弃曾有的“愤世”精神,而日益走向“谐俗”。
如前所论,李渔曾对愚昧的社会风俗严加批判,但从现实出发,如在人到中年时为求生子,他又不无迷信的地方。李渔有一首题曰《内子与侧室并不宜男,因信堪舆家言,改设二塌……》的诗有云:“衾裁裙样布,枕束内家书。”(《李渔全集》2:93)企图由此祈求生子,可见他的迷信与“谐俗”。又如,李渔在《笠翁别集》卷二《论桓玄伪旌隐士》一文中曾大肆抨击“只知得禄之为荣,不念失身之可耻”(《李渔全集》1:430)的晋代士人,但因为贫困等现实因素,他在人生后期却甘为山人、清客乃至“帮闲”;《又与岸初掌科》一信写到他一旦得到“王公大人”的“拂试”,便喜出望外,说“此中殆有天焉”(《李渔全集》1:207)。更有甚者,李渔甚至公开向人索取财物,其《与诸暨明府刘梦锡》一书云:“绨袍之赐,不妨遣盛使颁来”(《李渔全集》1:218),以致他自己在《耐歌词》之《多丽·过子陵钓台》一词中都自嘲说“终日抽风”、“面目可憎”(《李渔全集》2:494)。再如,李渔早年曾很清高地放弃科举考试,但到晚年却依然让自己的孩子去应试。其《严陵纪事八首》其七云:“未能免俗辍耕助,身隐重教子读书。山水有灵应笑我,老来颜面厚于初。”(《李渔全集》2:371)如此等等,无不传达出李渔在现实环境压力下摒弃“愤世”走向“谐俗”的声音。
就是在对待清统治者的政治态度方面,前述《丙戌除夜》与《丁亥守岁》中的诗句,表达的是李渔对清廷“剃发令”的愤怒,而《婺城行吊胡仲衍中翰》、《婺城乱后感怀》等诗也极其悲愤地谴责了战乱中清军在婺城即今金华杀人如麻这一重大社会事件,如前诗有云:“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轻则鸿毛重泰山,志士谁能不沟壑。”(《李渔全集》2:43)但到人生的后期,李渔对清政府的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如他在梓于康熙十年(1671)的《闲情偶寄》之《凡例七则》中写道:“圣主当阳,力崇文教。庙堂既陈诗赋,草野合奏风谣,所谓上行而下效也。”(《李渔全集》3:1)文中所展露的几乎是一副奴才相,而他在康熙十一年(1672)所写的《汉阳树》一诗中有“兴朝既鼎革,江山若重铸”(《李渔全集》2:17)等诗句,则更是对清统治者露骨的谄媚与逢迎。总之,前述《严陵纪事八首》其七“老来颜面厚于初”一句,可以说集中地概括了李渔一生人格心理从“愤世”到“谐俗”的本质嬗变。
“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全集》3:568)李渔不同的人格自成就其不同境界的文学作品。如上所举有关李渔的诗文,正是他不同境界人格的生动阐述。李渔一生文学创作的主体无疑是小说与戏剧,客观地说,它们是“谐俗”的李渔人格的对象化与逻辑演绎。如上所论,作为“谐俗”的李渔,由于其人格境界的平庸,因此终导致李渔小说、戏剧作品社会批判精神的整体缺失,也在根本上令他创作的诸多小说、戏剧作品缺乏真正的艺术精神。
二、“卖赋以糊其口”:片面推崇娱乐主义
娱乐的内容与喜剧的形式,是人们所熟知的李渔小说、戏剧的基本特征。但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并非真知。值得人们追问的是:李渔创作的小说、戏剧作品,难道就必定是娱乐的内容与喜剧的形式?其间是否有他的难言之隐?李渔由明入清,但其小说戏剧作品《十种曲》与《无声戏一集》、《无声戏二集》、《十二楼》,皆创作于清初,具体时间大致在顺治九年(1652年)至康熙七年(1668年)之间。清初社会动荡,对广大汉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为感伤的时代,而时代的重大变迁必定对文学创作发生巨大的影响;与李渔差不多同时代的小说、戏剧作家,对明清鼎革多有感慨。小说如蓬蒿子的《新世宏勋》、漫游野史的《海角遗篇》等等,戏剧如李玉的《千忠戮》、叶时章的《逊国疑》等等,皆以书写社会巨变寄托沉痛的家国之思。李渔决不是对时代缺乏敏感的人,与上述作家相比,黍离之悲、家国之恨,何以在他的小说、戏剧作品中消逝得几乎无影无踪?相反,笼罩于作品中的却是娱乐内容与一派嬉闹快乐的世俗景象?李渔小说戏剧作品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形,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才华,而主要是由李渔所奉行的趋时善变的市井实用主义人生哲学决定的。
清初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实行严酷的统治政策,李渔从事小说戏剧创作时所面临的基本的历史背景是:除清政府发布“剃发令”外,顺治十四年(1657年)发生了“丁酉科场案”,受牵连士人众多,李渔好友丁澎被发配当阳堡;顺治十五年(1658年),李渔友人尤侗《钧天乐》传奇上演,因有讽刺科场语,为地方官员所告,不得已走避京师;顺治十八年(1661年),则有李渔非常熟悉的作家金圣叹等因苏州“哭庙案”而被杀,凡此等等,无不威慑李渔。李渔既奉行趋时善变的市井实用主义人生哲学,必定趋利避害,由是不具备一个真正杰出的作家从事文学创作所必须拥有的无所畏惧的人格力量,他因此就既没有能像那些描写时事的小说戏剧家们那么敢于担当,也没有能如同时代同样有“愤世”精神,“狂固难辞”、“痴且不讳”(张友鹤2)写成“孤愤之书”(张友鹤3)《聊斋志异》的蒲松龄与稍后“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垒时”(郭豫适1)、以了无讳饰的写实精神写就《红楼梦》的曹雪芹那么勇敢。
惟是之故,本不乏“愤世”精神的李渔在《丁亥守岁》(1647年)一诗中就不无谨慎地写道:“岂无身后句,难向目前誊。”(《李渔全集》2:103)实即表明清初剃发令颁布不久,李渔受到震恐,惧怕说出不合时宜的话,即其人格已被扭曲。此种诗风,显然与他率真的个性不合,也与他《〈一家言〉释义》即自序中所标举的“云所欲云”这种浸透了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学思想精髓的文学创作主张不合。顺治十年(1653年),李渔在其创作的《意中缘》第三十出《会真》所写的下场诗也说:“李子年来穷不怕,惯操弱翰与天攻。佳人夺取归才士,泪眼能教变笑容。非是文心多倔强,只因老耳欠龙钟。从今懒听不平事,怕惹闲愁上笔端。”(《李渔全集》4:417—18)这里“怕惹闲愁上笔端”中的一个“怕”字,境界全出,可以说极生动地道出了李渔在现实残酷环境压榨下其人格心理的嬗变所导致的其倔强文心的变迁,不敢去写那些他其实很想写的“不平事”与“闲愁”,即为清统治者所忌讳的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悲情。而以时间论,这正是李渔开始从事小说、戏剧创作之初。李渔此种文心的转迁,从根本上制约了他的小说、戏剧作品在整体上将与描写“不平事”与“闲愁”无涉,而必定趋向“谐俗”。
与中国古代许多通俗文学作家一样,李渔从事小说、戏剧创作本身就有着十分明确的营生目的。黄鹤山农在《〈玉搔头〉序》中曾描绘他说:“挟策走吴越间,卖赋以糊其口,吮毫挥洒怡如也。”(《李渔全集》5:215)这指的就是李渔从故乡到杭州后从事小说、戏剧创作以谋生的经历。李渔在《复柯岸初掌科》一信中也写道:“渔无半亩之田,而有数十口之家。砚田笔耒,止靠一人,一人徂东则东向以待,一人徂西则西向以待。今来至北则皆北面待哺矣。”(《李渔全集》1:204)他晚年在《曲部誓词》中甚至专门声明“不肖砚田糊口,原非发愤著书”(《李渔全集》1:130)。李渔本无固定经济来源,试图依靠从事小说、戏剧创作为生,情有可原。但对一个人格真正健全的作家来说,他从事文学创作就是有相当的经营目的,也并不能注定要绝对回避社会现实与生活本质。李渔稍前的作家如冯梦龙、凌濛初等之所以从事小说、戏剧创作,不能说没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但他们并没有因之规避社会现实。诚然,李渔与冯梦龙、凌濛初所处的时代不同,他要直面险恶的政治环境,的确不得不谨慎处世。但一个真想要写出时代与社会生活本质的作家,一定有办法在险恶的环境中找到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何况李渔在《与陈学山少宰》中自许在“稗官野史”写作方面“实有微长”(《李渔全集》1:164)。如前所述,李渔同时代的蒲松龄与稍后的曹雪芹,同样面临清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但无不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如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谈狐说鬼,曹雪芹《红楼梦》的“大旨谈情”(曹雪芹高鹗3),分别写出了自己所处时代社会本质的许多重要方面。蒲松龄与曹雪芹所取的写作方式尽管不同,然他们之所以敢那样写,这正如徐中玉先生在《论“创作必须是自由的”》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不幸的时代所以仍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品,就因作家在困难环境里,内心还是自由的,大胆的。”(24)然而李渔由于其人格的趋向“谐俗”,终使他“无胆则笔墨畏缩”(霍松林26),他本就有着营生目的的小说、戏剧创作,因此必定只关注它们出版或演出后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其他。
职是之故,李渔从事小说、戏剧创作“心心念念地记住自己的服务对象”,并使“服务对象觉得有趣”(章培恒2),即戮力迎合最广大读者与观众(以戏剧作品而论)的审美情趣;如果读者与观众不喜欢他的作品,将有可能影响到他的生存。那么,如何才能使服务对象觉得有趣呢?李渔的办法就是让其小说戏剧作品趋向“谐俗”。他在《复尤展成先后五札》之五中曾对尤侗说:“弟则巴人下里,是其本色,非止调不能高,即使能高,亦忧寡和,所谓‘多买胭脂绘牡丹’也”(《李渔全集》1:191),这极生动地表达了他的小说戏剧创作对“谐俗”实即“媚俗”的自觉追求。李渔由是悉心揣摩读者或观众心理,以投其所好。他在《〈古今笑史〉序》中说:“世之善谈者寡,喜笑者众。”又说:“人情畏谈而喜笑也明矣。不投以所喜,悬之国门奚裨乎?”(《李渔全集》1:30)因此建议将原出于冯梦龙编辑的《谭概》改名为《古今笑》,“从时好也”(《李渔全集》1:31)。相反,不有趣、引人发笑的作品即使写得有深度,在他看来,人们是不会欣赏的,其《四方诸友书来,无不讯及新制填词者,不能尽答,二诗共之》一诗云:“近词颇似西湖月,纵好谁人耐冷看?(《李渔全集》2:327)概乎言之,李渔此种为着“从时好”而“投以所喜”、努力让人发笑的甚为“谐俗”的创作心理,无疑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小说、戏剧创作必定要走向内容上的娱乐主义,多有风格上的喜剧色彩,其《风筝误》末出《释疑》下场诗因之有云:“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惟我填词不买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李渔全集》4:203)这首诗极明确地道出了李渔将其戏剧作品当成经营的商品,所谓“一夫不笑是吾忧”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的戏剧创作极力偏向于娱乐主义的艺术追求。李渔在小说创作方面虽然没有明确地鼓吹娱乐主义,但他把自己的一部小说集命名为“无声戏”,并具体地用写戏剧的手法写小说,其小说从总体看显然也充满娱乐的情调与喜剧的氛围,有学者因此敏锐地指出李渔戏剧创作所追求的“一夫不笑是吾忧”,也是他的短篇小说《无声戏》、《十二楼》的创作旨归(徐凯160—62)。
客观地说,小说、戏剧本身就具有娱乐功能,李渔作为一个有着明确经营目的通俗文学作家,强调小说、戏剧创作一定程度上的娱乐性,本无可非议,即如冯梦龙、凌濛初的小说、戏剧作品,也未尝没有相当的娱乐性。但另一方面,小说、戏剧作品的娱乐功能不能妨碍它们对人生与社会本质的深刻揭示。徐渭就曾说:“道在戏谑。”(《徐渭集》2:582)他的杂剧《四声猿》冷嘲热讽、伤时骂世,却又颇多戏谑,如其中的《狂鼓史》便不乏嘲谑性的市井语言,《女状元》与《雌木兰》也甚多“谐趣”,至于写作于晚年的杂剧《歌代啸》则更是谑浪诙谐,但同时又弥漫“愤世”精神,不乏对时代与社会黑暗的深刻鞭挞。然而李渔由于丧失了“愤世”精神,其小说、戏剧创作所推崇的娱乐至上主义就与此不同,无论是他的小说如《无声戏》、《十二楼》,还是戏剧如《十种曲》,就绝不敢像徐渭的《四声猿》、《歌代啸》那样用娱乐的手段与谐谑方式,揭示有关时代与社会的本质内容。相反,李渔所写多为不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的男女风情喜剧或选取其他浅俗的生活题材,并没有真正深入开掘生活。
质言之,如果李渔的人格不发生嬗变,他的小说、戏剧创作即使有经营目的,也一定会如前所说找到恰当的方式,表达他强烈“愤世”的精神。但由于其人格从“愤世”趋向“谐俗”,这就从根本上限定了李渔文学创作只能专心致力于“砚田糊口”——即为营生而写作。为实现此目的,李渔由是就特别偏嗜娱乐主义——娱乐主义在他那里显然已成为一种吸引读者与观众的重要商业手段,而不仅仅是文学创作手法。卢梭在《忏悔录》中说:“当一个人只为维持生计而运思的时候,他的思想就难以高尚。”(卢梭524)李渔的小说、戏剧创作正是如此,人格的嬗变从本质上决定了他在艺术运思方面难以有高尚的情怀与远大的追求。从总体看,李渔的小说、戏剧创作因此并不是纯粹写作,而是他出于现实与世俗目的考虑的一种生存方式。
三、“取媚于时尚”:刻意追求艺术仿真
如果纯从创作技法的角度看,李渔完成了话本小说创作从改编旧作向文人独创的转变,其写作方式由此更为自由,并有显明染有李渔个人特点的浓郁喜剧风格;其戏剧作品情节新奇,科诨巧妙,排场热闹,语言诙谐,时或用丑角作主角,如此等等,的确有其独到之处,令当世人耳目为之一新。不过,正如他在《慎鸾交》第一出《造端》中所说:“年少填词填到老,好看词多,耐看词偏少。”(《李渔全集》5:423)李渔的许多小说作品亦然,一时让人觉得好看,却未必经得起推敲。李渔小说戏剧创作发生此种情状,究其根本,乃在于如前所论,由于人格的嬗变,李渔事实上是以并不健全的片面的娱乐主义文学观念去从事有着营生目的的通俗文学创作,因此就没有认真顾及小说、戏剧创作最为核心的两个方面:人物与故事情节,这就是他在《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上·结构第一》中所竭力主张的作为戏剧“主脑”的“一人一事”——李渔既视小说为“无声戏”,显然这也就应该是他小说创作的“主脑”;李渔的许多小说戏剧作品因之就缺乏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好看”而不“耐看”。
阿·托尔斯泰曾说:“人,是作家心目中惟一的客体。”(阿·托尔斯泰237)当然这并不是说小说、戏剧创作中其他因素不重要,而是说应以人物描写为中心。在实践上,李渔小说、戏剧创作却无不以故事情节为中心,又没有很好地把握住人物性格的发展轨迹。他固然相对成功地塑造了一些人物的性格,如小说《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中死节》与据此改编成戏剧的《比目鱼》中的谭楚玉、刘藐姑,小说《丑朗君怕娇偏得艳》与据此改编成戏剧的《奈何天》中的阙里侯以及小说《拂云楼》中的能红、《闻过楼》中的顾呆叟等等,但另一方面,李渔的确又勾画了很多“木偶”式的不成功人物形象。有学者指出:“李渔小说中的人物身份,凡状元、秀才、小姐、妓女、乞丐、优伶,都是一种符号,或者是人物外在活动的‘身份证’——秀才可以吟诗、妓女可以接客,而并不关乎他们的行为基调、内在素养和气质。”(崔子恩17)“这些形象并不具备完整的‘人’的内涵。”(崔子恩51)此说固然有些绝对,但基本道出李渔小说人物描写之大要。李渔的戏剧亦然。姑且以李渔小说、戏剧中诸多才子佳人为例,从表面看,李渔小说、戏剧中的“才子”如裴七郎、屠珍生、吕哉生、瞿吉人等,“佳人”如王又嫱、曹语花、刘倩倩、许仙俦等,为追求他们的“爱情”,固然有不同的外在行为,但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却不甚分明,如李贽所谓“同而不同处有辨”(蔡景康237),李渔根本没有充分触及到他们应当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心理因素。如《合影楼》中的屠珍生,因夏日倚栏而坐,看见墙下水中对面管玉娟的影子,遂生爱恋;《夏宜楼》中的瞿吉人于夏日由望远镜窥见詹娴娴,而一见钟情,如此等等,这些“才子”追求与表达情爱的方式固然不同,可他们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思想胸襟、情爱理想、性格走向等等则并不明显。如果我们将《合影楼》中的屠珍生,换成《夏宜楼》中的瞿吉人,也未尝不可;反之,亦然。与此相似,李渔戏剧中的“佳人”同样有此不足,她们基本是类型化的人物。如同样本是妓女出身的才女,《凰求凤》中的许仙俦与《慎鸾交》中的王又嫱的个性差异并不明显;而同一部作品如《奈何天》中同是“佳人”的邹氏与何氏,也无多个性差异,皆属形象非常苍白、单薄的人物。举一个具体人物来分析,如《慎鸾交》中的王又嫱,作者并没有写出她与华秀之间有着怎样至死不渝的深厚情感,但她却能立志非华秀不嫁,甘愿为他历尽十年的情感煎熬。在王又嫱身上,我们一点也感受不到她曾作为名妓所具有的妓女气息。在李渔笔下,王又嫱反倒成了那个时代的贞女节妇了。这如何不令人觉得滑稽、可笑?
在已经出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牡丹亭》与“三言”、“二拍”等著名小说、戏剧作品且叙事理论也已较为发达的时代,如前所说自许擅长“稗官野史”写作的李渔却没有很好地描写人,这确乎令人感到诧异。事实上,李渔懂得人物塑造之真谛。他在《闲情偶寄》卷二《词曲部下·宾白第四》中曾说:“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李渔全集》3:47—48)这说明他非常明了文学创作中人物描写应该个性化或者说典型化。但在具体的小说、戏剧创作中,李渔显然更看重故事情节,这是因为他深深地明白当时“绝大多数的观众与读者对戏曲和小说的兴趣都集中在情节”(章培恒骆玉明313),真正吸引他们的正是文学作品的故事性或者说娱乐性。而李渔的小说、戏剧创作如前所说主要就是为经营的商业化写作,他由此必定追求如其《闲情偶寄》卷二《词曲部下·格局第六》中所说的小说、戏剧作品故事层面“使人想不到,猜不着,便是好戏法、好戏文”(《李渔全集》3:63)的喜剧性,认为如此才会有最佳的娱乐效果,方能吸引众多的读者与观众,实现他所期盼的经济收益。惟是之故,李渔就无意于着力写出符合艺术真实的独特的人物形象。
再就故事情节而言,李渔为着片面地追求小说、戏剧创作的娱乐性,往往刻意求新呈巧,此诚如孙楷第所说:“大抵笠翁为文,才智有余而反为所累:《无声戏》如此,《十二楼》也如此。……是以无意不新,无文不巧,而往往流于迂怪,矫揉造作,大非人情。……徒张皇于关目结构之间。”(孙楷第158)所评虽为李渔小说,但其戏剧亦可作如是观。小说《生我楼》与由此改编成戏剧的《巧团圆》就是一个显例。就故事情节而论,《生我楼》与《巧团圆》可以说奇巧之极,作者企图因此吸引读者或观众。其一,尹小楼欲卖身为人父,恰巧碰到姚继欲出钱买父;其二,姚继在人行交易市场上买到一老妇人与一少女,少女竟然就是他到处寻觅的未婚妻;其三,尹小楼与老妇人原来是一对失散的老夫妻,又正是姚继的亲生父母。就情节而言,显然过于巧合,有明显的随意编造的痕迹,而人物也因此失真。以尹小楼而论,他既为财主,竟然会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插标卖身,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而姚继有如此多的巧遇,也让人难以置信。作者说这是“天赐奇缘”、人物“天性使然”(《李渔全集》9:269),实不妨说是对小说、戏剧创作艺术失真的苍白无力的辩解。小说《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与改遍成戏剧的《比目鱼》亦然。谭楚玉与刘藐姑的真爱,由于刘藐姑母亲的势利与好色乡绅的干涉而走入困境。刘藐姑为着爱,借演《荆钗记》钱玉莲故事而投水自尽;谭楚玉忠于所爱,也因之赴水殉情。两部作品写至此,已神完理足,作者却偏要让男女主人公双双获救,甚至让谭楚玉应试做官。如此等等,无疑是在强行改变生活的逻辑规律,演绎如他在《闲情偶寄》卷二《词曲部下·格局第六》中所说的其小说、戏剧创作崇尚娱乐氛围与喜剧情调的“团圆之趣”(《李渔全集》3:64)理念,以满足世俗的审美情趣。他如《十卺楼》、《奈何天》等等小说、戏剧作品也多有此种情形,即有他曾批评的“勉强生情,拉成一处”(《李渔全集》3:63)以博人一笑之嫌疑。
总之,李渔在通俗文学创作中绞尽脑汁“取媚于时尚”(坪内逍遥4),惟是之故,若严格地以真正的艺术标准去铨衡,李渔所创作的小说、戏剧作品,只有像《风筝误》等少数有相对比较完整、不乏艺术真实的个性化人物描写与耐人寻味的故事情节,其他绝大多数确实雕琢过甚,充斥浅薄的娱乐主义,缺乏真正艺术所应该具有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只是一种艺术仿真,而非艺术真实。要言之,李渔人格的嬗变所导致的其文心的转迁,确乎毁坏了他的才华,终使他错过了可能成为第一流小说、戏剧家的历史契机。在充斥消费文化与娱乐文学的时代,对于从事小说、戏剧创作的作家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沉痛的历史镜鉴。
注释:
①李渔之人格甚为复杂。浦部依子谓李渔乃“变色体质”之文人,实深得其人格之真髓。参见浦部依子博士学位论文:《李渔戏剧展现的女性形象》,上海:复旦大学,2001年。49。
②此参《李渔研究资料选辑》,见《李渔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按:本文下引李渔文,均见此书此版本。
③按:朱熹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才被康熙皇帝下诏配祀孔庙“十哲”之列,在李渔《论古》问世的清初,朱熹尚未尊显到不可被批评。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蔡景康选编:《明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Cai,Jingkang.ed.Selected Literary Essays from Ming Dynasty.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99.]
[2]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Cao,Xueqin and Gao Er.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09.]
[3]崔子恩:《李渔小说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Cui,Zien.A Study of Li Yu's Novels.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1989.]
[4]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Chen,Dakang.History of Novels in Ming Dynasty.Shanghai: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2000.]
[5]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Eckerman,Johann Peter.Conversations with Goethe.Trans.Hong Tianfu.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78.]
[6]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
[Guo,Yushi.ed.Selected Essays o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Shangha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1988.]
[7]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Lu,Xun.Complete Works of Lu Xun,Vol.Ⅲ.Beijing:People'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05.]
[8]卢梭:《忏悔录》,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Rousseau,Jean-Jacques.Confessions.Trans.Li Ping' ou.Beijing:Commercial Press,2010.]
[9]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Sun,Kaidi.A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Novels Found in Tokyo.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1.]
[10]阿·托尔斯泰:《论文学》,程代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Tolstoy,A.N..On Literature.Trans.Cheng Daixi.Beijing:People'e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0.]
[11]坪内逍遥:《小说神髓》,刘振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Tsubouchi,Shoyo.The Essence of the Novel.Trans.Liu Zhenying.Shanghai: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0.]
[12]徐凯:“传奇原为消愁设,一夫不笑是吾忧——论李渔短篇小说的创作指归”,《学术交流》1(2007):160—62。
[Xu,Kai.“On the Author' s Intention of Li Yu' s Short Stories”.Academic Exchange 1(2007):160-62.]
[13]徐渭:《徐渭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Xu,Wei.Collected Writings of Xu Wei.Beijing:Zhonghua Books,1983.]
[14]徐中玉:《徐中玉文论自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Xu,Zhongyu.Selected Literary Essays of Xu Zhongyu.Shanghai: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2009.]
[15]叶燮:《原诗》(内篇下)(一),霍松林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Ye Xie.On Peotry:Inner chapters Book Ⅱ.Ed.Huo Songlin.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79.]
[16]章培恒:“李渔创作论稿序”。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
[Zhang,Peiheng.“Foreword to A Study of Li Yu' s Literary Creation”.Beijing: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1997.]
[17]章培恒 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下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总社,2007年。
[Zhang,Peiheng and Luo Yuming.eds.A New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supplemented version)Vol.II.Shanghai:Fudan University Press,2007.]
[18]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Zhang,Youhe.ed.Annotated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Vol.Ⅰ.Shanghai: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19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