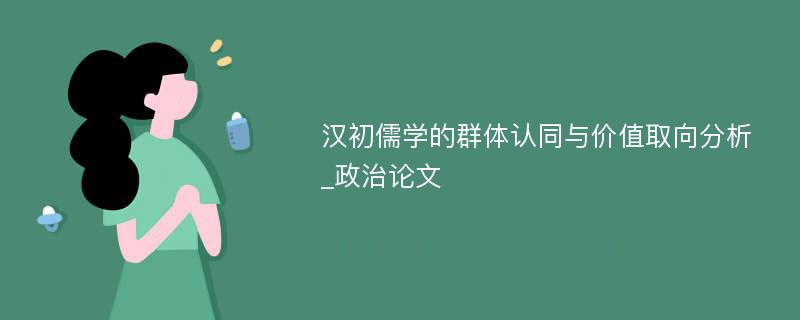
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与价值取向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士论文,探析论文,价值取向论文,群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36(2003)01-0036-06
汉兴,儒士们怀着对新政权的美好憧憬纷纷进入了汉初的大一统国家体制,他们为推动汉代政治的成功转型和儒学的复兴不遗余力。积极用世、直道而行、实现理想、改造汉政、变异儒学、推动经学思潮成为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和共同的价值取向。正是儒士们的群体认同和共同的价值选择,促进了汉代政治的发展,并使儒学发展为汉代的新儒学。本文拟就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和共同的价值取向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
史家认为,周秦之际的社会变革与政治转型,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之大事。然而,秦建立的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体昙花一现,继之而起的汉帝国承秦之制,又反秦之弊,对秦制作出了许多改造和补充。所以纵观两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华帝国,不难发现,“真正为大一统专制政治奠基并使其颇为完善的,乃是汉帝国而非秦帝国”[1](P79),先秦至秦汉成为我国历史的重要转型时期。汉王朝承五帝三王之业,定天下于一,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面对着政治的转型,汉初儒士虽经秦的暴政,遭焚书坑儒之害,但他们忧国忧民的心理意识则是普遍共有的。儒士们“除献身于专业工作外,还对国家、社会、乃至人类事业表现出一种最深切的关怀”[2](P2)。他们仍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自觉意识和实现理想与价值的强烈愿望,积极投身于汉初大一统帝国政治活动之中,试图以深厚的学理在汉初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以实现儒士们向往的理想政治和良好的人文秩序。
在汉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货志》)。为巩固汉帝国的统治,恢复经济、稳定政治已成为当时社会面临的迫切任务。于是,面对着汉帝国的政治要求,汉初儒士纷纷用世。史载,曹参任齐相时,向长老儒生问治国之术,“诸儒以百数,人言言殊”(《史记·曹相国世家》)。当时,儒士们都积极言政,发表自己对治国的见解和主张,掀起了汉初的思想争鸣,为汉初士风贯注了一种进取有为的学术意识和参政议政的主动精神。然而,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汉初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行与民休息之政策,用来缓解和抵消法家的消极影响。在此情形之下,汉初儒士积极进取的“有为”精神与无为而治的政治形势大相径庭。
其实,儒家思想的社会功能在于调和社会各种矛盾,是历代封建王朝政治之必需,士之主流的儒生才是专制政治的重要支柱。儒家思想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没有儒家士大夫的帮助和援助,他们便不能够完全统治。儒家意识形态确立了一个统一帝国的基本理想,为维系统一提供了制度框架和文化框架。”[3](P192)而汉初社会经过秦末之乱,各种制度都有待创立,所以好言礼乐的儒家急欲发展他们的抱负。秩序初建,儒士们就显现出罕见的入世激情。在当时儒士们的心中,入仕是实现他们的价值之重要条件,用世是他们的重要渴盼。一方面在于儒家之学的影响和儒士们对实现“治平”理想和价值的深切期盼,另一方面在于儒士们对旧秩序的憎恨而生发出对汉初新政权的认同并对之寄予了美好的愿望,带着对新政治的无限憧憬,他们纷纷投身于政治,为新的大一统政权构思王者盛世的理想政治蓝图,寻求长治久安之策,其参与政治之热情为中国历代所少见。尽管汉初的刘氏王朝不重儒士,但在汉初的中央政权里,儒士们仍积极用世,许多大政方针的制定都离不开他们的努力参与。用世进取、建功立业,已成为当时儒士们的人生信条。他们纷纷为汉初政权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像陆贾、叔孙通、贾谊、贾山、晁错、辕固等儒士莫不如此。史载,“有口辩士”陆贾常在汉称《诗》、《书》,为汉廷出使诸侯,定南越,除诸吕贡献力量。叔孙通于秦末归汉,积极为刘氏王朝政治上言直谏,特别是其定礼仪深得刘邦之赞许,被拜为太常。贾谊颇受文帝赏识,“贾生昭昭,弱冠登朝”,积极上书言事,为汉政草具仪法,更定律令。贾山亦积极上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言多激切,善指事意。晁错为景帝时的政治呕心沥血,甚至奉献出宝贵的生命……
当时,儒士们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迫切希望在新政权结构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政治作用。这实是汉初儒士对自身价值、责任与政治权力的充分自觉,也是他们积极发扬儒家用世进取的有为精神的重要体现。故王子今先生认为:“少年为吏,是汉代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特殊现象。”[4]这些少年有为者中显然包括许多真才实学的儒士,少好学、博学,是他们能胜任吏职的条件和入仕的直接原因。他们因其特殊的资质,对汉代政治发挥过特殊的作用。儒士们认为:“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新语·思务》),“质美者以通为贵,才良者以显为能”(《新语·资质》)。他们认为自命清高、隐身不仕实不可取。“杀身以避难,则非计也;怀道而避世,则不忠也。”(《新语·慎微》)儒士们极力称颂入世进取,他们批评出世之儒士“犹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忖度天地,用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视之无优游之容,听之无仁义之辞……当世不蒙其功,后代不见其才,君倾而不扶,国范而不持,寂寞而无邻……非谓怀道者也”(《新语·慎微》)。汉初儒士之言典型地显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连一些长久不仕之儒士亦积极用世进取,为汉帝国政治贡献才智。
西汉初年,对秦亡原因的思考成为社会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汉初儒士们承先秦百家争鸣的余绪,思想言论非常活跃。他们积极著书立说,批判秦政,形成一股强大的“过秦”思潮。当时,“人人争言秦汉间事”,探讨秦二世而亡之教训,总结古今成败之规律。各家学派之士相互论难,掀起了汉初的百家争鸣。这场“过秦”思潮以儒士陆贾、贾谊、贾山为代表。陆贾对于秦政的批判,着眼于秦统一天下后不“行仁义,法先王”。他建议汉高祖行“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治国之策。贾谊批评秦政“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不施仁义,使“天下苦秦”。他总结出“攻守异势”、“取守异术”等治国方针,并向文帝提出了“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汉书·贾谊传》)的治国措施。贾山以秦为喻言治乱之道,批判秦王朝赋剑重,虎狼心,不笃仁义,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遂向文帝提出仁义治国之策。他们的积极活动,极大地否定了秦朝的法家统治,使汉初统治者加深了对秦亡教训的认识,并废除了挟书律、妖言令、诽谤妖言罪等禁锢士人思想的法令。
然而,相对于法家而言,儒家在政治上可谓运途多舛。儒士们虽积极用世,但他们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儒士们的政治遭际是极为艰难的。汉初是军功集团政治,军功受益阶层“少文多质”。布衣将相集团阻碍了儒士们的思想话语对政治的渗透,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前途。在汉初,统治者实行的是君无为而臣有为政策,使臣下与君主、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日益尖锐。由于黄老政治本身的缺陷和不足给政治带来了消极后果,当权者逐渐发现思想文化的有用价值,开始有意识地启用儒生,希望儒生能以文化的力量对汉初政治进行改造,以加大文化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整合,为汉初政治提供一套长治久安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在此情形之下,汉初儒士凭借极大的政治热情赢得了对汉初政治用世的话语权力。
显然,汉帝国统冶者的政治取向,并非出于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汉初儒士抱着积极的用世进取之心而大量鼓吹,儒士们才得以参与政事,以其文化和政治理念对现实政治进行积极的规范和干预。无疑,汉初儒士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践履,对西汉政治从汉初以法家之术与无为之治为核心向中期以儒家之治为核心的成功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话语不等于言语,亦并非泛指语言实践或个人表述方式。相反,它是指语言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群体表现形式。”[1](P31)因而话语是没有单个作者的,它是一种隐匿在人们意识之下,却又暗中支配各个群体不同的言语、思想、行为方式的潜在逻辑。西方学者福柯曾说过:“个人不可能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说明一切。”处在汉初大一统社会之中,儒士们越来越深感自己与先秦先辈们的身份和地位大不相同。承秦之制的汉初政权,仍以法家之治为其核心。士人与君主的关系怎样,他们内心仍然不得而知。儒士们已意识到专制政治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和不适之感,从道与从势成为汉初儒士面临的重大选择。但是,汉初儒士明白,“守道者谓之士”(《新书·道术》),坚持“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贱而好德者尊,贫而有义者荣”(《新语·本行》)。他们虽被纳入了大一统政治的国家体制,但仍然承先秦之遗风,不愿以牺牲自己的思想言论、丧失人格尊严而委身从势,沦为帝国的附庸。他们认为儒家士人的规范品格,乃是志于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秉承先秦儒士的精神传统,汉初儒士仍如先秦儒士投入私门那样直言极谏,言词激切,抨击时政,指斥君主之过失。
儒士们首先认识到秦的暴政导致秦二世而亡。为了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和其自身理想价值的实现,汉初儒士极力劝谏汉初统治者审视秦王朝的统治政策,顺应时代要求。他们批评秦政缺乏‘仁义’之道义原则,缺乏足以摄万民之心的礼乐教化,缺乏约束君主、纠矫失误的规谏机制。他们对秦政的批判,都立足于汉代政治现实,其政治批判的目标是秦政与法治。由于“汉承秦制”,其“批判锋芒也就同时直指汉之承秦的那些方面”[5](P324),所以汉初儒士批判秦政,目的在于改革汉政。他们著书立说,上言进谏,都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理想与价值,为汉政提供新的指导原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初儒士以道自任的价值心态与传统精神并未改变。他们依“从道不从君”的原则,积极对社会各阶层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利益,作出合乎“仁义”的分配,以勾画出大一统封建帝国的政治理论体系,实现儒士们向往的理想盛世。然而,文化视野限制了汉初军功集团对古圣先贤政治理论的正确认识。这就给汉初儒士们实施其治平理想带来了很大困难。汉初儒士们对天下为一的政治的热切期盼和呼唤换来的却是汉代帝国政治对儒士的巨大压力。儒士们的美好愿望和理想被无情的政治深拒。他们深感大一统皇权专制的压力,自我选择的政治自由和思想言论自由的丧失。
但是,儒士们是思想文化的载体,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群体,他们具有超越的品格,坚持理想的价值和理念,坚守独立的节操和人格。他们不愿成为帝国的工具性角色。虽然他们进入了大一统政治体制,但他们对秦的严刑峻法深有感触,对汉承秦制亦有看法,他们怀着深切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情,在大一统专制的压迫下挣扎。儒士们深感“得失之道,权要在主”(《淮南鸿烈·主术训》)。无情的事实使他们逐渐清醒,他们想象出一种话语策略,以制衡无上的君主权威。儒士陆贾构建的灾异论,认为天道对有德者示以祥瑞,对暴君则降以灾异予以遣告。他创建的天人关系把天和人联系起来,国家成为天道的派生物,由天命决定兴亡,君主权力受天道制约。因此他的天人感应论和天降灾异论的建构,就是为了把儒家仁义观纳入官僚政体作为合理内涵,并对君道加以限制,给君主套上一个紧箍咒,使君主不能滥用权力,以实现士权与君权的合理化,为儒士们在专制王朝中实施治平理想创造条件。这也反映出他们直道而行、不愿委身从势的现实心态。其天人感应论和天降灾异论还被后来的儒士发扬光大,成为制衡君主的重要工具。
汉初儒士目睹了秦帝国政治大厦倒塌的无情事实。他们非常清楚:帝王之位可变无常,“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新书·修语》)。故古代传统的天命无常、唯德是辅的思想在儒士们心中萦绕。尽管他们的道义原则不如先秦之时,但许多饱学之士仍然具有传统儒家的气节和理想。他们认为守持道义、勇于直谏是儒士的立身之本。“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新语·辨惑》)汉初儒士明白:他们在大一统专制之下的治平理想和治国措施很难像先秦诸侯王时那样被积极采用。但“士志于道”成为君子儒的情怀仍在他们心中激荡。他们认为儒士“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的士节士风仍应保持。故在“道”与“势”的对立中,汉初儒士乃是考虑道的尊严,“壹其道而定其操”(《新语·思务》)。他们认为应“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故“忠臣之事君也……所以蒙死而竭知也”(《汉书·贾邹枚路传》)。儒士们言论的劝谏并不避君主的权威,死谏已成为当时儒士们的价值判断标准,以理抗势,冒死进谏之儒士大有其人。贾生数上书,好直谏,忠而被谤。辕固敢于在窦太后问《老子》书时说,“此是家人言耳”(《史记·儒林列传》)。甚至连“大滑头”儒士叔孙通在高祖欲易太子时,亦“愿伏诛以颈血汗地”(《读通鉴论》卷2),表示强烈反对,而并非一阿谀之徒。
汉初社会经历了从战乱到统一的政治变局,儒士们虽早已接受了君主集权统治的政治模式,自己也成为文士与官僚相结合的士大夫,但他们仍是思想文化和道义良心的保持者和维护者,是直道而行、实现自身理想与价值、改造帝国政治的有为之臣和直谏之士。正是儒士们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践履,激励了汉初士风健康向上的势头,张扬了儒学的献身精神。尽管汉初政治制度还处在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进程之中,承秦之制的法治传统仍需不断改造,但儒士们的理性反思和政治介入仍为新的大一统专制集权的发展和完善贡献了力量。同时,儒士们“毕竟在暴秦文化灭绝的余烬中重新拨亮了道义与士权的点点星火,这点点星火将在随后的日子里为汉代士人的文化仕途和心路历程指明道义的方向”[6](P86)。
三
经过秦的焚书和秦末之乱,汉兴,《诗》、《书》等儒家经典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破坏,散佚很多。经典文本的严重缺失,学术基础的薄弱使汉初学术精神普遍萎弱,儒士们面临着其阶层文化的全面陵替。汉初儒士认为:儒术之兴是社会的需要。恢复和发展儒学,既是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又是他们进入政治体制后的理想和价值的重要体现。为了构建服务于汉代统治的意识形态,恢复因秦火中断的“绝学”,儒士们对暴秦“焚诗书,坑儒士”作了大肆渲染。他们希望新建的汉政权能够重视儒士,重新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儒士们为了在汉初变异儒学、复兴儒学,推动经学思潮可谓不遗余力。
首先,汉初儒士们深刻反醒了他们在秦的不遇之遭,以前的教训给了他们深刻的启迪。于是,一方面,他们作出了改造儒学,促使儒学变异的努力,以使儒学能够更加适应宗法血缘家族伦理和大一统专制政治的需要。其实,汉初儒士早已意识到:孔子创建儒学,是处在王纲解体、礼崩乐坏的春秋战乱时代。孔子是希望为当时社会提供一套尊卑有序、群体和谐的社会政治理论和伦理道德学说,以使天下安定,社会有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其仁政王道乃是为分封制服务的。儒学作为一种思想,它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汉初,儒士们面对的是大一统专制的君主政治,他们的政治构想能否实现完全在于君主的权威。他们深知:儒学在先秦不被诸侯王采纳,“凄清冷冷若丧家之犬”,主要在于其思想“迂阔而远于事情”。要使儒学得以复兴,就要站在汉初统治者的立场上,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符合时代的要求和统治者的需要。汉初儒士在汉王朝废除秦以法一统、禁绝百家的专制思想,并“大收篇籍”时,纷纷著书立说,传播儒学,同时又不断吸纳各家学说精华,改变了儒学只重仁义德治的局面,使儒学形成了融合百家之长的新儒学。汉初的“三贾”(陆贾、贾谊、贾山)都立足于当时政治的现实,站在儒士阶层的立场上,以仁义为本,对先秦原始儒学和儒家思想作出了诸多调整和发展。陆贾为儒学增添了天人感应论及其黄老思想的内容,贾谊给儒学注入了德法并用思想,把道德与功利从原始儒学所认为的对立之中解脱了出来。汉初几十年间,儒士们“皆崇王道,黜霸术”,并对黄老之学实行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罢黜”。他们不断地对儒家经典进行初充和完善。儒士们认为,应把“先王之道”和现实的政治相结合,“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特别是汉初儒家学者几乎自觉地把儒学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积极地为大一统帝国吸纳儒学摇旗呐喊。他们有着与时俱进的现实主义精神。如果说叔孙通以这种现实的态度为汉王朝制定了一整套礼仪制度,那么三贾则企图从更高的层次上为汉帝国建构一个理论体系。这不仅开启了汉代儒学顺应时事、容纳百家的先河,而且为后来董仲舒的阴阳灾异论与德法并用的儒家政治学说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固然,儒家思想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乃在于其本身适应自然经济特色的农耕文明和以宗法血缘家族为基础的等级结构。但是,如果没有经过战国秦汉之际的巨大嬗变,没有汉初儒士对儒学的不断调整和发展,儒家之学还是很难迅速地与汉初封建大一统专制制度“亲密结合”的。所以,汉代儒学的很快复兴,与汉初思想界的弃法从儒、变异儒术分不开。如果儒学不与汉初的现实政治相结合,为巩固新政权服务,并为当权派所接纳,儒学在汉初的复兴并非易事。
另一方面,汉初儒士在促进儒学变异之同时,也积极推动汉初统治者对古圣先贤文化知识的认识,对汉王朝吸纳儒家思想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主张,这对促进儒学和经学思潮的兴起起了重要作用。汉初儒士明白:刘邦是在马上取天下的,汉初政权的建立者多是军功之人,“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汉书·文帝纪》),无文化教养的粗鄙是其特质。对于“一个缺乏充分的文化素养,清晰的历史意识的执政集团,不可能单由其自身来主动地完成对社会政治粗简、疏陋的改善和转变”[7](P44)。文化视野限制了汉初统治者对古圣先王政治理论的认识,需要具有深厚教育涵养的儒士的文化理性对政治的渗透,才能使汉初统治者认识到治国之术离不开《诗》、《书》之道。所以在汉帝国建立不久,汉初儒士就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积极推动汉初统治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儒士陆贾向刘邦进言:“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汉书·陆贾传》)叔孙通“知当世之要务”,当汉初军功阶层在朝廷上饮酒狂欢,拔剑击柱而使刘邦颇为厌烦时,他适时提出了“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得到刘邦的赏识。虽有“鄙儒”批评他“所为不合古”,对其人格不予肯定。其实,他的行为实为顺应汉初“轻狂”的时代风气的权宜之计,他在适时应变中并未完全放弃士人倡导的道义和良知。应该说,叔孙通对刘邦的说服和诱导对汉初统治者认识和接受儒术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不拘泥于古制成法,才促进了儒学在汉廷的发展,并使儒家在西汉政权中有了一席之地。因而,太史公赞曰:“叔孙通希世度制礼,进退与时变化,率为汉家儒宗。”(《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其后,为促进儒学变异和复兴的儒士可谓层出不穷。辕固、韩生推《诗》之意而解之,“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汉书·艺文志》)。伏生得《尚书》二十九篇教张生及欧阳生后,“《尚书》滋多于是也”(《史记·儒林列传》)。《礼》自孔子时其经不具,而高堂生之后,《礼》篇数日多……同时,推动统治者认识儒学的汉儒也不断涌现。他们的思想或学说也受到了汉初帝王的重视。所以,正是汉初儒士们的不懈努力,不仅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体系,扩大了儒学的影响,而且也促进了儒学与现实政治,特别是与官方权力的结合。正是几代儒士的不懈努力才使汉初统治者逐渐改变了轻视儒生和儒术的看法。史载,高祖于公元前196年发出了求贤诏,并亲自祭祀孔庙,开帝王祭孔之先河。高祖晚年还写了一篇《手敕太子》文,对其不重传统文化作了深刻反省。高祖之后的孝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皆置博士”(《孟子正义》卷首)。景帝时还始立《诗》、《书》、《春秋》的经学博士。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意识,也始自汉初。这都表明汉初统治者吸纳儒学和儒士的积极态度。由此可见,是儒士们促进了儒学的变异,才使儒学发展成为适应汉代社会的新儒学。是儒士们推动了统治者吸纳儒学,才使儒学逐渐得以登上汉代的政治舞台。
总之,在汉初社会积极进取的“锐气”之中,儒士们对新兴的汉政权充满了信心,他们以负载天下的雄心大志和昂扬进取的姿态、积极主动的用世进取精神,效力于大一统的汉政权,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直道而行,为实现自身的理想与价值,为汉政权的长治久安献计献策,为促进儒学的变异与复兴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在汉初儒士们的共同努力下,到武帝时,儒学已居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儒家文化也成为汉代独占鳌头的官方统治思想,并发展为延续二千多年的我国思想文化的主流。
收稿日期:2002-09-11
标签:政治论文; 儒家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