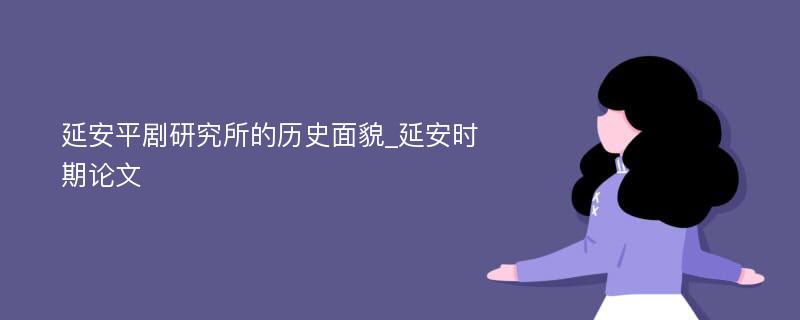
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历史面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面目论文,研究院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10月10日是延安平剧研究院正式成立六十周年。我借此机会写一篇文章,修正近 年来我所见到的一些报、刊和书上的许多文章中关于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叙述失实之处。 目的是为了尊重历史,恢复延安平剧院本来的历史面目。
(甲)关于延安平剧院的前身
1942年4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平剧团与八路军120 师战斗平剧社合并,组建延安平剧研究院(简称延安平剧院)。同年10月10日举行成立大 会(当时报纸报道“开学典礼”,是不确切的),宣布正式成立。只有鲁艺平剧团与战斗 平剧社而没有任何其他平剧团是延安平剧院的前身。往上追溯,鲁艺平剧团的前身是鲁 艺旧剧研究班。再上追溯,成立于1938年、解散于1940年的话剧、京剧、曲艺都演的实 验剧团是延安平剧院最早的前身。
一、许多文章,包括《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和《中国京剧史》等史书都说延 安平剧研究院是由延安鲁艺平剧团、延安业余平剧团、120师战斗平剧社和胶东平剧团 联合组建的。这个说法严重失实。①当时,在延安确实有很少数单位的京剧业余爱好者 建立了业余组织,但从来没有过一个统一的“延安业余平剧团”。曾有“延安业余剧团 ”,那是排演话剧的,与平(京)剧无关。②胶东平剧团远在山东,从来没有到过延安, 怎么联合组建呢?!
二、还有许多文章,包括原在延安平剧院工作的同志写的文章都写“鲁艺平剧研究团 ”(我自己也曾这样写过),这是不符合史实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在1940年4月5日发出“ 鲁字第七号”公告:“为集中旧剧人才,从事旧剧之研究改革工作,本院决定成立平剧 团(先从平剧着手)。”该团正式名称鲁艺平剧团。“研究”二字是原该团负责人后来加 上去的。原该团其他人员也都跟着加,于是该团名称就被篡改了。应当恢复正式名称。
三、有的文章写“120师平剧社”,有的文章写“贺龙领导的战斗平剧社”,都是不符 史实的。①该剧社名称是“战斗平剧社”而不是“120师平剧社”。全称就是“120师政 治部战斗平剧社”,一般省略“政治部”三字,是容许的,但省略“战斗”二字,是不 容许的。②写出“战斗平剧社”,可是不写“120师”而写“贺龙领导的”,这是不行 的。贺龙当时是120师师长,不是平剧社社长,他不直接领导平剧社。
(乙)关于延安平剧院的上级领导、组织机构和负责人
一、《延安平剧研究院组织规程》(下简称“组织规程”)的“三”写明“本院设正副 院长各一人,综揽全院一切事宜。”组建之初宜受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首任正副院长 由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康生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洁兼任。正式成立之后,改受陕甘宁晋 绥联防司令部领导,正副院长改由联防司令部参谋长张经武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任 柯仲平兼任。1944年划归中央党校领导,由该校教务主任刘芝明兼任院长(副院长缺)。 末任正副院长是专职,由杨绍萱、罗合如分任。最后几个月重归中央办公厅领导,正副 院长不变。有的文章中说阿甲“继任副院长”;《舞台深处——阿甲传》说:“后…… 由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刘芝明兼任院长,杨绍萱任副院长;直到1947年将要下山的时期 ,由罗合如、阿甲担任正副院长。”这些说法都不符史实。在延安平剧院,杨绍萱没有 担任过副院长,罗合如没有担任正院长,阿甲也没有担任过副院长。罗合如和阿甲是在 延安平剧院下山之后转到晋察冀边区,改组为华北平剧院,担任该院正副院长的。
二、《组织规程》的“四”和“五”写明“院长之下设院务委员会,院务委员七人至 十一人,由院长委任之”;“院委会在院长之下辅助院长,领导执行全院一切工作”。 被委任为院务委员的是(以姓氏笔划为序):卜三、王一达、王镇武、石畅、刘国桢、任 桂林、阿甲、李纶、张一然、罗合如、薛恩厚。有的文章说院务委员有牛树新、陈冲( 另一文章没有说有陈冲)、赵容美;而没有卜三、石畅(另一文章说有石畅)、刘国桢。 这是不符史实的。陈冲参加革命前是“票友”,本来是鲁艺平剧团的创始人和负责人, 任该团指导科科长,又是艺术骨干,兼任鼓师、教员和导演。论其经历与水平,不低于 任何一个被委任院务委员的同志,但他早从该团调出改了行。1944年归队来院,只任专 职研究员,未被委任院务委员。赵容美和牛树新二人参加革命以前是“内行”;在战斗 平剧社和延安平剧院都是主要演员、教员和导演;在本院剧场(演出团)扩大时曾分任( 演职员)大队下属两个分队队长,下乡巡回演出的特殊短时期曾分任院直属两个大队之 一的正副队长。他二人是艺术骨干兼重要干部,但不是院务委员。
三、《组织规程》的“六”写明“院务委员中由院长委任一人为主任委员,任期半年 ,执行院委会一切决议及院长指示诸事宜。”有文章说任桂林被委任为主任委员,不符 史实。事实并没有委任任何人为主任委员。原先由院委会主委执行的任务改由《组织规 程》没有规定设的秘书长执行。罗合如、王镇武先后担任秘书长。
四、政治协理员一职在《组织规程》里没有规定要设;但事实从1943年审查干部工作 开始后上级委派了先与秘书长平行、后与专职正副院长平行的政治协理员。相继担任政 治协理员的是:朱云峰、慕生才、许世平、余平若、孙方山、刘继久。《延安平剧活动 史料集》中的“延安平剧研究院全体成员名单”没有写上刘继久,把余平若写成首任政 治协理员,都是不符史实的。
五、《组织规程》的“七”写明“院委会下设研究室、教务处、剧场、院务处四部门 ,并设一办公室。四个部门的负责人是:①研究室——阿甲、张一然分任正副主任;在 “抢救”运动中,阿甲被调出院外接受特别审查期间,由张一然顺理成章代理主任。有 的文章没有写张一然任副主任而只写他是研究员;又写李纶曾任研究室代主任,都不符 史实。②教务处——任桂林首任处长,他在半年之后辞职。王一达继任处长。上述“全 体成员名单”没有写教务处;另有人写的“平剧院的院委会下设以下机构”一段中写的 教务处只有王一达任处长,还有其他文章也这样写,都不符史实。③剧场(实为演出团) ——首任主任和副主任由石畅和薛恩厚分任。一年之后,石畅辞职,王镇武继任主 任。他后来升任秘书长,薛恩厚改任主任。最后一任主任是魏静生。上述“全体成员名 单”写的剧场主任只有薛恩厚、魏静生;另有文章写的只有薛恩厚一人,都不符史实。 ④院务处——刘国桢任处长。《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和《中国京剧史》写“… …计划设立研究室、剧场、教学三部”,把教务处写成“教学”;还没有写院务处,都 不符史实。
六、当时,延安平剧院没有实行党委领导制,党组织只起监督保证作用。初期,全院 只设一个党支部,首任支部书记是孙震。中期,在扩大了的剧场(演出团)增设分支部, 简朴任分支部书记。后期,院支部升格为总支部,首任总支书记是孙方山(首任副书记 、第二任书记是魏晨旭)。有一篇文章说李纶曾任首任院党总支书记,不符史实。李纶 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就被派往山东开展工作去了,在那时之前,平剧院根本没有党总支 部。
(丙)关于本院创作和排演的现代戏
本院创作并排演的现代戏有:《上天堂》(张一然编剧,王一达导演并与任均、齐秀林 主演)、《难民曲》(李纶编剧,张一然导演并主演,王一达艺术加工),以上是京剧。 《回头是岸》(张梦庚、萧甲编剧,王一达导演并与任均主演)、《边区自卫军》(魏晨 旭编剧,王一达导演,张一然领衔主演)、《甩炸弹》(李纶编剧,王一达导演,霍秉龄 、沈玉琳主演)、《张学娃过年》(张一然编剧并导演,张梦庚、任均主演),以上四剧 是唱眉户调的陕北秧歌戏。《醒后》(张一然编剧,牛树新导演并与任均主演),此剧以 河北梆子演出。此外还演出了非本院创作的陕北秧歌剧《张丕谟锄奸》和《刘二起家》 (分别由魏静生和赵魁英导演并主演)。
一、有一篇文章说:“延安平(京)剧院十年间,阿甲编创演出了《松花江》等一批现 代戏。”这个说法严重失实。①延安平剧院只有五年的历史,哪里来的“十年间”?② 延安曾“编创演出了”《松花江上》(不是《松花江》),那是在1938年鲁迅艺术学院为 纪念抗战一周年而“编创演出”的。编创者是鲁艺戏剧系教员、剧作家王震之。该戏是 以鲁艺为主,联合抗大、陕公等校少数人员参加演出的,并不是延安平剧院“编创演出 ”,编创者也不是阿甲(他参加了此剧的演出,扮演剧中男主角)。③延安平剧院也确实 “编创演出了”上面所写的“一批现代戏”,那是在1943年秋至1944年春,从“抢救” 运动中期到平剧院下乡巡回演出归来的半年多短时期(个别剧目演出得更久一些)。恰恰 在那个短时期,阿甲因历史问题而被调出院外受特别审查(并非如那篇文章所说“运动 一开始阿甲就被抓去了”,更与关于平剧改革问题的争论毫无关系。)那“一批现代戏 ”的“编创演出”,阿甲根本没有参加。④那篇文章没有说到的,我做一补充:阿甲在 1939年曾创作并领衔主演(从前曾说是他编导,不对。实际是集体导演)一出京剧现代戏 《钱守常》。当时我和任均、任桂林、石天、罗合如等参加了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 那是鲁艺为纪念“9·18”八周年而演出的,不是在延安平剧院创作的。我之所以要作 这补充,是为说明,阿甲虽然在平剧院没有创作剧本,但决不等于他在延安没有创作剧 本。
二、《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中“10月10日”关于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的记载有失实之 处:把《松花江上》(错记为《松花江》)、《松林恨》、《钱守常》、《刘家村》、《 赵家镇》、《夜袭飞机场》(错记为《夜袭》)等现代戏记为延安平剧院“最初演出的平 剧”。事实上这些戏是1938年至1939年鲁艺及其所属实验剧团和旧剧研究班演出的。
三、《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第四部分“延安时期的戏剧演出剧目”中“1944 年首演剧目列入了《难民曲》和《上天堂》,写成这年”一月间延安平剧院演出“,不 符史实。此两剧是1943年冬首演的。同期还演出的《张丕谟锄奸》和《刘二起家》没有列入。1944年1月间首演的《边区自卫军》,错记为《参加自卫军》是眉户戏,不是京 剧。编剧、导演的姓名漏记。这年创作并演出的眉户戏《甩炸弹》和《张学娃过年》以 及河北梆子《醒后》,都没有列入,不符史实。
(丁)关于延安平剧院创作和演出的新编历史剧(包括历史故事剧)和改编的传统戏
一、本院创作并排演的新编历史剧,除《三打祝家庄》外,有:《嵩山星火》(张一然 编剧并领衔主演,牛树新等集体导演);《瓦岗山》(孙震编剧,赵容美导演并与简朴主 演);《河伯娶妇》(魏静生编剧并领衔主演,王一达导演,方华等联合主演);《武松 》后部(王一达编剧,牛树新、王洪宝导演并领衔主演);《大名府》(任桂林编剧,魏 静生导演并主演);《中山狼》(杨绍萱编剧,王洪宝导演并领衔主演,赵容美、齐冀民 联合主演)(此剧排成,但因决定离开延安,当时没有演出。后转到晋察冀边区,改称华 北平剧院后演出了)。
二、本院创作但没有排演的新编历史剧有:《江油关》(卜三编剧);《渡阴平》(卜三 编剧);《秦桧》(李纶编剧);《武松》前部,后改名《武大之死》(王一达编剧);《 红娘子》(石天编剧);《丹梁桥》(张一然编剧)。后三剧在1948年以后由陕甘宁晋绥联 防军区、后为西北军区所属平剧院排出首演。
三、本院排演非本院创作的新编历史剧,除《逼上梁山》外,还有《岳飞》(田汉编剧 ,王一达导演,张一然领衔主演。)
四、本院演出正式改编的传统戏很少,只有:《赤壁鏖兵》后部(王一达、石畅改编并 导演,阿甲、张一然、任桂林领衔主演,石畅、赵容美、王一达联合主演);《青风亭 》(魏静生、王一达改编、导演并主演);《清风山》(王一达改编,王洪宝导演并主演) 。此外,还演出了在原鲁艺平剧团时期创作并演出的《玉堂春》前部(石畅改编,王一 达导演,任均、简朴领衔主演,张梦庚、周聘雪联合主演)。
五、上述那篇文章还说:“延安平(京)剧院十年间,阿甲……编创、改编了《瓦岗山 》、《宋江》等一批新编历史剧。”这个说法也严重失实。①《瓦岗山》的编创者是孙 震,不是阿甲。②《宋江》的改编者是阿甲、李纶、石畅三人,不是阿甲一人。此剧是 在原鲁艺平剧团时期改编并演出的,延安平剧院组建后没有演过。③延安平剧院“编创 、改编了”的“一批新编历史剧”,各有其编创者和改编者,都不是阿甲“编创、改编 ”的。
六、上述《纪盛》还有一处失实:把“王一达、邓泽、石天合编的《北京四十天》” 与“任桂林、李纶、魏晨旭合编的《三打祝家庄》”并列为延安平剧院演出的“影响大 的”剧目,延安市(原延安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平剧研究院旧址”的碑记也是 这样记的。事实上《北京四十天》是1949年初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后为西北军区平剧 院)创作并首演的新编历史剧。
七、《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中“一九四七年首演剧目”写了“《红娘子》(新 编京剧)、石天、任桂林编剧,王一达导演,二月间延安平剧院演出”,不符史实。此 剧是一九四八年秋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平剧院首演的剧目,编剧只有石天,没有任桂 林,王一达任总导演,刘元彤、殷元和执行导演。
(戊)关于《逼上梁山》的创作、演出及其领导
《逼上梁山》是中央党校教职学员中的京剧业余爱好者们(他们的业余活动组织名为“ 大众艺术研究社)创作并首演的。主要编剧是杨绍萱,原排导演是齐燕铭,领衔主演是 金紫光和王连瑛。此剧剧作和演出的领导者是该校教务主任刘芝明,负责具体组织事务 工作的是该校俱乐部。此剧在1943年12月开始公演,取得巨大成功。毛泽东同志在1944 年1月第二次观看此剧的演出后,亲笔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一封回信,给予很高的评 价。主要的评语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 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 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划时期的开端。”
延安平剧院改归中央党校领导后,复排并演出了《逼上梁山》。复排导演是王一达, 领衔主演是薛恩厚和赵容美。(在本院演出中曾扮演林冲的还有从中央党校调来的金紫 光以及本院的霍秉龄、齐秀林。)平剧院的演出,在保证它的高度思想性的前提下,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它的艺术性。
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只说《逼上梁山》是延安时期创作演出的,不 说是中央党校京剧业余爱好者们创作演出的,也不说杨绍萱是主要编剧,齐燕铭是原排 导演,更不说是刘芝明领导了此剧的创作和演出。“四人帮”竟敢把毛泽东同志写给杨 绍萱、齐燕铭的信篡改成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这不是一般的“失实”,而是他们出于 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歪曲历史、篡改历史。为了彻底消除其恶劣影响,不能不在这里 旧话重提。②最近为纪念延安平剧院成立六十周年,中国京剧院赶排演出《逼上梁山》 。在说明书上也写的是“该剧创演于延安时期”,节目主持人也说是延安平剧院创作的 。我作为当年延安平剧院主要成员之一,在对中国京剧院现任领导和工作人员尽心尽力 主办这一系列纪念活动而深表感谢的同时,作为曾是中国京剧院负责人之一,对说明书 所写和主持人所说的失实而深感愧疚。这一事实充分说明“四人帮”的恶劣影响至今没 有消除,在这里旧话重提是十分必要的。③在一本舞台设计图的集子(忘其名称)里的《 逼上梁山》设计图下写的导演,不是原排导演齐燕铭而是复排导演王一达,这也是失实 。④在上述那同一篇文章中还说阿甲“重点领导了《逼上梁山》……的编、创、修和演 出工作”。这又是严重失实。中央党校刘芝明同志领导该校京剧业余爱好者们“编、创 、修和演出”的《逼上梁山》与阿甲毫无关系。延安平剧院复排《逼上梁山》的演出, 也不是阿甲领导的。他在延安平剧院是研究室主任,根本不领导排练和演出工作。
(己)关于《三打祝家庄》的创作、演出及其领导
《三打祝家庄》是延安平剧院创作并演出的代表优秀剧目。剧本是集体创作,任桂林 、魏晨旭、李纶执笔。执行导演是王一达(执导“二打”和“三打”)和魏静生(执导“ 一打”),导演团成员还有:阿甲(助魏静生排练:《石秀探庄》中向钟离老人问路一场 )、任桂林(沟通协调剧作者与导演之间关于艺术处理的设想和构思)、赵容美、牛树新 、王洪宝(分别设计并排练各个武打场面)。领衔主演是张一然(饰宋江)、魏静生(饰石 秀)、王一达和王斌亭(饰乐和)。联合主演有牛树新、薛恩厚、赵魁英、王洪宝、阿甲 、赵容美、萧甲、任均等。(曾饰宋江的还有齐冀民)领导创作、演出的是延安平剧院兼 院长刘芝明。负责演出具体组织工作的是本院剧场(实为演出团而非演出场所)。此剧的 创作和演出也收到强烈效果,也取得巨大成功。执笔编剧之一任桂林在退还通过江青借 来毛泽东同志存书一百二十回《水浒传》时,写信给江青致谢并请她代问毛泽东同志看 戏后有何指示。她正住院治病,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信给任桂林,也给予很高评价。信中 主要评语是:“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 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信的开头写的是“你给江青的信和还来的书均 已收到。江青因病住在医院。”信的末尾写的是:“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导演、演 员、音乐工作、舞台工作同志们致谢。”
关于《三打祝家庄》的编剧、导演及其创作、演出的领导者的叙述,失实的乃至严重 失实的很多。除个别一般的失实之外,严重失实集中在把阿甲说成《三打祝家庄》的编 剧、导演和此剧创作、演出的领导者。
如今唯一健在的《三打祝家庄》剧本的执笔作者魏晨旭在他写于1996年3月5日的《关 于<三打祝家庄>著作权问题的有关情况》一文中第二部分“《三打祝家庄》剧作者著作 权长期遭受侵犯的严重情况”一节里有详细记载。我不一一抄录,只摘引如下:“《中 国地方戏曲集成·北京市卷》”和“《中国戏曲辞典》”两书中的“《三打祝家庄》条 ”都写的是“阿甲、任桂林等于1944年编剧”;“《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 ”和“《中国文学家辞典》”第二卷两书中的“阿甲条”分别写的是:“在延安时期, 阿甲即参加……《三打祝家庄》……编、导和演出”;“1942年成立了延安平剧研究院 ,……他参与编导演出的新编历史剧《三打祝家庄》,曾受到毛主席的称赞”。“阿甲 的《戏曲表演艺术规律再探》一书”的‘代序’和‘编后记’分别写的是:①“阿甲同 志导演和参加编写的历史故事剧很多,其中主要的有《三打祝家庄》”;②“阿甲曾参 加演出、编写和导演了《三打祝家庄》,还写”阿甲在延安平剧研究院领导和参加了… …《三打祝家庄》的修改和演出工作”。发表在《北京晚报》、《北京日报》、《中国 演员报》上的几篇文章中分别写的是:①全国解放前的延安时期,任桂林、阿甲创作了 《三打祝家庄》”;②说阿甲在延安“参与编导京剧《三打祝家庄》等戏”;③说阿甲 在延安平剧研究院“重点领导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的编创、修改和演出工 作”。《光明日报》发表的《阿甲同志逝世》的报道写的是阿甲“参与编导了《三打祝 家庄》”。
一、魏晨旭同志在指出上述那些叙述严重失实的文章和报道之后,关于把阿甲说成《 三打祝家庄》的编剧问题,作了明确表态。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 三条规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由合作作者共同享有。没有参加创作的 人,不能成为合作作者。”本文第二部分所列的侵权言论,都把没有参加创作的阿甲宣 布为《三打祝家庄》的作者,违犯了这一法律规定,侵犯了我们的《三打祝家庄》著作 权。而且这种侵权言论都以文字的形式发表在辞书和报刊上,变成了无法消灭的书面资 料,成了过去和今后人们了解谁是《三打祝家庄》的剧作者的一种“根据”,因而已经 、还会使人们接受这种伪造信息的欺骗而发生侵犯《三打祝家庄》著作权违法行为。” 如今唯一健在的合法享受著作权的《三打祝家庄》的执笔作者魏晨旭早就作了如此明确 的表态;我在此文中已清楚说明了《三打祝家庄》集体创作的执笔作者是任桂林、魏晨 旭、李纶。阿甲同志没有参与此剧的创作。关于此剧编剧的失实叙述,我就没有更多的 话要说了。
二、关于《三打祝家庄》导演的失实叙述,除上述引自魏晨旭文章那些说法之外,阿 甲本人在他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承认自己不是《三打祝家庄》作者的短文中说是他 “和魏静生排了此剧”(话基本如此,我不再查找);还有个别文章写《三打祝家庄》是 王一达一人“导演”,而不写是王一达、魏静生二人执行导演,这也都是失实的。关于 阿甲发表的那篇短文我曾与阿甲面谈,他解释他的本意是说他和魏静生排了“探庄问路 ”那一段戏,承认他写的短文说得不清楚。我相信他的解释;当时我也不想在报上公开 说明。我绝对不否定阿甲“参与导演了”《三打祝家庄》的说法。因为他是延安平剧院 排演此剧的导演团成员之一,而且他以导演团成员和剧中人钟离老人扮演者双重身分, 协助执行导演之一、扮演石秀的魏静生排了石秀向钟离老人探问盘陀路那一段戏。不过 ,我不能不否定阿甲“导演”了《三打祝家庄》的说法。因为他虽是导演成员之一,但 不是执行导演之一,他没有执导三“打”的任何一“打”乃至任何一场戏。这是历史事 实,我如果不这样表态,就是对历史不负责了。由于自己的导演艺术创作权任人侵犯, 也是对已故的魏静生同志和我本人不负责任。由于把不是他创作的导演艺术作品强加于他,更是对我一贯视为益友、甚至在戏曲理论研究上视为良师的阿甲同志在天之灵不负 责任。
(庚)关于延安平剧院的后身
一、延安平剧院在1947年3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离开延安,途经晋绥边区,转到晋察 冀边区,归属华北联合大学,改组为华北平剧研究院(简称华北平剧院)。延安平剧研究 院的历史至此结束。它的直接后身就是华北平剧院。
此后的沿革是:华北平剧院在1949年进入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文化部领 导下,以华北平剧院为主体,组成京剧研究院。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之后,京剧研究 院改组为该院下属的中国京剧团。1955年中国京剧团扩建为中国京剧院。由于华北平剧 院是延安平剧院的直接后身,从这沿革得出定论:中国京剧院是延安平剧院最后的后身 。
这沿革和由此得出这定论的权威文字根据是:
①中国京剧院首任院长梅兰芳大师为1959出版的《中国京剧院演出剧本集》第一集撰 写的“序”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中国京剧院的前身是1942年在延安成立的延 安平剧院。”接下去写:“延安平剧院在党和毛主席大力支持和深切关怀之下,对京剧 艺术改革工作,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在戏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国京剧院继承了 延安平剧院的光辉传统,并且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指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 改革方针。”
②自1990年12月20日至1991年1月12日,由文化部主办的“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振兴京剧 观摩研讨大会”《纪念册》中对中国京剧院的介绍的第一句话也是:“前身为延安平剧 研究院”。接着写的是:“1955年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所属中国京剧团的基础上扩建为中 国京剧院。”
③比较全面、比较清楚的是中国京剧院首任副院长(实际主持工作)兼党总支(后升格党 委)书记马少波同志发表在《戏曲艺术》1981年第四期上的《剧目建设问题杂记》一文 所说:“文化部远在1949年就以华北平剧院(前身为延安平剧院)为基础,吸收了大批名 演员,成立了京剧研究院;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后,原京剧研究院改编为中国京剧团; 1955年,中国京剧团又改编为中国京剧院。”
④写得最全面、最清楚的是在1995年出版的《中国京剧院建院四十周年纪念册》中的 “中国京剧院简介”。其第一段写的是:“中国京剧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直属的 国家级剧院。其最早的前身是1942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成立的延安平剧研究院。毛泽东 主席曾为该院题词‘推陈出新’,为戏曲事业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指导方针。后该院 几经变化改组,先是与华北军区六纵队前锋平剧团与冀南军区民主剧团合并,改称华北 平剧研究院;建国后改组为文化部戏曲改进局所属京剧研究院、中国戏曲研究院所属京 剧实验工作一、二、三团;后来于1953年三个团合并为中国京剧团。在此基础上,于19 55年1月成立了中国京剧院。”
以上抄录的四段“权威文字根据”,无论写明或没有写明,都在事实上认定了延安平 剧院是中国京剧院的前身,最后一段说是“最早的前身”我个人就曾这样说过,我认为 这是比只说“前身”更准确的说法,因为中国京剧院的直接前身是中国京剧团。说延安 平剧院是中国京剧院最早的前身和我在前面写的中国京剧院是延安平剧院最后的后身是 一致的。这两种说法是任何一种是失实吗?我认为不是失实;相反,是历史的真实,是 本来的历史面目。这是无庸置疑的,也是不容更改的。
二、把延安平剧院的后身说成它的本身的事也是有的,据我所知一位已故延安平剧院 老同志写的一篇《忆梅兰芳首次观看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内容是写1949年第一次全 国文代会期间华北平剧院在“开明戏院”(即民主剧场,后改为珠市口影院)演出,梅兰 芳来观看的情形。文章内容的前部分写了是华北平剧院演出,可是在文章的结尾时却说 :“……梅兰芳先生首次观看延安平剧院的演出……”,甚至竟然以此为文章的题目, 这是严重失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