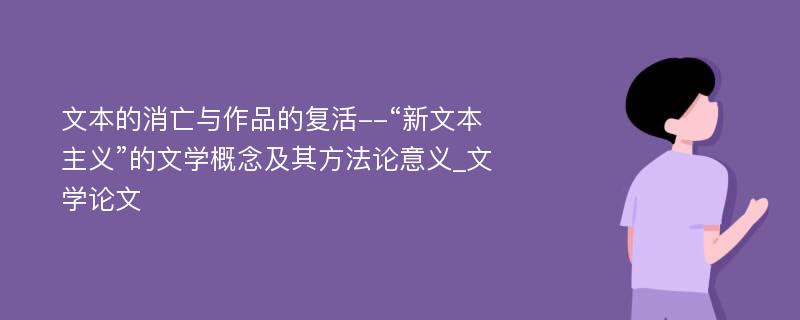
文本的死亡与作品的复活——“新文本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方法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观念论文,意义论文,主义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1年,罗兰·巴特在欧洲主流学术刊物《美学杂志》撰写题为《从作品到文本》(From Work to Text)一文,他列举七大理由申述文学研究将由“作品”走向“文本”的必然性①。然而,十余年后,西方主流文学界却以大致相同的面目作出了完全否定性的回答:“文本”不能代替“作品”,文学研究应由“文本”回归“作品”。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命名为“新文本主义”(New Textualism)的文学批评理论对罗兰·巴特的有力回应②。 什么是“新文本主义”?按照美国学者安妮·赫莉(Ann Hollinshead Hurley)的看法,就是指以文本的物理属性为理论研究基点,以文本的出版历史及传播状况为理论研究进路,通过追溯文本诞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与物质生产语境,挖掘潜藏于文本背后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的、性别的、文化的等因素对于文本意义的主导性建构作用,揭示文本存在形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认同文本之外的因素而非作者的意图为文本意义的源泉的一种文本与文学批评理论③。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话语,新文本主义并非空穴来风,而实有其方法论与现实基础。 一方面,盛行于20世纪上半叶文本编辑与文学批评领域的新文献学,直接质疑经典文本研究理论,从而为新文本主义理论的诞生提供了方法论基础。根据新文献学理论,经典的文本研究,无论是形式主义、阐释学,还是新批评抑或读者反应批评,都存在着致命的方法论局限,难以说明文本意义的真正来源,因而必须进行文学观念与方法的革命。首先,在文学批评视角上,要重视文本的物质存在属性,将文学批评的视角由“作者”(Author)转向“印刷者”(Printer)与“出版者”(Publisher)。其次,在文学批评内容上,在认可“作者”意图为文本意义来源的同时,要充分挖掘文本印刷风格、排版字迹、底稿誊录、开本设计、纸张质量、出版审查、标价折扣乃至供货渠道等各种非作者因素对文本意义的重新建构作用。第三,在文学批评宗旨上,要以吻合作者意图的文本为权威文本,通过追溯历代不同流传文本因文献讹误而导致的文本意义变迁,确定“讹本”与“正本”之不同,树立稳固的权威文本④。显然,相比于突出文本内在结构与符码意义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新文献学强调了文本外在因素对于文本意义的重要建构作用,打开了文本意义的多维认识视角,为文本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但对于一种想要彻底颠覆经典文本研究理论的新文本主义来说,它仍然显得过于保守,因为它无法在观念与逻辑两个层面为颠覆经典文本理论提供力量,无法在“作者意图”论主导下扩展文本阐释的全部力量。一种具有革命性的理论陈述,注定无法完全因袭过往的理论轨迹,它必须扎根于文本与文学现实,从文本与文学的历史深处,寻找观念的起点与话语的逻辑。这样,对文本编辑活动的历史考察就自然被推到理论铺展的前台。 新文本主义考察认为,虽然早期的文本批评,旨在确立文本的可信度,去伪存真,然而文本本身的历史却并不一劳永逸地限定其本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早期新圣经文本研究的权威主导与其时历史研究的长足发展,直接促成了其时文本研究观念的急剧变革。文本批评应铆准其编校功能,发挥其阐释力量,而非确保人们所阅读的东西为“真品”,是其时文本观念变革的主要表现。当专业出版机构面对多样的历史流传文本而真假莫辨时,文本批评学者接管其工作就有了更加合法的理由。文本批评接管文本的编校与阐释功能,意味着获得了一种文本研究方法与重建文本的力量,并在事实上成为后来库恩意义上的“规范科学”⑤。这种“规范科学”并不满足于确证一个信本或充当某一文本的技术性辑校,而是要提供一种更加普遍的方法论与更加可靠的观念逻辑,后者成了从事文学鉴赏、文学阐释、文学创作都必须凭藉的一种专业方法与观念基础⑥。 另一方面,20世纪中后期以来经由欧美文学界的文学自律性观念而催生的文学批评与文本研究的双重裂变,为新文本主义的诞生提供了直接的现实基础。自律性的文学观念认为,以文本辑校与文献考证为核心的传统文本研究,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外在式预备工作,不入文学研究之堂奥,文学研究理应将文本研究边缘化。传统文本研究在事实上的被边缘化产生了富有戏剧性的结果,如新文本主义的领军人物杰罗姆·麦加恩(Jerome McGann)不无揶揄地指出,传统文本研究的边缘化,一方面使得原本从事文本研究的学者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从而可以从事更加专业化与技术化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使原本从事文学批评的学者,再无义务去研修一种需要长期习练才能掌握的文本批评技能⑦。换句话说,自律性的文学观念演进使得原本从事文本研究的学者,只需戮力于精细的文本辨证,无须顾及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而原本倾心于文学批评的学者,则只需关注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无需深究文本本身的真伪。当文学的文本研究与批评研究发生分裂,而批评研究亦不愿意接管由文本研究让出的批评领地时,文本研究就只能另求它途。因为文学的现实已然是:文本研究应该适应20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自律性要求,文学批评不应该重返这门学科未成熟前的状态,亦即以哲学的、历史的、文献的分析为主导倾向的文学批评模式。这样,文学研究要在观念革新时仍是一个整体,文本研究要在时运不济时仍葆有价值,就不得不一方面进行再专业化的细分,另一方面进行观念革新;前一部分工作由专门文献研究来承担,后一部分工作则逐渐演变为新文本主义的批评理论。 当然,观念的流行,研究方法的使用,与理论的正式命名,常常并不同步。作为理论批评范畴的“新文本主义”一词,迟至1990年代才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两位学者、著名莎士比亚研究专家玛格丽特·格蕾西亚(Margreta de Grazia)与彼得·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在《莎士比亚文本的物质性》一文中正式命名⑧。在对莎士比亚系列剧本版本的比较研究中,两位学者发现,同一剧本的不同版本,因其编者不同,出版者不同,编排校印不同,装帧设计不同,竟可产生完全不同意涵的文本。这些不同意涵的文本,显然不是经典的文本理论,或结构主义式的文本理论,或形式主义、解释学的批评理论所能解释,因而有必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理论范式—“新文本主义”就此诞生。 新文本主义的核心概念“文本学”,亦称“文本批评”,“主要研究书写文本是如何最终形成的一门学问,并致力于探究如下两大问题:第一,研究作为物质产品的手稿或印刷文本,其形式要素对文本内容与意义会产生何种重要影响;第二,分析作为物质载体的文本,在经由作者、编者、印刷者、出版者合力成书或再成书过程中,新文本(印刷或在线虚拟)所展现的独特性与创造性”⑨。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的方法论,这当然不是新文本主义的独创,相反,它一直为多样的文学、历史、哲学研究所袭用。但新文本主义的重要不同在于,它将这种外在的文学研究“方法”提升为文学的内在“本体”,使文学作品的意义不再限于作者与文本中心——像传统本质主义与还原主义理论所秉持的那样,也不再取决于文本内在的结构要素——像罗兰·巴特等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所主张的那样,而是文本外在的物质要素与多样的生产传播要素,成为揭示文本内在意义的关键。 根据新文本主义,文学之“文本学”研究,应以文本的生产与演布为中心,而非以作者生活与作者意图为中心。新文本主义者为此提供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早期现代“著作权”概念的出现,实际上是通过文本序言、题词、注本、版式、装帧、设计、署名等一些带有鲜明性别、文化、阶级特征的文本内外因素所共同建构的结果,而非自然造就的。比如流传于19世纪至20世纪前期西方主流文学的权威文本与规范文本,就与其时盛行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密不可分;而那些经由编者再编辑的权威文本与规范文本,就无不打上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或性别主义的身份烙印⑩。新文本主义据此认为,在这种文本生产语境下,文本不再是一个由原初作者“意图”主导的固定文本,而是由众多生产者再编码的身份体认——后者通过文本语词使用、句式结构、主题意蕴、字体设计、版式装帧等文本内外形式与物质要素体现出来。新文本主义者为此经常举证的一个例子,就是著名的英国费伯出版公司在翻译出版非裔作家图途奥拉(Amos Totuola)的《棕榈酒醉鬼的故事》过程中,就将标题中原本带有黑人俚语色彩的“Drunkard”一词,修改为规范的标准英语语词“Drinkard”,以突出修订文本的身份与训导意义。再比如,几乎所有的现代编者在编辑英国诗人、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帖木儿大帝》时,都会将描述主人公的关键词语“snowy”修改为“sinewy”甚或“snowy-white”,以此突出主人公作为勇士与征服者的角色,并且巧妙地将主人公由原本的伊斯兰式典型形象,转变为像正统英国人一样拥有白色肤种的英雄(11)。所以,并非“作者”,而是“作者”、“编者”、“印刷者”、“传播者”,甚至“批评者”一起,共同构成了“著作权”主体。即使是单一“作者”因素,情况也相当复杂,因为“作者”实为复数——比如,作为文本构思写作的“作家”,作为文本编校纠错的“编者”,作为印刷出版的“出版者”等等——这众多的复数“作者”,其创作、生产与传播“意图”,也就必然表现为复数,必然表现为差异,必然难以做到内在同一。因为我们既无从知道这众多“作者”是否怀有明显的“意图”,也无从明晓他们是否始终坚持同样的“意图”,更无从断定其在共同“创作”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众多“意图”的内在同一。相反,我们所能知道的情况是:他们必然对原初文本进行外在形式的修改,必然对再生产文本进行表述意图的修改,必然对流传文本进行自我身份的修改。这种修改或出于读者阅读的期待视野,或出于文本编辑的责任要求,或出于政治环境的外在压力,或出于社会道德的一般规范,当然,也可能因作者自身写作意图的刻意转变。不管如何,动态文本应取代静态文本,封闭文本应让位开放文本,应是文本研究与文学阐释的观念前提。 正是基于这一前提,新文本主义突出了其理论研究的两大重心。 其一,文本研究始于文本形式介质而终于文学批评阐释(12)。相对客观化的文本研究与较为主观化的文学批评阐释之间,到底有无关联?强调外在形式技术的文本研究,如何施用于注重内在精神意蕴的文学批评阐释当中?前现代经典的他律性文本研究范式,如何在今天的自律性文学批评阐释活动当中博得一席之地?这三个问题共同构成了新文本主义关于文本形式介质与文学批评阐释思考的着眼点。文本总要以某种介质来承载,总要以某种外在形式来表现,无论是早期的甲骨、铭文、石刻、帛书、纸草、羊皮抄本,还是现代的印刷书籍、电子版本或在线文本,此乃常识。然而新文本主义的重要不同在于其认为,文本介质与形式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文本内容与意义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文本阐释范式的变化,会间接影响到社会与文化的历史性变迁。“当作者、出版者、印刷者选择特定的印刷材料以完成文本付梓时,它就同时进入一种特殊的社会、性别、政治与文化的复合语境,进一步造就一种特殊的文学权力。”(13)“由作者所创作的纯文本,只是一种独白式的作品,而经由出版者、印刷者等加工的文本,则成了对话体的作品(Dialogic Publishing),后者会直接影响乃至改变文本意义的生成。”(14)因此,不仅文本的内形式,如序言、献诗、题词、评校、旁注、疏证、插图等,具有文本意义的建构作用,而且文本的外形式,如编者、资助人、出版社、出版地、印刷排版、装帧设计、页面风格、卷册目次、图书分类等,也都会与文本内容相互作用而直接影响到文本意义的表达。 新文本主义认为,文学作品的阐释必然要以文本研究为基础,因为后者是唯一能够阐明关于文学作品生产者、传播者及传播媒介等复杂网络活动的载体;文本研究必然会影响到文学作品意义的变化,因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必然要生发于文本内外多重话语的交互建构。但倘若文本研究对文学阐释具有显著影响,那么文本阐释就先须超越文本编辑的史料校雠与历史钩沉而进入到观念史层面的逻辑反思。因为当文学作品的阐释依赖于固定的解释工具与文本批评程序,它就极易流于作品内容的简单甄别而掩盖了解释与批评活动本身的意义生成。一部手稿,一本作品,其意义并不限于语词系统的简单概念叠加,而是文本不同的形式结构系统与文本的语词系统的互文性意义生发。比如,信息时代为人们所广泛使用的电子文本,就是将不同的文本形式与介质,如视频、影音、图像、文字等融为一体,产生一种互文性的关联文本,这种关联文本由于链接地址的经常性变化,会迫使读者对文本自身进行同步的升级,由此产生同一文本的不同文本形式。这样,印刷时代单一文本形式的本体地位,就被颠覆为多样文本形式的互为本体性。按照新文本主义,这多样文本形式本体所昭示的,乃是文本背后巨大的文学与文化变迁(15)。由此也意味着,文学阐释虽然必以文本形式介质为基础,但它必须预设对文本历史变迁的理解,因为惟有如此才能拓展文学意义的阐释空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文本主义代表人物杰罗姆·麦加恩才反复申言:文本研究并不旨在追求文本校勘或讹误修正之技术层面的考辨,也不在于对文本中蕴含的事件及其真实有效性作出裁判,而是首先以阐明文本当下生发的意义为鹄的,通过征引文本变迁的历史史料,追问当下文本“意味着什么”,而非“何者为对,何者为错”的简单择一判断(16)。 其二,文学研究应从“文本”走向“作品”(17)。新文本主义认为,“作品”,并非如现象学与解释性所标举的那样,是一个纯粹的精神存在,而实为一个由物质与非物质文本要素组成的“混杂”(Hybrid)存在体;“文本”,也并非如形式主义与结构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内在的、自律的、具有自我指涉与自我生产功能的精神性存在,而实有其迁衍功能。因而必须把“文本”还原为“作品”本身,才能完整揭示文本的意义。设若“文本”仅为非物质的精神存在,其意义就难免局限于文本内部的语言及句法结构游戏,就难以因其文本环境的变迁而发生意义的扩展。设若“文本”实为物质与非物质的“作品”存在,其意义就会滋生于物质与非物质的内外张力,而文本的意义,将会在历时化的生存语境、多样性的阅读视角、多媒介的文本载体与多重身份的“作者”之间自由游戏。以多重身份的“作者”对文本自律性的颠覆为例,新文本主义理论的另外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查克瑞·莱辛(Zachary Lesser)通过对莎士比亚剧作出版史的研究揭示出,那种今天被人们普遍视为文本当然组成部分的“序言”,在16世纪至17世纪实由“出版者”而非作为“作者”的“作家”加入(18)。这种加入的“序言”文字既起着书籍商业广告的作用,同时又是对书籍内容的专业性介绍,此外还是职业性的文学批评——职业性的文学批评在早期竟然由出版社作出,并与文本内容自然融为一体,而非独立的文学批评实践。实际上,正是通过更改文本“标题”、插入匿名“序言”,加入“致谢”文字等一系列的文本再生产实践,“出版者”才取代“作家”而完成了“文本”向“作品”延展的一系列再创造。在这一过程中,“出版者”不仅基于自我商业利益而创造,亦要根据当时的社会惯习、文化取向、政治导向以及自我的审美喜好而完成文本的再创造。由此也意味着,“文本”不再是一个纯粹自律性的精神存在体,而是一个由多重物质与非物质要素合力而成的混杂“作品”存在体。 事实上,由“文本”走向“作品”也是新文本主义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结果。如查克瑞·莱辛所言,“文本只限于文献内传递信息,然而文献之非文本特质,却自有其符号学重量”(19)。新文本主义对“文本”形式要素的突出强调,将不可避免地涨破“文本”自身的边界而使“文本”的“非文本特质”——形式的、介质的、文化的、政治的等等“作品”因素——得以凸显,因为后者关联于文本背后的编者、印刷者、出版者、批评者等多重创造性主体,并使自身径直等同于“作品”。而“作品”不仅存在于商业化的物质网络中,更存在于广泛的权力网络中,系缚于“出版政治”的隐秘圈套——出版者总是力图通过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择偶而实现对读者的想象性操控,总是希图读者能够如其所愿地对作品作出“恰如其分”的理解,总是企图通过自身的政治背景、文化偏向、审美取向、价值导向影响并决定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偏向。这样的“隐秘圈套”最终将指向作为“读者”的我们,从而使任何阅读都打上“阅读政治”的烙印,使任何“文本”都成为“作品”的附庸。以中国经典文本《阿凡提借锅》为例,中国的官方出版者将其编入小学语文课本,与美国专业性出版者将其编入《中国民间故事》(Chinese Folk Tales),竟然生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阅读效果,产生两种不同的“作品”意涵:一为“聪慧”,一为“狡诈”。前者基于中国当代集体性官方文化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普遍性仇视,后者基于美国当代文化的个体性人格内涵,即无论何人何时何事,撒谎欺骗都代表了“恶”的人格内涵。可见,由“文本”走向“作品”的新文本主义研究,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外在式社会学、历史学探究,而是文学作品的内在批评本身。 若将新文本主义理论视为一种内在式的作品批评,那么,其方法论的明晰是必要的。 新文本主义舍弃结构主义式的纯文本分析努力,抵制文本非物质因素对文本意义的侵占,重新还原文本的原初生发语境,突出文本物质性因素对于文本意义的重新建构,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论原则:(1)在文本形式与内容不协调时,形式优先;(2)当文本观念与文本历史相冲突时,历史优先;(3)在作者意图与读者意图相背离时,读者意图优先;(4)在出版目的与传播目的相乖讹时,传播目的优先;(5)当原始版本与衍变版本不一致时,新近版本优先。 基于如上原则,新文本主义学者杰罗姆·麦加恩提出了新文本批评的一般方法论程序:首先,找出批评文本的主题、主旨,并运用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确定“文本的原始要素”。其次,找出文本对应的语境及其表现特征,划定文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次级要素”。最后,将第一个步骤所得要素进行范畴的分类,组成范畴系列;再将该范畴系列放入第二个步骤所得进行回归分析,解析其具体含义,厘定“文本批评的最直接要素”(20)。根据新文本主义,只有进入第三步骤的分析,文本的真正含义与隐含意义才会渐次明晰。具体来讲: 第一步骤:确定“文本的原始要素”,包括: (1)作者 (2)其他参与文本生产进程的人物或群体(比如合作者、编者、抄写员等) (3)原始文本不同的生产阶段或时期(各阶段相关参与要素明确的功用、目的、特征等) (4)原始文本生产进程中的材料、手段、模式(比如物理的、心理的、意识形态的等) 显然,第一步骤中这种类似于培根式的早期理性主义哲学分析模式在文本分析领域的移用,只是文本分析的预备工作,目的也只是获得文本批评的基本素材。 第二步骤:确定“文本生产与再生产的次级要素”,分为两类: (1)作者生前作品的再生产阶段诸要素 (2)作者身后作品的再生产阶段诸要素 如上两类均可涵括第一步骤中的全部或部分原始要素序列,从而便于使第一步骤所含的原始要素语境化。按照新文本主义,原始要素只有进入具体的生发语境,其意义才能确定。因为语境的不同,即可导致意义的不同;由此衍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文本关联要素分析重点的变化。比如,要分析“作者”,经典的文本批评秉持“知人论世”的分析方法,企图通过追索“作者”的出身背景、教育经历、社会环境、人生遭际、价值观念等要素来还原作者创作的真实意图,并以作者意图确定文本意图。而若将“作者”置入第二步骤划定的语境,那么,分析的重点将是“作者”的具体“再生产”过程,而非稳固的“作者”本人。换句话说,通过分析“作者”在不同读者、不同阶级、不同群体、不同机构、不同意识形态中所呈现的观念序列,使著作权意义上的“作者”退离文本分析的中心,而第一序列中所枚举的“其他参与文本生产进程的人物或群体”,则成为文本分析的新中心。同理,对“作品”的分析,第二步骤的语境化分析,也会使那种一贯戮力于作品形式与内容的经典文本分析,移易为对作品的“再生产”如何影响作品本身意义的分析。这种语境化的回归分析,当然并不止于单纯的技术策略,它还具有观念革新意义:“历史的某种模式,在文本中以一种完整文学化的形式得以表达;而对这些形式的批评性分析,则反过来引导我们透过纷繁复杂的人类现象及社会历史模型洞察出人类文学活动的真义。”(21) 第三步骤:确定“文本批评的最直接要素”。这主要指批评活动本身所包含的一些技术性要素,它常以某一类型的批评面目来呈现,表现为对文本文献、编辑、词汇、评论等不同要素的专业性具体分析,特别是针对“文本语词形式变化”与“文本语境内涵变化”(22)。 首先,当通过文本批评来揭示文本语词的变化时,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说明不同文本的不同语境会生发不同的涵义,而毋宁是要说明作品自身包含的意义冲突、张力。比如,一直被英语世界广泛誉为是继托马斯·艾略特之后最重要的英语诗人奥登(W.H.Auden)的作品《1939年9月1日》,首次发表于《新共和国》杂志。但由于诗人对这个诗篇并不满意,故而在1949年收入《奥登诗选》时,诗人删除了原诗的第二诗节,甚至后来诗人直接禁止这首诗的出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由爱德华·门德尔森(Edward Mendelson)所编选的《奥登诗集》,就删略了这个诗篇(23)。新文本主义学者举证这个例子意在说明,何以当我们阅读一部作品的任何一个语词文本时,其他语词文本也必须同样诗意地在场,否则其意义就会含混难现。再比如当代美国著名诗人玛丽安·穆尔(Marianne Moore)的代表作《诗》(Poetry),最初发表时为30行诗,此后在1935年与1951年出版的《玛丽安·穆尔诗选》中,这个规模的诗篇得以延续。然而,到了1967年出版的《玛丽安·穆尔诗歌全集》中,原初的诗歌被作者本人删减到只剩3行(24)。今天,这个只有3行规模的诗歌文本已被欧美学界认为是权威版本,尽管仍有30行版本的流传。举证这个例子,当然不只是说明不同文本体现不同意义,而是要表明缺乏对该作品其余文本的阅读将会妨碍我们对该文本意义的理解:我们阅读玛丽安·穆尔诗歌文本的活动,实际就是要求两个文本的亲密邂逅与意义生发,因为作为“读者”的我们,并不单纯是文本意义的释读者,而毋宁同时就是文本意义的建构者,是文本内在意义向外延伸的执行者;而作为文本创造主体的“作者”,也不在于要表达一种明显的写作“意图”,它毋宁是要创造一种文本的张力——在这种张力中,文本的多元意义生发才有可能。 第二,在文本语词分析的基础上,文本批评就可以通过分析不同的文本语境,比如大的历史语境(时代、社会、文化、政治等),与小的文本语境(不同编选收录文本之装帧、设计、排版、目次、序列等不同形式要素组合,与不同流传衍变文本之“注”、“疏”、“注疏”、“集注”、“汇校”、“注译”等不同内容要素融合),彰显不同文本隐含的非同寻常意义,揭示源文本与流传文本的辩证关系。根据新文本主义,同一文本,编入不同的文本语境,便会滋生不同的文本意义,产生不同的阅读感受。比如,我们将李白的《蜀道难》编入《李白诗选》,就与编入《唐诗选编》或《历代山水诗选编》,具有不同的意义:前者倾向于表现诗歌自身的审美特质,关注的是诗歌自身的审美意象;后者则进入唐代诗歌或历代山水诗歌的整体历史语境中,表现诗歌自身的意义张力。又如,将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收入《中国古典文论选编》,与收入《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前者突出的是中国古典文论独有的白描式批评风格,后者则构成了中国美学心路历程的重要一环。虽然同一文本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意义影响,常会由于读者无意地忽略而难以凸显,但它却无法根本泯除,而仍将以特殊的面貌与意义适时呈现。虽然同一文本的流传史与接受史,可能会由于某种历史的因缘际会而发生重叠,但却无法同一,它仍将依循效果历史的辩证结构交错前行。文本批评的第三步就是要阐明并解释这一事实,为进一步的文学批评奠定基础。 如果说半个世纪前经由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所发起的“从作品到文本”革命,是想从根本上颠覆文学的主流话语秩序与价值体系,树立单纯文本的权威;那么,今天由新文本主义所践行的“从文本到作品”的再革命,则是力图在传统话语秩序与文学价值体系内,对文学文本阐释的多样性与意义的建构性之再寻绎。不同的文学表现介质不会影响到我们对文学价值的悟解,不同的文学存有空间不会影响到我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这是千余年来几乎所有中西方经典文学理论所肯断的结论。这一毫无疑问的“定论”,成了新文本主义理论革命的对象。 而较之于罗兰·巴特等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所标举的文本观,新文本主义带来了五大文学观念的重要变革:一是在文学本体问题上,文学“作品”取代文学“文本”而再次成为新的文学本体;二是在文学创作活动上,作品的“编辑”“出版”等外在形式活动取代“作者”与文本内在“语言”而成为新的文学意义源泉;三是在文学阐释空间上,文本意义的封闭空间被延拓为作品空间与释读视域的无限融合,文本独立的语言系统与形式结构被移易为作品多维语境的跨时空关联;四是在文学批评标准上,文本外在的形式与情境要素取代文本内在的话语与结构系统而成为新的文学评判尺度;五是在文学存在形态上,作品单一的物质或精神存在属性被升级置换为多重媒介的互文性共生,文学的存在形态由此在不同媒介载体之间交织穿行。 回过头来看,那场流行于四十余年前欧美先锋理论家群体中暴风骤雨式的“文本”革命,今天已冷却为理性的深刻反思。但“文本”的光辉依然四射,它依旧是文学话语分析的利器。“作品”作为“文本”革命之前曾经的文学话语重心,今天所面临的难题,并不是如何完全走出“文本”话语的阴霾,而是如何克服传统的研究范式而实现自身的再革命。这就要求我们重回文学思想的源头,重拾那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古老命题:当我们谈论作品时,这意味着什么?当“文本”放大为“作品”时,它向我们敞开了什么? 而新文本主义循文本与文献为问涂门径,虽苦学精究于文本之外在形式与历史,却并不泥于部次甲乙、取便稽检之簿录工夫,而是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究文学之大道。因而不同于语文学(Philology)或文献学(Bibliography)意义上的文本主义——后者作为经典的文学研究方法,20世纪之前一直以发现最佳文本(best text)为嚆矢,而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原始文本,却不在其视野之内(25);虽然20世纪中后期以来形势陡转——学者们反思文学现代性的观念而坚持文本编辑的一致性与责任感,试图在文献文本与辅助性的历史材料之间作出明确区分,最大限度地还原文本的原初面貌——但力图寻找一个权威版本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并未改变;今日新文本主义所要做的,并不是揭示原始文本的原初风貌与原始意义,而是探究后世编辑者与阐释者在建构多样流传文本时,其活动本身所具有与所赋予的意义。世易时移,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知晓古希腊某一文本的原初语词与确切意义,正如我们永远无法明晓那一时期人们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样。原始文本的原初词语模糊了,原初意义失落了,但它会被新的语词所代替,会被新的意义所填充。因为文学本为人类活动之一种,人类活动的丰富性决定了文学文本内容与意义的丰富性;因为文学本是某种“存而不在”的话语敞开,不管是早期口口相传的话语吟述,还是后来多种媒介载体的有形叙事,抑或今天虚拟数字的符号刻录,只有当我们试图阅读、领会、理解、解释、传播时,文学之门才会豁然敞开。 而本文也更倾向于认为,由新文献学所启发并重新阐扬的新文本主义理论,虽萌生于文学自律性观念,但其有效性却基于开放的文学结构,因而不仅适应于对作为自律性的文学学科诞生之前,而且更适合对今日文学因媒介革命而复又走向“大文学”学科时代的文本分析。当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弥散一体,抑或当文学学科的发展必须打破学科壁垒以求得长足的发展时,“新文本主义”就有了用武之地。 ①Roland Barthes,The Rustle of Language,Translated by Richard Howard,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Inc.,1986,pp.56-64. ②作为文本研究与文学批评方法论意义上的“新文本主义”,不同于西方“后现代之后”思想理论界广为使用的“新文本”(New Textualities)概念。后者作为一种反映理论趋向的宏观描述,以反思“后现代”理论为起点,以价值与意义重建为鹄的,表现为“数字人文主义”、“传记写作研究”、“宗教转向”等系列“后理论”观念话语。关于“新文本”的基本理论旨趣与大致文献誊录,请参看:Global Literary Theory:An Anthology,Edited by Richard J.Lan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3,pp.721-859. ③Women Editing/Editing Women:Early Modern Women Writers and the New Textualism,Edited by Ann Hollinshead Hurley and Chanita Goodblatt,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2009,pp.xi-xii. ④关于新文献学的相关理论陈述,请参看:Arber,E.(ed),A Transcript of the Registers of the Company of Stationers of London,1554-1640,5 vols.(London,1875-94; rept,Gloucester,MA,1967); A.W.Pollard,Records of the English Bible:The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Bible in English,1525-161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1);W.W.Greg,A List of English Plays Written before 1643 and Printed before 1700,(M.S.G.Haskell House Publishers1902); R.B.Mckerrow,A Dictionary of Printers and Booksellers in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and of Foreign Printers of English Books,1557-1640(London:Printed for the Bibliographical Society,1910). ⑤⑦(16)(20)(21)(22)Jerome McGann,ed.,Textual Criticism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p.185,p.181,p.66,pp.191-193,p.193,p.194. ⑥“文本批评”与“文学批评”二者侧重点不同:前者以文本编校为导向,专注于文本语词及编校内容变化的历史;后者以相对稳定的文本为客体,讨论更加普遍的文学基本问题。前者讨论不同文本的变化产生什么样的文学后果;后者确立“好的文学”与“坏的文学”的界限并作出实际的评判。 ⑧参见Margreta de Grazia,Peter Stallybrass."The Materiality of the Shakespearean Text",Shakespearean Quarterly(44)1993:pp.255-83; 亦参见,Alan B.Farmer,"Shakespearean and the New Textualism",Shakespearean International Yearbook 2(2002),pp.158-179. ⑨⑩(11)(12)(25)Leah S.Marcus,Textual Scholarship,in David G.Nicholls,ed.,Introduction to Scholarship in Moder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2007,p.145,p.153,p.152,p.154,p.147. (13)Wendy Wall,The Imprint of Gender:Authorship and Publication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p.3. (14)Zachary Lesser,"Introduction-From Text to Book",in Zachary Lesser,Renaissance Drama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ation:Reading in the English Book Tra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25. (15)如Joseph Loewenstein揭示了文本中斜体字所承载的观念意识形态,David Scott Kastan分析了文学形式与文本格式的隐秘关联,Random Cloud阐述了剧本中语速与称谓对情节移位的重要作用,Leah Marcus讨论同一文本不同物质介体变化对文本表意及阅读的不同影响。参见Joseph Loewenstein,Idem:Italics and the Genetics of Authorship,Journal of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1990,pp.205-224),; David Scott Kastan,Little Foxes,in John Foxe and His World,eds.Christopher Highley and John King(Burlington:Ashgate,2001,pp.117-131); Random Cloud,The very names of the Persons:Editing and the Invention of Dramatick Character,in Staging the Renaissance:Reinterpretations of Elizbethan and Jacobean Drama,eds.David Scott Kastan and Peter Stallybrass(New York:Routledge,1991,pp.88-96); Leah Marcus,Unediting the Renaissance:Shakespeare,Marlowe,Milton(New York:Routledge,1996). (17)(18)(19)Zachary Lesser,"Introduction-From Text to Book",in Zachary Lesser,Renaissance Drama and the Politics of Publication:Reading in the English Book Trad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p.2,p.17. (23)Edward Mendelson,ed.,The Complete Works of W.H.Aude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24)Marianne Moore,Collected Poems,Macmillan Company,1951; Marianne Moore,The Complete Poems of Marianne Moore,Penguin Group Incorporated,1967.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本分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分析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自然语言处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