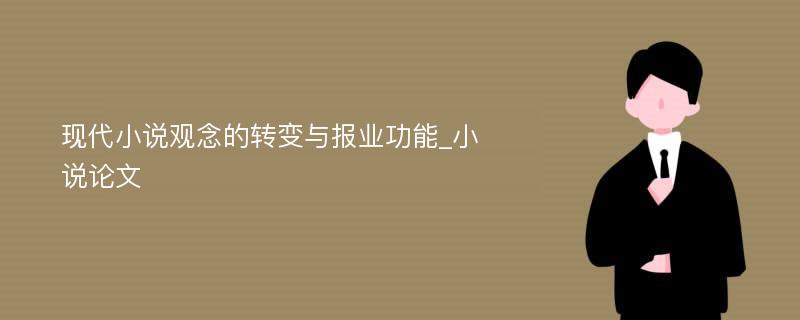
近代小说观念的转化与报刊业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报刊论文,观念论文,作用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清末民初的小说界和小说理论界与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密切结合的现象,是我国小说史上前所未有的。在笔者统计的92位近代小说理论家中〔1〕,有78人和报刊有着紧密的关系, 占这一时期小说理论家总数的84%。这些人一方面从事着报刊的编辑、出版等工作,另一方面又进行着小说的创作、翻译和小说理论的阐释、宣传。在报刊的周围,形成了特征明显、观点纷呈的小说理论家群体。大致说来,从戊戌维新前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因报刊杂志创办宗旨的相异和报刊杂志的发展而形成了近代四个不同类型的小说理论家群体:
第一类小说理论家群体大体上由政治家、思想家构成。由于这一群体的小说理论家各有各自的政治主见,手头也拥有不少的报刊,因而,这一由政治家、思想家构成的群体又可分为两个小群体。第一个小群体大致结合在以梁启超为核心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特别是早期的《新小说》杂志周围。除梁启超外,这些小说理论家还包括康有为、蔡奋、狄葆贤、麦孟华、麦仲华、韩文举、罗普、曼殊、浴血生、侠人、于定一等人。早期的严复、夏曾佑等人的小说思想也同梁启超等人的思想遥相呼应。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章太炎、陈去病、刘师培、黄小配、黄伯耀、陈范、张肇桐、叶小凤、高旭、何海鸣、马君武等人也创办或参与报刊的工作,发表小说主张,形成了第二个小说理论家群体。
这一类的小说理论家大多为政治家和思想家,多数人出过国门,都有“努力造世界,此责舍我谁”〔2 〕的救世精神和深沉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尽相同,甚至为此而产生过论战与对抗,但他们都是政治小说的热心提倡者,都主张小说发挥开启民智、改良群治、作宣传工具的社会作用,因而,其小说理论往往也局限在对小说社会作用的论述与强调上,把小说当作其宣传政治思想的利器,有相对忽视小说艺术特征与审美价值的倾向。
第二类小说理论家以《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及《新新小说》等杂志为结合部,相对集中了吴趼人、李伯元、欧阳钜源、连梦青、周桂笙、彭俞、王濬卿、侠民、陈景韩等人。
这一类的小说理论家群体不是政治家与思想家,提不出改革社会政治与改良小说的方案,但他们受时代风气的感染和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创作了大量暴露社会、官场黑暗腐朽的社会小说(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这些人从封建的营垒中游离出来,没有什么功名,也没有什么地位与财富,他们的职业大多为报刊的编、撰人员,靠编辑杂志和创作、出卖小说作品而生存。作为报人,他们刻意罗列时人感兴趣的官界、商界、学界、妓界等“话柄”,用各种商业手段促成报刊的畅销。在小说理论的阐释中,他们也吸收了部分西方小说理论观点,但更多的是对梁启超等人理论的发挥,对传统小说观念也颇多留恋,没有什么大的理论建树。第三类小说理论家群体相对汇集于《小说林》杂志的周围,以黄人、徐念慈、曾朴等人为代表。他们基本上反对将小说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是强调小说作为艺术的审美独立性,对梁启超等人的新小说理论以及谴责小说的弊端多有指摘,开始借鉴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来研究、构建近代意义上的小说理论。1904年,在《教育世界》杂志上发表《〈红楼梦〉评论》的王国维以及周作人大致也有着相近的小说理论。
第四类小说理论家群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鸳鸯蝴蝶派”。他们拥有众多的报刊,队伍最为庞大,包天笑、徐枕亚、吴双热、姚民哀、王钝根、许指严、李定夷、周瘦鹃、陆士谔等人都是其主力队员。这一类小说理论家群体生活在近代都市之中,基本上没有传统的功名,完全以写小说与编辑报刊、书籍来维持生活。他们传统的文化意识比较淡薄,政治热情不高,有些人还接受了一些西式教育,掌握了一至二门外语。他们生活在日益商业化的大都市里,其小说创作往往以经济利益为动力,以迎合市民需要为前提,有大规模制作小说的能力。因此,这一群体的小说理论家提不出有理论深度与新意的小说理论,相反,他们的小说观点大体上集中在对小说的娱乐性、消谴性功能的再三强调上,借“小儿女闲话之资”达到“警世觉民”〔3〕的效果, 将古代小说劝惩传统与小说世俗化、人情化发展趋向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都市派言情、社会之类小说,小说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又滑进了传统小说观念的旧道中。
我国近代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研究繁盛局面的形成,报刊业所起的作用是决不能低估的。这不仅表现在近代绝大多数的小说作品,不管是翻译小说,还是创作小说,亦或是小说理论思想的阐扬,几乎首先都在报刊上出现,而且更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创办报刊、编发小说的宗旨不同,对小说社会作用和本质特征认识的不同,才促成了我国近代小说理论家群体的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近代众多不同的小说理论家群体的存在,就没有近代众多纷繁博杂、精采纷呈的小说理论的繁盛局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近代小说理论格局的形成,正是源自于这些群体的不同的小说思想观念。
二
近代小说理论家既编辑出版报刊,同时又基本上亲自撰写、翻译小说,在主要是自己编辑的报刊上发表,这不仅使得他们因为报刊的关系而形成不同的理论家群体,而且也使得他们整个的思想和小说观念都发生了变化。
对于将小说用来开启开智、改良群治的政治家、思想家来说,他们创作小说、翻译小说,创办小说刊物,对小说的社会作用进行理论宣扬、阐释,着意提高小说的文学、社会地位,这对于国人轻视小说的传统观念,无疑是具有巨大冲击力与破坏力的。小说与小说家遭受歧视的不正常现象经梁启超等人的努力,得到了根本性的纠正。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新小说》杂志。此后,以小说命名或刊登小说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4〕。由于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宣传和亲自创作、 翻译小说,小说与小说家在社会上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5〕的新观念也深入人心。
近代以前的中国小说家是无法完全依靠出卖自己的创作小说来谋生的。传统小说虽然先天就具有商业化的品性,但古代小说家并不能据此而生存。但是,这种情况到了近代却发生了变化,近代小说家办报纸,编杂志,写小说,译小说,从事小说理论研究,其中不少人已作为职业作家的形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与传统的士大夫文人不同,他们基本上拒绝了官场、功名的诱惑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小说创作、小说研究与报刊的编辑出版中去。“这与以前的小说家形成一个对比。以前的作者中很少有人写过一部以上的小说。他们常在晚年动笔,提炼个人的生活经验,目的在于娱乐或启发读者。晚清小说家一般以编辑和写作为生,因此,他们经常同时创作几部连载小说。”〔6〕吴趼人“不治功令文”, “不治经生家言”,认为它是“愚黔首者”,他拒绝功名,大力创作小说,“先是湘乡曾慕陶侍郎饫耳君名,疏荐君经济,辟应特科,知交咸就君称幸。君夷然不屑曰:‘与物亡竞,将焉用是?吾生有涯,姑舍之以图自适。’遂不就征。”〔7〕李伯元也拒绝了曾侍郎的推举, “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辞不赴,……自是肆力于小说,而以开智谲谏为宗旨。”〔8〕林纾则更是自豪地宣扬:“幸自少至老,不曾为官, 自谓无益于民国,而亦未尝有害。屏居穷巷,日以卖文为生。”〔9〕
小说创作、翻译与编辑报刊成为职业,所带来的变化是小说家不再仰人鼻息,受人供养,寄人篱下。他们靠小说的稿酬、出售报刊的利润而立足于世。生活上自立了,人格上也独立了。人格独立,心灵自由,思想解放,创作与研究时的许多顾忌也就被抛弃掉了,他们开始从对封建统治者与其统治的依附与赞誉,走向了对他们的疏远与批判。这巨大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和近代作家、理论家手里有报刊作为谋生手段大有关系。
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士大夫独占的贵族文化。文化只在士大夫范围里流传,手抄、雕板或木活字、铜活字排版,手工印刷,在数量上和速度上都严重限制了文化的广泛传播。而且,传统文化以古代经典文献的形式流传于世,其内容主要是对经典文献和伦理道德的阐释、宣扬,它不仅限制了叙事类俗文学的发展,而且也使得书面语言与生活语言发生分离,文化成为知识阶层也即是士大夫的独占品。对文化的独占在士大夫阶层也成为主观上的一种自觉行为,表现出鲜明的贵族意识。
但是,这种贵族文化意识在近代却遇到了最致命的打击。报刊业的兴起与繁荣,促使不同群体类型的小说理论家都不得不面对广大民众,将能否符合民众的口味与习性作为刊物生存的条件。所以,贵族文化的范畴被突破,文学的发展走向与重心也发生了转变。
在近代,报刊与小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报刊登载小说的原因除开启民智的动机外,其主要的打算却在于利用小说来吸引读者,扩大报刊的发行量,获取更多的利润;而报刊之对于小说,也同样促成了小说创作的繁荣,促成了职业文人的最终出现。近代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进入了民众的消费领域,作为报刊的编辑、出版人员,近代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也无时不在关注着报纸、杂志的销路,密切注视着刊物同大众口味的贴进,及时、灵活地调整小说创作的步伐和和小说理论宣传、阐释的口径。近代小说家与小说理论家在利用报刊开启民智、传播思想或注重娱乐、讲究消遣的同时,也无时不在思索着小说素材的选取,注重挖掘、表现的事实是否能够吸引读者,这也同样影响着近代小说理论的发展走向。甲午战争的失利,国人救国热情高涨,痛恨腐朽没落的政府,“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10〕小说家们不失时机地创作了大量暴露政府、抨击官场的谴责小说,以迎合政治热情高涨的广大读者的需要。近代小说理论家们也第一次完全摆脱了古代小说理论家“羽翼经史”〔11〕的恭谦卑微心理,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力图用新的小说思想、观点来总结、阐释和指导小说的创作与变革。于是,“群知小说之效果捷于演说报章,不视为谴情之具,而视为开通民气之津梁,涵养民德之要素”〔12〕,小说观念因此为之陡然一变。
三
促成近代小说理论家思想观念发生转化的因素当然很多,但对于报刊业在其转化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还可以作更进一步的研究。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近代小说理论特色的形成和理论格局的构成,报刊业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戊戌维新前后的小说理论家群体多由政治家、思想家构成,他们办报刊,目的在于开启民智,为政治变革服务,小说报刊的创办,也是他们开启民智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1902年,《新小说》杂志诞生,其宣言便是“专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厉其爱国精神。”〔13〕那么,为“发表政见,商榷国计”〔14〕,给读者讲道理,用来比较、说理的论辨体当然是最好、最捷径的办法。事实上,近代早期小说创作中普遍存在着作者的议论,甚至连翻译的外国小说,也被许多译者加进了自己的声音。在小说作品中发表作者借题发挥的议论,成了近代小说创作、小说翻译的普遍做法,以至成为一种风气。即使时人批评这种小说“议论多而事实少,不合小说体裁,文人学士鄙之夷之”〔15〕、指责“我国志士”在“改革之初”,“皆以小说为社会之药石”,“议论多而事实少”,但这并不能改变议论化倾向的漫延。
这种小说创作中议论化倾向的出现,同报刊的作用有绝大的关系。戊戌维新时期,政论报刊崛起,以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时务报》为代表的政论报刊,既不同于当时以阐扬教义、劝人信教的宗教报刊,也不同于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业报刊,而是以政论为报刊的统帅与灵魂,政论成功则报刊兴,政论失去光芒则报刊亡。《时务报》前期大放光芒完全归功于梁启超政论文章的魅力,“《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16〕当时罗振玉称赞梁启超的政论文章“议论精审”,说他的文章使“草野为之歆动”。汪恩至则更是吹捧道:“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当为之蹶然奋兴,横涕集慨而不能自禁。”〔17〕《时务报》的广行,使梁启超声名大噪:“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8〕从此,政论成为报刊的灵魂,并为后来者所继承发展,成为近代报刊业的一个很大的传统。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陆续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进行他的启蒙思想宣传,他的政治思想和政论文体得到进一步的发扬,也显得更为成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于梁启超恣肆汪洋、震聋发聩的政论,黄遵宪称赞道:“《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日《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 无过于此者矣。 ”〔19〕
报纸政论的成功,政论报刊的巨大影响,使梁启超也用此手段来创办《新小说》杂志,用写政论文章的手段来创作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兹编(按指《新中国未来记》)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20〕在具体写作上,“拿着一个问题,引着一条直线,驳来驳去,彼此往复到四十四次,合成一万六千余言,文章能事,至是而极。”〔21〕这样的小说创作,“以大段议论羼入叙事之中”,〔22〕令人不忍卒读。书商也抱怨这种“新小说”“于小说体裁多不合也”〔23〕。究其原因,就在于梁启超等人是在用办政论报刊的方法在办小说刊物,在用写政论文章的思路在创作小说。
梁启超在评价《新中国未来记》时写道:“此编今初成两三回,一覆读之,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梁继续告诉读者说:“余欲著此书,五年于兹矣,顾卒不能成一字。况年来身兼数役,日无寸暇,更安能以余力及此。……计每月为此书属稿者,不过两三日,虽复殚虑,岂能完善。故结构之必凌乱,发言之常矛盾,自知其决不能免也。”〔24〕梁启超这种“与寻常说部稍殊”的创作小说的方法与态度,同样也受到了他创办《时务报》等报刊经验的影响。《时务报》中的不少文章牵强附会,繁芜驳杂,既反映了作者写作态度的轻率,也反映了作者认识的肤浅。为此,梁曾作过自我解剖:“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末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儿不免。”〔25〕造成这样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有“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俟后起者之发挥光大”之,“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26〕只要打开局面,言论传世,无须认真。另一方面则与作者对报刊文章的认识有关:“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27〕梁启超创办报刊目的是开民智,进行维新宣传,而他创办《新小说》杂志,也是维新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宣扬维新、开启民智的文章是为了“觉世”的,而非“传世”,因此尽可以不必认真。写小说是为了开民智,作者思想通过议论在小说中表达清楚了,那么,写作小说的目的也就可以完成了。至于小说艺术本身与小说理论的总结,那是次要的事情。梁启超的办刊经历与对报刊文章的认识,对他的小说理论与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时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些小说理论家在小说理论的阐释上,所取得的成就并不高,与梁启超等人报业观大有关系。
与这种为开启民智、改良群治而办小说刊物的宗旨相联系,近代小说理论家把小说的读者自然而然地定之为接受他们启蒙教育的下层愚民。梁启超率先将近代小说读者的范围圈定在“兵丁、市侩、农氓、工匠、车夫、马卒、妇女、童孺”〔28〕之内,邱炜萲则定位于“农工商贩”〔29〕,蔡奋将小说的作用限制为“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夏曾佑则干脆呼小说的读者为“妇女与粗人”〔30〕,直到1906年,还有人坚持认为“小说者,所以供中下社会者也。”〔31〕近代早期的小说理论家大都采用了这种居高临下的说教态度,其理由也非常的简单,“先知有觉,觉后是任”〔32〕。他们写小说,办杂志,目的就是为了教育民众。“这种报纸(按指《月月小说》)虽是几个读书明理人办的,却不是为着自己赚铜钱,实在是帮着列位开风气。不然,他存着整千整百的银圆,难道他自己,不会去叉麻雀,打茶围,坐马车,吃大菜,听夜戏吗?他既然慷慷慨慨,拿出来办报,可见得真心热心公益。”〔33〕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就不用再奢望这些小说理论家对小说艺术本身过多的关注了。
更进一步地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早期小说理论家,对于中国传统的小说真正思考的并不多,对西方小说也是耳食多于真知,对于外国小说理论更是处在略知皮毛的程度。因此,他们主张小说界革命,提倡政治小说之类的新小说,用小说来教育民众,希望借此改良群治,使国富民强,他们大声疾呼,用高度夸张、富于感情的口吻来“论文学上小说之价值,社会上小说之势力,东西各国小说学进化之历史及小说家之功德,中国小说界革命之必要及其方法等”〔34〕,他们的小说理论也大致限定于这个范围之内,还没有能力提出符合小说发展历史规律的小说理论来。正如梁启超自己所总结的那样:“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启超既与同志设《时务报》,哀号疾呼,以冀天下之一悟。譬犹见火宅而撞钟,睹入井而怵惕。至其所以救焚拯溺,切实下手之事,未之得也。”〔35〕梁启超主编的《新小说》杂志到第3期时(1903 年初)已没有什么作品可用来发表,只由罗普支撑着局面。直到第8号, 才得到吴趼人与周桂笙等谴责小说、侦探小说的接济,其创作宗旨已与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时重点提倡的“政治小说”大相径庭,《新小说》杂志至第9期以后,基本上已不见梁、罗诸人的作品,从1905年2月第13号起, 《新小说》杂志开始在上海出版,完全脱离了梁启超等人为它设计的运行轨道,面目全非。《新小说》的历史,也充分说明了梁启超们小说理论与办刊思想的偏颇与不足。
就《新小说》作为小说杂志来说,说它不成功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梁启超等人为发表小说而专门办期刊的做法,在当时却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1903年,商务印书馆礼请李伯元承办编辑《绣像小说》,于是,李伯元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文明小史》、《活地狱》等作品。这些作品和同时期发表在《新小说》上的吴趼人的作品都采用了类似《儒林外史》式的作品结构。阿英指出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新闻事业上”,“为了适应时间间断的报纸杂志读者,不得不采用或产生这一种形式。”〔36〕而且,谴责小说的繁荣,很大程度也因为报刊的需要。当时的报刊,不管是大报还是小报,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官场、商场、妓场进行猛烈的攻击,各式各样的官场之类话柄的搜罗成了大小报纸吸引读者的一项重要的手段。谴责小说则是把分散在各类报纸上的话柄连缀起来,作一些简单的变形、加工,便可在报刊上发表,并引起轰动。谴责小说理论家们并没有新颖、深刻的小说思想,即使象吴趼人这样重视小说理论建设的小说理论家,也并没有什么理论建树。由于这些杂志要面向广大读者,以赢利而生存,因而,这些刊物就不得不向大众的口味靠拢,迁就他们。谴责小说通常用一些夸张、显露的笔墨来“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37〕,这一派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多是办小报出身的,如吴趼人、李伯元、欧阳钜源等,他们早年就在上海花样百出地办各类小报,了解市民的口味,这样的经历,为他们的创作贴进社会,贴近民众创造了条件。《绣像小说》在晚清小说期刊中寿命最长,从1903年5月到1906年4月,整整四年,出版了72期。
在《小说林》杂志上,黄人与徐念慈虽然提出、发表了“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38〕和“小说者,殆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乎”〔39〕的新颖的小说理论,明显地对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有纠偏的作用,但这样借鉴了西方哲学、美学思想的小说理论,由于和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主流并不一致,因而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小说林》杂志也只出版了12期便告了歇业。王国维主编的《教育杂志》,发表《〈红楼梦〉评论》,也没有引起反响。
随着1911年革命的意外成功和随之而来的失向,国人的政治热情迅速消竭,小说创作立刻脱离革命而显示出都市商业化的主色。小说理论家们也不失时机地调整了重心,把兴奋点放在对小说“娱乐”、“消谴”功能的强调上。这一时期的小说主张多出现在新的报纸、杂志的发刊词上,给人以小说界创作理论思想改弦易帜、重起炉灶之感。《礼拜六》杂志吹嘘,这本杂志的趣味超过了“买笑”、“觅醉”、“顾曲”,“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40〕徐枕亚主编的《小说丛报》则干脆又一次以俳优视小说家,降低小说的社会作用:“原夫小说者,俳优下技,难言经世文章;茶酒余闲,只供清谈资料。”〔41〕这些小说理论家在“大陆风云,千变万化;神州妖雾,惨淡迷漫。本同人哀国土之丧沦,痛人心之坠落”的同时,却把“挽救狂澜”、“振兹危局、整顿乾坤”的重担御给了“贤者”,而他们却在“品评花月”,“聊遣斋房寂寞,免教岁月蹉跎。”〔42〕“有口不谈家国,任他鹦鹉前头;寄情只在风花,寻我蠹鱼生活。”〔43〕
事实上,民国初年的这些小说理论家们也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创作与理论主张之受人指斥,他们也发现了小说商品化所带来的迎合读者低极趣味、黄色小说泛滥的弊端,他们对自己的创作与理论主张也顾虑重重,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承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小说理论家也受到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影响,认识到“社会风俗,俚俗之小说造成之矣。”〔44〕对于自己编辑、发行的小说,更是明确声称“均选择精严,宗旨纯正,有益于社会,有功于道德之作,无时下浮薄狂荡、海盗导淫之风。”〔45〕他们的确不乏“警世觉民”的社会良心与道德责任感,然而,他们的创作和理论还是丢给了让人们批判的把柄。
民国初年小说理论特色之形成,与这一时期小说理论家作为职业报人和职业文人的身份是分不开的。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作家与理论家几乎全是小说杂志的编辑、出版人员,他们以报纸的副刊为阵地,逐渐扩大他们的影响,并且以报纸为基础,生发出许多新的杂志。这些报刊的编发人员都生活在上海之类商业极度发达的大都市里,他们创办报刊主要是谋利生存,要自负盈亏,他们没有梁启超等人创办报刊的经费与捐款,他们要生存,不能没有商业手段。这些报刊在编发小说时,首先考虑的问题便是“这本书籍卖得出去吗?这本书好吗?”〔46〕这类最实际,最基本的问题,即使他们不想媚俗,不想迎合社会,但作为报人,经济的杠杆与生存的、压力也会逼着他们去干。他们已别无选择。
由于这个缘故,这一时期的报刊大量刊登小说、杂谈、诗词、丛话、小品,特别是精心选择鸳鸯蝴蝶类作品。他们写寡妇恋爱,写新婚夫妇生活,写闺房乐趣,替广大市民们表达出了对包办婚姻的不满,反映了市民男女的心声、思想和呼号,在肯定人欲的同时,又对市民进行大面积的感官刺激和情欲的全方位的撩拔,迎合了其欣赏趣味。但在小说理论上,除了配合这类作品而强调小说的娱乐性、趣味性外,理论又撤退到了传统观念之中。
尽管这些报刊杂志推崇小说的娱乐性与消遣性,使传统的过于呆板严肃的伦理说教得到了淡化,客观上顺应了清末民初思想解放的潮流,但从整个近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也反映出了这一时期小说理论家理论素质不高,小说观念陈旧落后的先天性缺陷。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拿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开刀,也正说明了这一时期小说创作与小说理论的种种失误与不足。
注释:
〔1 〕本文近代小说理论家人员的列取参考了谭正璧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陈平原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及近、现代历史工具书等资料。需要说明的是, 近代小说理论家大多数同时又是小说作家或小说翻译家。为行文的方便与论述主题的集中,本文侧重于他们理论思想的转变研究,故在大多数情况下径称他们为“小说理论家”。
〔2〕梁启超:《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
〔3〕李定夷:《〈小说新报〉发刊词》,《小说新报》第1 卷第1期,1915年。
〔4〕参见陈平原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第一卷(1897 —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陈伯海、 袁进主编《近代上海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2月版。
〔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第1号,1902年。
〔6〕〔加〕米琳娜编、伍晓明译《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 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7〕李葭荣:《我佛山人传》, 见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3页。
〔8〕吴趼人:《李伯元传》,《月月小说》第1年第3号,1906 年。
〔9〕林纾:《〈践卓翁小说〉自序》,1913 年北京都门印刷局版,第1辑。
〔10〕〔37〕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章《清末之谴责小说》。
〔11〕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
〔12〕《〈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词》, 《新世界小说社报》第1期,1906年。
〔13〕〔34〕《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
〔14〕〔20〕〔24〕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第1号,1902年。
〔15〕俞佩兰:《〈女狱花〉叙》,1904年泉唐罗氏藏板《女狱花》。
〔16〕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
〔17〕转自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1年6月版,第83页。
〔18〕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二。
〔19〕黄遵宪:《致饮冰主人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转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第274页。
〔21〕平等阁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总批,《新小说》第2号,1902年。
〔22〕〔30〕别士:《小说原理》,《绣像小说》第3期,1903 年。
〔23〕公奴:《金陵卖书记》,1902年开明书店版。
〔25〕〔26〕〔27〕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卷一。
〔28〕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期,1898 年。
〔29〕邱炜萲:《小说与民智关系》,1901年版《挥麈拾遗》。
〔31〕陈光辉言,见《小说月报》第7卷第1号,1916年。
〔32〕梁启超:《举国皆我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五(下)。
〔33〕报癖:《论看〈月月小说〉的益处》,《月月小说》第2 年第2期,1908年。
〔35〕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
〔36〕阿英:《晚清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版, 第5页。
〔38〕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第1期,1907 年。
〔39〕徐念慈:《〈小说林〉缘起》,《小说林》第1期,1907 年。
〔40〕钝根:《〈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第1期, 1914年。
〔41〕〔43〕徐枕亚:《〈小说丛报〉发刊词》,《小说丛报》第1期,1914年。
〔42〕羽白:《〈小说旬报〉宣言》,《小说旬报》第1期, 1914年。
〔44〕宇澄:《〈小说海〉发刊词》,《小说海》第1卷第1号, 1915年。
〔45〕包天笑:《〈小说大观〉例言》,《小说大观》第1集, 1915年。
〔46〕〔法〕罗贝尔·埃斯卡皮著,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标签:小说论文; 梁启超论文; 文学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新中国未来记论文; 绣像小说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月月小说论文; 新民丛报论文; 清议报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