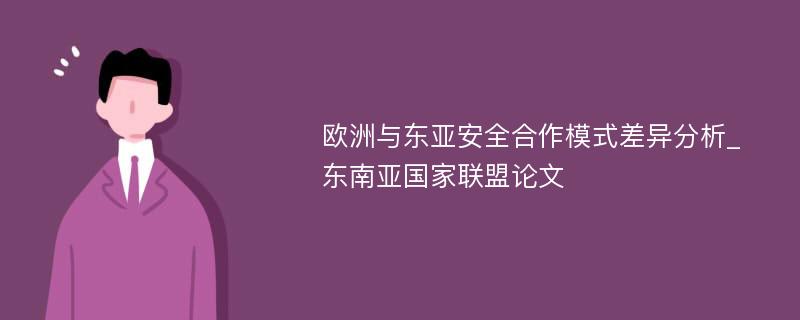
欧洲与东亚安全合作模式的差异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欧洲论文,差异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地区安全包括地区内的国家安全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两个方面。地区安全合作则是为确保这两方面安全、防止本地区国家间因军事对抗或政治矛盾引起冲突甚至战争,由地区内三个以上国家在普遍行为原则基础上通过各种多边安全机制协调相互安全关系的过程。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安全合作实践被公认为当今世界上最成熟的地区合作模式,其中,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欧洲地区安全与合作会议“赫尔辛基进程”,其有关“信任措施建设”、共同安全的思想等,已被联合国及其他地区组织吸收或借鉴。东亚自1967年建立第一个官方地区合作组织——东盟以来,在几十年的取他国之长、走自我发展道路的实践中,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本地区特色的合作模式,“开放性、协商一致和渐进性”等原则也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目前,东亚地区安全合作遇到发展瓶颈,处于重要的十字路口,对东亚安全合作的理论探讨也高潮迭起。从新现实主义的权力结构平衡理论到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化建设思想,再到社会建构主义的集体认同原则,以及借鉴欧洲模式的经验、寻找东亚合作出路,无不成为相关研究的热点。中外学者在比较欧洲与东亚两种地区安全合作模式时,基本上都认同两者间在历史背景及发展道路上的差异。本文在分析这两种模式形成过程中所依据的地区安全架构、合作理念与发展途径后认为:欧洲模式以共同安全为基础,突出“一国安全与他国安全的相互依赖性”;东亚模式以合作安全为核心,强调“确保合作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安全利益”。这两种地区安全合作理念反映了欧亚不同的地区安全结构背景及不同的道路选择。合作理念与发展道路的本质差异,导致这两种模式在某些关键方面存有内在的冲突而无法相容,从而使得东亚在地区安全合作上难以完全借鉴与仿效欧洲模式。
一
在地区安全合作领域,欧洲与东亚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进程,它们在合作架构、实现途径和合作理念上差异很大。
从安全结构讲,冷战以来欧洲地区安全关系发展呈三条脉络:即20世纪50年代初形成的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同盟;70年代初开始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进程;90年代初启动的欧洲联盟下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建设。以条约形式维系同盟内部稳定安全关系的北约和华约,通过规范性条文确保同盟内部的合作及政策协调,而欧安会借助区域安全对话与军事领域信任关系建设,为安全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间建立相互信任、保证地区安全关系的基本稳定提供了框架平台,使欧洲在两大对立体系外出现了一个包括其所有国家及美苏两大国的“地区安全机制建设”架构。在更加制度化的欧盟阶段,通过欧洲议会等超国家权力机构及欧盟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等法律条文,欧洲地区形成一整套安全和防务合作决策和行动机制。正是这些性质各异、层次不同的机制,构成了一个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多边安全框架,不同程度地化解了二战后欧洲多层面安全矛盾和种种复合性安全困境。这一事实典型地证明“制度的存在可以帮助国家确定利益和规范国家行为,使各行为体间形成相对稳定的安全关系”。①
冷战以来的东亚安全结构由三种力量行为体构成:即,域外大国美国和处于东亚边缘的苏联、地区大国中国和日本以及以东盟为代表的众多中小国家。尽管东亚也呈现出复合型安全结构的某些特征,但上述三种力量各自结成的双边安全关系构成东亚安全结构的基本元素。美国最初为遏制苏联及应对新中国成立对东亚安全关系的冲击,分别与日、韩、澳及菲、泰等签订双边条约或安全协定,逐步形成以其为主导的所谓“辐辏”式安全结构,而那些被美日同盟等视为战略威胁的“敌对国家”,如苏联、中国及朝鲜、越南等,也通过签订系列双边友好合作条约等,建立起各自的安全关系。美国一手建立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也规定美方行动只与缔约的每一方发生。即使在东盟成立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基本上还是以双边关系展开、互不隶属,如泰、菲、新分别与美结盟,非东盟成员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先后与苏中合作等。总体而言,双边安全结构基本满足了东亚各方力量对不同安全利益的需求:作为对亚太区域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既没有把东南亚条约组织变成另一个北约,也没有如推动德国融入欧洲一样促使日本加入亚洲的任何多边机构。②在东亚维持一种双边同盟关系,使美国不仅避免在多边同盟中所需承担的绝大部分责任和义务,还使其行动更趋自由和灵活。日本作为美国最重要的亚洲盟国,美日同盟既是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依托,又是其走向“正常国家”、成为亚洲大国的主要后盾。中国一向奉行不结盟政策,不希望东亚区域内建立一个由美国等域外霸权掌控的多边机构。东南亚国家既想借助美国的军事存在稳定东盟内部关系和平衡外部大国力量,又希望适当保持与美国及东亚其他大国的安全关系,使自己不完全依附于某个大国力量或束缚于大国主导的多边安全体系。
从实现合作的途径看,从1950年舒曼计划确立西欧联合的政治目标起,欧洲开始探索以地区联合而建立地区永久和平之途径。有“欧洲之父”之称的法国经济学家让·莫内将法德煤钢联营作为西欧一体化路线的开端。这个以成员国让渡一小部分主权为特征的超国家共同机构,既解决了德、法长期争夺煤钢资源的经济竞争问题,又推动两国逐渐消除了政治上的分歧和安全上的对抗。1954年,在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后,荷、比、卢等国随即倡议撇开安全问题直接讨论西欧经济的整合,欧洲经济一体化作为一种政治进程,正式成为推动地区安全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从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到1965年欧洲共同体,至1993年欧洲联盟,欧洲国家通过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货币联盟等经济整合及经济主权让渡,促使区域内国家经济相互依存基础不断扩大、相互间经济社会政治的政策融合与趋同加深。在逐渐形成的地区整体意识下,由经济主权让渡带来政治安全方面的主权让渡,包括欧洲理事会、欧共体委员会、欧洲议会等超国家机构,开始具有共同体国家的部分立法权、行政权和监督权。③1993年欧洲联盟成立,欧洲一体化步入“一个以提升欧洲整体竞争力,保持内部持久和平和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政治经济联盟”阶段。在欧盟框架下,任何一国都不能撇开别国单独考虑自身安全利益与对外政策。欧洲超国家机构作为欧洲整体代表在国际事务中的政治影响使它对地区国家产生“聚集效应”,又为解决区域问题和实现地区联合提供了前提。
在东亚,东盟组织的初始目标是为“缓解东盟内部的紧张关系并逐渐使之形成合作习惯”。但根据这些中小国家既渴望团结合作又希望摆脱大国主导、确保各自安全利益的心理,东盟采取了不同于欧洲联合的“东盟模式”:(1)强调合作的“非正式性和最小限度的组织性”④。东盟从未设立超国家的领导机构,它在决策程序中赋予每一成员国实际上的否决权;(2)实行“共同的、一致接受的行为准则”,任何议案只有在所有成员没有反对意见时才能通过,并依靠相互协商和寻求共同点来消除反对意见;(3)《曼谷宣言》特别强调“安全不受外来干涉”。面对东帝汶问题以及菲律宾、泰国的政变,东盟都以尊重各国的独立、主权、平等为由,采取不干涉政策,充分照顾不同国家的安全需求。东盟方式的核心是在确保各国安全利益的前提下,使东亚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不同文化宗教的国家,都能从维护自身特定利益出发决定其参与地区安全合作的程度和方式。它规定了东亚地区合作的基本路径。
目前东亚影响最大的东盟地区论坛和针对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都典型地反映了“东盟模式”的基本特征。作为东盟模式的延伸,东盟地区论坛从成立之初,就确定其是一个就地区政治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对话的机制,沿用正式和非正式(第一和第二轨道)两种形式,以“所有成员国都感到合适的速度”,通过磋商、讨论达成共识并一致做出决定。作为一种协商对话性质而非集体安全系统,该论坛没有正式的制裁措施,不直接干涉和影响其成员国的各自利益。六方会谈是一种针对次区域特定安全问题的合作机制,从2003年6月第一轮会谈至2007年第六轮会谈,无论是会议议题,还是会议地点和时间,都由六国经多次协商而定;特别是有关朝核问题各阶段行动方案的磋商,各方并没有因美朝双方立场差异而循机制化模式加以解决,而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协商讨论与沟通中,弥合分歧,逐渐推动朝核问题的解决取得进展。
从合作理念看,欧洲共同安全思想的形成,既是“赫尔辛基进程”的一种自然延续,也是欧洲人对冷战以来日益紧张的地区安全局势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大集团对抗下的核战争阴影严重威胁着欧洲的总体安全,使共处冷战前沿但分属两大阵营的欧洲国家试图通过军事政治措施摆脱相互不安全状况。从1972年瑞典首次提出有关建立信任措施(CBMs)倡议,至1992年欧安会通过“维也纳文件”,欧洲花了整整20年时间,历经三个阶段,逐步建立起包括宣示措施、透明措施和限制措施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性安全安排,确立了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信息交换机制,以避免在缺乏政治及军事互信情况下误判对方意图而导致的意外冲突。随着CBMs各阶段的推进,欧洲国家军事活动的透明度增加,开放性扩大,同时规模和范围逐渐缩小,两大集团开始修正基于竞争或威慑的传统思维。在对欧洲整体的安全责任趋向发展过程中,欧洲人将安全的获得转向相互信任和地区合作,逐渐确立了“一个国家在保卫其领土安全的防卫权利时必须同等对待其对手安全利益的合法权利”的新安全观。1982年,国际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帕尔姆委员会)在其“共同安全,生存的蓝图”报告中第一次提出用“共同安全”概念代替核威慑理论,认为“各国的国家安全及生存是相互联系的,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是各国共同的责任。各国必须通过坚持和平、自我克制及降低军备竞赛等手段避免核战争”。⑤共同安全思想确立了欧洲地区安全合作的基本理念。
在东亚,合作安全理念的内涵与特征及其所由产生的历史地理背景也不同于欧洲。东亚地区的合作安全及综合安全思想既是对“东盟模式”的某种发展和提升,也是东亚在冷战后期兴起的地区主义浪潮中对地区合作思想的一种自我探索。由于大多数东亚国家在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历史背景以及国力上差异极大,各国坚持的是一种内向性的国家发展战略,本国安全优先,经济发展及内部政治社会稳定为主要战略目标。在安全问题上,因宗教和种族矛盾、领土和经济纠纷、历史和政治问题引起的国家间冲突和内部政权动荡,成为各国首要关注。因此,当20世纪70-80年代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先后提出借鉴欧安会模式建立亚太安全合作框架的建议时,东亚国家应者寥寥。但这些领导人所提出的诸如“多层次合作范围、渐进式合作方式;不限制成员范围、非军事解决方式;强调在多边基础上建立对话习惯的作用和意义等”⑥合作原则,表达了一种新的安全合作理念,与东盟模式存在某种契合,迎合了东亚国家“现阶段最重要的功能不是创造规范,而是减少国家间的相互猜疑并加强现在的规范”⑦的想法。1995年东盟地区论坛《概念文件》正式规定以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两条途径建立和发展地区信任措施建设。与共同安全理念中“与敌人一起获得安全”的假设前提相比,东亚合作安全理念中关于敌人的概念更加模糊,这对于国家间安全关系互不隶属、安全利益存在严重差异甚至相互冲突的东亚国家是非常契合的。而将安全范围扩大至非传统军事领域,将经济发展、政治合作对话以及社会稳定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列入其中,以合作求安全,突出合作的功能性和议题性,强调从解决具体问题着手,使安全合作更具可操作性,与东亚国家提出的安全威胁多样性和多层次观点相近,满足了东亚国家对安全合作的各自需求。
二
欧洲模式从确保地区整体安全出发保障单个国家的安全利益,使区内国家对地区安全关切成为其安全战略目标中的首要关注;东亚国家选择从一国的安全利益出发逐渐走向地区的整体安全,国家安全成为区内各国的主要关切。从地区安全关系及安全背景、地区合作动机和目标、地区合作机制特征等视角看,这两大安全模式(即欧洲模式和“东盟模式”)存在三大明显差异。
第一,地区安全关系及安全环境的差异。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近代欧洲以主权国家间缔结条约形成的各种国际关系,孕育了欧洲机制化、规范性传统;而国家间合纵连横下出现的多边军事同盟、大国协调等多边安全组织机制,又构成欧洲多层次的安全架构,并延续至今。与此相比,东亚许多国家有长期被西方殖民统治的历史,对多边机制下的各种外部干预心存疑虑。东亚现有的国家和地区关系架构直到二战后大批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出现才形成,随之而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导致东亚安全结构分裂为美苏主导的两大体系,众多中小国家只能依附于其中一方,与之结成双边安全关系。另一方面,相较于20世纪60-70年代北约与华约在欧洲所呈现的势均力敌的力量态势及核战争恐怖,同期美日同盟与苏中同盟在东亚的力量对垒严重不平衡,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尤其如此。东亚国家更关注国内稳定和双边或次区域的安全关系,即使如朝核这种涉及地区重大安全利益的议题,也不足以让区内所有国家形成类似欧洲的整体性共同安全责任。“较低的威胁度使行为体通常选择低成本的非正式性合作,这种合作形式不需要经过复杂的批准程序,也便于修改或放弃。而高强度的威胁或高成本交易则刚好相反。”⑧
第二,地区合作动机和目标的差异。作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部分,欧洲地区安全合作进程自始至终是一种自主、能动的过程。为确保欧洲的长治久安,一个地区联合的政治远景成为二战后欧洲各国政治精英们的共识,并以此逐渐统合区内国家不同的安全诉求。西欧从1952年的煤钢共同体到1957年的经济共同体,不到5年时间就确立了共同市场目标,并对各阶段联合目标设定具体时间表。正是这种明确的目标和强烈的自觉,促使欧洲人在遇到类似防务共同体计划受挫等问题时,会设法以经济一体化手段加以推动;在核恐怖危及地区整体安全时,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能将对立各方统合起来。而东亚国家对地区安全合作的认识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不自觉的、受外部压力而来的被动性选择。无论是当初因所谓“惧怕共产主义势力”而组成的东盟组织,还是后来的朝核六方会谈机制,初始的推动力均来自于某些“特定安全威胁”,而非基于地区整体安全利益下的长远安排。因此,东盟从1967年成立到1976年通过《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花了整整10年时间才确定谋求地区和平稳定这样一个笼而统之的目标。与欧洲从1952年至1993年用40年时间实现了欧洲联盟的目标相比,东盟从1967年到2007年花了同样时间才基本确定启动“东盟宪章”。而2005年启动的东亚峰会进程,在各方不同的安全诉求和利益考量下,一开始就陷入有关目标、机制和成员资格的争论之中,迄今无法确立地区整体的发展目标以及各阶段推进表。
第三,地区合作机制上的差异。欧洲安全合作进程每一阶段的发展基本都以一个标志性正式条约为界,而如“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等里程碑式的条约更具宪法性质;即便是欧安会这样的开放性架构,有关军事信任措施建设的各阶段文件也是以逐步的强制性条款为发展方向。这种以制约性法律条文为基本架构的安全合作,不仅约束和规范各参与国在合作过程中的自觉行为,且有助于逐步建立起实施这些条约的超国家管理机构。目前,欧盟在相当广泛的政策领域内对违规成员国具有法律和机制上的约束力和强制力,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更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发动机的作用⑨。而作为东亚唯一一个渐趋成形的具有国际组织架构的地区安全合作组织,东盟只有一个激励成员国一起工作与合作的框架协定,即便是其最具机制化性质的秘书处,也仅限于组织、协调和执行东盟有关活动。东盟对区内的东帝汶问题和缅甸问题都无能为力,更遑论协调中日间的政治纠纷了。2007年东盟峰会通过的“东盟宪章”是东盟第一次为自己搭建的法律和机构框架,但它在坚持“不干涉内政”基本原则下只尝试提出“增加相互影响”条款,没有强制性条文及制裁机制。而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仍只是论坛性质的组织架构,六方会谈机制也还没有按一些人预想的朝着次地区安全合作机制方向发展。
从本质上讲,欧洲模式和“东盟模式”的差异在某些方面是无法相容的。比如,主权让渡性的合作方式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合作原则之间就存在不相容性。欧洲模式的共同安全目标,侧重地区整体安全利益,其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各国不断让渡部分主权。尽管在合作道路上,欧洲也一直围绕未来联合的目标是联邦还是邦联争论不休,但共同安全的基本走向都是以让渡部分主权求得联合,这与奉行“互不干涉内政”的东亚模式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东亚的合作安全强调单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安全不受外来干涉”已内化为东亚地区的一种共同意识。迄今为止,不仅“东盟从未打算成为一个将要求成员国交出某些国家主权的超国家组织”⑩,而且中国、日本等大多数东亚国家基本上也不认同主权让渡的合作方向。又如,在制约性的制度化合作建设道路与“以照顾各方舒适度”的合作原则方面,两大模式也存在不相容性。欧洲模式的制度性保障,是一种建立在法律条约基础上的机制化架构。为了统合各国不同的安全利益、实现地区共同安全目标,无论是经济一体化各个阶段的发展进程,还是军事安全领域的各种多边军事架构,都是在各种基础条约、条例指令、议事提案和表决规则等约束性法律化、机制化架构下演进的。而东亚目前的各种官方或民间论坛性合作框架,抑或以突出政治领域协商对话重要性的信任措施建设,都基本上遵循东盟方式最为人称道的开放性、协商一致和照顾各方的舒适度等基本原则。即便是最具约束性要求的军事安全领域的信任措施建设,东亚也基本是按照各国所认为的舒适度方式自行决定其合作与开放程度。
三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盟组织的无所作为及各国的各自为政,使东盟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近年来,随着朝核危机等潜在地区安全问题的不断浮现,以及东亚峰会、东盟宪章等启动,东亚安全合作发展方向再次引起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或决策者开始重新讨论东亚安全合作对欧洲模式的借鉴与吸收问题,如中日如何效仿德法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用制度化信任建设将合作安全思想机制化(11)、“建立一种以安全为核心的区域制度”(12)等。但根据上述分析,这些建议难以破解目前东亚安全合作进程所面临的三大困境。
这些建议难以破解的第一个东亚安全困境是如何在以美日双边同盟为基轴的二元战略结构中统合各国的战略安全利益,建立新的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冷战后,与北约主动反思结盟基础并及时调整战略相比,尽管美日两国也寻求在新的亚太安全结构中重新定位,并进行一些政策调整,如建立地区国家间的军事透明度、与同盟外的相关国家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向中国等提出旨在建立信任措施的建议等,但这些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美日“集体防卫”体制,只是将它们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变为共同对付地区安全问题的军事同盟。从美国1995年以来的《东亚战略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国威胁论”、“朝鲜核武计划”等依然是美日同盟赖以立足的主要依据;1997年“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确定的核心军事活动主要目标和基础,仍然是一种集体防卫体制;2005年出台的《美国日本同盟:为了未来的改革与调整》,重点就美日双方各自防卫责任进行重新划分,即由战后50多年来日本提供基地、美国负责提供保护的“单向依附性同盟”转变为日美两国世界范围内的“联合军事行动”。更让东亚国家担忧的是,美日双方有关军力配置的讨论,已完全突破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政治禁忌。
“当安全仍是稀缺,地区国家对其相对安全担心超过其绝对安全时,地区间的合作难以达成。”(13)以确保同盟单边安全、锁定地区主要威胁为基础的双边同盟,与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目标存在本质上的冲突。当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与区内某一大国结成排他性军事同盟后,这种安全合作模式,无论其内部结构与相互间功能如何调整,只是加强同盟内部成员间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相对于该地区而言,美日同盟的调整并不能改变其与对手间的对抗性关系,其调整方向没有欧洲安全合作进程中有关“信任措施建设”和“与敌国一起获得共同安全”的理念基础,也不可能与东盟模式的开放性特点相兼容。在此背景下,作为美日同盟防御的对象,如中、朝等,因无法确定美日双边同盟的军力调整会否转化为对其的进攻能力,尤其是对日本重新军事化的担忧,不会轻易相信美日对地区安全的承诺。而以对话和协商为重点的东盟地区论坛等,其对地区国家安全的承诺,根本无法与高度制度化的美日双边同盟相提并论。东亚国家仍然将追求自身安全利益最大化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
美日同盟作为既定现实及其对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力量体系,使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不可能绕过它而另立山头。以东盟方式和合作安全为基础形成的东亚安全合作模式,无法吸收美日同盟那样的排他性军事组织。而美日同盟更不能期望东亚国家会以美日为主导、将各自的安全利益统合在美日同盟的体系内、建立一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东亚难以破解的第二个安全困境是如何在尚存潜在安全冲突的东亚地区及在东盟开放式的安全合作理念下,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安全基础及有效的预防冲突机制。与欧洲在安全合作过程中已基本解决地区内部冲突不同,东亚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因冷战遗留问题而尚存潜在冲突的地区,这类潜在冲突包括南北朝鲜半岛长期分裂造成的半岛局势不稳定,台海分隔形成的两岸长期对峙,东南亚国家不时出现的政局突变造成地区动荡,以及中日、韩日、日俄间因领土领海之争而产生的政治摩擦等。近年来,随着地区安全形势变化,这些潜在安全问题出现新的变数:美国战略关注重回东亚,美尤其加大对朝施压,朝鲜则选择核发展战略加以对抗;逐渐坐大的台独势力频频挑衅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政府坚决不放弃对台动武的立场;日本修改宪法走向“正常国家”,在解决与东亚邻国间的领土、领海等纠纷时,放弃以往的对等协商原则,引起中、韩、朝和俄等国不满。
“对安全的担忧,对别国的不信任,决定了国家对力量关系变化和相对收益的敏感,这种敏感又进一步导致国家对安全领域合作的审慎态度。”(14)目前,在地区力量结构出现新一轮分化组合、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加的情况下,现有的缺乏集体行动能力的东亚各种安全合作机制,难以满足各国对安全的不同需求,大力提升国家军事实力成为东亚国家实现自我安全的最直接、最有效途径,而当一国为了其安全需求而进行自助努力时,不管其意图如何,都会引起区内相邻国家的不安全感,没有一个国家会冒险把自己的安全完全放到别国手中。(15)在这样的安全困境下,仅仅依靠开放性、协商一致原则进行国家间的协商与沟通,没有制度性建设有效保证政治信任建设措施的落实,难以彻底解决这些双边和次区域范围的安全问题;而这些安全问题不解决,反过来又会影响相关国家在有关军事透明度等军事安全信任措施建设上的投入力度。
东亚难以破解的第三个安全困境是如何解决中日两个地区大国力量变化而引发的相互猜疑和提防,使之建立起相互信任以及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领导核心。在东亚近现代历史上,中日两国力量对比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状态。冷战期间,双方分属两个完全对立的阵营,错过了“法德和解”那样的历史机遇。中国改革开放后,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政治外交关系也一度出现积极势头。但随着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调整,中日间的政治分歧逐步显现:日本确立“依托美日同盟而走向军事大国、修改宪法以加快正常国家步伐”的新发展战略。但在经济领域,素以亚洲领头羊之称的日本经济却在中国持续高增长的同时陷入长达十多年的停滞,随中日两国经济实力消长而来的是中国在地区及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增大。“力量转移通常导致冲突”。中国怀疑美日同盟关系调整意图,担心日本对地区的军事企图;日本则担忧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战略野心,认为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必然促其寻求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崛起。中日关系由于历史问题、东海资源等引发争端而不断降温。
“如果地区内的国家将国家安全利益放在经济发展目标之上,经济合作的深化并不能绝对带来地区国家在政治安全上的合作,即使两个国家都能从这种经济合作中获利,由于担心对方从中获取的利益能增加其军事威胁力,另一国宁愿放弃这种合作。”(16)中国为确保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大业的和平环境,希望在周边建立起一个可靠的、友好的战略依托,期望与日本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发展面向未来的双边关系;日本则希望摆脱历史问题的旧账,在加强与美国军事同盟、扩大其集体防卫自主权的同时,寻求与中国在没有历史负疚感基础上的“普通国家关系”。表面看,中日间的这种矛盾和冲突,是二战乃至甲午战争留下来的历史创伤所致;本质上,则是重新崛起的中国与已然成熟的日本在东亚力量结构变化中的新一轮角逐。
尽管有美国这样的“离岸平衡器”,但中日因力量的消长以及缺乏类似欧盟那样的约束性机制,仍摆脱不了存在潜在冲突的阴影,双方任何战略活动都会引起对方的猜疑和警惕,加深两国在政治上的对立和不信任感。如果中日间的这种历史问题不解决,相互间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如果东亚两个最大国家不能相互信任,东亚地区的信任基础将无从谈起。作为一个次区域组织框架,东盟要想胜任“小国领导大国”的角色,首先必须协调中日纷争,以此建立起地区间的安全信任。但东盟能否承担起调解中日纷争的大任,也颇不容乐观。
注释:
①Charles A.Kupchan and Clifford A.Kupchan,"Concerts,Collective Security,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1,Summer 1991,p.131.
②Chirstopher Hemmer and Peter J.Katzenstein,"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Regionalism,and the Origin ot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3,Summer 2002,p.582.
③[法]皮埃尔·热尔贝著,丁一凡、程小林、沈雁南译:《欧洲统一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10页。
④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Routledge,2001,p.5.
⑤Olaf Palme ed.,Common Security:A Blueprint for Survival,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Disarmament and Security Issues,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82.
⑥Seng Tan and Ralph A.Cossa,"Rescuing Realism from the Realists:A Theoretical Note on East Asian Security," in Sheldon W.Simon ed.,The Many Faces of Asian Security,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01,p.33.
⑦Paul W.Evans,"Assessing the ARF and CSCAP," in Hung-Mao Tien and Tun-jen Cheng eds.,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Asia-Pacific:Many Problems,Few Building Blocks,N.Y.:M.E.Sharpe,2000,p.170.
⑧Katja Weber,"European Security Integration:Lessons for East Asia?" Jean Monnet/Robert Schuman Paper Series,Vol.7,No.7,April 2007,p.6.
⑨刘文秀:“欧盟国家主权让渡的特点、影响及理论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24页。
⑩转引自倪峰:“论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结构”,《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第17页。
(11)Chang-hee Park,"Collective Security as a Means for Regional Stability in Northeast Asia," and Katja Weber,"European Security Integration:Lessons for East Asia?" Jean Monnet/Robert Schuman Paper Series,Vol.7,No.7,April 2007,p.4.
(12)杨丹志:“东亚安全困境及其出路”,《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9期,第27页.
(13)Mearsheimerrn,"Back to the Future: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1,Summer 1990,p.44.
(14)朱立群:“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兼论当前的中美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6页。
(15)参见John Her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9.
(16)Charles A.Kupchan and Clifford A.Kupchan,"Concerts,Collective Security,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1,Summer 1991,p.150.
标签: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军事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史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同盟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