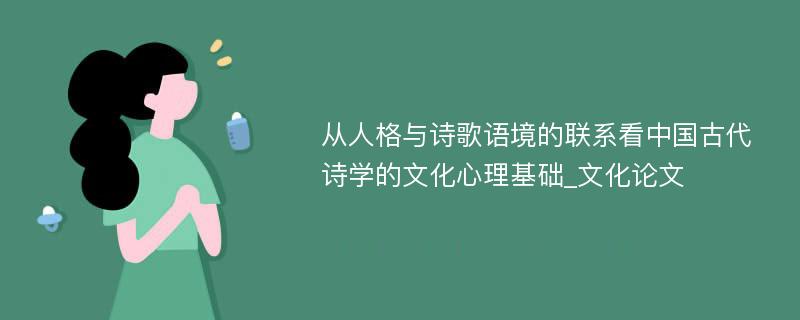
在人格与诗境相通处——论中国古代诗学的文化心理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人格论文,心理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试图对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一个前题性问题,即诗学观念生成的主体心理依据以及价值论基础发表一点见解,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主体的心理状态、人学观念、人格理想是如何显现为诗学观念的。这就首先要从文化学术上经常处于主体地位的士人阶层谈起。
上篇:士人的社会角色与两大诗学系统
1、士人社会角色的基本维度
中国古代的士人阶层是精神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和建构者。他们的特定社会境遇和心理倾向,对于一个时期的精神文化风貌具有重要的作用。士人阶层的原始生成,是由破产贵族(一说贵族之庶出子弟)以及偶然受教育的平民子弟所构成。汉唐以降,士人主要是指中下层官吏与平民知识分子。“士”在古籍中一般是指未做官的读书人而言,属于“民”的范畴。本文所说“士人阶层”则包括“士”出身的官吏,相似于古人所谓“士大夫”。
士人阶层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动态性、可塑性,他们介于并流动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管子·小匡》有“四民”之说,士与农、工、商同属于“民”。但农工商往往世代相守,具有稳定性,而“士”则大都怀有跻身于“官”的更高企望。他们进则为官,退则为民。二是他们拥有文化知识,使他们作为“民”而具有特殊性;同时使他们因此取得官僚后备军的资格,从而具有离“民”为“官”的可能性。士人阶层这两大特征,决定了他们可能扮演三种社会角色:民、官、文化承担者。
“民”是士人的基本社会角色,是他们自我重塑的起点,又是超越的对象。“官”是他们普遍的期望。“文化承担者”有时是他们不得已扮演的角色,也有辞官归隐者或虽不辞官却将全副精神用于某种精神建构的。这里每一种社会角色又往往包含着多种角色期望,或使上述三种角色交错重叠。角色期望虽不是现实存在而是一种心理倾向,但它却时时发挥着作用,有时这种作用还要大于角色意识。例如一个以官为角色期望的布衣之士,会常常站在社会管理者的立场来说话;而一位以建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为理想的官吏,也会陷入并不利于其社会管理的形上沉思之中。
上述三种可能的社会角色以及相应的三种角色预期在士人身上形成了两组角色冲突——民与官的冲突和社会管理者与文化承担者的冲突。这种角色冲突主要表现为相互矛盾的价值取向,作为民,士人希望得到统治者的关心和爱护,例如孔孟追求的价值“仁”、“仁政”,墨家的“兼爱”都是作为“民”的士人向统治者提出的规范。作为官,士人则向“民”要求顺从,希望社会安定,不要破坏既成秩序。例如尊卑观念、正名思想、忠义原则就是作为官(至少是作为官的角色期望)的士人向“民”提出的伦理规范。显而易见,这两种价值取向是矛盾的。但它们却同时存在于士人身上,譬如孔孟时而站在“民”的立场上制约、规范着君主及官吏;时而又站在“官”立场上限制、约束着庶民百姓。在他们身上这两种矛盾的价值取向形成某种张力平衡,从而使“民”与“官”两个社会角色相互重叠、彼此包容。作为“民”他们身上有“官”的影子;作为“官”他们身上又有“民”的印迹。这种角色冲突的结果,是使士人自认为对各阶层的人,以至于全社会都负有责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天下为已任”的社会使命感,或云“天下意识”。这种“天下意识”导致了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包括诗学观念)的一系列重要特征。
社会管理者与文化承担者是士人身上存在的又一组角色冲突。作为社会管理者,他们奉行一种现实精神;作为文化承担者,他们又具有某种超越意识或乌托邦观念。现实精神与超越意识是一对难于统一的矛盾,因此对于士人而言,这两种价值取向往往是彼此替代的而非同时并存的。至于何者居主导地位,则须看士人身处的具体情境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心理状态。这种角色冲突的现实表现是使士人分化为务实派与务虚派两大类。王充在《论衡》之《程材》、《量知》、《谢短》、《效力》诸篇中有“儒生”与“文吏”之辨,以为“儒生”好仁义之说而“文吏”多文笔理事之能;“儒生”求道而“文吏”求实。此所谓“儒生”近于我们所说的具有超越意识的务虚派,“文吏”则近于具有现实精神的务实派。但这种区分于先秦迄隋唐这一时期大致可行,而对于两宋以下则有欠稳妥,盖古代士人经长期自我锻造,至宋时已寻求到一种融“进”与“退”、“见”与“隐”、务实与务虚为一体的人格境界,绝少单纯的社会管理者与单纯的文化承担者了。
以上我们从士人阶层的基本特点、可能的社会角色以及角色冲突的角度对这一阶层所固有的复杂性、矛盾性进行了分析,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发现,士人阶层的这种复杂性、矛盾性对于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基本格局,对于诗学观念的发展路向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2、两大诗学观念系统
前述士人可能扮演的社会角色及两组角色冲突表现于文化价值观则为两大类型:社会现实型与个体超越型。前者旨在安排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关系;后者旨在安泊主体心灵,获得精神自由。与这两类文化价值观相应也形成了两大诗学观念系统:一是工具主义诗学,二是目的主义诗学。下面我们即对这两大诗学观念系统予以阐释。重点在于士人主体心态向诗学观念的转换生成。
工具主义诗学是士人人格结构中的社会关怀维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社会现实型文化观念在诗学中的显现。在这种诗学观念中,诗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手段而获得价值的,这种价值即等于某些外指性功能——就是说,诗的价值意义不在诗人或接受者个体心灵中获得实现而是在人的心灵之外的社会秩序中获得实现。因此对于诗人来说,诗只是实现其社会关怀的一种工具。由于这种诗学是士人阶层人格结构和文化观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故而它与士人的社会角色之独特征——亦官亦民有直接关联。这可以从这种诗学赋予士对之君主、执政者与对之百姓的各种功能意义上明显地看出来。
作为官之社会角色的扮演者,士人进入了以君权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序列,君主是这一序列的代表与象征,故而士人对君主自然而然产生依附性,他感觉自己对官这一社会角色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君主的恩赐,故而他对君主怀有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基于这种依附性与感激之情,士人要求着诗的“美”之功能——歌颂君主、赞美善政。自汉儒以“美盛德之形容”释“颂”之义后,后世历代士人均以“美”作为诗的基本价值之一。清儒程廷祚尝言,“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国风小雅为刺者多,大雅则美多而刺少,岂其本原固有不同者与?夫先王之世,君臣上下有如一体。故君上有令德令誉,则臣下相与诗歌以美之。非贡谀也,实爱其君有是令德令誉而欣豫之情发于不容已也。”(1)此言既是历代说诗者之共识,亦为历代诗人所持有的一种诗学观念,其根源盖出于诗人或扮演“官”之角色,或具有对“官”的角色期望。
作为民之社会角色的扮演者或者虽身入仕途却依然存有部分民之角色意识的士人,则对君主与官吏怀有一种规范意识,即要求他们关心百姓疾苦并能洁身自好,成为百姓之表率。另外作为文化的承担者,士人又具有某种精神独立性与社会批判意识,有某种乌托邦理想,因而他们欲以自己的价值观与理想来塑造君主,使之成为自己价值观的实行者。基于这种民与文化承担者的角色意识,士人又赋予诗以“刺”之功能——对君主与执政者进行讽谏、规劝、批评。自汉儒说诗有“变风”、“变雅”之谓以降,历代儒家士人均以“刺”为诗之基本价值之一,其与“美”相辅相成,共同承担着实现士人社会关怀的作用。应该说,将《诗经》的自然之“怨”,重新阐释为自觉之“刺”从而赋予诗以一种基本社会价值,是汉儒的功绩。汉儒——处身于君权至上和大一统社会的士人思想代表,已自觉到像先秦诸子那样任意著书立说、开宗立派、批评君主、抨击时政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们固有之士人人格又不允许其自动放弃社会关怀,于是客观情势与主观意愿的矛盾便迫使他们选择一种两全——既能满足社会关怀之心意需求,又能为客观情势所允许——的言说方式,这种言说方式便是诗。对于这种不得已而以诗为言说方式的情形汉儒即已有清醒认识。孔颖达云:“诗者,弦歌讽喻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而卑臣,君道刚毅,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稀,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恶”(2)。盖以士人本心, 其最宜者乃为帝王之师,求其次亦应为帝王之友,如此则可直指其过,直斥其非,即所谓“目谏”,亦即孟子所言“格君心之非”。这是士人独立意识,超越精神之呈露。但他们所处之现实却是“君道刚毅、臣道柔顺”、“尊君而卑臣”的,因此才须以诗的方式来规箴、劝谏君主。如此看来,诗之获得“刺”的价值实是士人有救世之志而无切实可行的救世之术,即目标之远大与手段之匮乏这一矛盾的产物。对此《毛诗序》亦有言及。其云:“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此言与其说是对《诗经》之风诗的解释,不如说是汉儒对诗提出的价值规范。既能使“闻之者”(君主)“足以戒”,又能保证“言之者”(士人)“无罪”,这自然是最理想的效果。不难看出,这是士人的自我关怀与社会关怀二种人格之维的统一,是在“自救”前提下的“救世”。基于这种二重关怀,士人对诗提出具体要求则是“主文而谲谏”。这是工具主义诗学的最佳表述——诗的文采、形象可使“谏”获得委婉而易于接受的形式。在这里“谏”乃为主要功能,“文”不过是使“谏”之功能得以顺利实现的辅助手段而已。
作为实际的或期望中的社会管理者(官),士人又要求诗对“民”亦应具某种功能,这便是所谓“教化”。士人自认是全社会利益之代表者,对于君主、执政者与天下百姓都负有责任。他们奉行“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信条,并当仁不让地以“先知”、“先觉”自居,在他们眼中百姓与君主一样,都是他们培养教育的对象。《毛诗序》说:“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因此,“教化”是士人阶层工具主义诗学观念对诗赋予的又一种价值功能,它同样是士人社会关怀之心理指向的一种表现。如果说“美刺”表现着士人阶层对统治者的希望与要求,那么“教化”则体现了他们对普通百姓的希望与要求。在士人的自我意识中,他们自己似乎是超然于社会之上的——这既是他们精神的伟大之处,又是他们的一切精神悲剧之所在。
与上述工具主义诗学相对的是目的主义诗学。简单地说,目的主义诗学就是把诗作为目的的诗学。诗之所以被视为目的而不再被看做工具,这是由于士人发现诗除了其外指功能外还可以成为自身心灵驻足之所。这就是说,诗被视为目的并不是因为它自身就是一个终极价值而不再是一种功能,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它仍然是一种功能价值才被当做目的的。这种功能是内指性的,仅仅对主体心灵言说,因而它虽是一种功能却又等同于目的,它只在主体心灵中实现。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精义及其现代价值只在于其内在目的性方面。同样,中国古代诗学的精华也在目的主义诗学方面。这种诗学也同工具主义诗学一样是士人阶层心理状态的显现形式。在本文下篇我们就来探讨这种目的主义诗学与士人心态的复杂关系。
下篇:士人的基本焦虑与心境的诗化
1、士人的基本焦虑
某些当代心理学家在对人的行为的心理驱力进行考察时发现,有一种近似乎本能的心理倾向常常是人们行为的原动力,这种心理倾向被称为“企图达到优越地位的努力”,它被视为诸种人格因素中最为关键的一种。研究者的实验证明,从幼儿园的儿童到养老院的老人身上都可见到这种人格因素的影像。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的这种“趋优心理”是以理智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它只限于客观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一旦它离开了理智基础而膨胀起来,人就成了妄想狂患者。因此一般说来人们的“趋优心理”总是指向一个可能的目标的。但即使如此,人们这种目标也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无法达到,于是“趋优心理”受到挫伤,这时在人的心理上便产生了一种被称为“基本焦虑”的消极情绪。
上述这种心理学观点对于解剖中国古代士人心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价值观、诗学观念是颇有帮助的。
士人“趋优心理”的具体指向直接与他们可能承当的社会角色相联系。如上文所言,在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角色主要是民、官(社会管理者)、文化承担者。民是士人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因而在古代他们被视为“四民之首”。对于绝大多数士人而言,他们甫一降生便获得了民这一社会角色,因而一般不把它作为一种角色期望。作为民,士人的趋优心理主要是指向另外两个社会角色的。由民而为官是大多数士人的奋斗目标,因此,官是士人最基本的角色期望,同样也就是他们“趋优心理”基本指向之一。一旦获得这一角色,则成为更高地位的官和巩固已有地位便成了他们“趋优心理”新的指向。孔子尝云:“学而优则仕”。又云:“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又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并自称是“待贾者”,这都说明“仕”是孔子的基本角色期望,只不过由于自我关怀(“免于刑戮”)与对文化承担者角色期望(“志于道”)的同时存在而使他为“仕”规定了若干条件而已。孟子就说得更直截了:“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这样孟子就将做官视为士人的天职了。孔孟的这种角色期望在后世历代士人阶层中都是有代表性的。然而对士人而言,仕途又被视为畏途,历来通达顺遂者极少,因此,对官之角色期望的受挫便是造成士人基本焦虑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作为文化的承担者,士人并非都是利禄之徒,除了官这一角色期望之外,名(名誉、名声、声望)也是他们的趋优心理的基本指向。官是一种社会角色,与之伴随的是许多实际的利益,因此对官之渴求可以说是一种功利需求使然。名不是一种社会角色而是社会对某人所扮演的某种社会角色的了解与评价,因此对名之渴求可以说是一种精神需求使然。这种精神需求虽可说人皆有之,但只是作为文化的承担者的士人把它看得有如生命般重要。孔子尝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这可以说是历代士人的共同心理。汉末魏晋之时,士林中更有“名士”之称,一为名士则社会地位便大大提高。汉末大名士郭泰身为布衣,但一般士人一经他的奖掖品题便身价百倍,甚至高官厚禄随之而来。唐宋以降,士人们对名的重视又有过往代,以至许多士人为了搏取名声而殚思极虑,矫揉造作,成了可笑可鄙的“假道学”。但令名令誉之难得又甚于求官,因此,追求名誉的心理需求更易于受到挫伤,这是造成士人基本焦虑的又一主要原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所谓“三不朽”之说,其中“立功”——建功立业——与做官相关,“立德”与“立言”则主要与“名”相关。当然,官做得好也可致名,故“三不朽”即是名垂千古之意。这是士人毕生奋斗之目标,倘不达目的,即所谓“功不成,名不就”,亦将给士人心理造成深重创伤。徐复观尝以“忧患意识”为中国古代士人基本精神品格。这“忧患意识”如自社会效应角度言之,即是所谓博施济众之希望,亦即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不得实现之产物,而自个体心理动机角度言之,则是对“官”与“名”的“趋优心理”受挫之反应,也就是说,是一种“基本焦虑”的心理呈现。
作为生命个体,士人又常常对人生之短暂与宇宙之永恒有极敏感的觉察与体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也许是士人忧生之嗟的最早记载了。历代士人,无论荣辱穷达,都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于是,对生之眷恋,对死之恐惧,对永恒宇宙之艳羡便成为士人经常性的意识内容,换言之,人生的有限性与宇宙的无限性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也是构成士人基本焦虑的原因之一。至此,我们可以窥见士人基本焦虑的全貌了——以功利需求、精神需求、生命需求为基础的三种趋优心理的受挫所产生的一种深刻而沉重的消极情绪。这种消极情绪在士人那里常常表现为三种心理体验。一是一种巨大的孤独感。《诗·小雅·正月》“有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这是一种类似于屈原“举世皆睡吾独醒,举世皆浊吾独清”的孤独感。孔子云:“道不行,乘桴浮子海,从我者,其由与?”这是一种难觅知音的孤独感。阮籍诗云:“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这是一种无所归属的孤独感。孤独感是趋优心理受挫后所产生的情绪反应,在这种情绪中,人感到自己彷佛被整个世界抛弃了,他无法与社会沟通,更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士人那里第二种来自于基本焦虑的心理体验是一种对生命有限性的无可奈何。《古诗》有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回车驾言迈》)。曹植诗云:“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箜篌引》)。孟浩然诗云:“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与诸子登岷山》)。此类诗句可谓数不胜数。这种生命忧虑是人的一种普遍心理,但在中国古代,惟有士人对它的体验最为深挚,因为士人建功立业与追求名誉的努力常常因生命的有限性而倍感急迫,而对功名的追求又往往因生命的有限性比照而显得毫无意义。因此即使功成名就的士人也常常会为这种生命忧虑而纠缠。
士人的基本焦虑在心理上的第三种表现是莫名的闲愁。王禹偁词云:“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点绛唇》)。见雨云而生愁,诚可谓闲愁。贺铸《青玉案》就更明了了:“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诚风絮,梅子黄时雨。”所谓闲愁,并非因无所事事而产生的百无聊赖之感。它是指一种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的淡淡惆怅、失意、哀伤之情。这种情绪是士人基本焦虑的心理呈现,它长期郁积于心理深处,当有外在景物刺激时便悄然而生。它虽是“有志不获逞”——趋优心理受挫的产物,但人们却因不自知其所从来而名之曰“闲愁”。一位为日用生计所困扰的农人或志得意满的大官僚都是难得有这样的闲愁的。
总之,高官厚禄、显赫名声、生命延续乃是士人阶层趋优心理最普遍的三种指向。由于这三种心理指向通常是难以实现的,故而在士人心理上造成严重创伤,形成基本焦虑,这基本焦虑又表现为三种心理体验经常地折磨着士人们的心灵。对于这种心灵的困境士人们并不安之若素,相反,他们无时不在努力寻求着自我超越、自我解脱的途径。正是由于这种努力,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特别是诗作与诗学才获得某些鲜明特色。
2、士人的自我超越
为了摆脱或者抑制基本焦虑所造成的消极心理体验,士人们可谓用尽了心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古代文化的精义恰恰是在心灵的自我解脱、自我超越,或者说是人格的自我锻造方面。从这点来看孔子和宋儒所倡导的“为己之学”倒十分切合古代文化的实际。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在古代占主流地位的三大文化系统——儒、道、释各自是如何承担心灵自我超越的任务的。
我们先看道家。老子哲学最典型地体现了士人人格四维,即社会关怀、自我关怀、超越关怀、现实关怀。譬如自然无为的观念即含有以上四义。首先,对君主与执政者来说,自然无为是一种治世之术,是使社会安定、消弭战乱的有效措施,因而也是一种社会理想。《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3)。 又:“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4)。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手段,其核心是以自然无为的方式引导百姓进入自然无为之状态,目的是天下太平。这无疑是士人社会关怀的表现。其次,对个体主体而言,自然无为又是一种心灵自救之术。其云:“含德之厚,比于赤子。”(5)。又:“绝学无忧”(6)。又:“见素抱朴,少私寡欲”(7)。又:“致虚极,守静笃……终身不殆”(8)。又:“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9)。 由此数例可知,老子是用以退为进的方式完成心灵自我超越的,也就是说,他主张摒弃学习、摒弃用智,甚至忘掉自身存在,以一种彻底的自然无为态度处世,则可超越心灵的一切忧患了。第三,对天地万物而言,自然无为又是“道”——万物根本的存在方式,这是士人超越关怀——本体论追问的结论。
老子哲学虽有多维价值关怀,但从整体上看,各维之间亦有紧密联系。其本体论玄思可以说是其治世之术与自我超越的基础。万物本体——道的存在样态是自然无为,因而社会与个体自我亦应向自然无为还原。从方法论上讲这是一个自我消解的过程,但在老子看来这才是最基本意义上的自我建构。“退”、“损”只是形式,“进”、“益”才是实质。社会有战乱争斗就消灭一切仁义观念与礼乐制度;个体自我有痛苦烦忧就消灭一切知识与价值关怀,惟其如此方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庄子那里主要是承续并拓展、深化了老子哲学中的自我超越方式。其所谓“坐忘”、“心斋”、“悬解”、“朝彻”、“见独”之论无一不是在个体心灵上用工夫,无一不是以心灵自我“清洗”的方式消解苦痛忧烦之可能性。与老子不同的是,庄子还借助于超凡的想像力而使自己的精神自我无限膨胀起来,从而塑造出一种超越时空、超越生死、超越忧乐的“古之博大真人”形像,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的人格境界。个体主体在想像中驻足于此境界之中,人世间的一切进退荣辱、生死病苦俱在瞬间中焕然冰释了。
我们再来看佛学。因在中国士人阶层影响最大的佛学思想乃是禅学,或者干脆说,禅学是中国古代士人用以完成心灵自我超越的方式,故而在此我们即简要地谈谈禅学。禅学之南顿北渐,五家七宗,宗派林立,见解繁富,但从根本处着眼,则亦不过是一个自我解脱、自我超越的问题。马祖道一说:“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拾、无断常、无凡圣。故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即是道”(10)。什么样的心才是这个平常心呢?由马祖之言观之,这里关键在于不以通行价值观念做人做事、看人看事。依通行价值标准来看人只有两种:非凡夫即贤圣,非贤圣即凡夫。禅学却教人既不做凡夫,亦不做贤圣。这就是说,要放弃原有价值标准,或者说不做价值判断。有弟子问赵州:“万法归一,一归何所?”赵州答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领布衫重七斤”(11)。有人问曹山:“如何是佛法大意?”曹山答道:“填沟塞壑”(12)。此二问皆涉佛法根本所在,而二禅师所答均文不对题,这是什么缘故?如果说前面马祖之言是讲必须放弃或摆脱通行价值观念、不做价值判断,则赵州与曹山之答非所问则是讲还必须放弃或摆脱常人的思维方式,即不按习惯了的逻辑去思考问题。那么,放弃或摆脱通行的价值观念、习惯的思维方式所为何事呢?为是的“悟”,是“见性”,是成佛。六祖慧能说:“凡夫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13)。这就是说,凡夫与佛、烦恼与智慧本非二物,关键看悟与不悟。所谓“悟”,即是由于放弃了惯常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而进入一个全新的精神境界中。这种境界是怎样的呢?临济义玄云“若得真正见解,生死不染,去往自由。不要求殊胜,殊胜自至”(14)。六祖云:“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15)可知在此境界中人的心灵获得某种自由,它不再为人世间生死畏惧、日常烦恼所纠缠。如此看来,禅学对于士人抑制或消解基本焦虑,完成心灵自我超越不啻一剂灵药,这也恰是唐宋以降士人多出入佛禅的根本原因。
最后我们来看儒家。如果说道家与禅学都是以心灵自我解构或云自我还原的方式摒绝外在价值观念的侵入,从而使心灵置于一个清净澄明、寂然不动的境界中,那么儒家却是以心灵自我建构或云自我充实的方式培养起一个昂然挺立的价值主体,从而使心灵提升到一个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自由自觉之境。最能代表儒家这种积极自我建构精神的范畴是“思”。《洪范》所言“五事”中即有“思”,并有“思曰睿……睿作圣”之谓。到了孟子更把“思”视做自我提升的主要手段了,《孟子·告子上》载孟子与公都子对话云:“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显然,孟子认为人身上潜存着两种可能性,一是成为大人,即精神自主者,一是成为小人,即为物欲而遮蔽者。而“思”则是成为大人的必要条件。“思”与孟子在其他地方所说的“求放心”、“存心养性”、“尽心”、“反身而诚”、“养气”等都是相通的,均是指对精神主体的自觉培养与提升。在宋儒那里“思”亦被视为“作圣之功”。伊川云:“须是思,方有感悟处。若不思,怎生得如此?……‘思曰睿’,思虑久后,睿自然生”(16)。周濂溪更言:“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机也”(17)。这就将“思”当做由凡入圣——自我解脱、自我超越的关键了。观孟子及宋儒所言,“思”主要是一种内省工夫,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某种潜在道德意识的捕捉与扩充。“思”可使人建立起一种强大的自信心与自强意识,如此则可消解一切烦恼忧虑了。可以说,儒家是借助“思”的工夫而使主体精神、道德意识成为最高价值,从而无形中消解那些造成人之忧虑烦恼的事物(如功名利禄和生命延续等)之价值,这样也就达到了抑制或消除基本焦虑的目的。儒学原本是一种以救世为主的学说,但由于其社会理想高远难达,再加上君权对士人阶层的压迫越来越沉重,故而士人们也就发展了儒学中的自救意识。儒家的心性之学,在我看来,即主要是一种对付士人之基本焦虑的学说。至于由“内圣”而“外王”,由“正、诚、格、致”而导出“修、齐、治、平”的理路,实则儒者本身亦未必深信,它只是起到使士人的社会关怀在理论上有一个着落的作用罢了。
以上我们分别简略阐述了儒、道、佛禅各自对士人超越自我的现实处境,解决基本焦虑问题所具之意义。如果将这三种文化系统综合比较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特别是在对那具有超越性的人格境界的追求上就更是如此。由于儒、道、佛禅三家学说中的相当部分都是对这种人格境界以及达于此境界之方式、途径的描画与设计,故而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重要方面可以称为境界文化,这是一种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学思想。
这种境界文化带有某种乌托邦性质,也带有明显的诗意。在古人所向往的那种人格境界中,人的主体精神是绝对独立的、自由自觉的,人的心理体验则是平和愉悦——由于这种自由自觉与平和愉悦是对功名利禄、生死烦恼超越之后所获得的,是一种无丝毫功利因素的精神享受,故而它即是审美的、诗意的,是人作为能思之主体所独有、所应有的境界。正是在这里,人的精神与艺术境界、诗意境界相通了。贺麟先生论儒学云:“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18)。又说:“如从诗教或艺术方面看来,仁即温柔敦厚之诗教,仁亦《诗》三百篇之宗旨,所谓‘思无邪人’是也。‘思无邪’或‘无邪思’,即是纯真爱情,乃诗教之泉源,亦即是仁”(19)。这即是说,儒家学说与诗学、儒家人格与诗境是相通的。钱穆先生论禅学云:“禅宗的精神,完全要在现实人生之日常生活中认取,他们一片天机,自由自在,正是从宗教束缚中解放而重新回到现实人生来的第一声。运水担柴、莫非神通。嬉笑怒骂,全成妙道。中国此后文学艺术一切活泼自然空灵脱洒的境界,论其意趣理致,几乎完全与禅宗的精神发生内在而很深微的关系”(20)。这就精辟地指出了禅之境界与艺术境界的相通性。钱穆又论中国文化整体特征说:“因此我们若说中国古代文化进展,是政治化了宗教,伦理化了政治,则又可说他是艺术化或文学化了伦理,又人生化了艺术或文学”(21)。这可以说对古代学术文化与文学艺术之紧密关系的清醒认识。让我们看一看宋儒对其所追求的人格境界的描述,我们就会对贺、钱二先生的观点深有会心了。二程说:“学至涵养其所得而至于乐,则清明高远矣”(22)。又说:“觉物于静中皆有春意”(23)。最能将人格境界与诗的境界融为一体的是明道先生,其诗云:“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24)。这首诗描述的是儒家的人格理想呢?抑或是诗的境界?二者融为一体,了无分别。至于道家,老庄的人格理想在魏晋六朝转化为诗歌境界、书画风格、更是文化史上的常识了。因此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境界文化即是一种诗性文化,是对人性中本有之诗意性、超越性的观念化表述,而其主要功能则是消解或缓解士人人格深层的基本焦虑。
3、诗的功能与境界
在中国古代,诗几乎与整个士人阶层都有着紧密联系。诗人不是一种职业或行当,诗也不是仅有少数人感兴趣的精神奢侈品。士人而不作诗不读诗简直是难以想像之事。文学史上那些有名的诗人只不过是无数个作诗者当中最有天才或幸运者而已。诗作之多、诗人之众在中国古代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这种情形与士人阶层的人格构成、文化心态有着直接联系。如果撇开我们论述过的工具主义诗学观念,仅就目的主义诗学观念而言,则诗对于士人阶层有两层意义:一是消解基本焦虑,二是外化其人格境界。下面我们对这两层意义分别阐述。
消解士人人格深层的基本焦虑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功能,这是目的主义诗学观念所自觉到的。孔子说诗“可以怨”,《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韩愈亦有“不平则鸣”之说。对这些观点以往人们多从社会角度予以评价:或引出诗的社会功能之说,或印证“愤怒出诗人”的道理,从未有人从诗人个体心理需求,即诗的内指性功能角度予以认识。现代心理学,尤其是情绪心理学与生理学早已指出,诸如焦虑、压抑、愤怒,忧愁等消极情绪长期积郁而不得宣泄就会导致生理病变与心理变异。因此宣泄消极情绪乃是人生理——心理上一种近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但由于种种外在原因,人们通常很难毫无顾忌表现自己的情绪,特别是那些与诸多精神因素相关的复杂情绪更难以用通常的方式宣泄出来。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诗是士人阶层宣泄这种复杂情绪的最佳方式,因而中国古代诗歌,就其主流而言,正是士人情感的形式化。诗论家钟嵘有一段话正说明这一点,其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禅,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诧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闰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品序》)。这可以说古人对诗歌内指性功能最为清醒的认识了。诸如“春风春鸟、秋月秋禅”等等自然景物乃因与诗人心中郁结之情有某种同构性或相近性而成为唤起这种情绪的因素,经由诗人加工,它们又进而成为诗的基本意象。诗人内在之情借此基本意象而外化于诗,内心于是获得轻松愉悦之感。“怨”、“愤”、“不平”、“穷贱”、“幽居”等消极情绪均因此而得到消解。中国古代诗歌发达且多哀怨之辞的原因在此,古代诗学中“感物起兴”之说的实质亦在此。心理学认为愤怒、悲伤等消极情感一经表现出来即刻得以缓解,依此理观之,古代诗人在诗中玩味、咀嚼忧愁苦闷相思之情,其实有着深刻的心理学原因。对于古代士人阶层而言,诗实具有心理治疗之作用。
诗对于士人阶层的这种心理治疗作用是针对已经形成的基本焦虑而言的。基本焦虑在心理上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能量,诗使这种能量顺利舒泄出去,使心理恢复平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基本焦虑这种消极情绪对于诗歌创作而言又成了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内驱力了。这也许正是“不平则鸣”、“愤怒出诗人”以及“诗穷而后工”等说法的确解了。如此则诗歌创作与前面所说的境界文化便处于矛盾,状态,因为境界文化——士人借人格的自我解构(道、释)或自我建构(儒)以消解基本焦虑的方式,恰好也消解了诗歌创作的心理驱力了。例如,宋明道学家大都轻视诗文甚至否定诗文之价值,他们本人也很少在吟诗作赋上用心思,偶一为之,也是信口道来,未加雕饰。这原因恐怕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人格修养已使基本焦虑得到抑制或消解,因此无须借诗文以宣泄了。依此理推之,倘士人人人都成为品格高尚、修养深厚的道学家或禅宗大师,那中国古代的诗歌园地必将一片荒芜。
对于诗歌创作与境界文化的这种尖锐矛盾,古代诗学采取了一种极巧妙的解决方式——将士人追求的人格境界转化为某种诗的意境,于是境界文化反而成为诗歌创作的动力。由人格境界转化而成的诗的意境与作为其模仿对象的人格境界的不同在于,人格境界是一种人生理想的实现,是人之精神经由常期修为而达于一个高度,因此人格境界具有稳定性、恒常性。处于此境界中人看待一切事物都会表现出那种精神的高度来,因而它既给心灵提供栖息安泊之所、消除基本焦虑,又对人的现实行为具有实际意义。诗的意境则不同,尽管它在超越性、无功利性以及自由愉悦等方面似乎完全是人格境界的再现,但它却不是人格境界。它仅仅是人的心灵在一瞬间驻足之所而不具有恒常性,它只能使疲惫的心灵得以小憩,却不能使人的精神真正达到一定高度,对于人的现实行为当然更不具任何实际意义,因为一旦人开始现实行为时,他的心灵早已从诗意世界中回到人世了。但是诗的意境又有人格境界所不及之处,那就是人格境界是纯粹个体性精神状态,它不具有可观照性,只有处身其间的人才能得到心灵自由的享受,诗的意境则表现为审美对象并给每一个欣赏者以美感。
人格境界转化为诗的意境,或者说是境界文化向诗学领域的渗入,最突出的表现当属老庄之学在六朝时以诗的形式显现了。如前所述,老庄之学除其社会关怀内涵外,主要表现为一种自我解脱、自我超越的心灵自救之术。老庄所追求的人格境界是冲虚清静、自然无为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是对一切社会文化规范与价值观念的彻底拒斥,是以“退”、“损”、“无为”的方式对社会现实的精神超越。对于老庄及其两汉以前的后学者而言,这种人格境界是作为人生理想而存在的,其外在形式则是老庄及其后学著述中所呈现的文化观念。它具有诗意性却不是诗的意境。到了六朝,主流文化的领导者是士族文人。士族是贵族化了的士人,他们既传承着文化,又世代为官,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拥有一定特权。由于这种社会地位,他们已不仅仅满足于领导着文化潮流,而且企图成为精神贵族——建立一种不同凡响的、脱俗的精神文化形式以便与自己的政治、经济特权相适应。玄学是士族文人这一心态的哲学化形式;以“缘情”、“绮靡”为特征的诗文创作以及以“飘逸”、“神妙”为特征的书画创作则是这一心态的审美化形式。于是老庄之学以其特有的超越性、玄妙性而受到士族文人的青睐从而在玄学以及诗文书画理论中展现自己。
老庄的人格理想在六朝诗学观念中被转化为诗的意境或境界、旨趣。这主要表现在一系列诗学范畴上。这些范畴主要有神、妙、高、远、清、飘逸、风韵、自然等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自然与飘逸。观老庄人格境界,实不出自然与逍遥二境。自然是消解了外在价值观念的入侵之后向心灵本然状态的还原,其特征是无私无欲、清静无为;逍遥是心灵还原为本然状态之后的自由自适,其特征是无拘无碍,俯仰自得。在六朝诗学中,自然成为一个重要范畴。刘勰谈及创作有“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之说,钟嵘评诗人作品有“自然英旨”之称,至于汤惠休“清水芙蓉”之谓则更是“自然”之境最形象的说法了。逍遥的人格境界则转化为“飘逸”这一诗学范畴而在六朝诗文创作中居于重要地位。这种转化完全依赖于二词词义的相近性。逍遥又做消摇,是指一种安闲自得的精神自由状态。《诗·郑风·清人》:“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句中之“逍遥”与另句中之“翱翱”、“陶陶”均指安适自得之貌。《礼记·檀弓上》:“孔子圣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亦指一种不累于物,超然自得的精神状态。“飘”的本义是飞举,“逸”的本义是逃脱,又引伸为隐退。“飘逸”这一组合词就含有潇洒、超脱之义,与庄子的“逍遥游”相近。因此之故六朝诗文书画理论中,飘逸也就成为一种昭示着老庄人格理想的审美范畴了。
一般而言,境界文化向诗歌意境的转化是六朝以至唐宋时期诗学观念演变的主要特征。例如唐代三位最有影响的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就分别代表了三种境界文化向诗歌意境的转化。李白被称为“诗仙”,他的作品自然清新、飘逸超迈,是老庄人格境界之显现;杜甫被称为“诗圣”,其诗稳健典雅、沉郁顿挫,是儒家精神之展露;王维被称为“诗佛”;作品空灵清寂,是佛释境界之转换。同样,在诗学理论上也是儒、释、道各有主张、并行不悖。例如皎然、严羽之论近于佛释,苏轼诗论近老庄,白居易、欧阳修则近儒学,等等。但有一现象又应予以特别注意:自唐末,尤其是两宋之后,士人的境界文化不再像先前那样壁垒森严;,而是呈现一种三家归一的势态。即使道学中的一流人物,如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等人也大都出入老庄佛禅,最后才落脚于儒的。因此宋代士人的人格境界大都是既超越又平实,既空灵,又充实的,用儒家的话说便是“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用禅学的话即是“平常心即道”、“担水砍柴,莫非妙道”。这种人格境界现之于诗文,则是一种活泼灵动、生意盎然的新气象。
在诗学理论上最能体现儒、释、道人格境界向诗歌意境转化的著作要算《二十四诗品》(原题唐司空图著,近来有人以为是出自明人之手)。其二十四种诗歌风格或境界又完全可以看成是二十四种人格境界。其中有的近儒,有的近道,有的近佛,有的则为三者融合。对诗歌风格或意境的这种总体性分类描述本身就是在人格境界与诗歌意境的相通处着眼的,这种诗学理论在人类文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只能产生于中国古代人文化的语境之中。
注释:
(1)《青溪集》卷二《诗论十三》。
(2)孔颖达《毛诗正义·〈诗谱序〉正义》引, 见《十三经注疏》本。
(3)(4)(5)(6)(7)(8)(9)《老子》第三十七、 五十七、五十五、二十、十九、十六、十三章。
(10)《指月录》卷五。
(11)《五灯会元》卷四。
(12)《传灯录》卷十七。
(13)(15)《六祖坛经·般若品》。
(14)《指月录》卷十四。
(16)《河南程氏遗书第十八·伊川语四》。
(17)《通书·思第九》。
(18)(19)《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见罗义俊编《评新儒家》。《文艺美术与个性伸展》,见《中国文化史导论》。
(20)《文艺美术与个性伸展》,见《中国文化史导论》。
(21)《古代学术与古代文学》,见《中国文化史导论》。
(22)(23)张伯行编《濂洛关闽书》卷四、卷八。
(24)朱熹编《伊洛渊源录·明道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