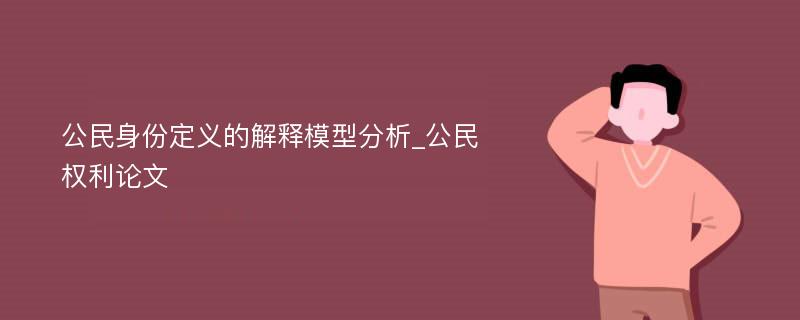
公民资格定义的解释模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定义论文,资格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民资格(citizenship)作为政治理论中一个重要概念,其历史和人类定居的共同体同样悠久,它规定哪些人是或哪些人不是某一政治—社会共同体的成员,以及该共同体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并进而与民主参与的本质、公共秩序的合法性、人类社会与国家的本质等问题密不可分。因此,考察公民资格将成为我们理解和构建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什么是公民资格?尽管它是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中一项最古老的制度,是许多寻求基本权利的社会运动所诉诸的基本概念,但用几句话来定义公民资格是非常困难的。博登海默(E.Bodenheimer)说正义宛如“一张普洛透斯般变幻莫测的脸”(注:E.Bodenheimer,Jurisprudence--ThePhilosophy and Method of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196.),这一说法也可以应用于公民资格。尽管人们不断努力用一种惟一的定义来描述它,公民资格仍然是一个有着多种涵义的词语。公民资格被定义为或者是一套公民态度,或者是公民参与的一个象征,或者是权利承担者显露个性的舞台,或者是一个生产性成员(productive member)的俱乐部。正是这种多重性使公民资格在政治理论中长期受到忽视,大部分论述政治制度、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权利与义务的著作都把公民资格当做一种不证自明的前提来处理,或者仅将它作为法学处理的问题。而政治理论往往集中于究问个人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公民资格仅仅被看做是一组权利和制度安排的反映。例如,《不列颠百科全书》用相当的篇幅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对公民资格做了一般意义的简约解释:“公民资格指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公民资格意味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份。一国公民具有的某些权利、义务和责任是不赋予或只部分赋予在该国居住的外国人和其他非公民的。一般地说,完全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是根据公民资格获得的。公民资格通常应负的责任有忠诚、纳税和服兵役。”(注:《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页。)
但事实上,公民资格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并且,这些丰富的内涵因人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和运用,形成了不同的公民资格定义模式。
一
公民资格理论的先驱马歇尔(T.H.Marshall)在《公民资格与社会阶级》(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一文中,将公民资格分为公民的(civil)、政治的(political)、社会的(social)三个方面,即公民资格的三个要素。公民资格的公民方面是个人自由所必不可少的权利——人身自由,言论、思想自由,财产权和获得公正的权利,与这些公民权利直接联系的制度是法院。公民资格的政治方面指参与以议会和代议制政府为依托的政治权力运作过程。公民资格的社会方面指公民的经济福利与安全以及公民“充分分享社会遗产和按社会一般标准过文明生活的权利”(注:T.H.Marshall,Class,Citizenship,and Social Development-Essays by T.H.Marshall,Doubleday & Company,Inc.Garden City,New York,1964,p.72.),与之相关的制度是各种社会服务和学校教育。但是,马歇尔并没有将公民资格的这三个方面分别在各自的领域进行论述,而是将三个方面的演进要么作为立法文件的结果,要么作为法庭判定的结果,例如,法治原则在18世纪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法院的工作成果”,在经济领域,法院在促进和提出工作权的“新原则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并且,社会权利也是由议会通过的诸如《定居和迁徒法》(Law of Settlement and Removal)等所确定的(注:Ibid.pp.74~76.)。虽然马歇尔从权利和司法角度来看待公民资格的发展,但他的主要意图显然不是为公民资格下一个正式的定义,而是分析英国公民资格权利与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公民资格的平等意义对社会阶级所包含的不平等的影响。在马歇尔看来,公民资格只是“授予一个共同体的完全成员的一种地位(身份)”(注:Ibid.p.84.),所有被授予这种地位的人在权利和义务上一律平等。在英国,公民资格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这个不平等的制度的发展过程相一致的。公民资格发展的早期阶段,即公民权利的发展是对封建特权的否定和竞争性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因此,公民资格在这个时期与资本主义并没有冲突,但随着公民资格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发展,即公民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平等的扩大,却对市场经济所造就的不平等形成了攻击,反过来,“经济不平等的存在对公民资格身份的丰富带来了困难”(注:Ibid.p.117.)。最终,马歇尔希望通过扩大社会服务范围来削弱或中和社会不平等。
总体上看,马歇尔认为公民资格权利的发展和扩展是立法决定而非社会斗争的结果,他所提供的解释是公民资格发展的表面化和具体化,但公民资格的主体——公民却缺位了。对此,吉登斯对马歇尔的批判起了补充作用,他指出,与其将公民资格权利的三个范畴看成公民资格权利整体发展的三个阶段,还不如把它们理解为斗争或冲突的三个舞台,即公民资格权利是作为“阶级冲突的焦点”出现的(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49页。),“与其说公民资格的这些权利的普及弱化了阶级分化(但无法消解阶级分化),倒不如说阶级冲突是公民资格权利得以扩展的中介”(注: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3页。与译文有出入,原译文为“更有效的说法应该是:解决冲突是公民身份权利得以扩展的中介,因而这些权利的普及并未弱化了阶级分化。”)。所以,马歇尔的分析虽然阐明了公民资格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联系,但他并没有把公民资格作为一个共享同一制度框架的不同群体和个人为了表达他们的社会处境并将制度的既定意义的边界进一步拓宽而进行斗争的领域。
二
公民资格是共同体自治和参与。这种模式强调参与政治领域的重要性和对公共社群生活的追求,即强调通过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而建构公共生活。这种模式在西方有很长的历史传统,并且与马基雅维利、卢梭、托克维尔等人的共和主义一脉相承。巴伯(Benjamin Barber)认为公民资格是“强民主”(strong democracy)的核心要素,这种强民主不是“将个人看做抽象的人,而是看做公民,因此,公共性和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定义性特征”(注:Benjamin Barber,Strong Democracy: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p.117、119.)。在他看来,公民资格是在一个共同体内参与过程的结果,“从强民主角度看,参与和共同体是一个社会存在模式——公民资格的两个方面”(注:Ibid.p.155.)。在巴伯的解释中,政治领域成了公民资格定义的根本领域,公民之所以是公民是因为他们讨论并参与政治,因此,公民资格排斥了个人离开政治领域的可能性,这样,巴伯就面临着将多样化的个人纳入惟一领域而剥夺其他领域涉入的可能,从而回到了古希腊。也就是说,公民资格忽略了时间和历史而以同一面目存在着。
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公民资格观首先假定一个有着共享价值的共同体,公民在其中“共享一种文化并注定继续共享这一文化”(注: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New York:Basic Books,1983,p.5.)。由于共同体本身就是一种最重要的可分配的善,并且政治共同体可能是我们能够掌握共享意义的最密切的领域,沃尔泽提出,公民资格是在“彼此间有某种特定承诺的男女组成的各有特色的、历史稳定的、继续存在的诸多共同体”中形成和发展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consciousness)”(注: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NewYork:Basic Books,1983,pp.62、28.)。这种由共同生活而形成的集体意识或民族特征(national character)不是“一个固定和永久的精神装置”,而是“一个历史性共同体成员间共享感性和知觉的生活事实”(注:Ibid.p.28.)。共享参与历史过程的经验说明共同体的成员通过讨论、斗争而建构他们自己的制度和法律,并由此而形成一种彼此共享而又独立于外界的生活方式。由此,沃尔泽将公民看做一个受特定传统决定和对社会意义达成一致的特定社会的平等成员,他们对共同体的存续都同等关注。也就是说,如果共同体面临危险,那么,所有的公民都必须集合起来保卫共同体,因为共同体的价值高于所有其他价值。沃尔泽将共同体的历史作为先在的,共同体的历史传统是共同体内每个人都同意的原则和意义的大仓库,不受挑战(注:Ibid.p.31.)。
由此,沃尔泽的公民资格是紧贴传统和社会意义的,而传统和社会意义一经公民同意,就不能质疑。他的公民资格根植于民主制度安排中,而且对公民资格的普适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在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中没有社会能够替代民主所起的作用,“真正重要的是公民间的辩论”(注:Ibid.p.304.)。但是,他的观点预设了既定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公民参与政治制度的义务。也就是说,沃尔泽的公民资格是在承认既定政治制度和传统不可挑战的条件下的积极参与。
三
公民资格是法律意义上的、普遍性的制度。达伦道夫认为公民是现代历史上的能动者,因此,“公民资格是……一个在法律中得到表达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法律思想。它描述权利,通常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人的特权……,它创造一个……法律至上的共同体;它使那些属于该共同体的人不受彼此之间的伤害,并且,通过创造一种俱乐部(club)而使他们免受外部的伤害”(注:Ralf Dahrendorf,"Citizenship andBeyond:The Social Dynamics of an Idea",Citizenship--CriticalConcepts,Volume II,edited by Bryan S.Turner and Peter Hamilton,Routledge,1994,p.292.)。
作为一种旨在保护成员不受彼此之间伤害的“俱乐部”,公民资格成为一种由法律创制的秩序,即法律共同体。由此,达伦道夫将公民资格看做一个规定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框架,公民资格因此成了平等的一个抽象维度,也就是说,在这个框架内,一个人之所以与其他人平等,不是作为具体的个人,而是作为权利承载者(right-bearer)。正如达伦道夫所指出的,“公民角色包括为所有拥有这一角色的人所拥有的一套平等的权利”,“公民资格是一种普遍化的权利”(注:Ibid.p.295.)。权利是进入公民首先作为权利承载者的宗教团体、社会阶级、共同体的成员的通行证,并且,作为权利承载者,公民之间的差别在涉及权利时一律不存在,也就是说,权利成为政治认同的惟一要素,历史、文化等其他要素都被忽略。但是,公民也是一个特定社会或群体的成员,有着对该社会或群体的政治、历史和传统认同。公民资格这种一般化的特点所面临的直接挑战就是非共同体成员——外国(邦)人的出现,因为外国(邦)人是被排斥在公民权利一般性之外的。因此,这种法律定义的公民资格就成为维护共同体政治秩序和稳定的制度设计,而这种制度设计的操作者就是司法部门,此时,这种公民资格将公民推到了司法制度的客体地位。达伦道夫对公民资格的法律定义由此倾向于关注入境移民和归化,而不涉及具体的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
四
公民资格是自足(self-sufficiency)。这种观点主要针对福利国家。马歇尔曾经说过:“(公民)最重要的义务是工作。”(注:T.H.Marshall,Class,Citizenship,and Social Development-Essays by T.H.Marshall,Doubleday & Company,Inc.Garden City,New York,1964,p.117.)米德(Lawrence M.Mead)通过对美国社会的贫困和失业问题的考察,认为只看到公民资格的法律特征是不够的,公民不只是权利承载者,而且还应当是工作持有者(job holder)和相关义务的负担者。他认为:“工作必须被当做一种公共义务,与交税和服从法律一样。”(注:Lawrence M.Mead,Beyond Entitlement:The Social Obligation ofCitizenship,NewYork:Free Press,1986,p.82.)因此,公民应当自立自足,这单靠公民自己是不可能实现的,需要有公共权力来保证这种义务得到履行。弗林威德(Robert K.Fullinwider)则分析了福利国家中公民资格的三个维度:作为自立自足的公民、作为好邻居的公民和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公民(注:Robert K.Fullinwider,"Citizenship and Welfare",Democracy and the Welfare State,edited by Amy Gutman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261~278.)。其中,自足是最重要的,能够工作却接受国家福利的公民的地位是低下的,他们需要从依赖地位提升到公民资格的真正地位,即自足。而提升工作应当由国家来做。由此,弗林威德进一步将自足而非工作作为公民资格的基本范畴,但自足却是通过工作来实现的。
五
上述这些公民资格解释模式都将公民资格作为一个超乎公民控制的派生词,在法律定义中,一部由立法机关制定并由司法部门以实际行动解释的法律(通常是宪法)界定着公民资格的轮廓;在将公民资格作为自足的解释框架中,工作和经济结构的要求设定了公民必须满足的条件。在马歇尔的解释框架中,通过法律确立而建构的社会权利使阶级冲突的缓和成为可能。在参与模式中,参与政治领域成为有意义的公民资格的标志。所有这些解释模式都既没有认识到公民对法律原则和社会实践的阐释的重要性,也没有认识到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中利益的多样性,因此,在这些模式中,公民是公民资格的客体,而非主体。任何人都是置身于具体的历史和传统当中的,因此,公民资格的抽象普遍性应当被置于具体的历史和当下相连接的斗争和原则中,也就是说,公民资格应当是过去和现在的连接点,是在具体的人类生活实践、制度和传统中发展至今的,我们应当把公民资格看做是具有历史的传统和实践的制度。因此,我们需要兼顾社会、历史、政治、法律和道德等维度,使公民资格的定义具有社会科学意义上的适用性。
首先,公民资格是有界限的,是一个有确定边界的社会一政治共同体(城邦、民族国家等)内的完全成员资格,是该共同体成员获得稀缺资源的基本途径。因为在人类的所有共同体中,“我们互相分配的基本善首先是成员资格,而我们在成员资格方面所做的一切建构着我们所有其它的分配选择”(注: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p.31.)。在共同体内,“公民”被赋予特定的权利,于是,公民资格就成为一个有界领土内“人格”的标识。也就是说,公民资格是成员资格的标志,是共同体中一定范围内的特定的人所戴的一模一样的面具,这张面具反映着共同体成员共享的认同,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也在不断地更新内涵。成员资格有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方面考察一个共同体内的非公民如何获得成员资格,即非公民——打着耻辱印记的种族、民族、性别、阶级或无能力群体——怎样获得权利并被承认为公民。对外方面则分析共同体之外的人如何获准进入共同体并归化为有参与权利和义务的公民。
第二,公民资格从其主体——公民角度看,包括权利和义务两个方面。权利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是完全不同的,消极权利指普遍的保护性的权利,主要是法律权利。积极权利指普遍的参与性权利,如政治权利。如果只有消极权利,仁慈的独裁者可以凭借有限的法律权利和范围较广的社会权利在收入再分配系统内进行统治。积极权利则将公民作为主人推到政治甚至经济的前台,公民们凭借积极权利分享政治和经济权利。消极权利是积极权利得以行使的基础,二者共同构成权利的完整内容。权利要求相应的义务履行来保证,但义务也必须约束个人的公民资格权利以使整个权利系统能够运行。简单地说,公民资格义务包括对国家忠诚、服从法律、纳税和服兵役。
第三,公民资格权利是经由社会—政治共同体(主要是国家)承认并写入法律的普遍权利,向全体公民实行。各群体可以提出某些权利主张作为公民资格权利,但由于各群体的出发点(利益或者亚文化)不同,所以,往往与其他群体(利益或亚文化)相冲突,而通过公共权力将公民资格权利写入法律则是以普遍权利形式来消除这种冲突的有效方式。因此,只有通过共同体写入法律或以其他方式予以承认的普遍权利才是公民资格权利,共同体的承认是公民资格权利合法化的必经途径。
第四,公民资格从根本上意味着平等。也就是说,具有某一共同体公民资格的所有人都拥有平等的地位。当然,这种平等不可能是彻底的平等,主要是程序性的——获得公共职位的机会平等,同等条件同等待遇。在某些情况下,它也可能包括对实质平等有直接影响的付酬和服务,例如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最低生活费。
第五,公民资格是共同体用以分配利益的边界。公民资格规定谁是或谁不是某个共同体的成员,而成员身份则是共同体分配的基础,诸如“按需分配”、“以应得而分配”和“自由交换”等分配原则都以成员资格为边界,如果超越这个边界,分配就不仅是非正义的,而且还可能威胁到共同体的安全(注:Michael Walzer,Spheres of Justice,p.21~27.)。
因此,我们可以说,公民资格是一个社会—政治共同体内所有成员在一定平等基础上所拥有的普遍权利与义务的集合,是共同体向各社会群体、家庭和个人分配集体性资源或利益的基础。
六
公民资格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政治形态相适应,而且,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会进一步发展以适应社会—政治制度的需要,同时推进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从总体上看,公民资格具有以下功能:
第一,用作区别原则(principle of discrimination)。就人类的历史经验看,它从一开始(古希腊时期)意味着特权和排除,主要表现在本国公民作为一个群体平等地享有的权利和待遇很少或完全不赋予外国人,无论该外国人是否在本国居住。这种区别原则从古至今一直得到各个国家的认可和遵行。
第二,保护公民不受来自市场多变性和其他领域不利因素侵害。以公民社会为依托的现代公民资格由于涵盖以公共权力为后盾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从而为公民个人存在和平等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其中的社会权利尤其成为使公民免受市场权力无情打击的保护伞。随着市场领域、国家领域、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之间的彼此影响和发展,公民资格的权利内涵也越来越成熟,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交互发展日益成为一种保护人们不受市场的多变和不确定性以及相关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不利因素侵害的社会和法律措施。
第三,从情感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成为世俗团结的一种替代性手段。公民资格可以通过权利和义务的互惠创造新型的社会团体,并促进国家的团结。简言之,公民资格成为现代社会公民宗教的一个方面(注:作为公民宗教的公民资格是直接来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一种思想。这种公民宗教只关注现实世界公民的命运,而不关注公民的彼岸世界,即宗教信仰。参见卢梭《社会契约论》第八章,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随着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公民资格这种通过国家对权利进行的普遍性公共供给在家庭和教会之外创造了新的代际忠诚与义务纽带,对促进公民在精神上的认同起着重要作用,成为公民教育的一个方面。因此,公民资格从情感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成为世俗团结的一种替代性手段。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公民宗教也可能削弱人们对社会的道德忠诚。例如通过税收由国家向穷人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容易造成人们对那些处于贫困中的人的冷漠,并且可能造成养懒汉的普遍搭便车问题,从而又削弱公民资格的平等内涵和团结功能。
第四,公民资格孕育并促进制度的创新。公民资格的每一种权利的发展都来自反映在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的人们的利益需求,而不同的利益需求的满足都需要寻求制度保障。在这个意义上,每一种公民资格权利的最终确立,都意味着国家通过自上而下的手段或民众(包括公民、非公民的弱势群体等)自下而上的运动变革了当时的相关制度。其中,国家针对公民社会中的各种需求,通过自上而下的手段主动丰富公民资格权利或在民众不反对的情况下增加公民资格义务,对于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