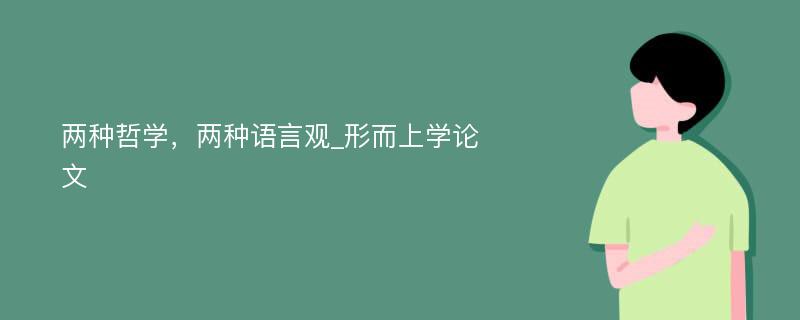
两种哲学,两种语言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哲学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 (2000)04—0102—07
1
人本与世界万物息息相通,融为一体,无主客之分。但人又不同于其他万物,人有精神性,因此,人总有一种超越其他万物、企图摆脱物质性或者说超越有限、奔向无限的内在冲动,这种内在冲动的过程表现在西方哲学史上就是几次哲学转向的运动。
第一次转向是柏拉图《斐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的,从在个别的具体事物中寻找当前具体事物的根源转向为在“心灵世界”(即“理念”)中寻找当前具体事物的根源,这一转向标志着人类超越物质性和有限性而突出精神性和奔向无限性的第一步。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是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而存在的。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明确地建立了近代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原则,从而进一步推进了人类超越物质性和有限性而突出人的精神性和奔向无限性的内在冲动,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二次转向。康德沿着主体性哲学的方向,更进而把先验性看作是必然性知识的来源,这是人类内在冲动过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也可以算作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三次转向(胡塞尔就是这样看的)。不过我还是想把康德哲学归入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大范畴之内。黑格尔是主体性哲学之集大成者,他完善了主体性哲学,他的“绝对精神”或“绝对理念”是绝对的主体,实际上是把人的主体性夸大到至高无上、登峰造极的神圣地位。人类企图超越物质性和有限性的内在冲动在黑格尔这里可谓达到了顶点,但这个顶点也是它走下坡路的开始。黑格尔死后,他的绝对主体被一些现当代哲学家们从各种角度撕得粉碎。西方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主体性哲学。
其实,在西方思想史上,伴随着这种突出精神性主体的内在冲动过程的,还有另一种与之相反的思想运动:首先是哥白尼关于人所居住的地球不再是宇宙中心的理论;后来是达尔文发现的关于人类的动物演化的理论;再往后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关于无意识对于自我意识或主体意识的重大作用的学说。这三种理论,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是对人类自恋的三次打击。我以为这三次打击也可以说就是对突出精神性主体的内在冲动的反击,是对主体性哲学所标志的人类中心论的反击。三次反击所构成的思想运动,说明三次哲学转向所标志的内在冲动再也不能一意孤行地继续下去了。当精神性主体在人的内在冲动中被抬高到如日中天之际,一种返回到物质自然和现实生活的反向运动开始了:人们愈来愈倾向于否认超越感性之外的绝对主体,人不能作为主宰一切的主体而君临于客体之上。
由黑格尔集大成的传统形而上学,即主体性哲学,基于内部的和外部的原因而走向终结。黑格尔死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特别是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流派纷呈,各有己见,但大体上都以强调超越主客关系,主张主客融为一体(海德格尔的“此在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主客融合论)为指归。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这一思想基本观点是整个西方哲学史上继笛卡尔、康德之后的又一次大转向。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一书中自称他的现象学是这次转向(“革命”)的开创人。胡塞尔不仅像康德那样认为认识形式或范畴的客观性来源于主体性,而且把认识内容的客观性也建立在主体性的基础之上,他主张认识对象在认识活动中构成自身,这实际上就是说,对象是在人与物的交融中构成的。正因为人与物的交融构成对象,正因为物必须在其与人的交融中显现其自身之所是,所以在胡塞尔看来,超越于人之外的独立外在的东西是无意义的,因而也不是他所谓“自明的”、“被给予的”或“直观的”(这是胡塞尔现象学不同于传统主体性形而上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后者把客体看作是与人的主体相互外在的)。换言之,人与物的交融构成整个有意义的世界,并使整个世界处于“被给予的直观”之内。胡塞尔由此而排除传统形而上学所主张的“超越”,认为这种“超越”就是承认离开人而独立外在的东西的意义。胡塞尔的这种哲学观点开始把人的注意力从传统主体性形而上学所主张的抽象的超感性的概念世界拉回到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即“生活世界”中来,哲学从过去那种苍白无力、枯燥乏味的贫困境地开始走向了与诗意相结合的境地。但胡塞尔毕竟还只是一个现当代哲学的开创人物,他的现象学哲学本身还包含许多传统的主体性哲学的旧框框和印迹。他的哲学中所蕴涵的许多连他自己也不明确其重大意义的开创性观点突破了他的现象学哲学自身。[ 1](P10)胡塞尔在不少地方谈到事物的“明暗层次”的统一,谈到事物总要涉及它所暗含的大视野,这实际上意味着在场的事物(“明”)都出现于由其他未出场的事物(“暗”)所构成的视阈之中,意味着胡塞尔不同意传统形而上学以“永恒在场的”超感性概念为万事万物之根底的观点而主张在场的与不在场的具体事物结合为一体。[1](P10)只不过胡塞尔的这些思想尚未有明确的阐发,胡塞尔仍然经常强调“在场”的优先地位。法国当代哲学家德里达批判了胡塞尔以“在场”为先的观点,并发掘、补充和发展了胡塞尔现象学所暗含的关于在场与不在场结合为一体的观点。
把在场的具体物与不在场的具体物结合为一体的现当代哲学观点,是对于自苏格拉底—柏拉图至黑格尔的传统形而上学所主张的那种抽象的概念哲学的反对,也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前基本上不分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不分主体与客体的哲学观点的某种回复(一种在高级基础上的回复),而从中西哲学比较的角度来看,则又可以说是与中国传统的人与万物一体或天人合一说(这里的“天”是取其自然或万物之意,而非指意志之天或封建义理之天)以及易老思想[1](第6章)的某种接近,尽管二者间有时代上和历史阶段性的差异。[1](第6章)
西方现当代的万物一体观或天人合一观(为了简捷通俗起见,我姑且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这样称呼),使西方人不再像自笛卡尔到黑格尔的主体性哲学那样过多地注重人与自然的斗争,过多地注重寻找普遍性,过多地注重认识(知),轻视人的情感和意欲,而转向重视作为知情意结为一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异性,重视各个人的独特性,从而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的研究。精神科学,或者说,关于人的学问,被提到比自然科学更受注目的地位(注:关于自然科学重在认识普遍性,精神科学重在人的个体性和相异性之间的沟通问题,请参阅拙文《语言的诗性与诗的语言》(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当前,在我国学术界, 有一种观点仍然执著于把精神当作自然一样看待,专心致志于寻找普遍性而忽视个人的独特性和人与人的相异性和相互理解的研究,这是否有辱人的尊严呢?
2
对精神科学研究的重视和对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理解的研究的重视,必然导致对语言的哲学研究的重视。
在人与万物融为一体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语言是世界的意义之寓所,每个个人所说的语言(言语)来源于作为世界意义之寓所的语言,前者(言语)是有言之言,后者是无言之言,前者之所以能发生,是由于对后者的聆听。
传统的语言观总是按照常识的看法,认为书写的东西是口头语言的符号,语言只是说话的主体的活动,总是涉及说话者或作者。这一基本观点,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的第一节(16a )中就已得到明确的表述。[2](P140) 海德格尔和德里达认为这种传统语言观“与主体性形而上学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在海德格尔的论题中,语言不能归结为说话者的活动,它勿宁需要(按照最简单的公式来表达)对某种言说的东西的聆听,而这某种东西是它在人类语言中发出声响以前就言说着的”。[2](P140)海德格尔本人说过:“说源于听。 ”它是对我们言说着的语言的一种聆听。因此,说并非同时是一种听,而乃预先就是一种听。这种以不显眼的方式对语言的聆听先于所有其他各种聆听。我们不仅仅是言说语言(the
language ), 而是我们从语言中言说(“Wir sprechen nieht nur die Sprache,wir sprechen aus ihr”)。[3]德里达从另一角度表达了与海德格尔相似的观点。 德里达批评了胡塞尔关于语言表达或意谓总是指向他人的体验而他人的体验对于说话者又不能“直观在场”的观点,他发展了胡塞尔所暗含的而又超出其自身的观点,认为语言表达可以独立于一切“直观在场的东西”:既独立于感性对象或客体的“直观在场”,也独立于主体(说话者)的“直观在场”。[2](P142)这也就是说,没有某个说话者或没有某个作者之前,早已有语言。
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关于语言独立于说话的主体的观点,是对传统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背离。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特点之一是把最真实的存在看作只是在场的东西,因此它又被称为“在场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和德里达都批评单纯在场的观念。海德格尔所谓“在手的东西”(Vorhandenheit,presence-at-hand )就是与单纯的看或直观相关的一种现成的在场。他认为比“在手的东西”更根本、更基础性的是“上手的东西”(Zuhandenheit,readiness-to-hand), 即人与之打交道的东西,或者说,人所操作、使用的东西(而非单纯的看或直观着的东西)。“在手的东西”是与主体对立的、预先摆在主体面前的客体,但海德格尔认为任何事物首先是“上手的东西”,或者用我们中国哲学的语言来说,首先是人与之交融在一起的东西,而“上手的东西”总是涉及隐藏在其背后的东西,并非单纯在场的东西,它的意义指涉着一个作为参考系的整体。这也就意味着,语言表达的意义不在于单纯的“直观在场”,而总是在场与不在场的东西相结合的整体。这种意义下的语言,就是一种先行于某个说话人或某个作者所说的语言之前的无言之言。借用庄子的话来说,我想强名之曰“大言”。“大言炎炎”(《齐物论》),意谓“大言”如燎原之火,照亮一切,使万物具有意义。
德里达从另一角度指出了单纯在场观念的局限性。德里达指出:胡塞尔所谓与“语言意指”严格分离的“前表达经验的层次”(即语言表达所指向的他人的体验,这种体验对于说话者是不能直观在场的),是一种单纯感性的在场,这种在场的“现在”并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与过去、未来有着本质联系的。它不是先有一个出场(在场)的“现在”,然后与过去、未来相联系;实际上,这种联系原来就是一个出场的“现在”之构成因素,这也就是说,没有单纯的自我同一的出场(在场)。德里达在《言语与现象》一书中把这种“现在”的特殊复杂性用“重复”的概念来称谓和说明,其要点是,“现在”在下述两种意义下包含一种重复的运动:(1 )当前出场的“现在”包括先前的“现在”的重复,这就是保留、记忆;(2)当前出场的“现在”, 即出场的形式,其本身是理想性、观念性的并从而是无限地可重复的。(注:同[2]书第143页;并参阅杜小真译德里达著《声音与现象》,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1—86、127—131页。我所提到的德里达著《言语与现象》一书即杜译《声音与现象》。)这种重复的特征被德里达称为“印迹”(trace),又称“延异”(différance)。根据这种“延异”的观点,封闭的在场就被解构了,即是说,语言表达或意谓的作用不要求达到单纯直观在场的目标,不要求达到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在场物,而成为独立于言说者或作者的在场以及独立于对象的在场的流变不居的东西。德里达所谓独立于主体与对象的语言,也颇类似上述海德格尔所说的人与世界相融合、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整体的语言。
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语言观,撇开二者论证的角度不同之外,其共同的思想倾向都是强调人与万物融合为一的宇宙整体能作无言之言。这种语言独立于说话人或作者的语言,前者通过后者而发出有言(有声)之言。显然,这种语言观的哲学基础是万物一体论(借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它和传统语言观之以主客关系论和主体性哲学为基础,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3
主客关系式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沿袭柏拉图主义的方向,把世界分裂为感性世界与超感性的概念世界、现象的事物与本质的事物(“真正的世界”),在这种哲学观点的指引下,语言表达的意义被归结为由说话的主体指向客体:或指向感性的对象,或指向抽象的概念,总之,都是指向在场的东西,前者是变动不居的在场,后者是永恒的在场。由于这种语言观以要求在场为意义的根本条件,所以,没有任何可能对象的语言表达,或与概念不相符合的语言表达,在它看来,都是无意义的,例如“一座金山”或“方形的圆”就被看成是无意义的。[4]
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和现当代的现象学否定了超感性的抽象概念世界,要求人们专心致志于具体事物本身及其自我显示,这样,事物的意义就不在于表面现象指向所谓“真正的世界”或抽象概念,也不在于由此一事物指向彼一事物,而在于指涉一事物所一向源于其中的万事万物本身之整体,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在于指向“世界”。所以,要理解某事物, 就要参照“世界”这一“敞开的参照体系”(an
opensystem of references)[2](164—165), 而不是参照抽象的普遍性概念或某一个别的事物,这就叫做“从事物自身理解事物”(tounderstand it from itself)或“自我显现”(self-showing)。[2](P164—165)这样,语言表达也就得到了重新的界定:语言的意义不是指语言要去表达独立于语言的某确定的对象或某确定的概念,而是(用海德格尔的说法)事物从中显现自身的“漂流着的世界”,是作为Dasein之Da的“言说”(Rede),亦即“世界”之展露口。[2](P164—165)
对于这种意义下的语言来说,某个具体对象的“直观在场”是不需要的,作为某一类对象的永恒在场的概念也是不需要的,它所需要的是一切存在者(beings)之“集合”,这“集合”就是“是”(Being )之本意。换言之,“是”(Being)集合着一切:在场的,不在场的,显现的,隐蔽的,而且这一切是无穷无尽、没有止境的。语言言说着这无底深渊的一切[5](PP163—218), 同时也言说着存在者的真正内涵——言说着存在者之所是。但是,我再重复一句,它并不需要某个具体对象或某个概念。正是在这种意义下,没有任何可能的感性对象的“直观在场”的语言,仍然是有意义的。[4]
其实,诗的语言之不同于非诗的语言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容许甚至偏重无直观在场的语言的意义。李白《秋浦歌》之十五:“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三千丈的白发显然没有直观在场的可能,但它把不在场的、隐蔽的愁绪生动具体地展露(显现)出来了,鉴赏者通过“白发三千丈”,可以在不在场的无尽空间中驰骋自己的想象而玩味无穷。叶燮的《原诗》曾举杜诗“碧瓦初寒外”、“晨钟云外湿”等诗句为例,生动鲜明地说明了不符合概念的语言亦可以有丰富的意义。且花点篇幅节录其中两段以见叶燮的分析之精彩:“‘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论之,言乎外,与内为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内外界乎?将碧瓦之外,无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气也,是气也,尽宇宙之内,无处不充塞,而碧瓦独居其外,寒气独盘踞于碧瓦之内乎?寒而曰初,将严寒或不如是乎?初寒无形无象,碧瓦有物有质,合虚实而分内外,吾不知其写碧瓦乎?写初寒乎?写近乎?写远乎?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辨,恐至此亦穷矣。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相象之表,竟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实相发之。有中间,有边际,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当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凡诗可入画者,为诗家能事,……。若初寒内外之景色,即董、巨复生,恐亦束手搁笔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拟而得也。”叶燮这段话的意思无非是说,“碧瓦初寒外”一句若按逻辑的道理(叶燮所谓“名言之理”)分析,则于理不通,不可解(“使必以理而实诸事以解之,虽稷下谈天之辨,恐至此亦穷矣”),然这一不符合逻辑之理或者说不符合逻辑概念的语言,却诗意盎然,使人“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再举一段关于“晨钟云外湿”一句的分析:“以晨钟为物而湿乎?云外之物,何啻以万万计,且钟必于寺观,即寺观中,钟之外,物亦无算,何独湿钟乎?然为此语者,因闻钟声有触而云然也,声无形,安能湿?钟声入耳而有闻,闻在耳,止能辨其声,安能辨其湿?曰云外,是又以目始见云,不见钟,故云云外,然此诗为雨湿而作,有云然后有雨,钟为雨湿,则钟在云内,不应云外也。斯语也,吾不知其为耳闻邪?为目见邪?为意揣邪?俗儒于此,必曰‘晨钟云外度’,又必曰‘晨钟云外发’,决无下湿字者,不知其于隔云见钟,声中闻湿,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钟声与湿相联,声中闻湿,颇与德里达所谓“方形的圆”相似,不符合概念,无直观在场,然而“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叶燮由此得出结论说:诗的语言虽亦言理,但此理非“可言可执之理”,而乃“不可言之理”。“可言可执之理”,乃“名言之理”,逻辑概念之理。此种理,无诗意的人,“人人能言之”。诗人之言则为“不可言之理”或称“不可名言之理”,斯为“至理”。正是这种“至理”才能达于诗意的境界。
总之,诗的语言既可以不需要具体的某个感性对象之在场,例如“白发三千丈”,或“一座金山”,也可以不需要符合普遍性概念的东西之在场,例如“声中闻湿”。叶燮对于这两个方面的不在场作了简明的概括:他把无具体感性对象之在场的事物叫做“不可述之事”或“不可施见之事”,把没有普遍性概念之永恒在场的理叫做“名言所绝之理”或“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或“不可述”就是无具体感性直观对象之意,例如三千丈的白发就是“不可施见”的;“不可名言”或“名言所绝”就是不可用通常的逻辑概念衡量之意,例如入耳而有闻的声与只与触觉有关的湿相联,就是“不可名言”的。诗意语言的“或”或“理”,若按毫无诗意的“俗儒之眼”观之,则“于理何通”(逻辑概念上讲不通),“于事何有”(没有感性直观中的对象)?真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了。然而诗意语言之事理乃是“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例如三千丈的白发就是想象以为事,声中闻湿就是幽渺以为理,此种事理能“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此决非无诗意的凡夫俗子所能至也。
这是否意味着诗的语言是可以完全脱离世界、凭空乱想乱说的呢?不然。非诗的语言要求有“可征之事”(即要求有具体的感性直观对象),有“可言之理”(即要求有符合逻辑概念之理),这都是拘泥于“在场”的观点(如前所述,前者是变动不居的在场,后者是永恒的在场),但诗的语言是集合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的无穷尽的东西于一点而产生的意义,所以它虽然一方面不要求单纯在场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是脱离世界的,世界是由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的无穷尽的东西构成的。“声中闻湿”,以单纯在场的概念衡之,声的概念不容许有湿的概念,湿的概念不容许有声的概念,声与湿各自坚执着自己的单纯在场的特性,所以按照这种“在场形而上学”的观点,“声中闻湿”这样的语言是无意义的。但从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相结合的观点来看,“声中闻湿”则能达于“妙悟天开”之境界,此种境界就是一种对无底深渊的聆听。叶燮《原诗》中所谓“能实而不能虚,为执而不为化”之“理”,实即“在场形而上学”之理,“实”者,在场也,“虚”者,不在场也,“为执而不为化”者,执著于界定的东西而不容许有变异性之意也。与此相反的“理”,叶燮则赞扬它“至虚而实,至渺而近”。实与虚相结合,近与渺相结合,正可以说是在场与不在场、显现与隐蔽的结合。“妙悟天开”的境界就在这两者的交会处。德里达说:“语言可称为在场与不在场这个游戏的中项。”[4](P10)我想,这里所说的语言,就其本质而言,应是诗的语言。叶燮《原诗》中的话:“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注:叶燮《原诗》中的这几句话虽系出自“或曰”之口,但属于叶燮本人所赞许之列。)这里的“之间”、“之会”亦未尝不可以解读为在场与不在场的“交会处”或德里达所说的“中项”。至于完全脱离世界、凭空乱想乱说的语言,如德里达所举的例子“绿色是或者”[4], 则丝毫没有集合在场的东西与不在场的东西之意,是真正无意义的语言(注:德里达区别“方形的圆”与“绿色是或者”两种不同的语言,认为前者虽无直观对象之在场,但它是富有意义的,后者则是全然无意义的。但他主要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的。),这种语言与诗的语言毫不相干。
收稿日期:2000—05—16
标签:形而上学论文; 主体性论文; 德里达论文; 原诗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现象学论文; 胡塞尔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