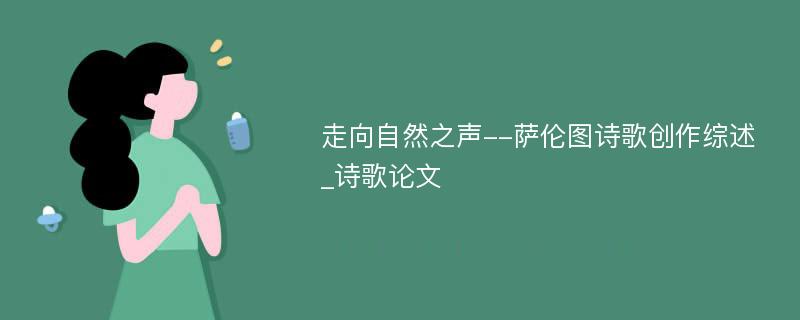
走向天籁——萨仁图娅诗歌创作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籁论文,走向论文,诗歌创作论文,萨仁图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蒙古族女诗人萨仁图娅(汉名傅月华)以坚实的脚步走上了诗坛,短短几年里她已经出版了《当暮色渐蓝》、《快乐如菊》、《心水七重彩》、《第三根琴弦》、《梦月》第五部诗集,尚在以红山文化为抒情背景的《东方女神》与表现成吉思汗的《天骄》在创作之中。萨仁图娅初登诗坛起点就比较高,她的处女集《当暮色渐蓝》同时用汉、蒙两种文字出版,并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优秀奖。她的第二部诗集《快乐如菊》作为中国皇冠诗丛的一种,独创了抒情九行诗的形式,颇获好评。《心水七重彩》是一本爱情诗的佳构。《第三根琴弦》则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散文诗集。而列入远东诗丛的《梦月》,是表现心灵与事物心灵化的短诗集,由月亮川、草原梦、远足秋、九角枫四辑组成。从五部诗集可以看出萨仁图娅在抒情方式上的变化与发展,也可以看出它们具有各自不可取代的价值与特色。《当暮色渐蓝》标志着萨仁图娅初创阶段的特色。从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她在创作之初就非常注意多方位的开拓自己诗歌的主题思路。该诗集的五辑诗作,分别涵盖了爱情诗、咏物诗、工业诗、生活诗和政治抒情五种诗歌主题和类别。从抒情方式上它们基本上继承了我国当代诗歌在五、六十年代所形成的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抒情调,当然这里也有重内心刻画的人物速写和转向自我的爱情之章,可是,那种乐观、欢快和清新的抒情,使我们一眼就认出了它同建国后十七年诗风的衔接。八六年以后诗风的变化,我们可以从《快乐如菊》中见出,这本九行诗集标志着萨仁图娅诗风的一次新变。促进这一变化的直接外部条件则是以朦胧诗等第三代诗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潮在诗歌抒情方式和技巧上的影响。但任何一种积极的影响都不是摹仿而只能是启悟和点醒创作主体的心智。我们看到,在《快乐如菊》中,许多诗从奔放的抒情走向冷凝的智思,使之具有言外之意的意象化特征,在语言上通过省略造成空白和跳跃,给诗语一种涩味。这本意是取法现代主义,实则又取得了同中国古典诗那种从语言的涩味到意象化抒情的认同,这可能是诗人创作时所没有预料到的。在《快乐如菊》之后,萨仁图娅本可以继续发展她那种充满现代主义意味的诗风,但她却没有走得更远,而沿着她那浪漫主义的抒情方式又糅进了现代主义的手法创造了后出的几部诗集。《心水七重彩》是一部爱情的多重奏,表达了一个中年女子特有的爱的心态。《第三根琴弦》以铺陈的笔法,从人、历史、自然的宏阔时空创造了有别于《快乐如菊》那种格律体的散体诗。这部诗集也不同于其它几部诗集那种清新与秀婉,而具有了劲健雄深的男性音调。从这部诗集我们才有可能一窥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的后代所流灌的大草原那粗犷强悍的血脉。
萨仁图娅在她后出的三部诗集中奠定与完善了她的美学性:浪漫主义的古典美。她的诗尽管有《快乐如菊》那种现代主义诗风影响下的变调,尽管有对大草原和九寨沟描写造成的劲健雄浑的变格。前者因时代诗潮所致,后者因选题制约风格的客观性所致。但萨仁图娅的诗风终归离不开她的个性、教养与诗的直接承传关系。浪漫主义既是她的气质又是她对中外诗歌的承传。不过,萨仁图娅的浪漫又决非放纵无拘之情,而是以理节情之情,这种情是与她的年龄、教养相适应的。这是一个具有高尚道德教养的中年女子的深沉挚情而决非少男少女的纯情。以理节情只能产生中和之美,它不属于崇高而属于优美。因此,婉曲深秀就构成了萨仁图娅的总体风格性。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她那些最具抒情特色的爱情诗之中,而这些爱情诗又占了她诗歌总量的将近半数。
二
抒情诗中的抒情主体一“我”就是诗人的化身。在萨仁图娅的诗中,创造了一个情感深挚的中年女子“我”的主体形象。表达了抒情主体俊雄、深挚而又淳美的人格力量。歌德说:“在艺术和诗歌中,人格的确就是一切。”有多高的人格,就有多高的艺术品位。萨仁图娅诗歌的人格力量,投射在对大自然互溶互渗的交融中。反映在对民族的讴歌里,映照于对人性的深细而多面的开拓上。
俊雄不是萨仁图娅性格的本色,正如男性很难具备女性的秀约一样。但是,寻找俊雄,撑起硬朗的骨力,却是诗人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唤,于是九寨沟的风景,大草原这民族的根系,便很自然地成为诗人情之所钟,性之所依的旨归。在《诺日朗》中,诗人面对飞流直下的瀑布这一壮美的自然景观,突然憬悟道:“选择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信仰是被一种伟大蛊惑的信仰,”“与其忍受平庸驱使,不如系在一念之间追求雄壮,即使陨落也陨落得灿烂嘹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求得生命的辉煌;同时也表达了生命拒绝平庸,追求壮烈和崇高的胸襟。从人化的自然中,诗人照见了一个新的自我:“匍匐前行攀援而进,我把艰难穿越当作一次庆典”。(《黄龙洞》)这是一种乐观的坚韧;“放一只小船给我,开一页彩帆给我,带着违拗于命运的自信航进命运。”(《五花海》)这是一种一往无前的执著。然而,这一切得自观光之作的雄壮性音调,都不能与一个生于汉蒙杂居的草原边缘的蒙古女子,扑向草原心脏那种返回母族的归化感相比:马鬃飘飞的心乘风而来炽热似火/浓浓烈烈,是一种情感的颜色/弓的草原琴的草原花的草原在山的那边一片梦绕魂牵之中”,诗人以“急切”叩击大漠的心跳寻根而来”。大草原“唤起游子阳刚之力阴柔之力生命之力”。捧一掬“思乡泪,化作一腔壮志磅磅礴礴”。(《草原梦寻》)《天骄陵前》是首献给蒙古族之魂──成吉思汗的大音。诗人作为抒情主体那种俊雄的人格力量在这里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死,是庸人生命的终结却是人杰圆满的休息/天地何悠悠,牧草何苍苍/抚摸跺地为坑的葳蕤大树/谛听远古旗幡掀动号角吹响/如鼓的大漠,奔驰的马蹄踏响一部雄壮的民族史/无限的草滩,射日的弯弓谱出一曲恢宏的乐章”。此诗写得大气磅礴,投射着诗人对俊雄人格的憬慕之情。
相比之于俊雄,深挚与淳美则是这位女诗人心性的流溢和深层人格。技巧可以帮助你去完善一首诗,但只有那固有的大心和爱心才能通过诗性的智慧发散出仁和之光,去拨亮一盏盏读者的心灯。萨仁图娅有着一颗敏于爱的心性,那怕只有一阵微风抚过,就会在心湖上激起一片涟漪,发出一种绝非人为的“天籁”。它是人生最淳最真的表露。这种由真与善所交凝的人性美使她的爱情诗既大胆坦诚又蕴藉沉婉。
爱情诗是萨仁图娅诗歌中最富于个性的部分。“是月华,不是月亮/我的名字透明而清凉”。“呵,我的名字由露珠洗净/我的名字被波浪拍响”。(《我的名字》)“当你拾起/一片片月光的纱,/再用心血粘连,/就会读到我的情感”。(《我是我》)对月光的描写,成为萨仁图娅早期爱情诗的重要意象。这柔的和爱的银白圣光,映照出诗人心地的纯洁,成为诗人人格的标识与象征。应该说收入《当暮色渐蓝》集子中的早期爱情诗的情感是真挚的,但显然心态还是不够自由,在爱情和为国效劳两方面,必须要作出抉择:“相聚,一百个温暖/别离,十万个思念/然而生命的船岂能泊在港湾!”(《当暮色渐蓝》)显然这还没有完全脱离五、六十年代那种劳动加爱情模式的潜在影响。及至到了《快乐如菊》和《心水七重彩》中的爱情诗,便获得了一种驱遣自由的心态。使这些作品,写得既大胆坦诚,又深挚沉婉。
对爱的勇敢追求和坦诚的告白,是现代女子表达个性自由,实现生命价值的体现。没有这种爱的真挚,也就没有爱的淳美,在《太阳明亮在永久的天上》中,诗人唱道:“为了爱,我同时间较量/把你心植到我的胸膛。”“她”要爱个“色彩芬芳”,“她”要心中的“太阳明亮在永久的天上”。《魂结》一诗,意象精美。当爱情在心里萌动、抽芽、着花,两颗美丽的灵魂象彩蝶一样结为一体。这也许是不该发生的恋情,但“真实的星辰”已经升起,又何回讳呢?“灵魂啄破茧壳错也错得美丽!”这是一种自我心灵的率真告白。还有别一种,即向社会坦诚的宣示:“爱,只有爱才使人愿意活着/对也好错也好任风去嫉妒/朗声地告诉世界:/我就是你的夏季!”(《我是你的夏季》)这石破天惊的胆识,无疑是对蜚长流短世风的挑战。
不过,我要说,以上爱的坦白和率真,毕竟还不是萨仁图娅爱情诗独具的特色。爱情如其说是一种感情不如说是一种滋味。作为一个具有丰富人生经验和社会道德感的中年女诗人,她的爱情诗与那些表现少男少女纯情的作品的根本不同即在于:纯情诗着意于爱的情感抒发,那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甜润和单纯,而萨仁图娅的爱情诗则着意于爱的多重滋味曲色,那是一种中年人成熟的人生百味渗透。它深挚沉婉,象佳酿陈酒,淳味绵延。其实,这种诗并不拒绝大胆,只不过它往往并非直接抒情,而是借助象喻,婉曲表意,更觉动人。如《见你,刚好是秋天》,女主人公既赞美了“你象大地一样充盈和丰实”的品性,又暗示对方“虽然错过了播种的时节”,但并没有影响爱的丰收。“我是田野一株豆荚/爱的籽粒饱鼓鼓地装满/为了大地的成熟与期待/情愿把自己的秸杆点燃/为什么你不操收获的银镰/秋,对你另有一番内涵”,在婉曲的表白中隐含着向对方爱的“攻势”,正是该诗的妙处。
爱的深挚人格,还特别表现在对恋人的忘情思念。“醒也听见梦也听见/你名字化作金线银线/把我不羁魂灵绕缠”。这奇特的比喻,神秘而美丽,照彻了爱的历程:“风是过去的雨淌汇成湿润的呼唤。”(《不相信情思曲曲弯弯》)今风昔雨,旧情新意,都化着“湿润的呼唤”即含泪的呼唤。这种深挚的苦恋,何啻社鹃啼血。爱的苦恋,可以达到不能自持的地步:“在我和生活之间/你就是一池沼潭/无论怎样挣扎也免不了下陷”。(《在我和生活之间》)这种爱的不能自拔和投入又会无意识间迷失了自我:“你如同一本书掀开序言/读你居然弄不懂了自己。”(同上)看来只有这种沉湎的境界才是爱的高峰体验,舍此,就难有爱的深挚。
从以上爱情诗不难看出,一个具有深挚、淳美人格的女抒情主人公,或率真坦诚,或沉婉缠绵,给我们以不同的审美感受和人格力量。
三
从放纵与收敛情感的矛盾中获得诗的强力,以智即理性作为情感的节制,完成着从情到智的渗透,并带来从滑到涩的诗语的转换,最后达到浪漫主义的古典中和美的创造。这说是萨仁图娅的诗歌艺术构成与发展。
萨仁图娅的诗歌在情感上有大胆放纵的一面,这我们在上述爱情诗中已作过分析。她的诗明朗、清新、热情而充满理想,很注重情感和想象,这都使她的诗更具浪漫主义色彩,但是她的诗多受理智的约束,情感常常被形象所包裹,形成了意象,充满了多层意味又具有以理节情的古典中和之美。
萨仁图娅有效地利用了社会道德感和女性羞涩感,这两个理性调节器,让情感之水纡回曲折地得到隐含的流泻。创造出一种言之不尽的沉婉之美来。
在《造虹的云中你飘来》中,萨仁图娅写出了中年女子之恋的复杂心态:“造虹的云中你飘来/意志是我却也凭添许多痛苦/纵然悠长的岁月发出疑问/也无法把心之窗修复”。意志本来是用以节制感情的,但愈制节反而更“凭添许多痛苦”,即使岁月越长,“心窗”却无法修复。由于意志和理智使感情具有了弹性,具有了放纵与收敛二者矛盾所显示的多重思索,这个中年女子站在传统与现实的临界线上不禁发出了这样感伤凄艳的叹惋:“我知道我是女性未免缠绵/走出峡谷心灵枝条抽出惶怵/传统与现实的交融中形成站立的自己/不知该如何扳回太阳的斜度”。人到中年,是否应该有爱情?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在感情和理智之间,未免惶怵。这是一种爱的复调,虽然缺了那根和弦,却只有苦恋中的不等不忿!在《昨天往事是一枚橄榄果》中,那个惶怵的女子,终于不顾“生命之钟摆过不可重拨”,决心要追回往事里那枚“青青橄榄果”,要去“体味背负传统行囊的沉重跋涉与探索”。而此刻心已从传统道德的束缚下逃逸:“那很远很远不设防世界充满诱惑/走去!共同完成一个心跳的选择”。就这样,情感在理智的控制下,一张一驰地流动,每一次情的被遏制,反而又为情的重新爆发蓄足了冲力。这既是诗内在张力不是靠技巧完成的,而是依其内容本身实现的。
当然,控制情感的理智,并非总是由道德感所致,理智也可以是对爱的逆向思维。如果说形影不离有可能酿成爱的过于甜腻或失败,那么,适当保持爱的空间距离,反倒会使爱在若即若离中两心相吸,时空距离所引发的心理距离是爱的美感的成因。萨仁图娅恰如分寸地悟透了这爱的个中三昧:“距离虽说不是难言的苦恼/可谁知苦恼蕴含的微妙/一旦宇宙骤然缩小没有了距离/千百度直接辐射难免会焚烧”。(《爱在两步之遥》)“爱与被爱”最好“款步在两步之遥”。何其巧妙地选择!有间距才有两心相吸的魅力,这又是一个以理节情产生诗的内在强力的好例。
羞涩的遮掩往往使爱变得更动情更婉曲美丽。羞涩使女性在表达爱的方式上变得含蓄遮掩,留下许多美好的想象。羞涩感便是放纵与收敛情感的背反心理,它使爱情诗在创造陷于爱情旋涡的女性淳美心态上显得楚楚动人。《即使我流泪了》这样写道:“即使我流泪了/也不要笑我软弱/你知道我,知道我/努力拒绝诱惑无法拒绝诱惑”,从春到秋,“坐穿孤独我依在你肩头/别飞出那个字别问为什么”。这儿活画出一个初恋女子的心态。“努力拒绝”又“无法拒绝”正是在这一悖谬中,使压抑的感情产生一种反推力,迸发出灿丽的火花。同样在《我是幸运的迷路者》中,那个偷食伊甸园禁果的女子,“依照其实的感情”,默默地把一颗爱心献给自己的恋人。“把最怕的最希望的给你/什么也没说什么都说过”。大概眉目的传情,行动的暗示,是最含蓄的表情方式吧。“什么也没说”又“什么都说过”又是一个悖谬。萨仁图娅是极善于表达热恋女子这种含婉、深挚心态的。这种独具的特色,几近成为她在表情方式上的专有。这里的情已不再是放纵的直抒胸臆,如她早期那些政治抒情诗和生活诗那样,也不大同于前述那些大胆坦露心曲的爱情诗那样直接,而是充满了意味的情。它已经化意为象,通过意象抒情,而获得了理性积淀。
当今的爱情诗至少有这样三种表现形态,即以林子《给他》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以穆旦的《诗八首》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和以席慕容的《七里香》、《无怨的青春》和《时光九篇》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萨仁图娅早期的爱情诗比较接近浪漫主义的林子,而她的《快乐如菊》所收爱情诗又比较接近于新古典主义的席慕容,直到爱情诗集《心水七重彩》使我们看到了一种浪漫主义的古典美的形成。所以,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就做了萨仁图娅爱情诗的两种培养基,也可以说成为她整个诗歌主流的基本美学特色。浪漫主义侧生于“情”:“只要你要,我爱,我就全给,/给你—我的灵魂、我的身体。/常青藤般柔软的手臂,/百合花般纯洁的嘴唇,/都在默默地等待着你……爱/膨胀着我的心,温柔的渴望/象海潮寻找着沙滩,要把你淹没”。(林子:《给他》,第一辑第33首)这种诗的优势在于真挚坦诚的抒怀,但缺乏咀嚼的回味。现代主义侧重于“智”,即理性:“你的年龄里的小小野兽,/它和春草一样的呼吸,/它带来你的颜色,芳香,丰满,/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穆旦:《诗八首》之二)这种诗的特点在于通过隐喻和暗示,引发一种象征性的多重感受,但弄得不好容易走向晦涩。新古典主义赋予爱情以道德感又颇富传统古典诗词的典雅韵味,这是一种以理节情的中和美:“如果能在开满了栀子花的山坡上/与你相遇 如果能/深深地爱过一次再别离”,“那么再长久的一生/不也就只是 就只是/回首时/那短短的一瞬”。(席慕蓉:《盼望》)可以说席慕容的诗能够获得众多的读者,主要在于她的诗以意象抒情带给读者的那股淳味。萨仁图娅是很得席诗真传的,不过,她又很不满足于席诗那种与时代有点隔的传统典雅味儿,而融入一种现代人的理想浪漫气息,正可作为一种补正。
萨仁图娅诗歌的抒情方式,以爱情诗为重点,经过了两次嬗变,第一次是从她的第一部诗集《当暮色渐蓝》那种浪漫的抒情转向第二部诗集《快乐如菊》那种冷凝的智思。即从外部情感的奔放转向收敛,并走向内部情思的深化。她的本意也许在于取法于现代主义,而她也确乎在现代主义诗风影响下使自己的诗路发生了新变,然而也许是席慕容的诗启发了她,使她的诗又特别接近于台港诗歌从现代主义回归民族传统的新古典主义风味。我们来看看这首收入《快乐如菊》中的九行诗:“相逢因了相同的梦/发如帆去赴约会/灵魂在腿上脚上亦梦非梦/你到底等了多久风/在我的夏天吹了很短的一瞬/我们的历程是红帆船的历程/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一万个秘密如星叠叠重重/月亮剪辑的情节很生动。”这首诗同她充满浪漫气息直抒其情的早期诗相比发生了重要变化。且不说诗体的凝炼、精短,即以表现方法论,主要采用了隐喻和象征的意象抒情方式,语言也变得由滑到涩,情转化为智,诗语的省略,造成了诗意的跳跃与空白,增强了理性的思索。千年宿缘其实就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你到底等了多久风/在我的夏天吹了很短的一瞬”。这种从感觉层次直跃到智性层次而省略情感层次的手法,是化情为意,它将外张的情感变为内聚的意象。“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一万个秘密如星叠叠重重”这不仅指出爱的必然,也道出了爱的美丽如星花灿烂。最后一句:“月亮剪辑的情节很生动”。看似与全诗脱节,却妙趣横生,原来,月老已将爱的全部秘密都偷窥了去。其它如《你目光落地的声音》运用了通感:“你目光落地的声音激荡/我抑郁几个季节的眼帘/从九月来你从秋天来/灿烂的笑明净我游云飘忽的天”。通感和词性的活用,都增强了这类诗从前期浪漫的热抒情到后期现代的冷抒情的特点。总之,这种抒情方式的变化有得有失,得多失少。也许正是分析了这种得失,萨仁图娅才在《第三根琴弦》和《心水七重彩》中,使自己的诗歌抒情方式来了第二次转变。这次变化很明显,既是对她早期浪漫主义诗风的复归,又是对《快乐如菊》这种现代主义或者古典味的现代诗风的重构与改铸。首先可以说,《心水七重彩》中的爱情诗,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是一种浪漫气息很浓的,以理节情的古典中和之美的创造,它既非崇高(客体压倒主体),亦非滑稽(主体压倒客体),而是优美(主、客体的融合与互渗)。
萨仁图娅的诗经过两次嬗变,今后还将增生新的变化。但她毕竟找到了自己得心应手的抒情方式,有些抒情特色是她独创的,这已经够了。
萨仁图娅是新诗格律化不可多得的追求者,她在新诗的视觉形式美和听觉的音乐美方面所做的多方面实验,应该专题论述,这里只好简要加以概括。
新时期以来,新诗在恢复自身和推动整个文学的诗性水平上是起了率先作用的。今天,当各种文学品类已获得普遍的诗性时,诗歌已经不能再漠视对自己固有文体特色的追求了。诗歌必须具有诗性,但它还必须具有区别于其他文体的视觉形式美和听觉的音乐美,这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新诗的格律化去完成。将强大的诗思安放在诗的固有形式中,让诗在限制中获得自由。萨仁图娅通过格律化的实践,同前辈的大诗人取得了共识。以形式的视觉美而言,她在自己的诗中基本做到了闻一多先生所提出的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当然,她排斥了那种死板的豆腐干形式,却取得了诗的矩型和凸凹型为基准的多变形式,给视觉以美的构图。在建节上,她实验了从两行到七行为一节的多种形态,在押韵上她实现了几乎让每一首诗都押上尾韵,又因其诗写得比较精短,多为每首两、三节或三四节。这样,对那些短诗,基本上可以做到易记,甚至能唱。这对于克服新诗不易传播无疑是个推动。诗歌只有具有韵律和音乐美才能插上翅膀飞遍千家万户。我特别要提到萨仁图娅在《快乐如菊》中所独创的九行诗。这本诗集的76首诗,全部为带韵的九行诗。它需要多么刻苦地精心制作!为什么是九行,而不是更多或更小,这除了经验的积累变为有意的选择,还因为“九”是蒙古族最完美最吉祥的数字。我国有四行一节的传统新诗体式,又有移植于国外的十四行体,现在,这种九行体。无疑又增加了新诗表达的活力。总之,新诗易精,不易散。萨仁图娅这种种格律化的探索,自然往往还带有不成熟的胎痕。但她对新诗格律化的自觉追求令我赞叹。
萨仁图娅是一位本色诗人,她的诗的魅力,不是来自外在技巧,而纯属那一颗敏悟的心性。技巧对她很重要,但是那种发自淳美之心的“天籁”,永远是对一位诗人最初也是最后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