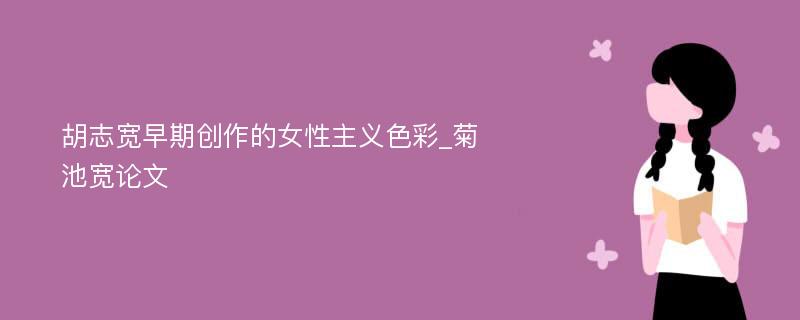
菊池宽前期创作的女性主义色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色彩论文,女性主义论文,菊池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作家菊池宽(1888-1948)的文学生涯跨越大正、昭和两个年代,创作量大,倾向驳杂,但其女性题材居多,尤其是在前期(1927年以前)创作中,表现出对女性命运、权利、性格的热切而深入的关注,呈现出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
女性中心世界的重构
由于四面环海的自然环境等诸多原因,日本远古时期的母系社会较之许多内陆地区都要固着、绵长得多,这一特定的历史形态给日本文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日本神话里就留下了女性中心世界的原型。譬如日本的太阳神天照大神就不像大多神话体系那样属男性神,而是一位温馨慈爱的女性神,并且她不是作为男神的配偶、从属、陪衬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独立不倚、至高无上的主宰神而存在(注:参照叶舒宪、李继凯:《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与儒学等男权社会文化的渗入,女性中心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已属隔日黄花,女性在文学中的地位也是每况愈下,到了江户时代,对女性的崇拜与依恋已经退居到潜隐的心理层面,而在作品的叙事层面,几乎尽是对女性的把玩与狎弄。女性由远古的神到近世的未能得到人之待遇的物,岂止是一落千丈,简直就是霄壤之别。
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勃勃生机,也给日本女性的解放带来了希望。1871年10月首次派遣女留学生赴美,1872年4月设立东京女学馆,同年10月宣布解放仆婢娼妓、禁止人身买卖,1884年6月《女学新志》创刊,1886年6月甲府雨宫制丝工厂女工罢工,1887年2月大日本妇女教育会创立,1890年3月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立,1901年4月日本女子大学成立……女权运动的渐次展开,给女性在文学中地位的改革带来了契机。女小说家樋口一叶以饱含热泪的笔触描写底层社会女性的凄楚命运,女诗人与谢野晶子在诗中大胆、率直地抒发觉醒了的女性心声,森鸥外、德富芦花、夏目漱石、田山花袋、岛崎藤村、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谷崎润一郎等男性作家也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切入了女性主义文学,其中对此关注最为持久、投入精力最多、开掘较为深入、因而最有代表性的当推菊池宽。
作为京都帝国大学英文专业毕业生的菊池宽,良好的英语能力与勤勉的翻译实践使他更易于接受西方人道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影响。他对女性的命运格外关切。小说《岛原情死》的女主人公锦木为生活所迫沦落风尘,在泥淖中挣扎十年之久竟然还挣不够赎身钱,连母亲生病也不能回乡探望。她与来往过几次的男子一起自杀,与其说是情死,毋宁说是另有涵义:一则在丧失了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爱情权利的生涯中,以死亡的代价自由地选择一次浪漫而虚幻的爱情形式,用以慰藉痛苦而枯涩的心灵;二则藉此得到彻底的解脱;三则权作对社会、对老鸨的最后的反抗。但她死后仍未能摆脱老鸨的盘剥,身上的唯一饰物——戒指,也被老鸨从冰冷的手指上摘去。《岛原情死》实在不是一个如题所示的浪漫传奇,而是女权(自尊、人身自由权、恋爱权、经济权等)横遭剥夺的写实悲剧。剧本《公论》中女主人公的惨死,不仅是所谓公论对个性自由的无情吞噬,而且也是男权对女权的粗暴践踏。这位容姿楚楚的美女即使出身于贵族,也未能免除买卖婚姻的厄运。五个金刚钻加上六颗黑珍珠,她就被代表家族权威的兄长卖给了富有而年迈的行商。同是贵族的子嗣,兄长品味的是获得珠宝的喜悦,妹妹却要咀嚼卖为人妻的苦味。说是人妻,其实倒更像买来供作欣赏的动物,为了防止她走脱平素脚腕上总要锁上银锁链。当看到她拖着银锁链唱着向往自由的歌时,看客还能对她寄予同情。可是,当她真的如歌中所唱,抛弃了金钱铸成的虚伪之爱、找到了心爱的年轻伴侣时,看客却转而对她恶语相向,进而忿然投石,直至将她打死。公众的价值标准归根结底还是倾向于男权,这位美女尽管有过挣扎,也确实争得过幸福,但终于倒在了无所不在的男权打击之下。
比起悲剧命运的描写,菊池宽倾注心血更多的是对女性魅力的探索与张扬。在表现女性魅力方面,日本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说。菊池宽对太阳女神的强力情有独钟,对中世文学中女性的柔顺性与近世文学中女性的媚俗性则不予认同,他所认可与张扬的是美妍、强力与性感融为一体的现代女性魅力。展示现代女性魅力构成了菊池宽作品的一道美丽风景。《珍珠夫人》里信一郎的新娘静子,石竹色般红润的脸蛋儿,秀气的樱唇,整个容貌浮现出半羞半喜的风韵,足以让新郎怜爱不尽。可是当瑠璃子出现在信一郎的眼前时,他立刻觉得自己所认识的女性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和这位女子媲美。她不仅姿容出众,而且眸子里闪烁着理性的光辉,她的身段、作派、面庞、眼神,显示出日本现代文明才能产生出来的美和神韵,又让人觉得她的背后若隐若现地发射出光环,那种压倒别人的威严很容易使人想到太阳女神,也许作者在创造这一形象时脑海里确曾浮现出大和民族顶礼膜拜的天照大神影像。在有的作品里,现代女性魅力分解于几个人物身上。《结婚二重奏》里,扶美子清纯而稍嫌怯弱,弥生浮躁但充溢着进取精神与火辣辣的性感,结果是后者率先赢得了立花芳雄的爱。尽管作者在理性上对强力性格的负效应有些担心,因而每每设置一个或两个对照性的人物,试图藉助传统的贞淑娴静来予以调和缓冲,但在他的人物群像中,最有光彩因而给读者印象最深的还是强力性格,这里大概就有太阳女神这一文化原型在起作用。近世传统型的柔顺性格则予以否定性的处理。譬如《再和我接个吻》里的倭文子,一味退让隐忍,甚至当后来误会消除、意中人村川来到她身边、二人可以远走高飞时,她还是瞻前顾后,忧虑重重,最终拖着村川一道投水。这一选择,与其说是殉情,毋宁说是避世,她所恐惧的东西太多,既怕惹上官司当证人,更怕回到有意招村川为婿的舅舅家,与嫉恨她的表姐京子相处。缺乏坚韧的生存意志,即使有温馨的爱情来抚慰,也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可言,甚至连生命本身都要白白地葬送掉。作者以冷静的笔触刻画出倭文子的性格弊病,以否定的形式发出对太阳女神性格的呼唤。
在菊池宽的许多作品里,女主人公无论是刚毅还是柔顺,无论是善良还是邪僻,都是名符其实的叙事中心:不仅是情节结构的中心,而且是感情指向的中心。《珍珠夫人》里,众多男子像众星捧月一样围着瑠璃子转,庄田胜平只得到了丈夫的名份而没有获得丈夫的权利,青木兄弟以及其他男子甚至连个口头上的许诺也未得到。如果说无论是瑠璃子这一本名,还是后来以她为模特的肖像画题“珍珠夫人”,都与天照大神的光有某种潜在的联系的话,那么,她的美艳吸引了众多男子而谁也不能如愿,这一点又很容易让人想到日本最早的传说《竹取物语》。传说的女主人公赫映姬因在竹筒中发光而被发现,三个月便长成一个姿容艳丽、光彩照人的美女,美名远播,惹得求亲者络绎不绝。其中石作皇子等五位显贵最为殷勤,也都很自信,但均被赫映姬用难以通过的考验拒之门外。当朝皇帝欲接她入宫,甚至为此派重兵试图抵抗上天来接赫映姬的使者,也还是无济于事,赫映姬最终留下不死药和告别信,飞回月宫去了。瑠璃子不是月宫仙子,自然没有什么不死药,但她把名义上的女儿——纯洁善良的奈子托付给了自己的情人直也,暗示着把纯洁的爱情留给人间,这又多像是月宫仙子之所为。《结婚二重奏》、《再和我接个吻》等作品中,不像《珍珠夫人》那样众多男子围着一个女性转,但男子为女性的魅力所吸引,女性的态度成为推进情节的原动力,也就是说,女性处于叙事中心这一点是共同的。
在女性中心世界里,延续了千余年之久的男性权威遭到了颠覆。《源氏物语》里男主人公那种朝秦暮楚、任性恣情的所谓风流潇洒,在这里受到了无情的嘲弄,《好色一代男》里男主人公居高临下、玩弄女性的放浪不羁,在这里遭到了痛彻的鞭挞。剧本《妻》的男主人公带着素有交往的艺妓去海滨旅馆,想以情死的话题试试艺妓是否对他有真情,以解除他对艺妓与另一男子关系的疑虑。这边暂且释然了,可是男主人公写坏了的遗书信封与带走手枪之事,却让妻子惊恐万状,到处挂电话追问丈夫的行踪,又托丈夫的朋友追到海滨旅馆来阻止情死。男主人公闻讯一面斥责妻子愚蠢,一面为妻子的挂虑而动心。艺妓见此不禁意兴索然,对他大加嘲讽。艺妓的伤感与忿怒,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性爱嫉妒,而是觉悟到男女不平等制度下自身的可怜与浪漫行为所包含的荒谬。是啊,一个心里装着妻室的男人,有什么理由去以所谓情死试探艺妓的真心呢?小说《羽衣》借用人仙相恋的传说题材表现对男权予以消解的现代主旨。渔夫伯龙英俊而贪女色,喜新厌旧的本能在他身上不加压抑而得到恣意流露,无论对什么女人都没有长性。同居半年,失去了对秘密的好奇,过了一年,了无乐趣,连了二年,便觉得讨厌得无可忍受,于是,便休妻另娶,几年之间,他休了四个妻子。他已经对结婚失去了兴味,对于慕名而来的女子只不过逢场作戏而已。有一天他得到了天仙的羽衣,以还羽衣为条件,与天仙订了三个月的婚约。以前的人间女子为妻,伯龙从来不必担心烧水做饭一应家务,而如今天上仙女为妻,除了给他以观感与性欲的满足之外,家务却水火不动,到了第二个月,伯龙就已经耐不住了,等到三个月期满,天仙终于上天去时,伯龙已经患了很重的神经衰弱了。天仙下凡,仿佛是代表女性世界来惩罚向来不知责任与道义为何物的男人似的。
自从社会的主宰由母权让位给父权以后,逐渐形成了关于男人性格的种种神话,譬如宽宏大度、坚韧刚毅、富于理性、责任感强等等,相反,则把小器善妒、柔弱胆怯、感情过剩、水性杨花之类贬名加在女性头上。生理结构的不同确给男女两性在心理特征上带来一定的差异,但其文化性格大半还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母系社会里女性的性格如何,现在缺乏实证性的研究,但从远古神话保留下来的吉光片羽来看,后世男性“神话”的种种优点加在女性身上决非过誉。菊池宽在他重构的女性中心世界里,在大力弘扬女性魅力的同时,对种种男性给予消解。崛田(《新珠》)把别墅的一套房子让给筱崎遗属居住,助人行义是假,嗜女猎艳才是真,冠冕堂皇的新潮婚恋观不过是骗人的幌子,不厌其多地占有异性才是其真实目的,如此男性,何言正直、明睿?立花芳雄(《结婚二重奏》)到底抵不过弥生的诱惑,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一失足成千古恨,何言理性、定力?藤十郎(《藤十郎之恋》)为了排演新戏体验角色,也夹杂着品尝一下偷情快感的好奇,在茶室里对女主人梶娘倾诉他“压抑了二十余年的深爱”,虽是艺妓出身但素有贞淑令名的梶娘先是感到意外,继而内心纠葛得全身发抖,终于燃起炽烈的情焰,以赴死般的决心吹灭绢灯,应和藤十郎的爱的呼唤。然而藤十郎却影子一样擦身而过,致使梶娘不堪侮辱与内心折磨而忿然自杀。藤十郎演出成功了,又自我安慰说:“为了藤十郎的艺术,一两个女人的性命算什么”。如此男性,何言责任感?丧妻一年多的木村健吉与早年的意中人秋山富枝邂逅(《温泉场小景》),因与丈夫感情不睦而离婚的富枝多么希望健吉能够重新唤起早年的恋爱激情,可是健吉却因怀疑富枝离婚后四五年间的贞操而托辞拒绝。如此卑琐、狭隘,有何宽厚大度可言?相比之下,富枝追求幸福的主动、热烈,则让人感受到太阳女神的余韵。
日本文化性格自然色彩较浓,裸体禁忌、性禁忌在儒文化影响圈中相对松弛,贞操要求也不似中国宋明理学所苛求的那样严酷。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接吻本不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但在菊池宽的不少作品中,即使到了倾慕不已、两情缱绻之时,女性却要拒绝男性的初吻,譬如扶美子之于立花、倭文子之于村川等等,这在今人看来显得不近人情,在当时的日本读者中也未必能够获得广泛的认同。作者之所以做出如此设计,不能排除一波三折、推进情节的考虑,但也含有女性主义的动机。有史以来,贞操禁忌主要是给女性设定的,对男性则网开一面,男人看中了哪个人,别说是亲吻,再深入的性接触也由着男人的意愿。而在菊池宽笔下,女人在没有产生身体接触冲动之前,决不委屈地接受男人的亲吻乃至更进一步的要求。这里诚然有少女的羞涩、矜持,但主要的还是出于女性自尊、自主的个性觉醒,她们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而不肯再做由男性任意摆布的偶人。这样,她们也许会阴错阳差地失去某个良缘,但能够清醒地把握自己,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女性中心世界作为一种历史形态,早已是黄鹤不知何处去。但在走向男女平等的合理美好的社会的近、现代化进程中,为了消解延袭数千年的男权影响,促进女性的解放并充分发挥其巨大的创造力,借取女性中心世界的原型,重构一个女性中心的文字空间就有了历史合理性。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菊池宽前期创作中,女性的目光与精力极少投射到工作权的争取上面,只有扶美子在大学毕业后曾经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翻译,婚后便与其他女性一样回到传统的丈夫出外谋生、妻子困守家庭的生活模式里去了。殊不知离开丰富的社会生活,离开工作权及财产权的获得,就不会有女性的真正解放,也不会有真正的男女平等。
复仇女神的再生
在古希腊神话中,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之所以被设定为女性,恐怕不是源于男权社会派定给女性的性格特征——善妒、阴冷、易记仇等等,而是起因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嬗变之际,女性权威受到严峻挑战,女性利益蒙受严重损失,女性为此而在想象世界里创造出一个母系亲族与女性权益的保护神。厄里倪厄斯的性格是暴戾的,一旦伤及她所保护的利益领域,必然激起惨烈的复仇。美狄亚为了爱情,别父杀弟,颠沛流离,可是竟然遭受伊阿宋遗弃,怎能不激起她的万丈怒火,于是便有了杀死新娘及其父甚至还有美狄亚的两个亲生儿子的惨剧。日本神话里的女神则没有如此严苛、酷烈。当弟弟连须佐之男命因不满于权力分配而要加害姐姐天照大神时,这位太阳女神也不过是借助八百万天神的干预,让连须佐之男命拿出赎罪物,并罚他割去胡须、拔掉手指甲和脚趾甲,然后把他赶走,以此了结了一场颠覆统治权的要案。当然,如此宽待,也许与当时女权尚未受到根本性的动摇有关,等到后来在现实社会里男权终于取代了女权,神话时代已经过去,女性宽厚、温柔、克制的性格已经作为文明初始期的文化积淀留存下来。所以,不仅在日本神话里找不见厄里倪厄斯式的神祇,而且在直到近代以前的文学史上,也没有美狄亚式的性格。《源氏物语》里,六条妃子对源氏所代表的男权反抗要算得上最为激烈了,但也不过是让自己的“生魂”出窍,去伤害她认为妨碍她专有源氏之爱的情敌,她至多不过是让“生魂”加速了情敌的死亡,而并未像美狄亚一样杀得天昏地暗,辞世之前,她不是希望女儿继承她的复仇意志,反而托孤于源氏,希望女儿将来以处女终其身从而避灾祸。六条妃子是把怨毒倾在同性身上,髭黑大将夫人则把愤怒直接指向男人,将一炉香灰扣到即将外出幽会的丈夫头上。即使如此柔弱的反抗,也只能在装痴作颠的假相下才敢偶一为之。
日本女性即便温柔,驯顺,也不会永远默默忍受男权压迫的屈辱与痛苦。积郁和复仇的火山终于在近代文学中喷发了。先是借助德国姑娘爱丽丝的发疯(森鸥外《舞女》)来控诉日本男权主义的罪愆,继而通过阿通与仇人的同归于尽(泉镜花《琵琶传》)向践踏女性感情的男权代表者复仇,接着又在夏目漱石的《我是猫》对性别歧视的反讽,有岛武郎的《一个女人》对男权世界的自觉复仇,等等。但就单个作家而言,对女性复仇主题有着持久的兴趣、在复仇题材的展开上有着宽广的疆域的,当首推菊池宽。
《结婚二重奏》里的扶美子应该说是富于个性的近代女性,女子大学毕业后,专攻英国文学,不甘于在家吃闲饭,从事一些翻译工作,从中品出了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兴味,而且决心毁弃不理想的口头婚约,与所爱之人走到一起。可是,当恋爱遇到挫折、意中人被其他女性捷足先登时,她的报复方式既不是伤害夺其所爱的竞争者,更不是直接伤害所爱之人,而是让自己平淡地移情于别的男性。这对于一直爱着她的立花芳雄来说的确是一种报复,但其日本女性的温和味道未免太重,并且报复的快感远不如自虐的痛感来得迅疾而沉潜。《新珠》里的烂子要比扶美子更具现代风采。崛田子爵虚伪的甜言蜜语先是送给瞳大姐,占有肉体的欲望受挫后又转向都二姐,欲望满足之后又把渔色的目光对准了三妹子。大姐被迫出走,二姐怀孕遭弃,当烂子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心里愤怒得好像要炸开一样,眼睛里燃起强烈的复仇之火,少女美丽的面容,凭添一种凄厉的表情。她佯诈喜欢子爵,实欲施行复仇。子爵玩弄女性的身心,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步一步诱敌深入,就是不给他吞食的机会,一拖再拖答应求婚的时间,直到约定的最后时间,给了他一个出乎意外的否定性回答,替两位姐姐与那些侮辱受损害的女性给予这个色魔一个辛辣的报复。尽管《新珠》作为菊池宽创作通俗小说的尝试,人物性格尚嫌单一,情节推进斧凿痕迹明显,但烂子那颗“女妖”似的复仇之心以及由此而来的凄厉之美则给日本文学的女性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
若单论报复性的人物,《再和我接个吻》里的京子要比扶美子强悍得多,报复心更重,手段也着实毒辣,伪造信件,设置“陷阱”,等等,必欲击败对手而后快。诚然,她仅仅为了缺少感情基础因而得不到呼应的性爱嫉妒就闹得天翻地覆,未免显得狭隘、苛刻,但是她的抗争乃至报复颇有可爱之处。村川在夜色之中误把京子当作倭文子热烈接吻,当发现原系误吻之后便后悔不迭,急欲抽身,可是在京子一方则是正中下怀,且穷追不舍。她大胆剖露心迹,并在热情激荡之中表示,之所以爽直地承受村川的接吻,正是出于爱他的缘故,若是据此就把她当作贱货,当作一时的玩具,那么,就要用各种手段来报复。这不啻为近代女性自尊、自爱、自卫的宣言。当她得知村川之吻原来竟是一场误会,便一面打起贞的旗帜,义正辞严地讨伐村川,一面苦苦请求,祈望与他结为百年之好,当遭到彻底拒绝之后,发誓无论怎样下贱卑劣也要报这一箭之仇。以接吻为爱情的凭证,一旦接吻就必须“从一而终”,否则便不择手段地施行报复,这种逻辑不无偏颇,报复的毒辣也为人所鄙,但京子火辣辣地表白自己的爱情衷曲,锲而不舍地追求爱情目标,寸步不让地维护女性尊严,从酷虐的报复中品味快意,这种性格则闪烁着近代精神的光芒,对传统女性的被动、驯顺、隐忍、退让、自虐性格不失为一种矫枉过正的弥补。对于这样一个人物,菊池宽在作品的道德层面上确有贬抑之意,但在作品的整个精神结构与艺术结构中,则将其置于中心地位,充分展示其性格魅力,揭示其作为新派女性向男权挑战、复仇的合理性,并于字里行间常常流露出欣赏、赞叹之情。在男权社会,京子之所为若放在男性身上,实在是司空见惯,不足为怪,一旦放在女性身上,则显得惊世骇俗,不可容忍,这本身就说明人们心中的女性模式带有多么浓厚的男权色彩,男女不平等在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中是多么的严重。京子反其道而行之,以偏激的形式表露出女性的不平之气与忿怒之火,菊池宽也借此显示出自己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女性主义立场。
复仇意绪是女权运动中刚刚觉醒的女性极易产生的情绪,就女性的长期受压来说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合理性,但若任其发展,反倒会妨碍女性心灵的健康成长与女性权利的合理获取。《珍珠夫人》就以充满张力的艺术建构深刻而生动地表现了复仇的二重性。
女主人公瑠璃子本来是心地纯洁、性情温和的少女。她与情人杉野直也在私下谈话中对暴发户表示了轻蔑,没想到被暴发户庄田胜平听到,招致了一场心狠手辣的报复。庄田胜平先是以30万元礼金的价码,向唐泽男爵提亲,要娶18岁的唐泽瑠璃子小姐为继室,遭到拒绝后便买下唐泽家的全部债权,频频逼债,然后设下圈套,将一幅名画假托他人之名寄存在唐泽家,诱使在债务逼迫下一筹莫展的唐泽男爵典卖名画救急,随即告到法院,将素有廉正清明之誉的唐泽男爵推到身败名裂的绝境。庄田胜平仅仅受了一点精神创伤就挥起黄金利剑疯狂报复的行径,在瑠璃子的心里激起了强烈的愤怒与狂热的复仇欲念。她想到了牺牲贞操、刺杀敌将、拯救全城的犹姬,决心效仿犹姬,以女性的美丽与智慧向庄田复仇。纯洁的心地因猝不及防的突变而深沉,温柔的性格因忍无可忍的迫害而强悍,单纯、纤弱的少女骤然间俨然成为凄厉而执拗的复仇女神。新婚之夜,她便借故回娘家,而后虽然重返田宅,但每天都以青春与美艳撩拨着庄田45岁正当壮年的欲火,却千方百计拒绝他行使所谓丈夫的权利。在叶山别墅那个暴风雨之夜,精心策划、自以为得计的庄田在欲施强暴之际,被白痴的亲生儿子扼颈致死,这意外的惨剧不能不说是瑠璃子刻意激起父子嫉妒的必然结果。瑠璃子冒着闺名受到玷污、贞操随时都可能被夺去的风险与庄田结婚,为的就是复仇:第一是向暴发户与金钱万能观复仇,证明金钱决非可能、金钱买不来爱情;第二是向男权主义传统的因袭势力复仇,表明女性的尊严与自由决不容许肆意践踏。在这场深入虎穴的复仇智斗中,瑠璃子历尽艰险,终于胜利了,可以说是个凯旋归来的巾帼英雄。然而,此时瑠璃子却感到了胜利后的悲哀与空虚。她在敌手临近死亡时看到了他身上未曾完全泯灭的人性光辉,而蓦然回首,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中,从手段及其严重后果来看,自己却近似一个恶魔,这不能不令她震悚与伤感,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在与庄田周旋的过程中,物欲享乐与戏弄敌手的快感腐蚀了她的心。如今,对这种生活的习惯性依赖,再加上庄田夫人的名份所担负的对庄田子女的监护责任,使她无法摆脱这种寄生型、享乐型的处境。
优裕的生活条件,天生丽质的美艳,新寡的自由身份,加上出众的聪明才智,奔放豪迈的举止风度,还有为应付庄田而练就的恣意玩弄男人的本领,使得瑠璃子一旦展开美丽的彩屏,便吸引了众多如饥似渴的男性。瑠璃子给他们以无限的希望,然而不给他们半点实质性的满足,借以发泄自己对男权传统的复仇欲,填补生活的空虚与无聊。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戏弄男性的快意,丝毫没有罪恶感。在她看来,既然男人见异思迁、喜新厌旧、践踏女性的尊严与权力而得不到应有的惩处,那么女人为所欲为地玩弄男人,豁出一条性命来惩罚一下男人的残暴与任性,为那些被男人玩弄而变成活尸的姐妹们报仇雪恨,又有什么不可!瑠璃子的复仇逻辑并非无可非议:一是如此一报还一报地循环下去,何时才了局;二是复仇对象已经从歹毒的、咎由自取的男人,扩展到纯朴、天真的痴情者、无辜者,岂不未免残忍;三是冠冕堂皇的复仇其实隐含着个人的享乐动机。盲目的、无休止的复仇,不会消泯仇恨、减少不幸,反而会增殖仇恨、加重不幸。纯情的青木淳不堪戏弄,决意自杀,一场意外的车祸使他如愿以偿。他的弟弟青木稔也坠入情网,被瑠璃子百般捉弄,当他终于明白兄长的死因与自己的处境之后,忿然刺死瑠璃子,然后投湖自杀。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复仇连环剧!
在古希腊神话里,阿伽门农家的连环复仇,在智慧女神雅典娜与太阳神阿波罗的斡旋下,终于划上了句号。在《珍珠夫人》里,瑠璃子的惨死与她临终前将庄田小姐托付给自己先前的情侣直也,寓示着这场连环复仇的终结。这一结局的设定显示了作者菊池宽对于女权复仇的理智主义立场。的确,男女两性是人类内部相互依存的两大群体,任何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都给人类自身带来创伤,只有阴阳和谐、友爱相处,才是美好的理想境界。对于男权传统来说,复仇女神的凄厉之美不失为一种有力的抗衡,但若让复仇女神任性而为,则无疑会加大现实与理想境界的距离。在这方面,菊池宽的前期创作至今仍给我们以隽永的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