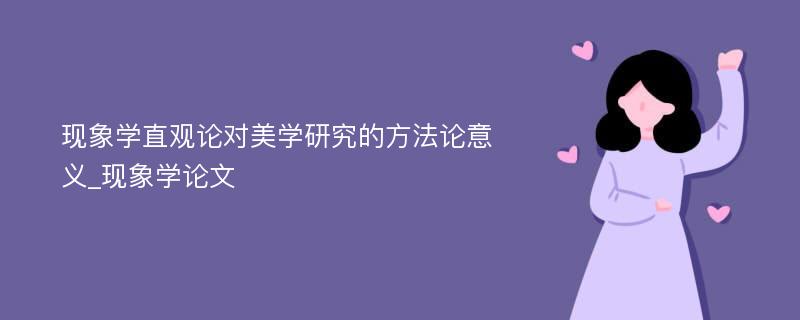
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理论对美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现象学论文,美学论文,直观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3)02-0108-05
在审美活动中,我们如何开启审美对象的意义世界(注:本文是笔者现象学审美对象的一系列研究文章之一。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论文在写怍过程中得到了现象学研究专家倪梁康教授的悉心指导。),如何进行审美体验?由于美学和哲学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性,不同的哲学就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方法,比如,经验主义美学与理性主义美学为我们分别提供了归纳法和演绎法。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哲学领域有现象学方法、分析方法与辩证方法三大方法。把现象学视为一种特殊的哲学方法,这是现象学各家的共识。比如,胡塞尔认为:“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典型哲学的思维态度和典型哲学的方法。”(注: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对海德格尔来说“现象学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个方法概念。它不描述哲学研究对象所包纳事情的‘什么’,而描述对象的‘如何”。”(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版,第35页。)在梅洛·庞蒂看来,现象学方法就是描述法:“要描述,不要解释,不要分析。”杜夫海纳坦言:“现象学向我们提出些什么呢?一种方法,它给哲学推论引进了一种崭新的风格。因此它能给那些根本不属于哲学的学科,如文学批评,带来启发,是毫不奇怪的。”(注: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孙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154页。)伽达默尔也明确指出:“现象学究竟是什么?……正如这个词本身所暗示的那样,现象学曾是一种无先入之见的描述现象的方法态度,在方法上放弃对于现象的心理一生理根源的说明或者放弃向预设原理的返回。”(注:《伽达默尔集》,邓安庆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页。)在现象学的诸多方法中如加括号、先验还原等,只有本质直观才是现象学各家在“回到事情本身”时所共同采用的方法:“我们的共同信念是只有通过追溯直观的源泉,追溯到从这个本源而获取的本质洞见,哲学的伟大传统才能按照诸概念和问题而为我们所利用;只有以这种方式,概念才能直观地被阐明,问题才能在直观的基础上被重新提出,从而能够在原则上被解决。”(注:《伽达默尔集》,邓安庆等译,第337页。)
现在,我们要问,作为现象学哲学方法的本质直观理论与美学学科尤其是审美对象问题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应该看到,尽管本质直观、悬隔、先验还原等方法都是为现象学的哲学问题与目标而设的,与美学学科以及各种美学问题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注:笔者曾就此问题专门请教于倪梁康教授,倪先生认为:“现象学本质直观理论与审美对象之问不存在直接的关系。至多我们可以说,我们通过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来把握审美对象的本质。但我们也可以同样说,我们通过现象学的中立性直观或现象学的悬搁来把握审美对象,如此等等。)。但是,不可否认,其中的一些哲学方法为解决某些美学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与方法基础。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早在1907年致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的信中就较为清楚地谈及了这个问题,这也是目前唯一公开发表出来的一份胡塞尔关于美学和现象学问题的完整论述文字。在信中,胡塞尔主要从对待自然与世界的态度,把握自然与世界的方法两方面来论述现象学哲学与美学的相近性。我们在此关心的是方法问题(注:对此问题的具体解释请参阅拙文“胡塞尔的现象学美学思想简论”(《外国文学研究》2001,1)。)。胡塞尔这样写到:“现象学的直观与纯粹的艺术中的美学直观是相近的;当然这种直观不是为了美学的享受,而是为了进一步的研究,进一步的认识,为了科学地确立一个新的哲学领域。”(注:《胡塞尔选集》,倪梁康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03页。)由此不难看出现象学哲学与美学之间存在的某种内在的联系。由于美是一种只有在具体的感性对象中,在人的审美经验中才能把握与领会的一种情感性价值,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它既不能用抽象的逻辑进行推演,也不能用经验进行归纳,而是通过直观的、无中介的方式如感知、想象等意向行为来开启、体验审美对象的意义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本质直观不仅是现象学哲学的方法论基础,也是现象学美学的方法论基础,为美学研究及开启审美对象的意义世界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库。
一
本质直观是胡塞尔现象学三大方法之一。其他两种方法是加括号(也称为悬隔)与先验还原,加括号就是排除“对存在和历史的信仰”,就是对其“存而不论”与“排除成见”,这是进行本质直观的前提。对现象学哲学时期的胡塞尔而言,本质直观又是先验还原的基础,先验还原是本质直观的最终归宿。具体地讲,从世界的角度看,在本质直观阶段,虽然对世界“存而不论”但世界依然独立存在,在先验还原中,世界不再独立存在,成为先验意识的相关物;从意识的角度看,本质直观中的意识是经验主体,先验还原中的意识是先验主体。“胡塞尔早期意识分析方法的最显著标志在于它的‘本质直观’的特征,本质直观的方法可以说是唯一一种贯穿在胡塞尔整个哲学生涯中的方法。从前现象学的《算术哲学》到描述现象学的《逻辑研究》,最后到先验现象学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本质直观的方法始终是胡塞尔哲学研究分析的坚实依据。”(注: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5页。)
国内外部分学者认为,胡塞尔的本质直观理论是对西方感性直观理论的新发展(注:也有一些学者对此理论提出措辞激烈的反对和批评,人员不仅来自现象学阵营之外如卢卡奇,同时也来自内部如布伦塔诺、施图姆福和梅洛·庞蒂,以及现象学运动的同情者如格式塔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神秘主义。)。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直观具有感性直观与本质直观两种含义,知觉与想象则是两者共同的意向行为样式。传统哲学所说的直观是一种感性直观,即对具体对象进行无中介的看,这种“看”只具有个别性而无普遍性;本质直观同样也是一种“直接的看,不只是感性的、经验的看,而是作为任何一种原初给予的意识的一般看,是一切合理论断的最终合法根源。”(注: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7页。)我们知道,传统哲学对本质的把握主要通过经验的归纳、思维的抽象与推理来完成,胡塞尔则认为凭借知觉与想象(注: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4页。)这两种直观行为就可以获得本质,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胡塞尔是如何通过直观来把握本质的?这需要在与感性直观的比较过程中来论述。
感性直观与本质直观有什么联系与区别?在胡塞尔看来,第一,感性直观是一种直观,本质直观同样也是一种直观,正如观念对象也是对象一样,而直观首先意味着直接把握对象的意识行为。第二,感性直观需以实际存在的个体为基础,本质直观则不受此限制,比如直观的对象可以是一客观对象如一座山峰,也可以是实际不存在的对象如方的圆。第三,感性直观是本质直观的基础,本质直观可以超越感性直观,前者得到的是事实性、个别性的东西,后者获得的是普遍性的直理。第四,就意识行为看,在感性直观中,知觉比想象重要,因为它所要把握的是感性的、具体的、个别的对象,知觉构成了想象的基础,两者的关系类似于原本一影像的关系;而在本质直观中,想象获得了比知觉优先的地位,想象构成了本质直观的主要方法。胡塞尔对本质直观的认识前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早期认为通过对一个感性直观的直观就可以获得本质,在《纯粹现象学通论》中(注: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2页。)认为仅仅依据一个感性直观还不够,需要对几个感性直观进行直观,这种变更被称之为“本质直观的变更法”或自由变更。胡塞尔在《经验与判断》一书中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理论阐释(注:《经验与判断》邓晓芒 张廷国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93-403页。)。在他看来,自由变更的实现主要通过变更多样性的创造性展现、在持续相叠合中的统一联系和主动确认差别之中的同一性三个步骤来完成。总之,本质直观就是无中介、直接性地看,这种看并非肉眼之看,而是一种精神之看,它需要通过知觉与想象尤其是想象的自由变更才能达到。胡塞尔还指出,对象本身具有无限的丰富性,我们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部分:“‘被看的事物’永远丰富于我们对于它们所‘实际地、真实地’看到的东西。看、知觉在本质上既是有某种东西本身,又是预先有某种东西,预先意味着某种东西。”(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胡塞尔把意识活动分为理智的与情感的两种,所有的科学活动都是理智活动,艺术活动则是情感活动。从科学观点看,理智的意识活动比情感的意识活动更具有客观普遍性,因此,理智的意识活动是情感意识活动的基础,这体现了胡塞尔鲜明的理性主义立场。
需要说明的是,胡塞尔没有专门的现象学直观与美学的理论论述和系统的艺术分析,只是在书信中或论述哲学问题时偶有涉及。比如,本文前面曾经指出,胡塞尔关于现象学与美学直观的看法是通过1907年的一封私人回信中来表达的。再比如,胡塞尔在1913的《纯粹现象学通论》中对丢勒画的分析,可以看作是对其上述理论的一次具体实践。面对丢勒的铜版画,我们需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镶嵌在画框中的这幅画以物的形式存在着,它是正常知觉的相关物;其次,在知觉意识的意向作用下,画面呈现出用黑色线条勾勒出的诸如马、骑士、魔鬼等图像,这些都是画的实相组成部分,还是比较凌乱的知觉材料;再次,在知觉意识的基础上,想象意识将这些图像融合为有机的图像客体,这一图像客体是这幅画的非实相组成部分即意向部分;最后,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到了这幅画所传达出来的意义。从胡塞尔对上述三个阶段的论述不难看出,对画面所呈现的意义世界的把握与体验始终是由知觉和想象这两种意识行为来完成的,传统哲学和美学惯用的感觉、判断、理解等理论术语被完全排除在现象学的理论范式之外。
二
胡塞尔之后,本质直观理论在两个维度发展:一是继续以胡塞尔的意识论现象学作为根基并有所修正,其代表人物是萨特。他对想象意识做了出色的现象学分析,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想象心理学》中。一是以存在论为基础来修正,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前者通过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存在论解读,提出了此在的想象理论;后者则论述了原初的意识行为——知觉,把知觉行为化、存在化,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知觉现象学》中。
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此在现象学标志着现代哲学的真正转型。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首先不是认识的关系,而是存在关系。也就是说,人首先烦忙在世而非直观事物,而胡塞尔将本质与存在生硬分开,本质成了无根性的东西,直观也就失去了真正的依托。海德格尔在1963年指出:胡塞尔“有意识地、坚定地转入到了近代哲学的传统之中。”(注: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第171页。)“无论如何,人的意识是以身体为基础的,而后者也是一个‘物理物””(注:德布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李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3页。)“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批判,首先针对的是意识的存在特征在存在论上的不可证明性。”(注:《伽达默尔集》,邓庆安等译,第317页。)胡塞尔的学生H·赖纳也曾经对两人的区别作了如下表述:“在胡塞尔看来,我们所有真正的认识都来源于(原本地自身给予着的、广义上的)直观。而海德格尔则解释说,我们并不是通过一种‘盯视’而经验到,例如什么是一张桌子或一张椅子,而是在将它作为一个‘在手之物’而与它打交道时(例如坐在它旁边或坐在它上面)才经验到它。”(注: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67页。)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视野中,本质直观的优先性不复存在:“‘思维’和‘直观’是领会的两种远离源头的衍生物。连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也根植于存在论的领会。……只有当我们获得了存在与存在结构的鲜明概念之后,本质直观这种看的方式才能决定下来。”(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 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80页。)海德格尔以锤子作比:对锤子特性的直观绝非静态的凝视,这种凝视只有建立在使用锤子的活动基础上才能被人真正把握。
萨特和梅洛·庞蒂分别发展了胡塞尔的想象理论与知觉理论。拒绝先验论,认为反思意识必然有非反思的意识为根基,想象意识这种直观行为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超越性和否定性等,这些都是萨特对胡塞尔意识直观论的修正。与萨特那种胡塞尔式的意识想象理论相比,梅洛·庞蒂的知觉理论则被海德格尔化。他的知觉不再是一种静观的意识行为,更重要的是一种动态的实践行为,知觉的首要地位是因为它是身体——主体在前意识状态中遭遇世界的原初“实践”方式。
在审美对象领域,就各家的师承来看,康拉德、英伽登和萨特主要受胡塞尔影响,杜夫海纳主要受海德格尔和梅洛·庞蒂的影响。就知觉与想象两种意识行为来看,除梅洛·庞蒂和杜夫海纳偏重知觉外,其余各家都偏重想象。与胡塞尔相同的是,萨特也是从意识的角度谈论想象,同样认为想象比知觉优先;不同的是,萨特更强调想象的情感性与否定性,他把审美对象看作一种想象对象,把美看作一种自由都是以此立论的。从情绪与情感方面来关注想象意识是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共同点,但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萨特的想象从经验意识出发,是在自在与自为的绝对对立中来论述想象的虚无功能的,而海德格尔把想象看作此在的基本能力,是从存在论立场来立论的,这从他对康德哲学的存在论解读和对《农妇的鞋》的精彩分析可以看出。此外,海德格尔强调想象与人的生活世界的紧密联系,强调想象具有把在场与非在场、过去和未来拢集在当下的功能;萨特强调的是人在审美活动中对所赖以生存的生活世界的否定与超越,强调想象的非在场性特征。梅洛·庞蒂更关注知觉,强调知觉在整个存在活动中的优先性,但在审美对象这一问题上鲜有论述。他的知觉理论在美学领域的影响主要通过杜夫海纳来完成。受其影响,杜夫海纳把审美对象看作一种知觉对象,力图确立知觉以观照审美对象过程中的优先性地位。
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方法的本质直观其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本质直观这个词反过来就是直观本质,其中直观是方法,本质是目的。这就意味着本质直观在作为方法出现时,总是与特定的内容与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特定的目的需要特定的方法,反之,特定的方法为特定的目的而设立。因此,本质直观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解读意义”、“发现意义”、“赋予意义”的精神活动。它对审美对象意义世界的解读,是意义与意义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是具有意义的意识视域之间的融合。对本质直观而言,它既然不是物理的、生理的目光,而是一种深邃的精神目光,那么,就不能建基于胡塞尔的先验意识中,而只能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来寻找其根源。比如,马克思说,人的眼睛与原始人的眼睛有不同的感受;恩格斯说,老鹰的眼睛比人的眼睛看得远,但人的眼睛看得更多,更丰富,其最终根源在于这些精神化、意义化的感觉的形成都是以往全部世界史的产物。现象学家施密茨的观点就非常具有代表性:“胡塞尔想以一种独特的、用几步就可以完成的归纳,有时简直是以无与伦比的巨大决心,一下子排除所有幼稚的偏见,以便有可能借助于无可争辩的、摒弃一切偏见的明证性进行先验的本质直观,从而在根本的批判性反思中达到终极的哲学认识。我认为,这样的事情是难以成功的。”(注:(德)赫尔曼·施密茨:《新现象学》,庞学诠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由以上所述可知,海德格尔等已经对胡塞尔的理论作了修正,朝着马克思实践哲学早已指出的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就哲学层面看,之所以进行本质直观,是为了直观本质即“回到事情本身”,再具体地讲,就是回到生活世界;就美学层面讲,本质直观是为了开启审美对象的意义世界,主要通过知觉和想象尤其是想象这一自由变更的方式来进行。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解说:本质直观从审美对象中直观到的意义世界究竟来自哪里?来自生活世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和审美对象的意义根源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需要专文对此加以深入细致的探讨,此处就不再赘述。
概言之,现象学的本质直观法与经验论美学的归纳法相比,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注重知觉、想象等意识行为在审美活动的作用和功能,其差异性在于经验论美学所采用的是一种“归纳法”,尽管它具有具体、生动、形象等鲜明的感性特征,但缺乏一种客观性、普遍性。与思辨论美学相比,两者都注重对本质的探究,都注重客观性与普遍性,根本区别在于思辨论美学主要采取的是一种“演绎法”。这种方法以概念作为逻辑基础,通过抽象的推理来阐释美学的一系列问题,缺乏具体性、生动性等美学自身应该具有的感性特征。本质直观则采取的是“显现法”,即通过感知、想象等意向行为让本质如其所是的呈现出来,这种方法力图把具体与抽象、个别与普遍、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质等有机地统一起来,在直观和体验中把握真理。因此,从方法论层面讲,现象学的本质理论是对归纳与演绎、经验与思辨这两大传统美学方法的扬弃。日本学者对此问题有着极为明确的论断:“现象学是作为一种可以综合演绎法美学和归纳美学并有助于在哲学方法论基础上阐明具体作品而出现。……其理由在于美学本来的学科性质与现象学的方法之间有着一种本质上的密切关系。(注:(日)今道友信:《美学的方法》,李心峰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52-53页。)前文已经指出,在诸多的现象学方法中,本质直观方法与美学的关系更为亲密,这个特征在现象学美学的代表性人物盖格那里有明确的理论表述:“人们既不能通过演绎,也不能通过归纳来领会这种本质,而只能通过直观来领会这种本质。……你观看一部艺术作品,并且在其中观察到悲剧的本质;你拾起一幅素描,并且在那里了解到素描的本质。与需要研究相反,这里只需要直观;与需要信息相反,这里只需要直观;与需要证据相反,这里只需要直观。”(注:(德)莫里茨·盖格:《艺术的意味》,艾彦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本质直观这种方法的获取,并不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先验能力,更不仅仅是人类一种先天的生理和心理机能,恰恰相反,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取得的,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而这恰恰是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理论最大的缺陷。因此,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看,人类在审美活动中,在开启审美对象的意义世界过程中所体现的本质直观能力,既不是人作为自然物种先天所具有的一种生理和心理的机能,也不是一种非人类的、神秘的先验能力,而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在某种文化历史沿革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功能与精神品格。
标签:现象学论文; 美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纯粹现象学通论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活动理论论文; 胡塞尔论文; 海德格尔论文; 萨特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