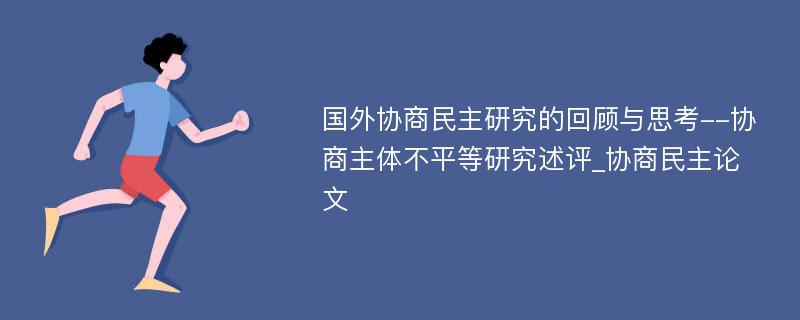
国外协商民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协商主体不平等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不平等论文,主体论文,民主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973(2011)04-0081-06
一、导言
关于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①这一概念,当前学术界并无统一定义,但其最核心的观点是,集体决策必须通过协商的程序进行[1]1。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涉及集体决策,所有受这一决策影响的人或其代表都参与了该集体决策,这是它的民主部分;另外,决策经由参与者论辩形成,这些参与者具备了理性与公正这样的品德,这是它的协商部分[2]。其中的论辩是一种自由、平等、理性的公共推理(public reasoning)[3],这种论辩必须证明实际决策(a practical decision)的正当性[4]3。这就意味着协商民主的首要特征是说理要求(reason-giveing requirement),而且协商过程中的理由能为其面向的所有公民理解(be accessible to all the citizens to whom they are addressed),当然,协商过程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is binding for some period of time),也是动态的(dynamic)[5]3-6。
不过,强调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通过理性讨论进行集体决策的观念并非原创,这种观念及其实践同民主本身一样古老,它们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2],但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协商民主,则是1980年贝赛特首次使用协商民主一词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并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国外政治科学家对民主治理的反思迅速兴起和扩散[6]。
如今,有关协商民主的研究文献数量已相当庞大且日益增加[7]1,其倡导者从若干方面阐述了它的优越性,如揭示私人信息、限制或克服有限理性、推动或鼓励一种为需求或要求进行正当性辩护的特殊模式、产生群体共同接受的最终决议、提高参与者的道德修养与知识水平、做正确的事情而不受讨论结果约束[8],甚至其批评者也认可了它的自然魅力[9]。但协商民主要从理论走向实践、要从美好的理论预期转换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不关注更具体的制度实践与施行问题,基本的哲学议题是不可能取得进展的[10]7。
而协商主体不平等正是一个颇具探讨价值的问题。因为,如果协商主体间存在不平等,那么自由将是受更多不当限制的自由,理性也将是扭曲的理性,协商民主观念的优越性就难以成为现实。对此,国外研究者已有所察觉,并在自己的相关研究中做了一定论述。为在这些协商民主理论先驱者与发扬者所作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协商主体不平等问题,进而为国内协商民主实践的推进提供理论与经验意义上的参考,笔者尽量查阅了相关研究文献,并围绕对主体平等的强调、对主体不平等及其影响的阐释、对解决不平等影响对策的探究三个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回顾,最后在此基础上简单地指出了既有研究的价值与不足,同时就后继研究的努力方向提出了几点建议。
二、对主体平等的强调
平等这一价值理念向来为哲学、政治学与行政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者所重视,协商民主理论家们同样表达了他们对平等的向往,这种向往既表现为目的性的向往,也表现为工具性的向往,前一个向往维度把平等作为协商的追求目的之一,后一个向往维度把平等作为有效协商的前提,文章所涉及的协商主体平等属于后者。
(一)指出平等重要性
研究者们首先指出了平等对于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性。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有詹姆斯·S.菲什金(James S.Fishkin)、科林·法雷利(Colin Farrelly)、卡洛斯·桑迪亚戈·尼诺(Carlos Santiago Nino)等。詹姆斯·S.菲什金(James S.Fishkin)曾提议通过“协商民意调查”来复兴美国的民主,他特别强调要将平等地考量每个人的偏好作为民主的关键前提,并做了相关阐释[11]29-34;科林·法雷利(Colin Farrelly)更直接地指出,尽管协商民主理想模式力促自由与平等的对话机会,但如果没有平等的第三个条件,即免于操控的自由,这种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12]228;卡洛斯·桑迪亚戈·尼诺(Carlos Santiago Nino)认为,协商民主理论价值的实现需要若干条件支持,如协商主体要在相当平等的基础上及不受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参与,在真正辩论中阐述与论证自身利益等等[13]129。另外,曼聚莎·古普特(Manjusha Gupte)和罗伯特·V.巴特利特(Robert V.Bartlett)在讨论环境政策时明确地将协商主体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平等作为协商的第一前提[14]。
(二)分析平等具体类别
除了指出平等对于协商民主实践的重要性以外,一些研究者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了协商民主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平等这一问题,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杰克·奈特(Jack Knight)、詹姆斯·约翰森(James Johnson)、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林·M.桑德斯(Lynn M.Sanders)等。杰克·奈特(Jack Knight)和詹姆斯·约翰森(James Johnson)指出:协商民主需要的是一种具体而相对复杂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是必要的,这种机会平等包含程序性与实质性的意义,而更为实质性的平等的政治影响力机会可以被区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协商要以资源平等为条件,其次是协商需要提出说服性观点的平等能力[15]。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与林·M.桑德斯(Lynn M.Sanders)也表述过类似观点——前者指出了能力平等、资源平等、机会平等及它们之于协商民主和有效社会自由的重要意义[16],后者则在反对协商这一主题下论述说:协商不仅要求资源方面的平等、要求保障有平等的机会来阐释有说服力的主张,而且要求“认识论权威”方面的平等,以便每个参与者都具备使自己的主张赢得认可的能力[17]。
总之,在协商民主研究者看来,协商主体平等是协商活动有效开展的重要前提、具有若干不言而喻的意义,而他们之间的平等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机会的平等、所拥有的资源平等、能有效阐述观点和进行公共推理的能力平等。
三、对主体不平等及其影响的阐释
协商民主理论对协商主体平等给予了分量不轻的强调,但在协商民主理论付诸相关的协商实践时,这种被理论家们一再强调的主体平等往往难以实现,并由此给协商民主实践造成了诸多影响。下文将围绕这个问题,进一步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
(一)关于不平等情况
对于协商主体间的不平等情况,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概括性的阐述,其中,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曾论述说:我将那些长期存在于大多数公共领域内的公共能力和功能的不对称叫做“协商不平等”,这种与团体关联的(grouprelated)不对称通常被区分为机会不平等、资源不平等和能力不平等[18]110。
多数研究者则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对协商主体不平等加以考察,比如,何包钢、林·M.桑德斯(Lynn M.Sanders)和爱丽丝·马里恩·扬(Iris Marion Young)。何包钢在分析中国浙江温岭扁屿村的民主恳谈实践时指出:“该村的现有社会结构格局有四个特点:一是外来人口和本村户籍人口的不平等差别;二是村领导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不平等差别;三是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等级差别;四是不同姓氏之间的势力差别……不同社会地位和阶层的人有着不同的行动能力……不同地位的人获得信息机会也很不相同”[19]58-59;林·M.桑德斯(Lynn M.Sanders)认为美国公民之间的沟通对话既不是真正协商的也不是真正民主的,在分析其原因时他论述说:这部分地归因于协商的一些必要的先决条件并不是平等地分布的,造成这一状况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些美国人比其他的美国人更善言辞,即他们在阐述自己的主张时博学而世故,所以易于被他人视为合理的主张,而不论他们的阐述实际上有没有价值、正确不正确。另外的原因是有些美国人的意见明显更容易被倾听[17];爱丽丝·马里恩·扬(Iris Marion Young)则提及了协商主体间的文化或结构性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异[20]。
(二)关于不平等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影响
综观既有文献可以发现,协商主体不平等对协商民主实践造成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强势一方对协商持傲慢与消极被动的态度;强势一方对协商过程的控制与操弄;协商结果有效性不足。
就强势一方对协商持傲慢与消极被动的态度而言,涉及政府与公民沟通对话的一些研究阐述了较具代表性的观点——约翰·S.德雷泽克(John S.Dryzek)称:国家很少或从来不会主动地推动民主的进展[21]87;何包钢在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协商民主实践时指出,尽管中国中央政府有要求、广大公民有需要,但很多地方领导者却不愿意尝试协商民主[22];爱丽丝·马里恩·扬(Iris Marion Young)在讨论激进分子对协商民主的挑战时论述说:结构性的不平等是造成严重不公平或社会危害的基础因素,那些拥有权力的政府官员们没有动机与他坐在一起协商[23];莫哈默·奥克德雷(Mohamad G.Alkadry)则通过对147名行政官员的调查研究证实了协商对话过程中行政官员不愿意听取公众意见的假设[24]。
至于强势一方对协商过程的控制与操弄,则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梳理这方面的既有文献。一是提出控制与操弄的理论问题,如爱丽丝·马里恩·扬(Iris Marion Young)曾分析称:处于支配地位和较为强势的团体的观点可能在公共话语及政策中占有优势[20],科林·法雷利(Colin Farrelly)认为,官僚主导的威胁对协商民主论者提出了新的挑战[25]214。二是对控制与操弄的可能情况进行理论分析,如爱丽丝·马里恩·扬(Iris Marion Young)在讨论激进分子对协商民主的挑战时指出,在实际的政治世界中,结构性不平等既影响着协商的程序,也影响着协商的结果,符合协商标准的民主过程通常都会偏向更有权势的参与方,他们有权力不公正地主导协商的过程,具体有协商程序的排他性、协商只具有形式上的包容、协商选择的强制性、协商过程中的话语霸权[23]。三是对控制与操弄的实证考察及分析,如何包钢在分析中国浙江温岭扁屿村的民主恳谈实践时提到了如下访谈记录:“19号村民说:‘村民说不弄,大队说弄,讲不讲一个样,大队早就定好了。我们的话一点也没用。老百姓的话没有一点分量。你说弄,他说不弄’”[19]59。保罗·J.麦金(Paul J.Maginn)在考察西澳大利亚州州政府推动的协商民主实践时指出,协商过程在政府的管控之下并被政府修改、缺乏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以便公众参与真正具有包容性的论辩和社会学习[26]。
而协商结果有效性不足可以看成是前述两大影响的逻辑延续,对此,林·M.桑德斯(Lyun M.Sanders)与保罗·J.麦金(Paul J.Maginn)的论述可谓是经典之作。前者考察美国公民之间的沟通对话后指出,他们之间所谓的协商民主既不是真正协商的,也不是真正民主的[17];后者通过对西澳大利亚州州政府推动的协商民主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后称,尽管西澳大利亚州州政府把自身描绘成复兴地方民主与公民参与的斗士,但其整体实践过程却偏离了协商民主理想[26]。
总之,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协商主体之间存在着种种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既涉及参与机会即是否能进入协商的问题,也涉及协商阶段及其后的决策中相关利益与提议能否得到尊重和体现的问题。诸种不平等成了强势一方对协商持傲慢与消极被动态度的致因,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强势一方对协商过程的控制与操弄,同时还影响了协商结果的有效性。
四、对不平等影响对策的探究
针对协商主体不平等对协商主体进入、对协商过程与结果及协商后决策产生的种种有悖于协商民主理想的影响,既有文献直接或间接地阐述了若干应对建议,这些建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立足于协商民主框架,他们要么直接针对协商主体能力的提升,要么注重协商实践方法的设计;另一类则在兼顾协商框架的同时放眼于协商框架外的一些条件,有的表达了借助现有正式制度条件加以改善的主张,有的阐述了对非正式对抗因素的合理利用。
(一)立足于协商民主框架的探讨
一些研究者将协商主体能力建设作为解决协商主体不平等问题的办法之一。如何包钢在分析中国浙江温岭扁屿村的民主恳谈实践时强调要“不断地提高大家的理性表达能力”[19]60、克里斯托弗·吉布森(Christopher Gibson)和迈克尔·乌尔科克(Michael Woolcock)在论述印度尼西亚农村的KDP(the Kecamatan Development Project)时提及了边缘群体的能力建设问题[27]、莫莉·安·帕特森(Molly Ann Patterson)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指出了个体与社会协商能力的发展及其意义[28]295。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他们所强调的协商主体能力建设途径,多数是一种依赖于本身并不完善的协商民主实践的发展途径。
但多数研究者则将协商主体不平等问题的解决寄望于协商实践方法设计的不断完善上,他们特别强调要注意政治和政策中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境况[20]。其中,一些研究者的论述较为系统化,如何包钢在分析中国浙江温岭扁屿村的民主恳谈实践时指出:“对有些不平等的遏制,需要……在程序设计上进行相应的完善和改进……一系列制度的设计(如主持人制度、参会人员随机选拔制度、事先信息发布制度、问卷调查决策制度、领导干部相对隔离制度、观察员制度)会有效地遏制社会不平等的影响”[19]60-61;有一些研究者的论述则比较具体,如迈克尔艾伦(Michael Allen)提出公开的非正式协商测试过程(open processes of informal deliberative testing)[29]、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和巴希尔巴希尔Bashir Bashir秉承协商的对话解释精髓强调了强势团体对决策要给出理由[30]61、克里斯托弗·F.卡帕维茨(Christopher F.Karpowitz)等人针对各协商群体彼此间的不平等指出要将群体内协商整合进市民论坛[31]、约·埃尔斯特(Jon Elster)提及了在公开的协商环境中避免强势一方公然使用允诺和威胁手段[2]。
(二)突破协商民主框架的探讨
在突破协商民主框架的探讨方面,一些研究者强调了现有正式制度条件的利用——现有正式制度是指那些协商框架外、业已存在多年并较为成熟的民主制度,如投票制度、政党制度、利益团体制度等。在这方面,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和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前者指出,团体可以利用制度中的权力创造并强化公共协商必需的条件,并使它相对持久化,这些较为正式的方式可以包括对受法律和政治权力保障的、制度范围内问题解决能力的运用,其旨在弱化不平等的原因和条件[18]133;后者阐述说:协商民主的理论家们对理性推理民主潜能的强调,几乎完全排斥了民主生活中作为强制面的权力。然而,民主离不开具有强制性的权力,同时也必须找到对抗强制的方法,这就需要政党、利益团体及其它可作为正式对抗手段的传统制度[32]。
当然,协商民主研究者们也注意到,要克服协商主体不平等及其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影响,还需要引入非正式的对抗因素。
一些研究者强调了集体行动者及集体力量,如詹姆斯·博曼(James Bohman)曾建议说,要创造新的公共协商空间,协商主体不仅可利用这些新公共空间表达新的公共理性,而且能够试着恢复范围更广的公共领域并使它更具包容性。为此,挑战者们需要通过动员团体间既有的非正式交流网络促成社会运动,从而组合成为集体行动者[18]133;简·曼斯布里奇(Jane Mansbridge)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论述说:民主有必要培养和重视非正式协商性抵抗领域,在这样的领域中,那些强制性运动中失利的人可以重新启动想法和策略、聚集力量[32]。
还有一些研究者强调了激情因素对协商与民主的积极作用,如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指出,公共的理性推理之外,还有其它一些要素,激情(passion)就是其中之一[33];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分析竞争多元主义时论述说: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务不是将激情泯灭,也不是将激情放逐到私人领域,而是要把各种激情动员起来,然后引导激情推动民主蓝图的实现[34];莎朗R.克劳斯(Sharon R.Krause)还明确反对政治理论将公民激情排除的做法,她声称这些激情能以积极的方式为公共决策合法性所必须的公正立场做出贡献[35]1。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特别注重自治公共领域对克服协商主体不平等的积极意义,如约翰·S.德雷泽克(John S.Dryzek)就反复强调了自治公共领域的重要性。他曾指出:自治公共领域内的、对抗于国家的民主对话实践不易被毁坏和操纵[36]114;后来他又再次强调了自治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并论述说:只有通过对既有权力结构进行批判,才能实现协商转向(deliberative turn)所坚称的民主真实性承诺[21]162。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如约翰·S.德雷泽克(John S.Dryzek)自身所言,他的协商模式和既有的制度之间是对抗性的关系[21]2,但这是一种温和的对抗,因为在他的模式里,公民社会发挥影响力的模式是公民社会的政治活动、静坐等特殊形式的集体活动、协商论坛、抗议活动、改变文化等[21]101-103,而在另一个协商民主研究者爱丽丝·马里恩·扬(Iris Marion Young)那里,则存在着扬(Young)本人所称的激进主义:激进分子建议关心增进公平的人们首先应参加批判性的反对活动,而别寄望于与支持或受益于现有权力结构的人们达成协议,激进分子避免和对立方进行协商,尤其是和官方代表进行协商,因为他认为通过双方都接受的理性论证以达成协议本身就是一个很可笑的建议[23],当然,这里的激进并不等于极端,因为激进分子认为蓄意的、针对他人的暴力做法在道德意义与政治意义上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反对如爆炸或焚烧这样蓄意的、严重毁坏财产的策略[23]。
总之,对于如何解决协商主体不平等问题,国外研究者从协商民主框架内外两个角度作了艰苦的探索,他们不仅关注协商主体能力的建设,还关注协商实践方法的优化,更关注协商框架外各种既有制度的利用与一系列新制度的促成。
五、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协商主体不平等及其对协商民主实践影响的研究是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随着民主化进程的纵深推进及协商民主理论的发展与协商民主实践的铺开,各种旨在推进协商民主实践的制度与机制得以不断完善,与此同时,有关研究文献也日渐丰富。本部分并不打算对国外这些年来的相关研究做全面的评价,只拟在前述回顾的基础上、简单地概述既有研究的价值与不足,并对后继研究的努力方向提出几点看法。
(一)既有研究的价值与不足
就既有研究的价值而言:首先,这些研究扩展了协商民主研究的视野,它是将协商研究由理论思考引向现实关切这一整体研究的重要元素,为协商民主研究进一步超越仅基于理想而非现实状况进行思考[18]的状况做出了积极贡献;其次,这些研究强化了协商民主理论家与实务者对协商主体不平等的思考,逐渐改变了协商主体平等问题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局面[37];再次,这些研究几乎论及了不同协商主体间的各种不平等问题——除了前面回顾中提及的公民彼此之间、社会团体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协商时的不平等,还有研究涉及了全球问题治理中协商主体的不平等[38],而且这些研究提及的不平等问题涵盖了协商机会、协商能力、协商资源等方方面面,它们不断深化了协商主体不平等问题自身的研究,同时也不断深化了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讨;此外,这些研究没有局限于就事论事,而是立足主体不平等本身,同时放眼于各种协商民主理论与实务甚至政治行政民主及政治行政文明的大背景下,剖析了协商主体不平等及其对协商的影响,提出了旨在解决协商主体不平等问题的一系列建议。既有研究的这些特点使它们具有了显著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为后继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文献支持。
但由于受到种种主观忽视或客观限制的影响,既有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或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第一,或许是由于研究问题与研究旨趣限制,也或许是由于各种理论准备不足与实践观察不充分,大多数研究涉及面太广,以致相关分析和讨论广而不精、多数应对主体不平等问题的建议也只是一些近乎原则性的空洞呼吁;第二,一些涉及如何建设协商主体能力的建议把能力建设寄望于协商理论与实践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尽管协商理论与实践自身的发展与完善对协商主体能力的提升具有不言而喻的积极意义,也能为主体不平等问题的解决贡献相关力量,但这种积极意义是相当有限的,而且主体不平等问题往往不是一个能力问题,或说能力不平等并不是主体不平等问题的主导因素;第三,实证的,尤其是其中定量的及比较的研究有待加强。此外,似乎当前的相关研究都存在一个倾向,那就是先假定协商民主是一个既存事实,然后再探讨主体不平等的问题,但目前协商民主实践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尽管这种实践“的确在民主决策方面有了实质性的进展”[39],但它“是民主决策的有益探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决策”[40],也就是说,目前我们是以协商民主理想为航标,通过开展并不断完善具有某些协商民主性质的民主实践以期渐渐趋近真正的协商民主。
(二)后继研究的努力方向
至于后继研究的努力方向,笔者以为:首先,在继续坚持将协商主体不平等问题置于各种协商民主理论与实务甚至政治行政民主及政治行政文明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的同时,适度的聚焦,尽量朝着研究的细化、具体化与深入化方向发展,比如政府与社会协商时的实质性不平等问题研究、潜藏于主体不平等背后的国家民主化宏观策略影响研究、劳资集体协商中的权力资源不平等问题研究,等等;其次,给予外在因素以更多的重视,一是要多考察协商民主框架以外的因素,二是要多分析强势一方之外各种因素的理性应用可能与程度;再次,通过社会观察甚至社会体验,强化实证性的研究。当然,我们必须随时谨记的是,协商民主依旧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理论预设,关于主体不平等问题研究的目的在于为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实现贡献可能的力量。
注释:
①目前国内关于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汉语译法并不统一,一些学者曾列举了7种译法——较有代表性的是谈火生,他指出不同译法(“审议民主”或“审议式民主”、“审议性民主”;“商议民主”或“商议性民主”、“商议民主制”;“协商民主”;“慎议民主”;“商谈民主”;“审慎的民主”;“慎辨熟虑的民主”)的同时称自己主张译为“慎思明辨的民主”,只是为行文方便才采用了“审议民主”这一译法(见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的《民主审议与政治合法性》一书第4页脚注)。另外,笔者根据有限的查阅还发现了以下三种译法:赵雪纲在他的译作《慎议民主的宪法》一书(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阿根廷学者卡洛斯·桑迪亚戈·尼诺著)第285-286页对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汉语译法做讨论时称,香港学者甘阳建议译为“权衡民主”;倪星和史永跃在他们合著的文章《民主评议政风行风的学理逻辑:代议制的视角》(深圳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42-47页)中译为“评议民主”。由此推知,目前关于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汉语译法至少达10种之多,为避免不必要的概念混乱,笔者在文章中采用中国大陆较为流行的译法,即“协商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