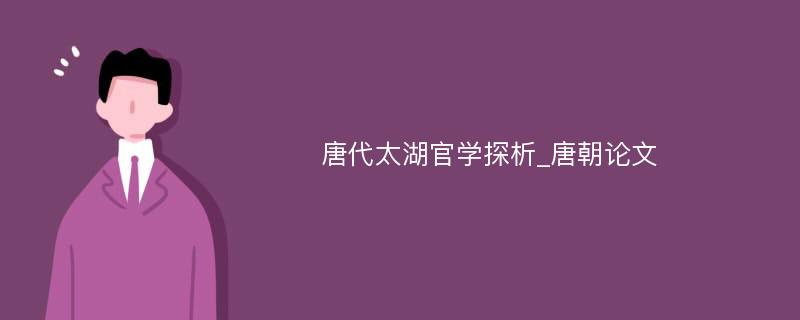
唐代太湖地区官学考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湖论文,唐代论文,地区论文,官学考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03)01-0052-05
一、唐前期太湖地区的官学
唐代重视学校教育,中央官学更是得到唐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植,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尤其唐太宗贞观时期,在中央官学“六学二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六学和弘文馆、崇文馆二馆)中的学生达到了八千多人,可谓唐代中央官学的极盛时代。
至于地方官学,唐前期,统治者在督办中央官学的同时,也多次诏令地方兴办州县乡学。唐高祖即位之初即对郡县学的生员数额做了规定:上郡学置生60员,中郡50员,下郡40员。上县学生40员,中县30员,下县20员[1](《旧唐书·儒学传序》)。高祖武德七年又下诏“州县及乡并令置学”[1](《旧唐书·礼仪志四》),玄宗开元二十六年诏令“天下州县里别置学”。[2]仅从诏令来看,唐代地方学校的设置深入到乡里。玄宗开元年间纂修的《唐六典》更是对唐代地方学校的教学内容、教师和学生数额等项制度做了较前代更详备的规定:府、州学设经学、医学二科,县学只设经学一科。按照府、州、县的人口多少划分学校等级。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设经学博士1人、助教2人、学生60人,医学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15人;下都督府、中州设经学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50人,医学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12人;下州设经学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医学博士1人、学生10人;京县设经学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50人;畿县和上县均设经学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中县和中下县均设经学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35人;下县设经学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20人。
唐代兴办州县学校的诏令和有关学制的规定,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理想的地方兴学的蓝图。然而在太湖地区(跨苏、湖、常3州17县),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笔者检索了该地区地方志中有关唐代州县学的记载,发现资料甚少(唐修地方志书稀少,传本多为明清时所修,故其中也应略考虑资料的缺失)。安史之乱以前只有湖州一州有州学的较详细的文字记载,“唐初有孔子庙,在霅溪(湖州)南,学附焉。学置经学博士、助教、生员六十员。天宝中,州助教、博士及学徒会食师资,诏废,惟留补州助教一人、学生二人,备春秋二社岁赋乡饮酒而已。”(宗源翰,杨荣绪:《(同治)湖州府志·舆地略·学校》)此外,据李栖筠大历三年在苏州“增学庐”这条资料看,苏州在唐前期似也有州学,但史书记载语焉不详,已无从考察。苏、湖、常3州17个县中,在安史之乱前有县学记载的只有苏州昆山一县,“唐有文宣王庙,庙堂后有学室,在县治东,以兵火废。”(李铭皖,冯桂芬:《(清150卷本)苏州府志·学校三·昆山县学》)有的县有庙无学,如苏州嘉兴县和海盐县,据光绪朝修纂的两县县志记载,只有孔子庙却无学校。大多数县则庙学全无。
资料表明:唐前期,太湖地区州县学校绝大多数没有建立起来,乡里学校更不见记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中央虽对地方学校的教师、学生数额和学习内容做了明确规定,但对办学资金、校舍等办学的关键要素却未做任何制度性的规定和保障,主要依靠地方自行解决。至于办学是否有结果,中央没有一套相应的制度、政策来督促检查地方官,这就难免不出现兴学诏令成为一纸空文的结局。只有个别富有远见的地方官吏舍得花费资金、拨出土地创办学校,而一旦他们调离,学校则随时可能遭受半途而废的厄运。此外,自武则天始,唐代重科举而轻学校之势愈益严重。因国子学、太学生员皆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弟,武则天为了排斥、打击士族官僚势力,提拔庶族地主子弟为官,尤其重视进士科取仕,借以奖拔寒族,学校因而受到轻视。史载:高宗、则天时“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因是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毁废矣。”[1](《旧唐书·儒学传上》)学校出身、参加科举而能及第的人数越来越受到限制,仕途越来越狭窄。唐玄宗为了改变这种现象,曾于天宝十二载(753)罢乡贡,规定举人必由国子学和郡县学。但终因重科举之势已成,故两年后又恢复乡贡。科举选官制度尤其是进士科取仕冲击了官学的发展。
二、大历年间太湖地区官学的兴起
虽然太湖地区官学在唐前期总的看来不景气,绝大多数学校没有建立起来,但是在中唐时期主要是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却出现了办学的活跃气象,资料记载较唐前期明显增多,姑择其典型事例说明之。
大约在大历元年前后,李栖筠为当朝宰相元载忌,由给事中出为常州刺史,于常州“大起学校”。后又迁苏州刺史,兼浙西都团练观察使,于苏州“增学庐”,“远迩趋慕,至徒数百人”[3](《新唐书·李栖筠传》)。从《旧唐书·代宗本纪》中可查知:李栖筠由常州刺史迁苏州刺史是在大历三年,即768年。湖州府学如前所述,天宝中减缩师资生员,学校已不具备教学的性质,仅“备春秋二社岁赋乡饮酒而已”。“大历五年(770),刺史萧定加助教二人、学生二十员”,重振学校(宗源翰,杨荣绪:《(同治)湖州府志·舆地略·学校》)。昆山县学在战乱中毁于兵火,大历九年(774),县令王纲重建学校,“大启室于庙垣之右,聚五经于其间,以邑人沈嗣宗躬履经学,俾为博士。于是遐迩生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李铭皖,冯桂芬:《(清150卷本)苏州府志·学校三·昆山县学》)。
上述现象出现在唐安史乱平定后不久。长达八年的战争浩劫,使唐政府统治力量严重削弱,财政发生困难,对学校则更无力顾及。战争期间国学生的廪食停给,生徒流散,校舍遭到破坏,这在代宗永泰二年(766)的诏书中反映出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1](《旧唐书·代宗本纪》)。中央官学尚且如此,地方学校更是荒废不堪,就连地处长江以南的昆山县学也遭到“兵馑荐臻,堂宇大坏”。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在太湖地区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兴学景象,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首先,“崇儒兴学”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稳定江南地区统治秩序的战略措施之一。安史乱后,北方藩镇势力强盛,不向中央交纳贡赋,唐王朝失去了北方这个重要的财赋基地,所能倚重的只有东南八道,主要是江淮地区。时人云:“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3](《新唐书·权德舆传》)尤其是江南地区,成为唐后期的财赋重地,“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4](《全唐文》)卷555)。因而,牢牢控制江南地区,保持这一地区的长期稳定,就成为关系唐王朝存亡的战略问题。于是,标榜忠孝义礼的儒家学说被作为维持统治秩序的法宝,重又得到唐统治者的大力推崇和提倡。而学校在传播儒家义礼道德、施行教化、敦厚民风民俗以及培养忠于唐王朝的官吏人才等方面,则有着科举制尤其进士科考试不能取代的作用。对此,代宗在永泰二年颁布的兴学诏书中明白讲道:“治道同归,师氏为上,化人成俗,必务于学。……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尽其师道,乃谓成人。然后扬于王庭,敷于政事,征之以理,任之以官,置于周行,莫匪邦彦,乐得贤也,其在兹乎!”[1](《旧唐书·代宗本纪》)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李栖筠等人在太湖地区地方官任上,大力贯彻“化民成俗,以学为本”的兴学宗旨,以儒家义礼忠孝作为学校主要教学内容。史载:李栖筠在常州“大起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3](《新唐书·李栖筠传》)王纲重建昆山县学,“听治之暇,则往敷大猷以耸之,博考明德以翼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厉之,使自趋之。故民见德而兴行,始于乡党,洽于四境。父督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李铭皖,冯桂芬:《(清150卷本)苏州府志·学校三·昆山县学》)。由此可见,太湖地区官学是因“崇儒”这一政治需要而兴。在唐朝统治者看来,学兴则儒教盛,儒教盛则民风淳,民风淳则乱贼不起、天下太平。“兴学”已不单纯是一项文化教育政策,更是唐王朝稳定江南地区的一项战略性国策。地方官学不仅是培养官吏和人才的储备场所,更是广大城乡地区施行教化、敦厚民风的重要阵地。
其次,“兴学”是李栖筠等一批官缭士大夫深刻反思安史之乱发生根源后采取的一项政教措施,是对科举取仕不重实行之弊端的批判和纠正。“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打破了唐人对盛世的沉醉,繁盛统一的大唐帝国开始走向衰落,这一惨痛的现实对唐王室和官僚士大夫的震撼是巨大的,引发了他们对安史之乱祸因的思考和对本朝各项制度、政策的深刻反思,各种批评的舆论主要集中在科举选官制度上。代宗宝应二年(763),因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请停进士、明经二科考试一事引起,围绕科举取仕制度,在朝廷中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以杨绾和给事中李栖筠等人为首的一批官僚,对明经、进士科取仕之弊端给予了批判,指出科举取仕制度的失误是造成道义沦丧、安史之类乱臣贼子所以产生的根源,建议停止科举取仕,除恢复汉代察举孝廉的选官法外,还要通过增广学校、大兴儒学来移风易俗,教化士子百姓。《新唐书》卷44《选举志上》记载了这段史实。代宗将杨绾上疏诏李栖筠等议,议曰:“宣父称颜子‘不迁怒、不贰过’谓之‘好学’。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生病为是非,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袭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乱臣贼子由是生焉!……今绾所请,实为正论,然自晋室之乱,南北分裂,人多侨处,必欲复古乡举里选,窃恐未尽。请兼广学校,以明训诱。请增博士员、厚其廪稍,选通儒硕士,闲居其职。十道大郡,置太学馆,遣博士出外,兼领郡官,以教生徒。朝而行之,夕见其利。”代宗宝应年间的这场朝廷议论,为此后的崇儒兴学活动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萧定、王纲等人虽未直接参与这场讨论,但他们在大历年间在太湖地区办学的实践证明他们是这种观点的赞同者。萧定在湖州增补助教、生员;王纲在昆山重建学室,大崇儒学;更典型者李栖筠在苏、常二州亲自以儒家义礼教示儒生,并躬身向学官执经问义,以示尊敬,“表宿儒河南褚冲、吴何员等,超拜学官为之师,身执经问义”[3](《新唐书·李栖筠传》)。李栖筠对科举选仕制度的批判,不是像有的学者所说目的是为了维护士族集团的政治利益,排斥庶族官僚集团,而是已超出了他所处的士族阶级的狭隘利益局限,真正为大唐社稷着想。正是从探求唐朝长治久安之道出发,才会有李栖筠等人在大历年间的大兴学校之举。从此点来看,李栖筠不愧为中唐时期有远见的政治家。
大历年间太湖地区兴学具备了哪些条件呢?首先,政治上的和平稳定为兴办和发展地方官学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如前所述,由于江南地区在唐后期战略位置的重要,而太湖地区又在江南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以代宗和李栖筠为首,君臣上下齐心,致力于以武力肃清不安定因素,使太湖地区免于藩镇割据和兵火之争。李栖筠刺常州时,“宿贼张度保阳羡西山,累年吏讨不克,至是发卒捕斩,支党皆尽,里无吠狗”,常州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安宁局面,李栖筠“乃大起学校……”。江淮地区自乾元元年(758)至宝应元年(762)连续发生大灾,饥民遍野,人心不稳,心怀叵测者伺机而起,“苏州豪民方清因岁凶诱流殍为盗,积数万,依黟、歙间”。奉诏讨平方清的平卢行军司马许杲“恃功,擅留上元(今南京),有窥江、吴意”,江南局势岌岌可危。代宗命李栖筠“为淅西都团练观察使图之。栖筠至,张设武备”,消除了战乱和割据隐患,苏州形势稳定下来,李栖筠则“又增学庐”[3](《新唐书·李栖筠传》)。
第二,中唐时期太湖地区经济的发展为兴办地方官学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安史之乱发生后,北方出现了人口南迁的浪潮。以苏州为例,当时避乱南下居苏州的人口很多,以至苏州户口从76421户增加到100808户。[5]劳动力的增加和北方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是太湖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为了确保财赋的征收,任职此地的地方官大多重视兴修水利、招徕流民、开垦荒地、发展生产。如李栖筠出任常州刺史时,“岁旱,编甿流徙,乃浚五渠,通江流,溉田,遂大稔”(于琨:《(光绪)常州府志·名宦》)。又如萧定,“大历中,有司条天下牧守课绩,唯湖州刺史萧定与常州刺史萧复、濠州刺史张镒为理行第一。其勤农桑,均赋税,逋亡归复,户口增加,萧定又冠焉。”[1](《旧唐书·萧定传》)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太湖地区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成为“良田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的美丽富饶的重要产粮区。如苏州嘉兴县就有“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4](《全唐文》卷403)之称誉。经济的发展为太湖地区改变文化教育长期落后于北方的状况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天宝末年至大历年间,北方大批文人名士为避战乱流寓太湖地区,出现了“多士奔吴为人海”的局面,为该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打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人才基础。太湖地区水陆交通便利,风光秀美,气候宜人,加之有长江作为天然屏障,阻绝了北方战火的蔓延,环境和平安定,是文人名士理想的避乱隐居之地。自天宝末年以来,流寓此地的读书人很多,如:华州华阴人吴筠,天宝中“知天下将乱,东入吴兴(湖州),卜居青山”[6](《万历湖州府志·流寓》),往来吴越间,尤善著述,“词理宏通,文彩焕发,每制一篇,人皆传写。虽李白之放荡,杜甫之壮丽,能兼之者,其唯筠乎!”[1](《旧唐书·隐逸传》)安定人皇甫冉,天宝中登进士,调无锡尉,避乱居阳羡(属常州,即宜兴、义兴)(于琨:《(光绪)常州府志·流寓》)。在此写下许多诗文,“每文章一到朝廷,而作者变色,当年才子,悉愿缔交,推为宗伯”[7](《唐才子传》卷3)。竟陵人陆羽,“工古调歌诗。兴极闲雅,著书甚多”[3](《新唐书·隐逸传》)。中唐初期寓居湖州、苏州等地,写出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如此等等,不一一而论。
第四,大历年间,代宗多用博学有闻的文人儒士担任太湖地区地方官,他们是该地区州县学校的直接创办者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有力推动者。除了上述所举李栖筠等人外,著名者如:颜真卿,“少勤学业,有词藻,尤工书。开元中举进士,登甲科”,大历中刺湖州[1](《旧唐书·颜真卿传》)。“初在德州尝著《韵海镜源》,遭难而止。至是,乃延文士纂而成文。又以饯别之文及词客倡和之作为《吴兴集》十卷。”(宗源翰,杨荣绪:《(同治)湖州府志·名宦》)韦夏卿,“应制举,策入高等。大历中出为常州刺史。夏卿深于儒术,所至招礼通经之士。后又改苏州刺史。”[1](《旧唐书·韦夏卿传》)等等。这些颇负才学、享誉士林的文官任职太湖地区期间,或延聘罗致通经儒士,直接兴办州县学校;或招致文士与修书籍,切磋学术;或与诗人往来酬唱,登临题咏,将风流雅韵播于三州。由于他们礼宾儒士,多倡文行,吸引了四方人才云集此地,以至出现了“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8](《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的文化昌盛、人才荟萃的局面,从而推动了太湖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代宗以后太湖地区官学的衰败
代宗以后,有关太湖地区兴学的史料记载又趋稀少,表明办学活动复归于沉寂。个中原因,分析起来主要有二。
其一,中唐初期,战乱刚刚平定,儒教凋弊,人心浮动。统治者迫切需要稳定社会秩序,将人们的思想言行纳入忠孝礼义的轨道。在时代的需求下,儒学得到了尊崇和振兴。一些有远见的地方官以“兴学”为宣扬儒教、施行教化、治理地方的绝佳手段,纷纷兴办地方官学。于是,这一时期地方官学的教学内容和任务便定位在了传经习礼上,儒学的地位在官学中大大加强。代宗以后,随着唐政府在江南地区统治的稳定以及进士科考试越来越被推重,成为士人入仕唯一之正途,自东晋南朝以来素有文学传统之优势的江南地区,摒弃经学奉文学为圭臬也就势在必然。因此,以传经习礼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地方官学在代宗以后的衰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二,德宗以后,唐财政日绌,制约了官学的发展,统治者不得不抽取一定数量的官俸来修缮学校。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国子祭酒郑余庆,奏请从官员月俸中抽取“修学钱”以修葺国子监。懿宗咸通(860-873)年间,令群臣“输光学钱,治痒序,宰相五万,节度使四万,刺史万”[9](《文献通考·学校考二》)。大顺元年(890)又令“内外文臣各于本官料钱上每一缗抽十文助修国学”[10](《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唐政府有心兴学却无力办学,中央官学财力尚且如此捉襟见肘,地方官学则更无助,难以支撑。太湖地区官学也难逃衰竭的厄运。
总的来看,太湖地区官学在唐前期仅在个别州县建立起来,而且天宝年间又多废弃不堪,远远没有达到唐兴学诏令和《唐六典》中所要求的数量和规模。但是到中唐时期,主要是代宗统治近20年间,太湖地区州县学却因种种原因呈现出兴盛景象。代宗以后又衰弱下去。从教育的内容和社会功能来看,唐代对地方官学不似对中央官学那样有严格的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方面的规定,太湖地区的官学教育内容受办学者的政治需要影响较大,而侧重于教授儒家义礼、推广教化,学生也以通经习礼为主要学习任务。尤其在中唐大历年间,太湖地区官学在讲习礼乐、教化士子乡民、淳朴民风民俗方面的德育教化功能得到空前加强,这与中央“六学二馆”以培养国家官吏和各种专科人才为主要办学目的有明显不同,从而构成了唐代太湖地区官学的特点。此外,根据史书记载:唐于“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医生。开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5](《新唐书·百官志四下》)唐政府在《唐六典》中对地方督府州学设置医科也做了明确规定。但事实上,地方并未贯彻执行,没有任何有关太湖地区州学设置并教授医科的资料记载就说明了这一问题。综观唐代太湖地区的三种教育形式:官学、私学和家学,最为发达的当属以文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家学,它为唐王朝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官吏和人才(详见拙作《唐代太湖地区家学初探》,载《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5期)这是以经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官学所不能比拟的。
由于太湖地区为其在唐后期的重要地位所决定,故而其官学的兴衰发展在全国有较典型的代表意义。将太湖地区官学这一个案推广来看,唐代地方官学虽在学校制度(主要是教师、学生数额)的规定上较前代更为周详,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由于唐代没有形成一套地方办学的保障机制,学校教育经费没有固定来源,教学内容也无统一的规定,致使“有令无学”的现象在各地较为普遍。即使有的地方有州县学,学校也只是施行儒家教化、学生习礼的场所。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北宋时期政府对地方办学经费、教学内容、教学计划与法规等做了正式规定以后,地方官学才开始步入正规化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2002-0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