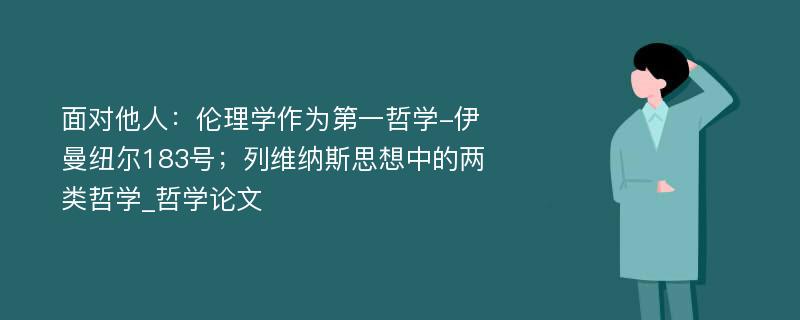
他人的脸: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伊曼纽尔#183;列维纳斯思想中两种类型的哲学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曼纽尔论文,哲学论文,伦理学论文,纳斯论文,两种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4)03-0038-15 来到雅典,我想不出有比哲学更好的话题。希腊思想家创造了哲学,希腊语是哲学的母语,而雅典则是古代哲学达到高峰之地。所幸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询问哲学,询问哲学之所是。而做这样的自我并非有幸而已,这既不是历史上的碰巧和偶然,也不是无分析的自恋情结。哲学,不像那些圣人创造的精神传统和非同寻常的启示,它始于人对智慧的关切。这是一种关切,也就是说,它在理性的引导下探寻意义、做论证以及自我批判:它也是彻底的疑问和解答,是对疑问自身的疑问,并且只接受那些在理性的法庭上得到辩护的结论。只有那些合乎理智的东西、有意义的东西、合理的东西才具有哲学的合法性。哲学就这样谦卑地自视为人类智慧,既非玄妙也不神秘。但与此同时,企求成为神圣的也正是人类的智慧,因而哲学也大胆地自视为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形式,是人类所能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智慧。总之,哲学自视具有或努力具有真正的智慧——立于真理的智慧。 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雅典产生了三位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都寻求那样的真理,是那种智慧的热爱者,然而他们各自以特色分明的方式为以后的哲学家们树立了哲学的类型和范例。 苏格拉底没有著作,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追问,尤其是向那些自认是智慧的人提问,就最重要的东西(善、公正、虔诚、爱、知识)的不变的定义去提问、测试、寻求和向人讨教。我们知道,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样的追问,对具有彻底性和不懈精神的哲学做了彻底的、不懈的证实。他的生命又是如此不平凡,他的死乃是古代世界中两个最著名的死亡事件之一。毫无疑问,他的死更显神秘性,而阿喀琉斯则以其死得壮烈而名声更大,后者为友情而死。 柏拉图,苏格拉底的学生,建立了第一个哲学学园,就在雅典离阿哥拉集市(Agora)大约一英里之处。他以写对话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流传至今的哲学形式,即让论辩者通过相互诘难和辩答来追求真理的那种既是戏剧又是推理的形式。柏拉图的那些对话写得如此之微妙,其思想又是如此之精深,它左右着我们对苏格拉底乃至对及乎今日的哲学本身的解释。柏拉图几乎是不见于这些对话中的(一次例外是在《申辩篇》中,他为救苏格拉底的命而出场,另一次是在《斐多篇》中提到苏格拉底死的那一天,他因病缺席),他以缺席的方式使得对话者之间的交流和辩论活了起来,这一点本身——与也是希腊人创造的悲剧、喜剧相对照——至今仍是一个极有意义的问题:非纯粹的、绝对的缺席,不是“是”的反面的无,不是“是”的退隐,而是柏拉图戏剧性的缺席,他的意见、观点、任务的不定性——如今,这种积极的缺席唤醒了人们理智上的活力。② 追随着前面两位大师,亚里士多德也在雅典创立了一个学校,吕克昂学园,在离阿哥拉一英里比柏拉图学园稍远一点的地方。在此,从天上到地下,从自然到人间,各种问题都被拿来认真研究,以期成为有严格标准的知识。他就所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讲课,这些就成了后来保存下来的专著;他又深入下去建立了各门学科,从物理学、生物学和伦理学到修辞学、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直到今天这些学科也依然很活跃。这一广谱的知识或智慧后来又深深影响了中世纪的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基督教。那时,谈到单纯的、最有声望的“哲学家”这个名称,人们所知的倒是亚里士多德而不是苏格拉底。 这真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它与权力、金钱和名声无关,然而光彩绚丽,以至于人们,尤其是哲学家们,就想成为一个古典学者,从而能在理智上与这些古希腊人长相厮守,即那谈话生动的苏格拉底、写出对话的柏拉图、进行研究而有科学论著的亚里士多德,还有他们的对话者、他们的前驱,及其拥趸和反对者。这里我且不谈智者,他们在语言、法律和政治方面的富有思想的教导。我们也没能忘却辉煌的古希腊文化遗产之宝藏:影响虽小却比较聪明的怀疑论者和犬儒学派的哲学,或者当时更加流行的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的哲学。关于最后所谈到的那个人,人们很容易证明,他有助于我们对当代的消费社会有更好的理解。不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位位高而德严的哲学家对理念的热爱,而是伊壁鸠鲁——他同意朋友间要有私人生活领域,追求有节制的快乐,大理好自己的家事,不要用那些难以控制的大事干扰自己和他人。在一切情况下,不管你喜欢谁,人们总是能在一种生活中想起这些古代的思想家,学习古代的希腊,遵循他们的理性,复活他们的争论和论证,心里怀有他们的教导和榜样,从未离弃他们的那些丰富教益。身在雅典,令人不禁遐想联翩。 不过,如你们所知,本次演讲不是关于希腊哲学的,尽管全部哲学永远都在争论中,并且如我们将见到的,也是与希腊哲学的无止境的辩论。这篇论文,你们从题目即可知,是关于当代哲学的,是关于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哲学,是关于其论哲学的哲学。说了以上这些,我必须接着就说,古希腊哲学也总是现代哲学。或者,更大胆、更完整地说,古希腊哲学既不是古代的,也不是希腊的,而这一点正是古希腊哲学最伟大的遗产。我会把自己的意思讲明白,不含糊其辞。理性,古希腊哲学最伟大的贡献,是不受时间地点束缚的,它没有日期,也不指这里和那里,不专属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因而不分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也不分希腊、罗马、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 当然,对这一说法必须要加一些限定,尤其是现代哲学使得我们意识到有限定的必要。时间是不能完全泯灭的东西,它不是幻觉,因为一个现代人是不能与一个古代人互换其位的。时间是单向度运动的,是通过积淀、记忆和历史构成和延续着的。然而,有了这些限定以后,我们却不能因此而糊涂——真理多少还是超越时间的,尤其是在数学和逻辑方面,而在文学、历史和性情方面则要弱一点。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尔维尔、《吠陀》、孔子、老子,佛陀,都能被翻译为现代英语,能够被理解;对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即使逻辑的发展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水平。此外我们也决不能忘记,历史时期的划分,从分分秒秒到一个个时代,总是现代人所规定的,是能够以这种或那种理由加以修正、建立和保持的。毫无疑问,文化教养会影响一个人去赞成或反对某种思想风格,如英国人可能喜欢经验主义,而德国人则喜欢观念主义。但是,喜欢不是强制,人还是自由的,而理性则是伟大的解放者。理性一旦发挥作用,决定论或因果必然性就失效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唯有理性才具有无人称、非文化、非文明或非时代的特征。 根据它自己的光芒,理性既是自由的也是以它自己的方式而限定的。合乎理性的人自由地思想、提问和进行挑战。但是合乎理性的人也是受限制的,不过不是受制于文化、历史、人种这些东西,而是受制于好的理性、好的证据、适当的证明、有效的论证这一类东西。这种特别的自由,受制于诸理性的自由,受着真理的牵引,是合理的自由,这就是我前面说过的那些话的意思,即古希腊哲学最伟大的贡献既不在于其古老也不在于其是希腊的。而是在于它产生出了理性的生命、合乎理性的生活。生于本土而不画地为牢,出当其时而不定于一时,它驰骋于时空,不断地提问和学习,同时又总是对自己的提问提出问题。关于这种具有理性的真理的杰出状况,希腊哲学有一个词叫做katholikos,经由拉丁文的渲染我们知道,其意思是普遍性(universality)。理性是普遍的,这并非因为它被剥夺了特殊因而是抽象的,而是因为它敞开地面对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在任何地点和时间都为真,以其能适当地限定自己思想的自由,从而适用于从数学符号到诗的隐喻和喜剧的智慧这些独立或互相关联的意义领域。 做了以上这些说明,现在让我进入这篇演讲的中心论题——那是列维纳斯说的一句话:伦理学是第一哲学。它说起来很简单,事实上颇有深意,在某种意义、某个方面也是很重要的“善”,它对于真和美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关于这点我们会把它说清楚。这个说法如果是真的(且将善必定是真这个已经明白了的悖论置于一旁),那就意味着,知识不是第一哲学。这个说法是革命性的,它罢黜了知识的长子继承权。由于哲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传统,人们会说,“知识是第一哲学”是希腊哲学的遗产,即便在今天的哲学界,仍有大多数人持这种立场。人们还认为,真正的哲学必须是科学的——无论是像物理学、化学那种形式的所谓“硬科学”,还是像社会学、心理学那种杂交的“社会科学”,以及像盛行于历史、比较文学那种“人文学科”中的自我反思式的学问,皆是如此。根据这个模式,哲学这门学科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知识的自我反思,是真的真理,是认识论。确切地说,因为列维纳斯不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傻,去触碰科学的真理和知识的有效性,如我们将看到的,他对于知识是坚决承认的,他要挑战的只是历史上与知识等同的哲学的老大地位。 如果我可以简单地回到古希腊哲学——任何事情最终都不可能离开古希腊,我要说,列维纳斯关于伦理学基本地位的说法是苏格拉底式的,但同时又不是苏格拉底式的。说是苏格拉底式的,那是指在苏格拉底精神生活的最关键的时刻(如我们由柏拉图《斐多篇》95c-100a中所知),在这个重大的意义上,他从对自然世界的研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即对事物之产生结果的、形式的和物质的原因的追问,转向了对人类世界的研究,也就是说,去追问像虔诚、知识、善和公正这样一些最终的目的。如果有人说,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斐多篇》里讲,“没有骨肉,尽管我有别的东西,我就不能做我所乐意做的事,那么他说的是真理;然而说我做下来了,并且我这样做是有理智的,但不是出于对最好的东西的选择,这就极其不顾理性了。因为这就不能分清真正的原因(即最终原因)是一回事,使原因成为原因的东西则是另一回事。”(《斐多篇》99a3)在这个意义上,列维纳斯所谓伦理学是第一哲学的说法是苏格拉底的——列维纳斯和苏格拉底都把对善的研究和追求放在优先的地位。但这又不是他们第一位重要的东西,似乎那只是他们个人的决定——他们二位都把善当作是必不可少的(sin qua non),是真理本身的必要条件。然而,苏格拉底认为要行善就要先认识善,在这点上,列维纳斯的说法又不是苏格拉底式的。苏格拉底寻求善的定义,像所有希腊哲学家一样,对于他来说知识是第一位的,即使他的注意力从是者的世界转向了最终目的的感召。相反,对列维纳斯而言,为通达善而从后门放进来的东西正是从前门被抛出去的东西,寻找善的真理又回到了置知识于优先的地位。然而,善之为善,只能在伦理学、在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中去寻求,这样才会在善的事情中尊重善,而不迫使它走向合乎认知和知识的方面。我们马上会看出这其实是什么意思。当然,关于苏格拉底所谓对善的“认识”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也可以无休止地辩论下去,但是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不只是历史上的学术问题——即便从那种角度去说,我也愿意站在列维纳斯的方面去看苏格拉底。不管辩论的结果怎样,有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即列维纳斯明白无误地反对把认知当作体察善之为善的直接途径,明白无误地拒绝了知识的优越地位,这就是说,反对把知识当作是善的最终尺度。恰恰在这里,恰恰在这一点上,列维纳斯与康德分道扬镳。如我们所知,像苏格拉底和列维纳斯一样,康德也强调“实践理性的基本重要性”,但是,康德与列维纳斯不一样,却与苏格拉底一样,他从认识论立场来阐述这个基本重要性,把道德纳入命题逻辑的规范,以矛盾律、排中律为尺度加以普遍化,于是,就从后门放进了已经从前门驱逐出去的东西。 对列维纳斯而言,哲学中首要的东西不是知识,而是伦理。列维纳斯已经站在反对整个希腊哲学传统的立场上了。这是一个令人敬畏而卓有成果的反对意见。这里让我们要立即再次强调那个重要的限定。在强调伦理学的首要性时,列维纳斯并不是说知识不再是知识了,或者它不再是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了;相反,其地位更加确定,其合法性甚至更大了。不过,现在因为它被伦理所规范,接受了伦理的要求,它只是哲学的一个方面,而非其自身价值的标榜或者统摄着伦理学。知识的地位因此而既变得谦卑又得以加强。我们务必不要误解,以为伦理的价值和知识的价值、伦理的目的和知识的目的二者的关系被歪曲了——为此列维纳斯说,那只是人们站到错误的立场上了。我马上就会回到这个关系方面来,回到以伦理学为首要性以后的伦理学和科学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更确切而清楚地说明其特征。但是,为了这样的说明,我先要交代清楚列维纳斯所谓的伦理学究竟是什么,它对于哲学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出于上述目的,我只是简单地勾勒了一下列维纳斯的伦理学,因为现在他的学说已经广为人知——在大学文科学界(liberal arts),乃至于人文科学界(humanities),尤其在聚集于这个庄严会议场所的哲学家之中。我的概括是简单的,但也是紧凑的,也就是说,紧缩的(我不用“精致”这个词),因而也许有点密集。首先是某些术语上的澄清:就“伦理学”这个词而言,我指的是对道德和正义的阐释;“道德”,即善待他人;“公正”,是指平等的关系或争取成为平等,例如,管制所有有关人群的法律。当列维纳斯说“伦理学是第一哲学”,他是说,一切有重要性的东西、一切可以理解的东西,一切意义都出于道德关系。 对列维纳斯而言,道德是从人内部的关系中产生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面对面”(face-to-face)。这里,两个“项”既在相互关系中又超出相互关系,是两个不可归约的独一无二的人的复杂的结合③,是人们相互依存于其中的两种不可归约的、不同的关系,因而是处于不对称关系中的两个人。于是,这个四重性的东西,两个项和两种关系,就有下面的情况:(1)被列维纳斯称为“他人的脸”④的他人之为他人,那不可归约的超越的踪迹,它不是理智上的抽象,而是一个从寄身于脆弱的有限人生的东西中萌生出来的东西的变式,他人性(otherness)总是我们碰不到的,是超越所面对的那个人的综合能力的。(2)从他人出发与我的关系:道德责任。他人并非首先是一个对象然后才有责任,他人首先是一个在负责的他人。(3)归入他人责任中的主体,被迫成为不可替代的第一人称、“自我”、“被选的”、因他人而“心灵受到创伤”,成为他人“人质”的被动性。(4)从我自己到他人的关系:对他人和为了他人的道德责任。以食物、衣服、帐篷、教育、谈话、爱、庇护以及所需要的东西,去减轻他人的痛苦,对他人的需要做出奉献、资助和回应。由于“自己”是在其中构成的,这些责任是免不了的,是个人性的;这一责任也是无穷尽的,是不能完全免除和彻底完成的——因为,他人是绝不能完全触及的,也是不能毫无往来的。确实,一个人能拒绝责任而作恶,或者为了他人而行善,但一切意义、一切重大的东西、重要性之为重要性,都从此开始了。 然而,这种产生在两个人之间、罕见而又过分的道德四重性是不充分的,或者说,在其中伦理学只对道德做说明,而不对公正做说明,而后者也是善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后者之为重要,是因为我所面对的他人也总是处于与另外的、我所不面对的他人的关系中。在这种道德里,一个负责任的自我即使对他人尽了最大的责任也是不够的,理由有两点:其一,如果我对于面对我的那个他人是完全道德的,把一切都给这个特定的他人——例如,我具有的全部食物、从我身上脱下来的衣服、我全部的钱;那么,不在场的他人就被否定掉了,也就是说,没有给他食物、衣服和钱。这真奇怪,我由于是道德的,同时又是不公正的。其二,面对着我的那个他人可能受到另外的他人的威胁,这时我的责任要求我保护我所面对的、受到另外的他人潜在威胁的那个他或她。人们可以看出,在这两个事例里,我是根据道德要求把一切都给予那个我所面对着的他人,还是根据我和他人的道德关系,对那个受到另外一些人的实际和潜在伤害的他人给予保护?这里就有一个修正道德的要求。对他人的无限的道德责任,这种道德,无论是照它去做还是就其理论本身来看,是会变得不公正的。于是这里就有了公正的要求,对他人和另外一些他人的一视同仁,作为公民在法律下的平等——例如,在法庭上的平等;再如,在医保和教育需求上的平等。所有这些也是道德所需要和企求的。作为两者间不对称、不平等的关系的道德,与作为众人间平等关系的公正,二者是不同的。但是,如果这两者不是同时存在,那么,其中之一也就不能自立。这与霍布斯是相矛盾的,他认为司法或国家主权所制定的既是公正的又是道德的;列维纳斯则与之相反,他认为,须以公正修正道德,去造成一个对邻人友善、道德盛行的世界,而不造成对他人的危害。 因为此文的题目是哲学,是列维纳斯所认为的哲学,我要强调一下列维纳斯说明道德和公正的最主要的方式。这就是说,我将说明不公正的、非对称性的然而是基本性的道德四重性关系在与公正所要建立的平等遭遇后造成的哲学上的后果。这一重要的方式就我所见,用列维纳斯的话来说就是“说”(dire)和“所说”(le dit)。尽管列维纳斯在其第一部名著《整体与无限》(1964)中刻画道德特征时已经用到了下面这些词语,如“表述”、“诚恳”、“谈话”、“交谈”⑤、“教导”、“评注”和“说”(“在关系中同时又从这种关系中解脱出来,这就是说”⑥),其第二部名著《“是”之外或越过本质》(1971)⑦,紧接着并且继续着第一部而写,在那里,“说”(saying)和“所说”(said)这两个术语就更突出了。 我们看到,对列维纳斯来说;他人的脸、他人之变化或人性是赋有道德责任的,由此而刺激着他所面对着的我,不是那个(外表所见的)主体,而是我自己,使之成为对他人和为他人而具有道德责任的第一人称的自我。另一种刻画这同一关系的方法是谈话。因为说话、交流和说对于道德和公正的实现也是很重要的。从道德的观点来说,因而对于试图对道德做解释的伦理来说也十分重要的是,谈话的第一个词不是“所说”,不是将说出的东西集合起来的谈话,不是一组命题和符号的混合——就是说,不是列维纳斯归结为“所说”这个词下的东西,它应当是“所说”之“说”——这里的强调不是偶然的。使这个观点得到清楚表达之困难加重的是,说的第一个词不是所说的一部分,而似乎总是隐含的。那是未说出的“听着”或“听我说”,这就是所说之说的“第一句话”。在说出来的话之前的那句话居然不是话,而是“话前话,是与他人的亲近”。⑧所交流的不是“什么”,即不是论点、主题、说明、命题、指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而“首先是交流的交流,给出指号的一个指号,不是在敞开状态中某物的传达”。⑨列维纳斯论证,没有这个说,根本就不会有意义。思想在独自中与自己的交往是沉默,那也只是一种理想的说法,实际上并没有这种沉默。因为,我们所谓思想与自己的交往实际上是内化了的对话。出于这个理由,也因为说是意义的超越性的条件,列维纳斯把说看成是“可理喻的”、“意义的意义”。他写道:“‘说’是交往,确然如此,不过它是作为一切交往的条件,是显露。”⑩在《整体和无限》中,列维纳斯称这没有说出来的第一句话是一个祈使句:“你不要杀人。”(11)因为不谋杀别人,在说着话的、带有其生动表情并将之体现出来的那个他人才向我显露出来;不杀他人是听见他人说些什么的首要条件。我既尊重他人之为他人,在道德上尊重向我显露出来的人,尊重那个在和平关系的谈话中以话语立身的他或她,这样就能在两个人之间建立起每一方的独立性都不受损失的关系。那不是两部分人之间的关系,即从全体中的部分来规定的两个项的关系,而是两个个体的项,是独立而又最亲密的两个人的关系。 当然,并非一切都像阳光普照的日子那样可爱。在两个人之间不只有理解、交往和实在的互动,也会有误解、交往错误和解释错误,甚至有语言上的冲突。事实上,交谈的这个方面,显露自身的这个方面,也是不可避免的。“说”说出所说,是任何所说的条件,我们要承认这一点;不过,“所说”也能够并确实有自己的生命,它成为一种产品,一种可以在时空中得到规定的东西。“说”说出所说,所说在世界上存在。就像任何产品一样,一旦说出来了,所说就有了对生产者的独立性,成了世界上的一种东西,一种指号、符号或密码,大家都可以去占有它、收编它和接纳它,等等。换句话说,被说及的东西,一旦说出来了,就可以从“说”分离开去,于是就成为与“说”割裂的一种作品、一个产品、一个商品、“著作”,成为世界中一件与说分离的东西。同样,因为脸在“说”着,脸也能够被当作是世界上的一样东西,一种时空中的东西,能作为一种宣明、面具、征兆和需要加以解释的符号而出现,一种能够给予多种解读的、敞开的表象,因而也能被误说、误释和误解。在被当作所说的所说中,因其隔离了说,说的踪迹会被忽略掉,而只是被客观地对待,或者被当作一种东西,一种在场或者不在场,即在场的不在场,或不在场的在场,而不是作为一种强加的道德责任。于是,真和假,以及列维纳斯归结到“形式逻辑”这个标题下的全部体系,甚至连海德格尔所理解的“是论”(ontology)以及“是论的差异”(ontological difference),都活跃在所说的范围内,而忘却了它的人性,就好像根本就没有“说”这回事。这样,反人道主义成了彻底“是论”的条件,就像实证主义的条件也是彻底“是论”的条件一样。所说能够——也是出于自身的要求——试图使自己成为仪式、程序、策略,来接近自身、理解自身,寻求内在性,以自己为自己定向,以便成为一个符号的、语义学的、符号学的世界,一个衍生出更多指号的有差异的指号母体,一出在场和不在场的戏——“是”和“无”的戏。说的作用则不同,它干扰矫饰、自以为是、自我满足以及一切这样的自我标榜的集合与理解。 列维纳斯所做的不是要进入这个体系,也不是要通过进一步的阐明让它们变得更加精致,而是要我们注意:在这种方式中,道德——并且唯有道德,才激发出这些泡沫,而不论人们如何单纯或多么聪明和善于思考。因为,这里有出乎规则的义务、未实现出来的责任、以诚恳使所说过分承载、道德的强制性、指责性的因素、重说、不说,以及以说去套取更多的所说——恰如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里反对记忆中所书写的东西而以生动的谈话所做的辩护。(12)就在《整体和无限》这部很难读的大师级著作写成但还没有出版供人阅读的时候,列维纳斯接着写了前言,其中已经写到了所说之说:“它就是语言的本质,它就在于通过前言和注释不断地把它的句子开释出来,在于不说出所说中,在于试图去除程式的重说中——程式是所说所乐取的,但不可避免的程式化已经妨碍了理解。”(13)为了反对只在所说中去发现可理解的东西——此说之勾引人犹如塞壬之召唤,列维纳斯坚决抓住“说”。这个活生生的话语,这个从不可归约的、变化着的他人向我的诉说中产生出来的道德责任,才是可理解性的源泉。 上面所说的一切最终把我们带到了本文的题目:列维纳斯对两种形态哲学的区分。现在你可以想见,这一植根于道德的区分是建立在区分说与所说的基础之上的。它是这样一种区分:一方面是通过对以他人的脸为根源的所说的踪迹的追溯,致力于对说的高涨和不合宜之处保持清醒意识的哲学;另一方面则专注于去理解所说之为所说、理解处于引诱人的在场和不在场辩证情景中的自我在场的哲学。另一种来表达这个区分的方法是,指出在柏拉图、笛卡尔、康德和列维纳斯的超越的或形而上学哲学与巴门尼德、斯宾诺莎、黑格尔和德勒兹这种内在论的或“是论”哲学之间的区别。 为了突出作为所说的哲学和作为说的哲学之间的区别,请允许我提供从列维纳斯那里摘来的三段引文,其中一条较长,另二条相对短些。列维纳斯的读者是知道的,他经常批评西方哲学,不过与此同时,也似乎显得有些矛盾,他自己提出的思想就像是哲学,而且确乎就像是不可冒犯其尊严的第一哲学。但是,如果人们区分两种哲学:其一是作为内在性、同一性、全面性、整体性和所说的哲学——那是列维纳斯所反对却为一切哲学所拥有的,另一是作为超越的、多变性的、责任性的、无限性和说的不可归约的无规则性——这是列维纳斯自己的哲学之路,那么,上述看上去的矛盾就不是矛盾了。当然,这两条路径、两种哲学都有其他的说法。我们记得黑格尔就曾责怪康德的“经验主义”和“非哲学”,这很出名——康德!——恰恰因为超越,康德才不可抹杀。(14)在这三段引文后,我会简单总结一下列维纳斯这样一种主张的哲学特征:伦理,也就是说,道德和公正的呼唤,是超越的最终形式,也是意义和可理解性的最终形式,因而就是哲学本身。 于是,那段长引文,出自《“是”之外或越过本质》将近结尾处的一个小节,标题为“怀疑主义和理性”,列维纳斯提到怀疑主义是因为形式逻辑对怀疑主义的拒绝,这是他所反对的。他提到怀疑主义不是要为怀疑主义的论证做辩护——那已经被否定掉了,他要为之辩护的是人性、超越,是将他人从聚成一团的“同”以及形成主旋律而被理解的东西里分离开来的不可共时化的“历时性”。这里的他人,是在说话的他或她。在这种情况中,他人是反对逻辑的。于是我们知道了,列维纳斯是要把作为在表达着的、“说着”的怀疑主义与被拒斥掉了的、作为被表达出来的“所说”的怀疑主义区分开来。他人的说不可归约地异于指号的演示,这种差异里面有人性,它拒绝将自己还原到包含在说出来的东西的不可拒斥的形式逻辑中去。列维纳斯不是说主体性是真理,而是说,真理依赖于主体性,亦即依赖于道德。这样,伦理学就是第一哲学。 非个人的逻各斯的可理解性和亲身的可理解性是相反对的。但是,公正、国家、主旋律、共时性、复述、逻各斯和“是”的理性性质,它们不是被吸收到了亲身的可理解性中,与之相一致并且展开在其中吗?后者不是必定要在前者的控制下吗?——因为我们现在的讨论就是根据所说来开展的,也因为在形成论题的时候我们已经将术语共时化了,在这些术语中构筑起一个系统,使用着动词“to be”,并把据说各种超越“是”的意义的东西都放进了“是”。或者,我们必须重提变化以及作为哲学时间的历时性吗?……哲学与怀疑主义是分不开的,怀疑主义就像影子跟随着哲学,哲学要赶走它,转眼间却又在它的脚下。这最后一句话难道不是哲学吗?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的。因为对西方哲学来说,说穷尽于所说的东西。但是怀疑主义事实上制造了一种差异,让说和所说去照面。怀疑主义是能被拒绝的,但是它又回来了。……哲学低估了否定性的“不属于”的广度,它是超出逻辑上的否定和肯定的范围的。正是对他人性(illeity)(作为“他”或“它”的他人,也即道德上对公正的呼唤)的关系的追溯,这是知觉所把握不到的统一性,在命令着我面对责任。……尽管哲学的言说以其所说而背离了亲近性,它在我们面前传递的仍然是说、亲近性和责任。哲学为生活道路划定界限,它以公正和知识、以智慧在第三部分人面前树立责任的尺度,它不是取消这个生活。它是对越出了主题的他人说。对拒绝在场的历时状态的回归造就了战无不胜的怀疑主义的力量。(15) 在此,列维纳斯当然是把“西方哲学”的特征看作是“说穷尽于所说”的谈话。在《整体和无限》中他把这一吸纳和消除的特征——说之归纳为所说——称为“整体”。这正是他所反对的哲学。 第二段引文出自1986年科尔尼(Richard Kearney)对他的采访: 哲学最伟大之处在于,它能把自己放进问题,对自己建构起来的东西进行解构,不说它已经说过的东西。科学则相反,它并不想不说自己,不去疑问或挑战自己的概念、术语或基础;它忘了向前,忘了进步……但是科学只是哲学语言的降级,它的语言最终是从哲学那里取来的,科学绝不能有最终的世界。海德格尔令人敬佩地总结道:科学不思想,它只是计算着……哲学不能把不同的意义全部纳入整体,让它们最终同时在场,这是事实,但我不认为这是缺点或错误。或者,用另一种说法,哲学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有所失。哲学之失于把意义整体化——尽管“是论”正企图这样做——这倒是好事,因为这样就把不可归约的超越的他人性敞开出来了。(16) 正如列维纳斯所肯定的,这就是哲学——进入问题,以不说所说来激发和鼓动说,唤醒对脸的追踪,通过对于比全面与广泛性更高的、迫切而重要的事情的关注,冲破种种整体性予以。这里,哲学提升到了批判和道德的高度。这就是列维纳斯本人的哲学形态。 最后,第三段引文,也出于《“是”之外或越过本质》(第一章)。这段引文也高扬作为说的超越性的哲学。 在其数番辉煌中,哲学的历史已经知道了这个与本质断了交的、还极为年轻的主体性。从柏拉图的没有“是”的“一”到胡塞尔的内在之中的纯粹自我、超越,它已经知道了从“是”所做的形而上学的提炼,即使其为所说所遗弃,像通过神谕的作用,例外被隐藏到本质以及瞬间便掉进规则的命运之中,并只被留在了幕后的世界。尼采式的人的意义就在于揭示这种环节……那个笑而不言的人。哲学家在哲学史对语言的滥用中重新发现了语言,在这里,不可说的以及超越于“是”的东西被传递到我们面前来了。(17) 这里,列维纳斯把贯穿在哲学史上的漫长而尊贵的有关说和超越的哲学谱系摆出来了。当然,这不是列维纳斯的发明,尽管他比别人更强调这一点,并且把超越立为道德的基本性质,因而比别人更坚定地把伦理学当作第一哲学。 我之所以选用上面第三条引文,不仅因为列维纳斯在此提到哲学史上的某些例外的时刻——不是比较而言的例外,而是根本上的例外,即在哲学史上通过所说迸发出说的时刻,因而可用来说明列维纳斯对两种类型哲学的区分;也因为它在招尼采的魂。不过请不要将之与列维纳斯对怀疑主义的召唤混淆起来,他对怀疑主义的论证是不同意的,只不过是取其不可归约的人性罢了。而列维纳斯对尼采式的大笑者的召唤则出于人性的名义,它遗弃进行综合的语言的遁词,后者的语义学、符号学和种种套话,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所有这些努力所追求的东西,都被尼采拒绝为“正经货”。列维纳斯并非赞成尼采的学说,例如,他对最高道德的无情攻击,他对荷马的辩护并站在柏拉图的对立面,以及求真意志,或者那些被列维纳斯归结为“屈从和幻觉”而被清除掉的amor fati(命运之爱)和永恒轮回的学说。(18)不仅如此,对列维纳斯来说,柏拉图的“超越‘是’的善”,像笛卡尔的“无限的观念”一样,与压不住的怀疑主义和尼采的大笑者一起,都是整体的破裂、中断和破碎,是在所说的踪迹中见证着说的冲击和输入。那么,哲学在其最高处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些时刻活跃起来,去动用它们的那些例外的压力,即列维纳斯所谓道德命令。这样,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就能用善的命令填塞到知识的语言中去,去冲破封闭的或者凝滞的符号体系,去完全冲破符号的地平线——在“形式逻辑的滥用”中,在夸张中,在语义学的沉重负担中,在道德的严正中,揭示出符号的使用者的第一个符号就是符号之给出,就是所说之说;从对某种超越的理解中,列维纳斯就看出了哲学的灵感。 我选用第三段有关尼采的引文,为的是要让大家注意一个对列维纳斯全部思想来说十分重要的结论,用一句话来支持列维纳斯那个重要而珍贵的、哲学上又是彻底合理的说法——伦理学是第一哲学。在《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论文的第24节,尼采提出了一个哲学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极端、最令人不安、最具严重后果也是越来越急迫的挑战——如我们所知,他提出了“真理的价值”问题。(19)他问道:为什么要讲知识?为什么要讲真理?难道真理不是说谎的又一个伪装吗?难道科学不是宗教的又一种遁词吗?也就是说,它不是软弱、病态、懦弱和迷信吗?尼采要说,国王是赤裸裸的——是啊!国王根本就不是国王。也就是说,真理不能证明自己,进而就是,知识、科学以及哲学和理性是没有最终理由的,它们都是谎言。在这样一个毫无依傍的世界里,一个虚无的世界里,尼采肯定说谎的意志,肯定以良心说谎。他置荷马于柏拉图之上,认为讲神话高于做推理,而说谎高于真理,并且毫无羞耻地“超越于善恶”,有意说他的选择比起谎话既不好些也不更坏。 请不要害怕,我明白此地不是提出我报告的结论的合适地方,甚至也不宜去多谈这样的问题,因为问题太大也太严肃,不能草率对待。不过,我做这样的结论是为了让大家明白,有其作为亲近和伦理的哲学概念,列维纳斯就能回答尼采的挑战,这一点他是以提出“为什么要哲学”这个问题的方式在《“是”之外和超越本质》的末尾予以清楚总结的。(20) 首先,作为亲近的哲学必定会唤起我们自己真正的人性,也就是说,它在不断地唤起我们每个人以及相互之间对于人类的道德责任,对于所有有感觉的被造物和一切被造物的责任性。没有比这一点更重大、更急迫和更有价值的了。因而,哲学——热爱智慧,必须将我召唤到它身边。哲学是觉醒,是启蒙,是对责任的召唤。其次,对我们正在谈的问题,即哲学之证成——道德需要公正,就这一点来说也是更重要的。说不只是所说,好像在所说中它是纯粹的失败;说之为说,需要所说的逻辑、“是”和无、在场和不在场的作用,也需要有无限、绝对的高度以及说的尊严。这就是说,通过承认伦理学是第一哲学,列维纳斯就为哲学的正当性提供了一种辩护,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真理的价值”。真理的价值,也就是说科学、知识以及哲学的价值,它们是这样的:没有真理(使不平等变得平等)就不能有公正,没有公正就不能有道德,而道德,如我们所知,是一切意义、一切价值的渊泉。人性寻求公正,因而也寻求真理,这恰恰就是列维纳斯所谓的“第一哲学”。 从学术的要求来说,我应当从列维纳斯那里找出更多的引文来证明道德和公正以及公正和科学之间的关联,但为了简洁,请恕我只以如下引文作结:“公正、社会,国家及其机构,交换和工作,都是从亲身性方面得到理解的。”(21)另一段引文是: 哲学通过在(说和所说、意义和“是”之间的)差异中提炼出问题,又把提炼出来的问题还原为差异,来服务于公正。这样就把平等带给了为了他人而对自己的克制,把公正带给了责任。从其历时性方面说,哲学是将意识分离开来的意识。这是一种兴衰交替的运动,就像怀疑主义遭到拒斥被还原成灰烬,最终又从灰烬中得到重生。哲学对“是”的规律和城市的法规做辩护和批判,去再次发现从绝对的“为他人的自己”(one-for-the-other)中剥离出来的自己和他人的意义。(22) 关于亲身性和知识的关系,列维纳斯写得还要简单。他说:“哲学是为爱服务的爱的智慧。”(23)我的解释是:“智慧”就是知识、科学、真理、主题、表述、使不平等成为平等的哲学;“爱”不只是情绪、喜欢、性爱,也是“爱邻人”、仁慈、道德、接济需要帮助的人、待他人为他人。所以,列维纳斯说的是:没有道德的公正和真理是暴君式的、非人道的,即使将其标榜为以最高理想的名义。没有道德的公正所标榜的理想只能是没有真正理想的、没有仁慈的、没有爱的,它是暴君式的,它把事情和理念置于人民之上。从另一个方面说,没有公正的道德就只是情感和喜爱、个人的仁慈、个人的自满自得,是躲在个人的天地里,它无视世界、无视别人、无视与我有距离的人,对他人的苦楚无动于衷。让我们一起,将作为知识的哲学置于作为伦理学的第一哲学的基础上,我们一起被嘱咐要互相善待,为了这份善待而去保持和扩大善待,我们也被嘱咐投入到长期、耐心的科学、技术、政治工作中去,去创造一个对所有人都更好、更神圣的世界。公正和仁慈是不能分的,这就是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的说法之重要性和最终的道理。 注释: ①本文是作者于2013年8月1日在希腊雅典大学哲学学院召开的“全球变化时期作为生活道路的哲学和文化”会议上的演讲稿。本文的翻译曾得到乔治·安德(Georges Enderles)教授的帮助,特此致谢!——译者注 ②参见Victorino Tejera,Modes of Greek Thought,Chapter V,"Plato:The Open Mind",New York:Appleton-Century-Crofts,1971,pp.129-149。 ③对这个复杂的组合,列维纳斯除用其他名称称呼外,还称之为“宗教”——“我们建议以‘宗教’来称呼还没有组合成整体的同类和他者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参见Emmanuel Levinas,Totality and Infinity,trans.Alphonso Lingis,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69,p.40.以下简称TI。与列维纳斯有关而令人感兴趣的是,1918年吉尔伯特·莫雷(Gilbert Murray),其时是牛津大学钦定希腊文教授,他说:“宗教,即使就狭义而言,总是在寻求救赎,为了逃命。”参见Gilbert Murray,Humanist Essays,New York:Barnes & Noble,1964,p.14。 ④不必一一引证,他的著作中到处都有“脸”这个词,尤其见《整体和无限》第三节“外在性与脸”(pp.187-147)。这里,因我们现在身处希腊,我要引一下肯尼迪·克拉克(Kenneth Clark)的《裸体:理想形式的研究》。他注意到,甚至注视裸体画和裸体雕像的时候,“我们首先看脸。正是通过脸部的表情,才会有亲近感”。(Kenneth Clark,The Nude:A Study in Ideal Form,Garden City:Doubleday,1956,p.205.) ⑤TI,p.39.“同和异的关系、形而上学,基本上就是从交谈中产生的。” ⑥Ibid.,p.215. ⑦Emmanuel Levinas,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trans.Alphonso Lingis,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88(以下简称OBBE)。 ⑧OBBE,p.5. ⑨Ibid.,p.119. ⑩Ibid.,p.48. (11)TI,p.199,p.198. (12)列维纳斯有一点是很出名的,他把柏拉图的《斐德若篇》奉为“哲学史上最好的四五部著作之一”(Emmanuel Levinas,Ethics and Infinity,trans.Richard A.Cohen,Pittsburgh: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85,p.37)。毫无疑问,对列维纳斯来说,柏拉图这篇对话的高潮在于苏格拉底关于“活生生的谈话”的优越性的论说(p.276)。谈话是能够自助的,这点超过书写的文本,后者“甚不能自辩、自助”(p.275);另外也让人感兴趣的是,在《斐德若篇》的结尾处,苏格拉底高调谈到他对伊索克拉底的希望。后者,如我们所知,站在他同时代那些智者的对立面,希望将“修辞”和德性联系起来。而修辞的理解,照耶格尔(Werner Jaeger)的评论,是“相互说服、阐明自己思想的力量”(Werner Jaeger,Paideia: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Vol.III,trans.Gilbert Highet,New York:Oxord Uiversity Press,1944,p.89);那么,列维纳斯想必是要我们明白,早在《斐德若篇》中,对“说”就有了高度的赞扬。 (13)TI,p.30. (14)参见G.W.F.Hegel,Faith and Knowledge,trans.W.Cerf and H.S.Harri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7。 (15)OBBE,p.167,p.168,p.169. (16)Richard A.Cohen,Face to Face with Levina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p.22.以下简称FFWL。 (17)OBBE,p.8. (18)Ibid.p.177.弗朗兹·罗森茨威格(Franz Rosenweig)和斯蒂芬·茨威格(Stephan Zweig)在反对尼采学说的同时,对尼采的个人主义及其个人奋斗表示钦佩。 (19)Friedrich Nietzche,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trans.Douglas Smi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28.“对禁欲主义的上帝的信念一旦破灭,就有了一个新的问题:价值的真理。”列维纳斯也同样不“相信”“禁欲主义的上帝,”不相信从是论-神学(onto-theological)方面规定的神正论的上帝。参见FFWL,p.18。那里,列维纳斯答复科尔尼(Richard Kearney):“关于上帝存在这件事,没有人能说我相信,也没有人能说我不相信。上帝存在的问题不是一个向运用三段论逻辑的个人心灵提出的问题。这是不能证明的。” (20)OBBE,p.157. (21)Ibid.,p.159. (22)OBBE,p.165. (23)Ibid.,p.162.标签:哲学论文; 伦理学论文; 苏格拉底论文; 柏拉图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道德论文; 斐多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