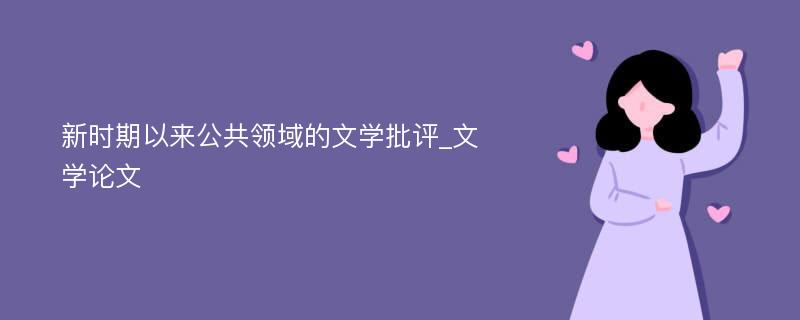
新时期以来公共论域中的文学与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批评论文,文学论文,论域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8-0077-03
对“公共论域”这个概念,这里不做经院式的考辨,它的通约性可以直接进入问题。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与批评,一直存在着与公共论域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通过媒体交换意见,表达对文学和批评的不同判断。在1980年代初期,由于媒体功能和掌控的绝对性,以及文学与社会生活的“蜜月”关系,除了公开批判背离主流文学的“异端”现象和思潮——比如对《苦恋》、《在社会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以及对“人道主义”、“异化”的批判、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等,文学在媒体中的形象总体来说还是正面的。198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对十年来文学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李泽厚甚至认为,新时期文学的十年,是继‘五四’以来新文学历史上最辉煌的十年,其成果无论从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以前,在艺术上和思想上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唐达成在代表中国作协的讲话中也认为,十年来我们的文学经历了从复苏到兴盛的空前发展,今天已迅速进入到建国以来最繁荣活跃的新时期,他特别强调,这个新时期应以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与上述表述略有不同的是张光年和朱寨,他们认为,新时期文学也许并非是社会主义文学最光辉的十年,但它无疑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十年,是文学起死回生、青春焕发的十年,是‘五四’以来又一个开放的时代。”① 虽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被称为“黑马”的刘晓波在同一时间提出“新时期”文学面临着极大的“危机”的论断,他认为:“不打破传统,不象五四时那样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中国人的生命永远摆脱不了理性化和教条化的束缚,文学就没有真正发展的一天。”② 但当时作为“非主流”的声音,虽然它在青年群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但面对肯定的主流还构不成挑战或威胁。
这种情况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历史上是很特殊的。在那个时代,文学的问题还没有、也不可能全部呈现出来。除了意识形态的规约之外,流行文化或通俗文艺还没有构成与文学和批评的竞争关系。那个时代的流行文化或通俗文艺的合法性还是一个问题,邓丽君或“书摊文化”还处于“半地下”状态。这种情况使1980年代的文学和批评在公共论域几乎没有有力的竞争对手,与意识形态密切缝合的改革开放初期文学在那个时代几乎一枝独秀。1980年代中期文学的分化,是文学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放缓了速度,部分文学,比如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分离了与社会同步的对应关系。这一变化使文学具有了两面性:一方面是文学不再直接地参与公共事务,不再对现实直接发言;另一方面,文学开始建构起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学的政治”。“文学的政治”在践行的同时也构建了新的批评标准,统一的文学批评尺度就是在那个时代结束的。但1990年代以后,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的合法性逐渐被承认,过去潜伏“地下”或“半地下”的流行文化迅猛地走向前台,几乎占据了消费文化的全部空间。现在被普遍认同的文学的“边缘化”,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现实的。
文学重返公共论域或再度引起整个社会关注,是1993年发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讨论出于对中国社会精神状况和文化状况的忧虑。比如普遍的人格萎缩、社会批判声音的消失、艺术与文学趣味的粗劣等。虽然那时的讨论对中国的社会现实都普遍缺乏切实的了解,使讨论一度陷于排队划线、更多的是在情感立场上展开,取得的学术性成果不多。但时至今日,回头看那场讨论提出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是变得越来越严重。人们对意义世界和价值观念的问题变得更加茫然。这种与现实建立关系的讨论,才使它有可能进入公共论域。这场讨论从开始至今整整十六年,十六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但人们在精神领域的变化究竟有多大是值得讨论的。包括当年参与讨论的学者,在社会结构中大多成了“中等阶层”,这些人的生活圈子也基本在这个阶层展开。他们的“生活经验越来越狭隘,缺少与社会下层的血肉联系。一个这样的在精神上越来越狭隘的人,他很自然就会逐渐远离那些尖锐的社会和时代问题。”③ 多年以来,文学的阅读处在越来越低迷的状态,与文学没有能力提出或处理当下生活中的尖锐问题是有关的。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媒体中对1990年代以来文学否定的声音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最集中的否定不是来自普通读者,而恰恰是包括文学研究者在内的“知识精英”群体。最集中的是发生在2006年的几起批评事件:一是《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的综合报道,“思想界”的学者认为:“中国主流文学界对当下公共领域的事务缺少关怀,很少有作家能够直面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最可怕的还不只是文学缺乏思想,而是文学缺乏良知。”“在这块土地上,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小说家中,还有没有人愿意与这块土地共命运,还有没有人愿意关注当下,并承担一个作家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④ 其次是岁末,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被歪曲地报道之后,国内作家、批评家作出的激烈反应⑤;第三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先生为该所“文情双月评论坛”所写的开场白:“为当今文学洗个脸”。这几起文学批评事件的态度和倾向大体相同。思想界对当下文学创作几乎作了全面的否定,而且言辞激烈;在顾彬的“垃圾门”事件中,尽管前提并不是真相的全部,但后来顾彬说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当代文学是二锅头,对当代文学还是否定的;而杨义先生对当下中国文学的批评,却是一个没有被歪曲的“中国顾彬”。他说:当今文学写作正借助着不同的媒介在超速地生长,很难见到哪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此活跃、丰富、琳琅满目。这是付出代价的繁荣,大江东去,泥沙俱下,不珍惜历史契机,不自尊自重的所谓文学亦自不少,快餐文学、兑水文学,甚至垃圾文学都在不自量地追逐时尚,浮泛着一波又一波的泡沫,又有炒作稗贩为之鼓与吹。于是有正义感的文学批评家指斥文学道德滑坡和精神贫血症,慨叹那种投合洋人偏见而自我亵渎,按照蹩脚翻译写诗,在文学牛奶中大量兑水,甚至恨不得把文学女娲的肚脐以下都暴露出来的风气。我们不禁大喝一声:时髦的文学先生,满脸脏兮兮并不就是“酷”。在此全民大讲公德、私德、礼仪的时际,我们端出一盆清凉的水,为当今文学洗个脸,并尽可能告知脏在何处,用什么药皂和如何清洗。我们爱护这时代,爱护其文学,爱护时代和文学的声誉及健康,故而提出“为当今文学洗个脸”的命题。⑥
这一评价对“当今文学”的不满溢于言表,他的基本看法与媒体中流行的看法没有区别。这种“道德化”的批评在今天是获得掌声的一个手段,但当今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用任何一种印象式概括或道德化的批评,都会以牺牲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性作为代价。文学批评在否定末流的同时,更应该着眼于它的高端成就。对这个时代高端文学成就的批评,才是对一个批评家眼光和胆识构成的真正挑战。这就如同现代文学一样,批评“礼拜六”或“鸳鸯蝴蝶派”是容易的,但批评鲁迅大概要困难得多。如果着眼于红尘滚滚的上海滩,现代文学也可以叙述出另外一种文学史,但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在“鲁郭茅巴老曹”,而不是它的末流;同样的道理,当今文学不止是被夸张描述的“快餐文学、兑水文学,甚至垃圾文学”,它的高端成就我相信很多批者并不了解。而思想界“斗士”们愤怒的指责,其实也是一个“不及物”的即兴乱弹。他们对当下文学的真实情况,也不甚了了。他们之所以义愤填膺地指责或批评当下的文学,只不过这是一件最容易和安全的事情。在对文学整体性否定的同时,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高度肯定和褒扬。在作家作品讨论会上,在文学专业刊物或大众传媒上,有大量对作家作品肯定赞扬的文章,那么,究竟哪种评价是真实的?因此,对文学的总体性的评价,是一个“承认的政治”的问题。
2004年以来,文学在公共论域上又一次引起普遍关注,与“底层写作”的大量出现和对这个概念的提出有直接关系。关于“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的讨论,从2004年至今一直是文学批评集中关注的话题。但是,关于这一文学现象的“认知焦虑”仍然没有成为过去。因为这是一个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文学现象。对这个文学现象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文学界,这个现象本身就不是所谓“纯文学”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继1993年关于“人文精神讨论”之后,十几年的时间里唯一能够进入公共论域的文学论争,因此意义重大。随着讨论的深入,问题的复杂性也逐步显露出来。比如,“底层”是社会学概念还是文学概念,是谁在写“底层”,“底层”的问题是否仅仅是苦难可以描述或涵盖的,“底层写作”的文学性如何评价,如何看待这一文学现象中的情感和立场,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了文学批评的进步和独立,在非“组织”的情况下,文学界主动介入这一话题,显示了文学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但另一方面,也有试图迅速将其知识化的倾向,这种“学院式”的批评似乎很“学术”,但历史已经表明,学院式的研究或批评首先要经过历史化的过程。急于将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纳入学院制度或范畴,结果就是远离了现实对象去纠缠概念、源流等“学理”层面的问题。因此,有些看似很学术的批评,恰恰将讨论引向了歧途。
“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等概念显然是临时性的概念。这种现象在当代文学中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伤痕文学”、“朦胧诗”、“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直到“私人化写作”、“70后”、“80后”等,这些概念都是临时性的,它们都还不是科学的概念,但这些概念是可以通约的,文学界都知道这些概念具体指的是什么。至于这些现象如何概括更合适,可以留给以后或文学史的研究。与此相关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底层写作”文学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在“专业”范畴里的讨论,对这个文学现象普遍的指责是“粗鄙化”、“苦难焦虑”等。对“底层写作”文学性问题的讨论是一个真问题,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清楚“文学性”究竟是怎样表达的。这个问题就象前几年讨论的“纯文学”一样,文学究竟怎样“纯”,或者什么样的文学才属于“纯”,大概没有人说清楚。
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说话曾经是不战自胜,“政治正确”也就意味着文学的合理性。但是,在今天的文学批评看来,任何一种文学现象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情感立场,同时,也必须用文学的内在要求衡量它的艺术性,评价它提供了多少新的文学经验。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许多年以来,能够引发社会关注的文学现象,更多的恰恰是它的“非文学性”,恰恰是文学之外的事情。我们不能说这一现象多么合理,但它却从一个方面告知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中一般读者对文学寄予了怎样的期待、他们是如何理解文学的。另一方面,急剧变化的中国现实,不仅激发了作家介入生活的情感要求,同时也点燃了他们的创作冲动和灵感。“底层写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纯文学”的讨论中,李陀说:“上世纪80年代所谓‘纯文学’的特点是去政治化,而未来的‘纯文学’很可能是很政治化的,会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商业文化提出特别强烈的批评和反驳。”④ 李陀可能将他的想法做了极端化的表达,但我同意他的看法。过去的“去政治化”,是因为政治对文学的干预太多,文学没有独立的精神地位;今天文学的“政治化”,是因为作家有介入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它是文学获得独立的另一个表征。当然。任何试图全面的概括都会词不达意,都可能走向片面。这些看法无非是在说明,文学走向公共论域,必须关心书写文学之外的“公共性”问题,对这些问题有提出和担当的愿望和能力。在我看来,文学的社会性和文学性不应也不会构成矛盾关系。所有的经典文学如果没有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它的经典性肯定是有问题的,又如何能够进入公共论域?如果仅仅潜心于“纯文学”,文学就只能在小圈子里流传和欣赏。这就是新时期以来文学给我们的经验。
注释:
① 陈骏涛:《从一而终——我的文学批评之旅》,载《芳草》2007年5期。
② 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载《深圳青年报》1996年10月3日。
③ 王晓明:《为啥“人文精神”大讨论不该忘却》,载《中国教育报》2006年3月3日。
④ 见《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南都周刊》2006年5月20日。
⑤ 见《中国作家、批评家集体反击顾彬》,金羊网2006-12-17。
⑥ 2006年12月23日06:16光明网-光明日报。
⑦ 李陀:《批评是批评出来的》,载《南方周末》2006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