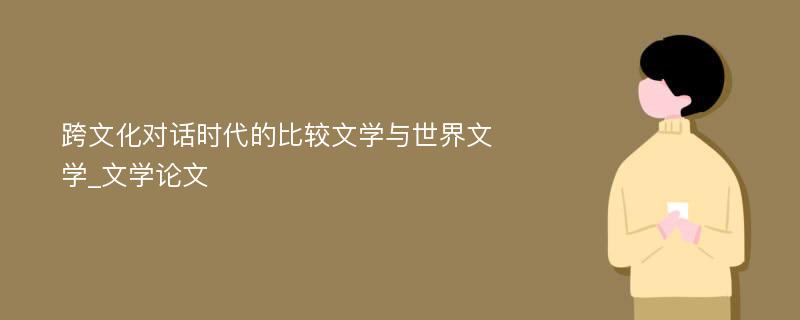
跨文化对话时代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跨文化论文,时代论文,世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这本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术集刊问世的此刻,我们距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国家二级学科被整合构建和教研实施,已经整整15个年头。时光流逝的速度总是超乎人的感觉和想象,当年热血沸腾、言辞犀利、为这一看似有些“拉郎配”的官方教育部门举措而展开学术论争的一代学人,现在大多已是两鬓染霜,只是不知道相互见面还会不会唇枪舌剑一番?如果意犹未尽,还有兴趣继续细探深究,这里又为诸位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专门为着研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学术关系整合而设。虽然出现得晚了些,但是就这一经过时间磨合之后正处在转型时代和面临提升突破的学科而言,似乎也算正当其时罢。其间,中国比较文学学界一干同仁的共识谋划和参与合办的各家院校的支持,无疑是这一平台得以建立的前提和未来持续发展的动力。仅仅是看一眼合办诸家院校的构成,我们也有理由对未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整合发展和学术创新表示乐观。
想当初,无论是为世界文学盘点,还是为比较文学划界,抑或是试图在两家之间说合结缘,无非都是为了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文学研究谋划和探路所作的努力。而今十多年过去,回想当年的认知,检阅近年的实绩,尽管可圈可点,但是当年看似不易调和的两支队伍,今天却在一个学科机制框架中似乎运行得不错,没听说哪个院校有分家的情形发生,重点学科倒是多了几家。瞧瞧网上的研究生招生目录,冠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招生院校几近百家,这规模在世界上大概也是数一数二的了。随便算笔账,教师没有一千恐怕也得八百。至于在读的研究生呢,哪怕是作最低估计,硕士、博士算上怎么也得有个两千多人吧。说给国外学者,无论谁听,都觉得这实在有些惊人。这情形恐怕也只有发生在当下的中国才不会让人感觉不可思议——实在是因为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大学生数量全球第一,如果将这些作为分母加以换算,与各国情形对照,说到底数量也多不到哪里去。
我想还是别忙着盘算家底,以规模取胜算不得真正的好汉,更谈不上领先的可能。其实在这十多年学科磨合发展过程中遗留下的问题,积累起来同样也相当多了,而且决不简单。不说当年争论的谁是谁非,很多问题并未时过境迁,就是这几年国内重新又拉开架势争论的,例如关于如何重新理解“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各自的热点话题,许多关节问题依旧与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纠结分不开。当然,首先应该承认,讨论的层次比过去无疑已经是高了很多,参与的学者也不再只局限于本土,许多国外知名学者也参与其中,已经逐渐自然接轨参与了国际文学研究的热点,算得上是站在了前沿。关于这一判断,有许多近年已经发表的著述和召开过的会议主题可以佐证,我在一篇文章中也有过简单介绍。①
应该指出的是,当年关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关系的争论,尽管观点五花八门,立场各自相异,但是,有一个基本的论述逻辑和叙述框架却是各方都无意间受限其中却不自知的,那就是大家都已经事先假定了各自学科在世界上学术存在的“历史独立合法性”和在中国学界的“挪移建构合理性”,然后才在如此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僵化基础上去讨论自身学科在相关学科结构之内的“存在正当性”和“不可替代性”。于是,主要的争论始终局限于从自身学科在中国的历史生成和积累去展开,完全无意关涉其在世界上曾经的历史生成过程中所遗留的问题,其在世界上目前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种种争议,以及学科挪移至中国本土后需要面对的文化水土和学术意义问题等等。于是,我们的争论基本只是指向本土学界的学科内战,包括通过学科在中国过去的发展和成就以图证明它们各自在学术上的有效需求,争辩它们的学科位置(譬如身处外语学科群还是中文学科群)是否恰当?它们学术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外语能力是否能够担当相应的学科使命?它们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理论侧重还是经典作品读解?它们的学术疆界各自在何处以及有多大的整合可能?等等。
不可否认这类学术论争的价值。也正是因为通过不断论争,才提醒我们注意各自学术疆域的问题和不足,并在学术实践中去不断加以修正弥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相互间的包容与发展。这也是十多年来,尽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被国家教育管理机构规定性整合为一个二级学科,学术上却依旧能够相安无事、各自发展的原因之一。而且近些年似乎还表现出学术上不断靠近、理性交流增多和有限整合不断加强的趋势,从而使得具有一定比较意识的世界文学研究和更加注重经典文本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渐次萌生。读读这些年发表的学术著述,看看近些年比较文学或者世界文学的学术会议上两个领域中学人交互参与,从客串到一身二任,从尝试到自觉交流的局面,情形令人略感欣慰。
但是,学科史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学科的存在和疆界是一成不变的,它们总是不断地处于生成、演变、相互整合以及成长为其他新的学科形态的过程中,没有哪个学科天生就具有亘古不变的治学格局。同时,我们也不能满足于这样一种基于并非完全自觉的学术选择和学术共识性不强的包容性存在状态。以中国今日社会和文化发展的趋势,以中国学界正在成长的国际学术对话和学科建设的迫切需求,像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具有国际性特征的人文研究学科,因其学科本身的特性,一方面应该通过直接面对和介入世界学界的学术嬗变,逐渐改变和增强学科自身参与世界同仁对话的方式和地位;另一方面,在建构中国现代学术的未来进程中,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更应该是义不容辞的先行者,从而理应有更高和更重要的学术担当。这一整合性的学科在性质上首先就是面对国际学界而具有跨文化交流特征的,但是它目前的发展现状相对而言却有些满足于国内学科疆界内的建构,自给自足,自我设限,总是情不自禁地在本土学术的圈子里打转,似乎总是被迫在数字化学术管理的重压下从事机械性的论著生产,想当然地自设和诠释着各种学术主题,却较少从学术前沿和热点问题意识的层面上去主动关注和参与国际学术对话。
譬如我们作为文化他者,选择研究19世纪英国小说家哈代的创作,如果罔顾这位作家在英国本土和国际学界研究的现状和经典建构变迁的实际情形,罔顾读解的文化差异,而是只管自己埋头读解阐释,40年前可以从当中揭示出阶级斗争的残酷和资本主义的罪恶,30年前则从里面发掘出人的异化主题和人道主义的价值,20年前从中找到人性善恶交战的永恒文学性追问,不久之前则开始关注作者对乡村环境的描写和热爱了,并试图从中去读出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证据,似乎3个世纪前的哈代便有了明确的环保观念。我甚至怀疑,接下来一些研究者很可能会从哈代小说文本那里发现早期绿色革命的见解和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证据。即便是借助比较文学的手段,将陶渊明拉进来进行比较,难不成结论中给中外经典作家和诗人一起披上一件绿色环保的新衣!这样的读解发明其实多有主观臆测和过度诠释的嫌疑,因为它和经典文本自身的关系是如此的游离,即便你把哈代换成简·奥斯丁,换成夏洛蒂·勃朗特,把陶渊明换成王维,解释似乎也一样能够成立。
我们迫切需要改变这种闭门造车、难如人意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虚假繁荣局面,如果呼吁学科研究回归文学的倡导是要回到这样一种完全外在于经典文本及其历史语境状态的研究,那我看还是暂时不回归的为好。即便是我们确信雅各布森和德·曼之类的文学性理论有道理,相信通过区分文学语言与日常普通语言可以从语义模型分析的精确层面去判断文学与非文学的差别,然而,在真正比较文学的意义上我们还是没有把握,即当阅读的文化语境发生了根本性跨越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对自己的分析确信不疑?一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是含蓄的。我们以为词华够鲜艳了,看惯纷红骇绿的他们还欣赏它的素淡;我们以为‘直恁响喉咙’了,听惯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是低言软语。同样,束缚在中国旧诗传统里的读者看来,西洋诗里空灵的终嫌着痕迹、费力气,淡远的终嫌有烟火气、荤腥气,简洁的终嫌不够惜墨如金。”②
我们的确有许多的问题需要研究和讨论,其目的心愿都是为了改变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在国际学界以规模取胜的局面,更是为了在这样一次重大的转型过程中通过理性的思考去接近学科研究的真实需求。毫无疑问,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经典文本的深入研究是一切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更需要反思学科本身,需要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样的学科研究重新置于全球学术对话的语境下,从思想史、学术史和学科史等不同方面去认真加以审视和思考,使其对外能够真正成为国际学术发展的有机部分,对内能够贴近现实的学术文化诉求并发出自己的声音,进一步认真去探寻学科的未来发展之路和价值目标,争取实现学科和学术上的世纪性提升。这正是我们不揣简陋,决意要在现有的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等众多刊物之外,再创办一个至少在刊名和学术宗旨上能够完全覆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杂志的意图。
众所周知,无论是比较文学还是世界文学都是十九世纪欧洲知识的学科化产物,它们作为一门学科“发生”和“建构”的历史,总是与欧洲资本主义和现代西方文明在全球的崛起以致一家独大的历史密不可分地纠结在一起。而今日作为非西方社会的一部分,譬如我们中国的相应学科则是在对方的学科遗产框架基础上的整体挪移、延伸性生长和套用式的建构。用达姆罗什的话说就是:“经过主要在北美和西欧的长期实践之后,比较文学现已在全球数十个国家里拥有其追随者。”③的确,我们就是追随者之一。其实,观察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研究和大学教育领域,从西方复制来的学科规模相对于由自己原创的学科,前者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由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面对这种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学科机制和发展态势,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地在师法西方,在忙着学习和搬用,并且一直在追问和质询这种学习学得像不像、学习得是否正宗,天长日久,潜移默化,这些学科的结构体制、研究范式、知识标准和方法论体系似乎就成了被自然接受的学科“真理”,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学科。学科所包含的学术普遍性要素被无限放大,学科的观念性错位、价值性悖离、根本性的结构缺陷却被掩饰和缩小,所谓的学科革新被理解成了一种拾遗补缺性的经典文本的搭配性补充和文学史章节的有限添加,学术范式的格局大致不变或略有调整,而原先的价值标准和体系整体却始终是毫发无伤。
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本来出生和成长于欧洲的所谓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从一开始就不是“世界性的”,而是属于欧洲那个“地区性”的学科门类,从一开始他们就存在着文化血统先天带来的各种文化中心主义局限,而我们却偏偏将其误读为不言自明的普适性学科了。这并不是个人作为文化他者情绪性或者文化民族主义式的论述,而是西方严肃学者自我反省之后十分较真的判断。
关于比较文学学科,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就直言不讳地说,“出现于19世纪晚期的学术研究的这一分支是专门研究欧洲文学的,它比较的文学作品都来自有着派生关系——渊源、影响和接受等——的不同语言,那时的研究题目包括现代文学的古典源头,欧洲文学中的彼得拉克传统,莎士比亚在德国文学中的接受等等”④,因此,说到底,比较文学是门“有着欧洲中心主义传统的学科。”⑤即使是在美国比较文学学界于平行研究、理论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方面掀起变革热潮并取得研究进展后,也至多是将这种格局挤开个缺口,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比较文学学科的欧洲中心格局,只不过换了一种表达,开始称为西方中心主义了。
而关于世界文学学科,意大利学者阿尔曼多·尼希则强调指出:“我必须再次重申,欧洲文学是在19世纪帝国殖民地的渐进征服中才完成了对世界之征服的,正如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了解的那样,而非歌德和F.施莱格尔所梦想的从欧洲心脏德国勃然而兴的那种‘普世诗歌’。爱德华·赛义德在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已明确指出了介于欧洲文学与殖民主义的这一结合点。”⑥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欧洲文学对世界这种征服的结果比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殖民要来得巧妙得多,它抓住人类文学阅读审美想象的可培养性、生长性和多元性特点,通过媒介传播、学校教育和浸染性影响,将欧洲文学的基本价值理念以及诸如文艺复兴、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关于文学的理论和历史观念进行跨文化灌输,也包含通过种种艺术范式和审美习惯持续不断地施加影响,不断使之深入人心,并渐次成为我们的审美无意识,成为批评的标准性元话语,令你想摆脱也难!于是,欧洲文学便在非西方的中国成了世界文学的代名词,即便是此后一段现代历史中陆续有美国文学强势挤占了欧洲文学的一些地盘,也有个别属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非欧洲文学点缀性地穿插其间,可依旧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所谓世界文学的欧洲基本盘面。
然而有些令人费解的是,在今日非西方的中国,历史上和现实中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这种实际存在的地区性学科真相与虚假的世界性学科命名之间的错位却很少有人去正视,也缺少类似的针对性热点话题讨论,好像谁也不愿意去指出皇帝新衣的虚幻性。我们似乎在以西方为主体的文学经典和西洋文学史、西洋文论读本的各种主义论述中被催眠了,思维被限定了。看看身边的学术活动,常有欧美名校的比较文学和英美文学教授来北大讲学,人家一个讲座常常能把《奥德修斯》的出征还乡经历与西方当代社会核心价值千丝万缕的关联讲个透彻,可以把介乎宗教哲学和文学经典的《神曲》中的宇宙本体观念与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梳理出切切实实的精神联系,而我们的学人外文口语会话虽然比上个世纪流畅了许多,然而同样的经典文本却始终只能是在机械的形象塑造、主题总结、叙事特征、人道主义和不着边际的哲理阐发上做僵化的诠释,流淌不出一点经典的鲜活气和生命力。当外面的和尚都时不时地在做点自我反省,批判自家欧洲中心主义学科历史观念的时候,这件本该由我们来推动的工作倒由别人率先来提示了。包括尼希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指出要向非西方学习,要坚持不断反省、修炼和克服自己文学上的沙文主义和中心主义意识——例如乔纳森·卡勒也在反复思索:“什么样的可比性能够引导比较文学从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学科向一种更加全球化的学科转化呢?”⑦老实说,卡勒的心结是要从质疑所谓的可比性去突出问题的所在,他这样的思路虽然有学科方法论上的价值,却很少质疑学科自身体制上的许多根本问题。不过,这样的反思和建构,按说,首先应该是由我们这些追随者在学科接受性建构和实践过程中率先来加以追问和批评研讨的,只不过我们的追问不仅仅是要去研究如何推动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从欧洲中心主义的学科走向全球化的学科,更在于立足我们自身古老的传统资源和现代学科建构需求所面临的众多障碍和挑战,既要有效地利用好资源和机遇,又要争取卸掉传统的自大心结和避免一切均被装进现代性包袱的陷阱。因为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追问:当比较文学真的走出欧洲中心主义之后,凭什么接下来就一定是中国出彩?日本、印度、韩国等其他同样边缘文化的全球化文学机遇又在哪里?
在经历了30多年的学术开放和外来理论的洗礼之后,我们早已开始深刻地认识到,一方面,理论的引进和革新对于研究深化和学术突破的意义是如此的重要,但是另外一方面,当舶来的理论问题越是被深入追问的时候,其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所遭遇的处处陷阱、文化误读和如临深渊般的感觉也越是突出。正因为意识到这种种的新挑战和新课题,在目前这样一个学术范式和学术伦理始终都在迅速改变的时代,我们不仅需要不断突破自身文化学术传统的各种精神禁锢,同时也必须对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学科意识和理论观点加以质询和重新认识,从而争取避免在后续发展过程中落入自设的逻辑陷阱,避免未来在面对更多非西方他者文化介入的时候所可能面临的今日西方式的文化质询的尴尬。
譬如,尽管一般学科史的叙述都能证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学科都是19世纪欧洲文化的产物,不过这里也许还是有必要强调,如同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文明的发展一样,它们之所以得以崛起,多多少少都是拜千年少有的历史机遇帮助而取得的成功。因此,苏源熙便试图进一步指出,“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所有文学都是比较的,受到许多溪流的哺育。”⑧他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的泥版文献、圣经、佛经等众多文献的内容、翻译和传播案例,证明跨越文化的交流很可能才是历史上文化发展的常态之一。沿着这一学理逻辑继续追问,我们自然便可以去大胆清理不同文化和文学的发展在历史上与其他文化交流共生的更多线索和事实。譬如目前有的青年学者已经开始尝试清理佛经翻译中群体译者之间的语言传递关系,分析译场权利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特征,由此期望经由不同的文化间不同的翻译历史和翻译实践路径的研究,去发现与西方传统译介学理论的差异,进而超越欧洲学科定义去对比较文学的历史生成和研究理路开启不同的认识。在这一意义上,将欧洲中心主义的比较文学推向真正全球化的学科研究就不再是口号式的愿景,甚至也不仅仅是面对未来的努力,同时也很可能是回头反求于学科历史和惯常经典阐释范式的切实的学术研究思路。这将进一步证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学科概念尽管出自欧洲的特定时期和语境,但是,其在诸如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地区的研究,却注定会有着明显不同的认识论基础,具有属于自身的理论逻辑起点,从而也就有理由在实践中去构建自己的学术主体身份、范式结构和方法学体系,推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文化异地重组和深化,使其真正成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的动力组成部分,使非西方的研究者由追随者变为创新者,由被影响者变为提问者,甚至可以反哺性地去推动曾经的学科发明者的学科意识更新与转化。
实际上,不仅对于过往学科史的反思具有催生新研究领域的可能,即便是对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际研究的新进展和新问题意识的积极参与,只要不是照单完全接受,而是基于自身真实的学术境遇去展开思考,结论也绝不会人云亦云。我们注意到,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性重大发展就是对于当代西方新理论、文化研究和新的批评方法的译介、提倡、构建、推广和发明应用。德·曼、德里达、杰姆逊、赛义德、斯皮瓦克、克里斯蒂娃等理论家的身影不断游走于各类比较文学的学术会议,热衷后现代主义研究的佛克玛还担任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主席。作为普遍的学术共识,必须承认,比较文学界对20世纪新理论这种积极推广的结果,使得人们的文本研究重心全面突破了传统的西方权威经典作品,进而面向了大量当代鲜活的非经典作品。比起以英美法德为主的国别文学系科,比较文学在西方率先开始解构了经典的秩序,推动了世界文学研究的进步。但是明显与其不太相同的是,诸如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研究者首先遭遇的尴尬却并非是要去解构别人和自己的经典,而是迫切希望通过大声疾呼和实际的努力,使自己被近代欧洲中心理论见解淹没的传统文学经典能够被重新认识和安置,使之融入现代文学经典世界的格局,解决一个所谓为世界所承认的难题。如果说在中国从事世界文学经典教学研究的学人面临的学术自我期许,是要通过自身的工作,让外国文学经典在异己文化中为中国读者所接受,而不是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把经典过度诠释致“死”,那么,对于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而言,刚好有一个相反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比较和诠释的辛勤工作,力推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走进世界,而不是像西方学者那样借助解构和非本质主义的种种理论去消解经典、改而面向一般文学作品。于是,中国的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界同时遭遇了关于经典研究和诠释的双重难题。要想不至于把外国文学的经典诠释致“死”,你就必须在本土文化前理解和审美接受屏幕当中去找到充满陌生化审美特征的外来经典欣然接受和分享的入口,开启有效的理解逻辑之门。而一个以毕生精力研究陶渊明、对他的每一件作品都如数家珍的中国研究者,如果不能联系西方的某些浪漫主义或者乌托邦理论,与诸如华兹华斯以及梭罗之类作家和诗人的创作做出深刻的比较性联系,他又如何去引导欧美读者像理解寒山那样的去认识陶渊明作品的诗意之美呢。经典的这种经典化过程和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不同文化语境中不断成长的历史经验,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本身的内涵价值之外,同时也离不开所处的外在环境,离不开比较和诠释的功夫,人们正是在比较和诠释的过程中筛选、认定和建构了经典的意义。既然闹了半天,关于经典的生成故事原来就是如此地与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联系在了一起,那么,说来也巧,现在我们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整合成为一个学科,难道不是正好顺应了学术历史发展潮流了吗?命运真会给人们开玩笑,你想进这个门它死活就是不让你进来,而你不愿进那个门却歪打正着地走了进去。按照一般的价值理性,我们该把经典视为跨文化的资本,可以直接当礼物郑重地送给别人。可是实际情形常常是这样,那就是你送给他他未必有兴趣收下,倒是经过一番吆喝和讨价还价之后,他却愿意花钱买下还说声值了。谁会说,这种文化交流的悖论不是新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得以链接的纽带呢。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在国别文学的逻辑理性认知路径和经典文本的价值确立理性之外,还有一个近于哈贝马斯式的跨文化交往和跨学科整合认知的学术路径呢?也许,它可能就是作为今日新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构的方法论关键之一。围绕着这一认识内核,我们显然可以期待建构起某种属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新的独特方法论结构,这一方法论体系既是比较文学的,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或者说,它们之间压根就没有本质的区分,本来就是一回事。
如果真的存在达成这种新的跨学科整合理念和方法论共识的基础,那么,我们到何处去寻找和发现类似的尝试性研究实践萌芽,或者说可以引发参照的研究范例呢?并非完全是无意和随机地,我们在这里还是第一时间想起了钱钟书。作为一个精通中外语言、经典和理论的学术奇才和成就卓著的大师,钱钟书的学术贡献完全毋庸赘言,学界早有定论。而他对于比较文学、尤其是比较诗学的原创性贡献,使得你几乎没法用现成欧洲中心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范式去界定他的研究,所以就是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如此类型的所谓比较文学家。但是,他的跨越多种文化和学科的研究实践以及学问理念,却无意间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新的学科形态构建提供了典范式的证言。清理他的学术著述,几乎无例外的都是从中外经典的文本细读和精读出发,又都是围绕着各种丰富的中外理论入手展开,他的分析充满似乎信手拈来的例证和比较,古今中外,风雅通俗,一片众声喧哗。他选定一个问题,譬如通感,譬如人化批评,譬如中国诗与中国画的关联,譬如诗无达诂等等,你会在他逐段逐节的研读分析中发现一种严谨而又生动有趣的论述逻辑。那就是,问题一旦呈现,往往先是中外理论大师的著述言论出场宣示观点,譬如亚里士多德和刘勰的言述;然后很可能是拉伯雷与罗贯中小说笔下的人物出来证言;接下来,中外剧曲或者书画艺术大师将走进来掺和;最后中外民间的街谈巷议和市井俚语也插科打诨出来帮忙圆场,就这样深入浅出地演出了一场又一场鲜活生动的跨文化文艺对话剧情。初看似杂乱循环无系统,其实话语底下的论述逻辑却严密得紧,不信你去改写一下他的文字理路试试,恐怕没那么容易找到缝隙。在他的论述视野中,不仅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没有了界线,甚至更多学科之间的壁垒也都纷纷坍塌,一概整合成为跨越性多元文化文艺对话的最佳场域。这,也许就是未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者企望的学术境界罢。
乔纳森·卡勒断言:“对世界文学发生兴趣,将其作为包含多重可能性、多种形式、多重主题、多种话语实践的包容性场域是可能的。”⑨这当然是就比较文学研究者而言。其实,对于一个曾经的世界文学研究者,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旦他突破旧有的学科藩篱,在跨文化对话的场域中,在各种富于启发性的理论言述引导下,换一种眼界来面对书柜中沉睡的世界经典作品时,他完全可以期待其中的社会生活和人物形象都会幡然醒来,闹哄哄地与众人一起走向文学的未来。
本着这样的学术理想和认知逻辑去重新关注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确让我们预先感受到了些许的兴奋。
注释:
①参见拙文《什么世界?如何文学?》,载《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2期第2页。
②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载《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页。
③达姆罗什:《21世纪的比较文学》,载《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前言”第3页。
④[美]乔纳森·卡勒:《比较文学的挑战》,载《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1期,第2页。
⑤同上书,第4页。
⑥[意]阿尔曼多·尼希:《全球文学和今日世界文学》,载《中国比较文学》2002年第2期,第129页。
⑦[美]乔纳森·卡勒:《比较文学的挑战》,载《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1期,第9页。
⑧苏源熙:《噩梦袭来缝精尸:论文化基因、蜂巢和自私的因子》,载《新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页。
⑨[美]乔纳森·卡勒:《比较文学的挑战》,载《中国比较文学》2012年第1期,第12页。
标签:文学论文; 比较文学论文; 世界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艺术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