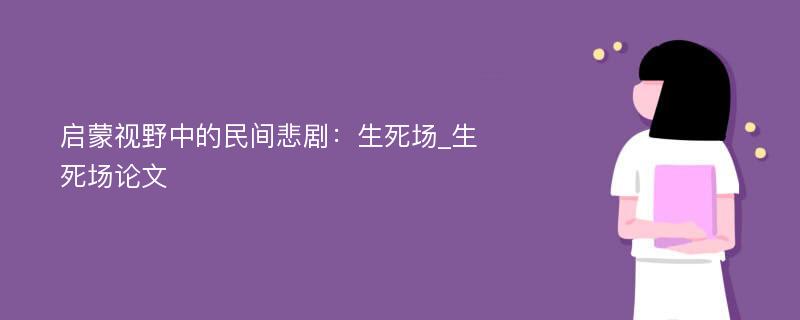
启蒙视角下的民间悲剧:《生死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悲剧论文,生死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4)01-0046-10
一、民间和启蒙的汇集与冲撞
在193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由于“民间”的进入,给新文学的创作带来了一股不同以往的生机和活力。民间文化的思潮不像“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陈独秀、胡适自主意识很强的情形下推动起来的,它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这些作家中,恐怕只有沈从文有些自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1930年代,“五四”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实际受到了很
大的阻力。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可能永远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无所依傍的状
态,所以这时很多知识分子,包括鲁迅,以及当时的一些左翼作家,都在思考以知识分
子启蒙精神为特征的文学,或者说文化普及运动,如何真正地跟它的对象——中国的民
众——结合起来。
这时就有一批新生代作家崛起了,他们的新的艺术实践,使得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创作上得到了回应。这批作家来自于中国民间和社会底层,跟“五四”一代不大一样。“五四”一代作家大多数都曾出国留学,接受西方思想,然后带了一套新思想或社会改革方案回到国内(北京、上海)来推广,有点像今天的海归派。而老舍、沈从文、萧红、艾芜、沙汀、李劼人等等,除了李劼人是留法学生,绝大多数来自于生活底层,带了一身属于他自己的乡土文化,进入到这个文坛。像老舍,他是从北京市民中长大的知识分子,与市民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萧红则来自开阔和粗犷的北方,坎坷的生活经历和敏感的内心,使得她的文字非常贴近中国的现状。我把他们的创作思潮,界定为民间文化的思潮。
由此而来的是民间与启蒙的关系问题。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对立的。以启蒙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民间始终处于封建的野蛮的落后的愚昧的生活状态中,是需要现代知识分子来启蒙的。启蒙,就是拿了西方先进的文明思想武器来开启民众的心智,提高民众的素质,这是启蒙文学的基本特征。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就有这个特点,我们读《阿Q正传》、《风波》、《药》等等,不难发现鲁迅笔下的很多人物处于被启蒙状态。而民间则是另外一种状况,当一批作家从民间社会来到中心城市,并且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便不自觉地连带出自身的生命能量,他们所要表现的是,在高度的压迫之下,在非常残酷的生存环境之中,中国的民间是如何生存的。
中国的民间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没有力量,它就不可能生存下去。如果以启蒙的角度来看,民间就是落后的、愚昧的,没有力量的,它也理所当然是不合理的,肯定要被消灭。如果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看,文明的一定要战胜愚昧落后的,强大的一定要消灭弱小的。但是,真正来自于民间的作家不是这样理解的,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民间那么愚昧、落后、糟糕,可是,它没有被淘汰,还在顽强生存。他们在追问维持这种生存的真正力量在哪里?中国的民间生活方式有没有合理性?这些问题过去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萧红谈到过她与鲁迅的区别:“鲁迅以一个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去悲悯他的人物。……我开始也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这似乎说明鲁迅真有高处,而我没有或有的也很少。……这是我和鲁迅不同处。”(注:转引自聂绀弩《萧红选集·序》,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这一方面道出了她的创作受到鲁迅的影响,《生死场》就有对国民性的批判,另一方面又表明萧红是站在与鲁迅不同的位置上来观察和表现生活的。她作品里面包含了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她是受了新文学的影响,她要用“五四”新文学的启蒙意识,来剖析她的家乡生活;可是另一方面,她自小接受的家乡民间文化与个人丰富的生活经历,抵消了理性上对自己家乡和这一种生活方式的批判。这两者之间就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冲击力。
《生死场》中,启蒙和民间两种元素体现得都很充分。从大的方面讲,作品写这里的人是如何从愚昧、麻木的状态到最后的觉醒和反抗,这很明显是以启蒙的眼光来看的。比方说作品中的人物,都如同动物一般生活着,用胡风的话说,就是“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1],用这种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民间生活,芸芸众生都像没有灵魂的动物一般。如麻面婆,作者总是用那些蠢笨的动物来形容她:“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那样,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让麻面婆说话,就像让猪说话一样,也许她喉咙组织法和猪相同,她总是发着猪声”。[2]同时,作品中对农民文化的软弱性的批判也很强烈,比如赵三本来要反抗地主的压迫,却不幸因失误而进了牢狱,地主为了笼络他,把他从监狱中弄了出来,他出来以后锐气顿失,不断地说“人不能没有良心”,拼命为地主讲好话。作者在写这个人的时候是用一种嘲讽的笔法,带着批判意味,至少可以说他是没有觉醒的,还处于蒙昧的意识中。这都带着启蒙的印记,但如果《生死场》仅仅是这些,那它最多是一部思想进步的作品而已,还谈不上是一部有生命力的艺术品。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作者凭着她对民间世界的了解和对底层人的情感,以她特有的艺术直感,写出了民间生活的自在状态,这使《生死场》又具有非常震撼的真实性。作者没有粉饰什么,就像赵三,中国农民就是这样,为情感而打动,重伦理,讲良心,看重民间简单的原始道义。中国农民天性中本来也有着不稳定性,受了惊受了挫折,他就不敢再尝试了,这是非常真实的,而没有故意去塑造一个高大的农民英雄。包括后来日本人来了,这里的民众已经萌发了反抗意识的时候,作者也没有刻意去拔高,写“爱国军”举着旗子从家门口走过,“人们有的跟着去了。他们不知道怎样爱国,爱国又有什么用处,只是他们没有饭吃啊!”(一五、《失败的黄色药包》)这是大实话。在第十三章《你要死灭吗?》中,因为抗日宣誓,找不到公鸡,只好杀与二里半相依为命的羊,二里半舍不得,但也清楚救国事大,所以酸酸地说了句:“你们要杀就杀吧!早晚还不是给日本鬼子留着吗!”但当人们在庄严地宣誓时,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只有二里半在人们宣誓之后快要杀羊时他才回来。从什么地方他捉一只公鸡来!只有他没曾宣誓,对于国亡,他似乎没什么伤心。他领着山羊,就回家去。”这是非常逼真的一幕,在中国民间,似乎没有什么比与个人生存相关的东西更被看重的了。作者在写这些的时候,并非一味地批判,相反,她在更大程度上是不断地在认同和强化这些生存的法则。
这里要谈到爱国主义的问题。那是什么时候?是抗日战争烽火起来的时候,“九·一八”事变,东三省已经建立了满洲国,日本人马上要侵略全中国,民族感情高涨的时候。在这种时候,很多人出于爱国,出于激励民众保卫国家的需要,往往是把日本人占领以前的生活描写得很好,田园风光,农民与世无争,处在田园牧歌中。然而日本飞机来轰诈了,老百姓流离失所,一切都变得暗无天日。有一首歌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就是说家乡的土地多好,庄稼多好,人多好,现在我们都失去了。当时抗日的时候,这样的一种宣传是需要的,而且这种宣传是能够激励起大多数人的爱国情绪。但是,萧红不是这样。萧红写到的那种不能忍受的生活,就像胡风说的,像蚁子一样的生活(我觉得小说的前半部分写得好,被占领以后的场景还是比较概念化的),恰恰是日本人占领以前,是在抗战以前的中国,一个古老的中国。那么当日本人进入以后,生活更糟糕,连蚁子一样的生活也做不到了,人都被杀掉了,然后这些人要起来反抗,那么,以前是不是值得留恋呢?也不值得留恋。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当我们在提醒读者做异国的奴隶是很糟糕的时候,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宣传了,就反过来说,我们宁做自己人的奴隶。做自己人的奴隶也是糟糕的。对于人类来说,只有两种生活状态,一种是自由尊严的生活,一种是奴隶一样的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生活。对于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生活,不管是自己人统治还是外国人统治,都是一个概念,都应该对这种生活方式深恶痛绝。所以,萧红的《生死场》整个境界就比当时宣传抗日的一般作品要高得多。但是这样的东西不容易被人接受,人家会说,中国东北的农民那么苦,那么落后,那么愚昧,日本人应该进来。可是萧红作为一个作家,就在这里体现了她的良知和严肃性。她并不因为日本人侵略了,就要把以前说得那么美好,这也是《生死场》比较独特之处。
过去很多启蒙知识分子离开自己家乡的时候,好像是掐灭一个香烟屁股,恨不得赶快把这噩梦一样的生活结束掉,然后奔向新的生活。就像上世纪80年代许多人出国时的感情一样,可是到了新的现实生活环境当中,在现代社会一滚一爬,沾了很多污秽的东西以后,突然发现生活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有的时候,这两种文学也是有冲撞的。这种冲撞在萧红的作品里表现得特别强烈。
萧红不像沈从文,沈从文是用美化自己家乡的办法来抗衡都市的现代文明,而萧红则在坚持启蒙立场,揭发民间的愚昧、落后、野蛮的深刻性与展示中国民间生的坚强、死的挣扎这两方面都达到了极致。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萧红应列于中国现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家之林,张爱玲跟她相比就差得多了,不是差一点,整个生命的容量不是一个等级的。张爱玲完全是大都市培养出来的一个非常苍白的聪明女人,可是,萧红是很不聪明的,很粗糙的,甚至有点幼稚、原始,但是,在生命力的伸展方面,她所能包容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远在张爱玲之上。中国的读者喜欢张爱玲而不喜欢萧红,我觉得是很可悲的。
二、《生死场》的文本解读
1.原始的生气和生命的体验
《生死场》创作于1934年。萧红跟萧军结合后,一人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萧军写的是《八月的乡村》,萧红是《生死场》。当年的4月20日至5月17日,《生死场》曾以《麦场》、《菜圃》为题在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副刊发表了前两章,后来萧红萧军从大连逃到青岛,在青岛完成了这部作品,并将原稿寄给了远在上海的鲁迅,那时他们也不认识鲁迅。同年11月,他们也到了上海,生活没有着落,作品也发表不出去,只好求助于鲁迅。因国民党图书检查委员会审查未被通过,鲁迅只好以“奴隶丛书”的名目自费出版,其中只有三部书稿: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鲁迅分别为它们写了序言,对于《生死场》似乎特别重视,还请胡风为它写了《读后记》。他们高度评价了萧红的创作,一下子就奠定了她和萧军在上海文坛的地位。
萧红后来还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一个短篇《小城三月》,都是非常精致的小说,但我对还不太成熟的《生死场》格外关注。并不是说我不喜欢《小城三月》和《呼兰河传》,其实《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一个精品,艺术上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状态,而《小城三月》是一个迷你的《呼兰河传》。但是,我更喜欢《生死场》,主要是看重它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冲击。这个作品很不成熟,但是它有原始的生气,有整个生命在跳动,有对残酷的生活现实毫不回避的生命体验。
《生死场》写了东北一个小村庄中一群人生生死死的生命状态,写法上可能会让人挑出很多粗糙的毛病,但作品中惊心动魄的力量也直逼人心。比如第七章《罪恶的五月节》中写到的王婆服毒自杀,棺材买了,坟也挖好了,剩下最后一点气息了,“嘴里吐出一点点的白沫”,这时候几年没有见到的女儿回来了,她不知道母亲这个样子,她本来是生活不下去,投奔母亲而来的,看到这个情景,感情有一个巨大的逆转:“那个孩子手中提了小包袱,慢慢慢慢走到妈妈面前,她细看一看,她的脸孔快要接触到妈妈脸孔的时候,一阵清脆的暴裂的声浪嘶叫开来。”这种哭声是迸发出来的,带着一种埋在心底的力量,非常有穿透力。男人们却在嚷叫:“抬呀!该抬了。收拾妥当再哭!”。好像人死了根本不当一回事儿,他们完全没有感情,只是在完成一件工作,所以要“收拾妥当再哭”,这也不是那种细腻的情感,而是粗糙的,没有一点软绵绵的温情。女儿的到来让大家弄清楚王婆自杀的原因,原来是当胡子的儿子死了。大家在心理上已经接受了王婆的死,可谁知道事情却突然又有了变化:“忽然从她的嘴角流出一些黑血,并且她的嘴唇有点像是起动,终于她大吼两声……”于是有人慌忙喊死尸还魂,怎么办?拿扁担去压!“赵三用他的大红手贪婪地把扁担压过去。扎实的刀一般的切在王婆的腰间。她的肚子和胸膛突然增涨,像是鱼泡似的。她立刻眼睛圆起来,像发着电光。她的黑嘴角也动了起来,好像说话,可是没有说话,血从口腔直喷,射了赵三的满单衫。”血都喷了人一身,写得够恶心的,但在垂死挣扎中人的顽强的、坚忍的生命力也可见一斑。写到这里,大家觉得她必死无疑了,人也装到棺材里面了,要钉棺材盖了,但是“王婆终于没有死,她感到寒凉,感到口渴”,她说了句“我要喝水”,就活过来了。前面非常夸张地写到了死前的挣扎,可是这么平静的几句叙述中她又活过来了,如果我们从理性的角度说,至少前面应该有一个铺垫,她没有死,可是前面写到她那么像死的样子,怎么又会活过来?当然一定要找理由也是可以找到的,赵三拿扁担一压,黑的血吐出来,就把毒的东西都吐出来。但是我觉得,萧红的小说里,好多这类场景中对生命的那种体会、那种感受,都写到了极致。生命不是按照我们正常逻辑在那儿慢慢演化,她写到人死的时候,就把死的状况写到了极点,好像生命已经死灭,可是突然一个转变,生命又活过来,爆发出一个新的迹象。在这种极端的状况下生命中本质的东西才显露出来。如果是进入到文明状态,她不会这样写,这种极端的状态属于另外一套话语系统。再比如里面写到金枝怀孕以后非常痛苦,她摘柿子,把青色的柿子摘下来,她妈妈一看到这个情景非常生气,就用脚踢她,然后她就说,“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二、《菜圃》)。看到这里,我就想到萧红的《呼兰河传》中所写到的“在我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萧红全集》P759、P760)估计这是萧红小时候真实的经历,在生命非常粗糙的环境当中,野蛮已经成为习惯,甚至弥散在亲人之间了。萧红有这种惨痛的经验,她才会写出金枝和她母亲的这种关系。
《生死场》写得很残酷,都是带血带毛的东西,是一个年轻的生命在冲撞、在呼喊。我觉得这样的东西才真是珍品!她的生命力是在一种压抑不住的情况下迸发出来的,就像尼采所说的“血写的文学”。这样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这不能用一般的美学观念去讨论,它要用生命的观念去讨论。所以,这部《生死场》是一部生命之书。
关于民间理论,我曾写过很多文章,但是,我一直没有写出一篇谈民间的美学理想的文章。民间的美是什么?很难一下子说得清,但它有这种能力,把一切污秽的东西,转换为一种生命的力量。这样一种东西,很难说美,美不美就看生命充沛不充沛。而生命充沛总是美的,它带来一种原始的血气、一种粗犷、一种力量,这样的东西在美学上,我认为是最高的境界。第一义的美一定是来自于原始生活,来自于朴素的大地,是健康的,与大自然是沟通的。至于残缺的美、病态的美、生肺病的美,这是第二义的,第二境界的。就好像我们在讨论人物,像林黛玉当然是很美的,但这是一种病态的美,病态实际上不美,它里面有心理层面,有感情层面,很多东西配上去才是美的。好像一片原始森林浩浩瀚瀚,郁郁葱葱,才是美的,总是比一个盆景,一棵松树树枝弯来弯去的要美。你把树枝弯了十二道弯,手工很巧,但这不是树本身美,是你做出来的。但是另一方面,自然本身又是可怕的,残酷的,当我们在讨论这个美的时候,绝对不能忘记它残酷的一面。中国的古诗、西方的名画在表现大自然的时候,总是表现恬静的静止的东西,它只选取一个场面,把某个大自然的景象定格下来,这当然非常美。但是,如果你进入到生活场里,到大自然本身当中去,它根本就不是静止的、定格的,它是生生不息的;它美,就是因为它有生命。当我们在讨论自然美的时候,静止的美是第二义的,更高的美是一种动态的美,永远在涌动的这样一种生命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美。这样一种美的东西,它一定是不纯净的、纯粹的。所以我想用一个词,这个词其实很不好,我把它活用了,就是“藏污纳垢”。藏污纳垢是很可怕的,污和垢都是生命当中淘汰出来的东西,但问题是,大自然一定是藏污纳垢的。我们仔细看看空气,空气里都是细菌、肮脏的东西,大地也是这样,生命也是这样。死的东西,它转化为腐蚀质来肥沃土地,就转化出另外一种生命。你走进原始森林,首先闻到的就是一股腐烂的味道,大量的树叶都掉下来腐烂,然后它形成一个新的有生命的世界。
《生死场》中所描绘的世界就是一个“藏污纳垢”的民间世界。这个作品的开场似乎是很诗意的田园图景。作者笔下的榆树、山羊、大道、菜田、高粱地、农夫,这是东北特有的风光,但你马上就会发现它跟沈从文笔下的场景截然不同。《边城》在言说自然美之后,接下来是写民风的淳朴,连妓女都带着情义,但《生死场》首先出场的是“罗圈腿”,他的羊丢了,就没头没脑地去找羊,又因踩了邻人的菜而打架。即使是农民劳动之后的休息时间,大家坐在一起闲谈,内容也毫不温馨,与沈从文笔下的老爷爷给翠翠讲的故事不能比拟。这里王婆讲的故事是充满血腥的,是讲她怎么把三岁的孩子摔死,这完全是一个混乱的、肮脏的、甚至令人恐怖的世界。小说中几次写到了坟场,那种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地方,是当地人生命状态的一种形象的展示,这个场景也充满着隐喻性。先是小金枝被父亲摔死后,所展现的乱葬岗的情景:孩子已经“被狗扯得什么也没有”,“成业他看到一堆草染了血,他幻想是小金枝的草吧!他俩背向着流过眼泪。”“成业又看见一个坟窑,头骨在那里重见天日。”“走出坟场,一些棺材,坟堆,死寂死寂的印象催迫着他们加快着步子。”(七、《罪恶的五月节》)生命消失了连个痕迹都留不下,可见生命的价值和分量。这里不是给亡魂们安宁的墓园,它是躁动的、永远也无法安宁下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所谓的痛苦和忧愁已经脱离了它本来的意义,变得既不重要但又深入骨髓。在第九章《传染病》中,瘟疫再次将死亡带给了这里的人们,作者写坟场的笔调很低沉,在这低沉的调子背后是一股强调的力量,被压抑得要崩溃的力量,它在展示生命如蚊虫一样低微的同时,也展示了生命的韧性:
乱坟岗子,死尸狼藉在那里。无人掩埋,野狗活跃在尸群里。
太阳血一般昏红;从朝至暮蚊虫混同着蒙雾充塞天空。
……
过午二里半的婆子把小孩送到乱坟岗子去!她看到别的几个小孩有的头发蒙住白脸,有的被野狗拖断了四肢,也有几个好好的睡在那里。
野狗在远的地方安然的嚼着碎骨发响。狗感到满足,狗不再为着追求食物而疯狂,也不再猎取活人。
完全是一幅生命自生自灭,没有人理会没有人关心的图景,这是民间世界自在的图景。它带着原始的野蛮和血气,就像作品中几次写到的:野狗在咬死尸,“嚼着碎骨发响”。这是生命跟生命之间凶残的吞噬,完全是一种令人颤栗的原始状态。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萧红能够感受到生活中的这种粗犷和力量,也正是她不同于别人的显得大气的地方。
2.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
接下来的问题也很明显,在这样一个民间世界中,人们之间究竟有没有爱的存在?有人认为,在萧红的作品里,男女之间的爱、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以及对祖国的爱,这三层爱的意义都是一个由肯定到否定的过程,换言之,爱在萧红的作品里都是毁灭性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对于民间文化现象的一种认知,在我们中国普通的民间,所有爱的萌芽都会被现实生活所毁灭。这种人生是悲哀的。这种悲哀是从“五四”以来启蒙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的,像鲁迅就说过,中国是一个“无声的中国”,就是说这个民族没有生命力。因为它所有的生命力都被统治阶级压抑住了,那种极端的贫困,那种野蛮的文明,把人的个性全部抹杀了,建立在个体之上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因素和感情因素都失落了。
那么,我们该怎么看《生死场》?从这个作品的出版到今天已将近七十年过去了,如果里面的小金枝活着,现在已经是老太婆了,为什么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讨论它,讨论爱存在不存在这些问题?我觉得事隔70年,农村的现实状况变了什么,还有什么没有变,这不是很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人类的感情生活、人类的生命力的表现,这个问题是超越时空的,而不是以时间为尺度来计算的。这跟科学不一样,科学有一个时间的界定,比如我们用的是什么车,我们可以用动力、速度等要素来加以区分,今天是马车,明天会变成汽车,后天火车,再后天会变成新干线、磁浮列车,它总要变,而一旦变了,就可以把前面的东西基本淘汰掉。历史也是有时间界限的,我们谈历史一定要谈时间,公元前是什么,公元后是什么。但是,文学是诉诸人的感情和生命的,而人对自我的感受,对生命的感受,永远是从一个原点出发,它不随着时间的发展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是没有时间的。我们今天读屈原的诗,读唐诗宋词,读《红楼梦》,读西方的一些文学名著的时候,如果我们说这本书只不过是古代的一部伟大著作,跟我们今天已经没关系了,那我觉得这部书就该淘汰了。但真正的文学是不会被淘汰的。我们今天读很多古代作品,不能感动,是因为语言变了,比如《诗经》或《楚辞》,我们先要拿了一本词典查,边查边读就趣味索然了。如果我们没有语言障碍的话,其中还是具有诉诸人的最基本的东西。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哪怕它隔了几百年、上千年,到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会有很多感受,它好像依然活在我们身边。这是文学的魅力。文学之所以一代一代不断地被人咏唱,就是因为它诉诸人的生命、人的感情。但感情是非常不牢固的,因为现实生活要发生变化,它不可能永恒、不可能持久,尤其是要达到非常纯粹的、跟生命相连的状态,只能是在人生中非常短暂的瞬间,它稍纵即逝。最好的例证在《浮士德》(Faust)里,浮士德一生都不满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才说,人生是多么美好啊,时光你停一停。那时候他的眼睛已经瞎掉了,他感受的是幻觉,但这个幻觉当他真实感受到并吐露出来时,他的灵魂就被魔鬼抓去了。因为他跟魔鬼签定了协定,不能满足,不能感受生活的美好。也就是说,即使在西方基督教文化里边,美好也只是一瞬间的,当你感受到这种美好的生活,灵魂已经被上帝或者被魔鬼带走了。但人类存在一天便会不停顿地去追求它、去迷恋它、去感受它,对这样一种情感或生命状态的叙述和表达就是文学,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代一代的文学。一代一代的文学作品反映咏唱的永远是一个主题,即我们人类生命最本体、最本原的东西,无论用音乐、用绘画、用文字、甚至于现在用现代化的电影。人类在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手段,他所表现的永远是稍纵即逝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像一块石头一样存在在那儿,那就不需要人类一代一代去咏唱,只要有一块石头就够了。而恰恰它不是永恒存在的,是稍纵即逝的,所以,爱情是没法证明的,你所有被证明的已经不是爱情,是另外的东西了,它真正存在你心中,也就是一瞬间。那就是人对于美好、对于完美、对于爱这样一系列人类精神生活的永恒探索。文学就是人类一代一代去探索的这样一个永远不能达到、但永远要追求的东西。
萧红的《生死场》首先就是把自己所有的生命感受跟生活经验毫无保留地、赤裸裸地写给大家看,所以,我相信,《生死场》就是萧红家乡的一个描绘,如果没有这种生活经验就不可能写到这个程度。比如她如果没有自己体会到生孩子的痛苦,她就写不出那么恐怖的生孩子的经验。同样,没有母亲那么残酷地对待子女,她就写不出金枝和她母亲之间的关系。(注:1932年8月的一个黑夜,萧红在洪水中的哈尔滨被急送到医院待产,后在极其痛苦的情况下产下一女婴。萧红后来曾在小说《弃儿》中记下自己这一痛苦的经历:“芹肚子痛得不知人事,在土炕上滚得不成人样了,脸和白纸一个样……”,“这种痛法简直是绞着肠子,她的肠子像被抽断一样。她流着汗,也流着泪。”(《萧红全集》,第157页)关于她跟生母和继母的关系大体是这样的: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三岁的时候,弟弟出世,后夭亡;六岁的时候,次弟出生,母亲把更多精力和爱心都倾注到弟弟身上,对她感情逐渐淡漠。九岁的时候,生母去世,不到三个月,父亲即续弦,“这个母亲很客气,不打我,就是骂,也是指着桌子或椅子来骂我。客气是越客气了,但是冷淡了,疏远了,生人一样。”(萧红《祖父死了的时候》,《萧红全集》,第927页)以上情况也可以参见季红真《萧红传》,第19章《生产前后》,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我们在冰心的小说里是读不出这些东西的,冰心整天在说“梦话”:什么天上下雨了,鸟躲到树里,是一种力量,一种真心的袒露。现在有很多作家,心理比较阴暗,老是去找一些肮脏的东西给人看。但是,萧红这个作品非常坦率地把她对生活的感受和生活的真相都告诉大家,她并没有刻意去强化它,她的有些议论是内心自然、真诚的流露。比如金枝的母亲打女儿,她就说:“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二、《菜圃》)她这些话中没有那种知识分子高于民众、对民众的愚昧的嘲笑,或者愤恨,而且正是在这种表现当中,萧红把自己的爱心也表现出来了。尽管她描写的所有的人都是野蛮的,都是我们今天看来不能忍受的,可是,所有这些人又恰恰是我们生活当中最最宝贵的生命,每个人都是有尊严的。就像麻面婆,她是一个低能的女人,可是这样的女人也知道努力,知道要引起人家注意,她“听说羊丢,她去扬翻柴堆,她记得有一次羊是钻过柴堆,但,那在冬天,羊为着取暖。她没有想一想,六月天气,只有和她一样傻的羊才要钻柴堆取暖。她翻着,她没有想。全头发洒着一些细草,她丈夫想止住她,问她什么理由,她始终不说。她为着要作出一点奇迹,为着从这奇迹,今后要人看重她。表明她不傻,表明她的智慧是在必要的时节出现,于是像狗在柴堆上耍得疲乏了!手在扒着发间的草杆,她坐下来,她意外的感到自己的聪明不够用,她意外的对自己失望。”(一、《麦场》)一看就很好笑,傻傻的,笨笨的,但作者的笔调却非常严肃,麻面婆一直想努力把事情做得好一点,这就是人活着的尊严。包括金枝,也包括王婆的丈夫赵三,还有二里半,都是很委琐的人,可是,到最后真正关键的时候,那种顶天立地的豪情也都迸发出来了。赵三在抗击日本人的宣誓中流着泪说:“国……国亡了!我……我也……老了!你们还年青,你们去救国吧!我的老骨头再……再也不中用了!我是个老亡国奴,我不会眼见你们把日本旗撕碎,等着我埋在坟里……也要把中国旗子插在坟顶,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一三、《你要死灭吗?》)他年轻的时候反抗地主没有成功,窝囊了一辈子,这个时候豪气又被激发出来了。二里半最后不也是在打听“‘人民革命军’在哪里”吗?萧红写了一群不像人的人,可是萧红没有说,这种不像人的人就没有生存的权利。这些人过的都不是正常人的生活,可是,就在这种生活当中,人也有尊严。正如胡风在《读后记》中所说:在一个神圣的时刻,“蚁子似地为死而生的他们现在是巨人似地为生而死了”(《萧红全集》P146)。
由此来理解中国民间社会“爱”的问题,很多问题可能会更明朗。爱本来是一个很抽象的名词,它只有跟情连在一起,并转换为一种感情,作为感情当中的一种因素,我们才能把它说到实处。在西方,爱的界定,我认为最早是跟宗教、跟神的概念连在一起的,爱首先是从对上帝的爱开始,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上帝,是献身。献身,就是把自己交给别人,或者说,把我的身体或一切奉献给一个抽象的东西,那就是上帝或者神。这个过程叫爱。这个感情后来世俗化,变成人的爱情、情欲、欲望等等,但是在世俗化里面,人们在界定爱情的时候,一定有个概念。比如,有人说,他们结合不是为爱情,她是为了一座房子,这种说法很多的,那就是人家看出这个爱里面有功利,你是有索取的,有索取的不是爱,爱是一种献身,是一种奉献。当你因为一种喜欢,而不是被迫的,愿意把自己一切交给对方,或者愿意为对方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甚至是力不能及也要去做,这样一种动力叫爱。
那么,这种动力是哪里来的?这是一个感情的因素,但是同时,我认为也有生命的因素。回到伦理学上来说,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在人的生命本能里面,有一种东西是要求牺牲自己的。因为人的生命没有永恒,生命从生出来开始,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死去,生命能量就是不断地在耗费。就是说,生命的过程不是一个生长过程,而是一个消耗的过程,就好像一盆火,火不会永远烧下去的,火点燃了以后,它就是在消耗燃料,到最后,燃料没有了,火就熄灭了。宇宙、地球,实际上都是一个消耗的过程,人的过程也是消耗过程,这是最本质的,生命就是这种状态。但是,生命跟其他东西不一样,一本书你把它撕坏,就没了,一个动物或者一个人,他虽然老了死了,可是他有再生殖的能力,会再生出另外一种生命力量。比如说,他通过结合生孩子,那么他把生命又移交给孩子,他死掉了,可是孩子还能够活着。我们说某某人的精神永垂不朽,如果这个精神没人问了,那早就死掉了;如果他的思想学说、能量能够传播给别人,别人继承下去,这叫永垂不朽。整个人类也是这样。生命不仅有消耗的本能,还有再生的本能。这是生命的基本状态。这样一个过程,是生命运动的过程。而爱,我认为,是一个人的生命本质的感情,它符合两个标准,一个是消耗的过程,所谓的爱一定要把自己的东西消耗出去。另外,爱是有再生能力的,比如我这个爱给予了她,她可以再生出爱。不是说一生只有两分钟的爱情,比如结合以后,爱的形式变了,会更爱,它会一直生存下去,那么这就是再生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如果人类没有爱,这个种族就不会延续下去,种族需要通过繁殖,通过生存来使生命延续。这个延续过程中,爱是一种凝聚力量。爱又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如果我们分解到原始的感情,那就是自我牺牲的感情。种族为了使生命保留下来,需要这种自我牺牲,他会牺牲掉某种东西来维护一个群体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在讨论爱的时候,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可是,随着我们进入了文明时代以后,特别是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人们的宗教意识已经非常淡漠。说西方人的爱是建立在上帝之上,这在两千年以前大概是这样,现在就很难说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对于物质利益的无限制的贪婪和追寻,人类原始的生命的东西已经渐渐消失,被遮蔽掉了。此后,对爱的意识和理解,已不是本质的东西,是再生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包括文学,包括很多东西,它在那里演绎什么是爱,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被各种利益所渗透和篡改的爱的意义。这种意义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所以当大家讨论到爱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是爱,首先想到的,爱应该是在一个很幸福的地方,家庭是非常和睦的,大家已经幻想出现代文明标准下面的爱。反过来按照这样一个在一定的物质条件、文明环境下面被修正过的爱的定义,大家就感到,超出文明圈的范围就没有爱。比如我们不能想象,像萧红这样的文学作品还有什么爱,里面到处都是打啊骂啊,都是吵啊闹啊,生命那么容易被消灭,哪里有爱?因此我觉得,我们读文学作品要有这种能量,即穿透今天遮蔽在我们眼前的种种文明世界给我们的障碍,深入到生命的本原当中去把握,人的生命是怎么来体现爱的。比如农民在萧红的笔下,首先表现为对土地的爱、对羊的爱、对马的爱。二里半为找一头羊可以发疯一样,王婆牵了一头马要去上屠宰场,这个时候那种深沉的感情,我认为这就是爱,这就是人类生命本原的表现,因为这是跟土地、跟生存、跟生命的原始状态连成一片的,所以它会有一种出自本能的爱。
我们不妨看一看第三章《老马走进屠场》中所写的人与牲畜的情感。作者首先写出了一个落叶飘零的深秋凄凉的情景:“深秋带来的黄叶,赶走了夏季的蝴蝶,一张叶子落到王婆的头上,叶子是安静的伏贴在那里。王婆驱着她的老马,头上顶着飘落的黄叶;老马,老人,配着一张老的叶子,他们走在进城的大道。”深秋的落叶,是生命终结的象征,老人、老马、老叶子,既是实景,又是互有联系的生命。这正是内心最虚弱的时候,偏偏又在路上遇到二里半,问她凌晨赶马进城干什么,王婆的表情和动作非常准确地体现出她内心的震动和悲痛:
振一振袖子,把耳边的头发向后抚弄一下,王婆的手颤抖着说了:“到日子了呢!下汤锅去吧!”王婆什么心情也没有,她看着马在吃道旁的叶子,她用短枝驱着又前进了。
二里半感到非常悲痛。他痉挛着了。过了一个时刻转过身来,他赶上去说“下汤锅是下不得的,……下汤锅是下不得……”但是怎样办呢?二里半连半句语言也没有了!他扭歪着身子跨到前面,用手摸一摸马儿的鬃发。老马立刻响着鼻子了!它的眼睛哭着一般,湿润而模糊。悲伤立刻掠过王婆的心孔。哑着嗓子,王婆说:“算了吧!算了吧!不下汤锅,还不是等着饿死吗?”
我们看到王婆的动作已经变得很机械:“振一振”、“抚弄”、“颤抖”,到“什么心情也没有”,这是内心在震颤。而这马也不是二里半家的,跟他应当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们看到他听到要送去屠宰后的第一反应,不仅是“非常悲痛”,而且是“痉挛着”,慌得不得了。这完全是一个农人对牲畜的天然的情感,这种情感丝毫不矫情,看他用手去摸马的鬃发就能感到真诚。在这里,牲畜是人赖以谋生的工具,但它们却不是简单的工具,而是无所傍依的农人们的伴侣、家庭成员,他们用对待自己孩子样的感情去对待它们。接下来处处在渲染老马的最后的情景,是用王婆悲悯的眼光,又痛惜、自责的心情来看的:
老马不见了!它到前面小水沟的地方喝水去了!这是它最末一次饮水吧!老马需要饮水,它也需要休息,在水沟旁倒卧下了!它慢慢呼吸着。王婆用低音,慈和的音调呼唤着:“起来吧!走进城去吧,有什么法子呢?”
细声细气地恳求老马这番话,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她在减轻自己内心的负疚感,从某种程度上看,王婆也从老马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运,是自己生命耗尽后所不得不面对的结局,下面这段话更清晰地道出了这一层意思:“五年前它也是一匹年青的马,为了耕种,伤害得只有毛皮蒙遮着骨架。现在它是老了!秋末了!收割完了!没有用处了!只为一张马皮,主人忍心把它送进屠场。就是一张马皮的价值,地主又要从王婆的手里夺去。”最为让人感到心酸的是王婆经历了对可怕的刑场的种种场面的回忆与折磨,终于将马送到了屠宰场要逃开的时候,马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它只想跟主人回去,所以又跟着她走了出来,“无法,王婆又走回院中,马也跟回院中。她给马搔着头顶,它渐渐卧在地面了!渐渐想睡着了!忽然王婆站起来向大门奔走。在道口听见一阵关门声”。最后王婆是送葬一样地回到家中。这像无声电影中的一个画面,生离死别的场面。如果说他们的生活是极其粗糙的话,那么在这种生活中,同样有细腻的、动人的情感存在。
从生命的本能来看,人是要生存的。生命在一秒一秒地消失,在这个消耗过程中,人类有一种本能的抗衡,这就出现了一个相反的概念,就是生存。生存就成为人类的伦理的第一任务,我们经常讲“生存第一”,因为它是生命最本原的,他明明知道自己生命一天一天在消失,但是,他必须要有一种意识把它拉住,其实是拉不住的,那你不拉住,生下来就死掉了,他还是要拉住。所以这里就出现了人的生命的张力,这个张力就是人跟自身的消耗之间,一场无情的非常艰巨的斗争,我想这个斗争的张力是人类生命当中的第一因素。这种张力在作品中就是鲁迅所说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2](第6卷,P408)。这是在死亡、饥饿、疾病等各种阴影的压迫下,人们默默生存的一种力量,一种坚持下来不被打倒的力量,像作品中一句话所说的那样:“死人死了!活人计算着怎样活下去。冬天女人们预备夏季的衣裳;男人们计虑着怎样开始明年的耕种。”(四、《荒山》)不是说他们没有感情,而是在强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的感情容不得从容地表达,只能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成业摔死了小金枝,如果完全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为什么还要到坟场去看?王婆摔死了自己的孩子,如果一点感情没有,为什么要不断讲起?他们的心上都是有伤痛的,他们这是不断地在挤出自己的脓血来疗治伤痛。《生死场》中没有太多温情脉脉的东西,它所展示的乃是人生最为残酷的也是最为真实的一面,而在这里蕴涵的情感则是人类的大爱、大恨和大痛。
三、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
有人以梵高的艺术来说明萧红的创作,这一点非常好。无论是梵高,还是萧红,他们都不是预设一个艺术形式,他们的创作完全是为了给自己的感情世界寻找一个表达存在的方式。梵高要表达一种非理性的蓬勃的感情,梵高的画只能这样画。从绘画来说,它主要是空间艺术,欧洲的绘画传统从达·芬奇开始,就有透视法、远小近大等等一系列表达空间的方式。可是,在梵高的作品里,所有的内在的东西都打开了,所有的都展示在一个平面。这样的创作方式,中国绘画史上也很多,中国山水画从来不用透视法。陕西户县的农民画也是这样,农民脑子里就没有空间概念,高兴在角上画一个房子,就画一个房子,高兴在这个地方画朵花,就画一朵花,他脑子里出现的是一种内在生命展现的平面,所有的意象都同时展示在一个空间里面。萧红的小说就给人这个感觉。小说是时间概念,它一定要有先有后,一个长篇小说一定要发生在哪一年,然后按照时间线索一路下来,如果写到以前的事情,那么还要有一个倒叙。可是在萧红的作品里,你很难找出一个时间线索。虽然仔细地看,她是有时间安排的,但在整个感觉上,她一会儿写这个,一会儿写那个,一个个场面同时展现在你面前,在同样一个平面上来展示她的叙事艺术。我们通常说萧红的作品是一种散文化的小说,或者说诗化小说。其实小说本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只是我们人为地加以界定,好像小说一定要有时间线索,有中心,有高潮等等。你看,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写《尤利西斯》(Ulysses)或后来的《芬尼根守灵夜》(Finnegans Wake)就是这样,其实只是很短一点时间,把它无限扩大以后,并置地写出许许多多时间段,在同一个场面上展示出来。他们把以前的对小说的理解完全粉碎了。西方意识流或者心理小说,虽然没有时间线索,但有心理时间,在萧红的作品里,她连心理时间都抛弃了,展示出来就是一个个人性的场面,这些场面争先恐后地出现。比如她前面一段写一个小女孩跟一个男人在那儿约会,后面一段突然写到一个老太婆牵一匹马去屠宰,这毫无关系,你找不出里面的线索,也没必要找。她的小说给人的感觉就好像中国农民画。这是一种给小说空间带来无限张力的表现方式,而且表达的容量也很大。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小说的形式?我的感觉,女性作家跟男性作家是不一样的。男性作家写小说,时间性是非常强的。时间的概念在男性的思维里面非常重要,所以他们的叙事往往都是直线,一条或者两条直线一泻到底。多数长篇小说都是男性作家写的,四卷五卷,一条基本线索连续不断,然后其他枝枝蔓蔓可以旁延出去。我觉得,男性作家表达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非常恰当,当然他要故意打乱叙事时间、搞意识流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女性作家的思维也有这样线性发展的,比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她跟男性小说的模式是一样的,完全是一种男性思维。而萧红开创了另外一种带有女性思维的叙事方式。
萧红的小说,每一个小阶段有一个旋律,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又是一个旋律,这样不断地推进,然而旋律跟旋律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这样的叙事特点当代也有,现成的例子如当代女作家林白,林白的小说就是萧红的思维,她也写长篇、中篇,但好像从来没有一个小说故事非常完整、一条线一贯到底的,她的故事也会发展,也会有主人公,但是她的叙事,她的情绪,总是一个一个小高潮,一个一个小故事。她脑子出现的空间场面,是一个一个片段,很多很多的空间并置在上面。关于这一特点,林白也好萧红也好,都还停留在比较感性的、不自觉的阶段,还没有提炼到一个高的层次。我读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的《海浪》(The Waves)时,有一种一 直压在海底下的感觉,就好像身体感受着海浪不断打上来,一波接一波。人生从生到死,就像海浪一样,一浪又一浪从年轻开始,到年长,最后到死亡,生命就是圆的旋律,一波一波的旋律。这篇小说的节奏感非常强,但是,难以找出一个中心人物,一个中心事件,一条主线。小说的整个故事是跟着生命的旋律在走。《生死场》也是这个样子,每一章开始的时候,往往是一个静态的画面和情绪,但人物出现了,就动起来了,当人的内心冲突达到高潮的时候,自然的画面又插进来了,形成一个回旋,接着再向前冲击开去,形成下一个轮回。从整个作品看,前九章是展现乡村的不同生活场景,但不是平铺直叙,而是在画面的内部有着激烈的冲突,生生死死的壮剧,都是在这种平静的叙述中,在略带着一点死寂的气氛中展开的。当瘟疫传播开来,人们感觉“要天崩地陷了”的时候,前半部分突然结束了,中间插进了一个第十章《十年》、十一章《年盘转动了》。这两章在全书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但绝非可有可无,它不但给前面的故事以缓冲的余地,而且启动了后面故事,在全书的节奏上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它作了一个小小的停顿,如乐章低沉下来的小回旋,但又酝酿着后一个高潮的到来。第十章只有四段话,但是萧红在语言节奏的把握上非常准确:“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旧似十年前。河水静静的在流,山坡随着季节而更换衣裳;大片的村庄生死轮回着和十年前一样。”就是这种不紧不慢的语调,而接下来开始缓缓地启动新的变奏了:“雪天里,村人们永没见过的旗子飘扬起,升上天空!”“这是什么年月?中华国改了国号吗?”马上紧张起来了,搜查、杀人、反抗都来了。有意思的是,这中间又插进了金枝到城市中谋生的遭遇,这不仅使后半部分的内容与前半部分有了联系,不至于割裂,而且又使小说后半部分的叙述呈现不同的层面,不单调。结尾,金枝要去做尼姑,实际上使叙述的调子再次低沉下来,而二里半的远行,则给了人们很多期待和猜想,再次上扬了一下,但不是高扬。《生死场》在整个节奏上就是这样一唱三叹,回旋往复,非常有特点。在西方文学里,弗吉尼亚·伍尔芙是一个异数,在中国文学里,萧红是一个异数。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文体意识的作家之一,她曾经明确地表达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要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注:转引自聂绀弩《萧红选集·序》,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在一生短短的创作历程中,萧红常有大胆的“越轨的笔致”,这从《生死场》中可以看出,到后来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已形成特有的风格,那带有诗意的笔致、抒情的句子、回旋的情感,形成了萧红独有的文体特点。但是我们的评论家对作品进行价值判断、美学判断的时候,常常情不自禁地按照比较传统的思维方式,去关心这部小说情节有没有高潮,线索是不是清楚,主线是什么,副线又是什么,矛盾冲突是不是激烈,因此用巨大的理性的思维方式去套萧红,去解读《生死场》,那你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她的表达不在这个审美的范畴里。但如果你仔细读《生死场》,换一种眼光去理解,去贴近这篇小说,你真会感到萧红的心在跳动,萧红的血在奔涌,感觉到她的灵魂跟你一起在那儿呼号,你仿佛听得见萧红的声音。我觉得这就是艺术,这就是艺术的冲击力。
收稿日期:2003-10-05
标签:生死场论文; 萧红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呼兰河传论文; 读书论文; 萧红全集论文; 小城三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