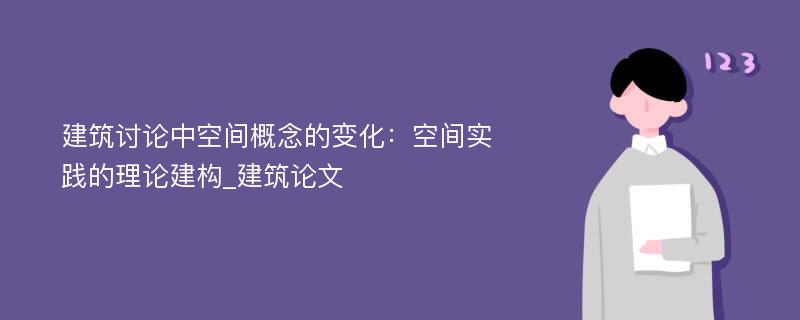
建筑论述中空间概念的变迁:一个空间实践的理论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论文,论述论文,概念论文,理论论文,建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空间?假如我们把这个问题当作一种历史性的理论询问,那么在空间相关的专业论述经历过所谓“多范型抗争”(multi-paradigmatic rivalry)情境后,对这种问题的回答就已经无法用现代专业辞典的工具性定义予以应付了——因为,关于空间的观点是由论述所界定的。我们必须处理建筑专业中关于空间的观点的变迁,为此,则需进一步考察在特定社会与历史情境下建筑话语(architetural discourse)的变化。
本文对建筑话语变化下不同空间观点的考察,目的不在于评介,而在于通过质疑的过程,试图建构一个政治经济学取向的理论架构,以期有助于空间的实践,特别是有关空间文化形式的建筑实践。
一、空间专业分化的趋势与空间理论的贫困
建筑专业关乎所有与空间有关的营造活动,广义地说,它关乎所有与空间塑造有关的直接活动与间接活动。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与专业分化趋势,造成了在空间的营建、设计、规划、管理工作中,至少可以细分为图绘与室内设计、建筑、地景建筑、都市设计、都市与区域规划、都市与区域政策等不同重点,以及再细分出环境规划、社区规划与设计等等。此处无需细列。一般来说,建筑师、地景建筑师与都市设计师主要将已接受的空间意义予以象征性的表现。因此,他们直接从事关乎意识形态效果的整个过程中的散发与转播工作,以求达成其传播与正当性及合法性效果,依赖的知识资源多为美学。建筑评论家也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者,透过制度的再生产而对空间的文化形式进行评价,因此他们是把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与既定权力形成结合。至于都市与区域规划师,则往往关心空间功能动作的管理,因此重视程序的理性。所以,规划师的作用必须分析近代国家的角色在空间向度上的支配、管理以及直接引领资本积累的作用。
由于分工造成专业差异,因而各专业对空间观点有所不同,衍生出不同的研究领域,逐渐与不同的知识传统结合,益发巩固了原先的观点差异。譬如说,建筑史与建筑批评主要是与建筑、地景建筑与都市设计的专业与作品互动;环境—行为研究则是由社会与行为科学(主要是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社会学,其中心理学家最为积极)同设计专业互动,扮演制度中的社会工程师角色;因文化研究方面的理论进展而展开的有关空间的社会文化因素之研究,以及关于营造形式与文化的研究等也都陆续受到重视。再譬如说,区域科学(Regional Science)与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分别与都市与区域规划有密切关系。由于都市与区域规划的执行实施,以及政策的形成密切关乎地方政府的角色与国家的作用,因而都市与区域研究也就与社会学、政治学无法分割。社会分工与专业的分化趋势在学院与研究单位中的发展,逐渐造成了空间论述的片断性,形成了资本主义基本结构之间的一些连结或不连结的特殊形式。论述之片断性使得规划与设计的部分专业者更加深陷于工具性操作,而拙于思考与分析的困境。于是,当社会改变,在社会科学被迫反省之后,空间专业(设计与规划专业)就因缺乏学术研究传统而显现出语言的空泛、思考的片断性以及空间理论的贫困,因而无法主动突破结构性分工,无法推动社会转化或指导实践。
因此,本文与其以静态的学科范畴将有关空间的专业加以分类,对各自空间观点做繁琐讨论,不如将由前述专业分工所形成的空间观点的不同取向,从知识论层次上审视其变化的社会根源。在这个基础上,空间概念如何在一种充满冲突的动态过程中以一种关乎语义系统的支配关系而被建筑起来,才能得以阐明。本文认为,这正是空间实践的理论建构首先所需要面对的课题。
二、空间论述的变迁过程
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曾论及现代化过程的发展动力,并生动地指出,将古典专业者的神圣荣光褪去而形成世俗色彩的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①这确实是形成专业之间论战的历史根源。
(一)实证主义主流范型的支配性霸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传统美学范畴支配的建筑形式主义范型,已不能负荷福利社会在国家大规模干预政策下的空间营造与管理任务。建筑论述一方面在社会分工的趋势下,另一方面在认识论范型转移下,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技术官僚的理性意识形态经由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而对传统建筑范型的改造,令我们看到了英美学院中对设计方法所提出的要求。并且,随着资本国际化趋势,它在文化表现上将现代主义风格进一步扩及全球。现代建筑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象征。
在建筑史与建筑批评领域中,黑格尔右翼唯心论的建筑史知识传统是凭借“理念之表征”(representation of idea)对建筑进行再诠译工作。理念是均质化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表现为自主存在的理念的单一历史。因此,建筑形式由“风格”(style)来做历史分类,成为断代与编年的理论范畴。在这种美学的形式主义取向中,风格成为建筑形式的一种特殊组织,风格或者是由建筑形式转化底层更深刻的力量——“艺术的意志”(Kunstwolen)——所推动,或是直接由社会所生产。于是,美学的形式主义经由风格的分类而建构了国际风格(International Style),或者以“时代精神”藏匿其价值取向而以超然中立的评论为现代建筑开辟道路,或是为建构民族国家建筑提供诠释所需的学院论述支持,如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与西格弗里德·吉迪翁(Sigfred Giedion)等。
平行于建筑领域中的范型转移,战后福利国家社会的正统规划理论是随凯恩斯模型的发展理论成长的。国家调节经济的循环,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引导资本的积累。因此,在空间功能的经理层次上,为了追求效率与科技理性的结果,都市与区域规划被大量适应于技术官僚的方法论(如系统分析、益本分析、土地使用与运输模型)和空间过程的实证主义理论(如新古典土地使用理论)所左右。技术官僚也开始在社会中取代旧的阶级而成为社会权威与控制的化身。空间,以实证主义为核心,在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由分析、科学和政策等各层面论述合成的体系里,是一个中性的、既定的客观存在。
在知识论层次上,当空间的规划与设计专业被迫参考外来学科时,不论是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心理学亦或系统理论与工程,这些学科并不能保证它们真能帮助解决建筑、地景建筑与城市规划所困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当借取知识时,空间专业本身并未有能力指出这些外来学科及科学是否已经解决了它们自己内部的问题。这些借用来的方法被假定为来自“较先进”的科学,会对比较“末流的”设计及规划实践有用。简言之,这种借用缺乏一种批判转用的能力。这种批判能力的欠缺是历史性的,它只能出现在主流社会科学因社会变动的冲击而崩解、而全面反省的社会与理论时势之下。所谓“科技整合”的方法,只是将几个方法不做批判地结合,结果,设计与规划的传统思维方式,在实证主义范型的霸权支配下,并未得到建构自身理论的能力与机会。
(二)人文主义与现象学取向的质疑角度与补偿效果
当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与矛盾日益复杂时,新的问题终究要求更细致的社会、文化以及心理层次的梳理。当技术官僚的大规模行动破坏了市中心既存的邻里网络,造就了充满敌意的空间,催生了20世纪60年代的都市社会运动时,社会运动迫使许多规划与设计的活动转向。像辩护式参与、市民参与、分权式决策过程与环境—行为研究对实质环境的检讨与评估,明显地采取了一些补救工作。人文主义与现象学分别由不同的知识传统出发,以一种替代性的论述形式提供关于价值、主观意义、空间之感觉经验方面的意识形态对应物。
这种与实证主义主流论述相对立的空间论述,软化了生冷无情的现代空间,抵制与质疑那些忽略人类主体经验的空间论述。德国传统美学中以“神入”(empathy/Einfuhlung)角度建构出来的空间观点,经由杰弗里·斯科特(Geoffrey Scott)、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等人的发展而为部分建筑史与建筑师的作品所运用。一方面成为现代建筑的有机建筑之核心观点,另一方面也成为英美人文主义的传统元素。不过有意思的是,这种强调主体体验空间的取向,在一些后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建筑师观点中被加以运用而向现代建筑宣战,并提出替代性的方向,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查理·摩尔(Charles Moore)和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等。在都市设计与实质规划领域中,凯文·林奇(Kevin Lynch)从空间的知觉角度要求空间的感觉品质,从而建构出一个完整的、针对专业实践的规范性取向。
有别于林奇所根源的英美经验主义的人文主义知识传统,克里斯蒂安·诺伯尔—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以欧陆哲学为出发点,重新编组存在的空间(existential space)的阵营,以对抗实证主义的空间论——被名之为欧几里德空间阵营。最后,他的研究取向导向海德格尔的居所(dwelling)与地方精神(genius loci)等观念。空间,是以人类生存其上的世界来界定为“地方”(place)并赋予意义的。同样的,来自新人文地理学方面的现象学影响,也直接冲击规划与设计理论本身,造成广泛的影响,如段义孚(Yi-Fu Tuan)与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的重要著作。这种新人文地理学取向,后来由安·布蒂默(Anne Buttimer)与大卫·西蒙(David Seamon)等人做了较完整的整理。一般而言,在设计理论、环境—行为研究方面,现象学取向以一种描述性语言,要求一种有别于实证主义分析的直觉和整体性的洞见,以彰显地方、建筑、地景等事物中某些被认为是恒常的普遍元素。
(三)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取向
20世纪30年代危机中浮现的凯恩斯模型,在70年代受到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与新的国际关系的挑战:不但直接导致通货膨胀的经济效果,而且在论述层次也面临了危机。7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危机,挑战了长期的、持续性的经济成长。其中,都市社会运动争取都市之集体消费,在这过程中,空间被视为社会的权利而非商品,都市服务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机制,它们转化了人们对都市的看法,改变了对空间的价值观。这些社会力量根本地挑战了常规性的主流范型,要求新的理论工具。此时,正如前面已经提过的,主流的空间专业论述的片断性,不但扩大了专业分工间彼此的鸿沟,而且与资本主义基本结构之间日益脱离,因此在新范型挑战下逐渐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支配与政治上的操纵作用。于是,对主流范型的质疑力量造就了空间理论的多范型抗争态势——批判性的新韦伯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李嘉图主义等都朝向一种更有力量及更广阔的分析方向前进,它们致力于能同时以科学与人文两方面视角来关注空间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取向的空间论述的形成过程中,最大影响莫过于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受结构主义间接影响的例子,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早期的操作性结构主义、奈希·泰玛(Necdet Teymur)的论述及其对环境—行为研究的批判等等。而直接运用阿尔都塞的概念来分析空间的典型代表有尼科斯·哈奇尼古劳(Nicos Hadjinicolaou)以及早期的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下面以哈奇尼古劳与卡斯特的理论概念作为代表,指出其特点与限制所在。哈奇尼古劳针对主流的学院唯心论的艺术史建筑史传统,提出一个精巧的理论模型,处理政经利益、一般意识形态与空间形式的关系。“意象意识形态”(imaged ideology)的概念是一种阿尔都塞式的“理论对象”(theoretical object),以取代“风格”的模糊观点。它是空间的形式与内容元素在每一个特殊的时机共同结合的方式。这个结合是社会阶级整体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所以,空间本身就是阶级意识形态的部分,而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空间必须与它所发生的结构一起来审视,必须掌握形式结构与斗争中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的结合。所以,空间形式是经由意象意识形态而掌握社会阶级整体意识形态的空间之特殊形式。
相比哈奇尼古劳,卡斯特尤有过之。他针对主流之都市理论直接提出了批判,认为它们以环境决定论的形式掩蔽了社会关系。卡斯特认为,城市是社会在空间上的投射,就像自然全由文化做出各式形状。人类在生活的斗争与对劳动产品不同的取用斗争中转化自己,以及转化其环境。然后,为了掌握社会空间形式的特殊性,卡斯特以阿尔都塞式的理论角度阐释空间:
空间是一种物质产物,关系着其他的物质元素——在其他之间,人,它自己具有特殊的社会关系,给予空间(以及其他所组合的元素)一种形式、一种功能、一种社会意涵。所以,它并非仅是社会结构部署之场合,而是所指定的社会中每个历史整体之具体表现。然后,就像对待其他真实对象的相同方式一般,建构问题,以掌握其存在与转化,以及,与历史现实之其他元素相连结的特殊性。这意味着即使是一个不清楚的理论,空间的理论也得是一个一般性社会理论的整合部分。②
在70年代初,作为一个经过修饰的阿尔都塞主义者,卡斯特虽然未忽略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可是,实践的主体确实深陷于重重机械性结构的网罗中,沦为失去主体意图的被动作用者。卡斯特试图以空间结构重新界定“都市”(urban)的概念。结构中不同系统与元素的组合与转化,是社会实践之中介所造成的,亦即由结构中之特殊位置决定的人的行动所造成的。然后,为了分析社会结构所表现的空间,则需研究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与意识形态系统之元素及其组合。换言之,他认为空间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形式,可由不同生产方式的历史连结的角度加以掌握,由社会实践的基本系统结合的特殊矩阵角度加以认识。所以,要分析空间作为社会结构的表现,就得研究空间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与意识形态等系统诸元素塑造的情形。这个精致的阿尔都塞—卡斯特模型对都市及区域研究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它将理论视为一种先验的抽象,脱离了经验研究之外而独立存在,割裂了理论与实践,滑向新康德主义的形式主义。所以,彼德·桑德斯(Peter Saunders)认为,这时卡斯特发展的空间社会学其实是对在特定时空中的社会实践之分析。对卡斯特而言,空间不过是社会关系的网络,空间的理论为发生在空间脉络中的过程理论所替代,为国家对都市过程之干预——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所替代。③
为了避免经验主义的表面直观,对空间的理解关键并不在于,因为它是一种真实对象的实质几何实体,所以我们需要理论的干预。用卡斯特自己的话来说,空间与时间为历史所界定,空间为社会关系所建构、加工与实践。空间像时间一样,是一种时势(或形势)并为具体之历史实践所连结。以下,通过针对70年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关于空间理论的两项课题:第一,空间与社会;第二,空间实践与理论。
三、对70年代批判之批判
(一)空间与社会
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的空间理论取向,往往为了质疑和挑战美学形式主义、技术决定论与短视的经验主义等在学院中的霸权而提出空间是社会的表现的观点。这在当时的历史与理论时势之下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模糊的空间观点将空间的特殊性没收了。
首先,我们可以审视早期卡斯特的空间观点:“空间是一种既定的,关乎历史地所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④由于空间不只是先于升在于社会的某物,而且是为社会所生产的某物,所以,空间就是社会性的。这里不是指空间是社会的逻辑等同,而是指空间是社会的具体化,是其形式上的构成。
其次,即使我们不同意在英国经验论土壤中形成的实在论观点,本文也仍可以引用实在论者之批判。实在论者安德鲁·赛耶(Andrew Sayer)认为,空间虽然部分地为社会所构成,但空间不能化约为自然的,也不能化约为社会的构成分子。
有意思的是,这种空间的化约倾向不仅出现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也发生在为结构主义所拒绝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昂希·列斐伏尔(Henre Lefebvre)70年代的都市论中(1976)。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并非一种排除意识形态与政治的科学对象,空间总是政治的,策略性的,意识形态性的。空间是一种充满了意识形态的产品。但赛耶指出,列斐伏尔的空间其实是日常生活中的领域,它化约为政治与意识形态,而忘记了空间形式。⑤至少,列氏并未能在理论上细致区分一般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与空间化的意识形态,忽视了空间的特殊性。
80年代,在结构主义与诠释学互补结合的基础上,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艾伦·普瑞德(Allan Pred)、爱德华·苏贾(Edward W.Soja)以及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称的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等等,都逐渐由不同的源头与领域出发,同样地提出了空间—时间结构化的理论角度。他们克服了过去社会理论对空间的化约,重新建构社会与空间之辩证关系,要求实质空间(physical space)与社会空间(social space)之聚密连结。所以,空间确实是社会的建构,但是,社会关系也在空间上建构,它造成了差异。苏贾试图建构“空间性”(spatiality)的概念来处理为社会生产出来的空间,以突破独立空间理论建构所需的理论对象。他认为所有的空间并非都是由社会所生产的,但是,空间性则是。空间性必须与物质性的实质空间相区分,也需与认知与表征的心象空间相区分。两者彼此均与空间的社会建构结合,但是不能将其概念化约为相同。空间不是生产关系绘布于其上的消极区位表面,也不单纯是一种限制条件(像距离)。事实上,空间性是一种整合性的与主动的条件。不只空间是社会地建构,社会也是空间地建构。空间不只是社会的反映,而是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一种建构元素。社会其实是存在于时间与空间的建构之中。用艾伦·普瑞德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变成了空间,空间也变成了社会”。这里潜藏的意旨也是结构—作用者(structure and agency)辩论中所关心的焦点。这时,我们可以引用后期的卡斯特对空间的论点,对比出政治经济学之批判取向中对空间与社会关系的转变,以及其中就结构与行动者关系所发展出来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xis)概念。他离开了阿尔都塞主义,然而却仍然在尼可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1978)与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遗产与成果中汲取养分:
空间不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的基本物质向度之一。独立地考量空间与社会关系,即使是有意研究它们的互动,也还是将自然与文化分割了,所以破坏了所有社会科学的第一原则:物质与意识的相互关联,这个融合是历史与科学的本质。所以,空间形式……为人类所生产,就像所有其他对象,按照既定的生产方式与特殊的发展方式,表现与展露了支配阶级的利益。空间形式会表现与执行在一个为历史所界定的社会中,国家的权力关系。空间形式会为性别支配与为国家所强化的家庭生活所实现与塑造。同时,空间形式也会留下被剥削的阶级,被压迫的主体,以及被侮辱的妇女们抵制的痕迹。这种矛盾的历史过程在空间上的材料将在已继承下来空间形式之上,在历史产品,在对新的利益、计划、抗议、与梦想的支持之上实现。最后,社会运动将又一再的崛起,挑战空间结构的意义,也因此尝试着新的功能与新的形式。这就是都市社会运动,都市一空间转化的行动者,也就是都市社会变迁的最高水平。⑥
上文提供的是一种关于空间与社会之间新历史关系的理论角度。对空间、历史与社会所交织成的研究领域而言,其实空间必须包含在历史之中,我们也无法想象没有空间向度的历史。而历史,是由人类行动所建构的空间与时间之间的连续性互动。这是一种社会—空间动力(sociospatial dynamics)所展现的社会政治过程。这种空间与社会之间的新历史关系要求空间实践与理论的结合。
(二)空间实践与理论
空间实践与理论的结合,这也是社会的古典课题。大卫·哈维说,空间的概念需经由人的实践来解决,而不在于哲学上的解答。
60年代末70年代初,空间实践的特殊性为政治实践之急迫性所化约,造成了理论上的形式主义结局。举例言,作为一个经过修饰的阿尔都塞主义者,卡斯特拒绝阿尔都塞主义中认识论干预(epistemological intervention)所主张的一种外在的、永恒的、用于区分科学与意识形态的认识论准则,而主张实践之认识论——要求以实践的社会效果来区分科学与意识形态。然而,卡斯特以政治实践替代了其他层次的社会实践。他说:“理论的正当化生产之主要条件乃是采取一种政治立场。”因而将认识论直接连接上阶级斗争的实践,结果造成了理论上的形式主义。
为了避免理论上对空间的忽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之实践观点,苏贾借用葛兰西—列斐伏尔的知识论架构界定空间。苏贾认为葛兰西所强调的“关系整体”所包括的特殊构造——具体化了在时间与空间、在特殊化的组构时势之架构中之生产方式——是行动策略形成时所必须掌握的脉络。这种行动取向要求对形势进行分析,因此需要重视近代资本主义之压迫/正当化与物质/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矛盾性功能对日常生活之作用。因为这密切关乎地方对集体消费之抗争及城乡动员。这样,在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条件下,葛兰西致力于推动运动之联盟。他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增之复杂性,因此主张提高政治与文化的抗争,以面对国家所仰赖的正当性霸权(领导权)。对葛氏言,反霸权(反领导权)的意识根植于日常生活之现象中。
苏贾将葛兰西之形势分析连结上述列斐伏尔空间化时势,将空间理论插入革命意识与抗争的中心。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借占领空间与生产空间以缓和其内部矛盾,这种资本主义空间直接关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空间组织变得关乎社会关系的支配系统之再生产,这是资本主义赖以残存的主要基础。这种社会地占领、生产与建构的空间就是生产的支配关系之再生产。经由国家权力对日常生活的穿透,资本主义结构了空间,所以资本主义之最终危机只有在生产关系不能再生产时才会发生,而不仅单纯地在生产本身的终止。因此,关乎日常生活空间之解放与重建的空间实践就可以做进一步之区分,而不仅仅限于生产领域而已。
那么,就前节所交待的空间与社会的新历史关系所要求的空间实践与理论结合而言,空间实践的各个层次,需分别就其社会行动的特性,提供能指引行动之适切理论。于是,传统的空间相关专业之分工,可以由新的角度,在新的历史时势下,就其专业实践提出批判性观点。
1.规划与设计作为空间实践之专业实践
(1)专业的象征实践是一种论述实践,需与经济与政治实践细致区分,再分别连结这些不同层次的实践效果。只有这样,作为社会行动者才得以建立能力,同时明白论述实践作为一种象征实践的限制,而又能充分运用论述实践之特殊社会活动的效果。套用拉康—詹姆逊式的说法就是,现实并非不可知,困难的是不能再现(unrepresentable),这关系着掌握与象征实践有关的符码、语言与媒介的能力。巴特曾经提醒过我们,建筑不仅是政治的象征形式表现,它们并不必然是相同的价值观。设计,作为建筑的语言表演,经由言语领域的差异,可以将知识经由实践做象征性表现。这种陈述行动是一种象征表现,设计使知识成为一种节庆的欢乐。设计者不再是被动的社会分工者与语言的奴仆,只转播已接受了的意义。设计者有机会在故弄玄虚的符号游戏中,在已拔除了安全阀的语言机器中,提出空间措辞方面的同形异质体,颠覆权力论述与理性。
(2)规划师与设计师们自我表现所需的书写与图绘,需与现实中的规划与设计专业执行加以区分。简言之,专业者所说的与现实中执行的差距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正是空间的社会生产所需细致分析的。现实不是不可为,困难的是实现过程中的扭曲、变形以及在社会、政治动态过程中的变化。这不但关系着分析的能力,更关系着在现实动态过程中折中的行动能力。
(3)空间形式与社会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建构关系,这种动态社会政治过程有无穷的可能性,这正是空间实践致力的关键。换句话说,规划与设计过程不是封闭的论述。规划与设计过程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为国家与资本的权力所支配的论述。动态的社会政治过程使社会的行动者不得低估社会运动的角色、阶级与性别的抗争、专业体制与意识形态的战斗。论述充满了冲突,承截着矛盾。因此,即使是空间的社会生产也涵括了空间的消费过程。空间形式之解读是多重的。规划、设计、评论与研究,其实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机器,而是一个意识形态与专业的战场,它的形式与主题不只是因应支配群体而变化,同时也需反应来自底层的声音。
2.专业者角色:有机知识分子的空间实践
在我们已经讨论了空间与社会的新历史关系,以及空间实践对时空形势分析的要求之后,专业者若自许为有机的知识分子,他(她)们的理论与实践连结要求就还应对空间实践与社会变迁、空间实践过程之组织、替代性空间计划之形成三个层次略作阐明:
(1)空间实践与社会变迁。在理论的层次上,前述之空间实践架构暗示了行动取向理论的迫切性。形式化的理论与巨型理论由于过多的抽象化、超历史的整全性、逻辑上的连贯要求,使得它(尤其以结构主义为代表)包容力虽广却无法处理研究对象内部以及地域社会与文化之动态丰富特殊性。另一方面,长期影响空间相关专业的经验主义取向,由于经验主义资料本身之繁琐,经验观察之成见,使得无视自身论述的牢笼。所以,我们其实需要深具弹性、在实践中可修正变形之知识架构。不仅如此,由于规划与设计的实践倾向,因而只要这专业不自甘沦为资本之积累性工具与国家之官僚作业所左右,它就必须面对社会的变动,必需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一方面,社会关系的分析是分析时空形势的核心,这是掌握动态社会政治过程的必要知识。另一方面,与实践相连结,社会关系的分析甚至暗示了专业角色的多重性可能。
(2)空间实践过程之组织。行动取向的理论是由实践的需要来建构理论。在实践的过程中,目标的形成是集体力量与工作推动的基础。一方面,空间实践需不自限于程序性理论模型的工具倾向与空泛,然而,另一方面,它也需拒绝意识形态层次的争辩。流于纯粹主义式的极端倾向。空间实践的过程中,对程序性理论理解的关键在于能形成技术上与时效上可以获致的目标,而这目标是在动态的社会政治过程中的策略性战斗。它必需累积实践过程所需的动员能量,关系着社会学习的过程。
至于如何组织空间实践的力量?我认为,空间实践的组织可类似于运动之动员,它需以目标来形成共识。它要求灵活、机动与弹性,以因应时空形势之变化,关键在于资讯流动的网络与团结网络(network)节点上作用者的主动性。对我们的文化与社会而言,这里潜存的挑战是:民主关系下地位平等的成员能否产生行动的力量,而避免封建文化中所遗留的父权支配关系,从而解放想象力?
(3)替代性空间计划之建构。社会变动要求专业者有理论诊断之能力,以界定问题与目标。这为的是研拟可行的替代性空间计划。另类替代式的社会改革计划需要特定的空间形式充当物质表现。另类替代计划可以作为一种动员弱势群体的政治计划(political project),促使特定的或相关的社会群体辨认自己,社会结构间不同的作用者也得以经由互动的系统而经营团结的网络。
在空间实践所提供的分析架构之下,我们可以较具体地处理空间意识与空间结构间的互动课题,以下我们用进步专业者与社会运动的某些诉求作为具体例子,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对空间的文化形式的特殊性略作补充。
当今进步的都市设计者强调空间与城市的“使用价值”,这不但挑战了今日植根于“交换价值”的以占有为导向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与城市,同时,它表现的文化价值与都市社会运动尤其是妇女运动密切相关。除了经济与政治层次的抗争之外,在文化的层次上,妇女运动的主张与造成的论战有深刻的涵义。妇女运动要求的社会关系之转化其实是社会一般角色的改变,它关乎整个社会的文化转化,而不仅仅是妇女而已。女性主义的文化要求不经历社会变迁的过程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妇女运动必须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历史的社会运动。它所要求的社会变革包括了对所有人自身的改变。有学者指出,“女性主义的城市”对抗的是“性别歧视的城市”(sexist city),目的在于使其朝向一个有意义的空间,转化单向度的功能性经验为多重向度的经验。它期待的是一种不以占有为前提的,平等的无异化状态之愉悦感,一种罗兰·巴特曾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了的游戏中的快感。或许,这种无异化空间的消费所关联到的愉悦感,仍是一种空间文化形式之社会建构。
所以,妇女状况与女性主义经由运动与论战,在社会创新的过程中形成新的角度,并作为文化与政治的反霸权斗争的课题,关系着未来城市之政策与未来城市之形状。
四、结语
总体来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空间论述面临的是一种主流霸权解除后的多元发展状态,这种多范型抗争的局面中,学术研究是百花齐放状态,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并存。今天我们要回答什么是空间?已经不能在建筑的论述中划地自限,而必须面对空间论述的变动与歧异,面对因自身缺乏理论所造成的语言贫困。空间的科学是实验科学,而不是学院中知识的游戏。我们已经强调过,关于空间的本质的哲学式问题,解答的过程在于人类的实践。实践所需的是一个开放性的理论假说,而不是重建定于一尊的,形式化的理论。
新的理论其实早已登场,新的课题正等待研究者提出。经济的再结构推动着当前空间再结构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特殊的资讯发展方式的空间表现为资讯城市之建构。资讯城市是社会空间组织的新形式,它的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流动空间(A Space of Flows)取代了地方空间(A Space of Places)。这是经济层次上资本逻辑的极致表现。基于实践的要求,我们需要有想象力的计划,它植基于社会意义的战斗之中。
注释:
①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New York:Penguin,1982,pp.90-95.
②Man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1972,p.115.
③Peter Saunders,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New York:Holmes & Meier Pub,1981,p.211.
④Mannuel Castells,The Urban Question,vii.
⑤Andrew Sayer,"The Difference that Space Makes",in Derek Gregory and John Urry eds.,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5,p.60.
⑥Castells,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p.311-3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