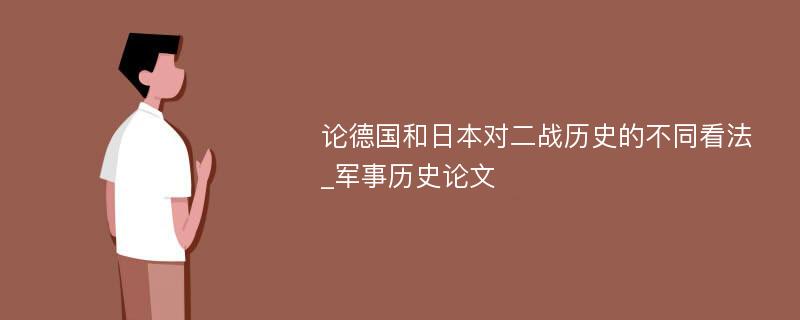
评德国和日本不同的二战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史论文,德国论文,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对待二战历史问题方面德国经历了与日本完全不同的过程。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形成鲜明反差的原因,不仅应该在战胜国对德、日两国的占领政策及两国战后的政治发展中,也应该在二战受害国对德、日两国的态度中寻找。如果日本不彻底改变它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它与邻国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有明显的改善。
在当代国际关系中,对二战历史的态度和对二战遗留问题的处理,是直接影响德国(本文专指联邦德国)、日本与受害国之间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1997年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60周年,对德国和日本的二战史观进行比较,特别是对两国形成不同的二战史观的原因开展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德国与日本对二战历史态度的重大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认识深度上有本质的区别。德国不仅承认侵略事实,承担战争罪责,并且认为纳粹政权和纳粹统治是导致战争和民族灾难的根源。因此,二战虽然以德国战败而告终,但由此导致了纳粹政权的崩溃,它归根结底对德国人民是“解放”。日本只提“终战”,回避侵略事实,掩盖歪曲二战历史,在战争根源问题上没有进行认真彻底的反省。第二,在认识过程上德国表现为逐步深化,由消极变为积极,从政府到民间,正确对待二战历史问题的正义力量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在认识二战历史问题上几十年徘徊不前,主张彻底反省侵略历史并承担战争罪责的力量始终处于劣势和少数地位。第三,绝大多数德国政治家,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有政治远见和政治责任感,在对二战历史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得比较深刻和超前。日本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应有的政治素质,有勇气、有远见的政治家为数极少。相反,民间少数有识之士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远比政府深刻。第四,从对外关系的大局出发,德国在处理二战历史问题时,尊重被害国家和被害民族的民族感情,注意国际舆论的监督,采取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态度,争取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日本在二战历史问题上顽固坚持原有立场,采取不合作和自我孤立政策。
造成德日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重大区别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可以总体上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外部因素包括:盟国战后对德国和日本不同的处理方式和不同的处理结果;战后各受害国、受害民族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对德国和日本采取的不同态度。内部因素主要包括:第一,德国和日本两国的国家因素,如政治体制和政府的有关措施及政策导向等;第二,非国家因素,如新闻传媒、教会、工会等非政府机构的作用;第三,国民素质,如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倾向、国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和政治教育水平等。第四,历史、宗教及文化背景、地缘政治因素以及国家对外开放及国际交流的程度等。
德国在讨论与本国有关的二战历史问题时,一般涉及三个主要方面:“第三帝国”(即纳粹政权和纳粹统治)、屠杀犹太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三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纳粹统治”成为讨论与德国有关的二战历史问题的核心。从这一点出发,彻底揭露和根本否定发动战争的极权体制是建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的基础。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德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本质上差别。根据《波茨坦协定》战后四大国对德国实行军事占领。随着德国的政治解体、“非纳粹化”及政治“改造”的强制性实施,纳粹政治体制和希特勒统治的社会基础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德国由此完成了政治体制上的脱胎换骨,实现了对旧制度的彻底否定。战后日本虽然被迫实行了政治改革,但远没有德国彻底。由于没有其他战胜国,特别是苏联直接参加对日本的战后处理,美国实现了它对日本的一整套实用主义占领政策。其结果是天皇制得以继续保留,旧制度的社会基础没有被彻底摧毁,军国主义的流毒远没有肃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及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处理宽容得近乎荒谬。在美国的庇护下,苏联审判日本天皇裕仁的要求未能实现,不少主要战争罪犯逃脱了审判。美国为了得到日本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有关资料,公然袒护日本战犯,致使与此有关的战犯无一被定罪。战后担任德国第一任首相的是遭纳粹政权迫害的阿登纳,而50年代末期的日本首相竟然是二战时期的甲级战争疑犯岸信介。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基础方面的巨大差异,不仅直接影响到两国战后历史的发展,对两国二战史观的形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德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对二战历史的认识和反省都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50年代起联邦政府对德国的战争罪责和二战历史明确表态。对外主要是向被害国和被害民族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或赔偿,以各种方式表明认罪立场。至1993年1月,德国已支付战争赔款904,93亿马克,从1993年2月到2030年,德国还将支付317.72亿马克。1996年12月德国政府又决定给纳粹受害者增加补偿。勃兰特和科尔以联邦总理身份先后向二次大战期间的波兰、特别是向犹太受难者下跪,是德国政府多次公开认罪的突出例子。联邦前总统魏茨泽克1985年5月8日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的讲话,将德国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推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他指出,“我们不可以把1945年5月8日与1933年1月30日割裂开来”,因为纳粹上台是导致战争的根源。他作为一个国家首脑第一次明确地提出,“5月8日是解放之日,它将我们所有的人从纳粹暴力统治的鄙弃人性的制度下解放出来。”在这里魏茨泽克代表德国人民对纳粹政治体制作出了最彻底的否定。1996年在现任总统赫尔佐克的提议下,德国政府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纳粹受害者哀悼日。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德国历届政府要人在公开或官方讲话时都采取严肃和基本一致的立场。1988年联邦议院议长耶宁格在议会发言中因有美化战前纳粹统治之嫌,立即遭到国内外舆论的抨击而辞职。这是联邦德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政界要员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因失言而下台。反观日本,不仅在赔款问题上与德国有天壤之别,更严重的是,从天皇、历任首相到政界要人,对二战罪责始终采取回避甚至否认的态度。由于天皇在战争犯罪问题上一直逍遥法外,日本的二战史观始终没有触及核心问题,即彻底揭露和谴责发动侵略战争的政治体制和统治集团。战后以来,日本唯有细川护熙前首相曾明确表示“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为此他竟遭到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80年代以来,包括在任首相在内的日本政界要人相继参拜靖国神社,在各种公开场合大放厥词,公然歪曲二战历史,进而否定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和犯下的侵略罪行。这已成为当今日本政坛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特有的政治闹剧。1995年8月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访问日本时,公开告诫日本人,“为了公正地判断战争中的罪行,不能对历史的真相视而不见”,“否认过去的人将冒重蹈覆辙的危险”。德日两国政府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差,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战后日本在政治上严重先天不足,没有像德国那样有一批具有政治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政治家,以致日本政坛长期涌动着怀旧和右倾化思潮,在二战历史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1995年6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不战决议”时,以各种名义加以反对的国会议员竟达到40%,右翼势力之强大,可见一斑。
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德国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地缘政治及外交政策因素。在位于中欧这一特定的地缘政治条件和国家分裂及冷战格局影响下,德国在50年代首先采取的是以西欧一体化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在此基础上,60年代末又推行“新东方政策”。上述外交政策成功与否的基本前提,毫无疑问是德国必须在二战历史认识问题上取得西部和东部邻国的认可,消除这些当年的受害国对德国的疑虑。德国在这一问题上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向受害国谢罪,建立与有关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最终实现它在当时地缘政治条件下所制订的外交政策目标。日本则不然,战后日本的外交方针完全由日美关系所决定,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与东亚国家的关系在其外交政策中不占重要地位。美国的扶植和岛国地理条件,为日本推行这一外交政策创造了条件。因此,对日本的战后外交政策而言,不存在积极地反省二战历史的迫切性和现实性。
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的讲话中说,“年轻的德国人在遇到波兰的同龄人时,他不必感到不自在。但是他必须知道当时德国人以德国的名义干了些什么。”要全体德国人民,特别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德国人承担战争的罪责是不公平的,但是他们必须承担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揭露并深刻反省这段最黑暗的历史,保证历史不会重演。基于这一思想,德国政府对内采取各种措施,继续追究有关战争罪犯,同时帮助国民全面地、正确地认识二战历史。这些措施包括设立一系列专门机构、研究所和纪念场馆。主要有路德维希堡的纳粹战犯追究中心、慕尼黑的现代史研究所、总部设在波恩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和一大批在原集中营旧址上改建的纪念馆。纳粹战犯追究中心与波兰、捷克、前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等国的有关机构协作,专门从事对战争疑犯的追查、拘押和提交审判。现代史研究所开展了对1933年至1945年德国现代史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在纳粹统治和二战史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果。在该研究所的推动下,有关纳粹问题的研究成为德国历史科学中最富有成果的一个领域。在二战史教育方面,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及其在各州的分支机构举办了大量的研讨会、报告会,自行和资助出版了一系列杂志和书籍并免费提供给公众,为在德国人民中广泛揭露纳粹统治,特别是大屠杀等暴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79年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在德国放映期间,北威州政治教育中心向该州中小学教师寄发了将近14万份有关希特勒“最终解决”犹太人的资料,对当时在德国开展的有关二战史和迫害犹太人问题的社会大讨论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60年代起至今,德国已在原集中营或俘虏营旧址建立了60多个纪念纳粹受害者的场馆,成为教育国民和开展二战史研究的重要场所。为了在二战历史问题上达成共识,德国政府鼓励民间进行对外交往。德国青年与其他国家的青年经常就二战历史问题进行交流与研讨,德国与以色列建交后,德国大学生组团访问以色列,并同以色列大学生讨论纳粹大屠杀等非常敏感的问题。
为了不使历史重演,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十分重视学校的历史教育,特别是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审订。与此同时,德国政府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分别与周边国家建立教科书双边委员会,讨论和解决历史教科书中特别是有关二战及战后双边关系的历史问题。在这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是1951年成立的不伦瑞克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在该研究所的组织下德国和法国的历史学家、历史教师和历史教科书编撰者,从1951年开始讨论两国在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教学中的协调问题,同年达成“关于有争议的欧洲史问题的德—法协定”。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推动下,德国—波兰教科书委员会在修改、补充教科书内容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经过20多年的努力,1976年汇集的“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及地理教科书的建议”,已被双方普遍接受。1985年提出的“德国—以色列教科书建议”同样被双方认可。德国政府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对在学校开展正确的二战史观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对消除德国人与二战受害民族之间交往时的障碍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日本虽然也很重视学校的历史教育问题,但反其道而行之。日本从50年代起就把军国主义思想塞进“学习指导要领”中。此后,日本文部省在右派势力的支持下变本加厉,多次通过所谓审定历史教科书,歪曲二战历史,掩盖、粉饰和否认战争罪行。为了维护正义,东京教育大学的家永三郎教授对日本文部省提出起诉。在这起长达30年多年的有关日本历史教科书诉讼案中,家永三郎被判败诉。近年来日本一些主要政党的组织和议员,在慰安妇等问题上不断掀起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恶浪。日本有关方面不顾中国和韩国等受害国的批评,继续坚持用被歪曲的二战历史误导和蒙蔽日本青少年,以致许多日本人对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径,既无反省之心,也无谢罪之意。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倾向。
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德国国民对反省二战历史采取了消极甚至对抗的态度。这一状况从60年代后半期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在国内外综合因素的影响下,随着议会民主制度的逐步成熟,在取得“经济奇迹”之后,德国在政治文化方面出现一系列新特征,其中最突出的是国民对政治的兴趣和参政意识明显增强。对政治感兴趣的人从50年代时期的20%~25%增加到60年代末的50%。从60年代末开始,国民对国内政治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与此同时,战后出生的一代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在价值观念上的差距也不断扩大。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和年轻人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代际冲突的特征,而冲突的一个焦点正是二战历史问题。年轻一代对他们的上一辈在二战期间的行为和战后处理二战历史的消极态度深表不满。冲突扩展到学校、政党直至家庭内部,震撼了整个社会。其积极后果是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战后一代人把加深对二战历史的认识、政治上承担德国的战争罪责作为自己不可推却的政治责任。民意调查结果证明,60年代末开始德国民众在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方面出现了明显积极的变化,正确的二战史观在整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1964年只有54%的德国人认为“纳粹国家是一个罪犯政权(Verbrecherregime)”,经过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重大的社会运动之后,1979年持这一看法的人上升到71%。在日本,由于政治体制的落后,加上固有文化传统的影响等因素,在取得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政治文化没有出现相应的积极变化。其表现之一就是国民,特别是战后的一代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政治意识和历史意识相当低下,以致日本对二战历史的态度几乎完全由政府和右翼势力左右。
在论及国民的二战史观时应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德国的知识分子在二战历史问题上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在无情地揭露民族黑暗历史时,他们走在最前列。特别是所谓“68年一代”,他们作为战后德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中坚,不仅在历史科学上对二战历史进行了严肃认真和全面深入的研究,而且在推动整个社会深刻反省二战历史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近的一个例子是,1995年3月至今,汉堡社会研究所举办的题为“毁灭性战争一国防军在1941—1945年的罪行”展览,已连续在德国十多个城市展出。日本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推动国民建立正确的二战史观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家永三郎等个别人的呐喊,没有得到日本知识分子的广泛响应和积极支持,因而不可能从内部对政府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不少日本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教授拒不接受“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这一正确的历史观,却坚持侵略战争是“东京裁判史观”,是战胜者一方强加的。更有甚者,由大学教授和历史学家组成的昭和历史研究所和有6千名会员的日本教师会,公然要求删改历史教科书中“从军慰安妇”、“南京事件”、“三光作战”等内容,妄图掩盖、歪曲日本的侵略罪行,积极充当右翼势力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日本知识分子的耻辱与悲哀。
在德国,议会各主要政党、工会、教会、新闻媒体和犹太人等外国人团体和社会组织都在反省二战历史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任何对德国在二战中的罪行进行歪曲、掩盖或淡化的企图,都会立即遭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反击。1995年在纪念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保守派右翼政治家、右翼作家和记者准备发起企图为纳粹统治辩解的纪念活动。它立即遭到各政党、新闻媒体、教会和犹太人组织的强烈抨击和反对,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原定的纪念活动被迫取消。对来自国外的揭露纳粹在二战时期所犯罪行的有关报道、影视和书籍,德国公众和媒体完全采取平静和客观的态度。继1994年《辛德勒的名单》在德国公演后,1996年由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戈尔德哈根撰写的《希特勒的心甘情愿的行刑者》在德国出版发行。尽管德国舆论普遍不接受作者对普通德国人民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心甘情愿”的帮凶的指责,但这本书很快被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足以证明德国人面对本民族黑暗历史的勇气。在日本却很难找到相同的例子。相反的是,在右翼势力的压力下,原定在大阪府举行的南京大屠杀画展被迫取消,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也不得不修改展览内容和用语,删去“侵略”措辞,为天皇开脱罪责。当年的战犯和不思悔改的老兵气焰更为嚣张。曾在日军荣字1644特种部队服役的石田甚太郎由于“战友会”的监视,长期以来不敢将他经历的日本侵略者用中国人做细菌试验的事实公开,1995年8月去世前夕才通过他在中国留学的亲属将此秘密在中国公诸于世。1996年8月,一名揭露其他士兵虐杀中国平民的日本老兵遭右翼势力的威胁,并被日本法院判为“损害名誉”。这证明日本要求彻底反省二战历史的正义力量长期处于少数和劣势地位。
德国国内要求彻底反省二战历史的力量之所以强大,除了政治体制等因素外,还有历史原因。纳粹执政之前,德国至少有14年的民主共和制度的经历,左翼政党曾发挥过重大影响。纳粹统治时期,特别是二战爆发后德国国内形成了抵制、反抗和推翻希特勒统治的抵抗运动,其成员包括进步政党、工会、学校、教会和军队等各个社会阶层和不同的政治力量。战后,回归的政治流亡者和抵抗运动的幸存者及其亲属成为一支拥护新体制、坚决清算纳粹罪行、彻底反省二战历史的重要力量。曾任社会民主党主席和联邦总理的勃兰特是其突出的代表。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民主共和制的先例。二战期间,日本国内不存在广泛的、有组织的反战争体制力量。战后,由于旧体制没有彻底改变,本来就十分弱小的反战力量不可能在反省二战历史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德国和日本在反省二战历史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还与各自的宗教及文化背景有关。在德国,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受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影响,基督教有关原罪和赎罪等基本教义已为广大教徒普遍接受,成为德国宗教文化的特征之一。因此,原罪—认罪—赎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因果关系程序。公开认罪并在良心和道义上进行忏悔,对信奉基督教的德国人已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有了这个宗教文化的基础,德国人在承认战争罪行、承担战争罪责时,就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对人的自我发现产生了重大影响。重视人的价值,强调生命的可贵,成为欧洲人文主义的核心。战后,通过对屠杀无辜生命的战争罪行的揭露,德国人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开始复苏。德国人勇于承担二战罪责,不仅仅是要求受难者予以宽恕的具体表现,也是他们对人性回归和重建的一种理性追求。由于没有欧洲历史上的宗教和人文主义诸因素,加之封闭的岛国环境和缺乏对外交往,日本形成了以神道、和魂和天皇崇拜等为特征的宗教文化传统。这种缺乏理性精神和开放意识的固有文化和国家至上、轻视个体的价值观,始终未能摆脱战前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阴影,以致日本人至今不能对其狭隘的民族心理作深刻的理性思考和无情的自我解剖。它严重地阻碍着日本对二战罪责作出清醒和彻底的反省。
在分析德国和日本不同的二战史观时,受害国的态度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战后50多年来,受纳粹德国侵略和奴役的国家和民族时时关注着德国反省二战历史的动向,始终没有停止对纳粹罪行的揭露和谴责,从未放弃追索战争赔款和追捕漏网的纳粹战犯。在受害国和犹太人这种强大的政治、社会和舆论压力下,德国不可能回避历史,更无法推卸战争罪责。受传统文化和战后国际政局的影响,大多数亚洲国家对日本国内的政治发展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日本的侵略罪行采取了过分宽容的态度。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正是利用了亚洲人民宽大为怀的仁慈心理和亚洲国家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弱点,公然掩盖甚至美化其侵略历史。认真清算二战历史是加害国与被害国建立良好双边关系的基本政治原则。战后欧洲被害国、被害民族与德国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已证明了这一点。引起法国乃至欧洲关注的对“里昂屠夫”巴比的审判、震惊意大利的对普里布克的审判,对法德关系和意德关系丝毫没有影响。波兰和捷克对德国在二战历史问题上采取的严正立场甚至不宽容态度,并没有对波德关系和捷德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相反,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德国和波兰建立了相互信任的睦邻友好关系,成为德国与二战时期受害弱国在战后建立良好的平等关系的典范。
1997年1月随着德国和捷克的和解协议的签订,德国与受害国之间在处理二战历史遗留问题上的最后一个悬而未决的争议圆满解决。然而,二战结束已经50多年,日军留在中国的成千上万枚毒气弹还没有处理,花岗事件赔偿案一拖再拖,深受当年日本细菌战之害的中国同胞至今在痛苦地呻吟,被迫充当慰安妇的亚洲妇女的灵魂仍在遭到践踏。日本在处理二战历史遗留问题上远没有德国所表现出的那种诚意和实际行动,这与它没有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直接有关。更有甚者,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以攻为守,鼓吹“中国威胁论”,混淆视听,用心险恶。日本国内顽固势力在二战历史问题上和在对华关系上的嚣张气焰,应该引起我们警惕、深思和反省。欧洲被害国,特别是波兰、捷克和犹太民族在对德关系上的有关立场尤其值得亚洲国家学习。
虽然德国在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方面表现得远比日本深刻和彻底,但并非完美无缺,无懈可击。即使在德国也有不少人认为,在正确树立二战史观方面德国虽不能说失败了,但也不是很成功。由于法律和司法程序有很强的独立性,德国司法成为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一个最右倾、最顽固的堡垒,也是德国舆论抨击得最多的一个领域。战后德国司法没有否定纳粹司法对逃兵、拒绝作战者作出的包括死刑等的判决。尽管教会和不少联邦议会议员为此曾多次进行呼吁,但二战期间抗拒或逃避作战的德国士兵至今未获平反。对引渡到德国的纳粹罪犯,德国司法往往以各种理由予以轻判。特别引起舆论关注的是前纳粹分子战后享受抚恤金问题。1950年德国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因战争造成伤残的残疾者有权获得抚恤金。当时曾考虑加入一条纳粹罪犯不能获得此项权利的规定,但被否定,理由是实行刑事处罚不属于社会权利范围。然而,根据一项特殊条款,在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罪行者,被剥夺享受抚恤金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德国司法公然实行双重标准,其要害是司法的政治右倾化。另一个引起德国舆论关注的是某些右翼史学家将希特勒统治与斯大林执政进行历史比较,通过“相对化”淡化纳粹暴政的罪恶,它引发了1986年的“历史学家大论战”。东欧巨变和两德统一后,“相对化”的倾向又表现为强调对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历史进行清算。但是,无论是德国司法还是史学界的某些右倾倾向,对德国有关二战史观的讨论都没有产生根本的影响。至于极右势力,如新纳粹组织及其活动也都在联邦宪法保卫局的严密监控之下。继一些极右组织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禁止活动之后,自1995年7月以来,已有两名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人被判刑。在德国公众舆论中极右势力已成为现实政治中的反面角色,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逆流和暗流在德国难以形成气候。德国政府注意维护自身的国际形象,密切关注国际舆论,特别是二战时的受害国、受害民族对德国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所作出的反应。打击极右势力、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是德国推行全球化外交时取信于国际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这一点很值得自以为爱面子的日本人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