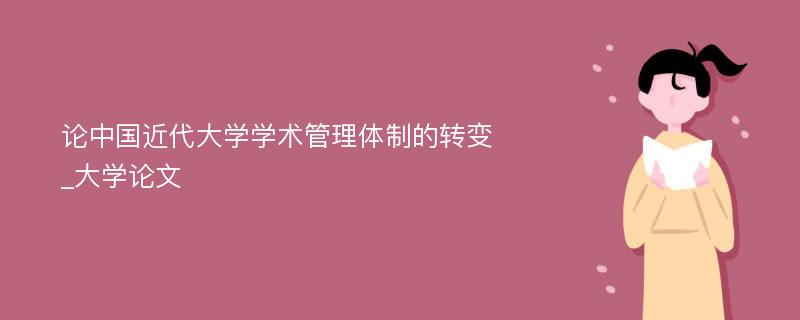
中国近代大学学术管理体制转型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体制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学术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1981(2007)10-0006-05
一、近代大学学术管理体制转型的表征
近代大学的学术管理转型是从近代大学的产生而开始的,但具备转型意义的则是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改革。陈平原在分析中国现代学术范型的基本特征时曾说:“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两代学者所创立的新的学术范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码可以举出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等。”[1]另有学者在讨论五四时期的学术转型问题时,提出如下四个特征的概括:即学术旨趣多元化;学术分类专门化;学术方法科学化;学术形式通俗化。[2]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逻辑起点之学术生产方式的转型带来近代大学的产生和定型,也使学术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改变,传统学术管理开始向现代学术管理体制转型。
(一)由个体学术生产方式向组织生产方式转型
学术组织的出现是学术发展成熟的表现,长期以来中国学术一直是个体经营的方式,在师法和家法的体制内传承和发展,这种个体化的学术生产方式尽管有着独立的优点,但也存在封闭的弊端。古代学术组织样式如翰林院,实际上是一项职官制度,唐代始设,最初的性质是“天下以艺能技术见召者之所处也”[3],后来主要用于起草诏令,议论时事,尽管翰林院在宋代有过辉煌的显赫时期,但其储存官僚、撰修书史、起草一般文书的职能没有改变,翰林院孕育了我国的文人政治,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组织。翰林院也有着学术研究的存在,但仍大多是个人行为,翰林之间的学术网络并未建立,也“不具备欧洲大学的自制性,但是它有对全国进行学术垄断的特征,是封建帝国官僚统治的有机组成部分”。[4]
19世纪西方各国的专业研究学会相继成立,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生产组织产生,以知识为指向的组织特征越发明晰,在国外的中国学生们看到学会活动对促进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也纷纷仿效,建立中国人的学术团体,这些团体对学科及学术研究的统一术语、译名等作出了初步的厘定。在民国前,国内学术管理的组织化也已呈现,但这些民间建立的科研机构都较小,人员少,缺乏系统。辛亥革命以后,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愈益重视,中国的科研机构已逐一建立起来。
近代大学组织的定型无疑是学术管理组织化的标志性事件。清末《奏定学堂章程》就始见大学设研究所的规定,其时称“通儒院”,1922年,北大设立了近代大学的第一个研究机构——国学研究所,此后各大学相继设立了诸多研究所,1929年《大学组织法》再次规定大学可设研究所,图书馆、杂志、报纸、社团等组织和机构也在大学里扎根。北大还有许多师生社团,诸如少年中国会、新闻学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化学研究会、史学研究会,另有学生社团雄辩会、行知会、新潮社等等,这些组织和机构使大学一跃而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特别是1917年12月由蔡元培、陈宝泉、汤尔和、王家驹等发起成立的学术讲演会,这是一个跨校际的学术组织,开院校学术联合研究的先例。1927年,蔡元培又效仿法国推行大学院制,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学术组织让学者有了归属感,学者在不同的学术场域中不失自我地进行学术研究,学者间的关系网络化,所谓浙籍章系、北大派、研究系等等,学者关系渐趋复杂。
(二)由松散型管理向制度化管理转型
对学术的控制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在近代大学诞生以前,学术的组织化管理是较少的,制度化更谈不上,尽管太学、国子监、翰林院等都已经制度化,但也只限于在教学、作息等方面,而从事研究的学术者则分散朝野上下,学术研究凭个人旨趣在儒学框架内进行,研究活动在学者、经费、时间、成果等诸多要素上缺乏制度化的安排。近代如中央研究院下设诸多研究所,建立了学术评议制度、院士制度和研究奖励制度。北平研究院设立了院-部-所(会)三级结构,建立了院务会议和学术会议,制定了各项章程规则、工作计划、概算及其他重要制度。其他学术管理组织也都有较完备的组织建构和运行制度,学术生产的制度性、规划性、合作性、国家性在学术组织的生产活动中得到体现。
在近代中国大学学术制度化过程最重要的是教衔制度的确立和学位制度的导入。早期大学的教衔制度是因校而异的,各大学对教衔等级的设置和待遇有所不同,蔡元培北大改革在聘任教授时往往靠举荐和社会声誉,没有确切的标准,常常破格。1917年5月教育部颁布《修正大学令》,大学教师分为正教授、教授、助教授、讲师四等;1919年发布的《国立北京大学规程》,设立聘任委员会,使教师聘任制度化,设置了正教授(分为六级)、本科教授、预科教授、助教、讲师(非常设教席)等级;清华则设置正教授、副教授、助教授、教习、助教等级;1923年,在蔡元培、蒋梦麟执笔起草的《杭州大学章程》中设置了正教授、教授、辅教授、讲师、助教、特别讲师等级;1927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正式设置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1941年又设置了部聘教授。
在西学传入的过程中,西方学位制度随着教育制度的导入也被介绍进来,而大批留洋学士、硕士、博士,使国人渐渐认可了西方学位制度,而教会大学学位制度的实施为近代大学提供了示范。清政府于1903年、1904年分别规定给予获得洋学位及新式学堂毕业的学生赐予科举出身,这是西方学位制度本土化的一种尝试。1912年10月公布的《大学令》对学士学位有了初步规定,1922年《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可设研究院,1934年又颁布《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这是近代第一个研究院(所)的专门规制,1935年国民政府修正通过《学位授予法》,正式设立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并对学位标准、学位授予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初步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学位制度[5],但有个问题一直存在,我国引入的学位制度一直是国家认可的学位制度,而非社会认可的学校学位制度,学位、出身、功名之间或隐或显地流露出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关注,从而学术水平的认定异化为社会化程度的认定,这给后来的大学学术管理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
(三)由官僚型学术管理向专家型管理转型
传统知识精英大多承担两种角色,其一为官僚,其二为学者,在履行学者身份的时候不免带有官僚的特征,这种惯习一直积淀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两种理想在这两种身份上分别得到体现。官僚学术或者官僚管理学术使学术永远在儒学的框架内进行,其边界只会缩小,而不会扩大,这也是传统学术的外张力、发展力和滋生力不够的原因之一。书院尽管孕育于藏书并得益于佛教的寺庙,学术的发展似乎可以突破垄断的限制,但作为非正规的民间学术机构自治只是在某些历史时期得以有限的实现,而统治者的些许控制就摧毁了它那脆弱的自治品格。近代中国政治因素、救国主题虽然有着极强的价值导向,但近代学者对学术的认识仍然很清醒,职业型、专业化的研究者开始出现,学者自治型管理模式产生,而蒋梦麟更是开始了近代大学的管理职业化,他的“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思想,首次提出了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分离的主张[6]。
蔡元培开启了近代大学的英雄时代,他继承和借鉴了德国大学的传统,将大学定义为探索高深学问的场所,1917年,蔡元培接任校长职务后,在就职演说中指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7]指明了办学、求学的宗旨,是为学问、学术。为此,把延请名师以提起学员的研究学问之兴趣作为主要工作,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相继而来,不仅活跃了北大学术空气,更为北大学术管理改革奠定了人才基础。正是这些懂学术的人来管理大学,蔡元培实行教授治校方略方才获得成功。顾孟余说:“先生长校数年,以政治环境关系,在校之时少而离校之时多。离校之时,校务不但不陷停顿,且能依计划以进行者,则以先生已树立评议会及各种委员会之制度。此制度之精神,以在教授治理校务,用民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8]1917年7月,张勋复辟,蔡元培辞职,沈尹默说:“这是蔡先生信任我们,他走了,学校要靠我们办下去。大家想想这话对,就开评议会商量,这时候评议会掌握了学校实权,对外行文。”[9]蔡元培建立教授会,目标就是“使学校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10]蔡元培的探索高深学问、培养硕学闳才、网罗众家、兼容并包、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理念经过北京大学的实践得以确立,理想的宽松、自由、合作、平等的大学学术研究氛围开始形成,奠定了学术权威进行学术管理的框架,其北大改革的成功实践也积累了他的权威资源,几乎成为当时大学发达的象征,而教授治校、选修制、学分制等制度设计也为当时的众多大学所仿效。其他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郭秉文之于东南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等等,无不体现了英雄对于一个组织的引领作用。在近代大学网罗了大批学者,甚至可以说,近代学术的中心就在大学,诸多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留学背景的学贯中西的精英大家独领学术风骚,诸如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鲁迅、胡适、李大钊、李四光等等,不用过多枚举,灿若星辰,这些学术精英支撑起了近代中国学术,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对学术管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胡适以《努力周报》、《独立评论》、《自由中国》所构建的胡适派学人群。学术权威构造的学术精英群体形成了由专家来进行学术管理的既成现实,学术权利被张扬。
(四)由整体化知识管理向学科化知识管理转型
中国传统学术是整合的、普遍的,知识的通约性很强,很接近纽曼所说的“普遍知识”,分治主张曾经出现。汉代太学有五经博士之说,南朝宋文帝于元嘉15年,开设“四学馆”,到胡瑗、颜元的分斋教学,桐城派的义理、辞章、考据等等,但这些分治实践都没有成为主流并孕育出完善的学科分类体系,对学术的分类认识停留于图书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或者止于教学的需要,学科概念始终没有建立。明清之际,传教士的学术传教活动将西方大学带入了国人的视野,利玛窦、毕方济、高一志等传教士与徐光启、李之藻等翻译了西方罗马学院、科英布拉大学的《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名理探》、《浑盖通宪图说》、《修身西学》、《寰有诠》、《灵言蠡勺》等教科书,国人对西方大学的教学内容、知识样式大致有所了解[11]。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就将课程明确分为普通学与专门学2类,经过梁启超、刘师培等诸多学人的努力,近代学科分类体例才渐趋成型,相关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符号及概念体系、术语、规则等渐次从西方传入,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并接受西方学术规则,有可能在同一层面上东西方展开对话。李善兰之数学运算符号、贾步纬之三角函数对数表、徐寿之化学元素名称、胡刚复之物理学、王国维之西方美学理论等等,通过普遍的学术规范,中国学者在学术的场域内终于和西方一起在场。1887年金雅妹在纽约《医学杂志》上发表论文;1908年,首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化学学术会议,并宣读了论文;1909年,王焕文在日本《药学杂志》发表论文[12],这种交流和对话无不建立在现代学术分科制度上,学术分科体制的建立是中国传统学术西方化的标志,也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关键。
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体现了张之洞的学术分类原则和分科思想。其立学宗旨仍强调“中体西用”[13],在大学分科上,仿西方神学设置,增设经学科,列为大学“八科”之首,另设政法、文学、医科、格致、农科、工科和商科。这种大学分科取法日本而又糅合中国传统学术分科,具有学术转型的特征。在各科下分设不同学门。[14]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大学学科门类,除经学科外,基本上是依据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分类标准来划分的,反映出清末教育改革的西学导向。
1912-1913年,民国政府教育部相继公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的学科及其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它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取消了“经学科”,分设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等七科,科下分门。[15]1919年,北大废科设系。至此,新的学科分类系统基本确立。
(五)由文本研究向综合研究模式转型
我国传统学术的源头是思辨研究,在基本的知识固定化成为文本后,研究的范围便局限于文本,这和西方相似,《圣经》产生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后,思辨研究也便向文本研究转变,经院哲学占学术中心位置。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自然科学的极大繁荣,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科学巨匠,产生了一些新的科学理论,科学的发展导致哲学的发展,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等蓬勃出现,对知识的景仰和向往及对知识强大作用和巨大价值的崇拜对大学影响深远。从实证主义哲学开始,知识生产更多地表现出现实性,知识从漫无边际的冥想逐步地走进现实,也使知识开始承担更多的使命。到了近代,知识学科化的转型导致研究的学科化分野,也带来了研究方法由文本研究模式向多元化研究模式的转变,特别是实验的自然学科的研究方法改变了学术研究传统的思辨研究观念,传统的学术研究引导求善的目标嬗变为求真。传统学术研究拘泥与文本,在故纸堆中寻觅历史的真相,考据、训诂、鉴赏,知识学科化开始后,史学研究的纸外发现给学者以巨大冲击。研究的学科分野并未能限制方法的跨学科使用,或者说在方法上原本就没有所属。胡适在北大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截断众流”的勇气和“平等眼光”的自信使其学术研究带有学术典范转移的意义,可以看作是以西学之法治中学的标志。胡适感叹说:“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森发现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发现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周口店发现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1 6]胡适此语有为其整理国故申辩的意思,但还是叙写了一个事实,新的研究方法开始影响传统的研究,甚至动摇了传统学术的根基。知识的学科性质导致学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各领域的研究方法开始相互借鉴和影响。桑兵认为近代国学研究“各学科的互动与整合实际上已经开始,……就学科而言,要求多学科的专家合作研究有关课题”。[17]近代大学也开始了自我转向,蔡元培在北大废科设系就提出理论上“要精确地限定任何一门学科的范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18]就认识到学科界限的模糊,进而图书馆、实验室逐步完善,特别要提及的是由北大促成的杜威访华成为学术交流的标志性事件,代表着中西学术交流的高层化,学术研究的开放特征彰显,出国留学、考察、学术交流被定型成为日常的办学行为,合作研究、兼容并包的制度设计等等都为研究上的综合提供了可能。
(六)由有限传播模式向媒介传播模式转型
传统学术的传承和影响由于历史的局限大多靠口口相传、师徒相授或家传世业,即使有些印刷,往往印量较少,无法广为传播。现代学术媒介之报纸大约始于唐代的邸报,仅供藩帅等少数官员阅览,宋代的邸报成为“朝报”。政府直接管理邸报,意在控制新闻发布权,将新闻传播纳入为政府服务的轨道。[19]邸报流行愈广、影响愈大,政府对邸报内容的控制也就愈加严厉。严格控制和书籍刊刻成本造成的有限性极大地阻碍了我国民间社会和上层精英的互动,也限制了学术的扩散性传播,从而开启民智成为一项艰巨的工作。
近代报刊、出版业等学术传播媒介的发展,为西方学术的传播、学术规范的建立、传统文化的保存起到了巨大作用。晚清中国,西书出版机构先后就有一百多家,按其属性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教会主持,二是政府官办,三是民间商办。[20]
近代大学在突破学术传播的有限性上作出了多种努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体现了学术开放的意识,而校内自由讲学、自由听课甚至出现大量的旁听生等等无不扩大了北大的学术影响。近代大学作为学术研究的中心,其学术成果的表达自然受益于近代传媒发展的巨大成就,近代大学也创办了自己的诸多杂志,近代大学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创办了《新潮》、《每周评论》、《努力》、《国民杂志》、《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学衡》等等多种学术杂志,1902年,北京大学创设了出版社,此后充分利用校内外传播媒介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成果,成就了自身新文化运动中心的美誉,在救亡的共同主题下,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在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过程中,近代大学为适应这种转型进行了艰难的尝试,较好地实现了西方大学管理模式的中国化,近代中国大学的组织设计体现了大学的理性精神。
二、近代大学学术管理转型的影响
对近代学术转型的研究,不仅需要从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入手,考察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过程,分析其转变的动因、契机过程,考察学术研究方法、立场、内容等范式转变;而且更要从学术发展的外部环境入手,探究清末民初社会结构、阶层变动、西学思潮涌动等因素对学术转变的影响,梳理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新旧学术体制、学术交流机制等转变的轨迹,研究中国现代学术的制度化、体制化、分科化、职业化等问题,[21]而对近代大学学术管理转型的研究,不仅要从学术着手,更要从大学组织着手,研究近代大学的历史遗留和现实局限,并深入探讨近代大学内部管理的权力分配对学术管理体制构建及转型的影响,研究大学学人和社会知识分子、社会学术机构如出版机构、社团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近代大学学术管理的转型是个复杂的过程,关系到学术主体、学术组织、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管理机制等多方面的问题。
近代中国大学作为后发外生型组织,在外力作用下,割裂了传统知识传承、生产的逻辑关系,在和整体社会互动下,近代中国大学深深陷入这种社会、政治、经济、学术等多领域、深层次、广辐射的整体转型过程中,开始了自己的匆忙转型。1903年书院改学堂的举措将我国特有的具备着大约与中世纪大学同属性的书院废弃,使近代中国大学全然丧失了根基。中国近代大学在内外压迫下的转型是不自觉的,其自我的逻辑基础被割裂了,因此早期大学的转型是困难的。这从京师同文馆设算学馆的争论乃至京师大学堂的老爷型书生身上可以看出传统学术逻辑的惯性和固执。现代西方学术范式为大学转型注入了新的动力,西方现代大学管理模式又为大学管理提供了良好的范本,但是,我们还是看到转型的诸多不彻底,范本的多样综合,传统知识逻辑的执拗回归,内在学术精神的培育与外在制度设计的冲突,等等。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等以“思想自由”的理想对大学的改造更多的靠人格的力量,而不是制度的力量,“兼容并包”制度设计中的自由裁量仍然带有非常浓厚的传统的人治色彩。以蔡元培为成功标志的北大模式也为后世大学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如其仿习德国的纯粹学术研究所设计的学术分校制度实际上加强了传统重学轻术、重道轻器的倾向,其后美国化的科层设计又带来官僚主义倾向,重文轻理的实际操作也没有实现其文理平衡的大学理想,后世大学一直在文、理之间来回纠偏,等等。在当今社会普遍的工具理性、制度崇拜潮流下,当代大学学术管理中泛制度化也产生了合理的权利漠视和压迫,评估、量化手段的滥用也背离了学术的初衷,借学术的名义,非学术的内容过多地侵袭了学术的领地,挤占了稀缺的学术资源。学术生产组织化也产生了项目制度,学术生产被计划安排,显然背离了学术生产的逻辑规律;管理的职业化导致大学内部管理行政权力泛化,无限挤压学术权力,儒生和吏员的传统斗争在校园内重现;学科知识大行其道,忽视整体性知识,人文精神弱化,批判精神失落,传统积淀的文化底蕴被忽视;研究的综合化导致人文学科科学化,科学的势力霸占价值领域,思辨失去了价值力量,开始向科学寻求保护;传播媒介的发达导致舆论话语的强权,大学往往在舆论的压迫下作出违背大学价值取向的选择;等等。在这样诸多管理失范的态势下,在近代大学的学术管理转型中,我们能借鉴些什么?一些传统的人格化管理力量、个体化的学术生产方式、松散的管理状态、整体普遍的管理趋向等等是否应该回复到我们久已疏离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