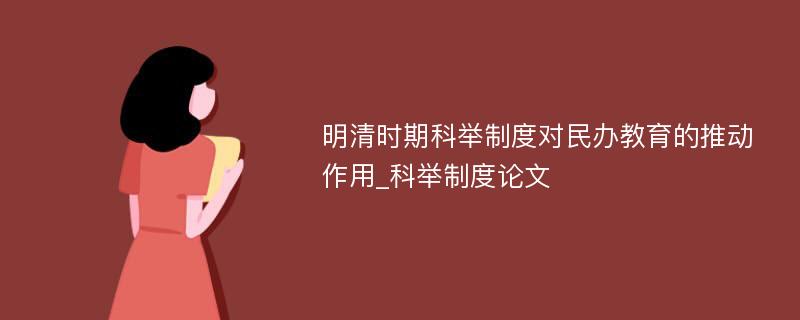
明清科举制度对民营教育的促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民营论文,明清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1)04-0098-07
一、明初科举制度的反复与规范
明初科举制度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反复,荐举曾被朱元璋视为纠正科举弊端的重要途径。本来新王朝刚刚建立,正是急需人才的时候,朱元璋曾首先取重于科举,于洪武三年(1370年)起连续三年科举取士。他说:“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才抱道者,耻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言。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毋得与官。”[1](卷七十,选举志二)但连续三年科举之后,朱元璋发现所取录的人大多是“后生少年”,虽然文章做得头头是道,却缺乏实际工作能力,“能以所学措诸行事有寡”。因此洪武六年(1373年)便宣布废科举而行荐举,要求有司采举“山林之士德行文艺可称者”,“备礼遣送至京,朕将任用之,以国致治”。“其目:曰聪明正直、曰贤良方正、曰孝悌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举人、曰耆民。皆礼送京师,不次擢用。而各省贡生亦由太学以进。”[1](卷七十一,选举志三)荐举制度推行到洪武十七年(1384年),另一类问题又凸显出来,就是被荐举者队伍日益庞大,几致无官可授的地步,而且被荐举者中亦良莠不齐,举主或疏于考察,或以权谋私,被荐举者往往亦奔竞钻营,“任不举职”的现象非常普遍。经过实践的比较,朱元璋认识到科举的优越性,便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八月下诏恢复科举,洪武十七年(1384年)定科举程式,命礼部颁行各省,最终确立起科举制度的地位。科举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诸如科举程式、场级、内容、名额分配乃至庶吉士制度都不断规范起来。明清两朝,参加府、州、县学考试的人数相当可观。乾隆初年,凡属大学(就规模而言,而不是指程度),应试童生自一千数百以至二三千人。因此,明清官学办学规模屡屡突破其初始的规制,表现为生员名目上,有所谓廪膳生员、增广生员和附学生员。与此同时,私学、家学、宗族之学也随之勃兴,“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重规叠矩,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海涯。”[1](卷六九,选举志一)明清学校之盛(数量),为唐宋以来所不及。
其次,明清有举人入监制度(始于永乐年间),即会试落第的举人,由翰林院择其优者送入国子监肄业。这些人称为“举监”。“举监”一面在监肄业,一面等到下次会试时出监应试。“举监”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国子监生的来源。与此同时,明清两朝规定的乡试取录配额,又特重国子监(或国子监所在地),加之生员录取数额毕竟有限,且从考取生员到应乡试要经过一系列的考试,而且有监生资格者,便可同生员(秀才)一样参加乡试,这致使不少人争相入监。特别是例监制的实施,报捐监生者人数更多。捐监散于全国,名为监生,实则大多数并不在监。其捐监的目的不外乎“提高声誉”和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其中后者是主要的。要参加乡试,就得认真准备,即使不在监读书,也不致随便荒废举业。因此,由科举诱导出的捐监制度,不仅推动了明清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规模上的扩大,而且丰富了国子监的办学模式。捐监近似于当代的函授,这就使国子监成为一所“开放式大学”。至于教育质量,不能因为捐监者中有纯粹出于“提高声誉”动机者,而断言捐监为滥收之举,皆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捐监者多为庶民,来自社会中下层。捐监可以提高声誉,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即使由捐监而例贡而入仕,在明清官僚队伍中亦属杂流出身,不受尊崇和重用,因此对大多数捐监者来说,捐监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们以此为跳板,参加科举考试,进而入仕为官。所以,尽管捐监生水平差异较大,但就总体而言,其读书态度是认真的,也是有一定质量的。
由于官学一般不能满足全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民营教育便在科举录用人才的感召下,在官营教育之外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二、文化和仕宦望族的家族教育——维持门风的科举教育
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录,专重才能。能否通过各级考试,最终获得功名出身,进入仕途,从理论上说取决于应考者是否有“才”。这就促使考生留意学问,勤于举业。特别是明清科举功令日密,立法周严,打击得力,就是达官贵族、豪强地主子弟,亦不敢贸然放弃学业,专事营求,希图以通关节而幸获,更遑论广大考生。这就在社会上,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自觉求学的风气。明清名人教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子孙应惜时勉学,立志成材。地主阶级自然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条件,可以让其子弟静心读书,以求科场显名。至于商人家庭,由于经济条件相对好些,更是竭力供其子弟读书,希望由此而改变其低下的社会地位。明清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的涌现使得知识阶层的数量大为扩大,不仅直接增强了科举考试的竞争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了学校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数量的发展。在科举面前,势家大族要维持住自己的地位,必须与庶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尽管家族可能提供给他们的经济条件较好,但那不是能否中举的充分条件或唯一条件,应举者的聪慧和勤勉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因而许多大家族对子弟的培养也是倾尽了心思的。明清时期势家大族的家学甚为发达,实际上可以看成是科举制度得以广泛推行的产物,也可以看成是大家族为维持自己地位所作的艰辛努力。这些家族的子弟大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以文化功名立身处世、光宗耀祖的精神抱负,“以为尔门户若是,闻见丽泽若是,而弗能是,是不肖者。从而曰:‘是某氏之子也!’可不惧哉!夫门第之盛,可惧如此,乃不若彼无所恃者之易于为贤,岂此之所负固重哉!”[2](卷十八)张习孔《家训》说:“世间平人多贵人少,科甲岂可常得乎!然书香不可绝。书香一绝,则家声渐夷于卑贱。家声既卑,则出人渐鄙陋。人既鄙陋,则上无君子之交,下无治生之智。其安于农樵负担者,犹为善也。甚至人既粗蠢,心复雄高,狎比下贱,冥行蹈险。呜呼!人生至此,不忍言矣。若敖之鬼,从此长馁矣。猛念几此,安可不教子读书。”这种强烈的不辱家声、不坠门望的上进心情正是其“不废而益勤”的精神支柱。像华亭沈易家族、奉贤王端家族、上海陆深家族、崇明施氏、宝山金翊家族、川沙沈璞家族等皆因此而科第绵延、簪缨联翩,门祚贯联明清两代。例如明朝天启七年(1627年)丁卯科举人潘桓,出身于明代上海县著名的官宦世家潘恩家族。潘桓的高祖潘奎,字用章,号颐庵,初充郡掾,嗣授河南项城典史,摄商水县令,潘桓的曾祖潘恩(潘奎长子),字子仁,特号湛川,后改号笠江,上海县人。嘉靖二年(1523年)癸未进士,初授祁州知州,累迁山东副使,历官工、刑二部尚书,后改官左都御史致仕,卒谥“恭定”。潘恩长子潘允哲(潘桓伯祖),字伯明,号衡斋,嘉靖四十年(1565年)乙丑进士,初知新蔡县,调令义乌,出守黄州,擢升山东副使。潘恩次子潘允端(潘桓祖父),字仲履,号充庵,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壬戌进士,授刑部主事,累官四川布政使。潘恩季子潘允亮,字士逢,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己未进士。明代上海县潘奎家族,自潘恩之后“其后不特任子、资郎,联镶接踵,即科第亦累传不绝。……衣冠轩冕,绵延百年。”[3](卷五,门祚二)潘桓即出身于明代上海县这个世代官宦之家的潘恩家族,该家族入清以后仍有仕宦之人。
清代嘉兴钱大昕家族形成了科第繁盛的局面。钱大昕长子钱东璧,17岁补博士弟子,太学生,游历京师,诗、古文名重公卿,有“小钱”之称。次子钱东塾,廪贡生,署吴县训导,善隶草、工山水,著有《月波楼诗集》等。钱大昕族子钱塘,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庚子进士,选江宁府教授,著有《律吕古义》、《史记三书释疑》、《泮宫雅乐释律》等多种著作。钱塘之弟钱坫,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甲午顺天副榜贡生,补乾州州判,历署兴平韩城、大荔知县,华州知州,撰有《史记补注》、《尔雅释义》、《圣贤冢墓志》等多种著作。
在上海地区,董其昌、徐阶、陆树声、徐光启、潘恩、陆深、王广心、王顼龄、王鸿绪、钱大昕、王敬铭、王鸣盛、王昶、印光任、徐恕、陈兆熊、黄体仁等均由科举入仕。吴仁安先生对上海望族的研究也说明了科举已成为望族得以形成的最基本途径。[4]
道光六年(1826年)襄阳知府周凯手订的《义学章程》的《序言》中说:“近因各乡村蒙馆太少,义学不设,以致风俗犷悍,好勇斗狠,轻生犯上,皆由蒙童失教之故。本府与诸牧令劝谕绅耆,就地设义学,以教贫民子弟,成为安身良民。”教育学童成为“安身良民”,不使“好勇斗狠,轻生犯上”正是清政府遍设义学的出发点。
《红楼梦》第九回:“原来这义学也离家不远,原系当日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不能延师者,即入此中读书,凡族中为官者,皆有帮助银两,以为学中膏火之费。”凡在外为官者,一般皆把培养族中子弟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曾国藩在江宁闻侄子考中秀才,十分欣喜,致书诸弟,充分表露了显宦对后人之期盼。信中说:“纪瑞侄得取县案首,喜慰无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励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5](P1193)左宗棠于儿子进学,亦表欣悦,致书谆谆戒勉勿进于骄满:“尔幸附学籍,人多以贺我,我亦颇以为乐。然吾家积代以来,皆苦读能文,仅博一(衿);入学之年均在二十岁以外,惟尔仲父十五岁得冠县庠,为仅见之事。今尔年甫十七亦复得此,自忖文字能如仲父及而翁十七时否?家太冲诗云:‘以彼径寸根,荫此千尺条’。盖慨世胄之致身易于寒畯也。尔勿以妄自矜宠,使人轻尔。”[6](P55)左宗棠在另一封信中又申明创立功名维持门风之意旨:“尔年十六七,正是读书时候,能苦心力学,作一明白秀才,无坠门风,即是幸事。”[6](P57)对于门风的维持使世家大族更多地致力于家族子弟的培养和教育。
三、商人家庭的文化教育——科举与实用教育兼顾
我们从许多文献中了解到,在传统社会中,商人阶层几乎并没有形成为一个稳定和独立的阶层,许多经商者只是为了改变自己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由商返儒。如闽西四堡马大昭“少攻举子业,不就,改而贸易,足迹几遍天下。”马孟吉“幼业儒,不售,弃而业贾,遂有盈余。”邹信亮“援例入国学,益攻举子业,制艺卓然浑成,战棘闱者再焉,然终困场屋……乃出门赁一书肆,名虽服贾,其实雅好与先生交。”邹朝锦“因家传清白,世路崎岖,随弃儒而就贾焉……由是束装随诸尔辈,携经史书籍,游于洞悉两粤之区……经纪数年,获利常倍。”邹新楚“家贫未尝读,日事耕稼,及壮,兼营商业,奔走市廛。”邹明镇“因家计稍艰,遂弃儒业,有遨游于东南两粤之地。”[7](P55)咸丰时同安的吴果堂“惟性敏喜读书,家贫不能专业,弱冠后撒欢能够于广东潮州,孝养父母不衰。”洪志荣“幼好学”,却因“家贫弃儒经商,经菲律宾依长兄培庆习贾”,后重治父丧,回家守孝,为长兄立嗣,为次兄娶妇,课次弟读书,后却因家计只得“复挈弟往菲营前业,适弟能树立可以赡家即归,而整理家政,构造夏屋,一手经营,不辞劳瘁,以少失学,善栽培后进向学。”[8](P55)侯官陈鸣凤是一个由求仕无门而经营小贩的例子。他“年十二即能文,下笔千余言,然试有司辄北,家贫遂弃举业而就小贩,未几父母相继殁,殡殓之资无所出,乃尽售家之什物得十余金以治两丧。”其后他带着兄弟“日为人司账簿,夜则就庐中共读,如是三年始还家,作麦贩生理,后家渐裕,光绪某年麦账被欠约千余金,其中有夫死而子幼者,母病而家贫者,鸣凤悯焉,尽出券焚之。某乡游某将卖幼女偿宿债,其妻悲不忍,舍出五十金代偿之,更与十金俾作小贩。”[9](P55)
明清时期商人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商业资本亦大量流入学校事业中。一般说来,在商业发达、商人集中的地区,学校文化设施也比较崇峻。如晋江安海出现了黄居中黄虞稷父子的“千顷堂”,藏书最多时达8万余卷,藏书的丰富自然为熏育人才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再从明代开科取士的数字看,有明一代,安海中进士33人,中武进士4人,中举人18人,中武举人25人。仅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一科,安海就中了5名。[10]浙江南浔是一个商业繁荣的集镇,“前明中叶,科举极盛,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入清以后,南浔更是“书场与机纾声往往夜分相续”。[11]在安徽徽州,商人“以诗书训子弟”,从而“子孙取高科登显仕者”代不乏人,他们倾大量的商业资本于兴办学校,促进了封建文化事业的发展,赢得了“东南邹鲁”的美誉。著名海商郑芝龙除“田园遍闽广”外,注重使子弟接受正统思想的教化,郑成功7岁时即延师课读,15岁补县学生员,21岁入南京太学,师钱谦益。[12]此外郑芝龙之弟郑鸿逵中崇祯十三年(1640年)庚辰科进士。在佛山,宗族内对获得科第者给予诸多奖励,商贾“供子弟读书”被列为一善。[13]日本学者寺田隆信考察山西商人时发现寓居外地的山西商人的后代很多亦凭借商业资本这个坚强后盾跻入到科举及第者的行列。我们说,明清时期商业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儒业,而儒业也日益依赖于商业。清人沈尧说:“宋太祖乃尽收天下之利全规于官,于是士大夫始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一切与古异矣。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农桑之业者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非父兄先营于前,子弟即无田读书以致身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益甚。”[14](P41-42)儒业与商业形成了互补共进的发展。
张正明在《晋商兴衰史》中说:“他们经商致富后,大多聘名师,办私塾,培养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如两淮科举中,商籍入考人数大大超过土著。据《两淮盐法志》卷49《科举志》统计:明代两淮科考中:进士共317名,其中歙人70名,陕西30名,山西6名,土著31名;举人歙人162名,陕西42名,山西9名,土著73名;贡生共88名,其中歙人3名,陕西3名,山西1名,土著81名。由此可知,明代两淮科考中经商家庭出身的徽、陕、晋籍进士106名,占总数的77%;举人216名,占总数的74%,贡生人数少,仅7名,占总数的8%。最有典型意义的是清代嘉庆年间,福建永定、上杭、龙岩及汀州等地的廖姓商众在福州省城共建试馆一所,把为族人参加科举考试提供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这些都反映了商人好儒的习性。
像山西商人、徽州商人、闽粤商人还兴办起实用知识的学校,如山西商人兴办河东运学,目的在于“建有专学,则师道立而教化行,理义明而风俗美”[15]。有的商人编写出商业专书在商业实践中实施对商人后继者的教育。
四、一般民众的文化教育——从科举走向实用教育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培养出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他们或者取得了更高一级的功名,或者考场失利,但他们多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夙愿,因而他们亦努力寻求服务于社会的可能方式,为吏佐治是一途,坐馆育才则是另一途。是科举考试培养的学生不断充实着民间教育中的师资力量,从而实现了教育的大众化和教育的全面普及。
科举作为一种选官制度,其意义不仅在于选拔出了一批能联系官民、沟通上下的官吏,而且还在于它为全社会的人们树立起了一批形象楷模。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16]说:早在明代中期的成化五年(1469年)己丑进士中平民出身率已经高达60%,上文所说的诸世家大族往往也是由一般民众成长起来的。
在许多蒙学读物中,亦充满了以科举激励儿童发奋读书的话语,如《神童诗》中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莫道儒冠误,诗书不负人,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遗子黄金宝,何如教一经,姓名书锦轴,朱紫佐朝廷。”“大比因时举,乡书以类升,名题仙桂册,天府快先登。”“喜中青钱选,才高压众英,萤窗新脱迹,雁塔早题名。”“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玉殿传金榜,君恩与状头,英雄三百辈,随我步瀛洲。”“慷慨丈夫志,生当忠孝门,为官须作相,及第必争先。”除此之外,还有《三字经》中的“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增广贤文》中的“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幼学琼林》中的“窦钧五子齐荣,人称五桂。”所有这些,都可能化为童子们强大的精神动力,提升着他们读书成名的品位。
当然,也有不少人并不一味地追求中科举,他们把教育看作是培养技艺的场所,树立优良品行的基地。如福州《通贤龚氏支谱祠堂条例》“书田”条说:“书田培元气也,子弟不可以不读书,不特发科甲高门第也。读书明大义识道理,即经营生理明白者,自不至于受人之愚,但往往父兄无力,遂至子孙废学,目不识丁,即数目字尚不能悉,何异马牛而襟裾乎?且长大何处觅生活也。谓宜捐置书田,立义塾于祠堂左右之地,请业师于其中,使贫无力之子弟得以肄业其中,上可以辍科名为祖宗光显,下亦可以识字明理,不至如马牛之踟躇,夫吾祖吾宗之所乐欤?”江苏昆陵《恤孤家塾规条》云:“生徒如质地平常,粗能识字记账,即须学习生理,藉以养母成家。拟于长夏饭后请熟于算法者一人,赴塾教孤子算法,酬送劳金,年在十一岁以上者方令学习,能出塾习生理,每生送钱一千四百文以助置衣履之费。”[17]这表明,教育的指向一方面是科举,一方面则是其他诸多实用的需要。但是,这些教育形式的兴起,都与科举的发展以及它为社会提供了足够的师资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清入仕倚重科举,科举制度的实施造就了数量庞大的科举人口。从生监、举人到进士,逐层筛选,除绝大部分进士、部分举人及少数生监入仕为官之外,其余的则自谋职业。作为知识分子,他们中大多数又以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为谋生手段,或受聘为师,或自立学馆,或讲学书院,从而加入教育这一行业。即使入仕为官者,其中亦有不少就职官学,或成为学校教师,或为教育行政官员,对明清教育发展直接起着推动作用。
实际上,明清社会各阶层都加入到兴办教育的行列。如《不下带编》中记一孤老“尽以蓄产为学田”。《郎潜纪闻》则记载:“台州府太平县李氏女,许嫁于林,未嫁而夫死,女奔其丧,奉舅姑以终,林故贫族,女以针黹营生,节衣缩食,有余即置田产,积十余年,有田六十亩,因无后可立,以其田呈请学使,每岁按试,取第一者主之,极所入息分为四,以其三助文生之贫不能应试者,而以其一助武生。”[18]其他一般农(主要是自耕农)、工、商家庭也颇重学业,尽力创造条件,让子弟入学读书。清代河北临榆县从乾隆到嘉庆、道光年间,共表彰有子女的节妇118人,其中含辛茹苦将儿子抚育成秀才者有43人。她们不少人靠“昼夜纺织”,“供其子膏火修脯之用”,一个由寡妇支撑的家庭当不会自甘落后。
明清民间教育固然把科举作为主要目标,但那些办学的倡导者们亦多致力于造就知书达礼、能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清人王鸣盛说:“立国以养人才为本,教家何独不然,令合族子弟而教之,他日有发名成业起为卿大夫者,俾族得所庇……即未能为卿大夫而服习乎诗书行义之训,必皆知自爱,族人得相与维系而不散。”[19]江苏昆山《李氏族谱》中说:“读书非仅为科名也,能研求义理,学为好人,即不必科名始贵。”江苏华亭《顾氏族谱》中说:“子弟入族塾就学,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培植根本,实行为重,非欲其专攻举业,求取功名。”福建连城四堡邹氏家族办族学教育子弟,也希望使族人都成为知书识字之人,“不辱我诗书礼义之乡”。[20]
由于科举把教育与为政直接联系起来,而为政被全社会普遍认同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方式,故兴办教育事业成为明清时期许多阶层认定的崇高之举,乃至形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风气。对于民间教育而言,有时并不一定仅在学校里进行,在科举精神的激励下,许多人在各项生计活动中,亦往往不舍诗书,从而实现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也当视为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积极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