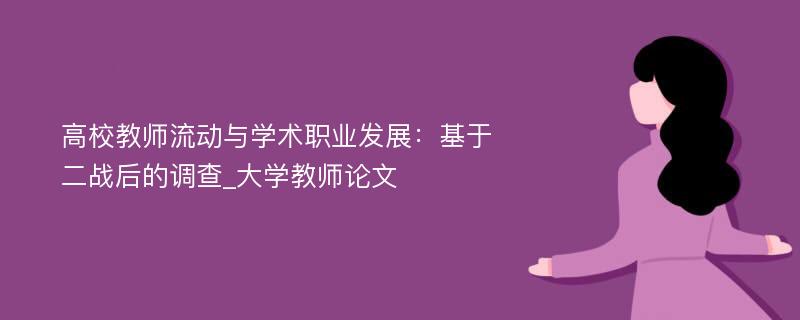
大学教师流动与学术职业发展:基于对二战后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后论文,职业发展论文,学术论文,教师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4)02-0043-08 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各国对于专业人才的需求大幅增加,学术职业作为培养专业人才的“关键职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学术职业大发展的同时,流动如影随形,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90年代至今达到高峰,在这一过程中,大学教师流动表现出几个较为显著的特征。 一、从结构性迁徙到制度性迁徙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数以万计的科学家逃离曾经的科学中心——德国,作为主要接收地的美国、英国等成为流动的受益者。尤其是美国,在早期就大量派遣学者赴德国留学,这部分人的回归带来了洪堡的教育思想,带回了尖端知识,并建立起精良的学术机构和实验室,结合美国自身对于高等教育服务理念的创新,美国在二战前就已形成了高等教育的“高原”。大批德国及其他“轴心国”科学家的到来,极大充实了美国的研究实力,带动了相关大学和研究所的发展,使美国从学术“高原”走向“高峰”,世界科学中心在德国盘桓近百年之后转移到了美国。 笔者将这种因种族、信仰和战乱等原因导致的教师大规模流动定义为结构性迁徙。比如在冷战期间,大批前苏联国家的科学家“叛逃”至美国,一定程度上使美苏竞赛的天平向美国倾斜。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大规模的俄罗斯科学家流向西欧和北美,动摇了前苏联科学发展的基础。一些区域性的战争或民族冲突导致的大学教师流动也属于结构性迁徙的范畴,并在客观上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一位南斯拉夫种族清洗的受害者来到美国,并最终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他在获奖致辞中说“成为美国公民,在我所热爱的工作中得到了承认,并有幸结识杰出的学生和同事,这一切我感谢命运”。① 结构性大学教师流动,与政治、战争和意识形态关系极为密切,但毛泽东等人所预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最终并未打响,世界竞争模式转变为经济竞争,教师的结构性迁徙下降为次要形式,制度性迁徙成为主流。本文提出的制度性迁徙,与结构性迁徙相对应,主要是指因教育、经济等社会发展形式和程度不同,出于对教师的吸引而形成的有规律流动。 1.教育方面 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先后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学校数量的激增和学生规模的膨胀一度使大学教师供不应求。在一段时期放松学历要求之后,对于教育质量的反思使各国高等教育逐渐走出混乱,逐步加强了对学术职业入职资格的限制,对于博士学历或博士后经历的全面要求提升了学术职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和吸引力。学术吸引力的提升通过至少三条途径促进了教师的国际流动。 一是直接吸引教师学术移民。“科学总是因它的无国界性而自豪,大学教授们也因此以世界主义者自居,往往降低了对于学校和国家的忠诚度。”②这种世界主义与低忠诚度可能与学术职业的特点有关:一方面,教师们更愿意向学术中心或者高等教育中心靠拢,正如中世纪旅行的教师们向往巴黎,19、20世纪的教师向往德国一样,随着院校系统的日益接近、学位逐渐在国际范围内广为接受,当代大量的学术人员为了追求学术事业而移民国外,那些处于高等教育中心的国家意识到高层次人才对于教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所制定的移民政策“越来越有利于那些高技能人才”,最终帮助大学“聘用全球杰出人才”③,这为教师移民打开了方便之门,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另一方面,学术职业与其他职业相区别的一大特征是学者的群居属性——他们更愿意聚集在那些本学科发展水平较好的地方,“学者不喜欢学术上隔离,好学者往往聚集到一起。这种聚集是特别有效能的环境”④。这也促使他们按照学科的发展水平选择流动或移民的方向。 二是间接吸引“准学者”移民。好的高等教育质量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目前世界范围内至少有250万学生在他国学习,其中一部分通过攻读博士或从事博士后工作受到了专业的学术训练,成为“准学者”。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完成学位以后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这使他们的祖国失去了这些训练有素的人才。这种途径虽然是间接促进了学术职业的跨国流动,但在大学教师流动的人数比例中却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阿特巴赫就曾指出,80%从中国和印度出国留学的学生在学成以后没有立即返回自己的国家。⑤MIT前校长特维斯也曾指出,“我国(美国)高校的出类拔萃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国际学者的开放。获得诺贝尔奖的MIT教师包括来自日本、印度、意大利、墨西哥的成员。我们的教务长出生于以色列。我们有出生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院长。他们几乎都是作为研究生来到美国的。”⑥学生的流动引发的间接的大学教师流动具有明显的学科特性。以美国为例,当前约1/3的理工科博士学位授予了外国公民。这些博士学位获得者当中许多人最初都在美国求职,其中大约40%永远留在了美国。⑦ 三是通过短期学者交流促进教师跨国流动。还有大量的学术人员并不在国外攻读学位和移民他国,而是为了从事研究或教学暂时旅居国外。以访问学者等形式出现的教师也大大促进了国际学术流动。目前世界上虽无确切统计,但有研究估计,全球约有25万名访问学者,2002年,美国的大学吸收了其中的8.5万名。⑧在中国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中,教师们进行1至2年的出国学术访问已极为普遍。如果再纳入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等其他短期的跨国学术活动,则人数更多。这一过程中多数访问学者在旅居结束后回到自己的国家,但也有一些人定居外国。 2.经济方面 在《爱弥尔》中,卢梭强调不应提升大学教师的工资,因为这会让他们陷入金钱的追逐而不是学术追求。但不得不承认,当代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正使曾经清贫的学术职业变得富有和分化。 作为整体的学术职业,因薪酬的吸引力降低,存在大量向其他职业流动的情况。就工资水平来看,目前各国大学教师的工资很难与同等教育程度的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相比,发展中国家这一情况尤其严重,有些国家教师的工资“连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也无法维持”⑨,有些国家的学术职业沦为外围职业。 与现实工资水平相比,工作的稳定性预期也在下降。很多国家对于教师的职业阶梯设计从终身职位变为更多的固定合同、短期合同甚至兼职聘任,比如在美国,新的任命中只有一半是传统的终身教职。这既导致工资水平下降,又导致工作稳定性降低,而且聘任制度的改变使得管理主义的作风蔓延至高校,教师受到更强的官僚控制,他们管理自己时间安排的权利也减少了。⑩ 在学术职业内部,薪酬差异巨大,这也导致了人才向待遇更好的国家和地区流动。比如加拿大学者的平均工资比中国学者多6倍(11),而其他很多国家则比中国还低。在发达国家内部,也往往因薪酬的差距引发教师们的骚动,英国经济持续低迷,最顶尖的学术人才往往接受那些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酬的国家和大学的邀请,英国为此已不得不拨付资金,以将最优秀的教授留下。(12)发展中国家内部,这一分化也极为严重。以巴西为例,1992年和2008年两次学术职业国际调查发现,该国教师平均收入水平均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但2012年笔者从巴西最好的大学——圣保罗大学副校长的一场报告中获悉,该校学者年收入近8万美元,这和美国同类大学已基本持平。 二战后至今,美国学术职业的发展与经济因素也密切相关。4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学术职业的组成在进入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教师人数、工作形式和机构使命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对在学术和非学术领域全球竞争的社会回应。(13)在这一时期,学术职业的增长比例大大低于其他职业。工资收入增长也落后于其他职业,这一时期学术职业收入年均增长3.5%,非学术职业收入则在3.5%到6.21%之间。(14)低工资导致了新入职人员增加缓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52年。学术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显著增加,增量部分主要来自于其他职业向学术职业的流动。1958年之后美俄展开太空竞赛,整个国家的主旋律是通过科学竞赛促进经济增长。这导致对博士毕业生的需求上升,学术职位增加。(15)学术职业的工资也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5.21%,是其他非学术职业的两倍(16),大量其他职业从业者涌入学术职业。60年代,美国的经济条件对于学术职业充满了复杂的感情。尽管学术劳动力市场有所降温,学术职业的工资与其他学术市场还是有可比性的。这一时期的学术劳动力市场更多以男性和白人为主,这一时期的学术职业具有高度选择性,入职和种族、性别、宗教和政治都有关系。(17)学术职业直到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没有什么发展。(18)1940年,大约15万人受雇于美国的大学和学院。戏剧性的增加发生在60年代,5年内学术职业增加了15万人。在60年代中期,学院教授工作流动的比例爆炸性增长。在这段时间,8%的全职大学教师改变了工作。该时期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收到两个或更多职位的邀请是非常普遍的。(19)大学教师增长中女性的增长比例占19%,尤其集中在护理、图书馆科学和家庭经济学等领域。(20)学术劳动力市场在70年代和80年代在工资和入职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收益被学术职业的通货膨胀和招录人数降低所蚕食,教师的平均工资下降了21%,全职和兼职教师数从40.2万增加到52.2万人,10年内增加了30%。(21)在1972年至1982年间,工资的实际增长却是负向的。 在当代,经济因素影响大学教师流动的最典型例子发生在阿拉伯湾。这里并不是高等教育的发达地区,却也吸引了来自埃及、约旦和巴勒斯坦等地的学术人才,一部分印度人来到这里,另一部分印度人流向东南亚,流动的背后多是经济因素的主导。即使非洲大陆,也因存在经济的差别,出现一些地区性的大学教师流动,南非、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就因较好的经济条件,将非洲各地的人才补充到自己的国家。 而这种情况也因经济变化以及政府当局对高等教育投资意愿的变化随时发生着变化,比如中国的研究型大学近年来大幅提高了教师待遇,更多的华人教师在国外旅居一段时间后选择回到祖国,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大学以丰厚薪酬为武器,也吸引了一批西方的教师。这种教师的回流成为21世纪前10年学术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小规模的工业化国家仍将发现自己在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而那些海外学术人才的回流正在缓解这种情况。 回流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回国移民,二是回国兼职。一旦出生地的工资、工作条件、学术自由得到改善,一些国家的学术人才就从美国或其他国家返回祖国。即使不是国籍的回迁,也经常以作学术报告、咨询、与出生地国家的同行进行合作研究或者接受兼职教授职位等方式,与祖国保持密切联系,这种趋势在中国、印度、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南非等国家和地区非常显著。 社会发展水平除了上述的教育和经济之外,还包含制度文化等内容,如更好的学术自由保障、更适合的人居环境、更高的国民素质,包括相关的法律环境等,也成为了大学教师流动的重要因素。 二、全球化、国际化、本土化与当代大学教师流动 国际性的大学教师流动开始于学术职业诞生之初,教师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使国际性成为学术职业的天然属性。20世纪后半叶,这种国际性的大学教师流动开始伴随着全球化的展开而日渐加剧,“大学以及大学创造的知识、招聘的学者、培养的学生最终都直接与全球知识经济联系在了一起”(22)。进入21世纪后,随着现代技术、互联网、日益频繁的交流、学生和受过良好教育人员的跨境流动,国际化成为大学教师流动的显著特征和生存之道,“没有一个院校系统可以在21世纪孑然自立”(23),同样,也没有一位大学教师可以在21世纪孑然独立。国际化成为教师必须面对的议题。 但仍有必要区分国际化和全球化这两个与学术职业流动关系密切的词汇。阿特巴赫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全球化和国际化这两个词联系紧密,被广泛使用和相互替代,但是它们指代的内容截然不同。“全球化是指‘当今世界对高等教育有直接影响并难以避免的经济、政治、社会、技术以及科学的广泛趋势’。国际化则更多地与‘由政府、学术体制和学术机构及各个从事全球化研究的院系所制定的政策和项目’相关。”(24)他认为两者的关键概念在于是否能够被“控制”,全球化及其影响不是个人、机构或组织能够控制的,而国际化却能被视为“社会和机构为了应对全球化影响的一种战略以及高等教育的一种人才培养方式”(25)。按照阿特巴赫的定义,可以认为,全球化是当前大学教师流动的背景性因素,高等教育不可能跳出全球化的环境,因为其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高等教育机构所在地区的财富、语言、学术发展及其他因素都影响其全球化的程度。国际化则是包含有制度设计、各国高等教育组织努力的一种人、项目或者机构的流动。 当代跨国学术流动与中世纪有非常多的可比之处,比如遇到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困境就极为相似。早在中世纪时期,大学教师流动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之争就已显现。博洛尼亚大学正是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不当,导致了大批优质师资的外流。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国际化和本土化的二元悖论。一方面,“闭关自守”从事科学研究已无法适应当今的学术发展要求,完全依靠本土培养顶级教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学术职业吸引力较低,那些获得国外学位的优秀学者往往滞留不归,这种不对等的人才流动像一个巨大的漩涡,吸走了发展中国家最优秀的学术人才。 与中世纪更多信奉宗教或学术追求的个人意志主导的学术流动相比,当今的国际学术流动表现出很强的制度性和规律性,这背后的根源是巨大的国际性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已基本成型。国际化疏通了跨国大学教师流动的渠道,打造了一个全球化的学术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遵循的是市场规律中的人才价值判断和支付能力筛选的基本原则,最优秀的教师流入市场,知识、能力和已有的声望成为交易的筹码,缺乏对国家和大学基本忠诚的学术市场极大促进了大学教师流动。欧洲国家自二战之后,经济增长缓慢,且无法提供充足的终身职位,导致学术职业薪酬收入下降(比如英国学者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这种情况下,19、20世纪那种美国学者奔走于欧洲街头的情景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大批欧洲教师的“叛逃”。欧洲国家中曾经较为独特的案例——德国,这个强调自由和寂寞,进行纯学术研究的国度,教师曾像修行的僧侣一般,恪守心中神圣的大学理念,在初级岗位上一待数年,直至教授职位空缺获得填补资格。但近年来,这种坚守也在向学术市场投降,一旦在初级岗位上得到来自其他国家大学的邀请,许多德国教师就选择立即离开。德国人已开始讨论这种行为对高等教育持久发展的影响,讨论减少初级研究者数量等举措。不仅是德国,很多国家很早就认识到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这对矛盾的重要性,目前基本的做法包括:通过增加薪金、降低教学工作量等提升学术职业吸引力,构建地区性的或跨国的学术市场联盟、鼓励教师在区域内流动,提供留学基金并签订回国协议等。 如果从人类知识生长的角度来看,国际化是有益的,而如果从保护弱势国家、促进地区均衡的角度来说,则本土化是有益的。正如不同价值视角的判断存在差异一样,目前国际化和本土化对于人才流动的争夺还在继续。 三、教学研究的分野与当代大学教师流动 与洪堡所倡导的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思想不同,当代大学教师流动开始出现教学和研究分离的状况。学术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正变得更加专业化,越来越多的教师只是被聘用来教学,并不从事研究或为学术发展做贡献。与此同时,大学中开始出现“非教师”(non-teacher)群体,“地位越高,与学生联系越少”。教学在巨型大学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研究则相反。过去统一的有关“大学教师”的指代演变成了具有鲜明层级性的群体分化,至少有三重结构:只做研究的人,教学和研究都做一些的人,只教书的人,教学成为教师功能的附属。(26)这一过程中,教师结构发生变化,研究型大学中精英教授群体数量降低,从事教学活动频率降低,但该群体掌握的科研经费、学术出版物的生产大大增加。美国研究型大学中这种精英教授占教授总数的比例不足20%,而剩下的所谓的“非精英教授”承担起主要的教学任务,却很少参加科研和社会服务。 在“影响学术职业变革的力量——多国比较的视角”国际会议上,多国学者都报告了本国学术职业存在教学和科研分离的状况和趋势。南非只有22%被调查的大学教师同意教学和研究是可以和谐共处的,有13%的人将自己直接定位为研究者。一些国家大学教师对于教学和科研的爱好失衡,带来学术职业发展的困境。正如一位墨西哥学者所讲到的,到2020年,该国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毛入学率达到60%,这需要大量的师资力量从事教学工作,而现实是,大学教师更希望成为研究者,这是该国学术职业发展必然要面对的一个矛盾。日本学者对比了1992年和2007年两次全球学术职业的调查数据,发现各国对于教学科研的态度、研究偏好都在发生变化。在过去15年当中,教学正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研究越来越重要。 学术职业中教学和科研分离的趋势,非常清晰地表现在了大学教师流动问题上:在教师任职谈判中加入了教学负担的讨论,大学在试图聘请优秀教师时,除了奉上有吸引力的工资,尤其是研究费用(在理工科众多领域,这一费用达数十万美元),“竞聘教师的出价还包括大幅度压缩教学负担的承诺”。(27) 大学教师流动中教学和研究的分野,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在大学对学者的争夺日渐激烈的情况下,迫于财力有限,大学不可能无限制通过增加薪酬来提升吸引力,虽然如此,大学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增加教授收入,这种间接的方式主要就是引导教授出售知识和智慧。无论是大学还是教师都意识到,最大潜力的额外收入来自于政府和私有部门的合同,同时他们也意识到,教学的好坏是较难进行评估的,因此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专利的申请、项目的申请以及维护与资助者的关系上,而这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循环,学术上的努力带来更多的项目资助,更多彰显学术水平的出版物问世,获得更多的奖励、荣誉和项目,更加轻视教学,最终的结果是“教学科研人员的努力从由政府固定拨款与学费资助的活动,特别是教学及相关活动,显著地转向在竞争性的、‘市场性的’领域中创造收入并满足那些奖励条件的活动”(28)。而且不仅出现教学和科研的分野,科研内部也分成了显性的科研和非显性的科研:在贴近市场的领域,教学科研人员受到最高奖励。这种显性和非显性最终体现为工资级差,即教师们从大学以外专业人员的劳动力市场赢得外部收入的能力。而那些所谓的基础学科,往往因这种能力的缺乏难以吸引到最优秀的学术人员,有经济潜力的研究优先于基础的或好奇心驱动的研究。 对于大学而言,是乐见这种情况发生的。大学之间彼此存在激烈的竞争,大学为此也需要维护和提高自身的声誉,大学希望引入更多的明星教授。正如克拉克·克尔所言,“那些试图在学术等级制中上升的大学往往可以通过新的学术专业和体育而迅速和轻易地吸引全国的注意——也可以通过雇用伟大的、有名的学术明星。一个‘野心勃勃的’大学的标志是它疯狂地争夺橄榄球明星和学术泰斗。前者不学习,后者不教课,因此他们形成了一个肌肉与才智的美妙结合”。(29)明星教授,除了可以显著提高大学的声望,也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研究经费。很多国家都已改革大学拨款模式为项目制拨款,学术明星意味着学科实力的增加,在这种竞争中往往拔得头筹。对于教师而言,他们也非常支持教学与科研的分离。一方面,这是增加收入的大好机会,他们附和着大学的做法并努力使之加强,因为他们很清楚,“研究导向和研究产出对学者来说就意味着最高的荣誉和(常常)最好的待遇,所以他们常常迫使学校强调研究是大学的关键使命”(30)。另一方面,当今大学教师非常重视即时声誉的获得,他们对轰动效应非常渴求,热衷于追求突破性进展,教学与科研的分离将使其拥有更自由和充分的时间为这种轰动效应努力。 教学与科研的分野,除了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也伴随有时代背景的影响或其他原因。比如高校教师分类管理的大背景。在高等教育和学术职业大发展之后,在承认劳动需要分工和人的能力有限的前提下,高校教师分类提上议程。有人将学术职业定义为学习、继承、传播、创造知识的职业,对应不同的知识生产者从事着不同的知识工作,如与研究相关的知识、与教学相关的知识、与专业训练相关的知识、与批判训练相关的知识等,目前对于学术职业的分工也大致遵循这种工作职能的划分思路。特殊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也一定程度导致了教学和科研的分野。法国和中国等少数国家,存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并世而立的格局,这种双轨制使得某些科研机构率先进行了教学和科研的分离。教学和科研的分野在推进分类管理、提高个体教授科研能动性等方面获得收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的出现。 一是大学教师流动性大幅增加,稳定性降低。首先是兼职教师的比例不断攀升。目前的文献中尚未见有学者研究,回答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教学和科研的分化-教学型教师地位下降-基于成本的考虑大学开始大量裁撤教学型教师-教学型教师成为流动的或有限任期的职业。但目前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在多个高等教育系统中,教学型教师的兼职比例正与日俱增并带来严重后果。如南美部分国家兼职教师比例达到了80%,并滋生了“出租车教师”(taxi faculty)的称谓——兼职教师只负责授课,到了上课时间才乘坐的士来到学校。美国30%的教学工作由兼职教师承担,尤其是公立两年制学院,在过去的大约20年内,为了应对已经远远超过政府增加资助意愿的学生需求的增长,公立两年制学院已经变得严重依赖低报酬的兼职教师。可以认为,教学型教师外围化和教学科研互动关系破裂,导致大量兼职型教师出现。(31)其次是教师向学术职业外行业流失。那些与产业关系过于紧密的教师容易流失到学术职业外,他们被称为“学术创业家”,在与产业界合作的过程中大量迁移到企业里,有时与大学完全脱离,有时则以兼职或“双肩挑”的形式出现。比如生物技术领域的相关学科,教师们往往“跳槽”到生物公司,“据说哈佛大学已经取消了禁止生物技术研究商业化的决定,担心这么做会造成最好的医学及相关的教学科研人员流失至生物技术公司。”(32) 二是造成学术职业的主体性缺失。中世纪大学的历史中,先有教师,后有大学。美国高教历史上也曾有过著名的观点,“教师就是哥伦比亚大学”。但教学与科研的分离,正使教师的主体性地位大为降低。教师不忠诚于大学,甚至也不忠诚于学科,而是忠诚于资助者——为他们提供项目的政府部门或者产业界。因教学科研的分离,他们跳出了对工资和福利的关注,他们成了大学的房客而不是主人,经常因为新的诱惑带着项目出走。正如罗切斯特大学校长艾伦·沃利斯所说的,“大学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旅店’。政府部门成了新的母校。研究型企业家成了欢快的精神分裂者。”(33)过度强调研究的应用性和商业价值,也使大学教师精力分散,难以安心从事本学科研究,“在中国的一些大学,教师们被期待出去提供咨询或做其他工作,这是他们学术职责的一部分”。(34)而且很大程度上,教师的这种分化正对学术共同体产出危害,虽然竞争是学术界的动力,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卓越和产出杰出成果,但是“它也会逐渐破坏学术共同体的氛围、使命和传统的价值观”。(35) 除此之外,教学与科研的分野还导致了其他问题的发生,比如在追逐学术资本主义的过程中,科学家与合作方的利益冲突,对于项目和资助的追逐削减了教师基于好奇心而开展研究的自由。 二战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教师流动在加剧,并从结构性迁徙转向制度性迁徙。依据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一些世界性和地区性的学术中心陆续出现,学术系统的中心与外围划分日渐清晰,外围学术系统中的教师正与中心学术系统保持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流动也日渐频繁。 大学教师流动的趋势正与全球化与国际化保持更为密切的联系,并表现出新的特征。当前,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学术能力的欠缺使他们的流动更多局限在本国学术职业中,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学术人才流失仍以学生流动为主(即准教师)。更多的是发达国家的教师活跃在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这一市场正像商品市场一样,正在形成全球性的定价体系,可以预见,不同地区和国家间教师的价格差将会促成更大规模的世界性的大学教师流动。与此同时,大学教师流动的趋势正在对一些传统的教育观念提出挑战,比如学术劳动力市场对教师的评价更多侧重于教师的科研水平而非教学能力,获得高质量教师的谈判正在以承诺降低教学任务为筹码,这与传统的教学科研结合的基本观念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①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M].蓝劲松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3. ②阿特巴赫.变革中的学术职业:比较的视角[M].别敦荣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32. ③阿特巴赫.高等教育变革的国际趋势[M].别敦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8. ④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3. ⑤阿特巴赫等.全球高等教育趋势:追踪学术革命轨迹[M].姜有国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30. ⑥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麻省理工学院与研究型大学的作用[M].蓝劲松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2. ⑦同上,113. ⑧阿特巴赫.高等教育变革的国际趋势[M].别敦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9-30. ⑨阿特巴赫等.全球高等教育趋势:追踪学术革命轨迹[M].姜有国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18. (11)同上. (12)阿特巴赫.高等教育变革的国际趋势[M].别敦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9. (13)Huntley G.Manhertz,Jr."Assessing Contingencies Associated with Mobility,and Earnings among Tenured Faculty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cademic Labor Market," Doctoral of Philosophy in the School of Education Indiana University,2012. (14)Howard Bowen,Academic Compensation:Are Faculty and Staff in America Higher Education Adequately Paid?(Teacher Insurance and Annuity Association.1979). (15)Allen M.Cartter,Ph.D's and the Academic Labor Market(New York:McGraw Hill Book Company,1976). (16)Howard Bowen,Academic Compensation:Are Faculty and Staff in America Higher Education Adequately Paid? (Teacher Insurance and Annuity Association.1979). (17)Theodore Caplow & Reece J.McGee,The Academic Marketplace(New York:Basic,1999). (18)C.E.Ladd and S.M.Lipset,Professors,Unions,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73). (19)Allen M.Cartter,Ph.D's and the Academic Labor Market(New York:McGraw Hill Book Company,1976). (20)C.E.Ladd and S.M.Lipset,Professors,Unions,an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Washington,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73). (21)Ronald Ehrenberg,Hirschel Kasper and Daniel Rees,"Faculty Turnover at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nalysis of AAUP Data,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3239.1990. (22)阿特巴赫等.全球高等教育趋势:追踪学术革命轨迹[M].姜有国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24. (23)阿特巴赫.高等教育变革的国际趋势[M].别敦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9. (24)阿特巴赫等.全球高等教育趋势:追踪学术革命轨迹[M].姜有国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21. (25)同上. (26)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4. (27)维斯特.一流大学卓越校长[M].蓝劲松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6. (28)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政策、政治和创业型大学[M].梁骁,黎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3-64. (29)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52. (30)阿特巴赫等.全球高等教育趋势:追踪学术革命轨迹[M].姜有国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17. (31)菲利普·阿特巴赫.大学的关键永远是教师[EB/OL].中国教育新闻网,http://www.jyb.cn/world/hwsj/200904/t20090428_268020.html,2009-04-28. (32)希拉·斯劳特,拉里·莱斯利.学术资本主义:政策、政治和创业型大学[M].梁骁,黎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16. (33)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5. (34)阿特巴赫等.全球高等教育趋势:追踪学术革命轨迹[M].姜有国等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80. (35)同上,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