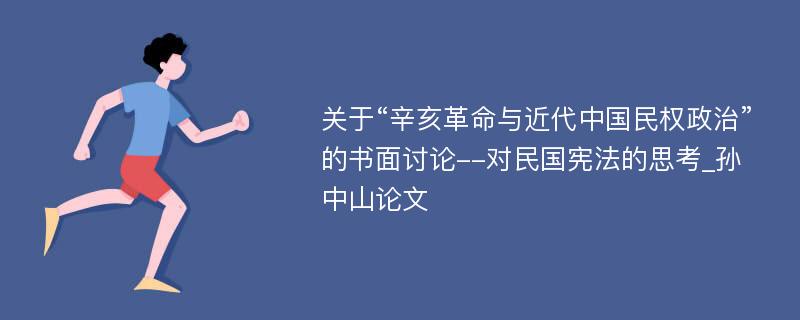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民权政治”笔谈——民国制宪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笔谈论文,民权论文,民国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末法制改革至今已历一百余年,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很多部门法已经在中国获得勃勃生机,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规范。然而宪法的移植在中国出现了排异反应,难以生根发芽。回顾民国制宪史,宪法的制定和实施遇到了强人政治、暴力政治和独裁政治的阻碍。
宪政不需要强人政治
自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至194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先后出台了八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这八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大都与政治强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较为明显的因人立法的痕迹。
武昌首义后,各省代表齐聚武昌,于1911年11月30日召开“组织临时政府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南北议和”的协定是如果袁世凯能劝清帝退位,则孙退袁继,袁任大总统。“《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取总统制,不设内阁总理,由总统直接总揽政权;《临时约法》则采取内阁制,总统为虚位元首,一切权力在于内阁。”改总统制为内阁制,是《临时约法》的最大特征。其目的是“为防止袁氏专横,乃设立内阁制之政府,以资抑制”。如此一来,《临时约法》因人立法,明显针对袁世凯个人。1913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史称“天坛宪草”),也承继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仍采取责任内阁制,并规定了国会对总统牵制权。可以说,“天坛宪草”也有限制袁世凯的目的,因人立法的倾向比较明显。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废弃“天坛宪草”,炮制“袁记约法”,都是其为自己量身定做、因人立法的重要措施。在袁世凯的操纵下,《中华民国约法》于1914年5月正式公布施行。“袁记约法”是对《临时约法》的反动,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权力至高无上。“袁记约法”完全是按照袁世凯的实际权力和独裁欲望而制定,为袁氏复辟帝制铺平了道路。
宪政是常人政治而非强人政治。强人政治带有浓厚的卡理斯玛(charisma)色彩,这种统治在本质上特别不稳定,无法长久维持。宪法首要在于约束政府权力,宪政不把国家治兴的愿望寄托在少数强人或伟人身上,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在“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同时,也将强人和强人政治纳入法律的轨道,让常人成为政治的参与者,让政治权力和公民权利可以在公开、有序、可预期、可持续的常态中运行。因人立法现象凸显了政治强人对立宪的破坏作用。无论是对政治强人的限制还是顺从,因人立法都偏离了宪政的轨迹。建设常人政治而非强人政治,应当是民国立宪乃至20世纪历史给后人最大的启示之一。
宪法与和平政治互为保障
武力政治是民国政治的一大特色。民国时期的八部宪法或宪法性文件,无一不被暴力政治所挟制,有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本身就是军阀纷争、武人干政的产物。其中,袁世凯解散国会和段祺瑞制定“段记约法”乃其适例。袁氏为摆脱《临时约法》的约束,采取各种措施反对《临时约法》,抵制“天坛宪草”,最终竟至宣布国民党非法、捕杀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然后在其武装护卫之下,制定了“袁记约法”。可以说,无论是被废弃的《临时约法》、“天坛宪草”,还是“袁记约法”,都是刺刀下的宪法,其制定或废止,都取决于武装暴力。
段祺瑞两次制宪的失利也印证了暴力政治对宪法的破坏。1918年段操纵的安福国会制定新的宪法草案。1920年,段祺瑞在直皖战争中失败,此次“段记宪草”亦随之消亡。1925年,临时执政段祺瑞宣布召开国民代表会议,制定宪法。同年12月《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起草完毕,国民会议尚未审议,段祺瑞被张作霖胁迫,北京政权易手。段祺瑞两次制定宪法草案,背景都是制宪之前他在武装斗争中获得胜利;两次宪草半途而废,都是因其在军阀斗争中失利。
军阀政治的本质是暴力,暴力的强弱决定了政治地位的高低。军阀武装割据,就是在特定区域内,某个军阀掌握了可以控制这个区域的暴力武装。“军阀统治的实质是实力之下的武治,它比寻常的封建统治带有更多的动乱性和黑暗性。”宪法被暴力裹挟,暴力成为公理、成为权力、成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暴力迷信恐怖而耻笑道德,权力与暴力互为表里,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争夺权力而不择手段,宪法垂之于枪口。暴力意味着更大的破坏,暴力政治不但招致连年兵燹,而且扼杀了新生的宪政力量和宪政建设。
宪法保障的是和平政治,反对暴力政治。宪法要排斥武力,捍卫和平,将国家武装力量限定在法治的范畴,让一国公民处于和平环境中,公民的权利得到和平、稳定、有效的保障。武装力量属于国家而非地方或者个人,应当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而不是用枪杆子绑架宪法。民国时期军阀干政、操纵宪法的历史告诉我们:暴力下无宪法,枪口下的宪法是暴政。
“通过独裁实现共和”的迷思
民国初年对于采取何种政体,颇有争论。君主立宪制、总统制、内阁制等,众说纷纭。但政体之争有其基本共识:反对独裁,反对帝制,建立共和。建立共和已成为世之潮流,醉心专权的袁世凯、段祺瑞也不得不打出拥戴共和的旗帜。值得注意的是:先反清廷专制,后反袁氏专权的孙中山,后来亦转向独裁;其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程序理论,体现了民国时期通过独裁实现共和的治国思路。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反思屡败屡战之革命历程,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自己没有成为握有重兵、地盘和绝对权威的领袖。他批评革命党内部涣散不统一,党魁缺乏绝对权威,认为自己身为党魁而形同傀儡,在南京临时政府时,名为总统,手无实权。因此,他决心成为拥有政治实权和绝对权威的“真党魁”,遂组建中华国民党。孙中山明确要求将服从自己一人作为入党的先决条件,建立个人独裁已然十分明显。
俄国十月革命对孙中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晚年建党思想与举措多效法俄国。他多次表示对俄共的赞美,认为要想革命成功,就要学俄共的方法、组织及训练。为建立俄式革命政党,孙中山以俄为师,进一步提出了“以党治国”的思想,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再至改组国民党,在其晚年的十多年中,他都坚持要用专制的手段来完成革命大业。对此,孙中山公开阐明自己要采取独裁手段,把俄国的以党建国作为自己建党的模范。
孙中山屡经失败之后,认为欲求革命成功,就要全力树立个人权威、组建专制政党、谋求党魁独裁、培植军事力量。从各个方面来看,他都致力于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新的拥有主义、地盘和军队的实力派(或曰军阀)。其晚年更是殚精竭虑组建一个超越国家的政党,而他就要做凌驾于这个政党之上的最高精神领袖和权力领袖。在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建国程序理论,被写进《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成为国民党的立党建国的指导思想。从此,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得以确立。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以尊奉和实现总理遗教为名,1927年创立了一个党权高于政权的意识形态政体。这个反民主宪政的党权之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党专政、党高于国、党大于法的独裁统治,宣告了辛亥以来追求的宪政共和、三权分立彻底终结。
在与清廷和袁世凯斗争的二十余年中,孙中山高举反对专制、建立共和的旗帜,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然而,在其追求共和、反对专制的斗争中,得出的教训是要用独裁实现共和,以专制达致民主。这种通过专制实现自由的悖论,却完整地体现在孙中山及其继任者身上。
孙中山游历欧美,眼界开阔,效法美式宪制,维护《临时约法》,最后竟与出身旧式官僚体系的袁世凯等人殊途同归,走向独裁,就深足我们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孙中山晚年逐渐背离了其在辛亥时期坚持的《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这究竟是孙中山迫于现实而做出的最不坏的选择,还是制定约法与护法运动等事件的目的是争夺政治权力而非实现宪政共和?历史没有给孙中山更多的时间去实践,却给了后人更多的空间去思考。历史人物产生并受制于特定历史环境,后人不能苛求孙中山。毕竟他理论中军政的目的是宪政,这种通过独裁实现共和的学说,在当时及以后也被普遍认可,至今遗风犹存。
尊重历史,还原真相,不溢美、不隐恶,应当是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历史,也不能武断地将历史功过归之于某个人。如果我们跳出袁世凯、孙中山及大小军阀是非功过的评判而省察更深邃的历史之实,就会发现他们因约法之争、政体之辨、帝制共和之分等而产生的政争,都是近代中国历史转型的一个环节,都是转型中新制初创、法律移植的尝试与实践。总之,历史人物都是其所在的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虽离不开特定历史条件之作用,而历史文化的型塑作用更具有根本性。法律移植亦须与其受体的文化土壤相适应,宪法移植频频失利的症结不在于一个或多个专制者迷信权力、排斥宪政,而在于中央集权的土壤难以为西来的宪政共和之苗提供养分。宪法的核心是限制公权、保障民权,要求实行横向与纵向的分权,这却与中央集权体制势同水火。由是观之,实现从强人政治到常人政治、从暴力政治到和平政治、从独裁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型,正是对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制度解构,是宪政共和的基本目标。
清末以降,救亡与启蒙的变奏,民主后进与国民改造的焦虑,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的催化,都在缓慢而有序地促进着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一直处在“自由先期”(pre-freedom period)的中国,将迟缓滞后但不可逆转地完成从帝制到民治的转型。
标签:孙中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民国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袁世凯论文; 段祺瑞论文; 宪政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北洋政府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