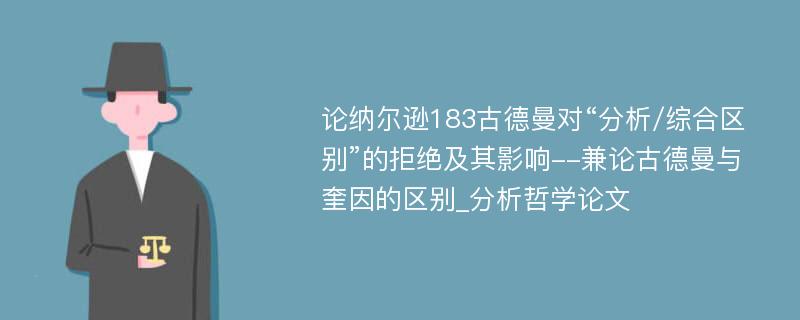
论纳尔逊#183;古德曼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拒斥及其效应——兼谈古德曼与蒯因的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德曼论文,纳尔论文,效应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10)06-0001-05
众所周知,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即:真值完全依赖于意义的真理与真值既依赖于意义又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之间的区分,构成了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支撑。从休谟关于观念间的关系与事实之间的区分和莱布尼茨关于理性真理与事实真理之间的区分,到康德关于分析真理和综合真理之间的区分,分析/综合区分,实现了其作为现代西方哲学教条性基础预设地位的确立。实质上,它以对一个再现与实在之间的关系概念的承许,支配着我们的认识过程以及我们对认识本身的认识,进而支配了我们的整个认识论。而在分析哲学中,这个区分则以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区分这种表现形式强化了其基础地位,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这个分析哲学的基本预设却遭到了以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W·V·蒯因(W.V.Quine)和M·怀特(Morton White),为代表的来自分析哲学内部的激烈批判,作为主力,古德曼通过一条独特的外延式意义分析路径完成了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批判和拒斥,肇始了分析哲学向后分析哲学的转向,并最终通过用“解释”替代“分析”概念实现了认识论的重构,从而催生了整个当代美国哲学的话语转换。
1
作为分析哲学基本预设的分析/综合区分之所以遭到了来自分析哲学内部的激烈批判,直接诱因就是它导致的分析悖论及其解决困境。事实上,早在1942年,郎福德(C.H.Langford)就在他的论文“摩尔哲学中的分析概念”中,针对G·E·摩尔的分析概念提出了这样一个分析悖论,即:“如果表现了被分析项的语言表达与那个表现了分析项的语言表达拥有相同的意义,那么,这个分析就述说了一种空洞的同一,并且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如果这两个语言表达并不拥有相同的意义,那么,这个分析就是错误的”[1]。这个适合于真实分析的指称分析悖论同样也适用于意义分析,譬如:
(D1)“单身汉”与“未婚男人”是同义的。
(D2)“单身汉”与“单身汉”是同义的。
(D2)显然是一个空洞的重复,它不增进任何知识,因此是无意义的。若(D1)与(D2)同义,那么它也是无意义的,因为与一个无意义的陈述同义的陈述自身也是无意义的,这就是朗福德悖论的第一个两难。而(D1)要避免这个结果,就必须保证它与(D2)不同义。根据意义分析的意义构成原则:一个复杂表达式的意义是它包含的表达式与它们的句法组合方式的一个函项,在(D1)和(D2)句法完全一样的条件下,如果要保证两者不同义,就只能是它们所包含的表达式“未婚男人”和“单身汉”在意义上有差别。但一个意义分析为真的条件却要求:述说了被分析项的语词“单身汉”与述说了分析项的语词“未婚男人”是同义的。因此,如果为了避免第一个两难而要求两者不同义,就会直接把这个意义分析引向第二个两难:它是错误的。这就是朗福德分析悖论:分析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就是错误的。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悖论或者如何避免这个两难呢?首先,要保证上述意义分析正确,就必须让“未婚男人”和“单身汉”同义,即“同义1”;其次要保证这个意义分析不是无意义的,就必须保证(D1)和(D2)之间的“同义”(即“同义2”)不能导致无意义。从上述例子中不难看出,导致无意义的恰恰就是“同义2”,正是因为我们把“同义1”和“同义2”理解为同义的,才导致了悖论。显然,“同义1”是这个意义分析正确性的充要条件,而“同义2”则是这两个陈述都是无意义的充分条件。因此要解决悖论,就必须保证“同义1”和“同义2”不同义,这样就可以在不违背“同义1”的前提下,避免“同义2”所带来的无意义结果。因为通过句法并不能让“同义1”不同于“同义2”,所以就只能通过假定一些抽象的对象,譬如弗雷格式的“内涵”,即:为“同义1”和“同义2”设定不同的内涵,以满足避免悖论性结果所需要的差别。事实上,这也正是A·丘奇(Alonzo Church)随后提出的解决朗福德悖论方案所采用的方法。
显然,丘奇—弗雷格式解决方案引入了自身难以说明的新的假定抽象对象,而对于具有唯名论倾向的古德曼和蒯因来说,这种做法是绝对不能接受的。1947年5月,古德曼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怀特写信给蒯因,表达了对它的不满,并随后把蒯因的回复意见转送给了古德曼,三人以通信的方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结论在1950年怀特的论文“分析与综合:一种无根的二元论”中得到了呈现:任何分析与综合的严格区分都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会最终被抛弃。蒯因则在美国哲学协会的一次演讲中表达了他的观点,最后归于1951年他在《哲学评论》上发表的著名论文《经验论的两个教条》。而古德曼的唯名论倾向则更为强烈和彻底,因此他对这种做法的不满也更为强烈,他认为,不仅迄今为止对“同义”和“分析”所作的任何解释都值得怀疑,而且更有甚者,他连这些术语在理论化之前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他在给怀特和蒯因的一封信中写道:“当我说我没有理解‘分析’的意义时,我是非常认真的。我的意思是,我甚至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语词。……如果给我任何一个谓词,通常我能告诉你它是否是可投射的,我在外延上理解这个谓词。但是,‘分析’,我甚至连这也不能理解,……我甚至没有任何一个清楚的标准,……当我不知道我正在定义的是什么时,我无法找到一个定义”[2]。在1949年发表在《分析》上的论文“论意义的相似性”中,他通过一种纯粹外延的意义分析路径,得出了“在一种语言里,没有任何两个不同的表达是同义的”这个结论,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拒斥。
2
在“论意义的相似性”这篇论文中,古德曼首先列举并考察了意义内涵理论关于“同义”的四种回答,最后发现,无论哪一种回答都不能令人满意。第一种回答是:两个语词或表达拥有相同的内涵,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相同的本质或者某个柏拉图式的理念。但是,这种回答却因为除非我们还拥有某些更加实际的工具否则就根本不知道如何断定一个语词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柏拉图式理念而陷入了认识上的困境。第二个提议是沿着第一种回答的基本路径进行的,即:相同内涵的两个语词代表了相同的心理理念或映像。古德曼认为,虽然这种回答用心理学取代了柏拉图从而增加了某种实践性,但我们仍然不能确定我们究竟能和不能想象什么;甚至很多语词(譬如“聪明的”和“超声波”)似乎并没有与它们相对应的心理映像。这同时也会把我们带到第三种更加自由的回答:两个语词拥有相同的内涵,当且仅当我们不能构想出只符合其中一个而不符合另一个语词的某种东西。这使得我们超越了想象的狭窄边界,但却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标准。实际上,我们可以构想任何美好的东西,因为我们根本不清楚我们谈论的是实际上符合一个而不符合另一个语词的东西,还是可能符合其中一个而不符合另一个语词的东西。若是前者,就会因为纯粹外延性的事实而排除可能性;若是后者,则会陷入可能性的循环。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即第四种回答:通过融贯性来判定。因为如果“是一个P或者是Q但却不同时是两者”,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谓词可以是融贯的。但是,如果没有假定抽象的意义,而P和Q又是两个不同谓词的话,这种融贯就是不可能的。如果为了融贯性而假定了抽象的意义,我们又怎样知道这些假定的意义呢?如前所述,因为这种“内涵”假定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我们又在循环的迷茫中回到了问题的原点,事实上,这正是古德曼反对分析悖论的丘奇—弗雷格式方案的原因所在[3]。因此,古德曼认为,如果没有实际的工具,内涵理论根本没有可能解决分析悖论,也不可能合理地解释“同义”和“分析”这些概念。
既然意义的内涵理论无法合理解释“同义”,于是古德曼就把视线转向了外延,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归纳、合取或其他手段确定两个谓词相同的外延,而无需确然知道它们所适合的东西”[4],并给出了“同义性”的外延标准:两个语词拥有相同的意义,当且仅当它们拥有相同的外延。但与蒯因不同的是,古德曼并没有直接指向“同义”,而是首先从如何解释意义的不同开始的[5]。显然,外延不同的语词意义当然不同,但很多外延相同的语词,意义也不相同。譬如,“独角兽”与“半人半马怪物”,它们的外延因为都是空的而相同,但它们的意义却显然不同。那么,怎样解释这种意义的不同呢?古德曼并没有像一般的解释者那样引入言外寓意或指称标准,而是求助于外延的多样性。他发现,语词不仅单独出现,而且还作为复合体的部分出现。譬如,“独角兽图”中包含“独角兽”,“半人半马怪物图”是“半人半马怪物”的复合语词。因此,一个语词的意义不仅依赖于这个语词的单独所指——第一外延(primary extension),而且还依赖于包含着这个语词的那个复合语词的所指——第二外延(secondary extension)。基于此,古德曼对“同义”标准做了如下说明:“如果我们把一个谓词自身的外延叫做它的第一外延,并且把其复合句的外延叫做第二外延,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两个语词拥有相同的意义,当且仅当它们拥有相同的第一外延和相同的第二外延”[6]。据此,古德曼对“独角兽”和“半人半马怪物”的意义不同作出了解释,即:虽然这两个语词的第一外延(空外延)是相同的,但是它们的第二外延“独角兽图”和“半人半马怪物图”的外延则不同,因此,“独角兽”和“半人半马怪物”这两个语词的意义也是不同的。其实,按照古德曼的路径,对于任何两个我们认为是同义的语词来说,都至少有一对不同外延的平行复合词,并因此拥有不同的外延。譬如“医生”和“医师”,我们总能设想出这样的复合语词:“不是医师的医生”和“不是医生的医师”,第一个复合词显然是一个“医生—描述”,而后者则是“医师—描述”。事实上,对于任何两个语词p和q来说,我们总能在使用“不是一个q的p”这个公式,并发现意义上的不同。于是,古德曼的同义性标准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在一种语言中,没有任何两个语词的外延是相同的,因此,没有任何两个语词的意义是相同的。如果没有语词是同义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可以理解的“同义性”,而以这个“同义性”为根据的“分析”也就丧失了其合法性和可理解性。于是,也就不存在任何命题是分析的,不存在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
至此,我们清晰地看到,古德曼通过一条独特的纯粹外延路径,从对“不同义”的解释出发,揭示了“同义”、“分析”和“分析/综合区分”的无根性,进而完成了对这个分析哲学基本预设的消解和拒斥。尽管有人会对古德曼的这条分析路径及其同义性标准的苛刻和严格提出质疑,尽管古德曼没有对此作出太多的说明,而只是以反对者不能证明外延标准的不合法为基础得出结论说“很多表面上的反驳对我而言是站不住脚的”[7],但无论如何,古德曼都已经客观地证明了严格“同义”和“分析”的不可能,至少是在一个语言整体中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同义词”,因而也不存在一个由分析/综合区分所支持的固定结构。事实上,从古德曼的整体哲学图景来看,这条外延路径的选择是基于贯穿其哲学始终的唯名论倾向的,这也正是古德曼和蒯因对解决分析悖论的内涵理论方案不满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古德曼更为明显和激烈的唯名论立场则直接源发于他与蒯因的拒斥路径差异,即;纯粹外延的意义分析路径和“不同义”的分析出发点。
3
然而,古德曼没有止于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消极批判。与蒯因不同,他并没有自始至终关注这个批判并“视之为自己全部理智生命的中心任务”[8],也没有像那些为这个区分的被拒斥所带来的毁灭性哲学后果而惊慌失措的人们那样堕入虚无,而是直接转向了对“分析”之后哲学的重构实践。就古德曼的哲学语境而言,首当其冲的便是对“分析”之后的哲学理念和方法的改造和重构。那么,“分析”之后,哲学实现其目标和任务的方法又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严格同义性基础上的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并没有完全否定我们进行另一种意义上的分析的可能性,只不过这种分析把严格同义性的要求转换成了意义相似性要求。正如怀特在与蒯因和古德曼的讨论结果中公布的那样:“我并不是在论证,一个分析性和统一性标准永远不可能被给出。我论证的是,还没有一个标准被给出,更准确地说,一个合适的标准似乎是把这个区分变成了一个程度问题”[9]。古德曼认为,虽然“一个不是p的q”这个普遍适用的公式会因为总能找到外延的区别而导致不存在任何两个同义语词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设想这个“不是p的q”过程中,却存在着难易程度上的差别。譬如,就“医生”和“医师”而言,设想一个“不是医师的医生”,总会比设想一个“不是半人半马怪物的独角兽”更困难一些。而这个设想难度的差别恰恰反映了语词之间意义相似性的程度,即:“医生”与“医师”的相似性,高于“独角兽”和“半人半马怪物”的意义相似性。虽然复合语词不可能在所有情况下都拥有相同的外延,但是,如果我们把它限制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就完全有可能实现一定条件下的外延等同,也就是说,在某种限制条件下,它们可以在由第一外延决定的基本意义相同的基础上相互替换,也因此可以在这个条件下的语句中相互替换。譬如,“脊椎”和“脊骨”,它们的第一外延相同,基本意义也相同,如果在医学话语体系中所有的“脊椎—描述”与“脊骨—描述”都是外延相同的话,那么,在医学话语中,“脊骨”和“脊椎”的意义就足够相似以至于它们可以在这种语境中相互替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目的和需要,用一个基于实用主义的灵活语境敏感性的意义相似性标准取代一个严格的语境中立的同义性标准而进行“分析”,但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绝对同义性的“分析”[10]。显然,古德曼并没有因为分析性在绝对意义上的不可能而最终抛弃分析,从而像蒯因在《论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结尾表明的那样直接“转向实用主义”[11],而是借助实用主义的语境标准找到了某种相对意义上的“分析”,进而在继承分析哲学基本理念意义上的“分析”模式的基础上对之进行了改造和重构。
他把这种意义上的“分析”称为“解释”,即:对有问题的或者说模糊不清的语词的重新概念化,就是用清楚的语词给出一个合适的定义。古德曼通过对定义种类的描述对之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定义有两种:“名义定义”、“真实定义”,前者的意义是被规定的,既不能为真也不能为假;而“真实定义”,则分为“意义分析”和“经验分析”,如果这个真实定义是关于语言表达式的,只谈论了这种语言中的一个表达式的意义,则称之为“意义分析”,如果它谈论的是作为一种实体的意义,就是“经验分析”,而“解释”就是名义定义和“意义分析”的杂和。它因为为了澄清某些问题作为一个语词被引入一种语言而具有了名义定义的规定性,同时,又因为要对被解释词进行解释而进入了意义分析的过程,因此,一个解释的充分性,并不是完全取决于解释词与被解释词的意义相同,因为它还受作为名义定义的某种规定性的限制。所以它的标准是:正确性、富有成效性和简单性。正确性保证了解释词被引入了一个精心构思和选择的讨论系统或者一个科学的语境,而富有成效性和简单性则保证了,这个概念在这个话语系统中可以很好地履行澄清和解释功能。因此,一个解释并不要求解释词与被解释词具有完全相同的外延和意义,而就一个解释系统而言,甚至只要求保持一种外延的同构性,正如他说的那样:“更一般地讲,一个系统中的所有定义词的系列必须在外延上同构于所有被定义词的系列”[12]。事实上,解释通过规定性而削弱了同义性要求的严格和绝对,同时又通过意义相似性的要求,限制了规定性的武断和随意。
至此,古德曼在通过一个外延式同义性标准否定了传统“分析”的可能性之后,用一条基于实用主义的灵活的语境敏感性标准取代了语境中立的同义性标准,从而实现了分析哲学澄清问题的基本方法从同义性“分析”向非同义性“解释”的转换。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模式转换的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出了自身,而从根本上导致了哲学的任务执行模式和目标的彻底改变和重构。
4
显然,分析/综合区分的基本预设,把命题划分成了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也因此把一个认识真理的获得过程分割成了一个纯粹的意义分析过程和一个纯粹的确定概念意义的经验分析过程,前者被划归为哲学的任务,而后者则被划归为科学的任务。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古德曼通过一条外延式意义分析路径论证了“同义性”和“分析”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纯粹意义分析过程的不可能;而且,以灵活的语境敏感性意义相似标准为基础的“解释”过程还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意义生成方向:不是一个语词的意义限制了它的外延和使用,而是一个语词的外延和使用造就了这个语词的意义,也就是说,甚至连一个语词的绝对的固定意义都难以获得,因此,这个为概念分析提供确定意义前提的经验分析也成为了不可能。不难看出,这种“解释”通过呈现出意义与外延以及使用的互动关系,把被截然分开的概念分析和经验分析结合了起来,从而消除了概念承诺与事实承诺之间的分割。如果说分析/综合的区分,承诺了一个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和实在之间的关系并支配了我们的认识论的话,那么,古德曼作为取代“分析”的“解释”已经动摇了这种关系,也因此而否定了绝对知识——作为概念和实在之间的认识关系的结果——的可能性。事实上,在分析/综合区分框架下被截然分割开的经验分析和概念分析,其实是同一个开放的创造性的“解释”过程,它的目标不是获得被截然分开的事实真理和意义真理,不是获得关于实在的绝对知识,而是通过主动地重新分类和解释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和理解的逐步推进。
于是,古德曼认为,“灾难就是那种被普遍认同的哲学——被视为哲学核心概念和问题的那些东西——又一次被证明是错误的。失败和模糊充斥着真理、确定性和知识这些概念。这要求我们对此作出某些修正、替代或补充,对概念上的工具进行检查,对哲学进行重释”[13],并建议用“正确性”、“采用”取代“真理”、“确定性”,并最终把认识论从狭隘的知识目标设定中解放出来,而代之以“不是一个确定最终的认识论成就的仓库,而是一个进一步探究的出发点”[14]的更广泛的“理解”。至此,古德曼在对分析/综合区分拒斥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从“知识”到“理解”的认识论重构和转换,而以分析/综合区分为基对哲学和科学任务的划归和分割也随之消匿。事实上,在古德曼的整体哲学语境中,哲学、科学、艺术被作为构造世界的方式纳入了统一的构造世界的实践进程,并因为在这个进程中推进了我们的理解而被承许为“理解”认识论的分支[15]。在这个意义上,古德曼对分析/综合区分的拒斥,不仅重构了认识论,也重构了哲学、科学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在完成了哲学目标从知识向通过解释实现的推进理解的转换的意义上重构了哲学。
若果说分析/综合区分构成了分析哲学的基本预设的话,那么,古德曼借助于外延式意义分析路径对之的拒斥以及“分析”到“解释”的转换,就在批判和改造的基础上推进了分析哲学向后分析哲学的转向,而在语境敏感性意义相似标准中对“实用主义”因素的引入,则在“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张力中推进了实用主义向“新实用主义”的转向;如果把从“知识”到“理解”的认识论重构置入一个更为广泛的哲学语境的话,那么,这种认识论及其背后的本体论言说,就会因为“构造世界”意义上的实践统一而直接促成基础主义、二元分立模式的崩溃,并因此而导致整个哲学问题结构及其言说方式的改变,就以“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美国哲学而言,则直接肇始并促成了当代美国哲学的话语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正如C·Z·埃尔金说的那样:“他(古德曼)的工作改变了二十世纪哲学的轮廓”[16],而这也正是古德曼对分析/综合区分拒斥的深层效应所在。
收稿日期:2010-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