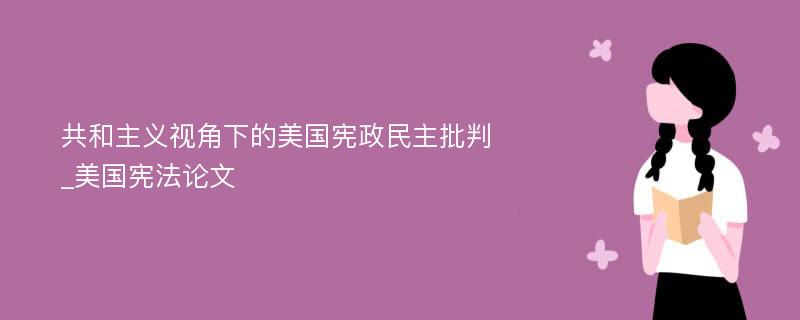
共和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宪法民主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和论文,美国论文,宪法论文,视角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论
政治哲学与法哲学是决定政法政策与制度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基。同一套价值理念在不同的政法哲学下往往会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多元、复杂的,这就要求我们对不同的政法哲学进行充分的研讨,以探求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最优的价值序列及其排序。但长期以来,人们的视线仅注视在美国宪法式的民主及其背后的自由主义上,美国宪法式的民主成为“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唯一标尺与“历史终结”①的完结点。自由民主的视野被无限放大,成为包罗万象的巨无霸。无论保守主义、经验主义、普通法理论、霍布斯主义,甚至共和主义统统被其收编旗下。法治主义、宪政主义本身则被视为必然是自由主义的,这种看待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忽视了它们对自由主义的内在规制。民主主义在自由主义大一统背景下与自由主义相互融合起来,民主的必然是自由的,自由的应该是民主的,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是通往自由的必然之路,成为大众的“常识”。自由主义或者民主,对很多学者来说是同一概念。如福山认为自由主义或者民主这两个概念是同意反复,沃特金斯将伯里克利的民主时代视为自由主义的真正起源②。对于其他的政法哲学如社群主义、共和主义却长期被人们忽视,甚至仅有的一点关注也被视为异端③。这些学者们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社会资本具有浓郁的压抑性,当前人们迫切需要的是主张个体自由的民主权利、对政府权力严格控制的美国式民主宪政。笔者认为,这些学者忽视了中国特殊的社会资本传统与政治经济形态,这些因素决定了在现阶段是无法与他们心目中的美国宪法式民主承接的。他们忽视了美国宪法民主生发的基本社会政治传统,忽视了美国宪法民主背后的经济心理背景。学者们的立场是宪政主义的,但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却是非宪政主义的。甚而言之,他们对美国宪法基本原则的理解也是很成问题的,许多学者所了解的民主美国是“意识形态化了的美国”。事实上,美国宪法的原旨是共和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或者民主政治④。自由主义或者民主政治是美国制宪者所批评的对象,在美国宪法上并不具有合法性。
人们对美国宪法式的民主及其背后自由主义的偏好很大程度上在于人们的错觉,在于人们对现今“自由民主”这一概念自以为是的美国式解释。“根据这一解释,自由民主主义者更像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是一个喜爱受到管制的经济人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人,喜欢运用福利措施去缓解贫穷和困苦的人,更为普遍的是这一术语也与仁慈和同情的态度相连。但是,从历史上来看,自由主义经常与针对穷人的冷酷无情的态度和政策联系在一起。”⑤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美国宪法民主”,探究美国宪法民主的真相。
一、共和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宪法民主批判
在西方政治理论领域,对于自由主义或者民主政治的批评由来已久,并在不断深化。在现代数量政治学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帝国天下,人们通过精确的数理分析和逻辑推理来检验民主,校验自由主义的自由,却得出了“民主的不可能”定理⑥与“自由主义的悖论”。在政治理论上,对自由主义或者民主政治的批评,既包括社群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批评,也包括自由民主阵营本身的反省,甚至女权主义也抛弃与自由主义传统的联合而投入共和主义的怀抱[1]。共和主义作为一种虽然不是十分完美但更加现实可行的政制方案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同。
纯正自由民主话语下的研究者,必然以政治层面上的自由和民主为人们的内在根本属性和根本需求,这忽视了经济层面的私利保障与社会层面的公正制度供给对民众的巨大效用。一般认为,自由主义或者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政治腐败、社会不平等的消除等不存在正相关关系⑦,反而会导致蛊惑人心的政客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以及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种族主义、文化中心主义、个人主义、地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与世界冲突的加剧等诸多不良后果⑧。共和主义却强调公职的神圣性与执政者的责任与义务,强调培育具有公民美德⑨的民众、强调民众的积极政治参与,强调民众与执政者的协商对话,强调民众的授权与政权的正当性,强调国家的荣光与公民的荣誉,因此共和主义更有可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昌盛,同时又保障拓展公民的政治权利与经济自由。
共和主义这一理想状态的实现在于共和主义内在结构的均衡:首先,共和主义政体的制度结构对外保证国家安全,对内保证国内秩序,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提供制度基础;其次,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协商保障民意的输入与展现,保证政府的自由与廉洁;第三,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伦理观念结构保证执政者与民众各尽其能、各司其职,为共和主义的价值诉求提供正当性辩护。
制宪者明确指出,民主与共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民主是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小社会,共和则是采用代议制的政体共同体⑩。民主制在当时几乎为所有的制宪者所诟病,“民主”(democracy)常和“暴民政治”(mobocracy)通用。爱德蒙·伦道夫在制宪会议上批评,国家遭受灾祸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民主政体带来的混乱和蠢行,最大的危险在于我们宪法中的民主成分。华盛顿也提醒人们不要通过仅仅是讨好人民的文件[2]。人们对民主的这一评价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民主名声的逆转以及伴随之后西方乃至世界政制范式的更改始自边沁与密尔等政治理论家的卓越贡献,也在于后人对麦迪逊式共和政体与民主政制的等同。到了20世纪的1997年,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才盛赞民主制度为人类的普世价值,是崭新的、典范式的20世纪产品。它的出现并被广泛地接纳为政府的组织形式,是20世纪最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3]。王绍光教授也注意到现代所谓的民主是被一次一次的阉割和限制后才被本质上反对民主的资本主义所接受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困境产生于现代民主制本身(11)。
卡罗琳·罗宾斯是第一个对“洛克的自由主义思想主导美国政治思想文化”这一传统定论提出质疑的共和主义思想家。他在代表作《18世纪的共和国》中提出,正是辉格党对权力和腐败的恐惧激发了美国革命,而不是基于权利的自由民主。辉格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富有革命性,自由主义主张对辉格党来说太过激进。戈登·伍德指出,以安德鲁·杰克逊时代为标志的民主政治是建国之父们所力避的,建国之父们确立的政体原则是共和主义而不是民主政治[4]。伍德反对所谓进步主义的历史学家用法国民主革命的模式来解释美国革命的企图。他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告诉世人,共和主义作为18世纪的一种政治上的而非社会上的激进意识形态,是建国者的政治理想。他在《民主与宪法》[5]一文中又指出,现代所谓的“民主美国”在于美国人将代议制与民主的等同。在麦迪逊的设计中,代议制属于共和政体,民主则是人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联邦党人对于民主是坚决反对的,他们制定的宪法是共和主义的。反联邦党人批评宪法的贵族色彩,要求加强宪法的民主性。为了让人民批准宪法,联邦党人使用了各种政治修辞手法,他们用民主的外衣把自己的贵族身份遮盖起来,人民不再质疑美国宪法中的“民主”,而是成为一种所有美国人和美国机构必须坚守的信仰。民主理论的鼓吹者罗伯特·达尔为此指出:美国人依然信仰他们的宪法,宪法的合法性依然如故,这将与他们对民主合法性的信仰长久地处于一种紧张状态[6](51)。
二、共和主义视角下的美国宪法民主再造
共和主义是与混合政体、法治、公共利益、公民美德等原则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政治思想和政体理念,是对自由民主原则的一种节制或限定。共和主义政制在于通过社会不同阶层对国家的共同治理,避免多数或者少数的专断与零和事件的产生,以实现国家荣耀与个人自由幸福。共和主义通过美国宪法完成了一次蝉蜕、一次超越,一次由古典共和主义向现代共和主义的飞跃。美国宪法中的共和主义作为现代共和主义的典范,它所表达的政体思想与政治实践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民主政治重视公民个体对公共生活的绝对话语权力与决策诉求,主张幸福的个人特殊性,怀疑政治精英的公民道德状况及其审慎理性水平,反对公共权力对幸福生活的建构。这为美国宪法制定者所忧虑与不快,他们制定的美国宪法以共和主义为政体框架,试图超越民主政治及自由主义,遏制其对个体权利和个体政治参与的过度要求,主张政府权力尤其是司法权与民众的适当间距,反对政府与公共权力的正当性对于民意情绪的过度依赖,倡导全体公民美德的培育,强调政治精英领导责任、审慎理性下的共和政治观。
以18世纪的标准来看,制宪者们制定的宪法可能是富于启蒙精神的。但是,有着更民主渴望的未来一代会发现宪法的非民主特征是令人生厌的——甚至是不可接受的。民主具有内在自我增长性,不断增长的民主渴望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公开的表达[6](38)。共和主义原则在美国宪法中确立以后达到了繁荣的巅峰。但就是在共和主义的成功之巅,它开始走向了没落。还没有等宪法的制定者退出历史舞台,联邦宪法便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蕴涵于宪法中的共和原则与精神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共和主义受到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势力的挤压,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美利坚共同体面临巨大挑战,国家公共善的存在与设定受到巨大挑战。
1787年制宪会议所制定的崇高根本法仍然是美国的宪法,但它有名无实。宪法的形式是一个经过精心调整的、理想的平衡政体,但现今美国政府的实际结构不过是国会至高无上的一种体制[7]。随着行政首脑的活跃,行政权力又进行了无节制的扩张,而成为替代靠群众会议来治理国家的万能政府。
宪法中的共和主义原则在宪法制定的过程中并没有得到一贯的认同与遵守。这种破坏宪法的动力源自于以杰弗逊、潘恩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派对个体民主与自由的过度要求(12)。共和原则的破坏性力量还源自于反联邦党人对宪法民主性缺陷的不满。民主运动不断扩展,党派政治开始产生,政府的权力日益受到诋毁。美国的民主化运动与自由主义的功利观颠覆了宪法制定者建立一个充满精英美德的强大罗马式共和国的梦想(13)。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使人们对法西斯国家主义深恶痛绝,并因而对任何形式的集体利益和公共善心有余悸,由此更加狂热地拥抱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主义。当代以哈茨(Louis Hartz)为代表的所谓主流学者决然断定:美国的传统就是一以贯之的洛克式自由民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因而美国在传统上没有保守主义,也没有共和主义,如果有,那也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假想敌,或者说这些保守主义和共和主义也是自由主义的(14)。
面对这种颠覆与解构,自由民主政治的强势让它的反对者举步维艰,但是人们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向往之火一直没有熄灭,自由民主主义对政治社会的解构更加激发了人们对深植于美国宪法社会中的传统共和价值的缅怀和向往。它的阶段性高潮表现为1955年开始的共和主义复兴运动。在这一复兴运动中,共和主义学者通过理论慎思,找到了宪法中的共和主义传统,他们希望通过复兴这种共和主义来“拯救美利坚共和国”,保卫美利坚共和国的共和宪法。以新雅典理论、新罗马理论与共和主义宪法理论为内容的当代共和主义就是这股共和主义复兴大潮的理论结晶。
三、余论
宪政主义本身具有保守主义的气质,它在内容上追求人类普适价值的同时,在方式上充分尊重既存的社会制度环境与社会资本传统。中国的宪政建设进程需要充分考虑到本国特殊的文化和政治经济环境,这是由宪政事业内在的属性决定的,也是学者推动政治进步的学术智慧。正如沃格林所言:历史已经证明,对于任何政治社会来说,如果一项知识性的事业会质疑它那宇宙世界对应物的价值观,这个社会就不会支持,哪怕是容忍这项事业的存在。
共和主义是与社会主义政治哲学非常相近但又有其独特优势的一种政治理论,既强调民族、国家的利益,又强调个人基本权利的神圣性与自然性;既重视政治组织的设计和政治系统功能的强大,更强调政治结构的分化与官僚阶层的责任伦理;既重视大众的政治参与与自治的重要性,更强调共同体的公共善与“法律帝国”对社会稳定的保障。共和主义在进行制度安排时,既不是纯粹的建构主义,又不是顽固的本土资源论者或生成论者。它既承认人类社会存在共同的价值共识,又尊重一国的特殊政治、文化传统,同时也不排斥与本国本民族文化、心理相适应的制度建构。中国的社会形态和社会资本传统由于历史悠久,具有根深蒂固性。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既要适应个体自由民主的政治发展潮流,更要正视本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形态。
共和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功能,“在当今的世界上,共和与民主被越来越多地写入国名与宪法之中。但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尤其是作为一种政体形式,在当代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研究中几乎被完全忽略了,在对当代的民主化和宪政运动的探讨中则更是如此。”[8]此外,中外学界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过多地将精力投入到自由主义的研究之中,对共和主义投入的关怀却寥若晨星。如,以马基雅维里的权力政治观和洛克的群己权界为模式解释国家,却丢弃了国家应有的伦理目的内涵,忽视了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中共和主义的面相以及洛克对公民教育的首肯与重视。
在现有的政治体系框架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要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要建设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局面,必须要有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对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说,他对自己生活在什么形式的统治之下是毫不关心的[9]。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了巨大成就,人民的民主意识有了很大提高,这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现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建设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支撑。
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政治体制的构建与改革也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概而括之,这些观点不外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主要强调的是个体的权利、大众的参与诉求或者国家的至上性利益。共和主义既强调国家的利益,又主张个人基本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既重视政治组织的设计,更强调官僚阶层的责任伦理;既强调人民的授权与政府权力的有限性,也强调国家的神圣与法治的正当性;既重视大众的政治参与,更强调社会的稳定与共同体的公共善。因而,共和主义原则下的政治体制构建方案和宪政文明建设经验值得我们重点研究。
当然,由于中国自身政治、文化土壤的特殊性,不可能照搬美国共和主义政治生成的经验与模式,但西方现代性的标准之于东方传统决非文明与蒙昧的对立,至少对中国的政治文明设计与实践具有反思与借鉴的价值。这是因为,“人类的政治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性的事实,即人为人类这一事实。……可以相信,不同的民族在同一智力和道德阶段上所具有的真正的政治制度,会表现出很大的相似性,就是那些政府外部形态上很不相同的地方也是如此。……人们的各种政治组织因此必定基本上具有相同的目的,并且必定会为了满足这些目的而普遍地采取同样的方式。”,[10]再者,中国作为“人民共和国”,人们过多关注的是“人民民主”,忽视了“人民共和”的面相,对美国宪政理论与实践中共和主义的认知与解读,有助于启发人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发展理论基础和路径的思考。作为一项渐进的社会工程,宪政建设不能仅仅依赖于宪政生成自生自发的规律,还需要考察和借鉴外在的先进经验与理论资源。
注释:
①福山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制度(liberal democracy)可以消解其内部产生的一切矛盾,自由主义或者民主作为政体设计的基本原理与制度安排已经不可能被修正或代替了。
②这就将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混为一体了,它忽视了两者对政治参与、政府权力迥然不同的态度。沃特金斯还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将古希腊、罗马时期以来公民法律之下的自由等同于近代(美国宪政模式下)以降法律之下的自由,忽视了不同时期同一话语内涵的巨大差异。(参见(美)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著,黄辉,杨健译.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③高全喜教授强烈批评了人们对社群主义、共和主义等政法哲学的关注,他认为这分散了人们对自由主义及其民主的关注。高全喜教授的批评决不是个案,刘军宁教授、丛日云教授等一大批主流政治学者也持此观点。(参见高全喜主编.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④有关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原旨论证,请参见万绍红.美国宪法的共和主义原旨解读[J].浙江学刊,2006(5)。
⑤(英)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著,曹海军等译.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224。安东尼·阿巴拉斯特在提出这一观点后,又举出了两个典型的例证。洛克在1697年贸易会议上的报告中,建议超过三岁的儿童应该在纺纱和编织的技工学校学会养活自己。配第认为,管制工资的法律“应该允许但仅仅是生存所必要的资金”。
⑥阿罗首次以数理逻辑的分析方法证明,将所有的个体偏好转化为一种社会偏好是不可能的。古老的“囚徒困境”从另一角度证明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性。
⑦有关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论述,可参见Larry Sirowy & Alex Inkeles,"The Effects of Democracy 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equality," Alex Inkeles,ed.,On Measuring Democracy:Its Consequenees and Concomitant,Transactions Books,1991.
⑧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和平、繁荣之间的必然逻辑关系正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同,并引之为本国政改的总纲。耶鲁大学蔡爱眉教授通过亚、非、拉和前苏联东欧的大量案例,分析指出此套西方主流话语的盲目采信已经给许多国家带来了巨大创痛、危险乃至惨剧。(参见蔡爱眉著,刘怀昭译.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在实践中,一国范围内的自由民主要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民主,其结果往往是专制的。
⑨所谓公民美德,或者说道德的公民,最重要的部分是一个共同体意识,意识到个体乃存在于共同体之中。公民德性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公民对国家律法的服从,对公共事物的关注与积极参与,对共同体的忠诚等;二是对其他公民的尊重、友爱与协助等。(此定义参见陈淳文.公民、消费者、国家与市场,载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民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87。)
⑩参见(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程逢如,在汉,舒逊译.联邦党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8-49.原文是a pure democracy,by which I mean a society consisting of a small number of citizens,who assemble and administer the government in person(参见The Federalist papers,by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1961:81.)程逢如、在汉、舒逊将其翻译为“一种纯粹的民主政体——这里我指的是由少数公民亲自组织和管理政府的社会”,不妥。麦迪逊反对民主,但又不得不在共和政体中容纳更多的民意,是以他将代议制纳入共和政体的范畴,这是他的一大创造,也种下了美国式共和政治乃至世界民主(代议制)庸俗化的种子。约翰·密尔后来评价代议制为完善政府的理性类型。许国贤教授分析了代议制民主的选举竞争成本与政治庸俗化成本,并把问题的解决方案归之于人民的自觉与自醒。笔者认为,这事实上就是共和主义所主张的公民美德,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与责任。参见许国贤.民主的政治成本[J].台北: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2004,17(2)。
(11)参见王绍光.台湾民主政治困境,还是自由民主的困境?[J].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7(65):249-256。不过,王绍光教授基于民主的偏好,主张用抽签的方式建立代议制体制则混淆了作为审议性机关的代议制机构与仅需作出常识性判断的西方陪审团之间的差异。
(12)潘恩作为卢梭民主理论的追随者,他认为立法权优先于行政权。潘恩的政治理论设计具有分权的形式,实际上是人民主权。
(13)它的突出表现就是发生在20世纪早期的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进步主义者对平民大众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建设大众政府,实现政治、经济民主是他们的目标。他们认为代议制政府的核心就是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直接参与。杰克逊式的民主取消选民的财产限制,缩短公职的任期,强调以行政权代表人民的意志,反对立法部门的专权。
(14)对美国保守主义的论述参见吕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对于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路判定,参见刘军宁.保守主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标签:美国宪法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共和时代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