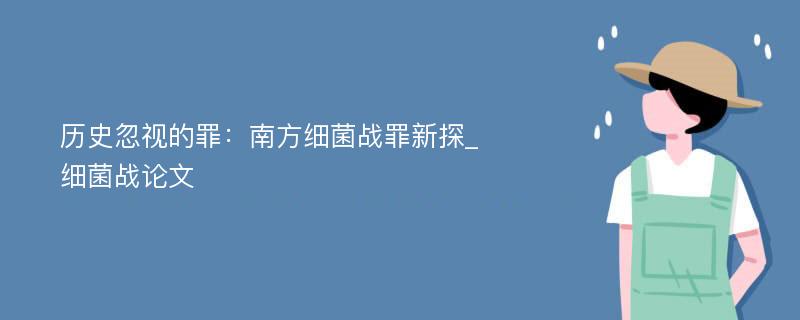
被历史忽略的罪恶——对佐藤俊二华南地区细菌战罪行的新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南地区论文,细菌战论文,罪行论文,罪恶论文,佐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3)03-0073-06
伯力大审判以追究日本进行细菌战的鲜明针对性而引发全球对日本法西斯这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广泛的关注,弥补了远东国际东京法庭的明显缺陷,功不可没。但是这一审判,由于日本主持细菌战的罪魁祸首石井四郎的缺席,同样地留下了无以弥补的缺陷。虽然当年苏联政府根据已掌握的证据,要求将石井四郎列为甲级战犯逮捕并审判,然而,由于美国政府以换取石井手中有关制造细菌战武器的材料为条件,把他保护了下来。因此,伯力大审判由于头号罪犯被庇护,其审判是不彻底的,而且留下众多漏洞,给在审的罪犯逃脱罪责以可乘之机。其中,少将佐藤俊二的轻判便是最典型的范例。
众所周知,石井四郎是以建立731细菌部队而臭名昭著的,而731部队在平房用细菌杀害3000名“马鲁大”,一直被视为其在中国进行细菌战最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可没人想到,当年佐藤俊二在广州,命令其8604细菌部队,于1942年元月开始,在南石头难民所用细菌杀害的粤港难民,其数量远远超过这几十倍,受害人数达到十万以上,却一直被隐瞒了下来。值得留意的是,1942年,正是石井四郎因大肆贪污被免职,一度离开细菌部队的时期。所以,这一罪行,佐藤俊二是无法推诿,赖也赖不掉的。
为了深入调查此事,2005年,笔者曾对日军在华南实施细菌战的主要场所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广州南石头村以及曾受到细菌战迫害的韶关、乐昌、桂林等地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并于2012年对这些地区进行了回访。通过日本军人、众多受害人以及知情人的揭露,笔者逐步掌握了日军在华南地区实施细菌战,进而屠杀、伤害中国军民的大量事实,对佐藤俊二在华南地区的罪行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一 波字8604部队与佐藤俊二
世界战争史上,首次正式使用细菌武器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出于对全人类安全的考虑,1925年6月,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然而,一些国家却一直在研究和使用。1935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就在中国建立了关东军满字731部队、华中派遣军荣字1644部队、华北派遣军甲字1855部队、华南派遣军波字8604部队等四支细菌战部队,并在中国及周边地域实施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其中,华南的波字8604部队的前身是昭和十三年(1938年)9月7日在日本大阪市创建的。当时其被称为“第21野战防疫部”,以井上少佐为首,大约有150人。广州沦陷后,1938年10月12日,该部在广东的大亚湾登陆,并于10月31日抵达广州,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设置了本部。作为华南派遣军司令部的直辖部队,而后开始执行使命,并改名为“波字8604部队”。该细菌部队的首任部队长是田中岩,之后依次是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以及龟泽鹿郎。其机构较为庞大,是配属1200多名专业人员的师团级单位。
除本部之外,该部还将兵力分派到福建、广西、徐州、香港的九龙以及广东省的一些地区。另外,在广州大石街附近的原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今华南农业大学、今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等处也都曾有日军细菌战的部队驻扎。他们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为中国人“防疫”和“救护”,背后却进行着他们所谓的“圣战”。
对波字8604部队首次进行披露的是一位名叫丸山茂的日军军人。他详细介绍了该部队的位置、机构部署以及一些细菌战行为等情况。后来该细菌部队的情况又得到了井上睦雄的进一步证实。井上睦雄于1995年8月13日发表了“他在广州波字8604部队第四科解剖室和昆虫室饲养跳蚤工作时的见闻”的文章,对该部队如何进行人体解剖和如何利用跳蚤等来散布传染病的事实作了进一步的详细揭发。
他们的证言不但使得日军的华南波字8604部队走入了人们的视野,也使得其部队长佐藤俊二再次受到关注。
佐藤俊二1896年出生于日本的爱知郡丰桥城,1923年在东京医科大学毕业。佐藤俊二从1923年起即开始在日本军队中服务,并先后两次进入军医学院特别训练班。后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担任过各种军医职务,并在该学院担任过讲师。1931年间,佐藤俊二因著作《葡萄糖凝结实验》一书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由于佐藤俊二在1931年即主张使用细菌战,并于1936年支持建立第731细菌部队,所以深得石井四郎的赏识。于是从1942年元月起就以大佐衔被正式任命为广州第8604细菌部队的部队长。当时这个部队被秘密称为“波”字部队。一直到1943年2月佐藤俊二先后历任3年部队长。而后,在1943年2月间,他又被调到南京去担任“荣”字第1644细菌部的部队长一职。直到1945年8月被苏联军队俘虏,他最后的职务是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
佐藤俊二积极支持和参加细菌战,在任期间曾多次立功和受到奖励。其中就因参加满洲事件获得了一枚四等“旭日”勋章,因参加中国事件获得了一枚“金鸡”勋章和一枚三等“旭日”勋章。佐藤俊二本人在伯力审判的陈述中也承认说:
我犯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1条所定的罪。我的罪过,就是我从1941年12月到1943年2月间确实领导过广州“波”字第八六○四部队,随后从1943年2月到1944年3月间我又领导过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这两个部队都曾从事研究和大批生产过用以攻击中国军民的致命细菌……我在任“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长时,领导过本部队内探求和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南京“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内所设训练部,在我领导下,每年培养出300名细菌学干部,以供进行细菌战的需要。我从1944年3月任日本关东军第五军团军医处长时起,就积极地帮助和支持了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来扩大细菌材料的生产。为了这个目的,我在1945年5月下了一道专门命令给第五军团各部队,要它们搜捕为生产细菌武器所必需的鼠类,以便送往第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里去。[1]57
由上可知:第一,日军在广州进行细菌战的阴谋筹划已久,建立的波字8604细菌部队是一支队伍庞大且机构比较完善的部队,而且保密性特强。根据目前查到的资料可知,关于该部队的档案,报刊、史书记载等均很少。第二,佐藤俊二是一位有着高深医学知识的军医,且对开展细菌战有着无比的兴趣和热情;佐藤俊二在华南波字8604部队地位相当重要,并在华南地区的细菌战中负有不可推卸的指挥责任,理应受到人民和历史的重新评判。
二 佐藤俊二对波字8604部队细菌战的否认
由上可知,佐藤俊二是华南细菌部队的重要人物,然而在当年伯力审判的整个过程中,他对自己华南地区的细菌战罪恶行为却只字未提,只是谈到在南京的事情。
在伯力军事法庭上,公诉人摆出了重要的证据认为他是一个“日本推行细菌战的领导者”。但是佐藤却坚持“自己只是执行命令,没有直接参加过细菌战的实施”。其时,一同受审的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之对佐藤俊二在731部队的罪行供认不讳。而后731部队生产部长柄泽十三夫也供认了一系列撒播鼠疫跳蚤的罪行,许多罪行都涉及了佐藤。这时佐藤俊二才不得不承担制造细菌的责任,但却绝口不谈用细菌直接杀人的罪行。之后,731部队所属的642部队长尾上正男和三品隆行等人又上庭作证。尤其是三品隆行两次上庭作证指出:佐藤俊二曾亲自带队向中国部队前线撒播过鼠疫跳蚤。
在这样的情况下,佐藤俊二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行为。对自己在细菌战部队的职位和具体工作等事实进行了承认和陈述。然而,在之后辩护的过程中,其辩护律师波加切夫却认为:起诉书上所定的这个罪名是极严重的。
……起诉书上所定的这个罪名是极严重的,并且基本上是理由充足的,但是我不能同意把佐藤与关东军领导人员同等看待。起初,他本是一个部队长,后来是第五军团军医处长。他这职位距上层人物还远。他仅仅是一个陆军军人,虽然他获有将军衔,他只是那些上层人物意旨的执行者……
……本案材料证实,佐藤被任为“波”字部队长是在1941年,即在该部队工作建立起来并布置就绪后已经有几年的时光了。我并不是说此种情况能完全辩白佐藤,但这一事实可以减轻他的作用和责任。
说到这里,我想请诸位注意到一件事情,佐藤在被告名单中占第8名,即在职位上比他较低的西俊英、柄泽、尾上等人后面。而这并不是偶然的。佐藤的作用,较之当时所进行的细菌破坏活动和在活人身上所作的种种实验,以及第七三一部队内部监狱刑室中有3000人被害死的事实说来,是要轻得多。我有根据地认定,佐藤并没有亲身参与过杀害那些落到“特殊输送”范围内而被当作“受实验材料”受过种种暴力和侮辱的不幸的人们。起诉书上并没控诉佐藤有此种野蛮行为,我对这点是同意的。
自1944年2月佐藤被任命为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后,有个时期离开过领导过该细菌部队的工作,并且一般地就离开了与准备细菌武器有关的活动。只是在1945年5月间,才由尾上向他提出请求,要他捕获鼠类送到海拉尔第六四三支队里去。佐藤为实现这种请求而颁布了相当的命令给第五军团各部队,因而他对准备细菌武器一事起过某种协助作用。
在庭审时,宣读过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长松村的口供,其中说道,那时关东军中几乎所有各陆军联队都进行过捕鼠工作。所以,佐藤在此场合所给与的协助并没起积极性的作用。他在这里并没表现过主动性,并没有起过倡导作用。他不过是重复了他周围人们所干的事情。
根据这一切实际材料……我请审判员同志们切实估计佐藤所干出的一切罪行以及他在准备细菌战中所起的那种远非主要的作用。[1]354-355
正是由于佐藤俊二及其辩护人极力声称的“他无非是在执行上级命令”和“他对准备细菌武器一事仅仅起过某种协助作用”等理由,尤其是回避了大量杀害华南地区军民的罪行,伯力军事法庭虽然认定“他担任过两支细菌部队的部队长,制造过细菌武器”,仍只判处了他20年有期徒刑。
当时,佐藤俊二也许是感到庆幸,所以,在法庭作最后陈述时,便假惺惺地作了一番“忏悔”:
从1941年起,我担任过两个细菌部队的部队长,并直接领导过准备细菌战的工作。此外,我当第五军团军医处长时也协助过准备细菌战的工作。我所犯的罪恶是与医生职责相抵触的,是与医学道德相抵触的。这种罪行是反对人类的,我的行为是反对世上一切善良东西的。此刻,我在法庭上完全忏悔我所犯过的罪恶。我很感谢辩护人,同时,我应该说明,当我听到律师替我这样一个罪犯辩护时,我真是心中感到惭愧。我认为我是配不上这点的。现在我请法庭对我定出公允的判决,这种判决将是完全相当于我所犯的罪恶以及我所应负的罪过责任的。[1]403
从这份“忏悔”词中,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到他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惧怕惩罚,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所以,千方百计,避重就轻,抵赖推诿;另一方面,尽管他在华南地区的细菌战罪行被巧妙地掩饰过去了,但是作为一名医学博士和病理学医生,却用所掌握的医学知识残害人类,他无疑也清楚自己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知道自己终将受到历史和人类的审判。
三 事实证明下的佐藤俊二的罪恶
伯力审判载入战犯审判史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追究日本进行细菌战的职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伯力审判对佐藤俊二等人的细菌战罪行仍然未能深挖下去。这无疑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个遗憾。
对华南波字细菌战部队实施细菌战行为首次直接揭露的是波字8604部队曾经的成员丸山茂。丸山茂在1994年日本举办第731部队全国展时受到感动,写了《不管以什么名义,走向战争史罪恶》一文,首次公开披露了华南波字细菌战部队的行为。为了应对日方某些人的质疑,丸山茂还于1995年7月在石敬一、糟川良谷等专家和日本电视台、报社记者们的陪同下到广州进行核实。不久原日军华南波字部队队员井上睦雄也于1995年8月13日发表了第四科解剖室和昆虫室饲养跳蚤工作时的见闻,进一步证实了广州细菌战部队的事实。
正是在这些事件的启发下,笔者于20世纪90年代对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和广州南石头村等地进行了相关的调查。通过对冯奇、何金、梁时畅、肖铮、肖永光、吴伟泰等一些经历者和见证者的采访对当时的细菌战状况有了如下了解:日军波字第8604部队研究细菌武器的大本营设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旧图书馆及其附近地方;伪粤海港检疫所是他们秘密进行人体试验的场所;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则是他们在广东进行细菌战杀人最多的场所。8604部队在华南地区进行细菌战作业的高潮主要有两个时间段:一是1942年初香港沦陷初期,强迫香港人“归乡”时期。这正是丸山茂证词中所说的时间段,也正是佐藤俊二直接指挥派人上东京取回沙门氏细菌杀人的日子。一个是1943年。当时香港的粮食问题日趋严重,强化了“归乡”政策,宪兵还可以当街抓人,强行押解上船出境。而波字第8604部队在南石头和“万人坑”杀人和埋人的时间则可以延续到1944年,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活尸解剖及生产大量鼠疫菌,更是可以延续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又遭美机轰炸之际,而且后期抓得更紧。
具体来看,日军在这里进行细菌战主要起因于日军占领后大批逃难到广州的粤籍难民。据史料记载:香港被占领后,日军为了掠夺更多的粮食、资源等物质,“早就想将一百六十多万的人口减到几十万人,以减低统治者他们要供应粮食的负担。他们尽了很大努力劝谕人们离开香港,或威逼、或利诱,务使香港市民尽早返回他们的故乡或原籍。这就是所谓‘归乡政策’”[2]。“当时香港居民归乡的路线除航空外主要有四条:第一,由九龙经深圳进入内地。归乡市民通常由深水埗步行至深圳再到广州,也有花数月步行至福建、上海及华北等地的长途客。第二,雇船到澳门转内地。第三,从油麻地码头坐船到广州。第四,雇船经广州湾(今湛江)进入广西。1942年1月11日起,当局安排的免费归乡船正式起航,香港居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大陆。1943年初,当局再次启动‘归乡运动’,原因是‘当去夏办理运送归侨时,适因内地水患而中止’。”[3]
我们找到当年的报纸,称“第19批”坐船遣返的就达5000余人,而这还是在1942年初。由于广州与香港历来的亲密关联,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很多人逃到香港投亲靠友,100多万人口的广州仅余20万;1941年12月底,香港沦陷,近100万人大都被遣返回广州,160万人口的香港又剩余不到60万。这些数字是惊人的,19批之后还有几十批,每批5000人,也就几十万人了。
这些经过艰难险阻到达广州的难民本以为灾难已结束,却不知自己又陷入了另一个魔窟。由于当时的广州已经成为了日军的“皇道乐土”,所以日军以害怕影响广州的治安为理由,将大批逃难的粤籍难民收容到南石头难民所。正是在这个难民所里,佐藤俊二凭借其所掌握的医学知识,指挥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大屠杀。
为了调查清楚这个事件,我们于2005年和2012年曾反复深入现场,采访了至今仍然幸存的钟瑞荣、范九、梁威、肖铮等人,对南石头、“邓岗斜”等细菌战“现场”做了进一步的清理。
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的前身是广州惩戒场。“其建于1912年6月,面积约31000平方米,是在河南南石头西边珠江白鹅潭畔的旧镇南炮台原旧址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原是国民党惩罚罪犯的场所。1941年4月日军和伪国民政府又在其北边设立粤海港检疫所。所长是曾任台湾总督府医院院长的日本人五级医官岛义雄。另外还有前台湾卫生技师、细菌专家、八级医官岩濑祜一以及中国和日本医官、兽医官、检察官、技术官、雇员、事务官、汽车夫等总共78人,其中日本人12人。”[4]
作为见证人之一的冯奇先生也曾描述到:
难民所正门口上有座小楼,里住保安警察。入门右边约50米远有个像排球场大的地方,有个水井,再去约30公尺又有个水井。入门口左边约30米有个厕所,附近有个水井。厕所过些便是化骨池。化骨池中间有几级梯板上化骨池。其上约有高1米多便是炮楼的行人道,城墙上四周筑有四个高几米的瞭望亭。城墙上四周都装有带刺的铁丝网。城墙上距地下有6米多高。正门是很开阔的。里面有保安警察守着。城墙上也有岗哨往来巡视。难民关进去不易逃出。①
原南石头惩戒所的容量为1200人,后又经过扩容增倍,但这只是正常收容的人数。1942年初开始,原先容纳数十人的容量,则可以关上100多人,这一来,平时关押的人数就可达5000人甚至更多,而且关押的人是在高速流动中,所以前后羁押的人数,则远远超过10万。
据见证人描述,当时难民所内死人的情况是很悲惨的。开始,还有两部猪笼车拉着尸体扔到邓岗斜的“万人坑”里。后来,由于死人太多,猪笼车被拉坏了,就由六个抬尸人日夜不停地抬尸走。当时,因人已瘦到皮包骨头,轻多了,因此有时是两个、三个叠在一起抬,而且还有一些人没死也被抬走了。晚上,甚至还有大卡车来拖。
早在1994年,香港记者采访钟瑞荣时,他就指证:当年掩埋人的邓岗斜至少有十万难民遇害。至于邓岗斜埋了多少人,几位见证人到现场作了指证。当时的“万人坑”就在当今派出所一侧长达100多米,宽也有近百米的地方,比一个足球场都要大得多。我们从中外的“万人坑”资料中可以看到:50、60米的大坑,每每就能埋进三五万尸体,一般程序是埋了、化了,再扔进去埋,再化,再往上加尸体。因此“万人坑”里面实际埋的人数则至少超过十万具,而且还不计算运走的及扔进“化骨池”中的。
这些还可以从20世纪50年代原南石头一带搞基建时挖出的数以千计的人骨头推断出。从南石头派出所算起,以南80米至100米都曾挖出过人骨头。到80年代,建职工宿舍时又发现,从地表至2米深处,至少有三四层。每层约有30厘米黄土隔开,中间混有人骨的厚度则有20厘米至40厘米,而且,成型的肋骨、颅骨很少,全碎了,数量之多,也无法估计。
邓岗斜的“万人坑”到底掩埋了多少粤港难民?我们只能提供面积与深度的数据。“万人坑”长100多米,宽约100米,面积在10000平方米左右。而近十年局部的浅层挖掘,仅两米多,便有三四层,尸骨与尸骨之间的土层为30厘米。用丸山茂证言说,最后,连覆盖尸体的浮土都没有了。一个人的面积能有多少,体积又有多大,而华南雨水多,尸体腐化的速度很快,所以,表面的土层迅速坍塌,又可以抛尸下去,再加几十厘米的土来掩埋——这都是证言所描述的,更何况,死者已骨瘦如柴,一付担架可以抬两三个尸体。到底埋了多少层,最大深度有多少?我们不难从坍塌的强度推测得知。
而邓岗斜的“万人坑”掩埋尸体时间,则是从1942年初开始,一直到1944年。丸山茂在南石头的时间,从其证言看,仅仅是1942年的一段,那时,已经埋过了几层,浮土都不够了。而1943年又有一次大规模驱逐香港难民的行动。当年香港难民,大都是1938年从广州逃亡去的,1942年,他们大都也只能回广州,但广州已不允许他们回去了。沦陷期间,香港人减少了100万,有多少被“留”在了南石头?
钟瑞荣、范九等人还指出,当时因难民所里人满为患,从香港来的船大都滞留在江面上,几乎把江面都盖住了,少说有上百条。而在当时这些船也成了临时的浮动的难民所。如在船上侥幸逃脱的何琼菊称:她的船上原有400多人。后来,死了的就被扔进江中,活着的则大都被陆续送进难民所与检疫所,而后,她再也没见到他们,到她逃离时船上就只剩40人了。当然,这些人除了饿死之外,绝大多数还是因为吃了放有细菌的食物而病死的。与何琼菊不在同一条船上的人也有类似的揭发和控诉。
另外,根据丸山茂、井上睦雄以及冯奇等人的描述,他们的行为还不只这些。佐藤俊二还曾下令:用活人作细菌武器实验,之后把那些感染了副伤寒却侥幸不死的人,转移到北江上游非占领区——也就是中国尚未控制的地区,利用他们作为“菌种”,以撒播细菌,扩大细菌战。
而据史料证实,佐藤俊二领导的这支部队不仅在广州进行细菌战,还在广东的韶关、乐昌、阳江等地以及广东附近的省份和地区进行过细菌战。他们通过撒播鼠疫跳蚤等细菌对这些地区进行侵害。中央档案馆等编写的《细菌战与毒气战》就曾记载:
1937年11月7日,3架日机由唐家湾起飞,在广九铁路附近投弹并撒白、绿、黄色药粉。经我军搜集研究,全系毒质,并有肺痨病菌。1939年6月1日,据中国铁道部运输司令钱宗泽电称:敌派汉奸冒充难民,携带热水瓶,内藏霍乱、鼠疫菌,潜入粤、桂、滇、蜀,散发于我军阵地水质(源)中,其派往重庆、桂林、西安、金华、韶关等地的已分由海南岛、汕头、汉口等地出发,第二批不久即赴长江各地。1939年10月,顾祝同致何应钦电文说,敌派细菌、化战专家30余人来沪转往晋、鄂、粤等省任指导。[5]
一直参与华南细菌战调查研究的糟川良谷先生就曾指出:“1942、1943年(广东)省内鼠疫的急剧发生,明显是由细菌战造成的。波字8604部队1941年参与福州战役,并于事后掘出尸体进行鼠疫鉴别检查,1941~1942年参与香港战役,另外和南方军防疫给水部(新加坡)一起进行人员转移,这些事实都得到了证实。然而对波字8604部队的调查研究才刚刚开始,今后还要不断努力。”[6]
在这些行为中,最悲惨的还是要数“活体解剖”。731在平房进行的“活体解剖”因其灭绝人性目前已为全世界所声讨。然而,在8604总部广州原中山大学医学院的“活体解剖”则比在平房的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老兵井上睦雄就曾亲自揭发,描绘了一位游击队员在未死前如何在他刀下被活体剖开的。
因此可以说,日军在华南地区的细菌战行为也是比较恶劣的,但为了掩盖这段历史,日军采取了杀人灭口的行径。的场守喜等人作为他投菌计划的具体执行者,事后都被派往了南太平洋前线,生死不明。这样日军在华南地区的细菌战行为就很少被人知晓。这也是导致佐藤俊二在伯力审判中,避而不谈其在华南地区的罪恶行为的直接原因之一。
由上可知,日军波字8604部队确实曾利用人类文明积累起来的先进医学知识与现代技术,在粤秘密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惨无人道、违反国际公约的细菌战。而佐藤俊二以一名医学博士的身份,理智地指挥着其部队成批量地生产尸体。虽然他极力掩饰他在华南以及附近地区对中国军民的迫害,虽然伯力审判只认定“他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只对他判处了20年的有期徒刑,最终未能得到真正的、彻底的清算,但是,细菌战毕竟是反人类罪最大的三桩罪行之一,因此,我们呼吁国际法庭,为了使这类罪行不再发生,有必要重启对大屠杀、细菌战、慰安妇等罪行的审判,对那些犯下大罪的石井、佐藤之类予以追诉。
收稿日期:2013-02-25
注释:
①本部分内容参考自1994年9月18日冯奇先生的第一次来信。冯奇先生当时为居住在佛山市的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