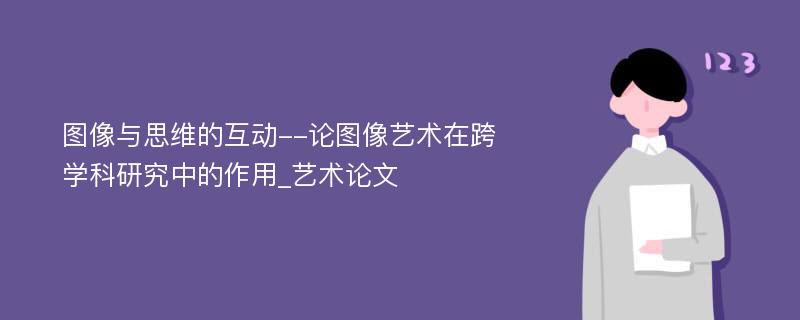
图像与思想的互动——谈跨学科研究中的图像艺术z,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像论文,互动论文,思想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对图像艺术的分析和阐释,是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中谈到的“图像”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指代了与图像艺术形式相关的各类视觉文化资料,包括传世的书画、器物,也包括墓内装饰、随葬品等考古资料,寺庙、石窟内的壁画、造像等物质遗存,以及地图、天文图等一般性的图像资料。传统的中国美术史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绘画史、传统绘画理论和鉴定研究。近年来,由于人文学科内多角度、跨学科研究趋势的带动,艺术史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目的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对人文的兴趣不断上升并且可能成为将来的主流之势。①与此同时,图像材料又被引入到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其他不同领域的讨论中。其中,艺术史与思想史研究的互动更是十分突出:图像作为史料进入到思想史研究的视野;而艺术史也开始讨论隐藏于视觉语言中的思想含义,解释由图像材料流露出的个人与时代的文化和思想。在这种背景下,艺术史研究不断呈现出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交叉而又努力寻求自身定位的态势。
图像与思想在人文学科内的互动,体现在视角、方法与观念多个方面。本文将试图从艺术史研究者的角度入手,分析该学科得以接受思想史与观念史影响的因素和学科环境,审视图像研究的新视角、方法与传统美术史理论,并探讨中国艺术史研究如何在人文学科的框架下重新确立自身的学术独立性与存在价值。这些方面将涉及对于当下学术格局的分析与反思,笔者希望通过对图像艺术研究的初步探讨,引起学者对图像材料以及艺术史研究更多的关注与讨论。
二、图像与历史
图像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这一观念显著地反映在西方文化史的发展过程中。自18世纪起,考古学家开始力图说服历史研究者,使其注意到图像艺术对于理解历史所具有的意义。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例如伏尔泰(Voltai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吉本(Edward Gibbon)等,虽然曾对视觉艺术抱有谨慎而怀疑的态度,但他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视觉艺术的感染。18世纪中后期,西方史学家逐渐意识到,图像作为历史证据在历史研究中应起到重要的作用。②有些学者甚至提出图像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文字资料更直接、更可靠地反映历史原貌。例如,文化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曾说:“只有通过艺术这一媒介,一个时代最为秘密的信仰和观念才能传递给后人,而只有这种传递方式才最值得信赖,因为它是无意而为的。”③英国批评家罗斯金(John Ruskin)于1884年发表了他对图像艺术的著名评论:
伟大的民族以三种手稿撰写自己的传记:行为之书、言词之书和艺术之书。我们只有阅读了其中的两部书,才能理解它们中的任何一部;但是,在这三部书中,唯一值得信赖的便是最后一部书。④
布克哈特、罗斯金对于图像作为史料所具有可靠性的描述似乎过于夸大,但至此,图像在历史研究中获得了合法的地位,被用来审视过去的社会、思想、政治以及宗教变革。视觉艺术成为开启往昔的一把钥匙,这促使欧洲各国的人们广泛地收集历史遗存、建立博物馆,以展示各自民族的辉煌历史。在20世纪,以图证史最终成了历史学家理解过去的重要方法。荷兰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甚至提出,历史意识是一种产生于图像的视像。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应以图像为先,因为只有通过图像,才能真正地发现往昔;只有通过图像,才能更清晰、更敏锐、更富有色彩、更富有历史感地理解过去。赫伊津哈后来逐渐意识到过分强调视觉艺术的危险,并在晚年开始对图像的历史作用持两面态度。⑤然而,不论当时的学者如何争论或反思,都无法否定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这正如当代史学家特雷佛·罗珀(Hugh Trevor-Roper)所说的:“忽视艺术和文学的历史是枯燥无味的历史,而脱离历史的艺术和文学研究则是一知半解的研究。”⑥
由于图像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形成了对艺术进行的专门研究。该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门与哲学、历史、语言文学、政治经济等领域并驾齐驱的学科,旨在从历史的角度对人类的视觉艺术进行研究,进而获得对其他历史现象的深入理解。事实上,早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文主义者就已经开始对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描述,例如瓦萨里(Giorgio Vasari)的《名人传》记载和描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家,是一部对后来美术史写作产生巨大影响的艺术家传记总集。⑦18世纪左右,德国古典主义学者温克尔曼(Johan Winckelmann)最先将“艺术”和“历史”这两个词语联系起来并作为著作标题,他的《古代艺术史》成为从文化角度研究古代艺术的奠基之作。在温克尔曼看来,艺术史的目的在于阐明艺术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并说明各个民族、时代、艺术家的风格差异。这种阐释方式成为日后艺术史研究的一种基本的叙述模式。⑧
艺术史学科真正成型于19世纪。德国是这门学科的策源地,称其为“Kunstgeschichte”,即“艺术科学”,因此有“艺术史的母语是德语”的说法。1813年,哥廷根大学创立了艺术史的全职教授职位,其后艺术史教职相继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大学中出现。虽然这一领域在当时与历史学、考古学、哲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基于有效的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的建立、博物馆与美术馆的兴起,以及该学科进入大学的殿堂,艺术史逐渐成为一门专业化的艺术科学。
该学科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是理论体系的确立。形式与风格分析方法的建立与完善,正是该学科得以确立的界碑。瑞士艺术史学家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提出艺术史是一种观看的历史,关乎智力和精神两个方面。形式不仅仅是单纯的形式,而且也富含意义。在他看来,图像艺术自身有其历史,揭示视觉层次才是艺术史的首要任务。沃尔夫林因此着重于艺术作品的线、轮廓、面、体积、重量、动感、造型、色彩、光线、明暗关系等基本艺术语言的研究,展示出一套全新的观看艺术品的方法。他尝试将视觉形式演变与社会精神态度的变化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⑨这种视觉分析受到了当时实验心理学的影响。维也纳艺术史学派在知觉研究新发现的推动下,曾采纳了类似的视觉分析模式,比如李格尔(Alois Riegl)提出的“艺术意志”,考虑到更多文化因素的作用,明确将艺术视为人类知觉与精神进化的坐标。⑩形式分析方法通过视觉材料展示人类关于“看”的历史,似乎正是艺术史不同于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的学科品质。
20世纪30年代起开始,沃尔夫林所代表的形式分析学派逐渐退居幕后,艺术史的中心移向英美两国,艺术史进入更加多元化的时代,以多种学科来探索图像意义的局面日益形成。瓦尔堡(Aby Warburg)、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等学者提出了图像学的理论,它的出现是对形式主义的反拨,关注于图像题材、象征含义与文化意义的研究。(11)图像学可以被视为以历史解释学为基础进行论证的方法,它的任务是对艺术品进行全面的文化解释,研究者需要对图像的历史情境和相关文献十分了解。将对视觉语言的阐释作为其主要目的,标志着西方艺术史研究的转向。图像学吸收了风格分析中关于形式因素的部分,母题成为其研究的核心。大致来看,图像学研究的过程可分三步:一是前图像志分析,即确认最初的或自然的主题;二是图像志分析,理解由母题组成的内容或故事;三是图像学的阐释层,探讨图像的内在意义与文化的象征内涵。在图像学研究的这三个步骤中,任何人都能不同程度地读懂作品。正是这种阐释的功能,使得图像学成为西方艺术史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分支。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贡布里希(E.H.Gombrich)、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等从哲学基础入手,建立了新的研究基础。波普尔提出“情境逻辑”,强调的是文化情境的重要性,把对艺术风格、母题内容、艺术功能的讨论,回归到艺术史产生时代当下的场合,也就是以当时的诠释方法来理解当时的问题。波普尔认为,社会的赞助可能导致风格的主流。艺术风格与赞助环境的关系,是从艺术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艺术作品,这是“情境逻辑”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后来的以哈斯克尔为代表的艺术社会学一派,试图重构波普尔的“情境逻辑”,也正是在此研究视角下,试图对艺术史发展中灵活因素进行变通包容。
从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温克尔曼将艺术的发展与精神进步相并列;布克哈特把艺术史与文明史联系起来;沃尔夫林将艺术史与知觉方式的演变相对应;瓦尔堡和潘诺夫斯基试图解读文本与图像意义的关联。这些研究构成了西方艺术史的核心框架。每种方法都有其具体的研究目的以及对应解决的问题,但同时也会引发未能解决的问题。正是在“发现问题——寻找方法——解决问题——发现新问题”的循环过程中,艺术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不断丰富,其现代学科体系也趋于完善。(12)
继传统艺术史的黄金时代之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西方艺术史研究,一直处于对传统美术史学的反思过程中,“新艺术史”风潮不断兴起,其中包括了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艺术史理论。这些理论源自政治、文学、语言学等领域,极大地拓宽了传统的艺术研究。这一风潮下的西方视觉艺术研究内容丰富,方法多样,使得艺术史成为新型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三、图像艺术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19世纪末,日本学界在观念与方法上受到西方学术研究的影响,开始认识到艺术史的重要性。东京大学于1893年聘请大村西崖开设东洋美术课程,而京都大学也于1909年由内藤湖南教授开设“中国绘画史”课程。“美术”等概念及理论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13)
中国的传统学术历来对图像艺术并不重视,艺术史也未曾从历史研究中得到流演、升发。虽然宋人郑樵曾创《图谱》,强调“左图右书”,提出在历史研究中图文需相互印证。(14)但是,正统史学家将图像视作史证的例子少之又少,《图谱》之说也未曾对后世史学产生较大影响。对于艺术品的专门研究,中国早就有画学和金石学的传统。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作为一部绘画通史在847年便已成书,远远早于意大利瓦萨里的《名人传》。但与《名人传》不同,它一直作为画学研究的重要材料,而未被视为中国文化史的经典。至明清时期,文人鉴赏风气使得画学著作更注重传记和画品著录,“重记载而轻论述”,史料价值多于其史学意义。(15)画学因此一直处于学术的边缘,而至于传世的图像、器物,更是没有得到历史研究的关注。金石学对于石刻、青铜器的研究,或以铭文为中心,或以著录为主。虽然其研究范围在清代有一定程度的扩展,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金石学的方向。在艺术品收藏方面,帝王与文人雅士历来收藏丰富,但这些藏品难以进入公众的视野,也使得图像艺术无法产生广泛的影响力。(16)
随着20世纪初外来词汇与学科理论的传入,画学和金石学研究逐渐朝着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学科形态转变。美术史的概念由日本引入中国。大村西崖于1910年完成了包括中国部分的《东洋美术史》。一年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澂编写的《西洋美术史》。美术史作为学科科目出现在民国元年(1912)教育部的文件《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上。1917年,姜丹书编写了作为教材、涵括中西艺术的《美术史》。(17)这一时期,国内出版的许多中国美术通史,有的直接翻译欧美、日本学者的论著,有的在国外论著的基础上重新编写。正是这些著作将艺术史的学科架构与理论介绍到了中国。另外,中国艺术史的最初建立,也与考古学关系密切。西方近代考古学的传入、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探险与考古调查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学者和美术史家走出书斋,开始了对于美术遗址的考察,推动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美术史学科的发展。(18)
除了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西方美术史研究的传入以及考古学的影响,近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促成中国艺术史学科创立的重要因素。蔡元培、滕固等先后留学欧洲的一批学者大力倡导艺术史研究在中国的确立。蔡元培先生在1925年邀请叶浩然在北京大学开授“中国绘画史”课程,使得这门学科进入到大学的讲坛。(19)滕固在1926年撰写了著名的美术通史著作《中国美术小史》。该书无论在体例上,还是在具体的作品分析上,都明显体现了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运用了历史观、艺术史发展和风格演进的模式。滕固还于1937年在南京创立了中国艺术史学会,马衡、梁思成、张政烺等都是该学会的成员。(20)此外,陈寅恪先生于《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也特别强调建立艺术史学科,系统整理、陈列和出版图像遗物的必要性。(21)
这一时期,艺术、考古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得到了全新定位。王国维、梁启超等史学大师均对图像资料流露过浓厚的兴趣。傅斯年在1928年所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主张,学者们应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利用实物材料或新出土的地下材料来验证古史。(22)郑振铎也四处搜集图像资料,编写《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试图改变墨守旧规的历史教学状况。另外,他还批评了中国轻图像而重文字的习惯,指出:
史学家仅知在书本文字中讨生活,不复究心于有关史迹、文化、社会、经济、人民生活之真实情况,与乎实物图像,器用形态,而史学遂成为孤立与枯索之学问。(23)
在学者的倡导与影响之下,中国逐渐完成了艺术史现代学科的基本建构。需要注意的是,中国艺术史的学科定位与西方艺术史研究有很大的不同,呈现出另外的倾向。这主要涉及现代的艺术教学问题。首先,20世纪初以来的一批从事中国绘画史写作的人,往往多是画家。这些画家试图从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绘画的传统,当然极为可贵,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他们提出问题的出发点和对历史整体的看法,通常从创作实践出发,同时他们要为回答“中国艺术向何处去”等问题而向历史深处寻找答案。(24)一些论著涉及对于艺术本体的关怀,也关注到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的变迁。但总体上说,一方面,这些论著较少讲求方法论的自觉性,多数从对美术品本身出发,忽视了外在因素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写作的美术史著作,以通史、断代史、画种史和画史专论为研究主流,将对艺术史的书写仅限于传世书画等经典作品,忽视了考古发现、物质遗存等一般性的图像资料。
其次,与欧美国家大多将艺术史系设在综合性大学不同,中国的艺术史系均设在美术院校。美术院校所培养的艺术史专业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了解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可以主动地探索中国美术创作发展的方向,但限于客观的条件,在艺术史的课程设置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支持不足。同时,在以创作和设计为主的学术环境中,美术史的书写需要服从并服务于美术实践,这使得美术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艺术创作的附庸。另外,艺术史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和影响也相对较少,缺少西方艺术史研究与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密切联系。因此,大多数美术学院的艺术史专业仅仅限于局部的美术史研究,较少考虑到艺术史作为一个整体性史料的发掘意义,缺乏内在的历史意识。这样的学科设置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图像研究在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影响。
由于学科传统、定位及设置的不同,相对西方艺术史研究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的状况,目前中国的艺术史学科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西方艺术史研究理念与方法的演变,持续影响着该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同时,在中国绘画、美术、考古等方面,海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也不断为国内的研究者们提供借鉴。
四、图像与思想的互动:以近年来有关中国图像艺术的研究为例
20世纪80年代以来,艺术史经历了从形式分析到视觉文化的多重读本,原先作为单一文化性状的“艺术作品本位的历史”逐渐代之以不同文化性状的多元化格局。(25)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美学、现象学等理论和方法,都以跨学科的方式移植到艺术史领域。有关中国艺术的研究,尤其是欧美学界对中国古代图像的讨论,在这种综合性研究的推进下,也呈现出向外扩张的景象。它与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频频互动,逐渐具备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知识平台。
欧美艺术史的人类学取向使其对于艺术作品的探讨偏重于文化史的研究,关注图像所展现的风俗、意识与心理方面的内容。近年来,艺术与宗教史、艺术与社会史等领域都涌现出许多重要的论著,例如,景安宁的《广胜寺水神庙》以寺观壁画为着眼点,探讨民间信仰以及佛道教角力。(26)柯律格(Craig Clunas)的《雅债——文征明的社交性艺术》(27)、乔迅(Jonathan Hay)的《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28)都从“社会性艺术”的角度出发关注艺术家的书画创作与社交网络,进而理解当时的社会与文化。
观念史作为历史解读的方式被引入艺术史研究领域,也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文献或文本入手,将思想、观念置于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的背景之中予以探讨,逐渐成为一种趋势。虽然这种包罗万象的观念史研究在西方最终没有形成一种学科行为,但其介入路径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研究的走向。艺术史研究通过器物、图像进入观念史领域,无疑顺应了这股潮流。例如,中国美院的范景中和曹意强十分重视艺术与思想、观念的关系,有意识地引进西方观念史的成果。他们于2006年开始组织出版《美术史与观念史》期刊,并在序言中明确提出:
美术史者,史之一辐也。虽然,寻繁领杂,务信弃奇,明白头讫,品酌事例,其揆一也;然终以图像为指归,以立载笔之准的。而析理赏览,探赜索隐,又以观念史为羽翼。(29)
艺术与观念的联系倡导研究者将图像艺术放置在历史场景、历史过程中去考察,并强调对艺术作品的解释除了关注社会文化,还应该体现出图像背后的思想观念。但艺术史提倡的是强化实物、图像在观念史研究中的独立价值。这既是缺失图像资料的观念史研究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艺术史在当下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所致。(30)
一些关于中国图像艺术的研究体现出了这种图像与思想、观念的互动。例如,罗森(Jessica Rawson)在探讨古代的建筑与艺术时,十分强调观念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分析视觉艺术的三个层次:日常的物质世界;体制性或制度性的世界;观念世界。她认为,每个不同层次皆包含了物质构成和社会结构,同时又由信仰系统所支撑。在第三个层次的观念世界中,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各种仪式和墓葬都属于这个范畴。关于宗教建筑、绘画和表演等表现形式也都属于这个层面。(31)罗森在《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中收录的若干论文《中国的丧葬模式——思想与信仰的知识来源》、《思想与图像的互动——从中国后世观念看随葬陶俑》,便是从观念世界的角度来探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与秦汉时期的随葬墓俑。(32)《作为艺术、装饰与图案之源的宇宙观体系》一文则探讨了“关联宇宙观”的哲学观念与图像艺术的联系,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变化视为重大的思想和信仰断裂的证据,并提出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框架与其物质的、人造的世界之间可以建立起紧密的联系。(33)
巫鸿也是在图像艺术的综合性研究方面十分突出的一位学者。例如,巫鸿的《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一书通过研究武梁祠石刻的图像内容,分析武梁祠整个图像程序展开的思想观念,考察武梁祠石刻与汉代思想、社会之间的关系。(34)《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中收录的许多文章更是围绕图像展开,发掘图像的历史意义,通过“中间层次”的美术史研究,试图构建图像与文献之间的桥梁,体现不同时期的社会体制与思想意识。(35)另外,巫鸿在分析东周时期的明器时,探讨了当时哲学家和礼学家对丧葬用器不断专职化和形式化的思考,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礼器分类。这种对于古代器物的研究和思想史、礼制史领域密切相关,正是从新的角度重新考察与发掘古代器物与艺术的历史意义。(36)
巫鸿的艺术史研究十分自觉地关注方法论的运用,这对国内的中青年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也有意识地考察图像艺术所蕴含的观念。这一点在墓葬美术方面尤为突出。学者们在结合考古学与艺术史研究的同时,充分注意到墓葬美术的特性,并关注葬仪与图像,以及图像的宗教及社会背景。如郑岩的《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试图解释图像背后的象征意义,探讨图像在研究精神文化方面的价值。例如他在分析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时,通过联系漆盘上的画面,提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士题材被赋予新的寓意,具有升仙的色彩,成为时人表达新思想的媒介。(37)邹清泉的北魏墓葬研究,则通过深入考察墓葬中的孝子画像,追溯古代孝道思想的传承与变迁,揭示北魏孝风盛行与孝子图流行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38)李清泉有关河北地区宣化辽墓的研究,考察了墓葬壁画的图像内容,提出备茶图和备经图题材反映出宋辽时期佛道两教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互相作用与影响,整个墓葬壁画集中地体现出辽代汉人的理想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39)
李氏的研究,受了德沃夏克(Max Dvorak)“作为精神史的艺术史”的影响,(40)试图理解表现或隐藏于造型形式中的思想含义,解释体现在图像材料中的个人与时代的文化和思想。为了探寻图像内容中的思想含义,艺术史学者借助于图像产生的时代、民族、政治、宗教、哲学和社会风俗等各种背景。这也正是艺术史研究进入人文社会学科范畴的重要因素。
与艺术史研究中关注思想意识的趋势相对应的是,思想史领域也开始倡导运用图像资料,拓宽视野。思想史朝着与社会生活史结合的方向发展,并强调思想如何在政治、宗教、社会背景中产生。葛兆光先生提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们应该重视图像资料的价值,并指出图像资料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辅助文献和用作“图说历史”的插图,也不仅仅是艺术史的课题,而是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隐藏了信仰、观念和价值。(41)这些问题和思路体现出当前思想史学界与艺术史研究的互动。
思想史引入新的材料,既是学者的有意为之,也是客观条件使然。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简帛文书的出土,为人们揭示了“经典”遮掩下日常生活和信仰世界的面目,同时又为不少曾被定论为“伪书”的著作恢复了名誉,使它们成为思想史的证据。(42)其次,许多学者认识到,如果仅靠文献材料,则难以充分了解中国人的信仰与思想。作为传达心声的工具,视觉形象与文字同等重要,有时甚至比文字还要重要。例如,姜士斌(David Johnson)提出,研究者应该考虑到古代中国绝大多数人是半文盲或文盲,图像材料因此在思想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43)
视觉图像可以补充思想史研究中的资料。葛兆光的著作《中国思想史》,其中“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背景和一般思想水平”一节建立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使用了马王堆帛书帛画的内容。在谈到考古发现中重现的秦汉时期的普遍知识背景,他还通过帛画与画像砖来分析秦汉时代人们心目中的三个世界,以铜镜铭文中表现的各种观念来讨论时人关于生死、幸福、子孙的观念以及他们心目中民族国家观念的生成与确立。(44)蒲慕洲在讨论汉代死后的世界观时,也以墓葬建筑形制、随葬品等作为研究资料。(45)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书写汉代的思想、文化与信仰时,也充分利用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展开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描述。(46)思想史学者通过研究图像材料,倡导对于非精英思想状况变化的关注。这些新的史学取向,极大地拓展了思想史的研究空间。
另外,图像资料还不断向研究者提出思想史的新问题。邢义田的《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释》一文通过分析汉画石上的一个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题材,既讨论了艺术创作的格套,又考虑到汉代“复仇”的观念,涉及儒家经典的理解,进而上升到秩序与自由、家庭与社会的层面。(47)比利时的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通过大量版画、绘画、地图、建筑等视觉材料,探讨中西之间的接触,以及近代中国如何接受和面对天主教以及欧洲的科学、思想、观念。(48)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著作表明,学科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艺术史与思想史学科之间对话的基础日益扩展。一方面,艺术史研究关注图像体现的思想含义,而另一方面,思想史也不断拓展视野、扩充材料。在这种趋势之下,思想史与艺术史研究在很多时候已经很难划分畛域。两者在关注的问题、选择的材料方面不断靠拢,艺术史家开始转向非经典的艺术作品,(49)探讨它们如何反映日常生活、文化、思想和信仰世界,这些也是思想史学者们的研究方向。两者在面对古代艺术品时,有时也会采用相似的方法和思路,来诠释历史中的图像。在撷取资料的时候,他们的身份,时而像一个具有历史知识的艺术家,时而又像一个涉及艺术的历史学家。而在解释艺术资料的时候,“他们的角色,好像既是艺术史家,又是思想史家”。(50)
五、反思跨学科趋势下的图像艺术研究
从思想史方面来看,图像艺术有助于将思想史的视野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视觉文化尤其是考古发现的大量遗存为书写思想史的工程提供了大量材料。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研究在对待、使用图像资料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许多研究者很容易出现“以图证史”的危险,他们用图像来说明文献研究已经做出的论断,或以图像充当文字的插图。这使得历史学科对视觉艺术材料的引用呈现出明显的“史料化”、“文本化”倾向。目前学界流行的所谓“图像证史”,正反映了这一现象。“图像证史”的目的在于强调图像作为视觉语言本身的价值。(51)但学界对“图像证史”的含义多有曲解,往往将图像看成是一种“读”而非“看”的“另类文献”,使得“图像证史”失去了其实质意义。(52)
将图像作历史资料的研究者很多,但问题是他们经常把内容放在首位。许多研究者入手便分析图像的内容,试图从画面里直接观察到某种历史,而不去考虑图像的构图、线条、色彩、比例等等。换言之,他们往往将图像材料放在自己学科的视野中进行讨论,忽视了视觉艺术的风格、技巧,或是其本身的艺术史脉络。然而,图像艺术具有传统和特性。不论是丝织品、瓷器、金银器等日常器物,还是墓室装饰、随葬品、寺观壁画等,均具有礼仪功能的视觉艺术,它们通常为工匠所制,拥有独特的设计与制作的传统。与文字一样,许多画面中的内容,也存在着程式化、格套化的部分。(53)例如,墓葬壁画中虽有大量描绘墓主生活的场景,但这些画面并不一定表现了现实生活。如何看待这些画面和构图,图像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对生活的记录,或是赞助人的选择,或是工艺制作传统的格套,这些都值得仔细地推敲。因此,使用图像的证据,应该回到其所在的美术史的传统中,去试图理解艺术品本身的特征。事实上,一些被历史研究者忽视的较为程式化的艺术表现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可能暗含了更多的历史信息,反映出深远的文化传统。面对“以图证史”的问题,葛兆光曾明确指出,思想史家应该重视图像资料本身特征的研究,需要探讨如何从图像本身的特征中观察到有趣的思想和观念。(54)
另外,史观、材料、问题、方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图像资料的使用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史学观念的基础上,而新的艺术品或考古发现也可能会带来史观或方法论的改变。然而,部分历史研究著作存在的倾向是将图像材料放置在老框架下考察分析,缺乏对图像艺术总体性的把握。这样一来,图像既不能作为第一手史料去阐明文献记载无法记录、保存的史实,也无法激发文献未能涉及的历史观念。
从艺术史方面来看,图像研究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与尴尬。首先,在“以图证史”问题的反面,是艺术史学科中“以史证图”的危险。一些研究者通过文献记载来诠释图像,把文献记载当成是印证视觉艺术的特殊材料。这一问题的症结可能在于图像的形式和意义之间,即认为所有的符号与图像都是存在含义的。然而,艺术作品中的许多母题或纹饰在传播、演变过程中已经丧失了其最初的象征意义,在许多情况下只具有装饰性功能。赫伊津哈早在《中世纪的衰落》一书中就告诫研究者不要在图画与文本之间无节制地寻找对应。这种方法既无法解释文字,也无法说明图像,只会扭曲文字与图像。(55)因此,防止对图像材料的过度诠释,以及避免无节制地寻求图像与文本间的联系,都是艺术史研究者应该注意的问题。
其次,一些艺术史论著,在与对方学科交叉时,往往忽视对方学科的学术传统,既没有充分地利用思想史、社会史或是宗教史的研究成果,也不去关注对方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试图仅仅通过对图像艺术的分析、解读,理解艺术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文化与观念。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来说,可以归结为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者个人的知识背景、思维方式以及治学态度,但深层次的原因,是不同领域的学科定位的差异。
再者,国内的一些艺术史著作,在使用自身的学科方法时也往往容易陷入误区。例如,分析图像的视觉语言时,形式分析常常局限于美与丑、雅与俗等方面的探讨,将“风格”理解为一个审美名词,不太注重对艺术形式语言的把握。“风格”一词,作为艺术史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后,就存在着许多问题。西方的形式分析与中国不同,更多是和美学、哲学联系起来,往往无法单独研究。沃尔夫林认为艺术形式可以脱离艺术家而存在,他试图创造一套抽象的形式发展规律,强调艺术与时代的关系。(56)但国内早期的图像艺术的形式研究很少把艺术与时代、社会联系起来,仅仅是进行审美意义上的阐释,将形式分析方法与中国传统画论中的品评术语混为一谈。这造成了国内美术界对于“风格”概念的把握停留在主观感受与经验之上。
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无疑丰富了艺术史研究的内容,但在这样的趋势下,一些学者开始忽视自身的传统,提出“中国画应被看作复合的、多元的或者多视角的……无需强调某种绘画的总体细化或者无用的类型化”。(57)这类不重视图像艺术类型化的做法使得传统的鉴定方法、形式风格分析,被一些所谓“新艺术史学者”视为陈旧或过时的东西。黄厚明在《什么是艺术史?为什么是艺术史?》一文中表现出对艺术学科危机的担忧:艺术史如果一味地接受外来学科的概念、术语、范式及旨趣,仅仅仰仗其他学科的准则才能确立其作为学科存在的价值,那么艺术史家的身份和立场何在?(58)的确,如果失去自身的方法与定位,艺术史研究又应如何与思想史或其他人文学科进行对话?如何为对方学科提供新的视角?我们是否需要确立一种新的认知和观察角度来维系自身体系的独立性?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
笔者认为,在学科淡化的趋势下,研究者们仍然有必要对自身方法论与学术传统进行界定与发展。任何一种“新史学”都应着意于对“旧史学”的扩充与建设,而不能置过往的研究于不顾,人为地造成学术断层。艺术史的研究也应如此。跨学科趋势下的新艺术史研究在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不能回避“旧”的问题,或彻底抛弃传统的方法、理论。艺术史要想成为独立的人文学科,要想进一步发展,就不能脱离对图像视觉语言的分析研究,忽视对作品本体语言的解读。只有立足于传统的艺术史方法论,研究者们才可以将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与图像艺术的形式和风格分析打通,在一个新的平台上重新考察艺术作品的视觉语言。对图像艺术的讨论,一方面可以通过风格分析、图像学等方法探求作品所表达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图像视为特定文化情景中的象征物,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审视。艺术史研究不仅要注意主体在艺术形式中如何呈现,也应将艺术作品的视觉分析还原到其所生成的历史场景中,进而理解视觉语言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
六、结语
上述关于图像艺术研究理论或是在思想史中使用图像资料等方法的讨论,都是对目前人文学科内部跨学科研究的探讨和审视。研究者既需要扩宽视野,思考新的问题,注意到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学术脉络,同时又不能脱离自身学科的学术传统,对“旧”的方法论进行推动与发展。艺术史研究只有重视和把握图像在文化脉络中的特征与意义,才能彰显出这一学科的独特品质。
早在1869年,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J.G.Droysen)发表的论文《艺术和方法》,就已经提出了一整套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技术的、社会的、形式分析的和文献批评的。事实上,直到20世纪西方学者们才真正在实践中使用这些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德罗伊森强调,艺术史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必须熟悉所研究的时代和观察事物的方法,熟悉研究材料的一般知识范围,这样他们才能解释隐含在艺术作品和相关事物中的意义。艺术史的方法与研究一般历史的方法同等重要,而所有这些方法:
在历史研究的王国里共同发挥作用,在相同的边缘运转,占据同等重要的中心。把它们在共同的思想中联合起来,发展它们的理论体系,但并非要建立客观历史的法则,而是要寻求历史调查和历史知识的法则——这便是历史的任务。(59)
注释:
①李淞:《代序:研究艺术的考古学家或研究图像的历史学家》,收入氏著《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8页。另外,李淞在讨论中国美术史学的发展与走向时,也提出将“图像”而非“美术”作为美术史学科研究的主要对象。“图像”一词比“美术”一词更加宽泛,前者倾向于描述对象的自然物理属性,而后者则明显强调其人文属性。就词汇表达的客观性而言,“图像”在理解力的角度更具公共性。当学科对象为“图像”时,学者们会感到更大的自由,并产生更具公共性的对话空间。
②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追溯了西方思想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运用图像材料理解历史的传统,并提出19世纪西方新史学的重要特征就是将艺术风格视为特定民族、时代的社会与精神索引。参见:Francis Haskell,History and Images:Art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ast(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3)201-216。
③布克哈特著,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页。该书并没有讨论任何艺术作品,但是依据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布克哈特通过艺术知识发展了自己对文艺复兴历史的解释。
④E.T.Cook and Alexander Wedderburn eds.,The Works of John Ruskin(London,1903)203.
⑤曹意强:《图像与历史:哈斯克尔的艺术史观念和研究方法(二)》,《新美术》2000年第1期,第62—63页。
⑥Hugh Trevor-Roper,Princes and Artists:Patronage and Ideology of Four Habsburg Courts 1571-1633.转引自曹意强:《图像与历史:哈斯克尔的艺术史观念和研究方法(二)》,第63页。
⑦瓦萨里著,刘耀春等译:《意大利艺苑名人传》,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3年。
⑧温尼·海德·米奈著,李建群等译:《艺术史的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0—114页。
⑨沃尔夫林著,潘耀昌译:《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⑩李格尔著,刘景联、李薇蔓译:《风格问题》,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11)潘诺夫斯基著,戚印平等译:《图像学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人文主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12)白巍:《从西方几种艺术史研究方法看中国绘画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144页。
(13)“美术”是从日本传入的一个译词。这个词语最初被引入中国时,曾囊括现代艺术中的许多门类,是一个比“造型艺术”范围更广的概念。例如,王国维、严复等学者对美术的定义与康德之后的“美的艺术”体系相吻合,包括文学、音乐、美术等给予人类精神美的启示的门类。见曹意强、罗戟、薛军伟:《国外艺术学科发展近况》,《新美术》2008年第6期,第5—6页。
(14)(宋)郑樵:《通志·图谱略》,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825页。
(15)薛永年:《导言·滕固与近代美术史学》,收入沈宁编:《滕固艺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5页。
(16)有关讨论,见郑岩:《论“美术考古学”一词的由来》,《美术研究》2010年第1期,第21页。
(17)近代中国美术史著述的回顾,参见薛永年:《反思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的美术史写作谈起》,《美术研究》2008年第2期,第52页。
(18)郑岩:《论“美术考古学”一词的由来》,第21页。
(19)陈葆真:《美育的意义与实践》,收入罗凤珠编:《人文学导读》,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第102—119页。
(20)沈宁编:《滕固艺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4页。
(21)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17页。
(22)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255—260页。关于“新史学”运动对美术史研究的影响,参见孔令伟:《“新史学”与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兴起》,《新美术》2008年第4期,第49—59页。
(23)郑振铎:《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跋,收入氏著《郑振铎艺术考古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24)郑岩:《论“美术考古学”一词的由来》,第22页。
(25)黄厚明:《什么是艺术史?为什么是艺术史?——方闻先生中国艺术史研究札记》,《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80页。
(26)Jing Anning,The Water God's Temple of the Guangsheng Monastery:Cosmic Function of Art,Ritual,and Theater(Leiden:Brill,2002).
(27)柯律格,刘宇珍等译:《雅债:文征明的社交性艺术》,台北:石头出版社,2009年。
(28)乔迅著,邱士华等译:《石涛——清初中国的绘画与现代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29)范景中、曹意强:《序言》,《美术史与观念史》2006年第1期。
(30)关于观念史对西方艺术史的影响,参见曹意强:《什么是观念史》,《新美术》2003年第4期,第51—52页;《观念史的历史、意义与方法》,《新美术》2006年第6期,第29—48页。
(31)Jessica Rawson,"Han Dynasty Tomb Planning and Design",Actes Des Symposiums Internationaux Le Monde Visuel Chinois.eds.Chrystelle Maréchal and Yau Shun-chiu Numéro Spécial No.2(Paris,2005):103-116.
(32)罗森著,孙心菲等译:《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3)罗森著,邓菲等译:《祖先与永恒——杰西卡·罗森中国考古艺术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34)巫鸿著,柳杨等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35)巫鸿“中间层次”的美术史研究,被许多学者所接受,它既不同于“低层”研究对个别器物或图像的关注,也不同于“高层”研究对整个艺术传统的宏观思辨,在于联结图像与文献、艺术作品与社会。
(36)巫鸿:《“明器”的理论和实践——战国时期礼仪美术中观念化倾向》,《文物》2006年第6期,第72—81页。
(37)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09—235页。
(38)邹清泉:《北魏孝子画像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
(39)李清泉:《宣化辽墓:墓葬艺术与辽代社会》,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
(40)德沃夏克著,陈平译:《作为精神史的美术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41)有关思想史研究对图像的运用,葛兆光先生已就图像材料的范围与使用方法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参见《思想史视野中的考古与文物》,《文物》2000年第1期,第74—82页;《思想史视野中的图像》,《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74—83页;《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开放时代》2003年第4期,第60—69页。
(42)王东杰:《重写思想史》,《读书》2001年第1期,第116页。
(43)David Johnson,"Communication,Class and Consciousnes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s.Johnson et al(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34—72.
(4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45)蒲慕洲:《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46)鲁惟一著,王浩译:《汉代的信仰、神话和理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Michael Loewe,Ways to Paradise:The Chinese Quest for Immortality(SMC Pub.,1994)。
(47)邢义田编:《中世纪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与艺术》,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第183—234页。
(48)钟鸣旦:《中欧“之间”和移位——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图片传播》,复旦大学文史讲堂讲座。
(49)传统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存在着“经典化”的状况,这与博物馆的收藏、美术史教育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参见巫鸿:《“经典作品”与美术史写作》,《读书》2006年第6期,第81—87页。近年来的美术史著作呈现出“去经典化”的走向,预示着新一代美术史研究重点的转移,从对名家名品的讨论转向对多种视觉形式以及社会文化的理解。
(50)葛兆光:《思想史家眼中之艺术史》,第30页。
(51)曹意强:《图像与历史》,《新美术》2000年第1期,第61—77页;《可见之不可见性:论图像证史的有效性与误区》,《新美术》2004年第2期,第7—13页;《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实例》,《新美术》2005年第2期,第24—38页。
(52)黄厚明:《什么是艺术史?为什么是艺术史?——方闻先生中国艺术史研究札记》,第81页。
(53)缪哲已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见缪哲:《以图证史的陷阱》,《读书》2005年第2期,第140—145页。
(54)葛兆光:《思想史视野中的图像》,第74—83页。
(55)Johan Huizinga,The 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trans.Rodney Payton and Ulrich Mammitzsch(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56)贡布里希:《论风格》,收入范景中编:《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
(57)文以诚:《中国画的终结》,收入《2002年东亚绘画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2002年,第424页。
(58)黄厚明:《什么是艺术史?为什么是艺术史?——方闻先生中国艺术史研究札记》,第80—82页。
(59)转引自曹意强:《图像与历史:哈斯克尔的艺术史观念和研究方法(二)》,第70页。
标签:艺术论文; 思想史论文; 图像学论文; 社会互动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美术论文; 名人传论文; 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