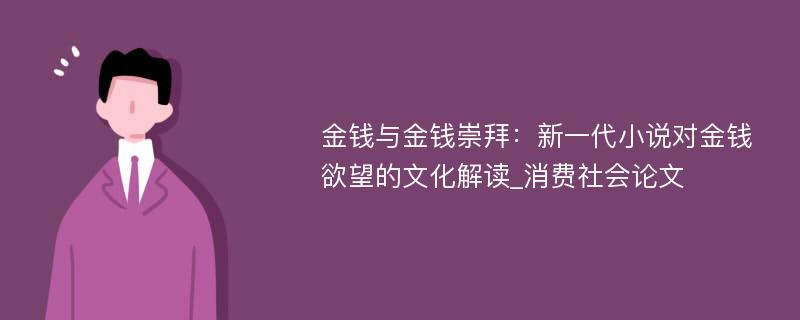
金钱和金钱崇拜——新生代小说中金钱欲的文化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钱论文,新生代论文,崇拜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与文化迅速变迁的事实,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出现在文学家面前,随着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农业型走向工商型,旧有的价值和审美观开始崩溃。如果说80年代张贤亮、王安忆等人对性欲的表达是当代文学对欲望禁区的第一次突破的话,那么,90年代新生代作家何顿、邱华栋、朱文等人的小说就以对金钱欲的认同和表达,实现了对欲望禁区的纵深挺进和突围,并由此赋予了他们小说以先锋性意义。
一
市场经济社会中以金钱为中心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的生活领域,无疑是当代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社会中最具活力的领域。这里不仅涌动着经济资本的浪潮,也奔腾着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的波涛,它们相互撞击相互融合形成的合力,为我们拓展出了前所未有的璀璨夺目的文化景观。正因为如此,何顿、邱华栋、朱文等新生代作家从利欲的方位上切入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分析中国当代社会经济和价值观念变化的最佳视角。
在何顿、邱华栋、朱文等新生代作家的小说中,金钱欲作为人类最强烈的基本欲望之一,在以赢利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不断为市场经济所刺激和调动,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驱动作用。发财致富,成为这些新生代作家小说中人物的共同心理和追求。在朱文《我爱美元》中,主人公“我”“渴望金钱,血管里都是金币滚动的声音”。这种对金钱的渴望,使他觉得:“尊敬这玩艺太不实惠了。我们都要向钱学习。”在何顿的《无所谓》中,不仅罗平、王志强等“对知识不感兴趣”,“在一起谈论的是赚钱”,“赚钱”才是他们的“正事”,就是一直在追求理想,企图在追求理想中“找到自身的价值”的李建国,在现实环境的逼迫下,最后也不得不为金钱而奔波、劳碌。在这里,人的精神追求被一种实利主义所取代,实利主义将人的一切需要都简化成对“金钱”“实惠”的需要。这种价值判断显然根源于一种“金钱意识”。这种“金钱意识”作为何顿、邱华栋、朱文等作家小说中人物的一种人格准则,成为判定人物是否成功的先决性条件。也就是说,愈成功的人就愈有钱,而没有钱的人的人生则注定是失败的人生。这种以“金钱意识”来衡量人的价值准则,无疑强化了何顿、邱华栋等作家小说中人物急于摆脱贫困的焦灼心理。既然成功与金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么,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经济上贫困而精神上优越就不可能完全赢得人们的钦羡。朱文的《我爱美元》中,主人公“我”认为:“与金钱的腐蚀相比,贫穷是更为可怕的。”在这种以金钱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没钱的人,不仅会像何顿《弟弟你好》中的“弟弟”那样,“因是穷教师被同学忘记在一旁”,而且也会像邱华栋《生活之恶》中的尚西林那样,由于“不仅没有钱,也没有权力、荣誉感和其他任何让他能感到骄傲的东西”,惧怕失去相爱了四年的女友眉宁。为了摆脱这种对贫困的恐惧的焦虑,使自我进入成功者的行列,“弟弟”、尚西林等将获取和占有金钱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不择手段地加入到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竞争与搏斗中。
在这种利益的竞争与搏斗中,“弟弟”、尚西林等的行为是以“利己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于是,金钱的诱惑和个人利己主义相纠缠,形成一种超社会、支配人们命运的神秘力量,随着“弟弟”、尚西林等求金者求金行为不断深入和展开,求金者们心理就会呈现出一种递进性的形式。“弟弟”等求金者获得的财富愈多,他们的求金心理就更加膨胀。这时金钱对求金者表现为一种强迫力量,它驱使着“弟弟”等求金者不断向敛财聚财的下一个目标奋斗。这种聚财敛财心理膨胀速度之迅猛,有时甚至是求金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邱华栋的《哭泣游戏》中的黄红梅,当初从偏僻的山区来到繁华的京城时,她的目标是“想挣一点钱,回到四川家乡去养猪、种花”,一旦她经营餐饮业挣到很多钱后,她又觉得“对我来讲,我是赚了很多钱,但这还不够。”她的金钱欲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在经营餐饮业的同时,又经营娱乐业和房地产业。何顿的《太阳很好》中的宁洁丽,从医院辞职来到龙百万的百叶窗厂,是因为龙百万的百叶窗厂的工资比她原来工作的医院的工资高出一倍多,然而,随着与龙百万的关系不断加深,她“暗暗有那种把龙百万占为己有的想法”。而将龙百万占为己有的心理根源,则在于对龙百万百万钱财的觊觎。对这种求金行为的递进性,仅仅用“贪婪”去揭示黄红梅、宁洁丽等求金者的心理根源是难以全面和深刻的。事实上,在贪婪的外在形式后面,黄红梅等人这种求金行为的递进性往往潜藏着求金者对安全感的渴求和梦想。黄红梅等求金行为的驱动力来源于他们对贫困的恐惧,而对贫困的恐惧又是与人们对安全的渴求相联系的。当黄红梅等在贫困时,他们的目标是为自己赚取足够维持基本生存权的钱财,以获取一种安全的感觉。然而,一旦进入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黄红梅等求金者要想获到安全感,就必须压倒对手。于是,要达到安全感所需的钱财就这样逐渐增加,而金钱作为一种等价物,又具有一种不能满足人的特点,这样,寻找安全——寻找金钱——寻找安全就形成了一种周期性循环过程。这种寻找金钱的周期性循环过程虽然并没有给黄红梅等求金者带来实际意义上的安全感,然而,求金者在周期性求金过程中不断出没的市场经济社会空间,却提供了一种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中远不具备的个人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是二位一体、没有分离的,一个人,诸如何顿《无所谓》中的李建国等,一旦被政治体制所抵制和排斥时,就意味着他们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的丧失。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和社会开始出现分离,一个市场经济社会的空间开始形成,这种市场经济社会空间作为一种以追求现实利益为核心的相对自律的空间,它是以肯定和保护私人化的经济关系的面目出现的。在这个特定的社会空间中,黄红梅等个人对金钱递进性追逐的欲望,不仅不会被斥之为“贪婪”而加以排斥,反而成为进入这个社会空间必备的资格和条件而被认同和肯定。正如朱文的《我爱美元》中写的那样:“后来货币就日益重要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它无与伦比的媒介作用赋予了我们更多的避免被埋没的机会,所以,我们要尊重钱,它腐蚀我们但不是生来就是为了腐蚀我们的,它让我们骄傲但它并不鼓励我们狂妄,它让我们自卑是为了让我们自强。”于是,市场经济社会空间在给人们提供摆脱国家控制的依附型人格的最佳途径的同时,也使人们体验到了经济独立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私人性的生存自由。正是市场经济社会提供的这种经济独立和私人性生存自由的空间,使何顿《无所谓》中的罗平、王志强,《弟弟你好》中的“弟弟”,邱华栋《生活之恶》中的尚西林、罗东,《别墅推销员》中的沈方等人脱离了传统体制的控制,毅然投入到市场经济社会竞争的洪流中。在这种充满自由竞争和搏斗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王志强、“弟弟”等去除了往昔身上的沉沉暮气,而重新焕发了一种自信自强的生机。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利益竞争者,“弟弟”、王志强等遵循的只能是市场的竞争法则,一种新的人与人的交往原则,即契约原则。在契约原则支配下,利益主体的个人私欲在市场经济社会空间自由释放时,也理应给予其他个体的私欲以同样的自由权利。这种契约原则生成的市场交换原则自然对计划体制下政治权力导致的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进行了瓦解,在金钱面前,人们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刘继明的《可爱的草莓》中写道:“佴城是一个没有同情心的城市,有的只是那一套冰冷冷的生存原则。在此原则面前,每个人都一视同仁。”任何人,只要他拥有足够他消费的金钱,他就可以买到过去普通大众无法接触的商品。邱华栋笔下的外来妹黄红梅就能够在京城购买“价值几千万元的大别墅”,与京城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平等地交易与竞争。
然而,倘若求金者像《我们像葵花》中的冯建军、《弟弟你好》中的刘金秋那样片面地追求私人性的生存自由,不择手段地去获取金钱,那么,他们就必定会损害和剥夺其他利益主体的私人性的生存自由。另一方面,人们的需求是多方面的,追求金钱和财富并不是人唯一的需要,冯建军等将人的需求限定在无止境地追逐金钱上,这就意味着他们需求的单一化和片面化,他们在将金钱当成自己唯一需求时,也使自己沦为金钱的奴隶,他们拜倒在金钱面前,将物作为自己的灵魂。更为严重的是,在市场经济社会,契约式的交换关系对精神价值的遮掩和忽视,使冯建军等求金者对人生价值和事物价值的取向都围绕着金钱来展开,并以金钱作为衡量标准,这就潜伏着他们将一切都视为可用金钱购买的商品的危险,使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为赤裸裸的物与物的利害关系,最终将导致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商品化和金钱本位化,使新生而又脆弱的交换关系中的契约原则的平等性崩溃和瓦解。
二
金钱欲的解放和对金钱的追求与获取,在成为何顿、邱华栋、朱文等新生代作家小说的重要母题时,一种快乐原则也成为他们小说的主要审美原则。在他们的小说中,金钱欲,既是推动人们追逐金钱和财富的驱动力,也是推动人们进行消费和享受的动力。随着赚钱欲望的不断满足,人们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也在不断膨胀和延伸。这种不断膨胀和延伸的消费心理,在极大地唤起人们的享乐感的同时,也将消费和享乐的生活方式等被传统理想原则支配下的文学所拒斥的东西转化为文学中全新的审美内容。
在何顿、邱华栋、朱文等的小说中,世界已成为一个巨大的填充我们胃口的物品,人的快乐的获得与增长,是与人们消费的增长成正比例的。消费的物品愈新奇,人们获得的快感就愈强烈。于是,在这个以消费和享乐为荣的世界里,刺激性与娱乐性代替和遮掩了文学的其它功能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功能。在何顿、朱文、邱华栋等人的小说中,这种刺激性与娱乐性追求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对物质的高消费。对于何顿《我们像葵花》、《无所谓》和邱华栋的《生活之恶》中的冯建军、王志强、罗东等人来说,都市的时髦就在于不断对最时髦东西的消费。而每一次对时髦东西的消费又意味着新的经验的形成。在小说中,王志强、罗东等不仅追求新的味觉刺激,而且也追求新的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的刺激。他们穿的是“意大利名牌‘胡利奥’牌西服”(《生活之恶》),或是“貂皮披领的意大利羊皮夹克”(《太阳很好》);戴着的是“价值18万元的翡翠塔链珠项链”(《生活之恶》),或是“金耳坠坠子上镶着两颗黄豆大的红宝石”(《太阳很好》);出入的是豪华宾馆、酒店、咖啡店。他们的味觉所及,则常常是“蚝油鲍片、干烧海参、红烧熊掌”(《生活之恶》)。可以说,无论是视觉形象的消费,还是味觉形象的消费,都极大地突现了刺激性和新奇性,而且,在小说中,这种带有强烈刺激性和新奇性的感官形象往往交织在一起,给“弟弟”、吴雪雯等人带来心理上极大的快感和满足。金钱在消费过程中具有的这种巨大的象征性功能,也自然使冯建平、罗东、吴雪雯等人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幻觉心理,那就是,在这个物质繁荣的社会里,一个人只要拥有金钱,他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买到他想要的一切。朱文的《我爱美元》中的主人公“我”认为:“欢乐从来不是什么希罕之物,只要你有钱,没有的东西都可以为你现做一个。”一个人有钱,他就可以像邱华栋《手上的星光》中的杨哭那样,将一群曾经红极一时的明星们请来为一家“并不起眼的信用社”的成立捧场;一个人有钱,他就可以像刁斗《证词》中的高民生那样,让“省内要人”为自己的一家小书店泼墨书写店名;一个人有钱,即使他没有任何官衔,也可以像邱华栋《音乐工厂》中的空气音乐制作公司的何可那样拥有社会权力;一个人有钱,即使他相貌丑陋,他也可以像毕飞宇《睁大眼睛睡觉》中的大龙头那样,拥有无数天仙般美丽的女人。无庸置疑,金钱作为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它确实可以买到一切商品,而且,靠金钱开路,既可以像何顿《弟弟你好》中的“弟弟”那样买通一些人为自己办事,而且也可以像邱华栋《哭泣游戏》中的黄红梅那样使自己身价倍增。然而,金钱作为一种商品等价物,它可以买到的也只可能是商品,而不可能买到商品以外的理想、爱情和幸福。邱华栋的《生活之恶》中的罗东,在第一次失恋时,“发誓要拥有财富,因为只有拥有了财富他才可能去任意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几年以后,他成为拥有两千万元资产的巨富,当他带着价值几十万元的项链和戒指去向吴雪雯求婚时,吴雪雯却只愿做他的情人而不愿做他的妻子。情感和自尊再次受挫后,他又以财富为诱饵,诱惑和挑逗眉宁,最终虽然赢得了与眉宁的一夜之欢,却仍未赢得眉宁的爱情。最为荒诞和滑稽的是,尽管罗东用金钱并未买到爱情,他却在与眉宁的性消费中获得了“快乐”的满足。然而,这种消费的满足作为化解他心头“自卑、懦弱和胆怯”的产物,弥补和掩盖不了他那没有爱情滋润的空虚的心灵。究其本质,这种性满足只是一种被动的、缺乏感情的幻想性满足。在何顿的《我们像葵花》《弟弟你好》、邱华栋的《哭泣游戏》《生活之恶》等小说中,冯建军、刘金秋、黄红梅、吴雪雯等的这种有钱可以买到一切的幻觉,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反而葬送了他们的前途和生命。
这种由人物心理对金钱的幻觉带来的人物行为和小说情节的荒诞性,使何顿、邱华栋等以金钱为母题的小说往往具有较为浓厚的喜剧性色彩。之所以说具有喜剧性,是由于这些小说中的汉建军、黄红梅等人在中断了对形而上的理想精神的探寻之后,原来作为手段的消费却成了冯建军等人的目的。这样,当冯建军、罗东等人以为他们凭借金钱征服了别人时,实际上他们征服的仅仅是商品化了的人。于是,虚假的目的在耗尽了他们力图满足需求的精力时,并没有带给他们实际意义上的快乐和满足,反之,给他们带来的是对生活的无意义感。邱华栋的《哭泣游戏》中的华仔,在用金钱寻求“神秘而又刺激”的消费后,便“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厌倦袭来”。这种厌倦和无意义感转过头来又迫使他们将自己的生活在无历史的瞬间中化成一次又一次纯粹的娱乐,在光与影的游戏和消费中,他们自身存在的不完美性被遮掩和忽视,被动地作了金钱的奴隶,在金钱面前丧失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和思考能力。冯建军、吴雪雯、黄红梅等人也有痛苦,但这种痛苦并非来源于自我对本体价值的追问造成的心灵冲突,而是来源于追逐金钱时的焦虑和用金钱消费后的无聊以及金钱丧失后的茫然。因而,即使他们死亡了,由于这种死亡被抽空了理想等精神性内容,悲剧就转化为一种极具观赏性的欲望化场景,它使人感到刺激,却并不令人震撼。
崇尚消费的快乐原则,在政治一体化的时代曾经长期遭到理想原则的压抑和控制。何顿、邱华栋、朱文等的小说对这种审美原则的突出与强化,标志着一种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新的审美原则的崛起。随着计划经济的结束,长期困扰人们的贫穷、物质匮乏的问题已基本解决,鼓励消费,已成为国家的基本经济政策。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追求快乐和幸福的权利,何顿、朱文、邱华栋等的小说中对“快乐原则”的认同,既是对人性的基本权利的肯定,也合乎一种时代潮流和风尚。不可否认,这种将个人快乐和幸福作为善的前提的审美原则,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世俗的既平凡又适意的色彩,显示了他们小说审美视角的独特性。正是何顿、朱文、邱华栋小说中的主人公们对消费和快乐的不断追逐,才使他们的平庸的生活变得不可预测而显得生气勃勃。然而,消费的活动应该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全面活动,消费的过程理应富有人性、意义感和创造力,只强调快乐原则,不重视理想原则,人们就会像邱华栋、何顿等人小说中的吴雪雯、冯建军、刘金秋那样,囿于现实而无法超越,由于没有理想之光的照耀,就会目光短浅,只图及时行乐,最终在葬送了幸福的同时也葬送了自我。
三
新生代小说的独特性不仅来源于他们对新的审美原则和审美内容的展示,而且也来源于他们小说中“说话者”对于这种审美原则和审美内容的认同。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马克·吐温等作家不同,金钱欲在新生代小说中并不是作为使人沉沦的因子受到严峻的理性审视和批判,而是常常作为当下人们的一种生存形象得到认同和肯定。这显示了新生代小说中的“说话者”,不再像巴尔扎克、马克·吐温等人的小说“说话者”那样处于权威性的位置来理解和把握世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文学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边缘人的身份,使他们难以保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那种发现真理的“俯视”眼光,而不得不采取一种与主人公的生存形态保持一致的“平视”眼光。这种平视眼光在拒斥了大众发言人的身份的同时,也拉近甚至消弭了“说话者”与主人公的距离。这种“说话者”与主人公距离的消失而生成的同构关系,使新生代小说具有一种强烈的私人化色彩。在小说主人公的求金“经验”和欲望化的生存“状态”中,我们总能看到作者的某种“经验”和“状态”的影子。何顿先做过教师,后又辞职做过生意,这种生活“经验”与《无所谓》中的罗平、《弟弟你好》中的“弟弟”等主人公的经验具有一种同构性。朱文是自由作家,这种身份与《我爱美元》等小说中的主人公的生存状态有着相似性。何顿、朱文等作家对与自身“经验”与“状态”相关和接近的叙事内容的选择,使一些论者往往将“说话人”的价值观完全等同于作家的价值观而加以指责:“他们对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必须遵从的基本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德都视为寇仇,践踏于地,对西方的没落的颓废主义和极端主义、金钱至上、个人至上、欲望至上特别推崇,大肆宣扬。”(注:余开伟:《文学的蜕变》,《文艺争鸣》1996年第5期。)这种指责显然违背了小说叙述学的常识,因而是难以使人信服和认同的。M·比尔兹利斯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说话者不能与作者划等号。”(注:M.比尔兹利斯:《美学》,纽约英文版,1958年,第240页。)虽然韩东在《弯腰吃草·序》中直言道:“朱文曾这样对我说,真实的写作将和你的生活混为一体,直到我们相互交织、相互感应,最后不分彼此。”即使如此,这时的“说话人”也不是作者本人,而是像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所说的“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这种隐含作者的位置处于叙述者和真实作者之间,他是文本中作者的形象,与真实的作者不同,他并不是具体的而是虚拟的。一个真实的作者可以写两部乃至更多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可能相同,也可能迥然不同。例如,在何顿《生活无罪》、《我不想事》、《太阳很好》等小说中,隐含作者流露出的是对主人公欲望化生存状态的认同;而在《喜马拉雅山》、《荒原的阳光》、《丢掉自己的女人》等小说中,隐含作者却又对理想等精神性价值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认同。显然,依据小说中“说话人”的价值观来指控作家是拜金主义者,是误将隐含作者的价值观完全等同于作者的价值观念了。这不仅会导致我们对小说中隐含作者的功能和意义的忽视,也会影响我们对何顿、朱文等作家小说的价值和意义的全面的认识。
进一步需要阐释的是,如何理解新生代作家的求金动机。新生代作家对他们的求金动机是直言不讳的。邱华栋在与刘心武的对话中坦承:“我本人也非常想拥有这些东西,……我表达了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机会这么多,那么赶紧捞上几把吧。”(注: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作家这种强烈的求金动机,遭到了一些论者义愤填膺的指责:“晚生代某些正在被文坛娇宠的作家对物欲的追求和占有的疯狂欲望极为膨胀,急不可耐。”(注:余开伟:《文学的蜕变》,《文艺争鸣》1996年第5期。)显然,这是将作家的求金动机完全等同于金钱崇拜了。事实上,在商品经济社会里,赚钱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欲望。马克斯·韦伯指出:“获利的欲望,对盈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身上。”(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页。)赚钱的念头人人都有,但有合理的求金观念和不合理的求金观念的区分。像何顿《我们像葵花》中的冯建军、邱华栋的《生活之恶》的吴雪雯、朱文的《我爱美元》中的“我”那样,无限地夸大金钱的价值、作用和重要性,并对金钱顶礼膜拜的观念,显然属于一种不合理的求金观念,因为它无限夸大和神化了金钱的力量和功能。反之,像邱华栋、何顿、朱文等作家,适当地认可金钱的价值、作用和重要性,则属于一种合理的求金观念。这种合理的求金观念是对金钱在商品生产、交换和流通中具有的各种职能,诸如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合理认同。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只有强化这种合理的求金观念,才会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潜能;另一方面,在一切都从现实利益出发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文学作为一种投入市场的产品,在商品经济的关系中是受到价值规律制约的,作家倘要生存,就必须从清教徒式“以穷为荣”的价值观念中挣脱出来,正视自己的欲望,才可能像邱华栋、何顿、朱文等作家那样形成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全新的价值观念和人生态度。反之,简单地排斥或者否定这种求金观念,不仅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必将使文学家的思想丧失物质基础和传播对象。进而言之,即使像朱文《我爱美元》中的“我”那样有着不合理求金观念的人,由于他的求金活动是规范的,就仍然不能将他等同于拜金主义者。判断求金活动是不是规范的标准,是市场的理性规则和道德法律。反之,像邱华栋《生活之恶》中的何维那样的人,表面上有着合理的求金观念,在他的旧情人用两千美元来收购他的“蓝布大短裤”时,他甚至扮演了不为钱财所动的精神牧师形象,对吴雪雯进行了一番人生意义的布道;然而,正是这个瞧不起金钱的何维,在求金行为上却运用了非法的、不道德和不合理的手段,为了赚钱,他可以与女影星做性交易,也可以将自己的情人“发给另一个男人”。这种人,不管他最初的求金动机如何合理,他在行为上却成了货真价实的金钱的奴隶。我们要反对的,就应该是何维等人这种不规范的求金活动。这种求金活动不仅助长人们疯狂的冒险和投机心理,而且将引起人际关系的冲突,最终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相反,理性和规范的求金活动,作为市场经济所蕴含的内驱力,不仅不应被反对,而且应大力倡导和加强。
重义轻利,在农业型社会结构中,一直占据着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这种价值观念,在90年代新生代作家何顿、邱华栋等人的小说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的以金钱为母题的小说不仅带给我们全新的经验、全新的故事、全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和全新的叙述角度,而且也带给我们全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然而,获得与失去从来都是相伴而生的,市场经济社会和新生代小说在带给我们全新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时,也带来了许多不完整的生命形式。不能不看到,金钱作为商品的等价物,它只能保证人的低层次的基本需要,而不能满足人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对金钱和消费的片面追求和强调,造成的恶果是片面发展的“单面人”,这种“单面人”作为金钱的奴隶,显示了人自身的异化和人与社会的异化。人类的发展模式的更新,不能停留在市场经济模式上,而应将生态文化经济发展模式纳入人类的视野,这种生态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将经济与生态、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协调统一,将人类生活的和谐放在首位。因此,我们既要警惕借批判拜金主义而否认金钱的合理功能与重要性,对金钱采取鄙视和与市场经济相抵触的思想倾向,又要警惕借口批判中国传统“重义轻利”观念,从而在“更新观念”的幌子下宣扬金钱崇拜的思想倾向;既重视文学的精神价值,又要重视文学的功利价值,坚持功利价值与精神价值并重的原则。由此,我们才能在人类生存的最大时空范围内,获得人的全面自由和发展,并使人的全面内在目的相统一,进而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