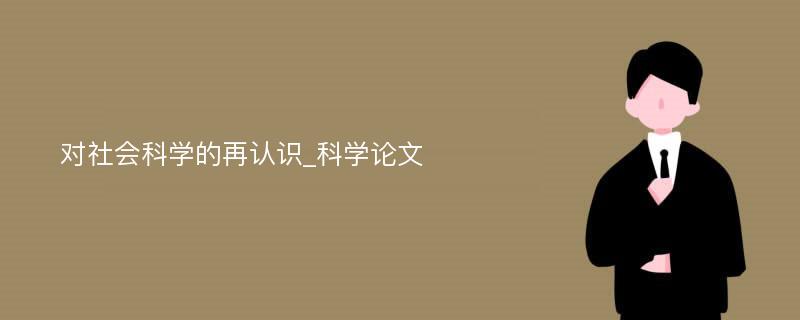
对社会科学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社会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理论界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的探讨已越来越深入,科学技术举足轻重的地位已日益被世人所认识,然而伴随着社会各部门、各地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领域又出现了这样一个“误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指的是自然科学技术,不包括社会科学。究其原因,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便凸现出来:社会科学到底是不是科学?笔者认为这一问题既是解决社会科学是生产力问题的关键所在,又是今天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突破口。笔者在对社会科学作了一番尝试性的研究之后,将自己的粗浅认识呈现于此,一孔之见,期大方之家指教。
一、“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
我们说科学中包括社会科学,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毛泽东早就讲过,世界上的知识有两门,一门是自然科学,一门是社会科学:邓小平也下过定性的论断:“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①;江泽民在中国科技“四大”上进一步指出:“大力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协同”。但是,理论研究是严谨的,它要求有理有据,所以我们应该去寻找导致这个结论的依据。为此,我们必须深化对社会科学的认识。
第一,要进一步理解马克思关于“科学”的论断,深化对社会科学的认识。
恩格斯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②马克思本人也预测:“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就象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首先,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基础,即人、社会与自然界的统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就是建立在这个共同基础之上的。自然界对人类社会保持着优先地位,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了人,人类社会便也随之产生。人既然是自然界的产物,它就当然包含着自然属性和自然物质的运动规律,人的意识也有其自然基础,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也不是赤裸裸的人对人的关系,而是在改变自然界的物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并以物质为中介的。自从出现了人和社会以后,自然和社会就处在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统一之中。人类社会是“人化了的自然”,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在它之中就以某种特殊形式包含着自然界及其运动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把物质运动形式划分为由低级到高级的五个层次: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社会运动。这五种运动形式不仅相互区别,而且相互联系。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又以扬弃的形式包含前者。前四种运动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内容,而后一种运动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既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有着共同的基础,既然将认识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归为科学,那么也理应将认识社会规律的社会科学也归为科学。
其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本质统一是由实践完成的。表现在从“自在的自然”变成“属人的自然”。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的自然界不断地向人的生成过程。在具体的实践中,一方面,人的目的实现出来,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自然界中,自然界被人化,社会化;另一方面,人在把自己的目的、愿望要求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同时,人和社会被自然化。在这种转化中,自然界的属性和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属性和规律是相互渗透的。由此可见,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既离不开对关于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的运用,也绝对缺少不了对关于社会规律的社会科学的认识。二者之中缺少任何一个,人类实践活动都无法持续,既然人类实践必须“两条腿”走路,在给自然科学以科学的美誉之时,将社会科学称为科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二,从社会科学的发生和独立,来深化对社会科学的认识。
人的主体地位一旦确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便相继地发生和独立了。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最初,人与自然界、动物界混沌未分。只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制造工具开始,开始了向文明进化的艰辛历程,最终使得自己从自然的一员上升到主体的地位。在众多的实践中,生产劳动是最基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还是他人生活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③正是由于这双重关系,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人的主体地位确立之后应运而生,相继发生和独立了。主客体结构可分为从低级到高级两个层次。一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形成的人与自然的主、客体结构:即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它所表现的关系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自然关系”,这是种最初的低级的形式。这种以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为轴心的人与自然的主客体关系便是自然科学产生的前提。二是建立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人与社会的主客体结构,起初以个人与社会对立的异化形式出现,但它却是社会科学产生的基础。后来人是主体,人或人的活动是客体,这种结构是关于“人的科学”产生的基础,人本身解放和全面发展此时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对象,而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关于人的科学就是这种含义。广义的社会科学当然包含着关于人的科学。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种认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人的科学)不但是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且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产生都是建立在大量重复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认识的飞跃。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都能达到“科学”的认识,只不过二者各有其特定的条件和途径。
二、社会科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马克思曾指出:“一般的社会知识已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生产力。”④可人们在接受自然科学是生产力时显得比较容易,而在接受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时,却显得很艰难。原因何在?主要还是不能把握社会科学自身的特殊性,而仅仅把社会科学只理解成一种意识形态,认为它是与反映客观现实的科学格格不入的。
第一,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
提起社会科学,人们很容易将它归结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认为其数量化程度低,精确性差,科学性很难保证,称为科学很勉强。确实,社会科学有着许多反映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可这仍然不足以说明社会科学是非科学的,在下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弄清问题的症结——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它们到底是对立的,还是同一的?对此西方理论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
法国的技术统治者雷蒙·阿隆和美国的丹尼尔·贝尔是最早对此表明立场的。他们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观点,即意识形态应该终结。他们是这样铺展他们的观点的:二战后,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已经到了可以以科技发展取代社会关系的变革和发展,意识形态已从外部失去了对舆论的影响,而且本世纪下半叶以来意识形态的冲突已告结束,人们在思想上日益趋向一致,剩下的只有个人或技术的选择。可见在新技术条件下意识形态已经过时。这一理论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对立,它从一开始就歪曲了当今世界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冲突。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化、价值观方面的问题愈益突出,这一论断的虚构性更加明显,人们越来越注意到用工艺技术无法解决精神文化问题,于是意识形态的使命和职能又被重新审视而再次被信奉。这样,技术统治论者的“意识形态过时论”又发展成了“再意识形态化”理论。但是无论是对意识形态的摒弃还是对意识形态的再认识,技术统治论者都没有能够揭露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腐朽的实质,只是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工具理论。他们对意识形态一取一舍的作为,不能不让人感到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混乱而肤浅的,他们的“再意识形态化”的重要内容,并不是将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同等对待,而是求助于资产阶级传统的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当然不是一种优越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意识形态,实质上只是一种衰亡的思想和理论原则,它的保守性是不言而喻的。
与技术统治论者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循着完全不同的第一条道路发展。他们不仅不赞同意识形态已经结束,而且着意分析西方意识形态统治的新内容和新形态。将其区别于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也有过争议,其中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这一争论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的,而科学是真理,二者对立。代表人物阿尔都赛。他对意识形态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它作为理论性的认识,歪曲了事实。所以,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是“一种纯粹的假象、梦想,即‘虚无’”。因此他提出意识形态和科学是对立的,这种对立表现在:科学是真理,它如实在地反映了客观现实和社会历史的真正过程;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则是一种“虚假意识”,是人对于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结构的一种想象的关系,即人对客观世界依存关系的主观感受,由于这种感受是以人的主观愿望、意志为出发点,因而它只是一种虚假的信仰,掩盖社会历史过程的真正面貌;科学与利益无关,也不为利益所动,意识形态则完全受利益支配,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体验,而形成的调整依存关系所应遵循的指导原则,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但他也并不认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没有丝毫关系,主张任何科学都是由意识形态“脱胎”而成的,在这种“脱胎”中就要求对意识形态的基本结构作彻底的否定,阿尔都塞将这一“脱胎”过程称作是“认识论断裂”。他也是第一个将科学与意识形态作为理论问题提出来的人。
第二类,认为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并将科学也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将这种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看成是一种虚假意识。代表: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强调人的独立和自由,社会批判和社会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实现人的解放和人性的复归。而科学的发展,机器技能的精致化和复杂化逐渐地使人的成就转过来反对人本身,人不但没有解放,反而成了机器的奴隶。这样,人便同自然分开,与他自己的本质存在分离开来,使他不能从事独立自由的劳动。人们从内部精神上的丧失为代价去获得外部的物质上的成就,所以现代技术的发展已形成了与传统意识形态不同的新的意识形态,即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造成了单面的社会,单面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对于科学技术变成新的意识形态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是第一个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值得一提的是在《认识与人的兴趣》一书中,他明确地将科学分为三类:自然科学、文化科学、批判科学,其实这其中的文化科学和批判科学都是社会科学。他将社会科学也包括在科学之内,认为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亦即社会科学的一部分),都具有双重功能:作为生产力和作为 意识形态。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它赋予某种政治统治和政治秩序以合法性。到了晚期资本主义时,“社会制度的发展看来为科学技术进步的逻辑所决定”,⑤科学和技术成为名列第一的生产力,并且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使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了。由于哈贝马斯认为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虚假的,所以他所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及“科学”包括社会科学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相同命题,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其将社会科学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含义值得重视,因为这一命题概括了当代科学革命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新特点和新结构。
第三类,将意识形态代表真理,把科学看成是一种虚假意识,将二者对立。代表:卢卡奇。他持一种肯定的意识形态概念。他一般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意识——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即关于无产阶级的真理,对科学持一种否定态度,他认为科学精神的实质是分析理性,把世界分解为独立、静止、不变的单元,这与辩证法的观点是对立的。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尊重事实,而事实就是现实,科学总在维护现实,反对社会革命,而无产阶级是必须参与历史的创造活动的。这样,科学与意识形态就对立起来了。
第四类,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关系。列宁认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可以代表真理而与科学同一。他将意识形态分为“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两类,意识形态并不必然与科学对立,也不必然是虚假意识。意识形态可以成为科学,科学也可以成为意识形态。比如马克思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它完整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意志,所以它也是无产阶级的真正阶级意识,达到了与科学的统一。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所以是虚假的,不在于它是意识形态,而在于它是“资产阶级”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观和以“资本主义制度永恒”的形而上学历史观之上的,这种局限性妨碍了它的科学性。
马克思本人对意识形态与科学的联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曾有过论述。他说:“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象是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⑥“思辩终止的地方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⑦在这里乍一看,好象马克思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起来,但仔细推敲一下马克思语句的前后逻辑,就不难看出,他这里指的意识形态,是指以鲍威尔等人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而这里的“思辩”是指“黑格尔的思辩哲学”。稍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所指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种颠倒的意识形态(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是虚幻的,不真实的。所以,不能说马克思是将科学与意识形态相对立,而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德意志的意识形态”是与科学相对立的。
倘若我们对“意识形态”作单独考察,它本身是无所谓科学或是非科学的,而应该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但当它参与社会实践时,就必然地显露出它肯定的(对实践具有进步的指导作用)或是否定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保守作用)的动能。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除了具有与社会意识共同的本质特征,即社会的全部精神生活过程是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社会存在)的反映以外,还具有它自身的一些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它的内在二重性:即它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并存的二重特性。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以理论形式表达出的一种实践要求,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在社会运用过程中,都要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客观实际相结合。意识形态中这种实践因素与理论因素的相互依存,也就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真理性的一面。马克思和列宁由于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斗争的需要,各自阐述了意识形态概念的肯定和否定功能,均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第二,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公认的。在具体的实践中表现为:为人们改造或改变社会关系,社会结构提供理论和方法,为社会的变革或社会的协调发展服务,改造自然和社会,进而改造人及其意识。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则是体现在对社会规律和人自身发展规律之中的。在社会科学的探索中存在着真理追求和价值追求并列的事实。我们说社会科学能够达到科学性和意识形态的统一,还要从社会科学自身的层次中反映出来,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及其对实践的关系为依据,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基础学科,这是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理论层次,也是最一般的社会科学知识。它是对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史、社会认识史的总结,是对人类长期发展中积累起来的社会科学的成果最一般概括,它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二是应用理论,它是基础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中间环节,由于它尚未直接应用于生产过程,在表现形态上仍以理论样式表现出来。这些理论是人们对某一社会领域中以往经验的概括,它们对人们在某一社会领域中的实践活动有较具体的指导作用,能对人们实践活动中的问题作出具体的回答,而它们的理论命运则也较为直接地接受着人们实践后果的判决。三是社会科学技术。是更为具体的针对某一具体的实践行动的计划方案,具有可操作可实施的具体性质,属于社会技术范畴,是社会科学知识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层次。它们与具体的个别的实践行动之间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而具体的个别的实践行动的成功与失败则会直接地、迅速地判定它们的正确性、可行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都是能够将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统一起来的。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总是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任何意识形态都要反映该社会的现实社会关系,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根本没有超社会、超人类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的意识形态中,总包含着不同程度的全社会、全人类的因素。资产阶级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观从本质上说是不科学的,因而建立在这种社会观基础上的社会学说也缺乏科学性,但也不能说它全部没有科学的颗粒。资产阶级创造的社会科学理论,经过分析、批判,排除其阶级局限性的成分,保留和发扬其科学性的内容,便可以成为真正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意识形态既反映了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利益,同时又以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基础,所以在这种意识形态中阶级性与全人类性是统一的。而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科学,它本身的科学性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科学要达到它的科学性,并不在于剔除其价值追求,它应该是真理和价值的统一。
科学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推动着历史的前进。社会科学是科学,也能转化为生产力。当社会科学在生产发展和整个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其科学性不断显现之时,并不意味着它的意识形态功能的丧失,因为它本身就是身兼二任,是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1975年至1982年)第4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7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20页。
⑤哈贝马斯《朝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波士顿烽火出版社1971年版第10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9页。
⑦同上书第30-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