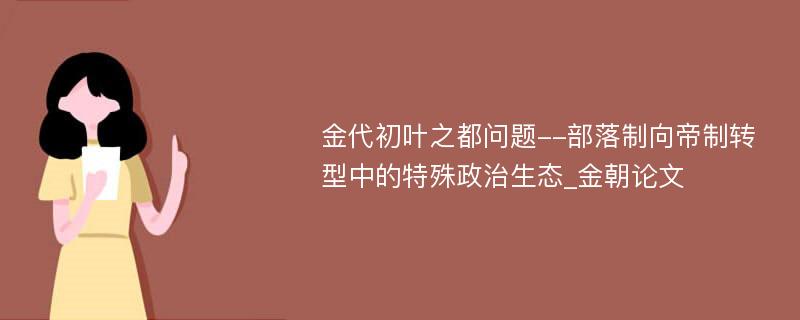
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叶论文,王朝论文,帝制论文,部族论文,国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金源一朝的国都问题,人们习知的常识是,自太祖至熙宗时代,定都上京会宁府,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迁都中都大兴府,宣宗贞祐二年(1214)迁都南京开封府。不过,辽金史研究者大抵都知道一个不寻常的史实:金朝前期的都城会宁府直至熙宗天眷元年(1138)才建号上京;同时,女真人在推翻契丹王朝之后,仍长期保留辽上京的旧称。自宋元以来,人们对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子)始终存在着许多误解,就是由于金朝初叶国都问题的特殊性而造成的。这应该是金代政治史上一个很惹眼的问题,但令人诧异的是,这么一个明摆着的疑点,居然至今尚未引起金史研究者的关注。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是女真政权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一种特殊政治生态,值得我们做一番深入探讨。
一、没有京师名号的“都城”
会宁府何时被确定为金朝国都,史无明文,这个问题下文再予讨论。至于会宁府建号上京一事,见于《金史·熙宗纪》:天眷元年八月,“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地理志》“上京路下”也有“天眷元年号上京”、“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的记载;“北京路临潢府下”则说:“地名西楼,辽为上京,国初因称之,天眷元年改为北京。”①可见在会宁府建号上京的同时,将原来的辽上京临潢府改为北京,《地理志》与《熙宗纪》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②
但在宋代文献中,此事系年有所不同。张汇《金虏节要》曰:“(完颜)亶立,置三省六部,改易官制。升所居曰会宁府,建为上京。”③据陈振孙说,张汇“宣和中随父官保州,陷金十五年,至绍兴十年归朝”,④因此《金虏节要》的上述记载很可能是宋代文献中有关此事的最初史源。张汇并未明确说明会宁府何时始建上京之号,《三朝北盟会编》把这段引文置于绍兴五年,是因为金熙宗即位于是年的缘故,而后人遂滋误解,故《中兴小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均将此事系于绍兴五年,⑤元人抄撮宋代文献而纂成的伪书《大金国志》,亦将此事系于天会十三年(1135)。⑥
会宁府天眷元年建号上京一事,虽然《金史》中已有十分确凿的记载,但仍有学者持不同意见。朱国忱注意到,《大金国志》卷2《太祖武元皇帝下》有这样一条史料:“天辅六年春,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其辽之上京改作北京。”且《金史·太祖纪》及《太宗纪》都有称会宁府为上京的例子。遂由此得出结论说,早在太祖天辅六年(1122),会宁府已有上京之号;在天眷元年改辽上京为北京之前,金上京与辽上京可能同时并存不悖。⑦这种意见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首先,《大金国志》是一部为学界公认的伪书,其中不乏篡改史料、混淆史实之处。⑨即如会宁府建号上京的时间,如上所述,此书还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卷9《熙宗孝成皇帝一》在天会十三年下说:“升所居曰会宁府,建为上京,仍改官制。”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此条下有馆臣按语:“金之建上京、定官制实在天眷元年,此书一书于天辅七(六)年,又书于天会十三年,重复舛误。”⑨可见此书的记载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其次,《金史·太祖纪》和《太宗纪》称会宁府为上京,应属史臣追叙之语。元修《金史》的基本史料来源是金朝实录,而《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分别成书于皇统八年(1148)及大定七年(1167),⑩均在天眷元年建号上京以后,若修实录时将会宁府追记为上京,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许子荣曾对《金史》纪、志、传中所见“上京”进行过逐条辨析,指出天眷元年以前所称上京既有指辽上京者,也有指金上京者,后者均为史臣追叙之辞。(11)其说有理有据。
既然会宁府晚至熙宗天眷元年才建号上京,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会宁府究竟是什么时候被确定为金朝国都的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知道会宁府创设于何时。《金史·地理志》述及会宁府沿革时说:“初为会宁州,太宗以建都,升为府。”据此,会宁州似乎得名于太祖之时,太宗建都,改州为府。不过这一记载在金代文献中几乎找不到旁证,其真实性值得怀疑。施国祁对“会宁”之取义有一个推测:“按二字当取天会、宁江之义。”(12)若按这种说法,会宁州(府)之得名不应早于太宗天会元年。宋代文献中有一则材料颇能说明问题,宣和七年(1125)许亢宗使金贺登位,由其随员钟邦直执笔的《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谈到此行行程时说:“起自白沟契丹旧界,止于虏廷冒离纳钵,三千一百二十里,计三十九程。”(13)书中逐日记录每日起止行程,对于此行的目的地,或称“虏廷”,或称“纳钵”,或称“皇城”等等,绝无“会宁”之称。这说明许亢宗宣和七年使金时,尚无会宁州或会宁府之名。
但笔者在金人王成棣的《青宫译语》中发现了一段值得注意的记载:天会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抵会宁头铺。上京在望,众情忻然。二十三日,抵上京,仍宿毳帐”。(14)王成棣一名王昌远,当系辽朝“汉儿”。天会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二十三日,他作为金军中的一名译员,跟随珍珠大王设野马押送宋高宗生母韦后等一行,从汴京前往金上京。《青宫译语》便是他此行留下的一部行程闻见录。(15)
那么,为何在天会五年成书的《青宫译语》中,会出现上京、会宁头铺之类的地名呢?这就需要谈谈此书的来历。今本《青宫译语》出自《靖康稗史》,《靖康稗史》为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题名耐庵者所编,卷首的耐庵序交代了它的来历:
《开封府状》、《南征录汇》、《宋俘记》、《青宫译语》、《呻吟语》各一卷,封题“《同愤录》下帙,甲申重午碓庵订”十二字,藏临安顾氏已三世。甲申当是隆兴二年。上册已佚,確庵姓氏亦无考。……上帙当是靖康元年闰月前事,补以《宣和奉使录》、《甕中人语》各一卷,靖康祸乱始末备已。咸淳丁卯耐庵书。(16)
根据这篇序文,我们知道《青宫译语》是经確庵、耐庵两位佚名的宋人先后编订,收入《同愤录》和《靖康稗史》,才得以保存至今,至于这部金人著作是如何传入南宋的,则已无从考证。今本《青宫译语》书名下题有“节本”二字,说明此书在辗转流传的过程中,经后人之手做过某些加工,显然已非原貌。书中上京、会宁头铺等地名,可能就是由后人追改的。会宁头铺等驿铺驿程,可信的记载最早见于洪皓《松漠记闻》卷下,而《松漠记闻》之成书已经是天眷元年以后的事情。《青宫译语》一书中出现的会宁头铺,并不能证明天会五年已有会宁州或会宁府之名。
总之,除了《金史·地理志》的那条材料外,目前在金代文献中竟然找不到会宁州或会宁府究竟建于何时的证据。《金史》中有记载可考的会宁牧,年代最早的一位是完颜奭,而他担任会宁牧是在天眷元年九月,即会宁府建号上京之后。(17)《金虏节要》谓“(完颜)亶立……升所居曰会宁府,建为上京”云云,若就这段文字来理解,似乎熙宗即位之后才有会宁府之名。故清代学者认为,《金史·地理志》“初为会宁州,太宗以建都,升为府”那段话,“‘太宗’当作‘熙宗’,传写之误耳”。(18)由于金初史料过于匮乏,这个问题恐怕只能暂且存疑。
尽管就连会宁府始置于何时都无法确定,但有证据表明,至迟从太宗初年起,后来的上京会宁府事实上已经开始成为金朝的政治中心。《金史·太宗纪》里有两条值得注意的史料:天会二年正月丁丑,“始自京师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驿”;同年闰三月辛巳,“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这里说的京师、上京都是后来的史臣追叙之辞。当时的南京是指平州(治今河北省卢龙县),在靖康之变前,平州是金朝的南疆重镇,而且当时正值金军对平州用兵以镇压张敦固之乱,所以需要在京师与南京之间建置驿道。春州即长春州(今黑龙江省肇源县西),泰州(今吉林省白城市)在长春州西,辽朝春捺钵故地鱼儿渫正好位于长春州和泰州之间,太宗在上京会宁府和长春州、泰州之间建设驿道,可能是为了春水捺钵的需要。
下面这个记载或许更能说明问题。《金史·太宗纪》:天会三年三月辛巳,“建乾元殿”。《地理志》上京路下有小注说:“其宫室有乾元殿,天会三年建,天眷元年更名皇极殿。”(19)乾元殿是金上京会宁府最早的宫室建筑,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在这里举行。(20)宣和七年(即天会三年)奉使金国的许亢宗,于当年六月抵达上京,(21)亲眼目睹了正在建设中的乾元殿:
木建殿七间,甚壮,未结盖,以瓦仰铺及泥补之,以木为鸱吻,及屋脊用墨,下铺帷幕,榜曰“乾元殿”。阶高四尺许,阶前土坛方阔数丈,名曰龙墀。两厢旋结架小韦屋,幂以青幕,以坐三节人。……日役数千人兴筑,已架屋数十百间,未就,规模亦甚侈也。(22)
天会三年建造乾元殿一事,说明此时上京事实上已经开始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但奇怪的是,这个政治中心当时既没有州府名称,也没有京师名号,甚至连一国之都的地位也不明确。
二、有关金上京的种种误解
由于金朝初叶国都问题的特殊性,尤其是因为天眷元年之前会宁府尚未建号上京,而原辽朝之上京临潢府仍沿用其旧名,这就给后人带来了许多误解,往往将金上京与辽上京混为一谈,造成不少混乱。
洪皓《松漠记闻》卷下记有金上京至燕京之间的驿铺驿程,其中说道:“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原注:上京即西楼也):三十里至会宁头铺,四十五里至第二铺”云云,又谓“阿保机居西楼”。(23)显然,洪皓是把金上京与习称“西楼”的辽上京混为一谈了。(24)这个错误后来又被李心传因袭下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4绍兴五年正月末:“(完颜)亶又升所居故契丹西楼为上京,号会宁府。”照说洪皓的误解是很不应该的。洪氏于建炎三年(1129)使金,直到绍兴十三年才被遣返南宋,滞留金朝达15年之久,而且会宁府之建号上京、辽上京临潢府之更名北京,也都是这期间发生的事情。洪皓以当时人记当时事,竟会发生这样的误解,金朝前期都城概念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25)
等到后来元人纂修辽、金二史时,他们笔下的金上京和辽上京就更是纠缠不清了。让我们看看《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上京道”的这段奇文吧:
上京临潢府……神册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显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临潢。涞流河自西北南流,绕京三面,东入于曲江,其北东流为按出河。又有御河、沙河、黑河、潢河、鸭子河、他鲁河、狼河、苍耳河、辋子河、胪朐河、阴凉河、猪河、鸳鸯湖、兴国惠民湖、广济湖、盐濼、百狗濼、火神淀、马盂山、兔儿山、野鹊山、盐山、凿山、松山、平地松林、大斧山、列山、屈劣山、勒得山。
清初以来不少著名学者,都为《辽史·地理志》的这段文字所误导,造成了许多误会。如顾祖禹据此考证涞流河:“涞流河在临潢西北,源出马盂山,南流绕临潢三面,谓之曲江。至城北,又东入福余界,经故黄龙府而东合按出虎水。至女真境内,合于混同江。”(26)由于顾氏对《辽史·地理志》的记载深信不疑,故如此牵强成说,但不知临潢西北的涞流河如何能够汇入按出虎水和混同江?又如曹廷杰所著《东三省舆地图说》,虽已指出巴林波罗城为辽上京临潢府故址,但仍囿于《辽史·地理志》之说,对按出河作出牵强附会的解释:“考按出者,译言耳环也。按出河,谓河像耳环形。查舆图,巴林之水泊亦有耳环形,故知临潢以巴林为是。”(27)金毓黻先生亦从其说。(28)又如清末景方昶撰《东北舆地释略》,对金上京附近水道考证甚详,但因误信《辽史·地理志》,故谓金上京之涞流水“于辽上京临潢府之涞流河则别为一水,音虽相同,字则各别”;他又对辽上京之涞流河做了如下考证:“所谓自西北南流,绕京三面,东入于曲江者,舍今之洮儿河,别无他水,与所述流域方位相合者。”(29)亦因误信《辽史》,而误指洮儿河为涞流河,相去就更远了。
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贾敬颜先生才首次指出《辽史·地理志》的错误:
作者把金上京误作辽上京了。极为明显,涞流河、曲江、按出(虎)河都是金上京左右的著名河流,鸭子河、他鲁河也与辽上京无干。另外,如辋子河、阴凉河等都在中京大定府的辖境之内,同样不该罗置于此。总之,这是一项杂凑的材料,居然混淆辽、金两上京为一处。《辽史》以疏忽著名,这也可算作一条典型的例子。(30)
其后,冯永谦先生又撰文对《辽史·地理志》所记辽上京附近水道逐一进行辨误,认为元人修《辽史》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错误,是“由于辽上京附近水道资料不全”,于是“误将金上京附近的水道材料混入辽上京中去了”。(31)贾、冯二人虽然发现了《辽史·地理志》的谬误,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并没有真正弄清元代史官的致误之由。当我们明白事实真相之后,恐怕不能一味以“疏忽”怪罪于元人,《辽史·地理志》的谬误,说到底是由于金朝初叶国都问题的特殊性而造成的。
《金史·地理志》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错误,“上京路下”有云:“旧有会平州,天会二年筑,契丹之周特城也,后废。”此事亦见于《太宗纪》:天会二年四月戊午,“以实古迺所筑上京新城名会平州”。《金史》卷72《习古迺传》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习古迺,亦书作实古迺。……后为临潢府军帅……筑新城于契丹周特城,诏置会平州。”很显然,实古迺所筑上京新城会平州,是在辽上京临潢府附近的周特城,景方昶和鸟居龙藏早已指出这一点。(32)《金史·地理志》将会平州列在金上京之下,也无非是因为元朝史官对金上京和辽上京常常混淆不清的缘故。
元人将金上京与辽上京混为一谈的情形,在元代文献中还能找到更直接的证据:
天德三年,海陵意欲徙都于燕。上书者咸言上京临潢府僻在一隅,官艰于转漕,民难于赴愬,不如都燕,以应天地之中。(33)
经查考这段文字的史源,当出自张棣《正隆事迹》:
完颜亮自己巳冬十二月杀兄亶而自立,守旧都于会宁。越明年,诛夷稍定,下求言诏,敕中外公卿大夫至于黎庶之贱,皆得以书奏对阙庭。是时上封事者多陈言:以会宁僻在一隅,官难于转输,民艰于赴诉,宜徙居燕山,以应天地中会。(34)
据宋人说,《正隆事迹》的作者张棣是“淳熙中归明人”,(35)还不至于分不清会宁府和临潢府,而到了元人笔下,“会宁”竟被妄改为“上京临潢府”。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由此可见,前面谈到的辽、金二史《地理志》的错误绝非偶然现象。
元人对金上京会宁府的懵懂无知,不妨再举一例。《元一统志》介绍上京故址说:“上京故城,古肃慎氏地。渤海大氏改为上京。金既灭辽,即上京建邦设都,后改会宁府。”(36)这里又把渤海上京龙泉府和金上京会宁府扯到一起了。后来《读史方舆纪要》、《柳边纪略》、《宁古塔纪略》、《盛京通志》诸书,皆踵其误。直至清光绪年间,曹廷杰经实地踏勘,指出金上京会宁府故址即阿勒楚喀城南之白城,才纠正了自元代以来相沿已久的谬误。(37)
《元一统志》是元初的官修总志,其成书之时去金亡不远,但该书作者对金朝前期都城竟已茫然无所知,或则于辽上京和金上京混淆不清,或则将渤海上京与金上京混为一谈,可见金朝初叶的国都问题给后人带来了多大的困惑。
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古人,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学者对于金前期都城存在各种各样的误解。如有学者误以为金太祖时代“曾一度以辽上京作为金朝的上京”。(38)更有学者声称:“金朝曾四易首都:建国之初在辽上京;金熙宗迁会宁府,称为上京,改辽上京为北京;海陵王迁都中都;金宣宗迁汴京。”(39)如果说元人分不清辽上京和金上京,主要是因为天眷元年之前临潢府仍继续沿用辽上京旧名、易与金上京会宁府相混淆的缘故,那么今人对《金史》的误读,则缘于对金朝初叶国都问题的特殊性缺乏真正的了解。
三、金朝初叶的国都真相
女真人在推翻契丹王朝之后,仍长期保留辽上京的旧称;而作为一国之都的金上京会宁府,反而直到建国20多年后才有京师名号。在熟悉中国传统王朝政治体制的历史学家看来,这岂非咄咄怪事?如果换一种眼光去看待北亚民族政权,要理解这段历史也许并不困难。
生女真建立的国家政权,有一个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的转变过程。建国之初,女真国家的政治中心与我们心目中的“国都”存在着很大距离。那么,在熙宗天眷元年会宁府建号上京之前,当时的金朝都城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呢?虽然金朝史官对此讳莫如深,但在宋代文献中可以看到许多亲见亲历者留下的第一手资料。
张汇《金虏节要》曰:
初,女真之域尚无城郭,星散而居,虏主完颜晟(按即太宗)常浴于河、牧于野,其为君草创,斯可见矣。盖女真初起,阿骨打之徒为君也,粘罕之徒为臣也,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乐则同享,财则同用,至于屋舍、车马、衣服、饮食之类,俱无异焉。虏主所独享惟一殿,名曰乾元殿。此殿之余,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其殿也,绕壁尽置大炕,平居无事则锁之;或开之,则与臣下杂坐于炕,伪后妃躬侍饮食。(40)
张汇自靖康之变后淹留北方,“陷金十五年”,(41)绍兴十年才回到南宋,他的特殊经历令他的上述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金虏节要》的这段文字绘声绘色地刻画了金初女真君臣的政治生态,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国家”概念及“国都”真相。至于金初的“朝廷”,宣和二年出使女真的宋人马扩曾经亲眼见识过:“阿骨打与其妻大夫人者,于炕上设金装交椅二副并坐。……阿骨打云:‘我家自上祖相传,止有如此风俗,不会奢饰,只得这个屋子冬暖夏凉,更不别修宫殿,劳费百姓也。南使勿笑。’”(42)当时还没有乾元殿,女真人的“朝廷”就是这个样子,这与张汇笔下乾元殿的情景可谓相映成趣。
张棣《金虏图经》“京邑”条,对金初的上京会宁府专门做过这样一番描述:
金虏有国之初,都上京,府曰会宁,地名金源。其城邑、宫室,类中原之州县廨宇,制度极草创。居民往来或车马杂遝,皆自前朝门为出入之路,略无禁限。每春正击土牛,父老士庶无长无幼皆观看于殿之侧。主之出朝也,威仪体貌止肖乎守令,民之讼未决者,多拦驾以诉之,其朴野如此。至(完颜)亶始有内庭之禁,大率亦阔略。
其“仪卫”条亦云:
金虏建国之初,其仪制卫从止类中州之守令。在内庭,间或遇雨雪,虽后妃亦去袜履,赤足践之,其淳朴如此。(完颜)亶立,始设护卫将军、寝宫小底、拏手伞子。迨赴燕,始乘车辂,衮冕、仪从颇整肃。(43)
《金虏图经》一书在宋人著录中或作《金国志》,《直斋书录解题》卷5云:“《金国志》二卷,承奉郎张棣撰。淳熙中归明人,记金国事颇详。”既称“淳熙中归明人”,表明作者出身于辽朝“汉儿”,淳熙间叛金投宋;入宋后授承奉郎,可知是一位读书人。据笔者考证,张棣之入宋是金世宗大定末年的事情。(44)金朝初年的历史虽非他亲身经历,但作为金朝士人,他的记载想必有可靠的文献依据。熙宗天眷元年以前的金朝国都,正是像他所描述的那样朴野和简陋。
前面说过,天会三年建造的乾元殿是金上京会宁府最早的宫室建筑。其实,终太宗一朝,它也是上京唯一的宫室建筑。熙宗即位后,于天会十三年为太皇太后纥石烈氏建造的庆元宫,是见于《金史》记载的第二座宫室。(45)直到天眷元年,才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宫室建设。是年四月丁卯,“命少府监卢彦伦营建宫室,止从俭素”;十二月癸亥,“新宫成”。(46)此举的直接动因是为了建立新的京师制度,会宁府建号上京就是这年八月的事情。
女真人的“国都”,在建国之后很长一个时期里没有京师名号,甚至连会宁府的州府名称也很可能是晚至熙宗天眷元年才有的。开国之初,这座都城就像宋人所描述的那么朴野,朴野得连一个正式的名称都没有。对于刚刚走出部落联盟时代的女真人来说,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知道,金初将以会宁府为中心的生女真的发祥地称之为“内地”,《金史·地理志》说:
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国初称为内地,天眷元年号上京。
而既没有京师名号、也没有州府名称的都城,当时被称之为“御寨”——这个称谓在宋代文献中屡见不鲜。赵子砥《燕云录》说:“御寨去燕山三千七百里,女真国主所居之营也。”(47)赵子砥是宋代宗室,仕至鸿胪丞,靖康之变时随徽、钦二帝北迁,后于建炎二年八月遁归南宋,(48)《燕云录》一书记述的是他在金朝的所见所闻。又《云麓漫抄》卷8记有宋金驿程:“自东京至女真所谓‘御寨’行程:……七十里至乌龙馆,三十里至虏寨,号‘御寨’。”南宋归正人苗耀曾谈到完颜阿骨打之死,谓“以白矾、大盐醃归阿触胡(按:即按出虎)御寨葬之”。(49)还有一幅南宋地图也值得注意。苏州博物馆所藏《地理图》碑,上石年代为淳祐七年(1247),据考证,原图由黄裳作于绍熙二年(1191)。(50)该图把金上京标记为“御寨新京”。(51)黄裳《地理图》基本上是一幅宋朝地图,长城以北地区主要取材于宋人所绘辽金地图,其“御寨新京”的标记应当是照抄底图的文字。从这个地名来判断,它所依据的那幅底图,成图年代当在天眷元年会宁府建号上京之前。“御寨新京”被作为地名载入地图,说明“御寨”确是当时金朝都城的正式称谓,可能因为绘图者担心宋人不懂它的意思吧,故特意加上“新京”二字,以区别于辽朝旧都之上京,表明它是金朝国都。另外,在宋代文献中,“御寨”又称“皇帝寨”,《三朝北盟会编》卷3说:“阿骨打建号,曰皇帝寨。至亶,改曰会宁府,称上京。”《大金国志》亦有“皇帝寨”之称,当是抄自宋代文献。估计御寨是金人的自称,而皇帝寨可能是宋人的俗称。一
金初将京城称为“寨”,与女真人传统的村寨居处方式有关。女真建国之初,“尚无城郭,星散而居”。在《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中,宣和七年许亢宗出使金朝,在到达黄龙府之前,每日行程一般是从某州至某州,而自三十三程进入金源内地之后,每日行程都是从某寨至某寨,说明在生女真的故地,此时还只有村寨而没有州县城镇。不仅如此,即便是当时的一国之都,仍具有村寨的遗风。前引张汇《金虏节要》,谓太宗时唯有一乾元殿,“此殿之余,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宋人《呻吟语》也说:“乾元殿外四围栽柳,名曰‘御寨’。有事集议,君臣杂坐,议毕同歌合舞,携手握臂,略无猜忌。”(52)以柳林为禁围,便是女真人村寨的特点。不仅皇帝有自己的“寨”,宰相、太子也有自己的“寨”,《大金国志》曰:“女真之初无城郭,止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53)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女真人走上汉化道路之后,便对金朝初叶的国都真相百般讳饰。在元人以金朝实录为蓝本纂修的《金史》,以及其他金朝官方文献中,绝对看不到称上京为“御寨”或“皇帝寨”的说法。不过,在某些金人笔记里,还是留下了些许蛛丝马迹。金人王成棣《青宫译语》记载天会五年作者随珍珠大王设野马押送宋高宗生母韦后等一行,从汴京前往金上京的行程,其中说道:是年五月二十三日,“抵上京,仍宿毳帐”;六月七日,“王令韦妃以下结束登车,成棣亦随入御寨”。(54)这是传世金朝文献中唯一一例金人自称上京为“御寨”的史料。另外,在金人可恭所著《宋俘记》一书中,屡屡出现“国相寨”和“皇子寨”的说法,(55)说明《大金国志》的上述记载也不是没有来由的。金朝实录对金初国都真相的讳饰,不只是删改“御寨”之类的说法而已。《金史》有“天辅七年九月,太祖葬上京宫城之西南”的记载,(56)有学者指出,“所谓‘宫城’者,是《金太祖实录》或元人修史时的追述之词。金代讳言太祖阿骨打称帝时之简陋,故而以‘宫城’来代替皇帝寨”。(57)在太祖时代,确实还没有任何形式的宫城。太宗时代的所谓“宫城”,据许亢宗天会三年使金时所见:“近阙……有阜宿围绕三四顷,并高丈余,云皇城也。”(58)可见虽有城垣,却也非常简陋。景爱认为,这个宫城是天会三年与乾元殿同时建成的,宫城之外,并未建筑外城垣,只是“于所居四外栽柳行以作禁围而已”。(59)金朝史家的曲笔,终究无法掩盖金初“御寨”的真实面貌。
众所周知,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国是一个典型的汉化王朝,但它对汉文明的接受毕竟有一个过程。太祖、太宗时代,金朝的政治制度基本沿袭女真旧制,部族传统根深蒂固。当时女真人对于汉文化传统中的京师制度还懵懂无知,完全不理解一国之都的政治意义,因此在建国多年之后,前朝旧都竟然仍被称为上京,而作为本国政治中心的金上京却长期没有州府名称和京师名号,姑且称之为“御寨”而已。
金朝政治制度全面转向汉化,是熙宗即位以后的事情。熙宗朝的汉制改革,从天会末年至皇统初年,大约持续了八九年之久。改革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都城制度等等;可以说,除了猛安谋克制度仍予保留外,其他女真旧制大抵都被废弃,基本完成了从女真部族体制向中国帝制王朝的转变过程。其中天眷元年的汉制改革被视为金朝走向全盘汉化的一个标志,是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是谓“天眷新制”。(60)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自金初以来实行20余年的女真勃极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废”,(61)以三省六部制取而代之。与此同时,宣布“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意味着中原王朝政治传统的京师制度在金朝的真正建立。
四、导致女真式“御寨”都城功能弱化的若干因素
上文曾经指出,至迟从太宗初年起,后来的上京会宁府事实上已经开始成为金朝的政治中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天眷元年建号上京之前,这个政治中心作为一国之都的地位始终不太明确,都城的政治功能相当弱化。究其原因,除了来自观念层面的障碍之外,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使“御寨”无法真正发挥国都的作用。仔细分析起来,这些因素似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女真军事民主制传统抑制了君主个人权威的发展,熙宗之前尚未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这是女真式“御寨”无法与汉式国都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
在熙宗推行汉制改革之前,由于女真传统的勃极烈贵族议事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还发挥着重要作用,当时的皇权是十分有限的。以皇位继承制度为例。太祖、太宗时代,专制皇权特有的君主世袭制尚未确立,太祖与太宗是兄终弟及,熙宗则是太祖之孙,所以当时也还没有皇太子制度,而是因仍女真旧俗,以元老贵族推选的谙班勃极烈作为皇储。(62)《金史》说:“国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谙班勃极烈即帝位。……熙宗立济安为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63)这样一种皇位继承制度,意味着谙班勃极烈的人选不见得能够合乎皇帝本人的意愿。如熙宗被立为谙班勃极烈,即非太宗之本意。太宗即位后,先是以其母弟斜也(完颜杲)为谙班勃极烈,在斜也天会八年死后,太宗有意传子,“无立熙宗意”,但左副元帅宗翰、右副元帅宗辅、国论勃极烈宗斡、元帅左监军希尹等元老大臣极力推举太祖嫡孙完颜亶为谙班勃极烈,“言于太宗,请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义不可夺,乃从之”。(64)太宗虽身为一国之主,但并没有专制皇权应有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因而不得不屈服于元老贵族的选择。
对于金初的君臣关系,宋人有一些很细微的观察。据说太祖阿骨打初至燕京大内,“与其臣数人皆握拳坐于殿之户限上,受燕人之降,且尚询黄盖有若干柄,意欲与其群臣皆张之,中国传以为笑”。(65)这也难怪,女真建国之初,贵族政治凌驾于君主的个人权威之上,在习惯了皇权政治的宋人看来,自然会觉得很可笑。赵子砥《燕云录》讲述的一个故事,最能反映金初君臣关系的真实状态:
金国置库,收积财货,誓约惟发兵用之。至是国主吴乞买(按即太宗)私用过度,谙版告于粘罕,请国主违誓约之罪。于是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毕,群臣复扶上殿,谙版、粘罕以下谢罪,继时过盏。(66)
此事亦见于《呻吟语》,系于绍兴三年(金天会十一年)冬。(67)按《燕云录》一书记载的是作者靖康二年至建炎二年滞留金朝期间的见闻,成书当在建炎二三年间,故此事似不应晚于建炎二年(即天会六年)。文中说的“谙版”,可能是指时任谙班勃极烈的完颜杲。这个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女真军事民主制的传统。我们看到,金初的皇权是如何受到女真贵族的压抑,谙班勃极烈完颜杲和左副元帅宗翰(粘罕)等宗室贵族有权对皇帝进行监督和处罚,甚至可以动用像廷杖这样的非常手段。
另一方面,与有限的皇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初女真军事统帅的高度集权。《金史·太宗纪》天会二年二月乙巳,“诏谕南京官僚,小大之事,必关白军帅,无得专达朝廷”云云。这里说的南京是指平州,天会元年平定张觉之乱后,镇守南京的军帅是宗望,史称是时南京军政事务“一决于宗望”。(68)金初军事统帅事权之集中、独立性之强,于此可见一斑。关于这一点,宋人也有很深入的观察,范仲熊《北记》详细介绍了他在金军中的见闻:
骨舍与粘罕至相得,而骨舍才尤高。自阿骨打在日,三(二)人用事未尝中覆,每有所为便自专,阿骨打每抚其背曰:“孩儿们做得事必不错也。”一切皆任之,以至出诰敕命相皆许自决,国中事无大小,非经此二人不行。至于兵事,骨舍又专之,粘罕总大纲而已。(69)
范仲熊乃范祖禹之孙,靖康元年为怀州河内县丞,是年十一月,宗翰克怀州,仲熊陷于金,次年四月被遣返南归,其间在宗翰军中盘桓数月,因撰《北记》述其见闻。(70)文中所称骨舍即完颜希尹(《金史》本传谓“本名谷神”,骨舍乃谷神之异译)。在金初的军事统帅中,左副元帅宗翰和元帅左监军希尹的强势强权确实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种强势与强权恰恰反衬出君主个人权威的卑弱。
由于缺乏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金初的军事统帅往往拥有对军国大事的决断权和处置权,不妨举一个实例。《金史·太宗纪》天会五年(宋靖康二年)二月丙寅有“诏降宋二帝为庶人”的记载,但据金人《南征录汇》可知,对于如何处置赵宋政权一事,虽有太宗废立之诏,其实主要还是取决于左副元帅宗翰和右副元帅宗望二人的态度。当时宗翰力主废立,宗望则主张保留赵宋藩王,即便在太宗废立诏送达开封城下之后,二人仍为此争执不下。宗望的理由是:“明诏虽允废立,密诏自许便宜行事,况已表请立藩,岂容中变?”宗翰坚执不允,宗望又云:“太祖止我伐宋,言犹在耳。皇帝仰体此意,故令我懑自便。”最终因都元帅斜也支持宗翰的主张,才将徽、钦二帝废为庶人。(71)《大金吊伐录》有一篇《废国取降诏》,其中说道:“既为待罪之人,自有易姓之事。所有措置条件,并已宣谕元帅府施行。”(72)这就是天会五年二月丙寅(六日)的废立诏。据宗望说,除了这个“明诏”之外,还另有一封“密诏”,允许二人“便宜行事”。虽然这一密诏未能保存下来,但事实已经很清楚:太宗实际上赋予了宗翰、宗望二人自行处置赵宋政权的最终决断权,这意味着最后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是与太宗的废立诏相冲突的。
如上所述,由于金朝前期尚未形成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皇帝所居的“御寨”并不具备汉式国都那样的政治权威和影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政治功能。
第二,金朝前期实行的二元政治体制,造成多个政治中心并存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御寨”作为一国之都的重要性。
金朝建国之初,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贵族议事会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如《金史·太祖纪》谓收国二年(1116)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73)但一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汉官制度。元人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74)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云云。(75)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76)
严格说来,金初的二元政治仅存在于1123-1138年。天辅七年(1123),汉地枢密院始设于营州广宁(今河北省昌黎县),后迁平州,再迁燕京,天会间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熙宗天眷元年八月,颁行“天眷新制”,以三省六部制取代女真勃极烈制度;同年九月,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这不只是简单地改换一个名称而已,它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汉地枢密院是作为双重体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书省则只是中央尚书省的派出机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标志着二元政治的终结。(77)
金初的汉地枢密院,是代表女真军事集团势力的汉地最高政权机构,对于朝廷来说,它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张汇《金虏节要》对汉地枢密院的政治背景及其重要地位说得很清楚:
斡离不初寇燕山,粘罕初寇河东,称都统府,至是改曰元帅府,乃刘彦宗之建议也。以谙版孛极烈斜也马为都元帅,伪皇弟卢你移赉孛极烈粘罕为左副元帅,伪皇子斡离不为右副元帅。……东路之军斡离不主之,西路之军粘罕主之,虏人呼作“东军”、“西军”。东路斡离不建枢密院于燕山,以刘彦宗主院事;西路粘罕建枢密院于云中,以时立爱主院事。虏人呼为“东朝廷”、“西朝廷”。(78)
据李涵教授考证,燕京枢密院与云中枢密院的分立是天会四年的事情,主要是为了适应左副元帅宗翰(粘罕)和右副元帅宗望(斡离不)两大军事集团分治汉地的需要。汉地枢密院的性质,其实就是听命于女真军事统帅的“军政府”,而被目为汉人宰相的知枢密院事,不过是都统府或元帅府的僚属而已。(79)由于金初尚未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缺乏专制皇权的强有力制约,汉地枢密院遂成为独立于“御寨”之外的政治中心,甚至被形象地称之为“东朝廷”、“西朝廷”。汉地枢密院的高度独立性,实际上也就是女真军事统帅高度集权的表现。
汉地枢密院对于朝廷的独立性,在官员选任一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赵子砥《燕云录》说:“金国、渤海、汉儿、契丹等,若差知州、通判、知县、场务官,更有元帅府亦差除;即如外知州、知县,若两处朝廷差官,元帅府更差,即是三人互相争权也。”关于汉地枢密院与朝廷在选任州县官员上的矛盾纠葛,他还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丁未(天会五年)冬,宰相刘彦宗差一人知燕山玉田县,国里朝廷亦差一人来,交割不得,含怒而归。无何,国里朝廷遣使命至燕山拘取刘彦宗赐死,续遣一使来评议,彦宗各赂万缗,乃已。(80)
刘彦宗时任知燕京枢密院事,由于自行辟署汉地州县官员,导致燕京枢密院与朝廷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冲突,但此事最后还是被刘彦宗用钱摆平了。“国里朝廷”当然就是指“御寨”之女真朝廷,之所以特意说明是“国里”朝廷,正是因为汉地还有“东朝廷”和“西朝廷”的缘故。“国里朝廷”的说法,想必也是出自金人之口。又据赵子砥说,更有甚者,有时不但“两处朝廷差官”,再加上“元帅府更差”,矛盾就愈加复杂了。由此可知,金初汉地枢密院的存在,对“国里朝廷”的政治权威构成了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国之都的“御寨”恐怕只能是徒有虚名了。
第三,金代帝王的捺钵遗俗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都城的政治功能,这也是“御寨”与京师的地位名实不副的一个原因。
金朝的捺钵可以说是女真人传统渔猎生活方式的象征性保留,金代帝王模仿和因袭辽朝四时捺钵制度。直至宣宗南迁以后,捺钵之制才趋于消亡。(81)
据宋人说,大约从熙宗天眷二年起,金朝捺钵开始形成较为完备的制度:“是冬,金主亶谕其政省: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并循辽人故事。”(82)与契丹的四时捺钵相比较,金朝捺钵的季节性不像辽朝那么分明,虽有“春水秋山,冬夏捺钵”之说,实际上只有春水和驻夏时间较长,也比较有规律,所谓“秋山”是指驻夏期间的围猎活动。
由于史料匮乏,金朝前期的捺钵没有留下太多记载,但在金、宋文献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零星的线索。上文提到,天会二年曾在上京(御寨)和长春州、泰州之间建设驿道,可能是为了春水捺钵的需要,估计金初暂且在辽朝春捺钵旧地行春水。熙宗即位后,于天会十三年“建天开殿于爻剌”,(83)此后爻剌遂成为熙宗朝春水的主要场所。《金史·地理志》上京路下有小注说:“其行宫有天开殿,爻剌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宫。”但《金史》没有说明爻剌的具体位置。据贾敬颜先生考证,爻剌当在会宁府宜春县境:“宜春县取义于宜于‘春水’,亦即春水爻剌之地,境内辖有鸭子河,故当求于今扶余、肇州等县地,兹暂订宜春于(吉林省)扶余县东南小城子古城,以待进一步探讨。”(84)朱熹在谈到金朝前期的捺钵情况时说:“金虏旧巢在会宁府,四时迁徙无常:春则往鸭绿江猎;夏则往一山(原注:忘其名),极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射虎。”(85)宋人所称的鸭绿江实际上就是混同江(鸭子河),故朱熹说的“春则往鸭绿江猎”也是指的爻剌春水。
驻夏(或称秋山)是金代捺钵的主要单元之一。金朝前期的几代皇帝一般都在山后地区驻夏,山后的炭山是辽朝传统的夏捺钵之地,在今河北省沽源县境内,契丹语称为“旺国崖”,《辽史》中多称“陉头”、“凉陉”,都是指的这个地方,金代文献中通称此地为凉陉。自太宗时起就有在凉陉驻夏的记录,天会七年二月发布的《差刘豫节制诸路总管安抚晓告诸处文字》说:“今缘逆贼逃在江浙,比候上秋再举,暂就凉陉。”(86)说明是年太宗即驻夏于凉陉。熙宗朝驻夏山后,《金史·熙宗纪》有明确记载。另外宋代文献中也有线索可考,天眷三年,熙宗指责左丞相完颜希尹说:“凡山后沿路险阻处令朕居止,善好处自作捺钵。”(87)就是针对山后驻夏一事而发。
由于捺钵制度的存在,金朝诸帝一年之中往往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不住在都城。总的来说,金前期的捺钵时间较长,中后期时间较短。如春水,就熙宗朝的情况来看,每年春水少则一两个月,长则四五个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春水”;而世宗、章宗时期,每次春水大都在25-40天左右。至于驻夏,与辽朝的夏捺钵也不完全是一回事,金朝皇帝的驻夏往往包括夏秋两季,因此也有人姑名之为“夏秋捺钵”。
金朝皇帝的春水秋山,动辄历时数月,在此期间,国家权力机构便随同皇帝转移到行宫,使得春水秋山行宫成为处理国家内政外交事务的重要场所。太祖、太宗时期的情况因缺乏记载无从知晓,姑以熙宗朝为例。熙宗时的汉制改革,其中部分内容就是在爻剌春水行宫进行的。天眷二年二月乙未至五月乙巳,熙宗春水于爻剌,“三月丙辰,命百官详定仪制”;“四月甲戌,百官朝参,初用朝服”。(88)另外,金宋两国的绍兴和议也是在爻剌春水行宫签订的。据《金史·熙宗纪》,皇统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宋使曹勋来许岁币银、绢二十五万两、匹,画淮为界”,正式签订了绍兴和议。而这年的二月三日至三月八日,熙宗一直住在爻剌的春水行宫天开殿。南宋方面的史料也记载说:“签书枢密院事何铸、知□门事曹勋至金国,见亶(即熙宗)于春水开先殿。”(89)这条史料可以与《金史》的记载相印证,唯“开先殿”为“天开殿”之误。
我们知道,辽朝的五京制度徒有虚名,契丹王朝真正的政治中心是在捺钵和斡鲁朵,而不是在五京之中的任何一个京城。(90)金朝的春水秋山虽然不像辽朝的四时捺钵那么典型、那么严格,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也不像辽朝那么大,但不可否认的是,捺钵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都城的政治功能,尤其是金朝前期更是如此。
综上所述,金朝初叶的“御寨”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国都,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由于缺乏中央集权的专制皇权,没有一元化的政治体制,再加上四时迁徙的捺钵遗俗,注定了女真式“御寨”无法发挥汉式国都的重要作用。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作为一国之都的金上京会宁府,为什么直到建国20多年后才有州府名称和京师名号。
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的宝贵意见。
注释:
①《金史》卷4《熙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3页;卷24《地理志上》,第550、551、582页。
②在海陵王迁都燕京后,上京之号一度被废。《金史·地理志》“上京路”:“海陵贞元元年迁都于燕,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府,称为国中者以违制论。大定十三年七月,复为上京。”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指出,《海陵纪》正隆二年(1157)八月甲寅有“罢上京留守司”的记载,据此推断海陵削上京之号应是正隆二年的事情。(第578—579页)按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164绍兴二十三年(1153)三月小注引海陵王迁都燕京改元诏,有“上京、东京、西京依旧”的说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682页),可知贞元元年迁都时尚未削去上京之号,《金史·地理志》此处所记不确。
③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166,绍兴五年正月所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第1196页。
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5《伪史类·金国节要》,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
⑤熊克《中兴小纪》卷18系于绍兴五年三月(《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7页),《要录》卷84记在绍兴五年正月末(第1388页)。
⑥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9《熙宗孝成皇帝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6页。
⑦朱国忱:《金源故都》,哈尔滨:《北方文物》杂志社刊行,1991年,第30—39页。
⑧参见刘浦江:《再论〈大金国志〉的真伪——兼评〈大金国志校证〉》,《文献》1990年第3期。
⑨《钦定重订大金国志》卷9《熙宗孝成皇帝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383册,第878页。
⑩《金史》卷4《熙宗纪》,第84页;卷6《世宗纪上》,第139页。
(11)许子荣:《〈金史〉天眷元年以前所称“上京”考辨》,《学习与探索》1989年第2期。
(12)施国祁:《金史详校》卷3上,光绪六年会稽章氏刻本,第29b页。按辽之宁江州在会宁府之西南,宁江州一战是生女真起兵攻辽之首役,故施国祁有此揣测。
(13)《靖康稗史笺证》,崔文印笺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页。
(14)《靖康稗史》之五,《靖康稗史笺证》,第188—189页。
(15)参见傅乐焕:《青宫译语笺证——宋高宗母韦太后北迁纪实》,《辽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14—325页;《靖康稗史笺证》,“前言”,第6—7页。
(16)《靖康稗史笺证》,第1页。按《靖康稗史》一书自宋以后诸家书目皆未著录,仅高丽有抄本存世,清末始传入国内,1939年王大隆刊印的《己卯丛编》收入此书。
(17)《金史》卷4《熙宗纪》,第73页。
(18)《钦定重订大金国志》卷9《熙宗孝成皇帝一》,天会十三年下四库馆臣按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3册,第878页。
(19)《大金国志校证》卷2《太祖武元皇帝下》谓天辅六年“大宴番、汉群臣于乾元殿”云云(第28页),显然是误抄宋代文献的结果。
(20)参见景爱:《金上京宫室考》,《文史》第36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49—255页。
(21)《金史》卷60《交聘表上》在天会三年正月之后、六月之前有这样一条记载:“辛丑,宋龙图阁直学士许亢宗等贺即位。”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指出,此“辛丑”当为六月辛丑(第1392、1415页)。据《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说:“于乙巳年春正月戊戌陛辞,翌日发行,至当年秋八月甲辰回程到阙。”按是年六月辛丑朔,许亢宗一行到达上京的时间当在五六月间。
(22)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靖康稗史笺证》,第39—40页。
(23)洪皓:《松漠记闻》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3、16页。
(24)王可宾《金上京新证》(《北方文物》2000年第2期)认为,洪皓所称“上京即西楼也”,这里说的西楼是京师的代名词,并未混淆金上京和辽上京。此说恐系误解洪皓原意,辽金传世文献及石刻史料中所见西楼均为专称,并没有代指京师的用法;况且《松漠记闻》同卷又有“阿保机居西楼”的说法,所指尤为明确。
(25)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宋人亦有能够分清辽上京与金上京者。如《契丹国志》元刻本卷首所载《契丹地理之图》,在祖州和木叶山以东有一“上京”,这是指辽上京;而在混同江(今松花江)以北又有所谓“新上京”,这显然是指金上京。据笔者考证,《契丹地理之图》当出自南宋人所作《契丹疆宇图》,其成图年代应在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之后,下限不应晚于绍兴二十七年(金正隆二年,1157)。(参见刘浦江:《〈契丹地理之图〉考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1907-2007》,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88—793页)
(2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8《北直九》“涞流河”,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55页。
(27)《东三省舆地图说》“临潢府考”附记,《曹廷杰集》上册,丛佩远、赵鸣岐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7页。
(28)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年翻印本,第401页。
(29)景方昶:《东北舆地释略》卷1《金上京会宁府考》,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影印《辽海丛书》本,第1002—1003页。
(30)贾敬颜:《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之十四“《辽志》的一段误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西兰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44页。此文最初以《东北古地理古民族丛考》为题发表于《文史》第1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9月)。
(31)冯永谦:《辽上京附近水道辨误——兼考金上京之曲江县故址》,《辽金史论集》第2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05—119页;参见张修桂、赖青寿:《辽史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19页。
(32)参见景方昶:《东北舆地释略》卷2《金史上京路属地释略·会平州》,第1007页;鸟居龙藏:《金上京城及其文化》,《燕京学报》第35期,1948年12月,第136—137页。王颋《完颜金行政地理》“建置录三”说:“天会二年,立会平州,军事,隶会宁府路,治会平县。……天会二年,析会宁县立会平县,隶会平州。”又谓“会平县治今黑龙江双城市东南……今双城市东南十里有‘双古城’,疑一为周特城,一为会平县故治”。(第125—126页)作者之勇于推测,令人生畏。
(33)《元一统志》卷1,“大都路·建置沿革”,赵万里校辑,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2页。这条佚文辑自《日下旧闻考》卷37“京城总纪”,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88页。
(34)《会编》卷242,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所引,第1740页。又《会编》卷244所引张棣《金虏图经》也有类似记载,文字大同小异。
(35)《直斋书录解题》卷5《伪史类·金国志》,第141页。
(36)《元一统志》卷2,“开元路”,第221页。这条佚文辑自《满洲源流考》卷12。
(37)《东三省舆地图说》“金会宁府考”,《曹廷杰集》上册,第163—166页。
(38)景爱:《金上京的行政建置与历史沿革》,《求是学刊》1986年第5期。前揭许子荣《〈金史〉天眷元年以前所称“上京”考辨》已对这一误解做过详细辨析。
(39)任崇岳:《谈晋皖豫三省的女真遗民》,《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第61页。
(40)《会编》卷166,绍兴五年正月所引,第1197页。据活字本及清白华楼抄本校正。
(41)《直斋书录解题》卷5《伪史类·金国节要》,第141页。
(42)《会编》卷4,宣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引马扩《茆斋自叙》,第31页。
(43)均见《会编》卷244,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所引,第1750、1752页。
(44)参见刘浦江:《范成大〈揽辔录〉佚文真伪辨析》,《北方论丛》1993年第5期。
(45)《金史》卷24《地理志上》上京路小注云:“庆元宫,天会十三年建。”(第550页)卷63《后妃传上》:“太祖钦宪皇后纥石烈氏,天会十三年,尊为太皇太后,宫号庆元。”(第1502页)
(46)《金史》卷4《熙宗纪》,第72—73页。据景爱《金上京宫室考》,天眷元年建成的宫室建筑有敷德殿(朝殿)、宵衣殿(寝殿)、稽古殿(书殿)等。
(47)《会编》卷98,“诸录杂记”所引,第726页。
(48)参见《要录》卷17,建炎二年八月庚申条,第346页。
(49)《会编》卷18,宣和五年六月九日引苗耀《神麓记》,第127页。
(50)钱正、姚世英:《墬理图碑》,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6—49页。
(51)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图版72。
(52)《靖康稗史》之六,《靖康稗史笺证》,第225页。据邓子勉考证,《呻吟语》为宋人李浩所撰,李浩曾随徽、钦二帝北迁,绍兴十二年随韦太后同归,参见氏著:《〈靖康稗史〉暨〈普天同愤录〉及其编著者等考辨》,《文史》2000年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第169—177页。
(53)《大金国志》卷2《太祖武元皇帝下》,第28页。同书卷33《燕京制度》亦云:“国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第470页)
(54)《靖康稗史》之五,《靖康稗史笺证》,第189页。
(55)《靖康稗史》之七,《靖康稗史笺证》,第244、246—249页。
(56)《金史》卷30《礼志三》“宗庙”,第727页。
(57)景爱:《金上京》,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第14页。
(58)《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靖康稗史笺证》,第38页。
(59)景爱:《金上京宫室考》,《文史》第36辑,第250页。
(60)《金史》卷4《熙宗纪》,第73页。按《松漠记闻》卷下载有天眷二年奏请定官制劄子及答诏,三上次男氏谓天眷二年实为天眷元年之误,此当依《熙宗纪》系于天眷元年八月,见氏著:《金史研究》第2巻「金代政治制度の研究」,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71年,第293—295頁。
(61)《金史》卷55《百官志·序》,第1216页。
(62)关于金初的皇位继承制,请参看唐长孺:《金初皇位继承制度及其破坏》,收入《山居存稿》,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78-484页。
(63)《金史》卷80《熙宗二子传》“传赞”,第1798页。
(64)《金史》卷74《宗翰传》,第1699页;参见《金史》卷4《熙宗纪》,第69页。
(65)《会编》卷12,宣和四年十二月六日引蔡絛《北征纪实》,第86页。
(66)《会编》卷165,绍兴四年十二月“虏主吴乞买以病殂”条,引赵子砥《燕云录》,第1194页。
(67)《靖康稗史》之六,《靖康稗史笺证》,第224页。
(68)《金史》卷74《宗望传》,第1703页。
(69)《会编》卷61,靖康元年十一月六日引范仲熊《北记》,第460页。
(70)参见《会编》卷99,“诸录杂记”引范仲熊《北记》,第731页。
(71)李天民辑:《南征录汇》,《靖康稗史》之四,《靖康稗史笺证》,第140-142页。此段末有小注:“见《武功记》、《秘录》、《随笔》、《劄记》、《日录》。”
(72)《大金吊伐录校补》,金少英校补,李庆善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84-385页。
(73)《金史》卷44《兵志》,第992页。
(74)《金史》卷78《刘彦宗传》“传赞”,第1779页。
(75)《金史》卷55《百官志·序》,第1216页。
(76)李锡厚《金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度说质疑》(《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不同意金初曾实行过南、北面官制的说法,按元人无非是借用辽朝北、南面官制之称来代指金初的二元体制而已,此处似不宜太拘泥于字面的意思。
(77)陶晋生《女真史论》(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年,第34-37页)将1123-1150年称为二元政治时期,即以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撤销行台尚书省作为二元政治终结的标志。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欠妥。所谓“二元”,一元是指女真制度(勃极烈制),一元是指汉制(汉地枢密院)。自熙宗废弃勃极烈制以后就全盘实行了汉制,“二元”已无从说起。海陵撤销行台尚书省,只是准备迁都燕京的一个步骤,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这与二元政治的兴废没有什么关系。
(78)《会编》卷45,靖康元年四月十五日所引,第339页。以活字本校正。
(79)李涵:《金初汉地枢密院试析》,《辽金史论集》第4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80-195页。
(80)《会编》卷98,“诸录杂记”引赵子砥《燕云录》,第725页。前一段引文窒碍不通,以活字本、明抄本、清白华楼抄本校改数字,恐仍有讹误,但其大意可以明白。
(81)有关金朝捺钵的系统性研究,请参看刘浦江:《金代捺钵研究》(上、下),连载于《文史》第49、50辑,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2000年。
(82)《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第2142页。《大金国志》卷11《熙宗孝成皇帝三》将此事记于皇统三年(1143),不可信从。
(83)《金史》卷4《熙宗纪》,第70页。
(8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65页。按:据《金史》卷24《地理志》,宜春县“大定七年置,有鸭子河”。(第551页)
(8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3《本朝七》“夷狄”,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192页。
(86)《大金吊伐录校补》,第535页。
(87)《会编》卷197,绍兴九年七月引苗耀《神麓记》,第1418页。
(88)《金史》卷4《熙宗纪》,第74页。
(89)《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二月戊子,第2313页。
(90)参见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72-213页。
标签:金朝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宋朝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大金国志论文; 女真族论文; 金史论文; 会宁论文; 元朝论文; 辽朝论文; 南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