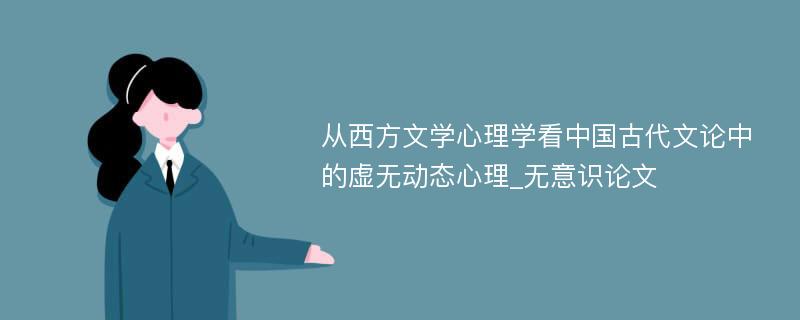
从西方文艺心理学看中国古代文论中虚静的动态心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心理学论文,文艺论文,古代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6-0020-04
虚静,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审美范畴,被广泛的用于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对其内涵和表现形式,古人众说纷纭。老庄认为,虚静是认识“道”的基础,能突破人为知识和视听的障碍,达到无知无欲的“大明”境界;荀子认为,虚静是思想活动前的准备,能让心摄取和明察万事万理;陆机、刘勰第一次将虚静运用于艺术创作,认为虚静是艺术构思的前提和准备,排除外界干扰和内心杂念,促进灵感的到来。无论是从认识论方面还是创作论方面,他们对虚静的认识均有一个共通之处,即摒弃杂念干扰,为认识或创作提供一种特殊心境和心理状态。
然而,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养气篇》中却发现了在认识、构思和想像的虚静状态下真实存在的动态心理,他说:“水停以鉴,火静而朗。”[1](P367)他注意到了人处于虚静状态时仍然存在较为复杂的心理活动,而这种“动”则可能是引发某些认识、构思、想像的基础和前提。但他仅从表象上作出了描述和猜测,并没有对其内在心理机制作更深入的探究。由此,笔者尝试从西方文艺心理学角度对虚静和创作构思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一、虚静中的动静相宜
1.外“静”与内“动”
虚静虚即虚怀以纳万物,静则静虑以明事理。一般来说,创作构思是目标的思维活动,这个目标使创作依循着理性的道路。然而,文艺的创作构思其很多结果似乎更依赖于非理性,也就是说,来源于意识前的无意识活动。对此,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中的“无意识”,为深入探讨人的内在心理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客观潜存于人的心理之中的。他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无意识与意识,二者中间的联系和过渡为前意识。意识是无意识内容突破意识界限而呈现于理性中的思维活动,前意识是准备进入意识领域的内容。三者前后相继,且须经过层层筛选,那些无法进入意识的部分又还原为无意识。由此看来,作家在文学创作的理性思维前实际上还经历了无意识活动。古人极力强调的构思前的准备阶段——虚静,则正是企图表达某些无意识内容进入前意识乃至理性构思所必备的条件。正如一些作家创作时常有略一沉吟的过程,这一沉吟虽有长有短,但实际上都是企图通过短暂的虚静而使原本没有察觉的无意识活动转化为某种可以知觉的情感、意识而进入构思,即外静内动。
那么,虚静状态中“虚”、“静”、“动”三者有怎样的联系呢?
首先,虚与静始终处于不可分割的状态。从表征上看,虚静的特点是“静”。古人常讲创作前须“凝神聚气”,远离浮燥,近似于禅宗的“打坐”。这是一种外在的理性抑制,其目的在于“扫尽俗肠”,排除干扰与内心杂念,留出纯净自由的心理空间,即“虚”。于是“虚”中已包含了“动”的内容,不过这部分“动”仍然是理性控制的结果。“虚”之后要容纳,须为构思时的理性思维作准备,此时作家难以觉察的非理性活动开始自由浮动。“虚”所形成的心理空间正是为这种非理性活动提供的。由静而虚,由虚而动,从外在的静态到内在的活动,虚在中间有重要作用,才使得“虚静”与一般的“静止”、“沉静”等状态在表象上就区别开来。
其次,外“静”不仅为内“动”创造了空间,也直接导致一系列复杂的无意识“动”的发生。心理学认为大脑皮质的活动“在任何时候都是兴奋和抑制复杂的镶嵌式,兴奋和抑制是相互紧密地联系着和经常发生相互作用的”[2](P476-479),即抑制的边缘同时会产生另一个过程——兴奋。“静”使作家有意将有逻辑的意识活动抑制,使大脑一部分细胞进入“抗活跃状态”,意识内容压抑回到无意识层面,通过正诱导规律,这一部分细胞兴奋起来,导致无意识活动。内“动”机制很复杂,经历着弗洛伊德所说的从无意识到前意识再至意识的层层筛选过程。只有当外界刺激与其产生共鸣或自身能量积聚到一定程度时,才以非自觉的方式在无意识层面内导,规范着心理活动,进行信息处理。
此外,“动”中情绪也驱使无意识活动并导致构思发生。不带情感、情绪的创作不叫文学创作,构思创作实际就是情绪的宣泄,因此构思前情绪在无意识层面同样活跃。巴甫洛夫认为情绪与大脑皮层神经系统的稳定结构相联系,是皮质下的无条件反射活动破坏其稳定,引起情绪的变化,因而具有“本能性、情景性、易变性和不稳定性”[3](P141)。许多作家常常会由于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莫名情绪而产生构思的冲动,这种内在情绪唤起心理深层内容,经过内导而进入构思。
虚静状态中外在的理性抑制形成没有干扰的心理空间,并引起一部分大脑细胞无意识兴奋活动,同时在内“动”中又通过对无意识内容的规范选择,情绪驱动,为进入理性构思作好了充分准备。
2.虚静中的集体无意识心理
一部耐人寻味的作品一经形成,总是带有普遍意义,震撼读者心灵,引起广泛的深远的审美共鸣,甚至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这便是荣格说的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是作品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在特定心理模式上的重建和一致的身心感动。
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民族心理记忆,荣格将其表现形式归结为原型心理形态。这一研究的提出使文艺创作从作家个体心理拓展到整个人类生存空间。人们逐渐意识到人遗传的不仅有生理基因,还有以往漫长历史形成的思维习惯、心理经验、文明意识,沉积于现代人思维结构的底层。它展示的是人共有的心理气质。因而处于比个性心理更深层的位置,更难以被作者意识到。中国古诗的深远意蕴恰就在于组合的意象和萦绕其间的脱离具体细节的情感给千百年的读者留下多种遐想与阐释的空间。这种独特的抒情方式直接来自中国文人的生存处境与内省的思维方式。考察历代文人的人生经历即可看出,他们始终徘徊于人世与出世之间,最大的人生目的莫过于入世做官,实行自己认为的“美政”,而做文章只是入世的桥梁;当受到排挤或贬斥,选择的另一条路则是归隐或出游。文人的生存处境是尴尬的,他们的人生飘忽不定,怀才不遇,经不起政治风浪的几番沉浮,积淀于心理底层的原型总是与忧患意识、失意惆怅、山水仕途等意象或情绪有关。这些原型代代相传,在作家的不同作品或不同作家那里都得以呈现。“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因在外未谋得一官半职,想家而不能归,这是古人生命的痛苦。唐代刘希夷借女子青春易逝感叹人生无常:“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白头吟》)张若虚描写春江美景时又写道:“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春江花月夜》)李白亦有所感叹:“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把酒问月》)诗人创作心境、主题内容各不相同,但在心理深层却有相同的内容不自觉的涌现出来。
于是集体无意识以原型形式通过个性心理呈现,作为共性外显于构思。原型不是人生经过的若干往事留下的记忆表象,它是一种不明晰的意象、经验。虚静的无意识活动同样须唤起处于更深层的原型。在外在意识松弛状态下,原型以怎样的方式最终呈现在意识中呢?荣格研究了情结与原型的关系,认为情结起源于集体无意识,原型是情结的核心。作为最原始的带有普遍共性的中心,原型会在周围逐渐吸引相关经验、情感,也就是作者后天自觉不自觉的各种积累,便形成情结。这样原型以共性的内核,融入了带有个性的情结,才得以呈现,“情结从这些附着的经验中获取了足够的力量后,可进入到意识中。原型只有作为充分形成了的情结的核心,才可能在意识和行动中得到表现”[4](P46)。可见,情结的释放实际上也是原型的展现,共性通过个性显露于意识之中。所以我们描述作品风格时说李白浪漫挥洒,杜甫沉郁顿挫,苏轼豪放豁达,柳永婉约凄美,这都是创作时作家的主导情结在起作用,而无论风格个性多么不同,我们还是可以从作品中体察出文人共同的心理特质。许多学者认为古代文人有一种歌女原型,当失意不得志时,文人总愿视歌女为知音,而且古乐以悲为美,这些歌女的不幸身世和她们常唱的清曲商音极易让失意文人产生共鸣。从《古诗十九首》的“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到白居易《琵琶行》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再到柳永大量徜徉青楼的井市慢词,构思中的意识总是以强烈的个体倾向为表象呈现,文人心里歌女原型潜存于或忧郁、或婉约、或豪放的个性中,以此原型为核心,吸附着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以及人生态度,而形成有个体差异的情结。尤其柳永一类的词人,这个情结已左右着他颇多创作构思,成为体现歌女原型的突出代表。
3.虚静中的个性因素
每一部成功的作品都可挖掘出两方面内蕴:个性与共性。前者使我们区别不同作家的独特风格,后者能使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产生共鸣。这不是文本所独立生成的,人们普遍认为构思应体现共性与个性,实际上还可追溯到更前的阶段——虚静,没有作家心理深层内容的积淀而仅靠当前的客观信息,构思也无从发生。这还要先从个性心理谈起。
曹丕曾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5](P158、159)。“气”即个性气质,它的产生有多方面因素。个人气质修养,知识经验积累,尤其是情感体验在心理上形成能量传递和转换,有些已被意识消耗(比如曾作为创作素材被利用等),但仍有很大一部分积累遗留下来成为记忆痕迹,它们是一串串具有情绪色彩的观念或思想,荣格称之为情结。作家心理众多情结中有些有较强的驱力,常“强有力到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3](P267)。因为个性心理的不同,各个作家占主导地位的情结也不一样,这才致使风格各异。比如同样是对国家的忧患、人生的感慨,就有屈原式痛苦、李煜式痛苦、曹雪芹式痛苦,他们的经历不一、个性不一,自然内心情结也不一,使作品带上了个体差异性。
而外在刺激即导致情结释放,作为个性外显于构思。荣格认为情结存在于个人无意识层次,比较容易为意识接受,但本人往往难以注意到。虚静中无意识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调动一系列情结,尤其是多次左右作家心理情感趋势的那一类,使进入构思意识活动的内容不自觉地带上个性色彩。心理学上解释要使情绪或情感引起神经中枢的各种变化,还在于刺激。本文认为刺激不光来源于外在事物,也包括人心理上的,外界感官刺激在虚静提供的心理空间中寻找内在契合点,相应情结便在神经网络系统内导下被召唤出来,但外物刺激并非缺之不可,作家创作也常常只靠自身情感的内在驱动,心里能量充满之时强有力的情结自然释放进入意识。沈括的《梦溪笔谈》与惠洪的《冷斋夜话》都曾谈及王维作画“多不问四时,如画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莲花同画一景”。外界自然景象并未影响王维,他更为注重的还是任凭自我情感的自由抒发。王维一生亦官亦隐,且早年开始信奉佛教,当仕途坎坷,命运蹇塞之时,佛家空无寂灭、超凡脱俗的思想便从长期积淀的心理深层突现出来,所以他的创作与世俗格格不入。屏息作画前,那种莫名、失意,更有超然闲逸、傲行于世的主导情结早已调动,等待一个释放的机会。他并非有意表现与众不同,是内心情结使然,而绘画正好成为他释放这种情结的载体。
综上所述,虚静的外在“静”与“虚”为这一系列复杂的“动”提供了活动空间。
二、虚静与梦幻迷醉状态的契合
创作方式多种多样,有一些特殊状态也可构思产生灵感,比如酒醉作诗,梦中偶得佳句,似乎谈不上创作前有所准备。这些状态中构思被触发,产生灵感,更为明显的体现出虚静的动态特征。
1.梦里不知身是客——梦与虚静求同存异的心理特征
梦幻是人的一种特殊的状态。根据尼采的观点,“梦的静观有一种深沉内在的快乐”,“为了能带着静观的这种快乐做梦,就必须完全忘掉白昼及其烦人的纠缠”[6](P13)。显然,梦幻与虚静有相似的首要前提:排除外界干扰。
从生理学角度看,“睡眠是一种特殊的能动过程,而不是一种完全无活动的状态”,“在睡眠时对白天所积累的信息进行特殊加工,但是人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相应的保证意识的皮质机能系统是被抑制着的”[7](P42)。因此,整个睡眠过程中一部分细胞仍在进行无意识思维活动,其活动方式分两种情况:慢波睡眠与快波睡眠。前者脑电波频率和各内脏器官活动节奏明显变慢,肌肉保持较为紧张的状态,此时较少出现梦;后者相反,脑电波频率加快,各内脏器官的活动出现不规则变化,肌肉完全松弛,梦往往出现在这个阶段。所以,梦的内在活动机制同样是:抑制导致兴奋。
梦与别的思维方式不同,它没有想像的介入。梦是自发的,包括大脑中的抑制与兴奋过程,所有活动均在无意识层面自发进行。这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人做的许多梦都没有意义,即使是作家灵感思维也只会在偶然的时候出现,并无规律可循。因此,梦中灵感实际是一种非理性思维的跃变,是心理空间里所有积存内容的不可思议的奇异组合,理性无可奈何。它遵循无意识活动规律,只是自始至终完全失去了理性的参与。
梦幻和虚静的外在状态似乎是相似的,都为静态,实质上有很大差异,梦的意识抑制是不自觉的,而虚静是在人为控制下进入静态。但虚静因为静引发内在的兴奋,而且这种活动在无意识层面进行,梦的这个特征更为明显。比较二者可看出它们的内在机制相似,即以静诱动,动是核心,静是切入点,为“动”提供充分活动的心理空间,使思维有了产生灵感的可能。
2.沉醉不知归路——醉与虚静并行不悖的内在机制
醉被尼采认为是灵感来临的心理准备,它与虚静一样使人处于意识松懈状态。根据兴奋与抑制相互诱导规律,思维活动转到处于兴奋的大脑皮层部位,无意识开始活动。尼采描述了这种完全忘却理性而陶醉于某种情感的无意识状态:它是“高度的力量,一种通过事物反映自身的充实和完满的内在冲动”,“时间感与空间感改变了”,“那些原本有理由互不相闻的种种状态终于并生互绕,相互合并”[6](P350)。这不正是无意识心理深层内容被兴奋机制激活而融合调整的过程,与虚静状态的内心活动相类似吗?
虚静与醉的动态活动的机制又是理性与非理性交替互动。醉使人忘却理性,使内在生命力高涨,产生种种审美状态。但醉并未失去理性。正如虚静一样,醉的形成是由于受到外界感观情绪上的某种刺激,人自觉抑制意识,而让无意识自由活动。因此,尽管意识完全松弛,但理性由于一开始就参与了活动机制,也仍会不自觉地守候在无意识旁,“受着神经系统相互诱导规律的支配,虽然越轨,但仍有一定的范围,仍遵循一定的轨迹”[7]。所以那些闪现高度灵感光芒的“醉”后作品并未思维混乱,毫无逻辑。虚静也是一种特殊的混沌,是混沌而又澄清的状态,虚而纳实,静而求动,没有理性不自觉地从中规范,非理性内容难以清晰而有意义地呈现出来。可见虚静与醉的内在活动机制有相似的特点:理性与非理性相互参与,交替互动。
虚静作为古代文论家频繁涉及的术语,其作用毋庸置疑。从文艺心理学角度分析,它更多的表现为内在活动机制,活动过程纷繁复杂,本文选取其中三种较为常见的动态,分析其中个人内心情结的唤起,原型意象的调动,非理性的驰骋,理性的参与等等。而外在有意识的入静,排除了杂念,涤荡了心志,为“动”准备了必要的心理空间,是创作构思的重要基础。从文艺心理学角度来观照,虚静之“动”对于创作构思无疑功不可没。
收稿日期:2003-0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