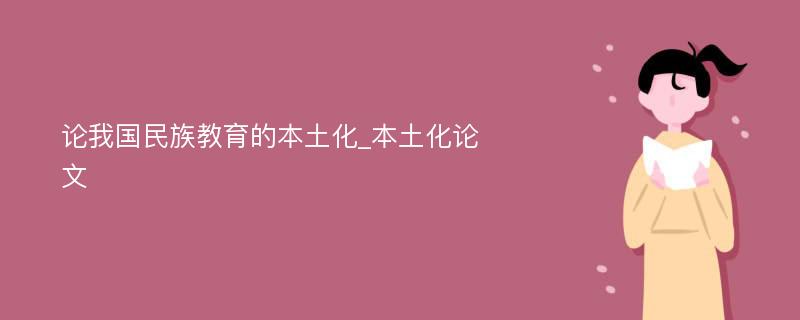
略论中国民族教育的本土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中国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全球现代化模式的多元化发展,发展中国家面对着西方化的种种冲击,各个领域都传出了激昂的呼声,教育领域也不例外,要求重新调整教育方向、适应本国的社会-文化现实的呼声日益强劲。正是在面对传统与西化的两难选择中,人们提出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要求”。中国的民族教育学的理论建构是在中国民族学和教育学的双重本土化历程中逐渐完成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于20世纪初年由西方传入,迄今已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注:何星亮:《略论21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中国教育学的近代化历程,从洋务教育、维新教育到资产阶级教育,再到无产阶级教育,从19世纪中叶一直到今天,也是中国教育学本土化的历程。(注:王鉴:《我国少数民族教育课程本土化研究》,《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如何认真审思中国民族教育学本土化的历程给我们的启迪,结合当今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发展和完善中国民族教育学,不少学者都曾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意见。笔者认为,从多元文化教育视角去理解“外来与内在”、“传统与现代”、“西学与中学”、“现代化与本土化”等中国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中的这些“二律悖反”,将对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形成本土化理念,中国民族教育本土化历程的方法论启迪
作为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现代教育相碰撞而导致的教育本土化研究可追溯到洋务运动与我国近代教育的萌芽。随着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帝国主义开始瓜分中国,清政府为了求强求富,抵御外患,防范内忧,维护自身的统治,支持洋务派,于是出现了洋务运动,在教育领域出现了洋务教育。洋务教育不同于传统的封建旧式教育,在内容上增加了西方文(外国语言文学)和西艺(西方一些科学技术知识)课程。这样,在课程设置上除了原有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外,增加了外国语和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概括地说,也就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迈出了教育本土化的第一步。这种“中体西用”的课程设置,是我国学校课程近代化的第一个里程碑,对后来学校教育的课程极有影响。(注:参见吕达著:《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8第51—53页。)
教育本土化研究与实施的第二个阶段便是维新运动与我国近代课程雏形的确立。所谓维新运动就是企图使旧的封建主义的中国变为新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的一场政治运动。维新运动在教育方面的主流便是废八股、变科举、改书院、兴学堂,最终导致了近代教育(包括近代学制和近代课程)在我国的确立。(注:参见吕达著:《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8第51-53页。)维新派的主导思想是认为学校课程应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并倡导我国学堂的课程改革应仿效日、美的模式。可见维新派在教育本土化的探索上比洋务派更激进、更西化,但仍不可避免地要兼顾“中学”。近代中国思想文化教育领域里,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持续了几十年,直到清朝灭亡,旧学与新学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地被解决。从一方面而言,这是两种思想力量的冲突与较量;另一方面,这也是人们在探索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时所处的一种方法论困境。作为本土化的过程必然伴随并顾及两种文化思想体系。这一点也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德国“真正社会主义流派”的时候,曾经说他们把法国那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他们不懂得“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注:《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7页。)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成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它的后果为基础的。”(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544页。)近代中国的西学(新学)课程是从西方搬来的,它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还缺少生根的土壤培植,因此,也为后人对教育本土化的进一步探究留下了艰巨的任务。
“五四”时期,教育领域里掀起了改革传统封建教育,倡导实用、科学、积极学习、引进西方近代教育的热潮。“五四”运动之后,西方教育思想被大量地介绍到中国,而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诸多教育活动的开展,实际上又构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一个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注:参见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第649页。)。其主题和核心,即是科学和民主,矛头直指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的内容与方法。这一时期的教育,首先是把教育与救国联系在一起,出现了较有影响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等。接着,中国国内一大批资产阶级教育家和爱国知识分子,从教育救国的立场出发,以西方的教育理论为武器,批判封建旧教育,并从各自不尽相同的目标出发,对教育的诸多方面进行改革,形成了较有影响的平民教育运动、科学教育运动、国家主义教育运动等。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各种教育实验纷纷在农村出现,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在1925年-1935年的10年间,各种农村教育实验区就有193个,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教育实验、晏阳初的河北定县实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验、陈鹤琴的“活教育”实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验、李廉方的开封教育实验、邰爽秋的“民生教育”实验等。以“五四”运动为先导,本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改革与实验,在课程和教学方法方面进行了本土化的探索。显然,它们均有来自西方的教育理论作指导,又都立足中国社会而开展实验研究。
如果说从晚清到“五四”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时期,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教育领域的改革与探索又使中国教育走上了现代化之路。以“教育学”这门探究教育现象及规律的学科而言,“中国化”的历程从“苏联化”到“多元化”再到“中国化”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道路和剪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领域的新探索。(注:陈桂生著:《“教育学视界”辨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4第432-444页。)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教育领域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思想的指导下,借鉴和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教育理论和经验,从办学形式到教育内容,从办学思想到管理方法,都在中国特色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着历史性创造工作。教育现代化是一个过程,虽然它已经开始启动,但它必将延续到未来,在这一过程中,本土化的中介与桥梁作用仍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教育学领域的探索相比,民族学领域的本土化研究的展开却是延续了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循中华民族与国外民族之比较而进行的,这一线索与教育领域的近代化、现代化是一致的。另一条线索则是沿着中国民族族群社会的探寻进行的。
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把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译成汉文,介绍到中国。1904年,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上刊登《中国人种学考》,从人种学的观点分析研究了中国之民族。1900年英国学者罗威的《民种学》,由北京大学学堂书局出版,并被清政府学部确定为文学科的大学主课。民国时期,孙中山提出“五族共和”的民族观,倡导“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五族为一人”,“国家之事由全国五族人共组织之”,“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丕兴实业,促进教育”。(注:《孙中山全集》第二卷(1912年),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第358页,第60页,第105页。)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论是早期的反满、“五族共和”,还是晚期的反帝与“民族自决”,都是在20世纪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实现中国各民族平等的一个典型方案。中国民族学的本土研究就是继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之后,于20年代至40年代,兴起的所谓“中国学派”的本土民族学研究类型。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民族学一直强调对本土社会的研究。1926年,蔡元培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就引用了大量中国上古文献,说明了西方人类学在本土族群研究中的可运用性。30年代,吴文藻带动下的一批富有创见的研究也是针对中国农村少数民族社会展开的。1930年,凌纯声前往合江及松江两省松花江下游调查通古斯系的赫哲族,“这是中国民族学的第一次田野调查,成为中国民族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注:李亦园:《凌纯声先生与中国民族学》,《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7第413页。)50年代的“民族学运动”则是在前苏联反西方的“东方论”指导下进行的,对推动中国民族学的本土研究作用重大。80年代以来,在谈到“中国化”时,中国学者往往把视角集中在“如何利用西方民族学为中国民族学现代化需要服务”这一问题的解答范围之内,而很少对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问题加以阐述。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具体研究历程,费孝通先生对“中国学派”和“本土观点”的论述,为民族学的本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费孝通开创的中国本土人类学,无疑将对人类学的反思和发展起重要作用。(注:费孝通著:《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6.9第127-142页,第313-356页。)费孝通本土人类学的核心内容有三:首先,费孝通主张,社会人类学应以本文化为立足点兼容异文化研究。其次,研究者应力图“进入”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又应懂得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问题。即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第三,对本土观念的强调,有助于消除文化距离造成的误解,也有助于促成文化的对话。
民族学中倡导的本土研究,绝非推广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或自我封闭的研究类型,本土化研究的目标在于“试图通过促使研究者充分地贴近于自身所处的社会场域,摆脱泛文化的认识论支配并提出替代性的解释模式。”(注:费孝通著:《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6.9第127-142页,第313-356页。)我们植根于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社会复杂、文化丰富的“非西方”社会,开展本土化的研究既要提防跌入西方现代化理论指导下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陷阱,又要医治充满偏见的“颠倒的东方论”影响下的心理危机。(注:费孝通:《跨文化的“席明纳”》,《读书》1997.8。)
我们评析教育领域和民族领域的现代化与本土化在中国的演进过程,目的在于通过已有的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去探究中国民族教育的现实与未来研究之路。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学和教育学为民族教育学的基础领域,更为重要的是本土化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第一,我国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可以从民族学与教育学的本土化历程中,确立自己本土化研究理念,从我国民族学、教育学的研究中汲取营养。第二,民族教育学本土化研究的目标与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目标相一致——“建立不同的理论概念,发展不同的研究方法”。(注: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序言,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1年。)第三,民族教育学研究从理论、方法到内容上的本土化,即教学论与课程论的本土化。正如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谈到人类学的本土化时指出的那样:“一门学科研究的本土化,不但包括研究内容要是本地的,本国的,更重要的是应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体现出本国文化的特色,而不是一味追求西方的模式。”(注:李亦园:《人类学本土化之我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二、双语教学之外,开发一种注重文化的教学法
在多元文化教育的视角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是世界多元文化教育潮流中的一种模式,中国各少数民族教育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中的朵朵奇葩。中国民族教育学的本土化一方面指的是相对西方多元文化教育的中国化,另一方面指的是相对于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化”。前者被称为“大多元”,后者被称为“小多元”,再加上少数民族的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中国民族教育的本土化研究就显得十分丰富。不过,有两个方面却是反映多元文化教育所必须的,这便是双语教学与多文化课程。
关于双语教学,我们一直把它作为民族教学论的特色加以研究和贯彻,我们研究的重点在于构建双语教学论的体系,从概念、模式、理论基础,到双语教学的方法、原则、机制,所有的实验与理论建构的目的在于从形式上使民族教育中的教学与普通教学有所区别。这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深入拓展,并十分有必要深入拓展。笔者在这里强调双语教学,是指我们在研究双语教学时被忽视的领域,那就是对注重文化差异的教学法的开发利用。
首先,我们必须审视传统的、舶来的、陈旧的教学法对双语教学造成的流弊,它成了双语教学法中的主导模式。目前民族地区应用的正式课程及其教学法均是来自内地,正因为这样,尽管我们在双语教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甚微,双语教学法偏重对两种语言使用形式的追求,而很少去看重教学方法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在有的地方,甚至人为地为双语教学而办双语教学。显然,与双语教学这一形式相配的不仅仅是双语教学理论本身,还包括双语教学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手段这一本质内容。
其次,随着教育民主化的进程和教学法的革新,传统的教学法在不断地更新着。这也引起了舶来教学法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反思双语教学中的教学法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由此在民族双语教学论领域开始关注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最新成果。先是对这些理论的移植,后来才是这些理论的本土化。民族教育学家反思这样的问题:认知是学习者的生活、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组成部分,这就是“环境认知”的概念,用陈旧过时的学习原则和异文化产物的方法来禁锢学生的头脑,这样做公平吗?有没有一种关于教学法的理念可以强调在不同文化中影响到不同学习方法的潜在的社会-文化因素?所以教学法的效果与教学法的使用对象关系密切,关键是方法要切合文化的需要。我们教育学中讲得最多的教学规律中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的关系问题就是对这一关系的反映,课程理论中所谓的儿童、知识、社会三要素关系问题也是对这一现象的把握。
再次,教学法的本土化应该注重两个领域:一是方法本身的研究,这就要求与民族教育心理学的理论相结合,研究儿童的认知特点、思维规律,研究民族文化传统与教学方法的关系等。二是对民族师资的反思,即要求双语教学中的师资必须是有双语现象背后的双重文化知识的教育者。因此,教学法的本土化要求反思教师。我国民族教育中的双语教学与师资队伍的建设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但都走了一条由“外来化”到“本土化”的道路。民族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教育学的角度考虑较多,从民族学的角度考虑较少,所以照搬内地教育模式。80年代以后,随着多元文化理念的形成和教育民主化运动的推进,民族教育中本土化的内容和方法才逐渐得以重视。民族教育中师资队伍的建设亦然,先是引进汉族教师较多,再是汉族教师和民族教师并重,也是80年代后才逐渐重视本土师资的培养。可以说在我国民族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汉族教师深入民族地区长期从事民族教育工作,为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具大贡献。他们是现代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启蒙者,但他们却基本上一直站在现代民族教育的边缘,当他们从文化上真正融入到该民族时,他们已经到了快退休的年龄。如果总结他们的教育经历,恐怕就是从外来化到本土化的过程。
双语师资就是强调开发一种注重文化差异的教学法,只有立足本土文化,进一步强调教师在课堂上重视文化遗产,才能把它写进积极的教学法,同移植照搬的模式相比,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教学法更容易让人接受。在民族教育中一味地照搬移植教学法容易将异文化“反省”和“反省实践”的非本土化思考观念融入现实教育体系。托马斯(1955)曾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注:参见V.K.拉伊纳:《发展中国家师范教育的本地化:印度的情况》,《教育展望》(中文),2000年第1期。)托马斯在研究中发现,马来西亚学生中种族众多,而课程制定者却没有利用三个主要种族的丰富的文化背景。事实上,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等东南亚民族在艺术、讲故事和音乐等方面都颇有才能。这些多文化遗产借助各家夜总会和全年众多的公共节目,在校外得到尽情展现,但却常常被课程制定者贬低。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导致很少有人关注学校教育领域。在我国的民族教育中这一现象同样存在,我们在进行民族学田野调查时发现,在藏族地区,有些学校在当地不受欢迎。究其原因,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这些学校的办学与本地本民族的实际脱节,相比之下,一些寺院倒是颇有吸引力。本来现代学校教育要比寺院教育大有市场,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不得不让人反思学校的课程与教学法。可见,再好的课程与教学法,如果不与本地本民族的实际相结合,也难以产生好的效果。
民族双语教学论的建构如果只重视语言的形式而不注重语言的文化本质,这样的体系必然是不全面的,教学论学科长期探索“怎么样教?”的问题与课程论领域长期追寻“教什么?”的问题不是截然对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教学论常常把课程作为教学内容研究的一个主要原因。由此而观之,民族教育中的双语教学仅仅是一种手段,真正的目的是传递文化,目的为手段服务,教学法为传承文化服务。
三、多元文化课程,三级管理体系
1999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即三级课程、三级管理(见决定第14条)。显然中央的决定是在借鉴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确立的新世纪课程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体系分为传统教育和现代学校教育两部分,传统教育部分的课程主要指民族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科学知识、生产生活经验等方面的内容;现代部分的课程主要指有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内容。由于国家一体课程中较少考虑到少数民族传统教育的内容,因此照抄照搬内地课程模式成了必然的选择。
80年代以后,随着地方安排课程、校本课程在我国的兴起,少数民族地区先后出现了民族地区统整课程。民族地区的一些学校也开设了乡土课程、民族文化课程等。这些课程的开设使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学校教育中融为一体,跨文化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的课程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中所占比例正逐渐扩大,作用也日益显现。多元文化课程的三级模式也由此形成。
(一)国家统整课程模式
国家统整课程模式的范围包括中华民族内部的56个民族,通过达到全国性的系统化行动而设置的课程,它不仅包括少数民族,而且包括主体民族。这决非是强迫推行,而是国家民族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各族人民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客观要求。以前的国家一体课程,如历史、地理、语文、社会、艺术等课程内容中已渗入了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些因素,但这还远远不够。
国家统整课程的表现形式分为显露课程和潜在课程两种。可以有必修课,也可以有选修课;可以正规课程形式反映,也可以非正规课程形式反映;可以学科课程实施,也可以活动课程实施。具体地讲,专门课程可通过两种方式来完成,一种是在已有的一体课程中增加多元文化教育的内容,如在语文、历史、地理、艺术、哲学、社会等课程中以平行式策略、附加式策略、普及式策略增加多元文化的内容。另一种是在改革学校课程的过程中以选修课的形式增设如“多元文化学习计划”之类的课程,让学生了解多元文化的社会与价值、多元文化学习的最大目标、教师的态度、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等。也可以是两种方式相结合而体现专门课程的内容。国家统整课程中的潜在课程的实施,多以活动课程的类型来完成,也可以是非正规课程的一种。要求国家的教育从师资培养、学校评价、学生课外读物的出版发行、社区的环境等方面多渠道体现多元文化的内容,并最大限度地以积极的方式影响学生的语言、行为及态度。要求学校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一些课外活动和校外活动,有助于学生了解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及价值取向,培养学生之间共处的态度与能力等。
(二)民族地区统整课程模式
民族地区统整课程包括各民族层次和乡土、区域层次。提出民族地区统整课程模式的依据有: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取向等方面均有不同的内容可供编入课程;各民族居住的特点上有共同之处,有大聚居区,如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有小聚居区,如各民族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各民族有相似的民族教育任务,既要面向世界,又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还必须弘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
民族统整课程模式要求少数民族教育课程体系的确立与完善。有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24个)的课程设置,应以双语教学为体系,以民族语文为载体完成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生物、艺术、体育等课程的相应设置,教材编写内容也应突出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特征。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和已经采用汉语文的民族(如满族、回族)的课程设置,在教材的编写上同样可反映出民族文化的特征以及多元文化的社会与价值。这些课程,从课程计划来看,可以是学科课程,也可以是活动课程;从课程性质而言,既可以是必修课,也可以是一些选修课。例如,藏族教育,除了实行藏语文、汉语文并行的双语教学体系外,其课程体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要求有形式和内容上的“通车”,形式上指藏语为载体,内容上指反映中华民族文化、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教材编写上,从照搬普通教育教材到双语教学教材,从翻译、编译藏族各科教材到编写修订藏族各科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多元文化的内容和民族文化的筛选应作为主要的材料。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课程设置的科目不同,编写的教材也就不同,即使是相同的科目,也因教育的对象不同,编选内容的范围与程度也应有所差异。这样的课程及其配套的教材同样还必须结合国家的课程计划和一体课程,才能作为民族层次的统整课程。至于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少数民族和转用汉语的少数民族,其课程与教材的体系虽没有以民族语为工具的课程体系强,但从民族层次上,以多种形式,或学科课程、或活动课程、或潜在课程、或选修课程等等,统整本民族教育中的课程,既使其课程体系表现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征,也表现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三)学校整体课程模式
该课程模式主要适合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学校和散杂居区的民族学校。学校可在国家课程计划、民族统整课程的基础上,通过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两种类型来改革学校环境,使之以潜在课程的形式进行多元文化教育。在西方称其为校本课程,校本课程开发指学校根据自己的教育哲学自主进行的课程开发,它实质上是一种以学校为基地进行课程开发的决策过程。校长、教师、课程专家、学生以及家长和社会人士共同参与学校课程计划的制定、实施和评价活动,涉及学校教育经验的各个方面。
学校系统内的课程设置可以专门课程与民族课程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专门课程系指学校在学科课程之外附加的特殊课程,多以选修课和潜在课程形式存在,是由教师的多元文化教育意识、能力、态度和学生的学习兴趣所决定的。民族课程是学校与社会某些机构、家庭等通过分工合作方式,以活动课为主要类型,通过校、班、组的参观、访问、调查、参与活动、社会实践、教育实习等,了解体认本民族的社会文化特点、现实状况、未来发展之需要,从而培养本民族的认同感、责任感、使命感等,培养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人才。
以上三级课程模式并非彼此孤立的,也绝非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中齐头并进。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多元文化教育的课程仍以非正规课程为主,以选修课居多,这些课程的理想是否能够在国家的正规课程中有所反映,仍有赖于多种形式的试点实验的成果及其推广,有赖于多元文化教育及其课程理论研究对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影响。
正因为这样,笔者认为,多元文化教育及其课程理论在我国仍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若要系统而全面地反映到实践当中,仍需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实践者的不懈努力。从世界多元文化教育发展的状况与我国多元一体教育发展的政策、进程方面来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教育课程的贯彻与实施,将是21世纪中国民族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这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标签:本土化论文; 民族学论文; 双语教学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社会教育论文; 教育学论文; 费孝通论文; 课程论文; 多元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