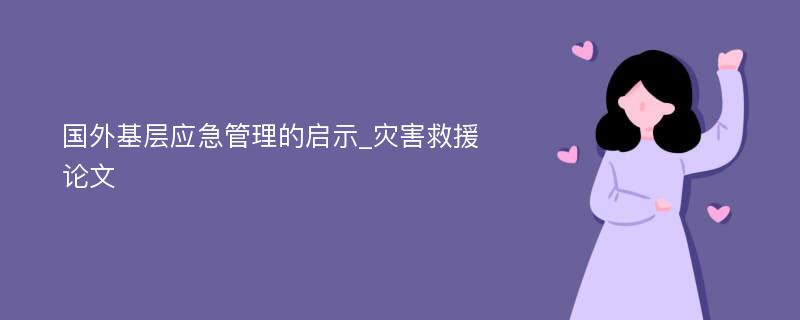
国外基层应急管理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层论文,启示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应急管理是指针对灾害和危机等突发公共事件进行预防监测、应急处置和恢复重建的全过程管理,欧美各国称之为“紧急事态管理”。为有效预防与应对各种灾害和危机,建立一个更安全的世界,联合国呼吁国际社会在灾害与危机的管理、民众个体的安全保障、安全社区建设与公众参与、政府的政策支持与防灾应急能力建设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一些发达国家从本国实际出发,结合民众需求,在基层应急管理的理念更新、制度建设、组织管理、能力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一、国外基层应急管理的工作理念
(一)防灾行政一元化、行政风险分散化、防灾参与社会化
近年来,各国都在构建和完善危机管理体系,应急管理工作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基层管理中呈现出防灾行政一元化、行政风险分散化、防灾参与社会化等趋势。特别是“9·11”事件后,各国普遍认为,包括基层在内的原有的防灾行政体系远不能适应新型危机的各种挑战和综合协调,需要导入危机管理的理念和模式,进行更高层次的、综合性的资源整合和组织业务整合。因此,在2001年,美国纽约市的紧急事态管理办公室即升为局级单位,开始提供综合性危机管理服务;日本各地方政府在最近五年中,也纷纷改组机构,成立危机管理机构,建立及时、有效应对各种危机的政府体制。
(二)以居民为主、立足于基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世界性灾害和危机频繁发生,人们的生活环境、地区社会的安全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化,基层民众对防御和应对灾害和危机事态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以居民为主、立足于基层成为各国推进应急管理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理念。比如,在东京地铁沙林恐怖事件后,东京市民要求政府在传统的防灾减灾体制的基础上,增强针对生物化学恐怖袭击的应对能力;而欧洲各国居民也普遍要求本国政府与欧盟认真处理疯牛病问题。
(三)高质量、高效率的民主型危机管理
政府的公共安全保障和应急管理的目标,不再局限于减少公众生命财产损失,更涉及到维护政府的正常运转和公信力等。在应急管理行政体制上,各国通过行政改革,在重视综合防灾减灾的基础上,趋向于构建符合现代社会民主的危机管理体系。这种危机管理体系,要求进行高质量的、有效率的民主型危机管理,即在现有的民主与法制的框架中,政府在预防和处理危机事态等非常态事务中,实现具有充分的预测和预备、能快速应对、高效率、透明公开、责任明确的目标。在基层防灾行政或公共安全事务中,民主管理、权责分明、绩效评估、领导问责等方式更加明确。比如,英国政府应急管理的三个目标之一就是不论是基层,还是国家,必须保障民主和法治的程序。
(四)重心下移,从强调“政府的作用”转变为重视“建设应对灾害能力强的社区”
联合国在1999年“国际防灾战略”(ISDR)中提出的“在21世纪建设更安全的世界”的三大战略之一,就是倡导重心下移,从强调“政府的作用”转变为重视“建设应对灾害能力强的社区”。2005年的联合国减灾大会进一步强调防灾社区建设的问题,而早在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即提出了“安全社区”的概念,并制定了安全社区的认证标准。随后,安全社区的建设在全世界被推广,并通过教育、沟通、培训等方式,提高社区的自救互救能力。
此外,为了防止民众过度依赖政府、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分散政府的应急管理风险,有些国家在法律中强调政府应急管理责任的有限性原则,明确基层居民自救互助的职责。如日本在1961年制定的《灾害对策基本法》中,对国家、都道府县、地方公共团体的责任及相互协作和居民等的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关于基层居民的责任,第7条规定:地方公共团体的居民在自己采取防备灾害手段的同时,必须努力参加自发的防灾活动,为防灾工作做出贡献。《东京都震灾对策条例》明确规定了东京政府知县、市民和企业的职责,也在条例开头强调了两个理念:一是根据“自己的生命自己保护”的自我责任原则的“自救”理念;二是“我们自己的城市(社区)我们自己保护”的“共救”(互救)理念。根据这两个理念明确市民和行政的“公救”的原则以及合作方式,要求市民在努力确保自己安全的同时,相互合作,并必须努力采取相应措施。加拿大的《联邦政府紧急事件法案》等法律也规定,灾害发生后的自救互援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职责;各个家庭也有义务在72小时内做好自救工作,并强调受灾人员之间应该做好互救工作。加拿大《联邦政府紧急事件法案》等法律规定,灾害发生后的自救互援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职责;各个家庭也有义务在72小时内做好自救工作,并强调受灾人员之间应该做好互救工作。
二、国外基层政府应急管理程序和思路
(一)常态与非常态相结合的事前准备
1.预案体系
为了提高基层民众的应急能力,使应急预案精细化,强化可操作性,是十分必要的。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除了制定全国防灾计划外,还制定了社区版的“可持续减灾计划”;美国紧急救援中心通过对已发突发公共事件的总结,不断修改应急预案,使之更详细、实用,更接近实际,更具可操作性。应急预案不仅包括交通、通讯、消防、民众管理、医疗服务、搜索和救援、环境保护等内容,还包括重建和恢复计划、心理医治等内容。预案随科技进步适时修订,并注意针对新的突发公共事件及时制定新标准,以适应应急管理的最新发展。
2.预警系统
把风险防范与管理纳入到常态管理中,建立灾害风险和脆弱性评价体系以及早期预警系统,是联合国提倡加强防灾应急管理工作的主要策略之一。印度尼西亚政府指出,没有建立早期预警系统,同时缺乏对居民的灾害教育培训,是导致印度洋海啸损失惨重的最主要原因。与此相对,日本在全国建立覆盖全面的基层无线网系统,包括户外扩音器、家庭接受器、车载无线电话移动系统,并由基层政府办公区、学校、医院、福利设施、消防等机构的防灾网络系统构成。当发生地震等灾害时,居民的第一反应便是打开电视或收音机了解灾情。
3.应急规划
国外许多城市在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中均把安全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同时,有基层居民参与的安全街区规划设计也成为一种新生事物。联合国防灾战略事务署特别强调,在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时,必须综合考虑社区安全与降低自然危险、人为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东京在2000年城市发展战略中就提出建设“防灾生活圈”,实现“不用逃跑的街区,安全安心的街区”的建设目标。
建设应急疏散避难场所和应急通道,能够提高灾民避难成功率。各国以平常的社区活动范围为中心,事先建设和指定避难场所。到2002年4月为止,东京在地区居民生活圈附近学校操场、神社、寺庙院内、公园、绿地、小区广场等地指定临时避难所4663处。此外,各区的小学、中学、高中和公民馆也被指定为室内避难收容所,在校内必须设立仓库,储备食品和药品、帐篷等应急物资,标准为每2人3.3平方米左右,按照学区单元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二)快速高效的事中处置
1.快速响应
重视发生灾害时的第一时间启动(先期处置)和紧急动员机制是政府应急响应能力的重要表现。以地震为例,东京政府制定了应急处置时间表,分别对灾前、灾后3小时之内、灾后3~6小时、6~12小时、12~24小时、24~48小时、48~72小时之间的主要工作作了规定。灾害后3小时之内,必须召集职员,设立灾害对策指挥部,收集受害损失信息,向市民通报和披露信息,媒体报道灾情,请求自卫队出兵救援,对危险源设施等采取应急措施,引导居民疏散避难,布置保安警备,对交通进行限制和管制,开展救助和急救行动,收集和传达医疗救护信息。东京都规定在成立灾害对策指挥部后,根据灾情,发出1级到5级的紧急状态动员令,动员各局、各地方派驻机构以及政府总部的职员紧急出动。最高的紧急状态为第5级配备状态时,即在第4级配备状态不能应对或发生烈度6度以上的地震时,灾害对策指挥部总指挥发令动员约13万政府职员全部进入应急状态,并可以在就近的社区开展应急救援行动。
2.应急救援
在应急救援方面,突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跨区域的应急救援合作。在高龄化社会中,对灾害弱势群体的关怀和救助也成为当今发达国家基层应急管理的关注点之一。美国的国家服务公司成员包括美国和平队、美国志愿者协会、民间社会团体和退伍军人协会,服务公司负责组织工作小组到最需要志愿者的地方帮助年老的、有身体伤残和精神伤残的、低收入的人员。日本最近建立了“灾时需要救援者救援的制度”,灾害弱势者通过事先登记的方法,向社区提供信息,在发生灾害时能够得到社区的救助。
在跨区域合作方面,东京政府与周围其他地方政府、其他大城市合作,签订多项72小时相互援助合作协议。协议中对于救灾物资的提供和调拨,救灾人员的派遣,救援车辆、船只的供应,医疗机构接收伤员,教育机构接收学生,以及自来水设施等的修复和供应,垃圾和下水处理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说明。一旦东京发出援助请求,签订协议的周围地方政府都会“挺身而出”,及时提供救援。阪神大地震后,日本全国2000多个市町村都签订了72小时相互援助合作协议,使得联合防灾救灾形式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和山村。
(三)重要保障
1.法制保障
针对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的需要,发达国家构建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明确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团和公民个人的权力、职责和义务,强化了“自救、互救、公救”相结合的合作关系。以此使应急管理工作法制化和标准化,保障基层工作依法、有序地开展。同时强调政府应急管理的责任有限性,明确基层居民自救互助的职责。
日本多次修改1961年出台的防灾应急管理的母法——《灾害对策基本法》,该法明确规定了各级政府、中央及地方公共机构、企业和居民的基本责任和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其中,第5条规定了市町村长必须完善消防机关、防洪团等组织体系,加强本地公共团体等防灾组织及以邻里合作精神为基础的自发性防灾组织的力量,努力发挥政府的所有功能。
2.应急物资储备
为了减轻突发事件应对中政府的负担,有效地分散政府应急管理的风险,让民间部门和社会团体以及各种社区积极参与到防灾减灾和应急活动中是十分必要的,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便采取了与民间部门和团体事先在灾前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以确保能迅速调配和整合的应急物资和避难空间。除了与政府的合作外,灾前协议型伙伴合作机制还包括民间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安全合作。
根据《灾害救助法》第37条,东京都每年必须将前三年地方普通税收额平均值的千分之五作为灾害救助基金进行累积。2002年累计有110亿2629万7,495日元(相当于1亿美元)。除了都政府之外,各区和市町村政府也进行大量物资储备,至2002年底,市区建有1,500立方米的地下应急供水池47座、100立方米的地下应急供水池17座;至2003年4月1日,简易厕所达371805个;设在学校的救灾物资储备仓库有1516个,设在社区的防灾储备仓库610个,其他为144个,共2271个。这些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以及每家每户自备的避难急救袋,就足够维持灾后72小时的应对。
(四)群策群力
1.社会动员
在社会动员方面,各国重视完善各类基层防灾应急组织的建设,鼓励志愿者活动,发挥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作用。
纽约市通过公民团(Citizen Corps)、社区紧急事态反应队以及政府-私人紧急情况计划(PEPI:Publicprivate Emergency Planning Initiative)等组织形式,提高公民的志愿者服务水平和危机防范意识。公民团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起的一个项目,旨在充分发挥公民中的志愿者精神,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志愿者服务水平。公民团理事会(Citizen Corps Councils)主要负责处理州和地方志愿者的活动,帮助营造更加安全的社区,加强社区应对恐怖主义袭击、犯罪活动、公共卫生事件及其他种类灾害的能力。
新加坡构建了社区民防系统,实施民防志愿者计划(Civil Defense Volunteer Scheme)。截至2002年5月,已有6万名民防志愿者参加了该计划的技能培训,学习急救、救难、撤离和救火知识,以便应对社区的紧急状况。
在发达国家灾害与危机事态应对过程中,大量的志愿者组织参与其中,成为基层应急管理的一支重要辅助力量。英国在基层应急管理中也鼓励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建立应急救援队伍,承担部分公共服务功能。日本政府通过修改《灾害对策基本法》,明确规定了志愿者活动在防灾行政事务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并将每年1月17日定为“防灾与志愿日”,将每年1月15日至21日定为“防灾与志愿周”。2001年5月,消防厅开设“灾害志愿者数据库”,为志愿者中心提供方便的检索服务,促进地方政府与志愿者团体的信息沟通和交流。2003年6月,日本全国都道府县(省级政府)和所有计划单列城市,都设立主管志愿者的部门。
2.公共沟通
公共沟通主要是加强传递信息,推进全民减灾教育运动,塑造应急安全文化,以此提高具有理性的国民危机意识。
英国政府部门高度重视与社会公众及时、双向沟通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美国纽约市紧急事态管理办公室(OEM)在危机爆发前,通过它的公众信息办公室(OPI)不断地向公众宣传防灾、减灾知识;危机爆发后,该办公室协调公众信息战略,确保纽约城从各政府机构和相关组织向外界传递信息的一致性。
新加坡通过紧急公共信息中心(EPIC)向公众及时提供官方的信息。2001年2月,向95万户家庭派发了各种语言的《民防实用紧急手册》。2005年,政府印制了110万册《流感疫情指南手册》,介绍禽流感和流感的预防措施等。俄罗斯发动基层力量,建立了信息员制度,全俄境内每个村、居民点设立信息员,将灾害情况及时通过网络报告紧急状态部门。
防灾安全教育分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企业教育,三者相互结合。发达国家比较重视学校安全教育,从小学抓起,把防灾安全教育纳入教学大纲。社会安全教育往往与社区活动相结合,通过各种活动展开。美国社区紧急事态反应队的活动也深入学校。如在华盛顿州的Marysville中学成立了中学生紧急事态反应小组,让学生学习急救知识、地震灾害和应急反应对策等等。
日本的防灾教育特点是,在点上抓学生教育,在面上开展国民防灾教育运动。神户市兵库县制定了“新防灾教育计划”,强调“心”、“知”、“技”,把防灾应急内容渗透到各门课中,使学生增强防灾应急安全意识,不断根据本地区的特点,掌握应对各种灾害的相关知识,提高防灾实践能力,在灾害中实现“自救”。同时将道德教育、课外特殊活动、综合学习相结合,成体系地推动防灾教育,培养学生相助和志愿者精神,为安全、安心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了纪念死亡14万人的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日本把每年9月1日定为“防灾日”,全国各基层都会组织开展防灾训练和教育活动。各地还建立了很多防灾安全科技教育场馆,宣传应急安全文化,并与资格认证培训工作相结合。
三、国外基层应急管理具体实践中的闪光点
(一)以居民为本的预警系统
建立以居民为本的早期预警系统,是联合国汲取印度洋海啸的教训,在2005年联合国减灾大会上提出的。它与推广灾害风险评估法、构建灾害风险和脆弱性评价体系一起,作为“构建灾害防御能力强的国家和社区的2005-2025行动框架”的5大重点领域之一,要求在全世界推广。日、美、澳等国的具体实践充分反映了除了依靠科技外,还应重视居民的参与,以居民为本的理念。
(二)安全社区——社区睦邻组织、防灾生活圈
通过社区睦邻组织建设,创建防灾生活圈,能有效提高社区的抗御灾害和灾后自我恢复能力。社区睦邻组织运动,最初由英国东伦敦教区的牧师巴涅特发起,后来发展成为由教会、慈善组织、基金会共同参与运行的社区互助运动。日本在城市和社区建设中采取了“防灾生活圈”和“应急避难场所”的措施,在基层组织上重视扶持各种防灾组织。在阪神大地震后,日本着重加强建设抗御灾害能力强的社会和社区,提出“自己的生命自己保护”、“自己的城市和社区自己保护”的基本防灾理念,不断加强地区居民特别是社区居民之间的连带感,促进行政、企业、地区和社区(居民)以及志愿者团体等的合作和相互支援,以建立一个携手互助的社会体系。
(三)都市圈应急救援合作
在流域圈、生态圈或经济圈的社会经济关联中,一个城市与周围城市以及与农村或山区建立协作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当发生大规模的灾害或重特大事故时,需要整个城市圈的合作及与周边农村的合作。通过合作,建立城乡防灾圈和跨区域防救灾机制,将形成一个以大都市为中心的防灾与危机管理的合作圈,促使城市对农村的支援、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援,有助于提高城乡和区域的共同防御能力。如日本签订72小时相互援助都市圈应急救援合作协议,值得参考。
(四)公私合作的应急物资储备
如何减轻政府的应急物资储备的负担也是政府基层应急管理的重要问题。像日本等一些国家的地方政府采取了与民间部门和团体事先在灾前签订合作协议的方式,这种做法不仅减轻了突发事件应对中政府的负担,有效地分散政府应急管理的风险,而且使民间部门和社会团体以及各种社区能积极参与到防灾减灾和应急活动中,确保能迅速调配和整合的应急物资和避难空间。
(五)居民应急的“土”办法
在建立灾害风险、脆弱性评价体系及早期预警系统时,不可忽视本地居民的力量,要让居民参与,发挥居民传统应急机制的作用。联合国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在亚洲开展了“可持续社区减灾试点”活动,主要是通过居民参与风险评估过程,加强社区对脆弱性的认识,挖掘居民防灾应急的“土”办法和完善传统应对机制,确立开展持续性的参与机制和行动机制,建立有效的社区防灾应急管理数据库。
标签:灾害救援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 社区志愿者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安全理念论文; 国外工作论文; 国外教育论文; 行政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