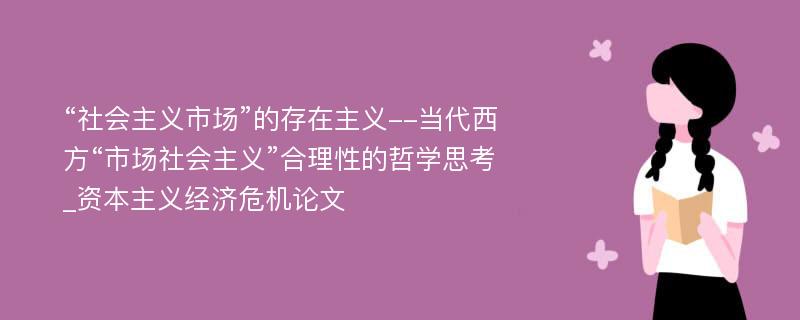
“社会主义市场”存在论——对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合理性问题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论文,性问题论文,当代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04
上个世纪90年代问世的各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对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主义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现代性似乎是惟一能生存下去的襁褓婴儿”的观点的反驳 ,也是对奥斯卡·兰格率先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课题的重新思索和探讨。
我国学术界对容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注:Yunker,T.A.,1992,Socialism
Revised and Modernized:the Case for Pragmatic Market Socialism,NY:Prager
Publishers.)韦斯科夫的“民主的基于企业的市场社会主义”(注:Weisskopf,T.,1993 ,A Democratic Enterprise Based Market Socialism.Market Socialism:the Current Debate,Oxford University.)以及罗姆的“配给券市场社会主义”(注:Roetmer,John .E.,1994,A Future for Soci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等模式都进行了介绍 和论述,然而迄今为止,所有的论述几乎都停留在是否有参考价值的平台上。本文拟从 经济哲学的视野,对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合理性问题给出自己的思考和探 索,并论证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市场”概念。
一、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础应当是什么?
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或理论的提出,首先必须以对失败的社会主义经济的 辩护为前提;第二必须以对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对兰格“市 场社会主义”的批评的反批评为前提。如果说,对前者的辩护说到底还是依赖可以有一 个不同于前苏联和东欧的合理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话,那么论证“市场社会主义”的 合理性,仍然首先取决于能够给予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对“兰格模式”的批评以言之成理 的反批评;其次才是通过对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性探索,思考如何给 出可论证的彻底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或模式等问题。
“兰格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该模式的提出,首先依据 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关于市场均衡状态时商品的价格等于生产成本的结论,其次是 依据维塞尔、帕累托和巴罗涅等人的有关研究。熊彼特曾说:“巴罗涅的研究或任何与 此相类似的研究的主要结果是:无论对于哪种中央控制的社会主义,均存在着这样一组 方程,这组方程具有一组惟一确定的解,其意义和条件一如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 注:熊彼特,1994,《经济分析史》,第3卷,第348页,商务印书馆。)
但是,这个模式还是受到了以哈耶克、米塞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的批评。首先他们提 出,仅仅计算问题就是不可解决的。这不仅因为涉及到计算的“无穷性”和“滞后性” 问题,更因为这种计算在原则上就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由哈耶克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 “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含义。哈耶克认为,社会科学涉及的知识散布在一种(比如资本 主义的)社会制度的所有方面,而且“社会”、“市场”、“法律制度”等等都不是代 表“实体”的概念。所以,这些知识只对在该社会中的行为者的决策起作用,并且由这 些行为所表现的“事实”其实只是行为者观念的外化,“事件”也只是一种假设、设计 或解释系统。可见,我们从市场经济中获得的统计数据根本不适用于非市场经济的社会 ,反之亦然。
应当说,计算问题主要是针对计划社会主义的(巴罗涅曾给出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体制 的资源配置模型),但实际上也关系到“兰格模式”。因为即使该模式运用“试错法” 确立了符合市场均衡的计划观,但一旦按照计划从事经济活动,对计划的非市场执行也 就破坏了原本的市场均衡状态。然而,哈耶克等学者对“兰格模式”的最根本的批评还 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计算问题,甚至也不是“计划会破坏资本主义生命力源泉的核心结 构”的观点,而是他们所论证的下述论点:与竞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化是英美传 统的个人主义观点,以及市场必须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观点,亦即只有在市场、私有制、 自由竞争三个基本要素的组合社会中才有“柏拉图效率机制”的观点。一句话,最根本 的批评是针对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本身。
应当承认,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最初对计划经济与效率之间的冲突估计不足,囿于效率 问题长期无法解决,才想到了“兰格模式”,要搞“市场社会主义”。但是他们(诸如 南斯拉夫等原东欧国家的学者)仍没有认真思索“兰格模式”的合理性和问题所在,没 有思索熊彼特结论的外在性,只是把市场羞羞答答地搬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比如他们提 出的所谓“分权模式”,一方面仍然是一个游离于真实市场活动之外的模式,因为在该 模式中,连作为生产资料的产品市场都没有;另一方面,分权只是把大计划分成若干小 计划,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冲突依然存在。所以,他们既未能实现持久的效率,也未 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平等目标,他们的实践失败了。
“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是英国工党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倡导的。1995年4 月29日,英国工党通过了对原党章第4条款的修改,修改以后的条款是:“本党赞成在 公共利益的基础上管理强大而来源丰富的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的存在既是公正社会,也 是有生命力的成功经济的重要基础;本党既需要有社会责任感和适当控制的私有因素, 也需要有奠定在效率和公共基础上的公有制。”(注:转引自吕薇洲,2002,《市场社 会主义论》,第7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修改后的第4条款与原条款的最大区别在于, 承认私有制的合法地位和要求公有制必须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可以认为这个修改的确 已经涉及到哈耶克批评的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并且正是基于这些实质性的变化,当时的 工党领袖布莱尔(Tony Blair)明确提出了在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妥协的“第三条道路”的 口号。他说:“第三条道路是最好的道路”,“第三条道路是对社会民主的重要的重新 评价,它深刻地影响了左派对新的基本探索的估价。”(注:Blair,Tony,1998,The
Third Way:New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The Fabian Society.)20世纪90年代 以后的各种“市场社会主义”,与“第三条道路”所反映的“市场主导”思想是基本一 致的。有人把这些新模式的共同特征总结为:第一,它们都致力于兼顾效率和公平;第 二,它们都以某种形式保持“公有”;第三,它们都允许企业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追求 “最大利润”;第四,它们都力图建立一个有效而民主的投资管理体系。(注:转引自 吕薇洲,2002,《市场社会主义论》,第117~11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然而,这4个 处于现象层次的共同特征之间的关系是否是逻辑自洽的呢?
我们不妨选择相对合理而且完整的“配给券市场社会主义”蓝图作为一个典型。罗姆 提出,社会主义者想要的东西无非是以下三个:(1)自我实现和幸福的机会平等;(2)政 治上的机会平等;(3)社会地位平等。所以,社会主义就是平等。而且由于物质不平等 是首要的不平等,它影响着其他的不平等。因此罗姆认为,只要构思出一个实现了利润 平均分配又保留市场机制的社会组织体制,也就给出了合理的“市场社会主义”蓝图, 这个蓝图就是他设计的“配给券市场社会主义”蓝图。(注:罗姆在《社会主义的未来 》中给出的“配给券市场社会主义”方案可概括为:在这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种 资金制度,商品资金——货币用来购买消费品;分配资金——“配给券”用来购买公司 的股权,两者不能兑换。每一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可获得一份相等的配给券,但用配 给券购买的股票不能转让,公民去世后由国家连同未用完的配给券一并收回。公司的发 展可通过国家银行管理的信用市场,以及依据国家计划将公司发行股票而收回的配给券 兑换为货币的方法获得资金。)其理由是,该蓝图建立了一种新的资产所有权关系—— 运用“配给券”平均分配社会资产收益,这种新的财产关系又能够避免企业受到政府低 效率的干扰,能够保持竞争和创新的活力。
然而,在所谓的兼得目标实现等问题上,罗姆的蓝图仍然受到许多学者的言之成理的 质疑。对于“平等”,萨斯指出,真正重要的平等是一种用“非物质”术语表达的地位 平等,因为地位不平等意味着权力不平等。而那些处在市场边缘地位的人,必然受服从 或服务于他人的传统规范的影响,从而必然损害他们的尊严,甚至有可能导致自暴自弃 和堕落。(注:Satz,Debra,1996,Status Inequalities and Models of Market
Socialism,Equal Shares,Making Market Socialism Work,The Real Utopias Project ,Volume 11,pp.71~89,Verso Publications Inc.)这就是说,这里有一个市场对个人 行为方式的系统性效果会破坏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问题。对于民主,科恩和罗杰斯指出 ,我们能判断民主(democracy)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有两个尺度:(1)政治权力 在公民中平均分配地传播;(2)与民主决策制定程序有关的决策范围。他们认为,范式( 2)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注:Cohen,Joshua & Rogers,Joel,1994,My Utopia or
Yours:Comments on a Future for Socialism,in Politics and Society,22:4,pp.507 ~522,Sage Publications Inc.)这就是说,可能存在的地位权力、机构权力和系统性 权力也都将暗中破坏民主程序。
对于效率,虽然这些模式都声称解决了机构问题和代理问题,并且接纳了市场,但一 方面仍然存在着“谁监督监督者”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则正如普特曼所言,利润的平 均分配实质上摒弃了市场依赖帕累托效率来提高社会福利的途径。而且,若再考虑再生 产领域中的信用度和信用成本问题、债权人的回报和控制等复杂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 “软预算约束”的麻烦问题等,这些模式可以说没有解决市场发挥作用对社会介入的要 求是如何的问题。(注:Putteman,Louis,1996,Comments on a Future for Socialism,in Politics and Society,22:4,pp.159~169,Verso Publications Inc.)实际上,也 就是未能顾及哈耶克关于经济现象内部的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的警示问题,以及在实现 社会主义目标时各种无形的因素仍将会损害效率的问题。所以,当今西方的“市场社会 主义”模式实际上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一张类似于早期菲利普斯曲线为政府提供的可供 选择的菜单:降低失业率或者降低通货膨胀率——效率或者平等由君抉择。惟一的区别 仅仅在于模式的制定者总是许诺:通过交替实现方法最终是可以实现效率和平等这两个 目标的。但事实上,又无法证明这双交替前进的双脚是否踩在跑步机上。
剖析模式建构的逻辑可以发现,他们把平均分配看做是实现平等的惟一手段,把财产 关系的变更看做是实现平均分配的惟一条件,然后再把作为工具的特定市场拼接组装进 来,于是一个既能实现社会主义又能实现效率目标的“市场社会主义”方案就建构出来 了。但是,当他们承认这个拿来的市场是以自利性为动力时,财产关系就必然面临着两 个相反的适应方向,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我认为,拼接组装本身意味着 他们对市场工具性的误解:虽然市场是产生效率的工具,但如果把某个特定社会的市场 照搬到别的社会中去,那么这个具体工具就存在一个适用性和非中性的问题,因为任何 社会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这表明,模式的建构者未能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未 能对“市场实用的重要性事实(case)远比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事实更为强烈”,(注:
Folbte,Nancy,1994,Roemers Market Socialism:A Feminist Critique,in Politics
and Society,22:4,pp.596~606,Sage Publications,Inc.)以及市场让人类经济活动指 向最优效率这样的基本论点展开深入的剖析,从而不知道市场的这种工具性必须以市场 的中立性为基础,不知道必须从作为特定市场基础的“一般市场”的中立性出发,才能 建构出在不同社会中可以同样发挥工具作用的不同市场。说到底,他们没有找到真正合 理的理论基准。
二、如何说明市场中性论?
特定市场非中性特征的显现,使得一些原来赞同和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人转而反 对和放弃了“市场社会主义”。他们反而说市场只是“罐头起子”,(注:伯特尔·奥 尔曼主编,2000,《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第139页,新华出版 社。)“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机构”,(注:斯威齐、贝特兰,1975,《论向社会 主义过渡》,第6页,商务印书馆。)“市场社会主义”是个“神话”(曼德尔),(注: 《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1992,第15期,第407页,商务印书馆。)“市场社会主义 ”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术语”,一如“后现代”术语一样(斯威齐)。
将“市场社会主义”术语与“后现代”术语划为一类显然是欠妥的。因为就词义而言 ,后者类似于“圆的方”术语,而前者至多类似于“会飞的龙”或“长着牙齿的鸟”之 类的术语。但问题的核心仍在于市场是否有中性,市场是否是实现人类目标的工具,这 个问题可能与货币经济学中的货币中性问题相似。关于货币是否是中性的问题已经争论 了数百年,而且依据货币是中性的或不是中性的都建立起了逻辑自洽的货币理论(前者 如“货币数量论”,后者如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同样,认为“市场和资本主义绝对不 是一回事”的观点,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有人提出,“问题的关键全在于把具体的市场过 程的历史社会条件,同在社会关系中居于中立地位的市场技术原则区别开来”(海曼)。 (注:托马斯·迈尔,1996,《社会民主主义导论》,第9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
诚然,就历史在场的资本主义市场而言,市场已不是一个孤立元素或绝对的框架了。 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观点,关于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把人的利益置于物的控制之下, 关于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被当做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木偶”和“机器的附属物”的观 点,讲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的非中性特征。但是,正如货币中性论者虽不能否 认现实货币经济中的货币对经济活动的非中性影响,却能够指出产生非中性的条件和原 由,并提出在何种视野和何种意义上货币是中性的一样,市场中性论也不否认资本主义 市场的特有属性,而只是要说明从“一般市场”的视野出发,市场并非以私有制和个人 主义为前提才形成效率,并且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也并非要连同市场一起被否 定。因此,对市场中性论的说明就可以被归结为对以下两个问题的说明:(1)造成市场 资本主义属性的条件何以是相对的?(2)是否存在着塑建一个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基础?
第一个问题归根结底涉及到自由竞争条件的惟一性问题,以及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否惟 一地取决于自由竞争的问题。通常的观点认为,自由竞争以自利且自主的社会单元的存 在为前提。然而,对于创新和奋斗的动力而言,自利条件并非是绝对的,自利性仅仅是 决定资本主义特征属性的绝对条件。因为人不是一般动物,人有价值理想,并且有不少 人在物质利益得到一定满足后,实现价值理想的愿望就会迅速增强。其实,即使在资本 主义市场中,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惟一地以价格机制为中介。尤其是总还存在着 “忘我地”工作和“愉快地”劳动现象,存在着对他人命运的关怀和对他人困难的帮助 等等现象,而这些现象或活动显然不是以“自利性”为动力的。所以,与自主性条件相 比,自利性条件不具有绝对意义,更何况自利性要求并非只能与现存的资本主义财产关 系形式相对应。因此,私有制和自利性都不是表现为自由竞争形式的创新和奋斗动力的 必要条件。对于形成市场的单元而言,真正惟一的条件是自主性,但这种自主性一方面 并不局限于物质利益领域,另一方面又以承认所有人的自主性为前提。我们看到,在资 本主义市场中,大多数人的自主性往往会受到伤害,这就会反过来影响到健康的自由竞 争。可以说,资本主义市场中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正是这种不健康竞争的结果。特别是 当今资本主义市场面临的诸如“可持续发展”问题和“人造风险”等所谓现代性的问题 ,更是与把由自利性驱动的自由竞争作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惟一条件直接相关的。
此外,我们还看到,即使对于资本主义市场,市场机制的作用也以合作为动力,在这 个市场中,合作现象是极容易受到破坏的现象。但它的存在至少表明,“竞争”并不是 惟一的动力,而对它的说明,特别是关于合作现象能否广泛化和深入化的说明,则涉及 到对第二个问题的说明,亦即涉及到现存的市场机制是不是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 陈述的那种“无基础”的操作问题。罗姆认为,市场机制是有基础的,它的基础就是非 市场的计划和设计。(注:Roemer,John,1994,A Future for Socialism,in Politics
and Society,22:4(December,1994),pp.451~478,Sage Publications Inc.)说市场的 基础是非市场的计划和设计,并不是说现实市场经济是一个“二元经济”(加尔布雷思) 。自近代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以来,诸如合同法、专利法、遗产法、税法、反垄断法和反 倾销法等等都是人为设计并不断修改的,市场活动是在人为制定的规则制约下的活动, 市场本身是不断演变的。此外,在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代理问题时,德、日资本 家依据不同于英、美资本家的制度监督他们的管理系统的情况所表明的市场本身的可塑 性,都意味着存在着一个作为特定市场基础的“一般市场”。
考察“一般市场”的基本特征有必要从理论高度审视市场起源,从起源视角看“市场 ”,“市场”仅仅是经济交往的共同体,构成这个共同体世界的基本元素是“交易”。 对于交易事件,“自由竞争”仅仅是该活动过程中某个阶段的活动样态,“互利合作” 才是贯穿整个过程的活动样态。因为所有的商品交换事件从出发点和结果来看,对交易 各方都是增效的;从经济活动整体来看,则是以分工为前提的合作活动的完成。所以, 自由竞争仅仅是市场机制钱币的反面,它的正面是互利合作。这样,现存的资本主义市 场仅仅是“一般市场”反面特征发展的产物,亦即它是把“一般市场”的反面特征上升 到主导地位的市场;“一般市场”完全允许我们发展它的正面特征,亦即塑建一个把“ 一般市场”的正面特征上升到主导地位的市场,它就是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 。不言而喻,这个基于“一般市场”特征而被塑建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同样能履 行实现效率的工具作用。因此,人们创建合理和彻底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或理论, 必须以“一般市场”的中立性和工具性为基准。
三、“社会主义市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如果说,“一般市场”的中立性和工具性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的可能存在,那么 ,“社会主义市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它有些什么基本特征?
我认为,它的第一个基本特征是:在这个市场中,“按劳分配”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分配机制。所谓“按劳分配”,也就是平等劳力的平等所得(这个“劳力”绝非仅指体 力的支出)。显然,该分配机制对于劳动和创新的积极性,既大大超过“平均分配”, 又大大超过“按资分配”。并且,它还极大地避免了按资分配所导致的不平等。应当承 认,在允许私有制存在的市场中,一定程度的按资分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于千差万 别的社会成员和突发的偶然事件而言,社会福利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并不能否定 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在原则上可以通过不断的改革和立法,把一个既定历史条件下形 成的现实市场逐步塑建成由“按劳分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分配体制(本文并不探索如 何建立一个“按劳分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分配机制问题)。因为“按劳分配”的主要 基础,正是作为“一般市场”绝对条件的市场成员的自主性。
它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这个市场中的活动不仅以竞争和效率理性为基础,而且更是 以合作和价值理性作为初衷和归宿。由于迄今为止,人们所看到的仅仅是资本主义市场 ,这就导致大多数人都把资本主义市场的系统性效果等同于所有市场的系统性效果。我 们已经指出,对于一般市场而言,合作精神和价值理性是同一枚钱币的更重要的另一面 ,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塑建一个合作精神和价值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当然,这并 不是说只要建立起沃里克所主张的劳动者自治的合作企业,市场就有了占主导地位的合 作精神和价值理性。今天,当经济学家从更抽象和更一般的视野——博弈视野看待市场 中的经济决策活动时,合作精神和价值理性的支配作用就已经不可避免地被阐发出来了 。因为博弈虽然是竞争,但任何博弈都离不开对他人相关行为期望的探究和把握。特别 是在存在“纳什均衡”的博弈中,按均衡支付给出对策并尊重“超越”现象是理性的。 (注:当一组参与者的每个人都愿意使其处在X地位而非Y地位时,并且每个参与者都相 信他们能够组成一组,即作为一种联盟而坚持他们的偏爱时,X便超越Y之上。若X超越Y ,Y则不出现。)毫无疑问,这样的经济活动是局中人遵守规则、讲究信用的结果,也是 局中人在对策变换过程中不断学习的结果,亦即是局中人在良性循环的对策变换中突破 “个人利益第一”观念的结果,是在“合作上押注”的合作理性在实践中不断增长的结 果。只有当所有的局中人能够受合作理性支配而实现“均衡”或“超越”的结果时,才 能够实现总体的最大化。所以,资本主义市场的最大化只是理想的非现实最大化,只有 在受合作精神和合作理性支配的社会主义市场中,才有现实的最大化。
那么,是否所有的市场活动都允许我们通过法规、教育等被引导到受合作理性支配的 活动中呢?特别是对于不存在“纳什均衡”的博弈难道不是惟有竞争和对抗吗?事实上, 市场中大量存在的这类博弈,并非永无休止地处在轮流变换对策的状况之中。我们总看 到在某个节点上,某个局中人终止了改变对策的动机,导致契约或交易的实现,问题是 以往人们总把该现象看做是一方的屈从。今天,有人针对该类现象提出了一种崭新的“ 策略型均衡”博弈理论,该理论指出,均衡仅仅是“自我支持”的策略组合。终止改换 的策略只要是自我支持的,也就是合理的。而且,由于这种“终止”从原来的标准和环 境出发似乎是吃亏的,所以这个“自我支持”必定是按不同的标准(诸如价值理性)和环 境出发的。这表明,对于不同的局中人存在不同的目标和不同性质的理性,从而该契约 所呈现的策略组合是一种“联合理性”的组合。(注:保罗·魏里希,2000,《均衡与 理性》,经济科学出版社。)由此可见,受一般市场特征属性的潜在影响,即使在资本 主义市场中,价值理性和联合理性也在不断滋生。
它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共同富裕。按劳分配和联合理性组合事件的大量存在必然导致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就是说,一方面按劳分配的结果已经消除了极端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对于许多境况较好的社会成员而言,救贫、扶贫决策可以是自我支持的理 性决策,亦即这种决策相对于他们的价值理想是自我支持的。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中 ,共同富裕目标完全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诚然,一个符 合上述三项基本特征的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只要我们紧紧围绕 市场活动的基本元素——交易的规则和体制,本着上述基本特征的要求实施改革,它绝 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基本特征之间并不存在原则上的冲突,并且这些基本特征都 源自“一般市场”的本质。
四、“可选择的现代性”
令人遗憾的是,当代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建构者几乎都回避了历史哲学高 度的论证,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一些人也总是心存疑虑。我认为,这两方 面的情况都源自于这些人所理解的,已经在他们头脑中僵化了的历史决定论或历史必然 性观念。在经济学领域,历史学派在19世纪问世的理由在于对古典经济学进行批判的需 求,但该学派未能对古典经济学存在的概念问题和经验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批判;相反 ,该学派实际上表现为对由“边际革命”形成的新古典理论经济学的反动。根本的原因 在于,他们所讲的历史规律或历史必然性,是从一个事物或事件(原因)到另一个未来事 物或事件(结果)之间的决定论或必然性。他们忽略了把握这样的决定关系或必然关系, 是以把握对象及其环境的全部情况,以通晓宇宙中的全部规律为前提的。而我们所能给 出的理论,却只是对某种抽象关系的陈述,它们都只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假言命题系统。 其实,即使在自然界,人类迄今所能指出的严格的必然关系也仅仅是所谓的反事实条件 关系。我们知道,一个被手托着的球,当抽回托球的手时球就会落地;我们也知道,动 机是制造不出来的。在逻辑上,这种必然关系仅仅是违犯必要条件的推理结论必然为假 的关系。因此,科学的历史决定论给出的历史必然性命题也只能是假言命题,依赖它并 不能保证我们就能对处在现象领域的社会历史演变和未来历史事件作出无误的预言。这 正如我们仅仅依赖于生物进化论,并不能通过对现有物种的研究而预言未来的新物种一 样。这也就是说,人类所能给出的“历史规律”在命题性质上都只是“趋势定律”,都 只是对现实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的众多趋势的揭示,尽管我们认为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 演化的基本趋势。
所以,把马克思给出的人类社会演进抽象地、机械地套用到任何国家都是无效的。事 实上,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俄国问题时,考虑到历史已经演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提出了 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命题,而这本身就表达了关于具体人类社会结构的 可组合观点,并且在实质上也表达了远不同于机械历史决定论的关于“未来”的可选择 论思想。亦即表达了对于既定的“当下”而言,各种复杂的因素和趋势使“未来”在我 们面前呈现的无穷无尽的“可能世界”,人类的能动性就表现为自主选择和因势利导, 这与当代经济学把所有的经济活动都看做是选择活动是一样的。总之,现象领域的选择 论并不与抽象领域的必然论相互冲突。
美国技术哲学家芬伯格说,马克思著作中有两种经济技术理论:“一种是基于资本主 义经济的,而另一种是基于其组织形式的社会学”。这第一种可称为财产理论,第二种 可称为劳动过程理论。而我们以往只重视第一种理论,但事实上生产方式的改变比财产 关系的改变更重要。因此,他从技术的可选择性出发批评了穿着“自然必然性”外衣的 资本主义现代性,提出和论证了“可选择的现代性”命题。①虽然本文不能就现代性和 “后现代性”展开论述,并且也不完全赞同芬伯格关于“自然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 ”的观点,但应当把“可选择的现代性”命题与历史的决定论统一起来,亦即把“可选 择的现代性”看做是历史进程中“历史必然性”的存在形态。
我们从市场中性论或工具论出发所建构的,由社会主义市场作为组成部分和框架的“ 市场社会主义”方案不仅在原则上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相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它 的确又是“可选择的现代性”。
标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存在论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