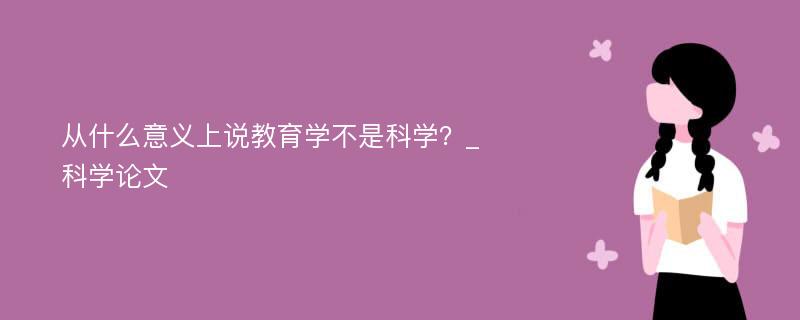
教育学在什么意义上不是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科学论文,意义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33X(2004)04-0006-04
一
什么是科学?由于可以这样简单地提出这个问题,当然希望会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事实上,答案如此复杂,以至于至今仍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结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进行下一步的探讨。在未经言明的情况下,科学一般指称自然科学或经典科学。
自17世纪牛顿力学体系建立以来,自然科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它不仅成功地解释了地球物体以及天体运动的经验现象,而且正确地预言了一些未来的事实。逐渐地,科学作为人类理性活动的结晶慢慢上升为一种具有自己鲜明特征的文化,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观念意识。毫无疑问,人类生活甚至将越来越依赖于科学的进步,科学成了人类理解生活、把握世界的可靠方式。科学也就居于现代社会的话语中心地位。这样一来,毫不奇怪在其他领域,如“管理科学”、“娱乐科学”、当然还有“教育科学”……其实践者是如此急迫地宣称他们所从事的是“科学”。
由于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科学的尊贵和荣耀以及话语权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一旦这种“荣誉”滥用,又是不幸。人类会从对科学的依赖转变为对科学的信仰:将整个生活都被托付给科学,科学成了给出生存意义的唯一源泉。它不可避免地鼓励了唯科学主义倾向——即夸大科学的适用范围,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全面引用到其他领域,如模仿科学的风格、专门术语和数学化形式等等。这实际上也消解了其他学科自己本身的学科性质,更是对科学的“污染”。因此,科学的划界问题成为了科学哲学的首要问题。
科学自挣脱神学的桎梏之时,培根就认为科学应当严格建立在观测和实验等感性经验的基础之上,一方面我们通过观察归纳出新知;另一方面,对陈述的正确与否,可以通过仔细的观察来证实。后来康德进一步区分了现象与物体、事实与价值、物理与伦理等,提出了超验实在的不可知论,把科学严格地限定在现象世界之中。孔德改造了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确立了实证主义原则。
逻辑实证主义为了实现“科学是唯一的知识、永恒的真理,任何现象都要以科学加以说明”这一笛卡尔科学主义的理想,建立了“意义—证实”或“理论—经验”认识论模式,“一个命题的意义,就是证实它的方法”。“一个陈述的意义是由它能够被证实的方法确定的,而它的被证实又在于它被经验观察所检验”。[1]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能否为经验证实(或确证)就是区分科学与各种非科学的绝对标准,凡是能够为经验证实或确证的就是科学的,凡不能为经验证实或确证的都是非科学的。显然,教育学远远达不到这样的“科学”标准。然而,面对新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就可以发现,一系列的自然科学新成就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已经无法用经典的理论来解释。科学划界的批判理性主义就出现了。
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波普尔主张抛弃传统“科学知识确定性”思想,代之以“科学知识可错性”观点,提出“证伪原则”:任何理论或命题,凡在逻辑上可证伪的(可反驳的),并在经验上证实了这种证伪性的,便是有意义的、科学的,否则便是无意义的、非科学的。据此,重言式命题、列尽各种可能性的命题、形而上学、宗教、神话、伪科学都属于非科学。教育学不过是一些可能性的命题和意识形态的“宗教式”呓语,当然不可能是科学。不过,在科学的历史主义看来,不管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批判理性主义都有可能脱离甚至歪曲实际科学。
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库恩在批判科学的证实或证伪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科学范式理论。“只要仔细关注科学事业就会发现,正是常规科学而不是非常规科学,最能把科学和其他事业区分开来”,而一个领域进入常规研究的标志,就是“拥有一个范式,有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2]因此,把科学与一切非科学(哲学、艺术、前科学等)区分开来的标准既不是证实,也不是证伪,而是在于有无范式以及是否在范式的指导下进行解决疑难的活动。库恩认为,范式是常规科学特有的,非常规科学没有形成范式,是前科学时期,科学发展是范式的更替。而教育学形成了范式吗?称教育学为科学还是勉强了点。不过,在库恩那里,划界问题已明显淡化,范式只能作为科学与前科学的划界标准,而不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
科学划界发展到库恩这里,已表现出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绝对走向相对、从理性走向非理性的倾向性。而后现代历史主义者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已是一种宗教,是科学沙文主义,科学与非科学没有必要也无法区分开来,科学并不比非科学特殊,主张“怎么都行”的多元主义标准——这是另外讨论的一个问题。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科学划界的实质是为了维护科学的理性。从中至少说明两点:
一是科学的划界,既是为了不使自己受到“污染”,表明自己的尊贵和荣耀,同时也是在限定“科学”的作用范围,并不是所有的学科领域都必要或可以“科学化”的。这个世界不仅仅需要“科学”的解释,也还需要“非科学”的解释。在面对解释我们生活其中的自然界、人类社会、人自身等方面的问题之时,不存在着谁比谁更高贵的解释。回想一下在中世纪神学占据社会的主流话语的时候科学的境况,我们也没有理由把科学推向神学曾经的“尊荣”,更没有理由歧视不能纳入科学范畴的“非科学”。而一旦科学不再像它起初那样只是回答一些具体的问题或超出科学的划界实际上所传递的“限度”,而试图回答所有的问题,那就会走向“科学主义”的迷途。把所有的自然、社会、人的问题纳入“科学化”的范畴,以科学理念、科学方法来关照一切,这样,唯理性的“科学主义”与在中世纪的“神学”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这本身就是对科学的消解和戕害。并不是人类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是可以纳入“科学”的结构之中的,也许这样的“非科学”的存在还会对科学本身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当然我们也不必嫉妒科学在影响人的生活和人、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尊崇科学也是应该的,不能因为“非科学”没有享有这样的荣耀就要么敌视科学,要么拼命“科学化”装扮自己,以为这样就可以分享科学的荣耀之羹。这都是片面的,恰恰也是不科学的,起码就没有科学的态度”。
二是科学的划界,既是在澄清自己的独特性,说明科学与其他学科是不同的,同时也是在表明自己的主张。科学之所以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其他学科却没有,为什么呢?也许换一个思维方式来提问恐怕会明确一点,科学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一直涵容的东西(其他学科所欠缺的)到底是什么?是科学理念吗?是科学方法吗?是科学思维吗?任何一种回答恐怕都会失之简单性。“科学主义”不是尝试将“科学”的理念、思维、方法移植到其他领域吗?可效果却并没有令人惊喜。科学的指称是独特的,“科学化”是没有任何实践意义的;也许我们该领悟的或借鉴的应该是“科学精神”!而不是具体的方法。科学作为人类探求未知的实践活动,必然具有自身特定的精神气质,也就是人们经常所说的科学精神[3]:一是“求真”。亦即探求未知,追求真理。萨顿认为科学的主要目的和最大报酬就是真理的发现。科学的求真精神,不仅仅是求得关于世界的知识或了解,也包括对世界的利用和改造,井由此增加人类的幸福和力量。二是“批判”。科学本质上不是一经建立便永恒不变的知识体系,而是在不断地批判谬误、破除迷信的斗争中达到对真理的认识。波普尔说批判正是科学的生命。三是“自由”。科学活动是自由的探究活动,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没有不可以怀疑的对象,因为世界乃至宇宙从来没有任何享有怀疑豁免权的绝对权威。这种自由是伴随着求“真”的。
“科学主义”把科学推向极端,成为“标准”本身,这正验证了列宁的话,真理向前跨出半步就是谬误。完全违背了科学自身所独具有的批判与革新精神。科学主义与科学精神是相对立的,或者说科学主义恰恰是背离科学精神的。
二
自17世纪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问世,教育学才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几乎就在教育学确立的同时,严格意义的科学也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了。科学的成就使得科学的法则不仅支配着人的世界观、价值观,而且支配着方法论,“科学主义”渗透到了一切学科领域。教育学也没能脱俗。
“科学主义”的教育学主要表现在[4]:第一,在教育学的学科性质上,用“科学”来诠释教育学。典型表述就是:“教育学是一门……科学。”从四五十年代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到八九十年代我国出现的100多个版本的教育学,都这样千篇一律地定义教育学,表现出“惊人”的一致。第二,在教育研究上,以科学方法为效仿的榜样,精确、定量、客观、价值无涉地对教育事实和规律进行准确描述;运用数学统计、实验研究等科学方法研究教育问题,把主观、情感排除在研究过程之外。第三,认为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可以简约化,把科学作为教育活动的决定因素。在教育的作用与效用上用物质生产过程的规律来说明学校“生产”过程;把教学过程主要看作是一种认知活动过程,包括知识授受、科学研究和问题发现,认定这一过程有客观和稳定的程序、方法及规则。心理化成为其追求的目标。第四,视学生为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师生关系是“我——它”关系,关注课堂教学的速度和质量远甚于学生的人格状况;学校教育奉行经济原则,优先追求教育效率,即灌输最大数量的事实给最大可能数量的学生。
教育学在外在压力(科学的主流话语权力对教育学所造成的挤压)和自身动力(享有荣耀的虚荣或找不到自己的发展方向)的双重作用下,走进了“科学主义”的迷途而慢慢丧失了自己的学科独立性。或许我们可以重新来关注科学和教育学的某些研究基础上的不同表现,可能更加理会“教育学在什么意义上不是科学”以及”教育学到底从科学汲取什么”。
1.在活动的对象性关系和目的追求方面
事实上,从人类产生的那一刻起,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是人们一直孜孜以求的希望和发展的动力。对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解释也就有了神学、科学、哲学(人文学科)的纠缠、统一、分化,也形成了不同的学科领域,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世界进行解释。
科学活动以自然界中的“物质及其运动”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象性关系主要是“人——物”的关系、主客体的关系,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物在“客观规律”的作用下生成“发现——被发现”、“描述(说明)——被描述(被说明)”。这种“人——物”关系是客观的、理性的,人所认识和把握的是先验存在的客体,以价值中立的科学思维和态度来关照客观对象,不断追求或逼近对客观对象的真理性认识。其目的在于增进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及对人类认识的无限性和对生命本体的肯定。科学活动就是以科学家的理性和睿智在纷繁复杂的无序世界中寻求有序、寻求人的活动的依赖性规律,使人生活在确定、有可能幸福的生活世界之中。
教育活动则以“人及其关系”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象性关系主要的是“人——人”关系、主体间性的关系,这里的“人”是具有情感、自我意识的主体,都不可能像科学的“物”一样被描述和被说明,而有自己的思想、策略(面对教育活动的反馈)和文化背景,教育活动就不能仅仅是对教育事实的描述,更在于通过它而达到对人的意义的体认和价值的实现。教育活动以“教育家”的智慧和“善”的情感促进人的人格发展和生活意义的追寻。
人的世界是一个科学无法完全企及的世界。这是因为人不仅是生物性的存在(科学能够企及的),而且更是精神性的存在,他不仅要活着,而且要不断追问为什么活着,科学对此无能为力。科学活动(研究)面对的是确切而有效的知识,把握的是事实。“这种科学知识总是特殊化的论题。它对生命似乎没有提供目的,对推动人类的主要问题似乎没有解答,甚至对自身的重要性的意义也不能提供一个有力的识见”。[5]如果我们将科学所能证明的知识和我们所赖以生活的信念相混淆,那将会陷入一个混乱的境地。
抛物运动现象是自然界普遍的规律,可是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所抛的“物”不是无生命的,而是有生命的,如鸟,还会有那么优美的抛物线吗?鸟恐怕是不会遵守抛物运动规律的,它会飞向树林、蓝天!更何况“人”这样有思想和自我意识的高级生命体!
教育活动不同于科学活动,但并不是说教育活动不具备科学的性质。这是因为教育首先也是“物理性存在”,人们为什么能够在某种共同理解的程度上进行教育的沟通和交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样的问题有可能有共同的期望和不同的解释?就是因为教育存在着通约的人们能够共同认识和把握的客观的东西,也就是教育的公度性。否则,教育就不可能延绵、交流、对话,也没有存在的必要。教育的历史与现实表明,人们对教育的认识是沿着两个方面逐步深入的,一是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二是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并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一系列教育规律,可以说教育是一种规律性的活动。[6]那么这种教育规律的发现和实践运用必然要遵循科学的规范。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教育活动为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总具有某种价值指向。在教育活动中,教育主体(教育活动中的“人”都是主体性的人)都是对教育有某种需要和期望的现实的人,他们都会把自己这样那样的需要与期望赋予教育活动,从而实现某种教育价值目标。可以说,教育活动又是一种价值性活动。[6]从事实描述是无法推断价值判断的,教育活动的价值性是无法“科学”分析的。教育世界具有两面性,既是事实世界,又是价值世界。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可以做事实和价值的相对区分,但在教育实践活动的本体意义上,是决不可分离的。所以说,教育学不可能完全科学化,但又必须、可以汲取科学的养分。
2.在研究的原创性方面
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有个原创性问题。原创性是一个相当大的逻辑鸿沟,把自身与先行者分隔开来。只有在发现与发明(创造)取得让人惊讶的时候,它们才具有原创性的品格。科学活动与教育活动的原创性是有共通之处的,那就是两者的原创性都令人欣赏、给人以无限美的享受和震撼。不同之处则在于,科学活动原创性的欣赏“在于科学家比别人更深入地看到事物的本质的能力”;[7]而教育活动原创性的欣赏恐怕就在于教育家睿智地唤起人性觉醒的创造力。
原创性是任何人类实践活动的生命力。原创性要求科学研究必须面对原始的科学问题。杨振宁曾经谈到理论物理学研究读最新的文献是必要的,因为这可以了解你所从事的领域中别人在想些什么。但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必须面对原始的简单的物理问题,而不是别人的猜想。[8]如果把研究活动比作探险,面对原始问题就好比是在原始森林里探险,而不是参加有明确目标和带队科学家的科学考察,更不是去登泰山或游黄山。在科学史上,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能解决别人提出的二手问题不容易,但能提出有意义、有价值的原始问题更不容易。也许科学精神就体现在这样的原始问题的追索之中。这也是科学激荡人心之根本所在。
教育活动同样具有原创性。回顾一下夸美纽斯、洛克、卢梭等人的教育研究,不难看出教育活动的原创性同样是令人激动的。唤醒人性的光辉必然使得教育活动是一种充满创造力的实践,这需要教育家(教育者)以一颗博爱之心,满怀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赤诚来开展教育的原创性研究。可事实上,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教育学之所以地位低下,其他学科对教育学的空间的挤压,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教育学的原创性研究的欠缺。教育学为学科地位的“尊荣”,更应该汲取科学的原创性研究的精神,借以求实、批判、创新、自由的科学精神来开展教育学的原创性研究。教育研究需要的恰恰是“原始森林”中的探险,而不是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去游黄山,这也是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作为科学的教育学何以可能必须考虑的。
3.在对事件的解释方面
科学必须建立在具有可重复性检验的科学事实上,一个科学事实是可以在相同的实验条件和实验程式下重复出现的,至少存在相当高的概率;一个事实不能得到较高概率或重复出现就不能被证认为是科学事实。科学解释是通过将作为解释的经验事实作为相关普遍必然规律的个例置于该规律之下实现的。事件由于其特殊性、偶然性、不可期性等而被驱逐出科学研究的圣地。换句话说,科学不说明、解释事件,因为科学理论是强调普适性和可预测性的。“只要给出某一物体当下的基本参数,原则上可以得出其在过去或未来任意时刻的运动轨迹”。[9]也就在一般意义上,科学以“客观性”、“普遍性”、“规律性”、“预见性”为最基本的定性,而对事件是漠视的、排斥的,至少是不会去解释的。
教育活动中,尽管我们不愿意,可不得不承认事件的存在和巨大作用。对学生影响至深的往往是教师的一个鼓励的眼神和一句推心置腹的话语,而这有的会影响学生的一生。教育实践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尽管我们的教师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教育活动不是纯粹的、客观的“科学”活动,而是非常“复杂性”的人类实践。教育不能也无法以“还原论”、“决定论”的简单性思维来把握和预测,教育具有情境性和不确定性。
自然把尚未完成的人放到世界之中,它没有给人作出最后的限定,在一定程度上给他留下了未确定性。[10]而以未确定的发展中的人为培养对象的教育活动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教育规律(如果存在)所发生的效应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蝴蝶效应”——任何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通过叠加作用都会引起结果的巨大不同,而且不可预测。教育活动、教育效应都无法排斥教育事件。也就是说教育事件不像科学活动中的事件一样不具有合法性,相反它是教育活动必须考虑和加以研究的。教育事件最能体现教育的情境化意义。
那些离开具体的教育情境,“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的废话”,不是教育研究的目的所在。教育活动也只有根植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才有可能实现教育的效应。在这个意义上,教育“培养学生个性”、“因材施教”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总之,教育学与科学的各自独特指称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必要将二者归为同一,也没有必要孤立二者。而是在某种共通的基础上,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从目前教育学的发展现状来看,恐怕教育学更应该向科学学习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