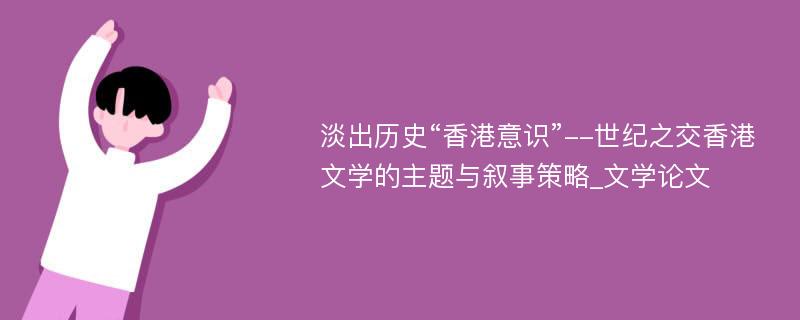
淡出历史的“香港意识”——世纪之交香港文学的主题与叙事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世纪之交论文,意识论文,策略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观察世纪之交以来香港文学,人们会感到因“九七”回归而急遽膨胀的“香港意识”的虚幻,那些一度被遮蔽的香港本土的现实问题,诸如底层群体的生存状态、性别与婚姻、殖民与本土、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历史等再度浮现出来,“香港意识”则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野。
1999年,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由青文书屋出版。叙事的背景选定为1984年至1998年的香港,正是香港历史上极为敏感的政治“过渡时期”。故事以香港回归中国一周年的日子作为开端,用第一人称手法,记述某大财团的二把手张得志在台湾遇袭,濒死时回首前尘往事的经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有意识地以极富政治色彩的历史时段作为叙事背景,陈冠中却显然对所谓“香港意识”持有不同的看法。如果说黄碧云充满病态、伤痛的《失城》,一定程度地契合了时代的政治文化焦点,可以代表90年代香港文学的一种主流倾向的话,那么陈冠中则是以反讽的叙事,试图消解“失城”话语的“霸权意识”,他提出了一个对应的叙事主题——“什么都没有发生”,并以传统的言情故事,老练的人情世故去写某一角“香港”的深层心理与集体无竟识。在这样的叙事中,政治事件依然会影响社会整体的发展状态,但个体心理感受与生存状况的差异性得到重视,发自个体真实体验的声音对某种时代“共名”性的情绪产生抗衡、互补的作用。
张得志自述:“就算像我这样一个在香港长大、并不算特殊的香港人,也总有些事情,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若要找一个时间上的切入点,我会选1984年,即中英签署联合声明的一年。那声明跟我没什么关系,只不过一般人习惯用一些事件来标志日期。和我有关的是一包黄糖,冲咖啡用的那种。”“她们这些大陆人,每人一生都有几件戏剧化的遭遇,跟历史呀,国家呀扯在一起,可以很轰轰烈烈的告诉别人。我一生有的都是些琐事,历史跟国家没烦我”。①张得志在香港长大,但本质上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1954年出生于上海,4岁以前的记忆是“和妈妈一起在一个很暗的房间里面”生活,父亲在香港另外有了女人,在他4岁那年,母亲含泪将他送往香港,从此生死两茫茫。在严格意义上,张得志的人生经历并非与政治、历史毫无瓜葛,但他有意识地淡化了个体对时代政治的体验,“我还记得火车开动的一刻,像天摇地动,惶恐之后立即是兴奋。开动中的火车是我最早的快乐记忆,我从此爱上背井离乡”。按照后殖民理论的观点,第三世界的文本常常可以看作是民族的寓言,那么张得志与父母的疏离、聚合似乎可以象征香港文化身份的形塑过程,由于外在的原因,他被迫离开生母,在懵懂无知中投奔父亲,他最初的童年记忆就源于身份的重置状态,母亲“拿了一张照片给我,叫我认住照片中的男人。那是我爸爸。照片后有我和爸爸的名字,和他在香港的地址。妈妈再三叮嘱,见到爸爸,一定要大声叫他,我还练了几次大声叫爸爸”。离别生母/故土/亲情,使他的生命开始陷入一种无根状态,他需要调整自己的角色意识,寻找新的身份认同。他见到了父亲,可是因为继母的关系,他无法融入父亲的家庭中,被委托给父亲的朋友照顾长大,“我没有大人管,整天可以在街上玩。……不到晚饭不回那尾房,每天在天文台一带跟附近的野孩子玩”。“父亲”喻示的社会体系虽然接纳了他,却无法帮助他形成完整的自我意识,他面临再度放逐,在不断的漂泊中养成特有的生存观念,这是一种以“过客”心态为核心的思维意识,它不同于离散文学中常见的“孤儿意识”,最大的差异是没有对母体/民族/国家血泪充盈的怀恋与追慕,而以对家国、血缘观念的主动离弃、超越为精神特征。张得志回到香港的家中,不会获得归属感,“我决定下次回港,应像去了陌生地一样,住入五星酒店。我并决定把房子卖掉,与宝怡一人一半分家,从此干干净净”。宝怡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是父母离世后他在香港惟一的亲人,可是他们之间除了经济结算以外没有任何亲情,张得志卖掉了房子,也彻底割断了自己与香港的血脉联系。对大陆,他同样无法产生认同感,“我去上海的时候,故意去‘故居’凭吊一下,以前叫霞飞路,解放后改叫淮海路。我住的房子,那里弄,已改建成伊势丹百货公司。我站在那里,拼命想挤出一丝怀乡思故人的酸的馒头愁,却一点没办法。根,对我真的是一点没意义的,装不来。”根的断绝,曾经令黄碧云笔下的主人公无所寄托,终于彻底失去了生活的希望,然而,在同样的时空中,显然还存在不同的生命体验与文化心态,陈冠中的“香港叙事”提醒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喧嚣一时的“香港意识”,究竟是谁的“意识”?
由“过客”心态导致的政治冷感在香港社会具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面对“九七”,许多港人产生心理焦虑的原因不是身份认同的危机,而是对原有生活状态能否维持原貌的担忧。按照斯图亚特·霍尔的观点,“身份”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经由文化的塑造和建构才形成,在这个过程中,“身份”因循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诉求,处于一种变更、移位、涂抹、同化和抵抗的“运动”状态。这样的“文化身份”是一种必须在不同的语境下加以“想像”及“再现”之物。联系到香港的情况,我们应该说,如果要开放出“香港意识”的多种可能性,兼顾各个阶层而不只是某些群体的声音,是一种不能忽视的立场。陈冠中的“香港叙事”显示出“香港意识”更宽泛的内涵,他超越了一般研究者局限于“中国人”、“香港人”之间身份辨析的思维方式,思路更加大胆,不仅抛弃地域观念,而且尝试超越民族意识。他笔下的主人公张得志不会“自寻烦恼”地叩问“身份”的归属,他只关注当下,只计算利益,某种程度上他是“世界人”的象征,是现代商业文化与国际化都市孕育的时代“产物”。这样的典型在全球化时代已经不再具有“另类”的意味,也较少受到伦理政治的批判,他们的存在为传统的身份认同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思路。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他们才昭示了“香港意识”的真正涵义。
许子东在“三城记”之香港卷——《后殖民食物与爱情》的序言中谈到,90年代香港小说(主要是中短篇小说)中占据主流地位的文学类型是“失城文学”,常以“此地他乡”或“失却城市”的叙述方式,内在的体现出香港意识的觉醒与危机。“九七”之后这种主题类型有了发展变化,“简而言之,‘漂流异国’的故事明显减少,‘此地他乡’的感慨由激愤张狂(比如《失城》)转向戏谑婉转(例如《后殖民食物与爱情》),新旧移民依然在往事回忆中显示对繁荣城市的陌生感,但艺术上最有收获的却是青年作家们对都市异化状态的或荒诞或朴素的抗议。从‘香港意识’的角度来看香港小说的近况,可以说香港小说进入了一个比较犹疑不定的时期。”②这确是对近年来香港文学主题趋向的准确观察。从“香港意识”的角度考察文学的发展状况,曾经比较切合特定时期的时代思潮,亦能满足一些“不在场”的读者的阅读期待。不过,正如历史在最初总是由无序多元经过梳理而变得有序一样,任何概括都意味着一种牺牲,有关“香港意识”的文学诉求无法涵盖香港文学的整体面貌,对文学中“香港意识”的讨论最终也将被关于“香港文学意识”的探讨所取代。
事实上,香港文学在传统上与大陆文学的最大不同,应该就是体现在前者较少涉及社会政治问题。像大陆20世纪文学那样密切关注意识形态变迁的创作状态,香港文学中除了“九七”题材以外,很少见到。“香港小说不太注意‘重大’题材,而较为注意展示日常经验。”③因此,准确地说,“九七”之后香港文学主题类型的变化,并非意味着“香港小说进入了一个比较犹疑不定的时期”,而恰恰是向文学传统意识的回归。这种文学转型在2000年以后的香港文学中有进一步的表现。周蜜蜜的小说《归宿》④,着力呈现香港人在走进大陆社会时由犹疑到逐渐信任的心理转化过程。情感失意的尤贞选择“看楼”这种特殊方式来观察别人的生活,“看楼”的目的本是为自己找个家,找个最终的归宿,而尤贞的动机显然不止于此,她更重视的是生活常态的比较,在比较的过程中她体会到一些香港人的情感两难。卖房的王太迁就两个儿子的意愿,准备离开香港去大陆生活,但“说到底,他们毕竟舍不得香港,舍不得这个家,对未来的年月,又觉得茫无头绪”。“对香港人来说,大陆本身,就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一时封闭,一时开放,总有些令人摸不着头脑似的”。对此尤贞是有同感的,我们似乎又感受到某种“失城”情绪的曲折表达,但香港真的如想象中那样可以信赖、依靠吗?尤贞的丈夫有了外遇,她不能容忍而导致家庭破裂,香港的家失落了,她的归宿在哪里呢?尤贞最终听从好友芳玲的劝导,与她一起到大陆“看楼”,她受到同车游客情绪的感染,“不住地向车窗外望着、望着,心中渐渐滋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舒畅感觉”。“展示在眼前的这个楼盘,设计就像欧陆式的建筑,环绕着的人工湖,碧蓝如天一色,湖心的喷泉,在阳光下拱起一道七彩虹幕,看得人心花怒放,同车来的香港人,看得高兴地‘哗哗’叫起来。”大陆并不似想像中的那样隔膜,他们很容易就获得了亲和感,尤贞也重拾了久违的舒畅心境。尽管没有点明,故事的讲述方式还是给人留下寻找归宿还是在大陆更切实的印象。联想到从前香港文学中依凭经济优势而对大陆人表现出来的冷漠、轻视情绪,我们大体能够感受到香港人今昔的观念转变。颜纯钧评论香港女性写作中涉及“房子”的诸多小说,指出“她们都试图通过对‘房子’的寻找和营造来明确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关系,明确自己在整个外部世界中的位置。这至少说明一点:香港作为一座过去的殖民地孤岛,长期以来在文化上的多元与政治上的驳杂,确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了香港人,特别是一些具有更高精神追求的女性作家的内心创伤。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香港的回归便是双重的:它既是地理政治上的,也是精神上的”。⑤
“城市与人”的关系是香港文学中贯通了两个世纪的主题,也是香港文学中最能体现艺术创新与人文关怀的领域。有趣的是,香港之所以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完全依赖于现代城市的迅速发展,港人的生活境遇、既得利益无不与都市的发展有关。然而,香港文学中却较少见到对都市现代性的呼唤与礼赞(这是80年代前期大陆文学中的突出主题之一);而对现代性的反思,对都市给予人的精神戕害的揭示却常常成为城市题材小说最突出的创作意识。70年代的舒巷城、海辛,90年代新生代的作家,都一如既往地批判都市现代性给人类造成的异化与疏离。陈丽娟的《6座20楼E6880**(2)》⑥写得简练、冷峻,将现代都市人程式化的生活、麻木的情感刻画到近于冷酷的程度,“E6880**(2)刚下车,踏在地上的脚步还不太稳。他在巴士上坐了一个小时15分,穿过了3条隧道、一条钢索大桥和不知几多条公路才回到他住的‘XX山庄’。‘XX山庄’没有山,没有动物,只有手腕那么大的几株树,却有很多楼,很多巴士和很多菲律宾来的佣人。”完整感性的生活被程序化的事物彻底分裂了,甚至连性爱也程序化了,“嗳,还不快点来?我明天返早班哪!”“来什么?”“当然是那个啦,要不要我请你?”“干吗?今天才星期三。”“一向都是星期四的,不是吗?”“那……噢……对不起搞错了!E6880**(2)连忙拉起掉了一半的裤子,另一只手抓着公事包,嘴里嘀咕着。他急步往大门走去。”人被异化为机器,无暇顾及个体的尊严与情感,都市现代性的负面影响特别的令人触目惊心。曹婉霞《疲劳综合症》描写一位辛苦工作20年的文员,某一日忽然倒下,只知吃饭、睡觉,别无病症。“高耸入云的商厦在夕阳的余晖中耀眼生辉,我眯着眼睛,注视着路上匆匆而过的行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安稳,在这儿跟我相像的人何其多呢。”⑦游静在《陪我睡》中写下的一段话更为犀利,“香港人比较特异,不论是在80年代初香港经济最蓬勃,或90年代香港经济最PK的年代,我们的祖先都保持着每天平均睡眠时间最少的全球性纪录”。⑧
我们注意到,在有意无意之间,香港文学意识发生了一个根本的改变,作家们不再只是宣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故事”,而且要思考“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城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
黄虹坚《生存的守望》将都市文学中常见的城市与人的关系,细化为城市中的“人与人”的“战争”。她不是简单化、符号化地图解城市生活样态,而侧重展示人为适应生存环境所做的灵魂搏斗。小说主人公原是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男孩”,可是这种纯净却不能为香港社会所容。在有了一次“为公理挺身而出”,结果遭人解雇,生活陷入困窘的经历以后,他开始调整自己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当再一次遇到麻烦,女上司试图牺牲他而保全自己时,他放弃道德原则,以自己偶然发现的女上司的“外遇”相要挟,希望保全自己的职位。他的问题是,为生计而不得不为之的道德堕落令他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我跑到海旁,坐了很久,我要独个儿把看不起自己、讨厌自己的情绪细细体验够。”⑨但他后来“用一句话把自己从沮丧自责中挽救出来:我是按生存基本法办事罢了”,他引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一句话为自己开脱,“一个不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的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微地活着”。这样的文学典型在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施叔青的《香港的故事》系列中都有塑造,他们共同建构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反现代性思潮。与大陆文学同中有异的是,中国大陆因为有深厚的乡土文化传统,文学中的反现代性主题与叙事能够体现出“破坏”与“建设”两种意识,并大体沿着对立的两种思维意识发展:一是批判都市文明与价值缺失;二是营造浪漫、健康的乡村净土,这在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废名的田园小说中都有具体的呈现。香港由于地域狭小,都市化进程迅速吞没了乡土社会,严格意义上的“乡土文学”并不存在,因此所谓都市与乡土的冲突只是一种虚设。作家们成长于这个城市,城市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都已先天性地融入他们的血液,他们的苦闷、孤独、压抑、隔绝、敌意、逃离等情绪都与城市密切相关,对乡土他们缺乏生命体验与想像能力,虽然渴望解脱,他们却不能指出理想的乐园所在。这样的写作背景决定了香港文学中的反现代性叙事常常只见破坏,少有建设,写实主义文学发展充分,而浪漫主义文学严重欠缺,从文学审美性的角度考察,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香港的历史上并不缺乏震撼社会的大事件,鸦片战争、省港罢工、“六七”暴动等等,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也曾因之几度变更,但奇怪的是,除了“九七”,香港文学中对这些历史事件的关注热情一直很低。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是,作家们更喜欢以自己“内在化”的生活经验演绎时代的变迁,这是一种写作姿态,也是香港处于政治夹缝地位中养成的文学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世纪之交出现了一些“成长小说”,它们似乎表明了作家们在寻求香港文化身份的困惑中,尝试以个体生命经验调整观照世界方式的愿望。蓬草的《我家之——街道》⑩,以“儿童视角”观察社会人生,对生活细节和个体生命体验有细致入微的揭示,不同于一般都市文学抽象虚化的讲述策略。在香港这个华洋杂处的国际都市中,中/西、雅/俗文化兼容共生,生存其间的市井小民并不必然产生文化抉择的困惑,孩子们既对中国传统民俗意义上的丧葬仪式感兴趣,也热衷于围观讨论具有明显西方特色的街头广告。作者要探讨的问题是:都市文化给予人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什么?他关注的是“成长的经历”,是在特定的生存境遇中个体的心灵体验。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王良和的《鱼咒》(11),小说以人、鱼互比,斗鱼的生存困境正可寓言化地象征人的生存境遇,而对往昔生活记忆和朋友的有意逃离,预示的也正是对旧我的决裂。小说特别记述了主人公少年时期朦胧的性经验,今天的性爱场面与童年时代的感受形成一种互涉的关系,这样的“成长叙事”比传统上只局限于时代政治等外在因素的观照要贴切、新颖得多。
如果说香港文学在都市题材的开拓中主要体现出探索精神的话,从西西、海辛、颜纯钩、阿浓等人的创作中,我们还感悟到深厚的平民意识与底层关怀。在经济上两极分化、观念上崇尚竞争的现代消费社会,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常常成为“失语”的一群,他们的苦痛、哀怨、期盼、困惑无从表达,几乎要被历史遗忘。大陆文坛90年代曾有“人文价值失落”的讨论,反映出部分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与道德焦虑,但理论的争鸣并未给创作太大的冲击,小资情调、游戏文学仍有相当的市场冲击力,“五四”时代倡导的平民意识、人道主义传统不同程度的失落了。在香港特定的文学语境中,严肃的文艺作品向来难以获得普遍的反响,文学创作在很多时候成为作家自我的精神慰藉,但仍有不少作者在自觉的体现平民意识与底层关怀。西西的《照相馆》写老年人的生命体验和对现实的无奈,白发阿娥因为自己租的房子要出售,不得不借住在朋友的家里,“找房子住多么困难,分期付款,连首期的款项也没有;租房子,租金也昂贵”(12)。借住在简陋、拥挤的小照相馆里,白发阿娥有本分的满足感,但照相馆内留存的各种照片,依稀让她产生韶光流逝的哀伤情绪,年轻时穿着“丝绒夹旗袍,头发都梳到脑后,还戴金丝眼镜,穿粗高跟凉皮鞋,披一件短身绒夹克”的俏丽身影,在不知不觉间已被白发、穿短袖子花布衬衫和素色直身半截裙的“老太太”取代,她不知怎样表达自己模糊的心理感受,但想到人世的生生死死,她还是“感到有点颤栗”。西西对时间的敏感,对低层人关于生活的失落与留恋的体察,使这篇小说格外具有一种平静中的震撼力量。此外,海辛《在风暴中失踪的船轿鬼新娘》(13)里出于对生命朴素欲望的尊重而流露的善意祝愿,和对传统陈规陋习的无情批驳;阿浓《人间喜剧》(14)中描述的新生儿净化父亲情感的动人瞬间,都在体现出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与人文情怀,是在商业社会中尤为令人钦敬的人格品性。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世纪之交的香港文学摆脱了寻找文化身份的焦灼心态,自足的展示多采的艺术风貌,从文学传承的角度看,这是香港文学在新世纪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
注释:
①陈冠中:《香港三部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18页、41页。以下作品引文皆出自此书。
②罗岗:《“文学香港”与都市文化认同》,《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1期,12页。
③许子东主编:《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13页。
④赵稀方:《寻找一种叙述方式——评“香港文学选集系列”丛书的小说》,香港:《香港文学》2004牟7月,59页。
⑤⑦(11)(12)(13)(14)陶然主编:《香港文学小说选(一)》,香港:香港文学出版社,2003年,221页、78页、122页、1页、52页、193页、58页。
⑥颜纯钧:《香港女性写作的一种景观》,《香港文学文论选》,香港:香港文学出版社,2003年,28页。
⑧原载香港:《素叶文学》1998年11月第64期,特引自许子东主编《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177页。
⑨原载香港:《明报·世纪版》1999年11月9日,转引自许子东主编《后殖民食物与爱情》,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184页。
⑩陶然主编:《香港文学小说选(一)》,香港:香港文学出版社,2003年,53页。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香港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艺术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父亲论文; 陈冠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