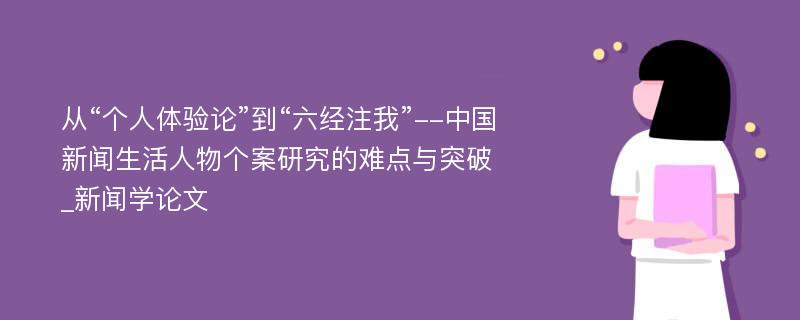
从“亲历者说”到“六经注我”:论中国新闻学界健在人物个案研究的难点及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界论文,个案论文,难点论文,中国新闻论文,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是“利他”,即研究成果必须对别人有用,否则便无异于制造学术垃圾。
那么,在今后20年内,就中国新闻史学的人物研究而言,何种选题可能是“前人所未及就而后世又不可无”(顾炎武语)的?在笔者看来,关于“健在学者”的研究当属此类。
以甘惜分(1916—)、宁树藩(1920—)、洪一龙(1925—)、方汉奇(1926—)、何梓华(1931—)、赵玉明(1936—)、白润生(1939—)、刘继南(1939—)、童兵(1942—)、罗以澄(1944—)、孙旭培(1944—)、郑保卫(1945—)、吴廷俊(1945—)、李良荣(1946—)、陈力丹(1951—)等为代表的学者们[1],之所以值得研究,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学术成就,而是因为他们有的经历了政权的更替,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变迁的亲历者。把他们置于社会变迁与学术环境变迁的时代背景之下与中国新闻学术史的源流结构之中,他们的价值便“超越个案”。
一、中国新闻学界健在人物个案研究的难点分析
在2008年以前,中国新闻史学界学位论文层次对于健在学者的个案研究为零。乔云霞教授曾不满于1949—2009年间中国新闻界人物研究中“研究死人多活人少”的现象,认为“究其原因:其一是只缘身在此山中,难识庐山真面目。由于多方面原因,太近了的事情反而难以看准。其二是评说人物太敏感,容易引发人际关系紧张,甚至政局不稳。”[2]而在笔者看来,认为“健在人物”“不好研究”的原因则至少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盖棺论定”的迷思
在新闻史人物研究中秉持“盖棺论定”,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亦存如下之迷思:
“盖棺论定”的迷思之一:“求全的心理”。“全面地”看问题,是认识论的基本要求。对于人物的个案研究——亦应既微观到研究对象的局部,也宏观到研究对象的整体。
当研究对象健在时,由于其整个生命长度并没有完全地呈现给研究者,此时开展研究,事实上只能观照到研究对象生命历程的局部,因而,似乎不是最佳时机。待到研究对象“盖棺”之后,将可以对其生命历程进行完整的考量,届时可以实现“全面地”审视研究对象的目标预期。
所以秉持“盖棺论定”者认为,既然只有当研究对象“盖棺”后,才能实现“全面地”审视其生命历程的目标,因此,当研究对象健在时,自然就不宜对之进行研究。
“盖棺论定”的迷思之二:“定论的追求”。“盖棺论定”的核心是“论定”,“盖棺”则是实现“论定”的条件。事实上,这一广泛流传的成语容易使人误解——似乎只有“盖棺”才能“论定”,或者至少是“盖棺”后才具“论定”之可能。对于研究对象秉持“盖棺论定”的学者而言,“健在者”由于没有“盖棺”,因此也就难以“论定”,那就意味着研究之时机尚不成熟,因而只有“逝者”才能够作为研究对象。在这样一种“追求定论”的价值取向中,自然也就不会将健在者纳入到研究者的视阈中来。
(二)“距离过近”的顾虑
新闻史学界“研究死人多、研究活人少”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研究者存有与研究对象之间“距离过近”的顾虑。此种顾虑,实际上,并非自然层面的“时空距离过近”,而是社会层面的“情感距离过近”。
“距离过近”的顾虑之一:自己能不能“认清”。历史研究的基本目标是“求真”。当代人研究健在的当代人常常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困惑,往往有能否实现历史研究“求真”目标之殷忧。
“距离过近”之顾虑还有另外的隐喻,那就是研究者与健在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情感关系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客观认知。譬如,当代人研究所熟悉、敬仰的或曾有恩于己的健在学者,在史料的选择上就可能出现自觉或不自觉地挑选那些有利于凸显研究对象业绩的事实,而对其他于研究对象不利的事实要么避而不谈,要么轻描淡写,倘是这样,显然有悖治史“求真”之目标。
对于此种因情感因素“距离过近”对当代学者的研究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但“旁观者清”,而且,研究者本人对此也不难有清醒的认识。一旦认识到由于“距离过近”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那么,在开展健在人物的个案研究时,很难不顾虑重重:对于研究对象,自己能不能“认清”?
“距离过近”的顾虑之二:学界能不能“认同”。“距离过近”所顾虑的另一方面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所做出的评价能否得到学界的“认同”。其关键在于能否做到“不隐恶,不虚美”。
对于“不虚美”而言,由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的情感关系或利害关系,研究者在研究中可能会有意“虚美”;即使研究者并无“虚美”之意,但这并不能排除其他人认为研究者有虚美“阿谀”之嫌。
对于“不隐恶”而言,研究者在研究中有可能碍于情面或出于其他原因,有意隐恶;即使研究者师法董狐,秉笔直书,实际上并没有“隐恶”,但这又可能被研究对象及其他人认为有意“中伤”。
如此一来,似乎无论怎样研究,研究者都将处于或“隐恶”或“虚美”的两难境地。
以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健在人物的个案研究为例,即使研究者出于纯学术研究选择了被学界冠以“某某学派”的某一位健在的人物进行个案研究,而没有选择被冠以其他学派的健在人物进行个案研究,虽然研究工作启动在时间上有先后,这本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现象,但却有可能被某一学派的学者认为是有意投靠另一学派,进而无端猜测,甚至变友为敌。
同时不难看到,虽然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努力追求“不隐恶、不虚美”,但“知易行难”,要真正做到却有很多困难。一方面由于研究者的学术功力局限;另一方面由于是否“不隐恶、不虚美”,需要留待学界“公论”。而无论学界“公论”的意见“统一”或“不统一”,都将给研究者造成心理压力:如果学界“公论”的意见统一,一致认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没有做到客观公正的“不虚美,不隐恶”,那么这一研究几乎就毫无价值;如果学界对这一研究成果“不隐恶、不虚美”的问题有褒有贬,对于该项研究持负面意见的学界观点,仍将给研究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笔者认为,“盖棺论定”的迷思与“距离过近”的顾虑,对于新闻史学界“研究死人多,研究活人少”难题的长期存在,即使不是其全部原因,也至少是该问题的主要症结。正是由于这两大症结的存在,使得新闻史学界对于健在的人物,虽然不乏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值得”做全面、系统、深入的个案研究,但由于“不好”研究而只得“悬置”不论。
二、中国新闻学界健在人物个案研究的实践取径
将问题“悬置”起来虽然不失为一种处理办法,但“悬置”起来的问题终究仍是问题。从知识增量的意义上来考量,知识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来自对学术难题的破解。对于“悬置”的学术难题如果不思解决之道,那么,难题将永无解决之日;相反,如果学界不断尝试破解难题的方法,在学术实践中不断地“试错”,[3]那么,难题或将有解决之可能。
(一)以“亲历者说”为方法的口述史取径
口述史成为学问始于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创建。[4]我国的口述史,台湾地区“起步较早”,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于1955年注意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并于1959年10月开始访谈。1960年,近代史所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合作,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口述史访谈,迄今已访谈700余人,成稿超过1000万字,访谈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俗节庆和生活习惯等多个方面,并从1982年起,以《口述历史丛书》的形式发表。[5]
就中国大陆目前新闻学界的研究动态而言,口述史研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做群体学者的口述史,通过口述史来开挖新史料,减少学术史上的疑点;一种是以学者个体为研究对象,通过学者口述,研究者整理编辑的方式研究口述史。
就前者而言,近年有不只一位学者开始着手以“口述史”的方式研究中国新闻界人物。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陈娜博士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着手对丁淦林、李良荣、方汉奇、郭镇之等学者进行群体“口述史”访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王润泽教授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新闻界人物的口述史研究”。但就2013年3月笔者写此文时所见,相较于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健在学者的人数而言,在中国新闻史学界开展口述史研究的学者还太少,国家社科基金对于开展口述史研究项目的立项支持也并不多。毕竟,相对于其他研究而言,口述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面临着一个“与时间赛跑”的问题。因为“口述史料的实质是‘历史学家希望给历史留下什么’,而传统史料则是‘历史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什么’。”[6]
而就后者而言,目前还没有见到新闻界人物个案研究的口述史成果,但这并不等于说学界目前没有人物个案研究的口述史成果。[7]
其实,在破解中国新闻学界健在人物“不好研究”这一难题上,采用研究者设计结构化的问题进行深度访谈,以学者口述的方式来回答问题,以研究者整理编辑的方式来书写口述史,不失为一条可行的研究取径。对于有志于新闻学术史研究者而言,在硕士论文层次指导研究生(或者自己)以口述史的方式做健在学者的个案研究,较选择“邵飘萍”、“黄远生”等做低水平的重复研究无疑更具学术价值。况且,在没有新史料发现的情况下,目前研究“邵飘萍”、“黄远生”和百年之后再研究他们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研究“健在学者”则不同,目前研究是机会和学术增长点,若想留待以后再研究,那就可能是永无机会和永存遗憾。2011年丁淦林先生(1932—2011)逝世就已经提醒新闻史学者:对于健在学者的个案研究,是需要提上议程的紧迫之事。目前全国新闻院系选择新闻史作为研究方向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人数并不少,只要其中的一部分着手去做就可以了。
(二)以“知人论世”为追求的本体取径
通过学术成果来梳理研究个体学者迄今都做了什么,在此基础之上,以直接对话研究对象的方式,追问他为什么那样思想和行动,最终是实现“知人论世”,这种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既是研究者进行学术训练的有效途径,也是书写高水平新闻学术史的前提性工作。回访学术史,不只一位前辈推荐此种治学方式。美学家蒋孔阳先生(1923—1999)就曾提倡:
“一个人做学问,最好是先对某一门学科的历史,有一个全面的大概的了解;然后,再选择其中的某一个代表人物或某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的专门性的研究,等到有了一定的成果,再扩大范围,旁涉各家。最后,联系现实的实际问题,摆脱对他人的依傍,自立门户”。[8]
费孝通先生(1910—2005)也尝言:
“一个想踏进社会学这门学科,希望在这门科学中能作出一点学术上贡献的人,最结实的学习方法一是在对社会学有了概括的初步认识后,挑定一个在这门学科中有一定成绩的学者,把他一生所发生的著作,有系统地阅读一遍,追踪他思想发展的经过,然后把他各个阶段的思想放入各时期社会学发展的总过程中看这个学者的地位和特点,再把这些变化和特点放进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去研究他这种思想所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其发生的历史效果”。[9]
并且,费孝通先生生前就曾指导过博士生丁元竹作过《费孝通社会思想与认识方法研究》[10]。
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出于对上述前辈学者所示治学门径的笃信,笔者在方汉奇先生的全力支持和倪延年教授的精心指导下,于2008年开始攻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之际,即选择“方汉奇60年新闻史学道路研究”为论题,通过多次面访和先后往来200多封电子邮件的方式,直接请教方汉奇先生,力求“知人论世”,最终完成博士论文。一位匿名专家在评审时,虽然认为“历史人物研究宜过较长时间以后为好,当代人写当代人,很难摆脱现实环境的影响,难以做到全面和公正,因而此文选题不宜作为博士论文”,但同时也承认“作者对于方汉奇先生的史料搜集极为翔实和丰富,这是要予以充分肯定的,展现方先生的一生,叙述力求平实、客观,论之有据,总体做得不错”,并且认为“有些材料很有历史价值”[11];而另一位专家则认为:“方汉奇教授是我国新闻史研究权威人物,对方汉奇60年新闻史学道路的研究,有助于新闻学科的发展,使该课题具有较大的价值。”[12]
就书写高水平的新闻学术史而言,无论采用何种指导思想和研究进路,从“知人论世”这一立场出发,最终都离不开对于学者的深入的个案研究,也就是说,书写学术史,首先需要研究学者史。而目前关于中国新闻学术史的研究时段性的宏观和中观研究,包括研究学者群体的成果,已然不少,而对于新闻学者的个案研究,尚不多见。
李秀云教授的《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13]既是第一部研究中国近现代百余年新闻学术史的有开创意义的个人专著,也是第一篇博士论文级别的研究中国新闻学术史的专著,但既非学者史研究,也非人物个案研究。谢鼎新教授的《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14],旨在重点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新闻学研究的学术环境和研究思路的演变史,出于论述策略,一般不涉及具体学者。张振亭副教授的《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15],以“5W”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聚焦1978—2008年中国新闻传播学术史,也非以个案学者为研究对象。
在新闻学术史著述中,以学者研究为聚焦点的,绕不过去徐培汀教授。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16],是其与裘正义所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7]的姊妹篇,该书有多章涉及到个体学者,采用以学者的小传和成果内容评述相结合的方法,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提要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说的谱系,但也并非是学者个案研究。
此外,戴元光教授的《中国传播思想史》、[18]丁淦林教授、商娜红教授主编的《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19]、吴廷俊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20]虽然都以某种方式关照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部分健在学者,但无论戴著,还是丁、商、吴主编之书,呈现的都是学者群像,而并非个案研究。这昭示着开展健在学者个案研究不但必要,而且必须。
(三)以“六经注我”为旨趣的主体取径
就中国新闻学界健在人物个案研究而言,除了“亲历者说”和“知人论世”两种研究方式之外,还可尝试用社会科学理论进行指导,追求“六经注我”式的史识表达。
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深层次的问题并不在“认识论”层面,而是受研究者“价值关切”的影响——尽管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是对之进行评价的前提和基础,“正确、科学的历史评价必须依赖科学的认知成果才能做出”。[21]而“价值关切”问题,对于“理性人”而言,归根结底是要经过“评价”和“选择”环节。因此,研究健在学者,对之进行“评价”就在所难免。话虽如此,但是“评价”本身蕴含着多种方式,绝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选择何种评价方式进行具体的学术研究实践?而这,又要看对之进行“评价”的目的是什么。
如前所析,对于健在学者的个案研究,以“追求定论”作为评价目的永难实现,因此,放弃以“追求定论”为目标的“垄断式评价”便不是一个选择的价值判断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承认与否问题。于是,评价健在学者学术贡献便可以不成为研究的重点,毕竟,即使通过研究得出其学术贡献很大,与研究者本人并没有任何关系,学术贡献无论大小都是研究对象的。有鉴于此,在笔者看来,开展健在学者个案研究时,可以考虑“六经注我”的“关系式评价”。亦即在研究某位学者的学术之路时,选择哪些关节点作为研究的聚焦点,选择与否的标准不在于其在这一方面的成就,而在于研究者以研究对象这一方面为凭依,有哪些自己可能和想要发挥的观点。
如此一来,则既可以避开“追求定论”的研究陷阱,也有望省去对健在学者“偏于褒奖”则有“阿谀之嫌”或“偏于贬损”则有“中伤之虞”的质疑顾虑,而且还能够为后来者继续研究预留下广阔的空间,因为,除“我”之外,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研究健在学者而表达自己不同于前人的史识。但这并不是“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是承认一千个人(由于不同主体间的异质性)事实上即使看见同一个哈姆雷特也是会有一千种不同的思想的。也正因此,以此种方式展开的健在学者个案研究,也就不可能是“学术评传”,而是研究者的一家之言。这就提醒研究者“借题发挥”不但必要,而且必须——否则“所思”就名不副实。
标签:新闻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