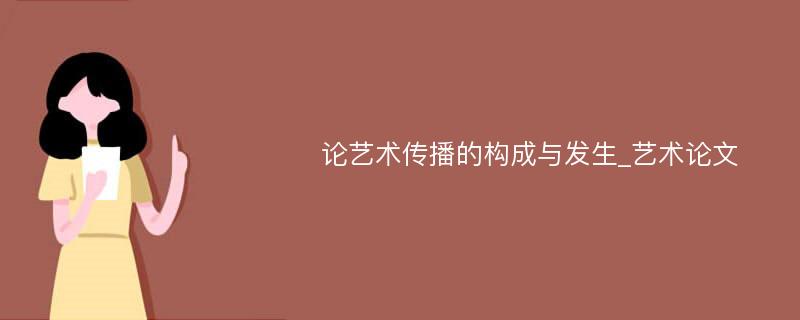
论艺术传达的构成与发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达论文,发生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艺术传达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在艺术理论领域,却只有艺术创作学而无艺术传达学。正如接受理论有别于鉴赏理论一样,艺术传达学虽与创作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也有自己的理论视野与角度,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艺术是一种传达活动,但在有的论者那里,却认为艺术与传达无关;而在认为艺术是传达的人那里,关于什么是传达、艺术作品传达什么,则众说不一。其中包括著名美学家克罗齐、列夫·托尔斯泰等。本文试图对艺术传达的构成、内传达的发生、外传达及传达期待等问题作一思考,以呼唤系统的艺术传达理论早日问世。
艺术传达的构成
传达是人类传递信息、交换信息的行为。“传”字最早出现于周朝金文中。按《说文解字》的释义,传(繁体字作傅)左边义为“人”,右边义为“六寸薄”(注: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7页。)。“传”的字义为行夫手持六寸长的竹简,有“授”、“送”、“述”、“说”之意。“达”则有“通”、“畅”、“出”、“彻”等意。传与达合在一起,有传通、传告、告知之意,其现代含义是“把一方的意思告诉给另一方”。这是指日常意义的传达。
在英文中,传达与传播是同一个词:communication。但是作为文艺学的传达与新闻传播学的传播,二者却有较大的差异。就内容来说,传达,以情感为主,传播则以事件为主;传达,是审美行为,传播则一般是非审美的;传达带有较强的创造性,传播则一般不具有创造性。由于以上不同,在思维深度上,一个显得较为深层,一个较为浅层;一个只能由部分人(艺术家)进行,另一个则可以是大众参加。
“传达”这个词在古典文艺理论中是一个常用的词语。如在黑格尔的笔下就随处可以见到:
诗人的想象和一切其它艺术家的创作方式的区别……在于诗人必须把他的意象(腹稿)体现于文字而且用语言传达出去。(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3页。)
人一旦从实践活动和实践需要中转到认识性的静观默想,要把自己的认识传达给旁人,他就要找到一种成形的表达方式,一种和诗同调的东西。(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页。)
在黑格尔这里,“传达”是作为一个较为普通的词来使用的,但在列夫·托尔斯泰那里,“传达”这个词显得十分重要,他说:
正像人们借以传达思想和经验的语言是使人们结为一体的手段,艺术的作用也正是这样。不过艺术这种交际手段和语言有所不同: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感情。(注:《西方文论选》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64年版,第432页。)
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条件之一,传达是一种交际手段,而且传达完全是指感情内容而言的。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艺术感染力的大小所取决的“三条件”:“(1)所传达的感情具有多大的独特性;(2)这种感情的传达有多么清晰;(3)艺术家的真挚程度如何,换言之,艺术家自己体验他所传达的感情时的深度如何。”(注:《西方文论选》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64年版,第439页。)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十分重视传达,但所关注的传达的内容始终是“艺术家本人的感情”。
艺术仅仅传达感情吗?回答应是否定的。艺术的确是传达感情的,但艺术不仅仅在于传达感情,我们注意到,传达具有自身的独立的意义。艺术传达感情的说法,仍是把艺术放在从属的位置,艺术仍摆脱不了工具、手段的非本体的地位。
传达不是简单的“告知”,它是发现美、创造美的艺术工程。艺术传达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行为,它的功能是双重性的:一方面,艺术家作为精神的寻求者,努力去感受人类的真实境遇,感受人类所承担的命运,在完成这种传达的同时,另一方面以形式的创新满足人们的审美需要。
宗白华在谈到艺术创造过程时说:“艺术是自然中最高级创造,是精神化的创造。就实际讲来,艺术本就是人类……艺术家……精神生命的向外的发展,贯注到自然的物质中,使它精神化,理想化。”(注: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诗人的精神生命是如何向外发展的呢?诗人的精神生命在向外发展时,一方面是精神的自我强化、清晰化,另一方面即是“贯注到自然的物质中”,使之物化、形式化,或称符号化。在此,黑格尔对艺术特征的如下概括是十分准确的:“艺术作品之所以为艺术作品,既然不在它一般能引起情感(因为这个目的为艺术作品和雄辩术、历史写作、宗教宣扬等等所共有,没有什么区别),而在它是美的。”(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2页。)也就是说艺术的关键不在于有否情感。他强调的是艺术的美。美才是艺术的根本特征。因此,艺术传达的构成应包含以下两方面:一是开拓意蕴,二是给定结构。
意蕴,属作品的内容因素,是作品中的情感、思想的集中体现,是艺术作品的深层次内涵。黑格尔说:艺术借助于其外在形式,“显现出一种内在的生气,情感、灵魂、风骨和精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意蕴。”(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5页。)艺术作品深层丰厚的意蕴,是艺术家每次创造活动所努力寻求的。
艺术作品的深层内涵是艺术家生命质量的表征。胡经之说:“艺术活动就其本质而言,不是模仿,而是揭示;不是宣泄,而是去蔽;不是麻痹,而是唤醒;不是功利目的追逐,而是精神价值的寻觅;不是纯然的感官享受,而是反抗的承诺和人类生命意蕴的拓展。”(注: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因此,艺术的意蕴,是一种发现和探求,是一种精神的开拓。意蕴的开拓,实质上是创造主体心灵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对话,是在主客体关系的交流中进行的。
因此,现代艺术意蕴的开拓,一般也在主客体两个方向寻求,表现为外射型思路与内敛型思路。所谓外射,即是诗人将自己的情思与时代感、历史感、民族精神、宇宙意识接合,使诗情得以提升与熔炼。正如有的诗人所说的:“以诗人所属的文化传统为纵轴,以诗人所处时代的人类文明(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为横轴,……处在‘坐标点’上的我们的诗,也因此具有了某种自觉的‘纵深感’:两个领域互相渗透,使它同时成为‘中国的’和‘现代的’。”(注: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72页。)外射思路是发散型的,时空距离拉得较大,艺术视野开阔舒展。内敛型思路与之相反,强调向生命的内心深处作透视。有的诗人认为,“现代新诗的本质是人生复杂经验的聚结,只有思索的触角深入到意识的各个遥远的部落,意识和记忆里过去与现在极其复杂的见解才会相互渗透。”提出要把诗的触角“深入内心隐秘的地方”,因为生命本身“具有一种远非我们的洞察力和意志力能够企及的本质”。(注: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版,第149页。)应该说,主体与客体都是我们认识的对象、审美的对象,更是艺术表现的对象。艺术意蕴从上述两方面开拓,均有无限的可能性。
根据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品的意蕴或意义是由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双方共同实现的。传达者是意义的第一给出者,而接受者则是意义的第二给出者。艺术传达只有在第二给出者参与下才算最后完成。
艺术传达的第二项内容是给定结构。结构,就是艺术作品内部各组成部分的组合关系。给定结构,就是对艺术作品所要表达的内容予以形式的限定。艺术是通过这种限定,通过限定的诱导,进入艺术的特定图景和境相之中,领略其“诱导”之美与“限定”之美的。因此艺术就是创造“限定”。它虽是限定,却是一种非限定的限定,是一种“超限定”。作为精神产品,艺术总是凭借结构的“有限”而进入意义的“无限”。一个好的结构总是能使内容更大限度地生展,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因此,好的结构,就是最佳内容的最佳安排。在一个结构中,各个部分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成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是某一部分可有可无,并不引起显著的差异,那就不是整体中的有机部分。”(注:亚里斯多德:《诗学》,《〈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页。)一个结构就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的基本特点,系统中的各部分共同指向整体意义,整体意义大大超越了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之和。
意蕴的开拓与结构的凝定,是在同时进行的。不过,在艺术的酝酿期,这种结构只是内在的潜在结构,只有当它最后外化并凝定,才成为定型的外在形式。由潜在到定形,由内在到外化,是一个不断生展、调整、完善的过程。意蕴的开拓是艰难的,结构的凝定也非一蹴而就,这充分体现了艺术传达的创造性质。
意蕴的给出,结构的凝定,意味着一个艺术品的最终诞生,对创造主体来说,也即意味着艺术传达的完成。
内传达及其发生
艺术传达始于何时?一般的说法,是把艺术构思与传达并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传达即始于构思成熟之后。其实这是把传达简单化了。我认为艺术传达是包含获取信息、内心进行信息再加工,然后外化为形式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创造主体向外界获取信息,将信息作内向传达,在此期间,信息在心中几经整理、再生、扩大、积累,逐渐丰富化、定型化,这就叫内传达阶段;第二阶段,即是把内心已丰富化、定型化的材料外化为艺术符号,这叫做外传达阶段。内传达是外传达的必要准备和必经阶段,是整个传达活动的潜在阶段。
艺术的自我(内向)传达,与信息的自我(内向)传播性质相通。信息的自我传播,是每个人本身的自我沟通。作为客体的外部世界不时向主体的人提供信息,而主体则在心理和生理上作出反馈。人在饱览大自然风光时的自我陶醉、自我表露、自我宣泄,即是这种自我反馈的很好说明。而且它还可以表现为自我思考、内心冲突,乃至于自言自语、自吟自唱。演员心中的“潜台词”,电影中的画外音,文艺作品中人物的内心独白,都是这种自我传播的符号形式。自我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不同之处在于信息的传播者与接受者是融为一体的,而且这种自我传播的互动过程,仅限于自身,常常不要求、不希望与他人共享。因此,主体的自我传播的活跃程度决定了人脑信息库的内储信息量的多寡。艺术的自我传达亦同此理。联想、想象等心理活动都是一种自我传达,这种内在传达的活跃导致了信息的积累,是外向传达的必经阶段。内传达与外传达在艺术创造中是相依相存的。朱光潜指出:“画家想象竹子时,要连着线条、颜色、阴影一起想,诗人想象竹子时,要连着字的声音和意义一起想,音乐家想象竹子时,要连着声调、节奏一起想,其余类推。……由创造到传达,并非是由甲阶段走到一个与甲完全不同的而且不相干的乙阶段。创造一个意象时,对于如何将该意象传达出去,心里已经多少有些眉目了。”(注: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页。)这段话,一是说内传达中,既有内容因素,又有形式因素;二是说内传达是外传达的基础和准备,而外传达则是内传达的显示。在写作过程中的反复推敲、修改等都包含内传达与外传达的互动。所以说内传达与外传达是互为关联,不可能截然分割的。内传达与外传达的完美结合,才构成艺术的传达。
作为艺术传达第一阶段的内传达,是以信息的获取为始点的,它的直接的触发机制是审美感知。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感觉是站在最前列的,是二者沟通的桥梁,感觉使人与世界相遇。感觉和知觉统称为感知,都是人对外界的直接反应。列宁曾说:“感觉的确是意识和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是外部刺激力向意识事实的转化。”(注: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页。)所谓“转化”,正是内传达的开始,感知对内传达的触发作用也正表现在这里。
艺术创造是一种机缘,往往在不期而遇中到来。艺术创造到来之际,常常只是一种莫名的冲动,一种预感。有的诗人形容这种心情如暴风雨前的低气压状态,不知风从那一抹草叶间跃起,闪电从哪一片乌云中耀出。这时,情绪在急剧地膨胀,想象在疾速地驰骋,诗人的各种心理能力全方位地被呼唤调动起来,寻觅最后的那个突破点。法国诗人瓦雷里曾这样表述:“一个意外的事件、一个外界的或内心发生的小事、一棵树、一张脸、一个题目、一种情感、一个字就能触发人的诗情。”(注:瓦雷里:《诗,语言和思想》,《现代主义文学研究》(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54页。)可见创造预期到来之时,正是感觉起到了突破作用。
感知是认识的始点,感知也是传达的发端。外部的信息进入内部,艺术家的内心随时作出反馈,这种反馈又进一步激活人的感觉器官,催动感官对外界作进一步的探索。孙绍振说:“作家的观察的过程,就是从外部世界到内心世界,又从内心世界到外部世界不断互相说明,互相揭示的过程。”(注:孙绍振:《文学创作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8页。)在传达的过程中,感觉可以调动情感,情感也可以支配感觉、调动感觉。知觉与情感浑然化为一体,相互渗透、相互加强。情感的加入使得知觉更为活跃、敏锐、自由。感知虽是认知的初级阶段,但感知本身具有一定的理解力。人的感官是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践中逐步发展完善起来的,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的各种感官变得日益敏锐,富有理性和创造性。思想是感觉的积累,感觉中则往往包含着思想。感觉的理解力和穿透力,为内传达的丰富性和深度提供了可能。可见感知不仅启动了人的内传达,而且提供了大量信息,作为内传达的材料。
内传达的催动机制是审美体验。体验是主体的“经历”在主体身上留下来的结果,表现为由情感出发去感受、去思索生命的意义、生活的真谛。它的形成过程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只要某些东西不仅仅是被经历了,而且其所经历的存在获得了一个使自身具有永久意义的铸造,那么这些东西就成了体验。”(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生命本身是由命运、遭遇、诞生、死亡等要素组成的,这些要素也构成体验的要素。体验者必须要有一个内心要求:把感性个体与生活世界及其命运遭遇中所发生的许多具体事件结为一体,也即所谓“承担命运”。体验的目的即为从自己的命运和遭遇出发感受生活,力图去把握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体验具有内在性。内在性指艺术家在感受生活时必须有一个先在的意向结构,这个意向结构,类似于皮亚杰的“内在图式”,它体现了生命的深度,也决定了感受的向度和深度。因此,体验就是反思生活,把自已溶浸于生活之中,体味其中的真义,并审察自我内心。
体验由于情感的强度不同,分为一般体验和高峰体验二类。一般体验是情绪情感相对平和恬静状态下的体验,主客之间的交流表现得平静、从容、和谐。至于高峰体验,是人所体味到的最高的整合、同一和完善的感觉。心理学家W·詹姆斯描述过这种情感体验的状态:“当美激动我们的那一瞬间,我们可以感到胸际的一种灼热、一种剧痛,呼吸的一种颤动、一种饱满,心脏的一种翼动、全身的一种摇撼、眼睛的一种湿润……以及除此而外的千百种不可名状的征兆。”(注: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0页。)上述两种情形下的主客体契合、情感的震颤形成的心理反应,本身既是内传达活动,又是外传达的准备。
审美体验,是一种内向传达,主体既是传达者,又是接受者。在传达中,审美体验是传达的催动机制,这种“催动”作用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是催动情感的明晰化,进一步把握情感的性质。创造主体的情感体验,是伴随着情感理解的一种自我认识过程,它带有创造、发现、整理、组织和探索人类情感奥妙的性质。科林伍德描述这种情感体验的过程说:“首先,他意识到有某种情感,但是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情感是什么;他所意识到的一切是一种烦躁不安或兴奋激动,他感到它在内心进行着,但是对于它的性质一无所知。”(注:科林伍德:《艺术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由模糊到“明朗化”,只能通过情感信息的不断的内向传达,伴随情感理解和情感认识,才能达到。
二是催动对生活意义和价值的揭示与发现。这里所说的意义和价值不是指摆在外层伸手可取的具有明显功利性质的那一种。艺术家所要揭示的是人类生命、现实生活和历史中最内在、最本质的意义,使生命敞亮、世界澄明。
第三,情感的积累、思维的深化,促使艺术家最终产生艺术表现的欲望。情感在创造主体心中形成、保持并发展,到最后必定要求以某种形式加以确认,使之“不断加工直至完成”。艺术家形式创造的冲动,是情感积累的必然结果。
审美感知与审美体验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心理活动,都是在与对象的关系中产生的人类精神行为,两者互相渗透。但两者又有所区别。从内容上看,体验重在情感意义的把握,感知则重在传递外观形式;体验在综合的基础上进行,而感知则注重客体的方方面面。审美体验离不开审美感知,感知是审美体验的基础。审美体验的催动与审美感知的触发,导致了内传达活动的发生。
外传达及传达期待
克罗齐把传达叫做“外达”,(L'estrinsecayione)。在他看来,艺术的完成并不需要传达,必要的只是在心里直觉到一个情感饱和的意象。情感与意象猝然相遇而忻合无间,这就是直觉,就是表现,也就是艺术。它可以是诗,可以是画,也可以是其他。他认为把这个直觉到的意象,传达到一个外在的作品里,那是为自己备忘或是为便于旁人鉴赏,是一种有功利打算的实用活动,并非艺术活动;传达出来的作品也只是物质的事实而非艺术的事实。因为传达与艺术无关,传达所用的媒介不同也不能影响艺术本身的性质。
对克罗齐的传达观,朱光潜作了较全面的批判,他指出,艺术离不开传达。我心中尽管想象出一棵美好的“竹”,可是提笔来画它时,却手不从心,不能把它画出来,或者画得与心中所想象的相距甚远。可见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不仅在于能够直觉(一般人所为),尤其在于能产生“作品”(艺术家所为)。传达是艺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抹煞。此外,克罗齐没有分清有创造性的“传达”(语言的生展)和无创造性的“记载”(以文字符号记录语言)的区别,而朱氏认为这二者的区别很清楚。“传达”在克罗齐看来不是艺术活动,在朱氏看来却是很重要的艺术活动(注: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81~83页。)。
以上观点孰是孰非十分清楚。艺术创造是一种审美活动,而审美活动却不一定是艺术活动,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艺术传达。艺术家的审美体验只有传达出来才能成为艺术品,才能将个人的体验与感受传达给他人。黑格尔曾说:“艺术家的这种构造形象的能力不仅是一种认识性的想象力、幻想力和感觉力,而且还是一种实践性的感觉力,即实际完成作品的能力。这两方面在真正的艺术家身上是结合在一起的。”(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9页。)这里所谓“认识性的想象力、幻想力和感觉力”指的即是美的发现,后者“实际完成作品的能力”即是美的创造与完成,也即外传达的能力。
作为传达者,艺术家是传达行为的施予者和承担者。艺术传达能否成功,能否产生最佳效果,取决于创造主体的“传达期待”。
所谓“期待”,是一种心理结构,与接受美学的“阅读期待”一样,“传达期待”也是主体的一种建构性能力。所不同的是,“阅读期待”的主体是接受者,“传达期待”的主体是艺术传达者。传达期待是艺术创造者有别于旁人的主动的积极的心理准备,是艺术家多种心理能力的综合。在艺术传达活动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两方面的创造潜能:情感向具象的转化力、形式感或构形能力。
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使用的是形象,后者使用的是概念。别林斯基对此作过这样的阐述:“艺术和科学不是同一件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不在内容,而在处理特定内容时所用的方法。”(注: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428~429页。)两种思维方式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创造者。如同科学家能把思维上升为抽象的科学结论一样,艺术家也有其独特的潜能,迅速把握形象,将抽象的情感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画面。隶属于心理范畴的情感本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但在诗人笔下,不管是“喜怒哀欲爱恶惧”,都能够变得可见可闻,可感可触。例如,“思念”是一种不可见的情感活动,而在诗人笔下,思念却是一幅气韵生动、色彩鲜丽的图画:
我对你的思念充满春意/前面是波纹鲜明的流水/背后展开一片绿色的原野/ 寂静的云彩下面/你的微笑有如鸟群翩飞(注:蔡其矫:《生活的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诗人很巧妙地把“思念”与“春意”建立起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幻化出一幅想象图景,这幅图景空间异常开阔坦荡:前有流水,后有绿野,上有云影,中有飞鸟,生气与灵气充溢流荡其间,令人神往。再如“欢乐”也是抽象的情感概念,但在诗人笔下又可以转化为生动的意象:
告诉我,欢乐是什么颜色?/像白鸽的羽翅?鹦鹅的红嘴?/欢乐是什么声音?像一声声芦笛?/还是从簌簌的松声到潺潺的流水?(注:何其芳:《预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
情感需要转化为具象,这是艺术的本质规定性所决定的。人类的情感表现有两类,一为自然表现,一为艺术表现。自然表现是宣泄性的,如快乐时放声歌唱,悲伤时黯然垂泪,愤怒时暴跳如雷……这种表现是直接的、随意的、瞬间即逝的。而情感的艺术表现是通过呈现意象来实现的。只有当情感转化为意象,才是艺术的表现。情感的艺术表现,带有创造、发现、整理或探索感情之奥妙的性质,因此,它的着眼点不在情感的发泄,而在情感的保留与呈现。这就是艺术表现的特点。而艺术家更具备这种情感向具象的转化能力。
一个艺术创造者,必定有强烈的形式感与形式意识,这同样构成了传达的期待内容:形式感或构形能力。
正如一切创造行为一样,构形同样是人类的本性之一。歌德曾这样说:“人有一种构成的本性,一旦他的生存变得安定之后,这种本性立刻就活跃起来;……因此野蛮人便以古怪的特色、可怕的形状和粗鄙的色彩来重新模塑他的椰子、他的羽饰和他自己的身体。而且虽则这些意象都只有任意的形式,形状仍旧缺乏比例,但是它的各个部分将是调和的,原因是,一个单一的情感将这些部分创造成为一个独特的整体。”(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页。)以上讲的是人类在绘画与体饰上的形式创造。诗人的形式创造也同样如此,诗人的“想象会把不知名的事物用一种形式呈现出来,诗人的笔再使它们具有如实的形象,空虚的无物也会有了居处和名字。”(注: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52页。)艺术创造活动中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确定形式,使情感各得其所,获得各自的位置。有了形式,艺术品就作为精神产品成为这个世界的一种独立的存在物。
那么在内容与形式之间何者是决定因素呢?对理论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这个问题,只要放到艺术传达的整个过程中去,分阶段加以考察,就可合理地、科学地加以解决。也即在内传达阶段与外传达阶段,内容与形式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内传达阶段,内容起着更大的作用,是内容在呼唤形式、寻找形式,形式是内容生发出来的,只有在有了内容需要表达的时候才去寻找表达的形式。而且特定的内容本身就已包含着它采取什么显现方式的依据或要求,“艺术之所以抓住这个形式,……是由于具体内容本身就已含有外在的,实在的,也就是感性的表现作为它的一个因素”。(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63页。)所以在内传达阶段,内容对形式有更多的决定作用,这种决定作用,表现为内容对形式的选择与呼唤,而此时的形式,只是潜在形式或隐性形式;反之,在外传达阶段,形式一旦形成,它既显现着内容、生展着内容,形式对内容有了更大的决定作用,而且形式本身具有审美价值,成了审美对象。
每种艺术都有其独特的形式。文学艺术中,小说、散文、诗歌的形式各有不同。形式对读者的阅读起到某种规范引导作用,即“教导人们学会观看”,而且是教导人们学会以此种形式而非彼种形式去看。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总会带着特定的形式意识或形式期待去接触作品的:即阅读一篇小说时,你是把它作为“小说”来对待,阅读一首诗歌时,你也必须在心理上有把该作品当作“诗”来阅读的期待,对散文、戏剧等都是如此。内传达时内容决定形式,但当作品完成以后,也即外传达实现后,形式即已规定了内容的文体属性。换言之,同样的一个内容,由于形式改变,其文体属性或文体感也会随之变化。比如说,某位作者对如下事件作这样的陈述:
跃出水面挣扎着而又回到水里的鱼对跃进水里挣扎着却回不到水面的诗人说:“你们的现实确实使人活不了。”
这完全是一种散文化的叙述,可以把它看作一则寓言,或者是一则幽默性的讽刺小品。但台湾诗人非马在把同样内容作了如下排列后,效果截然不同:
跃出水面/挣扎着/而又回到水里的/鱼//对//跃进水里/挣扎着/却回不到水面的/诗人//说//你们的现实确实使人/活不了
(《鱼与诗人》(注:刘登汉编:《台湾现代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页。))
谁都会说:这是一首绝妙的诗!意象生动单纯,对比鲜明强烈,意蕴深刻丰满,具有极大的艺术张力。而这却是散文化陈述所无法达到的。这是一种“文体效应”。因为每种文体都有构成它的独特的“语言使用场”,有它自己的语言规定性。当一种语言形式脱离了原来的文体,改变了所属的语言场后,它的功能就随之改变,接受了另一种规定性,产生了新的文体效应。
语言艺术是这样,其他艺术形式也是这样。这说明,在作品形成以后,即艺术传达完成以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已起了变化,不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对内容的生成起了决定作用。形式展现了内容,形式还可以规定内容、改变内容、创造内容,强化或弱化内容。当然形式的探求总是指向内容和为了内容的。形式的作用既然如此,对于艺术传达者来说,形式感与构形能力就显得十分重要,每次艺术传达都是对创造主体构形能力与形式意识的极大考验。
卡西尔说:“艺术家是自然的各种形式的发现者,正像科学家是各种事实或自然法则的发现者一样。各个时代的伟大艺术家们全都知道艺术的这个特殊任务和特殊才能。”(注: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与艺术结缘,意味着与形式的创造结缘。创造主体必须从形式的期待出发,进而走向形式的辉煌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