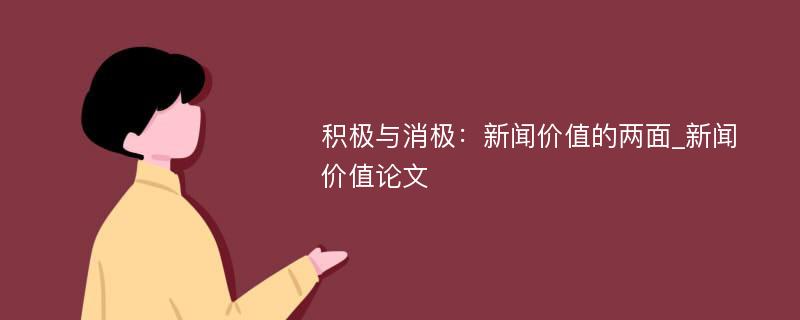
正向与负向:新闻价值的两面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面性论文,价值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闻价值是新闻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迅速发展以及西方传播学的引入,我国新闻学界对新闻价值的讨论逐渐升温。从最初的新闻有益论,到对新闻价值客观性的讨论,再到以受众需要为中心的新闻价值理论的形成,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渐趋辩证。这期间,一些哲学上关于价值论的研究成果的引入,更进一步深化了新闻价值理论的研究。但不可否认,关于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仍然存在着一些尚未理清的问题,甚至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盲点问题,例如关于新闻价值的社会属性问题、关于新闻价值的正向价值与负向价值问题等,需要进一步探讨。
一、新闻价值的价值属性及特点
对于价值的主体性和客体性、主观性和客观性,历来有着不同的争论。西方主观主义价值论者更倾向于把价值定义为一种观念和评价,认为价值是作为主体的人依据自身的情感、兴趣、欲求、好恶态度等对客观事物作出的评价;而客观主义价值论者则认为价值虽然同主体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从客体的自然属性演变而来,并不依赖于主体对它的意识、态度和评价。一个最通俗的比喻是某个地方有储量为一吨的黄金矿藏,黄金的价值确实是相对于人而言才有意义,但无论人们有没有发现这一矿藏,它都是自在的,它的黄金属性是不会改变的,它并不因人的“未知”而消失或减少,也不会因人的“已知”而有所增加。没有客体也就无所谓价值,价值对客体具有很强的依存性,亦即价值具有客观性。杜尔克海姆在其著作《社会学和哲学》中谈到价值的客观性时说:“简而言之,价值就是由一个事物的固有特征所引起的结果的实际证明。”日本哲学家和教育家牧口常三郎对这句话评点说:“这段话中包含着一些真理,没有人会怀疑赋予一个客体以内在价值的主要原因在于客体自身。”[1]他认为如果没有客观价值,人们对事物的评价就一定会失去基础。他举例说:“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人要一定量的稻米,他设想的价格同市场上的稻米价格相比,贵一点或便宜一点,其差别就不会很大。稻米的当前市场价格就被叫作稻米的客观价值,即作为社会大部分所同意的价值。”[2]
正是从这一客观主义价值论出发,于是有一些学者也倾向于从客观性的角度来诠释新闻价值。
陈国少认为新闻价值“是它本身所固有的,并且有一个由该新闻的内容所决定了的量。”[3]卢惠民指出,“写作技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妙笔生花’的作用,但技巧只能使本来有价值的事实表达得更精彩一些,而绝不可能把石头涂上油彩变成珍珠。”[4]“新闻价值像一种矿藏,存在于某些事实之中,记者只是探明它之所在,并设法将它开采出来,但决不能凭空制造它。”[5]新闻价值是选择和衡量新闻事实的客观标准,即事实本身所具有的足以构成新闻的特殊素质的总和。素质的级数越丰富越高,价值就越大。[6]“新闻价值是新闻客观所具有的能够及时满足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提出的对各种信息的需要的特殊功能。”[7]“客观事实中存在的,能够满足社会主体需要的新闻属性,我们称之为新闻价值。”[8]
上述这些关于新闻价值的客观性的论述是否正确,该如何看待和理解新闻价值的属性呢?新闻价值的属性与一般价值的属性是有区别的,用一般事物价值属性来套论新闻价值的属性并不合适。关于一般事物价值的属性说有两种:一种是“主体属性”说,认为价值产生和存在于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意识和意志之中,价值因人的意志而转移。另一种是“客体属性”说,它认为客体的价值是由客体的存在本身所决定的,是客体物自在的一种属性,客体存在,其价值也就存在;客体消失,其价值亦即消失,与主体并无关系。而对于新闻价值来说,它是既非主体属性亦非客体属性能够概括得了的。由于新闻是一种社会存在,本身主要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映,如时政新闻、经济新闻、军事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等,它既非完全的客体存在,也非完全的主体存在,这决定它的价值属性既不同于完全的客体属性,也不同于完全的主体属性。
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其价值不同于一般事物价值的最重要一点,应是它的社会属性,新闻价值是从社会属性演变而为价值属性的。这一社会属性与其他事物(例如黄金)价值的自然属性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主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闻价值具有模糊性的特点。新闻不同于一般自然客体的很重要一点在于,一般客体的价值可以做到精确计量,而新闻价值却难以做到。例如,对一座矿藏评估后得出的经济价值,与对一条人类登陆月球消息评估后得出的新闻价值,两者显然大有不同:前者是对自然客体的评估,可以进行精确估算,并且具有客观价值标准;后者是对人类社会活动的评估,只能模糊概算,不可能有精确的客观价值标准,而只能依靠一些相对主观性的价值标准(如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进行评价。
二是新闻价值具有相对性的特点。从构成新闻价值的共性因素考察,所谓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以及利害关系、反常等的新闻价值判断标准,都是从事物相对于主体的意义来作出的判断,或者说更主要是从价值主体角度作出的判断。所谓价值主体是指“在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中的需求者,即在一定的价值意识的指导下,按着对一定的价值目标的要求,从事创造活动的人。”[9]价值主体对价值的评价和判断难免带有比较强的主观色彩。日本哲学家和教育家牧口常三郎论及价值的主观性时说:“价值是根据每一个个人所怀有的无法言传的标准而定,这标准即是被感情所左右的不稳定不确定的心境。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处于同一心境的人们赞叹说:‘这真美啊!’而别的人却不一定附和同意。”[10]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也是这样,主体的差异性,甚至认识时机的差异性都会导致人们对价值的把握难免见仁见智。由于价值主体是由“个体价值主体、群体价值主体、人类价值主体”等多层面构成的[11],它可以包括个人、男女、集体、民族、国家等,即使是个体的人,也是千人千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因此,这就决定了新闻价值取向的多层次性,不同层次的受众对同一新闻信息所包含的新闻价值的判断是不同的:“人是处于一定历史之中的人,就是在同一时代,社会人们也是分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兴趣等的各个部分的。一些新的事实,对这一部分人,新的信息数量大些,信息的质量高些,而对另一部分人,新的信息数量少些,质量差些,还可能对某一部分人,根本没有什么新的信息。”[12]新闻价值的这种相对性说明新闻价值是一种相对价值,而不是一种绝对价值。
三是新闻价值不具有恒定性,而更具有暂时性、变动性的特点。其他客体价值,例如自然客体的价值都具有比较恒定性的特点,很多自然客体的价值甚至具有重复使用的特点。相对于这些自然客体的价值而言,新闻价值更具变动性的特点。一方面,新闻是“易碎品”,有些新闻一经传播,其价值会迅速衰退,而且不可重复使用:一个厂家可以持续生产一种产品,一家商店也可以持续售卖一种商品,但一家报纸不可能天天刊发同一则新闻,甚至昨日刊发的新闻今天也不能再拿出来填充版面,否则就被斥之为“炒冷饭”,报纸就会失去读者,这与其他事物的价值具有很大的不同;另一方面,社会传播活动决定着一些新闻的新闻价值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记者写好稿件之后,其新闻价值并未实现。如果它被‘枪毙’了,或‘压死了’,那么它的新闻价值就永远不能实现了。”[13]而在有些情况下,媒体则在推波助澜地创造着新闻价值:一些本来默默无闻的歌手经媒体的包装炒作,成了明星,于是他们的一举一动甚至绯闻就都具有了新闻价值,称之为“星闻”。但很显然,这块“黄金”的价值是人造的,或者说是媒体制造的。这些都体现出新闻价值的社会属性。
当然,强调新闻价值的模糊性、相对性和非恒定性,并不是完全否认新闻价值的客观性,新闻价值是一种社会属性而不是纯粹的主体属性,这本身就是对新闻价值的客观性的强调。新闻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毫无疑问遵循着一定的价值规律。新闻价值的这种客观性主要体现为一种受众对新闻的社会属性的共性把握。例如新闻业界和新闻学术界总结出的一些构成新闻价值的共性因素,包括重要性、显著性、时效性、接近性、趣味性等,这就是一种对新闻价值的共性把握,这种共性的把握就是一种客观性。西方新闻学一般都把读者兴趣作为新闻价值的客观评判标准,他们把读者的共性趣味归纳了一下,像利害关系、金钱、性、冲突、反常、大规模的事件、竞赛、犯罪等,认为这些内容是受众最为感兴趣的,因而也就成为判定新闻价值的客观标准。
受众对新闻价值的这种“共性把握”,更多地受制于主体的社会性,而不是主体本身,这也是新闻价值客观性之所在。从新闻价值方面来说,由于受众个体的差异性,同一条新闻对不同的受众主体可能具有不同的新闻价值。例如,一场顶级球赛对于一个不喜欢球类运动的人来说,可能就没有任何新闻价值;一条发生在高校的论文剽窃事件对于种田的农民来说也同样不会感兴趣。这看似是新闻价值是由主体决定的,但实际上,它是由主体的社会性决定的,是由主体的社会化程度以及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决定的。艾丰在谈新闻价值的这一特殊性时就曾明确指出:“新闻价值不同于事物的那些自然属性,乃是一种社会属性,它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14]新闻价值有赖于主体对新闻事件的“共性把握”,它只有相对于主体才有意义,但不能说新闻价值完全是主体的附庸,成为主观意志的玩偶,如果那样新闻价值将因主观随意性而变得不可衡量,新闻价值将成为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
二、新闻价值不是单一的正向价值
价值的本意具有“可贵、可珍惜、令人喜爱”等内涵。“价值”这个词在它的最早使用阶段,主要只是在经济意义上使用,而且具有正向意义。如日本哲学家和教育家牧口常三郎就认为“真正的价值概念是由得、善、美构成的。”我国著名的价值哲学研究者王玉樑亦认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主要是对主体的发展和完善的效应,从根本上说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和完善的效应。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包括对主体生存、发展、完善的效应。客体对主体生存的效应,是价值的初级本质;客体对主体发展和完善的效应,是价值较深层次的本质。在客体对主体(包括个体主体、群体主体、社会主体)发展和完善的效应中,客体对社会主体的发展和完善的效应,是价值更深层次的本质,也是价值之所以成为价值的根本点。客体对社会主体发展和完善的效应,是评价客体价值的最高标准。”[15]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学者们主要是从有利于主体的完善和健康发展的正向角度来定义价值的。
与此相同,在我国新闻学术界,很长时间以来,对新闻价值内涵的诠释也是沿着正向来进行。王玉樑认为,“所谓新闻价值,应该是指新闻本身所具有的能够给社会以积极影响的功能。”[16]孙世悦认为,“价值是指客观事物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作用或积极作用。新闻价值,就是新闻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积极作用。”[17]沈如钢指出,“什么是新闻价值呢?新闻价值指的是新闻作为新闻的本质、内涵、特性所具备和表达的程度;指的是新闻作为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物,它的完美的程度;指的是新闻作为传播消息、组织舆论的手段,对人民群众吸引和感受的程度;指的是新闻作为传播文化知识和思想教育工具,它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生活的改善和人类社会进步事业的发展所起实际效果的程度。”[18]
进入到21世纪,一些新闻学著作仍然承续着这一倾向。例如对于构成新闻价值的趣味性这一要素,一些学者对此所作的解释是:“趣味性不同于西方新闻价值理论中的‘人情味’,它既包括新闻事实能够提供的和谐多彩的审美情趣和健康向上的生活乐趣,也包括新闻作品在内容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和贴近实际,以及作品风格上的生动有趣和喜闻乐见。其实质是新闻对受众精神与情感的善意满足。”并认为西方新闻理论中把女人、金钱和罪行奉为最有价值的三类新闻是一种“荒唐的新闻价值观念”。[19]
上述从新闻有益的角度对新闻价值进行的定义,也包含了对新闻价值的评价,但这一评价却是不完善的,它只包含了对新闻价值的正向评价,而没有包含对新闻价值的负向评价。平时经常谈到“价值取向”一词,所谓“价值取向”就是一种价值评价,于是就有了“正确的价值观”和“错误的价值观”、“积极的人生价值观”和“消极的人生价值观”之说。也就是说,价值不仅包含有正向价值,还应该包含有负向价值。研究价值学的学者曾明确指出:“价值是一种新质,这种新质的规定性就是客体对主体生存或发展的效用或意义。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利与害、善与恶、美与丑、好与坏、有用与无用、正义与非正义、合理与不合理,等等。”[20]这里即指出价值的评价不应只包括正向的评价。牧口常三郎在《价值观》一章中首先引述李普斯的价值论说:“不能否认,自私的欲望的满足也是快乐。可是,在我们的官能快乐是由伤害别人所取得的时候,在自己的利益依靠损害所有权而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同意这样的快乐是有价值的。”牧口常三郎接下去反驳这一观点说:“我不同意上述的观点。因为社会上流行的‘价值’的这种用法不仅意指道德的行为,而且也意指着卑劣的和不道德的行为。确实,官能的欲望和自我利益的满足不能被叫作是‘道德的’,但是这些又被广泛地承认是经济价值。”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将价值一词赋予更多的褒义,把对生活有帮助的、肯定的方面看作是“有价值”的,而对生活具有负面影响和破坏作用的方面则被视作是“无价值”的,这一定义显然具有不妥之处。正如牧口常三郎所说:“如果对生活有用的肯定的方面被认作是有价值的,其否定的方面被称为负价值比称为无价值就要更加合适些。可以保险地说,如果价值归于零后,再沿着同一方向进展,就会达到负价值的状态。”“我认为,明确地把正价值和负价值区别开来,把前者作为肯定价值,后者作为否定价值,是比较合适的。”“在我们考察外部世界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两种,一些对人类的存在具有积极的用处,另一些则是有害的。与善相对的恶,与得相对的失,与美相对的丑,就代表了人类生活的否定方面,我们叫这些否定的价值为‘负价值’,而不用‘有价值’或‘无价值’这些词。而肯定的价值叫做‘正价值’。”研究价值学的李德顺对这一问题也做过明确阐述:“‘好坏’就是口语中的‘价值’;‘价值’,就是学术化的‘好坏’。”“单说‘价值’,就是指‘好坏的价值’,是个中性概念。其中‘好’的一面,可以叫做‘正价值’或简称‘价值’;‘不好’或‘坏’的一面,则叫‘负价值’。”[21]
三、引入“负面新闻价值”的意义
在新闻价值的讨论中,引入“正价值”和“负价值”概念也是非常必要的。这可以帮助人们更加客观全面地考察新闻价值的本体意义,尤其是在讨论西方新闻价值观以及新闻报道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时,这两个概念的引入将有助于更辩证地审视一些问题。
一直为新闻学术界所诟病的一个现象是,为什么新闻媒体的“煽、色、腥”新闻此消彼长难以根除?为什么一些对社会风气有不良影响的节目收视率却一直居高不下?例如美国的谈话节目《奥帕拉·温弗瑞》,经常涉及性、强奸、乱伦、卖淫、吸毒等非常敏感、刺激的新闻话题,但却拥有最高的收视率?[22]当学术界一再指斥这类节目内容没有任何“价值”的同时,它们却受到受众热情的追捧,这是为什么?
引入“负向新闻价值”这一概念的意义就在于:从新闻的社会评价来说,过去对涉及凶杀、色情等具有负向价值的新闻多以“毫无价值”一言蔽之,言外之意是这类新闻对社会毫无益处。但实际上,“毫无价值”应该指的是既无益处又无害处,也就是牧口常三郎所说的价值“归于零”。但是很显然,有很多“煽、色、腥”的新闻,它们的影响并非停留在零上,而是产生有负面的影响。而“负向新闻价值”正可以诠释这一现象。从受众角度来说,很多“煽、色、腥”新闻虽然具有负面社会效应,甚至很多受众也深知这类新闻的负面影响,但这类新闻却有着广泛的受众市场,为受众所需要,也就是说,对于这些受众来说,这类新闻是有“价值”的。而且受众的这一“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媒体的价值取向,推动着媒体对“煽、色、腥”新闻的追逐,那么这个“价值”是什么?这就是“负价值”,或者说是“负向新闻价值”。如果继续使用“零价值”或“无价值”这些概念,而拒绝引入“负价值”概念,就不能解释诸如一些媒体卖力地刊发“煽、色、腥”和媚俗新闻这一行为。
那么如何定义“正向新闻价值”与“负向新闻价值”?所谓“正向新闻价值”,就是从新闻有益论角度进行的概括,是指新闻对社会发展、公共利益以及民俗风尚等具有正面的建构意义。例如新闻有利于正确的舆论环境的营造,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创造与积淀,有利于科学文明的传播与承续,有利于健康审美情趣的培养等,这些都是正向新闻价值的体现。所谓“负向新闻价值”是指新闻价值对社会发展、公共利益以及民俗风尚等具有负面的、或破坏性的作用。西方新闻价值学中,把色情、暴力犯罪、名人隐私等视为重要的新闻价值标准。而这些内容对社会具有负面的教化作用,这类新闻过多则会导致社会风气败坏、犯罪率上升等,因此把这类新闻所包含的新闻价值称之为“负向新闻价值”。负向新闻价值可以包括以下一些内容:
偷窥价值。例如对明星、重要领导人等的隐私的报道,即是迎合了受众偷窥的欲望。
宣泄价值。例如对一些罪案、暴力事件的报道,可能会迎合一部分受众的灰暗心理,体现出一种不良社会情绪的发泄。
审丑价值。对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的报道,例如一些媒体热衷报道血腥的画面、带有色情性质的新闻等,就是迎合了部分受众的审丑心理。
习恶价值,或可称“伪榜样价值”。一些罪案报道中,涉及犯罪手段、破案过程的报道可能会为犯罪分子所模仿。例如有媒体在报道一些青年学生中流行喝“摇头水”这一新闻时,详细介绍了“摇头水”的配方、喝“摇头水”的感受等,这样的报道可能会给一些青少年提供模仿的途径。
从根本上说,新闻是相对于受众的一种消费品,它的价值是相对于受众需要而存在的,正如童兵所说,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满足社会需求的特殊要素的总和”[23]这里最重要的是“需要”二字,它强调的是从主体出发来定义新闻价值这一概念,正因为它是受众需要,所以才有价值。既是需要,那么就有“正当的需要”,也有“不正当的需要”;有“健康的需要”,也有“不健康的需要”。与之相对应,新闻价值也有“正价值”与“负价值”之分,这样,对新闻价值的研究和诠释才能够趋于全面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