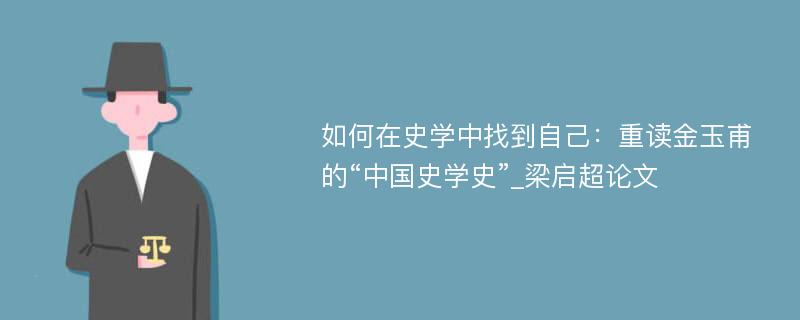
史学怎样寻找自己——重读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史学史论文,金毓黻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金毓黻是20世纪上半叶很有成就的史学家,以精于东北史研究、宋辽金史研究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为世所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收入了他的《中国史学史》,这是中国史学史这门专史在开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在40年代至60年代有一定的影响。
金毓黻,原名毓玺,一名玉甫,字谨庵;又字静庵,别号千华山民,室号静晤,辽宁辽阳人。他生于清光绪十三年五月(1887年7月), 卒于1962年8月,终年76岁。其父金德元为乡间塾师,重视教育, 故金毓黻6岁即入乡塾就读。16岁时,因家境所困,辍学。1906年,20 岁时入辽阳县启化高等小学堂就读。1908年,考入奉天省立中学堂,1912年中学毕业。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堂文学门,1916年夏毕业。求学期间,深受启化小学校长白永贞和北京大学教授黄侃影响,前者爱其才而特许其免费就读,后者使其懂得治学。金毓黻后来写道:“余少受知于佩珩先生(白永贞,字佩珩),承其奖饰拔擢,始出泥滓而履坦途。四十年来,得时时温理故书,日与古人晤对,而不致为君子所弃者,师之赐也,如何可忘!”又赋诗追叙受业于黄侃云:“廿七登上庠,人海纷相逐。廿八逢大师,蕲春来黄叔。授我治学法,苍籀许郑优。研史应先三,穷经勿遗六。文章重晋宋,清刚寄缛郁。”这可见他对于师情的诚挚。
北京大学毕业后的20年间(1916—1936年),是金毓黻踏入仕途的时期,先后就职奉天省议会秘书(1916年)、 黑龙江省教育厅科长(1920年)、吉林省财政厅总务科长(1923年)、东北政务委员会机要处主任秘书(1929年)、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日寇逮捕,拘押三月余,后经人斡旋得释,出任伪省图书馆副馆长。1936年,以考察文物为名,假道日本东京,回到上海,继而转赴南京,经蔡元培、傅斯年介绍、推荐,受聘为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兼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参议。1937年5月,赴安庆, 出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38年春,中央大学迁至安庆,旋回中央大学担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1945年秋,转至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任教,兼任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后改为文科研究所)主任。1944年4月,再回中央大学执教,兼任文学院院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6年回到东北。1947年,任国史馆纂修、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秋,赴北平,任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旧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 金毓黻转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兼任教授,同时在辅仁大学兼课。1952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直至1962年逝世。
2
金毓黻博极群书,功底深厚,学有渊源,于理学、文学、小学、史学皆有造谐。尝曰:“余之治学途径,大约谓始于理学,继以文学,又继以小学,又继以史学。”自谓1923年以前,治学兴趣主要在理学、文学、小学;1923年以后,兴趣转向史学。其治史,则深受清人之影响,他写道:“余之研史,实由清儒。清代惠、戴诸贤,树考证、校雠之风,以实事求是为归,实为学域辟一新机。用其法治经治史,无不顺如流水。且以考证学治经,即等于治史。古之经籍,悉为史裁,如欲究明古史,舍群经其莫由。余用其法以治诸史,其途出于考证,一如清代之经生,所获虽鲜,究非甚误。”要之,金毓黻的学术渊源出于理学;而其史学方法,则出于考证。这是他的学术上的特点。
金毓黻之治史学,正值社会动荡、民族危难之机,出于忧乡、爱国之心,故首先研究东北史。他先后编纂了《辽东文献征略》8卷( 1927年出版);《奉天通志》260卷(1937年以前印刷出齐);《辽海丛书》10集,收书87种(1936年印竣出齐);《渤海国志长编》20卷(1932年底完稿)。
1930年以后,金毓黻写出了他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三部著作,即《东北通史》上编、《宋辽金史》、《中国史学史》。《东北通史》上编,初撰于1936年,1941年修订,始上古,迄元末,由东北大学石印出版。这书系统地勾勒出了东北古代历史发展的轮廓,是关于东北史的奠基之作。宋辽金史的研究,是与东北史研究密切相关的。诚如金毓黻在《东北通史》引言中所说:“东北史不过为国史之一部,欲研史之士集中精力于此,势有不能。第研史之途径不一,全视研史者之兴趣如何。倘富于研究辽金史之兴趣,则对于东北史亦不能不有相当之注意,于是研究辽金史饶有兴趣,而研究东北史亦才有兴起矣。”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经数年之讲授、修改,金毓黻于1944年撰成《宋辽金史》一书,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史学史》一书,始撰于1938年,1939年定稿,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征引资料较富,编排清楚,叙述严谨,纵控自如”,是作者比较满意的著作。这三部书,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撰述。(注:以上内容,参阅《静晤室日记》前言,以及金景芳所撰《金毓黻传略》(《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此外,金毓黻还有著作多种,不一一列举。而他的《静晤室日记》(1993年辽沈书社出版)这部169卷的巨帙,是其自1920年3月6 日至1960年4月30日长达40余年的心血所积累,凡550余万字。它不仅铭刻了作者治学、做人、处世的心迹及其所得,而且也在一定的意义上反映出了20年代至60年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若干侧面和史实,既可作为日记来读,也可视为传记来读,甚至也可视为长编来读。这是作者留给后学的一份极珍贵的遗产。
3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撰写,查阅《静晤室日记》,作者有如下的记载,兹转录于此,或可有助于对此书的认识: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23日:“始撰《中国史学史》, 无可依傍,以意为之。梁任公于其《历史研究法续编》中有‘中国史学史作法’一节尚可取资,惟语焉不详。闻卫聚贤撰有是书,由《大公报》出版,亦未之见。”
2月26日:“撰《史学史》导言竟,接撰第一章古代之史官, 约得三千余言。近三四日思绪棼乱,若不可梳理。今日闭户沉思,略得端绪,伏案撰稿,乃如剥笋抽蕉,书卷奔凑腕下,不觉头头是道矣。凡事须于苦中得乐,此之谓也。”
3月2日:“撰《史学史》稿第一章《古代之史官》竟,取材不丰,笔不达意,殊未惬心。”
3月4日:“撰《史学史》第二章《古代之史家与史籍》竟。”
5月5日:“撰《史学史》第五章竟。”
5月8日:“余撰《史学史》原定八章,兹以尚有未备,增二章,非十余万言不能尽。原期于六月底毕功,为时仅月余,暑假将届,只好延至下学期补足耳。”
7月7日:“撰《史学考》中改修《宋史》之一节,颇能究其始末。”(引者按:《日记》中常常用《史学考》,说的就是《史学史》。)
7月22日:“撰《史学考》改修《元史》一节竟。 续撰自正史中分撰之别史,如马、陆二氏之两《南唐书》是其例也。钱士升《南宋书》亦自《宋史》分撰,欲以上继《东都事略》,而实非其伦;其可称者,其谢启昆之《西魏书》、吴任臣之《十国春秋》乎。”
7月29日:“撰《史学考》第七章,具稿已六七十页,而未毕其半,何繁而不杀,一至于此耶。”
8月24日:“闭户草撰《史学史》,凡得十余页,近一月来所未有也。”
9月15日:“撰《史学考》纪事本末一节,于诸家所论之外, 又有采获,自谓不无一得。”
9月22日:“撰《史学考》第七章竟,凡得六万余言, 约当第一章之五倍,第六章之三倍,殊患其繁,然亦欲简而不得者。”
10月14日:“撰《史学考》第八章竟,约得二万余字。”
10月24日:“撰《史学考》第十章,以近顷重要之发见为基础,如殷墟之甲骨、敦煌之木简及写本、内阁大库之档案三者是也。”
11月17日:“续撰《史学考》稿,每日约得二、三千言,期以十余日毕功。”
11月26日:“撰《史学考》结论毕。自本年三月始功,十一月末讫功,凡九阅月,中间旅行约一阅月,实为八阅月,计二百四十余〔日〕。全书十章,合导言、绪论,凡得二十万言,每日平均撰稿一千字上下,此旅川以来读史之所得也。”
12月17日:“改撰《史学考》第一章古代史官,原稿十存其三四,易者约十之六七。”
12月22日:“改撰《史学考》古代之史家与史籍一章,大致已毕。因未细读原文,改过之后,方知重复。可知删改之作,有不如原文之佳者,凡事求之过细,往往欲益反损。”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31日:“整理《史学史》稿略竣。”
2月10日:“以《史学考》中《最近史学之趋势》一章, 送《新民族周刊》发表。”
2月22日:“修改《史学考》第五章粗毕。”
6月3日:“订补《史学考》全稿,竭一日之力,仍未能毕,此稿凡订补多次,甚矣,撰作之难也!”
9月15日:“修订《史学史》稿本,须费数日之力,拟托郭任生携往香港,交商务印书馆排印。”
9月18日:“修正《史学史》稿毕事,稍有增窜。”
9月19日:“诘朝入城,访郭任生,以《史学史》稿交之, 托其携往香港。”(均见《静晤室日记》第六册,卷九六——卷一○一)。
以上所节录的这些文字,可看作是这部《中国史学史》的撰述史。它生动地反映出来这部《中国史学史》的撰写过程,反映出来作者在撰写过程中的心境和思想的轨迹,反映出来作者在撰述上曾经碰到的问题,而有些问题对今天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仍有学术上的启发。我以为,这些文字的可贵性,是作者的其他一般性阐述所无法替代的。
《中国史学史》的撰写,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1938年2月至9月,为撰述阶段;1938年12月至1939年9月,为修改订补阶段,首尾约一年半时间。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作者没有说明的,即在撰写过程中,作者有时称本书为《史学史》,有时又称本书为《史学考》,且频频出现这两种名称。这当然不是作者的笔误,把“史”写成了“考”,而是作者可能确有这样的想法,即本书最终也可能会取名《中国史学考》。这当然只是推测,但这推测一是以《日记》为依据,二是考虑到作者推重清人考据学成就的缘故。在没有发现作者本人的其他说明之前,姑妄言之,存以备考。
4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一书,在整体内容的安排上受梁启超的启发,在撰述方法上受考据之学的影响。
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时,可资参考者甚少。其1938年2月23日日记说是“无可依傍,以意为之”的话,确乎事实。同日日记提到“卫聚贤所撰”外,此时还有一些学人如曹聚仁、卢绍稷、何炳松、罗元鲲、周容、陆懋德、李则刚等,也撰写了与中国史学史有关的论著(注:朱仲玉:《中国史学史书录》,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虽都不是有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但金毓黻也未曾见到。当时,他所能见到的,主要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日记》作“续编”)中关于中国史学史做法的论述。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三的第三章讲到“文化专史及其做法”时,专有一节阐述“史学史的做法”。梁启超认为:“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它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他还提出自己的设想:“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率先提出“史学史”作为一种文化专史必须进行研究以及如何研究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创见。这是近代意义上中国史家对史学之史的新认识,对史学史学科的创建、发展有重要意义。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主要是受到了梁启超上述认识的启发。他在1944年版的《导言》中说:“本编内容略如梁氏所示四目”。他在1957年的修订版《导言》中也说:这书“谨遵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诚如白寿彝先生所指出的那样:“金毓黻的书,是在梁启超设计的蓝图上写出来的。这书在分期问题上,也大致是按着梁启超所说的办法。梁启超对于分期说得不清楚,金的书在分期的概念上也不显明。梁启超主张史学史要写史官、史家、史学,金的书也就按照这三个部分去写。梁启超推重司马迁和班固,金氏书把司马迁和班固列为专章。梁启超在说史学发展的时候,举出刘知几、郑樵、章学诚,金的书没有把郑樵看得那么重,但还是把刘知几和章学诚列为专章。从全书的结构上看,金毓黻就是在梁启超的蓝图上填写了史书的目录,有时对这些书做了简单介绍和评论。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我说这话并无意贬低金毓黻所做的工作,他所选的书目和解说,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把书目写得那么详细,解说得那么有根据,体现了他治学的功力。我们如果对于他的书能够善于利用,对于研究史学史还是有些帮助的。”(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66页。)作为中国史学史这一专史的创始之作,必有一个由晦而显、由略而详、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的发展过程,这是不难理解的。
此书在撰述方法上受考据之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排比材料为主。关于这一点,金毓黻在1957年为《中国史学史》所写的“重版说明”作了这样的阐述:“本书创稿于1938年,系大学授课讲义,1944年始在重庆出版。当时著者并未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之历史观点,因而缺点甚多。而尤要者,则在只就过去三千年间之若干史家、史籍加以编排叙述,殊不足以说明祖国史学产生发展演变之主流所在。兹以编著新型的中国史学史尚需时日,而本书徵引资料较富,可供教学研究参考之用,爰由作者略事修订、删削,权作参考资料而重版,当为读者所谅许。”作者在撰写此书后的二十年,其间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传播,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著作,其所感受,自是出于真诚。此书对于史学之时代特征、发展阶段、思想成就等均着墨甚少。然而,自此书修订版面世至今(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1962年中华书局重印),我们今天来看待金著《中国史学史》,还是应当肯定它在40—60年代产生的学术影响,肯定它在推动学科创建中的积极作用。
首先,此书在结构上,吸收古今史家论述的成果,力图把史学的源流、义例、发展及趋势撰为一书,虽未尽如人意(尤其是对义例的分析和发展的脉络着笔甚少),但草创之功,殊为不易。如果说作者在初版的《导言》中对“编纂要义”还阐说得不很明确的话,那么在修订版的《导言》中作者则进一步明确地阐述了此书的“编纂义旨”:一是讲史官、史家、史籍的产生及官史、私史之区别;二是讲史学之重点在撰史、论史两个方面;三是讲撰史途径中的两个转折,即“于魏晋南北朝启其机缄,于唐宋以后拓其境界”;四是讲史料在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今天来看,这几点“义旨”的逻辑联系也还是不很明确,但作者显然已经触及史学的成立、史学的主要内容、史学发展中的变化、史学发展与历史文献之关系等问题。
其次,此书在初版时,作者在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认识上并不明确,而在修订版的《导言》中,作者就当时的认识作了说明:“全书结构,括以九章,并为便于叙述,略分古代、汉魏南北朝及唐初及唐宋迄清为三期,权作商榷之资,藉为就正之地 ”。这是修订版《导言》中增加的几句很重要的话。结合此书各章内容来看,第一、第二章,分别讲古代史官、史家与史籍,是第一个时期第三章至第五章讲马、班史学,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私家修史及汉魏以后史官制度,是第二个时期;第六章至第九章,是分别讲唐宋以后官史、私史、刘知几与章学诚之史学,以及清代史家成就,是第三个时期(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初版时的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作者在出版修订版时删去。其实这一章对于了解作者当时对史学趋势的认识,是很重要的)。当然,这个分期还比较笼统,而尤其对于分期的依据少有论述;但对于清代以前之史学“由简趋繁”的大势,朦胧分为三期,已见端倪。这也是作者在撰写此书后二十年所提出的新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分期问题,作者在撰写此书之初,已经有所关注, 并提出了初步的设想。 作者在1938年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中国史学可分六期:一为萌芽期,上古讫汉初,史家以孔子及左丘明为史家之冠,而《尚书》、《春秋》及《左氏传》,又史籍之卓出者也;二为成立期,两汉之世属之,史家以司马迁、班固两家为冠,而史籍则《史记》、《汉书》是也;三为发展期,魏晋南北朝私家修史之风极盛而所成之史亦多,《后汉书》有七家,《晋书》有十八家,十六国、南北朝各有专史,而作者非一人,崔鸿又因以成《十六国春秋》,李延寿因以成《南史》、《北史》,胥汲马、班之流而结灿烂之果者也;四为中衰期,而唐讫清中叶,史由官修,定于一尊,私家修史多以肇祸,故史学最不振;五为复兴期,清中叶讫民国初,导源于唐之刘知几、宋之郑樵,而大成于清之章学诚,吾国至是始有成家之史学,而浙东史学之一派如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亦足以为章学诚之先河;六为革新期,即现代也,西学东渐,史学亦为所震撼,章太炎先生之论史已异于前人,而梁任公更以革新相号召,近有何炳松亦以新史名家,将来之趋势恐呈中西合流之观,此今昔之不同也。以此六期榷论为史,或有一当,第恐不能发挥要义,以尽诵说之能事耳。”(《静晤室日记》第六册,卷九六)。
作者是由于“不能发挥要义”,还是后来感到此说有未妥之处,因而本书的撰述没有采用“六期”说,我们已不得而知。今天看来,“六期”基本上是以史家、史书为标准进行划分,且所谓萌芽、成立、发展、中衰、复兴、革新之名目及其时段划分,皆尚可商榷,但它反映了作者的思想轨迹,对于史学史学科的认识史来说,还是有研究价值的。
再次,此书在初版及修订版的《导言》中提出了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以及关于史官、史家、官史、私史、撰史、论史之区别的见解,还有《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为“中国史学史之滥觞”的见解、“私家成就殊胜于史官”的见解等,虽也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对推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
此书之内容,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这是从整体上说的,如第四、六、七、九各章,从目录上看,几乎全是列举出来的史家、史书名称。从局部来看,作者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独立见解。如第五章论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学,是近代以来的较早的系统论述,而所论“《史通》以扬榷利病为主亦兼阐明义例”,论章学诚“论记注与撰述之分”、“论通史”、“史学之阐明”、“因事命篇为作史之极则”以及关于“刘章二氏之比较”等,都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认识。对有些问题,作者也不苟同旧说,而提出新见,如对元修宋、辽、金三史,就后人“以三史成书太速为病”、“后贤又病《宋史》冗杂、《辽史》简略”等问题,一一予以辨析,读来都能使人有所启发。当然,此书在有些评论上存在的偏颇是很明显的,如评价《文献通考》高于评价《通典》,认为《宋元学案》优于《明儒学案》等,早在40年代已有论者指出所论不妥。又此书在体例上因贯彻作者关于官修之史与私人撰史之不同这一主线,故于内容安排多牵就依傍于此而呈现出首尾零乱、时间重复,“史”的特色未能鲜明地反映出来。凡此,读者均可有自己的认识,唯不必苛求于作者就是了。
总的来说,金毓黻所著《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或这门专史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是有它应有的地位的。
标签:梁启超论文; 中国史学史论文; 金毓黻论文; 史学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日记论文; 东北发展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宋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