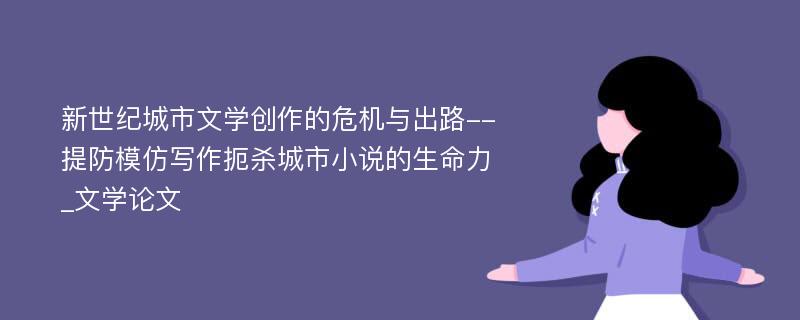
新世纪城市文学创作的危机与出路——警惕山寨化写作窒息都市小说的生命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山寨论文,生命力论文,出路论文,文学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0年代以后,在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强力推动下,都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几乎所有的城市成为无边的工地,在林立的摩天大楼的背后,被遮蔽的是如火如荼的圈地与拆迁运动。借着都市化的东风,城市文学/都市文学也就成了文学新贵。许多研究者将城市/都市文学与现代性挂钩,甚至用“城市/都市现代性”概念来概括其本质特征。笔者在博士论文《准个体时代的写作——20世纪90年代中国小说研究》中专门设有一章,标题为“90年代小说的城市焦虑”,其中特别关注1990年代中国城市文化的复杂性,即时间维度上的新旧杂陈与空间维度上的异质混融。在写作姿态上,有将城市视为欲望渊薮的“背对城市”的写作,有出没于城乡之间的“郊区写作”,还有卷入城市的写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作家和学者以理想化姿态强调城市/都市文学的发展有利于推动理性的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成熟,但是,“打掉牙齿往肚里吞”的虚伪的“平民意识和金钱至上的享乐主义”,似乎正在动摇建立在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基础上的现代市民意识的根基。
在1990年代,当新生代作家与所谓的“70后”作家不约而同地将笔触伸向城市空间,日常化与奇观化成为其审美的两翼。一方面是鸡毛蒜皮,另一方面是动人心魄。在两难之间摇摆的写手们大都缺乏化腐朽为神奇的功力,只好迷失在都市崛起的新大楼、涌现的新名牌、爆发的新富人的万花筒中,在写物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这些作家的作品,不少以酒吧作为存在空间,主人公也多是酒吧DJ或者歌手。在这里,酒吧不再是简单的背景而是一种显豁的主题,甚至如一些批评所言:成了表现“90年代中国的最好的舞台”。当酒吧成为都市精神的某种象征时,纷繁复杂的城市就被压缩和肢解成了一种干瘪、苍白、浮泛的碎片。这种抛弃历史重负抓住当下瞬间的时尚化情感,已经成了疲惫的都市大众借以填充精神空虚的另一种麦当劳。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媒体格局的变化,城市题材小说的类型化倾向日益明显。起点中文网就按照类型设置了“玄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言情”、“历史军事”、“游戏竞技”、“科幻灵异”、“同人漫画”等板块,晋江文学城的“原创言情站”包含“都市言情”、“青春言情”等板块。慕容雪村的《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以类似于黑幕小说的写法呈现都市挤压下人性的黑暗与欲望的贪婪,而这篇文字之所以能够成为天涯社区的文学标牌,与文字中渲染情色的写法密切相关。现在不少研究者提到这部作品时,指涉的往往是经过大幅度删节的纸质本。从安妮宝贝到顾漫、匪我思存、辛夷坞、人间小可等成名于网络的写手,在网上都有大批忠实追随的粉丝。值得注意的是,网上流行的都市言情类小说多有“小白文”的特征。所谓“小白文”,是网友对那些轻松诙谐、言语直白、拒绝深度的类型化小说的指称,这种文字之所以受追捧,关键是读者读起来不费脑筋。其粗糙与温馨使写作和阅读都没有语言和文体的门槛。“小白文”之所以风行无阻,关键在于网络类型文学读者的阅读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读者都习惯于接受通俗易懂的文字,阅读与欣赏水平高的网上读者所占比率极低。有趣的是,网友对都市言情类作品的划分非常细致,譬如有“种马文”、“女尊文”、“后妈文”等说法,种马文是指男主角见谁爱谁、财色通吃的都市小说;“女尊文”的主旨是男卑女尊、一女多男,甚至让男人生孩子;而“后妈文”则指那些有虐待/受虐情节的文字。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文字都非常直白地道出了都市男女在现实中饱受压抑而难以达成的隐秘欲望,正因为如此,“种马文”、“女尊文”的作者和读者都有非常明晰的性别标签,食色男女在此形成了泾渭分明的性别对垒。
总体而言,在都市言情类作品的作者和读者中,女性占据明显的优势。美国文学中的chick literature可直译为“时尚女孩小说”,但在台湾会被翻译成都会小说,这种小说特指那些女性写并写女性的作品,其核心内容是女性的“时尚血拼”以及如何摆设俘虏男人的玫瑰陷阱,其主流趣味是幽默、轻松,有时会在这些文字垒成蛋糕上加上一颗红樱桃——浪漫的点缀。写有超级畅销书Milkrun的Sarah Mlynowski和都会小说编辑Farrin Jacobs有这样的界定:“那么到底什么是都会小说?它是描写现代女性在工作、友情、家庭或恋爱间的日日挣扎;是关于女性的成长、在‘我是谁’和‘需要与欲望’间的探究;是观察人生,寻找在种种境遇、改变和不同个体上的幽默;是有关成年人(不论年龄为何,从八岁的豆蔻少女到中年妇女皆可成为都会小说的主角);是女人为了女人而写;是诚恳而忠实地反映现代女性的希望与梦想、苦难与磨练;是非常畅销、带点趣味,又鼓舞人心的小说。”[1]这类作品在美国常被改编成以家庭妇女为目标受众的肥皂剧。国内张欣、王海鸰的婚恋题材作品与美国的这类作品可谓异曲同工。不可忽略的是,强大的电视传播为国内的都会小说插上了强大的翅膀。六六的《双面胶》、《蜗居》的写作方式也没有跳出这种类型的窠臼。最近几年在国内青春文学市场上被炒得无比红火的小妮子、可爱淘、明晓溪走的“女孩子”路线,似乎更为贴近美国“时尚女孩小说”的内涵。
从《上海文学》和《佛山文学》在1990年代中期联袂推出“新市民小说联展”,《花溪》、《南风》等在新世纪初改版为女性时尚小说杂志,到《最小说》、《鲤》等青春文学杂志遍地开花,这些期刊都聚焦于都市青年男女的时尚变化与情感波动,期刊在与网络、影视等媒介形式的跨媒介互动过程中,都市题材小说的类型化趋向日益明显。不同类型有不同的写作套路,还有针对性明确的目标受众,譬如《花溪》的目标读者就是“中学女生”。都市小说向类型化的都市电影、都市剧的叙事套路的靠拢,其图像化逻辑正在不断地削弱文字的表现力。电视连续剧《蜗居》的盛况空前犹在眼前,根据匪我思存的文字改编的《佳期如梦》和《来不及说我爱你》也在2010年高居收视率排行榜的前列。“白领女性的职场攻略”加“追男秘诀”的《杜拉拉升职记》更是全媒体通吃,同名的图书、电影、电视赚得盆满钵满。但也正因为其迎合受众趣味、过度商业化的策略,其作品多有过度雷同化的硬伤,在网络常年灌水的积弊以及对影像叙事方式的屈从,这类作品的文字不仅难有文采,甚至文句不通,错字连篇,通篇都是人物对白的堆砌。
类型化的都市小说正是苏霍姆林斯基曾说的“一看就懂的东西”,是不值得重读的,在这类产品包围之中的读者养成了“走马观花”和“不求甚解”的习惯,满足于“看”而忽略了“思”。这类作品的生产与消费遵循的是快感逻辑,以唤起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感官与心理刺激为目的,这种审美体验是“由感官感受直接产生愉快的生活快感”[2]。李泽厚在《美学四讲》一书中对美感的审美形态划分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志悦神”等三个层次,而浅出版的审美目标也基本定位于“悦耳悦目”的功利性感官愉悦,无法上升到走向内在性灵的情感洗涤,更无法进入超越感性和个体的思想性、社会性的美感。
类型化的都市小说创作模式是模拟写作或曰山寨化写作。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汉魏六朝作家并不讳言自己的写作模拟了其他作家的创作,而且惯常在标题与序言中确认模拟了何人何作。譬如模拟屈原《离骚》骚体赋有贾谊的《吊屈原赋》、班固的《幽通赋》和杨雄的《反离骚》等,司马相如、蔡邕、曹植、陈琳、王粲、阮籍等都模仿了宋玉《讽赋》和《登徒子好色赋》,绵延成一个以止欲为核心主题的美人赋系列。有趣的是,这些自成一家的模拟者反复强化原作的开创意义,在自己的创作中对原作的审美功能、文体形式进行小幅度的修正与补充,在较小的自由空间中融入自己的创意与个性,使原作在历史的演进中被确立为具有经典意义的审美范式。形成有趣对照的是,时下的模拟写作常常刻意掩饰原作痕迹,譬如郭敬明写上海的《小时代》,将各种元素拼接在一起,总给人在大街上不断遇到熟人的感觉。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时下的文学市场畅销的正是布迪厄所说的一个个“有名的、得到承认的名字”,至于作品写得如何,已经少有人深究。
越来越多的都市小说习惯于在作品中罗列时装的品牌、地标性建筑、流行音乐,其写作遵循时装逻辑,时兴与否成为其能否取得市场成功的关键。正因为如此,都市小说写作相互模仿,缺乏原创性。其传播与接受也就呈现出迅速蹿红又迅速衰落的波浪式轨迹,一种写法一旦得势就有大量的仿作涌现,这种铺天盖地的蔓延迅即引发读者的餍足心理,在退潮之后只在沙滩上留下满地狼藉。吊诡的是,与时尚流行的逻辑相同,都市小说的写作套路就像过气的旧时装一样,在添加一些新元素后,过几年又可能再度走红。在这种循环的怪圈中,类型化的都市小说也就在封闭的定式中内生出一种强大的惯性。对于真正抱有文学理想的写作者而言,不断抵抗这种惯性是其突破瓶颈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