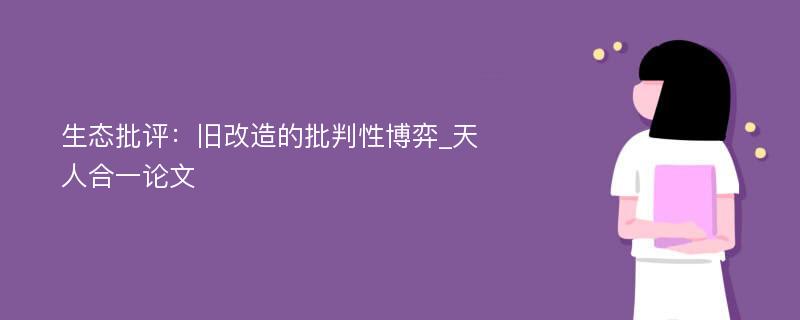
生态批评:一种以旧翻新的批评游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生态论文,游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有时候也被称作“文学与环境研究”(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是二十世纪70年代在欧美兴起的一种文艺批评范式,是当下解构中心、消解权威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后现代批评话语策略。从整体上来看,它当属于当下风头正劲的“文化研究”范畴中的一枝。它与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族群研究等等一道构成“文化研究”的宽阔的批评景观。生态批评近年传入我国以后,一时间在批评界蔚为壮观,吸引了大批研究者和批评者的兴趣。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时涌现。这种批评话语仿佛让当下略显沉闷的文艺批评重又看到了辉煌前景,让当下显得纷乱芜杂的批评话语及思维路线重又得以“敞亮”。因此,很多批评家跃跃欲试,有点抑制不住内心狂喜地想要采摘这束看似“鲜艳欲滴”的批评花朵。
诚然,作为向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起挑战的一种批评范式,“生态批评”固然有其他批评方法不可替代之处。但是,将“生态批评”看作是具有开创性的批评理论,或者把它抬高到原生状的一种文艺批评元理论,当作当前甚至未来文学批评的主导方向,却又未免夸大其辞。因为,在我们看来,生态批评从理论基础到具体的操作方法,都看不出有许多理论的原创性,相反却有着许多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一
生态批评是在地球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精神生态出现重重危机的情况下,伴随西方后现代主义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文化批判思潮。其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先期的生态批评与当时汹涌整个世界的生态运动密切相关,提倡保护纯粹的自然生态,主张人与自然成为友好睦邻。但随着生态批评的不断发展,理论的不断深化,生态批评理论家们近来也注意到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于是将对自然生态的关注逐渐转向社会生态平衡的关注,认为社会生态平衡也应纳入生态批评的视野中去,因为它同样是维系自然与人类健康发展、维系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因此,新近的生态批评要求用一种自然和社会生态平衡整一的视角来思考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关系,审视人类的一切活动,反对将人和自然置于相对立的两极,而主张将人类的全部活动置于维系生态的整体平衡之中。
将生态批评理论用之于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几种鲜明的倾向:一是直接的对所谓的“生态写作”进行文本分析;一是对经典作品中的“自然”的描写进行重新审视,检验“自然”在这些经典作品中作为背景或象征的意义。
其实,有关自然和社会生态平衡整一的观点,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是个一以贯之的焦点问题。从西方思想史来看,希腊哲学最初就在混沌、不确定的原始物质里寻找万物的本原,泰勒斯和他的学生坚持以水、气、火等没有确定性的物质实体作为“始基”。这些人类思想的最初形态说明,在人类世界观形成之初,世界与人的关系并没有形成绝对对立的局面,相反却肯定了人与世界由某些物质共同构成的状态。但以后工商业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思维的明显分化,从而改变了最初世界和人类一体的看法。它典型地表现在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形式主义,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柏拉图的理念论,都要从现实事物背后寻找一种普遍而绝对的尺度,来揭示世界的普遍规律,从而形成西方文化对超念世界的追求。普罗泰哥拉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苏格拉底提示人们:认识你自己。这样,通过超验世界的追逐,西方文化以人类为中心的参照系得以形成。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由于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需要,强调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突出人的中心地位,将人的地位置于所有存在物之上。而唯理主义的过度膨胀,将人的认识作用强调到极致,“我思故我在”,用思维来求证存在,把与人相伴的自然生态撇于一边不加计较,从而形成了人类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观念。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就是在这么一种前提下,自然与人类对立与统一的矛盾一直是西方思想界激烈交锋的焦点之所在。
生态整体观古已有之,古希腊“万物是一”、“存在的东西整个连续不断”等可谓生态整体主义的最早发端。而亚里斯多德的“有机统一论”可以说是较早体现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完整论述。亚里斯多德提出,人类与自然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是由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当各个组成成分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时,事物就出现新的变化。正象生物的发育成长一样,人类与世界也是相互依存的。只有维护生物的有机统一和生命平衡,物种才得以延续、繁衍生息下去。同样道理,人类也只有与自然保持平衡,才是世界的有机统一,才是世界的整一体现。不然,人类与自然就会失衡变态,直至消亡。
难能可贵的是,亚里斯多德将他的这种前瞻性的世界观演化成他的一种美学观,直接在《诗学》中将“整一”观用之于对“悲剧”理论的分析实践,亚里斯多德将“悲剧”定义为“一个严肃、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并从“整一律”出发,规定了“悲剧”的“完整”性,即“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2]对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的理解,以往我们大多偏向于对情节结构紧凑、合乎逻辑的性格演化等等方面,其实,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是与其“有机整体”观念密切相关的。他更注重戏剧的平衡性、整一性以及和谐性,也就是说,在悲剧创作和欣赏过程中,应将悲剧看作是一个像有机体一般的、浑然天成的整体,不能进行人为的切割划分;不能将创作(欣赏)主体的意志强加于其上,从而造成任何程度的断裂。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亚里斯多德可以说是欧洲最早具有生态平衡观念的文艺理论家,他最早注意到了文学中有机整体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亚里斯多德的“有机整体论”具有一定的辩证法因素,在欧洲哲学和文学批评史上影响极大,在一定的程度上奠定了欧洲对立统一思维的整体倾向。因此,可以这样说,今天的“生态批评”中的生态整体主义“整体”观念,反人类中心观念,实质上是在亚里斯多德有机统一哲学思想基础上的发展和深化。
二
无独有偶,中国古代的“道”、“齐物论”和“天人合一”等观念可以说是上述这种生态整体主义的一种东方式表达模式。老子从“道”出发,讲“天”、“人”及其关系,正是试图探讨自然规律与人事规律的关系。“道”在老子的表述中,是作为宇宙本体而存在的,是自然总体的概念,是天地万物最普遍最本质的联系。老子认为,道无私、无争、无求,即“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3],老子还认为“大道周行而不殆”。整个自然界有秩序、有规律、有条理地运动变化着。自然秩序是按照不争、不有、不主、不私、不长、自均、无为、平等的原则而运行的,这是宇宙运动的根本规律。只有以自然秩序为社会秩序的准则,才能达到自然和社会的平衡整一。老子之“道”,虽然带有一定的神秘论色彩,但实际上却孕含着丰富“天、地、人”合而为一、混为一体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他不仅把宇宙看作是一个混然生成的整体,更将人类社会也纳入其中作整体思考。而且在具体地论述人与自然关系中,还提出了人的“清静无为”思想。这样,老子就具有预见性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调和在其“道”的整一观之中。在老子那里,人类与其说介入自然宇宙之中,不如说消融于自然宇宙之中,化于自然宇宙之中。这为后来中国传统思想中核心观念“天人合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从这些方面考察,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占中心地位的论题。换言之,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生态主义从一开始就成为我们思考自然宇宙与人类社会问题的一种带根本性的立场。
庄子除承继了老子的生态整体观念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了宇宙事物平等整一,没有哪一种东西是占绝对优势的,能够统率其他事物的,超越于其他事物之上的。这就是著名的“齐物论”。一般认为,“齐物论”包含齐物与齐论两个意思。刘琨《答卢湛书》说:“远慕老庄之‘齐物’。”《文心雕龙·论说》也有:“庄周‘齐物’,以论为名。”这是倾向于前者。王夫之则相反,在其《庄子解》中,他说:“当时之为论者多矣,而尤盛者儒墨也:相竟于是非而不相下,唯知有己,而立彼以为耦,疲役而不知归。其始也,要以言道,亦莫非道也。其既也,论兴而气激,激于气以引其知,泛滥而不止,则勿论其当于道与否,而要为物论。物论者,形开而接物以相构者也,弗能齐也。使以道齐之,则又入其中而与相刃。唯任其不齐,而听其自已;知其所自兴,知其所自息,皆假生人之气相吹而巧为变;则见其不足与辨,而包含于未始有之中,以听化声之风济而反于虚,则无不齐矣。”[4]其实,依我看来,从庄子全书来看,“齐物我”应更切合庄子整体思想。“齐物我”亦即“无心”,也就是心与物化,就是消除了物我之间的根本对立,而将二者消融为一,有机结合成一个浑然天成的境界。其最高典范庄周化蝶,就是这种心与物化的一个杰出案例。
无论对庄子的文本作出如何解读,但庄子的整一观自始至终都是非常明显的。他不承认世界万物其孰长孰短,也不相信万物之间孰优孰劣。他始终坚信万物都是平等整一的,因为,在庄子看来,万物无论它有何不同,但不同背后隐藏着更多的同一,即无论事物如何变化,最终都是运动变化为一。这个“一”即是“无”。自然事物是这样,社会事物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庄子在这个基本立论上,进一步讨论的是“齐论”的问题。庄子认为人们的各种看法和观点,看起来也是千差万别的,但世间万物既是齐一的,言论和辩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再说,因为对一个“论”的持“论”正确与否谁也无从确定标准,又怎么能判别“论”之高下呢?因此,就“论”而言,世界也是平一的。
庄子的这种“齐物论”固然有“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思想因素,其立论也是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待世事万物,但无庸置疑的是,正是这种具有一定消极因素的理论本身却同时又包含着朴素的整一观念。这种整一观念,将世界万物置于同一水平,一方面表现了老庄以“清静无为”为“道”之核心的“静虚”处世思想,一方面又彰显了世界的整一性精神,使得人与自然关系得到了终极性的解释。
“天人合一”思想更是完整呈现了中国古代思想精英们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整体平衡主义的理念。它将古代中国社会的自然观、社会观和艺术观有机地结合于一体,构成一种浑融推衍的整体世界信仰。“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古代理性最基本性的表述,也是最具根本性的实现。“天”笼统地表达着古代中国的自然观,其最初来源对人类的经验和观察之解释。观察到的自然之“天”经由解释便经验化与社会化,成为人之“天”或由经验确证的“天”。对此,成中英教授结合中国古代“圣人”观念的考察,总结了“天人合一”中“天”与“人”之间的几个共同之处:“天与人本源为一体,同是生生不已的生命,这是本源的一致;天与人是相互交流而无间隔,因天赖人以成,人赖天以久,天人为创造而实现同一目的,即生命的丰富与充实,这是终点的一致;天与人均以动与创造来发挥其本源,实现其目的。故又在过程上是一致的。”[5]
如果说老庄、易经中的“天人合一”观念还过多地强调天人浑融为一整体,人与天一,更多地强调人对天的依赖性,那么,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则更强调了人与天的相互作用性。首先,儒家不仅特别强调“天人合一”、强调整体性;而且特别强调自然整体内部天、地、人之间各部分的关系,特别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联系。孟子的“亲亲”、“仁民”、“爱物”可以说是这种观念的一种较集中的表达,它把人对世界的关怀分了层次和远近。张载在《西铭》中所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表明了天下百姓皆我同胞兄弟,天下万物皆我同类的观念,主张以仁爱之心善待他人,在关爱他人的同时也关爱生态,关爱自然万物。这种看法可以说是儒家生态整体观念的一个典型呈现。王阳明更是从自然生命的“心性”体验出发,来阐述自身的“万物一体之仁”的“天人”思想。他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惟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6]这样,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缝合了道家“天人合一”中将天人关系单极化的处理,而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得讲求纯粹自然的生态整一变而成为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生态有机整一关系。这种生态整一观念在今天社会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生态也严重失衡的状况下,显得尤有意义。正如英国生态批评家布克钦(Murray Bookchin)所说,当我们今天面临着生态学之外的更大更紧迫的社会危机,即“等级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家长制的和阶级的矛盾加剧和发展”时,“要解决这些社会危机,只有通过依照生态的路线,以生态哲学和生态思想作为指导来重新组织社会的方式才能实现。”[7]因为,正如有学者指出,“人类社会是生态系统的一个最重要的子系统,人类是生物共同体中最有能动性的物种,他既能一手造成当今的生态危机,也能、而且只能依赖他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平衡。”[8]因此,生态整体观应在力求确保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的重要性的同时,还要突出强调人类在保护生态系统整体利益方面的不可替代作用。
中国古代的上述观念,尤其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精粹。按季羡林先生的说法,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综合思维方式也是在“天人合一”基础上形成的。[9]“天人合一”观念,说明东方文明中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独特的理解,较早地表现了东方对自然和社会生态的一种极大关怀。作为一种素朴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它不仅看到了自然生态的整一,更重要的是强调了人类在整个自然和社会生态之间起到有机平衡能动作用。因此,它为西方生态批评从纯粹自然生态批评向社会生态批评的转向作出了基本理论铺垫。
三
在十九世纪,马克思经典理论家们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资本生产规律与资本社会规律问题。在他们的时代,人类社会正处于大力发展生产的时期,尚来不及过多地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也远未恶化到今天这样难以容忍的地步。但是,作为人类思想的高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凭着他们对社会实践和理论经验的敏感,在一些著述中已经显露出某些对自然和人类生态的高度关怀,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问题表现出智者莫大的智慧和胸怀。比如,马克思就曾经非常直接地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人甚至“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0]在这里,马克思将自然生态看作是人的有机躯体,表现出一种对宇宙世界整体把握的睿智。这固然可以看作是亚里斯多德“有机整体论”的整一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完美延伸和深刻阐述,更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始终是以一种生态系统的胸怀来把握的。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将自然和人类视为一个统一体,还注意到了主体与客体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依存关系。所以,马克思又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人还是人的存在物。”因为,“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11]其基本意义在于,它使人们看到,人不仅是自然的产物,而且还对自然起着一定的能动作用。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就显得特别,人既是自然的主宰,同时又与自然是相依存的,他既有开发利用自然的权力和力量,更有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持生态整一的责任。
特别让人敬佩的是,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马克思更进一步考察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开发利用以及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自然生态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当时尚处于或然性破坏阶段,而马克思却敏锐地认识到开发自然的物质技术和生产工艺在实际过程中的反自然性。固然,马克思考察的重点是资本主义城市化、集中化生产特征及其本质,但他始终把这种反自然性当作一个关注的焦点。面对因扩大化再生产而不断集中的城市人口,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2]”从一次次人口的迁徙,马克思却看到了长远的土地生态之破坏力。从这个案例可见,马克思对人类生态整体平衡的洞析何其深刻!
面对十九世纪以来的生物进化理论,人们一度表现出极为狂热的欢呼。恩格斯也曾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细胞学说一道视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但是,正是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给取消了。”[13]从恩格斯的整体思想来看,一部《自然辩证法》,与其说是一部考察自然界物质运动变化规律的思辩性哲学著作,不如说更是一部警示人们把握并遵守自然规律的劝诫书。
因此,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笔下,生态问题虽然还不是他们所讨论和批判的主要问题,但是他们的思想又处处体现了人类生态整体观念和深刻的生态危机意识,体现了作为极具前瞻性的伟大思想家的博大胸怀。因此,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这些生态观,对于当代生态批评从理论到实践都起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1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当下批评界风头正健的所谓“生态批评”,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从基本理论到方法论,它都不过是一种早已有之的思想的翻版。它是亚里斯多德有机整一理论的当代发掘,也是古老东方“天人合一”的晚来发现,更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移植。当然,生态批评还包含有其他的思想资源,比如说胡塞尔、海德格尔的某些带有东方色彩的直观认识论思维思想等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这一理论。诚然,任何一种理论之间都有“互文性”和“文本间性”,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概莫能外。在某种程度上说,理论之间的“文本间性”甚至可以说是新的理论的起点和策源地。也许,生态批评只是西方理论中以旧翻新的一种话语策略,或者是一种“新瓶装旧酒”式的粉墨登场。我们想要质疑的不是“生态批评”的学理合法性问题,只是想要说明:对这样一种并非原创性的理论,我们必须保持必要的学术警觉,保持批评自身的“生态整一”,以免出现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尴尬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