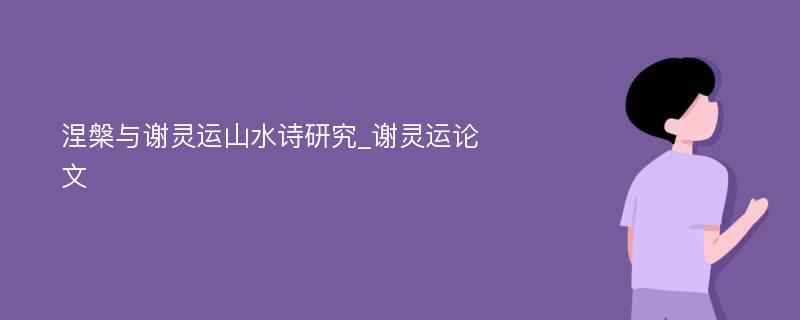
大乘涅槃学与谢灵运的山水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乘论文,谢灵运论文,山水诗论文,涅槃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4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2000)04—0018—08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刘勰的这句话是说,两晋文学经过谢混、殷仲文的改革后,至宋元嘉,以“寄言上德(老),托意玄珠(庄)”,“诗必柱下(老)之旨归,赋乃漆园(庄)之义疏”[1](《文心雕龙·时序》)的宣扬道家思想的玄言诗终于退出了主宰东晋文坛的历史舞台,代之而兴起的是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由玄言诗中的“庄老告退”转变到谢灵运等山水诗的“方滋”,标志着诗歌“从哲思又逐渐回归到感情上来,以情思取代玄理”。[2](P175)那么, 谢灵运的山水诗是否真的摆脱了“哲思”呢?谢灵运的山水诗不但没有摆脱“哲思”,而且还深化了“哲思”。只是这“哲思”不再是道家的“玄理”,而换成了佛教的哲思。因此,谢灵运的山水诗,表现的佛教哲思不再是藉诗歌的外在形式直接以哲学语言来阐明,而是以一种审美的情思来表现或抒发佛理。这就把山水审美与佛教哲思有机地融为一体,使人在山水审美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受和体悟佛理。在谢灵运的时代,佛教已摆脱了依附玄学的从属地位而升居到了主流文化的位置,佛教的各种思想、流派竞相涌现,如禅数学、毗昙学、成实学、般若学、涅槃学、净土思想、四论学等。那么,谢灵运接受最多的是哪一学派的思想呢?这是前人和今人都未曾深究的,本文拟就此作一些探讨。
一
作为刘宋元嘉时期“山水方滋”的代表人物谢灵运,不仅是诗人、文学家,而且还是著名的佛学家。因此,他在接受佛教哲学思想时,首先注重的是在义理方面。在谢灵运的时代,风行东晋时期的大乘般若学已经过了顶峰期。般若学说基本上是宇宙本体论的变种,不管它的花样如何翻新,仍然摆脱不了空有不二、体用动静相即,总是在概念、术语、范畴上兜圈子,给人抽象、空洞、玄远、不可明了的说教感,它在解决现实社会人生的问题方面,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而佛教哲学的本质和最终目的,则是要说明和解决现实人生能否摆脱烦恼,从苦海中脱离出来而成佛以及现实人生是否具有成佛的内在根据等问题。当般若学在东晋红极一时的时候,从天竺传入了一股新的佛学思潮——大乘涅槃佛性学说。这股思潮来势凶猛,迅速席卷南北、朝野、僧俗,至晋末宋初,已完全取代了般若学在哲学思想界的主流地位。“佛教理论的重心在中国由魏晋时兴盛的般若学的本体论转向了涅槃学的心性论。这一次探寻人之佛性已远远高于早期印度佛教所揭示人生之苦难的阶段,它是要揭示人是否具有成佛的内在根据的真实问题。”[3]任继愈说:“南北朝到隋唐,继魏晋玄学之后,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由本体论进入心性论,佛性论由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支流上升为主流,从而把中国哲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4]佛性论成为哲学上的主流,自然就是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之主流。在涅槃佛性学说这股汹涌澎湃的主流中,晋宋之际的许多文人被席卷了进去,而谢灵运并不像一般文人那样只是随波逐流者,而是一位起着关键作用的弄潮者。
涅槃(Nirvāna),也译泥日、泥洹等,意译灭、灭度、寂灭、解脱、圆寂等。原意为火的熄灭或风的吹散的状态。佛教用以作为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境界。小乘一般以“灰身灭智,捐形绝虑”为涅槃。大乘空宗以“诸法实相即是涅槃。”[5](《中论·观法品》)有宗则把涅槃说成具“常、乐、我、净”四德的永生常乐之佛身,以众生皆有佛性为涅槃之根据。大乘涅槃学即是以有宗的佛性学说为核心。佛性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伴随着《涅槃经》的翻译而深入的。东晋隆安三年(399),著名高僧法显,西行天竺留学求法, 前后达15年,所到29国,独自返回中土,携回大量佛典,其中包括《泥洹经》[6](《高僧传》卷3《释法显传》)。是经于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十月,由天竺禅师佛陀跋陀罗(Buddhabhadra)与宝云译出,共6卷。 该经首先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主张。 所谓“佛性”(Buddhatā,Buddhatvā),原指佛陀之本性。 小乘不认为众生可以成佛;而大乘则以成佛为目的,故认为众生也有佛陀之本性,后来“佛性”发展成为众生成佛的内在的根据。《泥洹经》译后记云:“愿令此经流布晋土,一切众生悉成平等如来法身。”[7](《出三藏记集》卷8《六卷泥洹经记》)因而,大力宣扬佛性论。(注:赖永海博士认为,“中土的佛性思想,如果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最早者当算慧远的‘法性论’。”(赖永海《中国佛性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愚以为,慧远的“法性”虽与“佛性”为异名同义,但它主要讲的是人的灵魂可以超越形体而独立存在,即形尽神不灭,属于佛教的轮回学说中的“神我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佛性论。与《涅槃经》所倡导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及众生皆得成佛的佛性论有很大的不同,似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泥洹经》的译出和佛性论思想的介绍,在中国的宗教和思想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佛性论成为人们谈论一时的主要话题。在这股佛性论的热潮中,理论建树最大、影响最广的是竺道生。
道生“入庐山,幽栖七年”。鸠摩罗什到长安后,他“与慧睿、慧严同游长安,从什公受业”,学习大乘般若中观学说, 义熙五年(409)南返建业。道生的佛性论思想,据《高僧传》卷7载:
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言:“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报,顿悟成佛。又著《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等。笼罩旧说,妙有渊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与夺之声,纷然竞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师,生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阿阐提(即一阐提)人皆得成佛。于时大本未传,孤明先发,独见忤众。于是旧学以为邪说,讥愤滋甚,遂显大众,摈而遣之。[6]根据这段记述,道生的佛性论思想主要有两点:1.顿悟成佛说;2.“一阐提”人皆得成佛。前者是在六卷本《泥洹经》翻译之前在大量研习佛典的基础上形成的。它认为“理不可分,悟语照极”[8](慧达《肇论疏》),即所悟佛理是完整而不可分隔的,觉悟也不可分出阶段,而是一次性的完成,悟此佛理即“反迷归极”。这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提法,有力地动摇了传统佛学的渐悟说,因而不被当时佛教界所接受,遭到了“守文之徒”的嫉妒和怀疑。后者是在《大般涅槃经》译出之前提出的。六卷本《泥洹经》虽提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又认为“一阐提”(Icchantika,指断绝一切善根的人)没有佛性,不能成佛。而道生却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这就违背了《泥洹经》的经意,因而其时佛界斥其为“邪说”。据唐道暹《涅槃经玄义文句》卷下载,当时于阗沙门智胜宣讲六卷本《泥洹经》的“说一阐提定不成佛”时,众高僧“盛宗此义”。当他们闻知道生的说法,义愤填膺。智胜数次与道生辩论,均不敌对手而败北。尽管道生在理论思想上比“守文之徒”们更具有新意,也更适应了现实社会的需求,但他在佛教界保守势力的围攻下,毕竟显得势单力弱,无奈,被逐出建康,居虎丘。元嘉七年(430)又被迫躲藏于庐山。
在道生极度危难的时候,他的好友谢灵运公开站出来声援道生,写下了著名的文章《与诸道人辨宗论》[9](《广弘明集》卷18), 与法勖、僧维、慧驎、法纲、慧琳等名僧及名士王弘等进行论辩,对道生的顿悟成佛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谢灵运的“宗”即是成佛之理或作圣之理。中国传统思想一般认为圣人是不可通过学习而企及的;而传统佛是则认为佛是可以通过修行(渐进)而达到的。谢灵运认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综合二家又超越其上。他在《辩宗论》里用般若空宗的层层否定或超越的方法(“傍权以为检,故三乘咸蹄筌;既意以归宗,故般若为鱼兔”)(注:道生的涅槃佛性学说,是在总结般若学的基础上以空出有的。《大般涅槃经》说:“从般若波罗蜜出大涅槃”,即是道生之根据。谢灵运亦如此。),来探讨佛性论。他说:“物有佛性,其道有归。”[9](《辩宗论·答琳公难》)不仅认为“有情”(Sattva)众生(人和有情识的生物)皆有佛性,就连“无情”(Ansattva)的物(草木、山河、大地、土石等)也有佛性,而且他们都有其道而归于佛理。这就把般若学统摄于佛性论之中,把宇宙本体与佛性主体相统一,彻底地贯彻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佛性论。由是看来,谢灵运与道生一样,其佛性论均突出一个“理”字。与谢灵运辩论的王弘,将他与谢灵运的问答书信转送给了道生。道生对谢灵运的声援非常感激,他说:“究寻谢永嘉论,都无间然。有同似若妙善,不能不以为欣。”[9](《广弘明集·竺道生答王卫军书》)道生在感激之外,又对谢灵运的答辩深表赞同和肯定。
二
谢灵运既然在宗教哲学上是以佛性论作为主要思想的,那么,他在其他的文化活动中也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贯彻和体现这个主导思想。他的山水诗则是涅槃佛性论在文学审美活动中最为集中的体现者。前人在论及谢灵运的山水诗时,都指出“理”乃是其基本特征。如黄子云《野鸿诗的》谓:“舒情缀景,畅达理旨。”沈德潜《古诗源》卷10谓:“山水闲适,时遇理趣。”王夫之《古诗评选》卷5谓:“理关致极, 言之曲到。”谢诗的确十分好用“理”字:
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入彭蠡湖口》)
投沙理既迫,如昂愿亦愆。(《还旧园作见范二中书》)
沈冥岂别理,守道自不携。(《登石门最高顶》)[10]除此之外,据粗略统计,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还有八处。从这些“理”来看,显然与《辩宗论》中所说的“理”是一致的,它主要是指涅槃佛性之理。这是他的佛性论思想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如果说此“理”还兼杂有其他思想的话,那也是统摄于他的佛性论之中的。谢灵运的佛性论思想竭力要突出的就是这个“理”:如他在《辩宗论》中说:“理在情先”[9](《答僧维问》);“其理既当,颇获于心”[9](《答慧琳难》);“理妙者吝可洗”,“一悟理,质以经诰,可谓俗文之谈”,“词微理析,莫不精究”[9](《答王卫军问》)。 从思想渊源来看,谢灵运的这个“理”,即来自于道生的涅槃佛性论。而道生的“理”,则又是从对《大般涅槃经》、《维摩诘经》和《法华经》的注解中总结出来的。道生认为,理即是佛、当理为佛、理为佛因。他在《注维摩诘经》中说:“从理故成佛果,理为佛因也”,“佛为悟理之体”,“佛以穷理为主”,“穷理尽性”,“既入其理,即为彼岸”,“如来身从实理中来”[11];“观理得性”[11]。在《大般涅槃经集解》中说:“当理者是佛,乖则凡夫”;“以佛所说,为证真实之理,本不变也”;“善性者,理妙为善,反本为性”;“法者,理实之名也”[12]。在《妙法莲华经疏》中说:“如来理圆无缺,道无不在”[13]。从道生的这些注释中,可以归纳出他的“理”的特点:1.理即是佛、理为佛因、当理为佛。道生认为“理”既是非有非无、又即有即无的中道之理体,又是佛教之真理;既是佛陀之本性,又是成佛之根源。无所不在的佛教之真理无不从中道理体体现,因此,悟理也就是悟佛,当理也即为佛。2.理即是法。法即是法性,“然则法与法性理一而名异”[11](《注维摩诘经》卷2)。法性即佛性, 故理亦即佛性。由此来看,谢灵运的“理”虽没有道生的“理”如此细致,但二者的意义是一致的。因此,谢灵运的“理”亦是佛性之体现,当此理即当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谢灵运才特别强调说:“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14](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于此,我们即可明了谢灵运强调的“理”,其着眼点乃在于“求性灵真奥”。谢灵运说:“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15](《全宋文·游名山志》卷33)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的出发点是通过山水物质的存在形式,来探讨和发掘人生之精神真谛。此所谓“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10](《登江中孤屿》)是也。因此,后人评谢诗,多着眼于其“真情”:所谓“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16](皎然《诗式》)
三
俄国宗教美学家E.Γ.雅科伏列夫在谈到艺术与宗教的关系时指出:“艺术和宗教相互作用的这个历史过程导致的结果是,世界宗教几乎把所有的艺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艺术——都纳入自己的结构中。但是,这个过程也产生出致命的后果:由于各种艺术对宗教意识的多方面的影响,宗教意识的樊篱已被拆除,宗教开始丧失自己独特的幻想内容。与此同时,形成了一个与传统宗教思维相距甚远的、新的美学和艺术的环境。”[17](P4)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文学与佛教的关系是这段话的有力例证。当谢灵运同时面对和走向山水文学和佛教时,他的审美观和文学创作实践即被纳入到了他的佛教意识的结构之中。在代表佛性的“理”与代表审美的“情”的关系上,谢灵运的看法与道生的也颇为一致。
情不从理谓之垢也,若得见理,垢情必尽。[11](道生《注维摩诘经》卷2)
理感心情恸,定非识所将。[10](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
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10](谢灵运《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
理在情先。[9](谢灵运《辩宗论·答僧维问》)二者皆把“理”看作是“情”的先导、主宰,“情”只有服从于“理”,才能得其所,反之,即是污垢;诗人如果是“见理”、“理感”、“理来”了,那么“情”即可“尽去”、“无存”。这就是说,诗人的审美情思不是没有目的或随意飘动的,而是要纳入其佛性论思想的范围。道生是出家僧侣,他是完全站在佛性论的立场上来看待“理”和“情”的关系,而谢灵运虽然也是佛教信徒,但他更主要的还是一个诗人和文学家,然而在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上,他的艺术观却跳不出宗教意识的大网。
正是在这种宗教意识结构的作用下,谢灵运的山水诗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记游——写景——兴情——悟理。如《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朝旦发阳崖,景落憩阴峰。舍舟眺回渚,停策倚茂松。侧径既窈窕,环洲亦玲珑。俯视乔木杪,仰聆大壑淙。石横水分流,林密蹊绝踪。解作竟何感,升长皆丰容。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10]这种模式不光表现在谢灵运一人的山水诗作之中,同样还表现在谢灵运族弟谢惠连的诗赋中。
日落泛澄瀛,星罗游轻桡。憩榭面曲泛,临流对回潮。辍策共骈筵,并坐相招要。哀鸿鸣沙渚,悲猿响山椒。亭亭映江月,浏浏出谷飚。斐斐气幕岫,泫泫露盈条。近瞩祛幽蕴,远视荡喧嚣。悟言不能知,从夕至清朝。[10](《泛湖归出楼中望月》)前面所写的山水之景,最后都要归结到“悟言不能知”的“理”上。又如谢惠连的《雪赋》在描绘瑞雪初降后,归入到了“理趣”:“节岂我名,洁岂我贞?凭云升降,从风飘零。值物赋象,任地班形。素因遇立,污随染成。纵心皓然,何虑何营。”[15]不管是随遇任化,还是素而变污,其性灵永远保持着高洁。作者通过赞美“雪”而获得心灵上的解脱。大小谢的这种模式是宗教规范和艺术规范的结合体。它虽然给人以一种桎梏的感觉,但在宗教艺术思维结构里,却有着重要的意义。这种模式不仅维护着文人们的一般生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在不停地、随时随地地调节并组织文人的宗教和艺术生活的精神结构,尤其是文人的心态变化,使他们保持着相对完整性和稳定性。因此,这种宗教与艺术混合体的规范虽“不能绝对地决定艺术思维的特性,只是在一定历史范围里它才能在一定的内容——形式层次上去构成艺术整体的稳固性”,但它“更加强调出在其框框范围里进行创作的艺术家的才能和特色,因为要想在规范的狭窄框框里创造一部有影响力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就应具备巨大的创造潜力,具备克服教规的能力。”[17](P100)谢灵运的山水文学创作就是在佛教规范的框框内进行的,但他的创作却能在这个规范前进得来,出得去,因而他的山水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一般的模山范水、一般的赏心悦目,而是一种十分富有个性化的哲学思考,如“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10](《述祖德》),“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10](《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研精静虑,贞观厥美”[15](《山居赋》)。这不是一般的山水审美观照,而是一种以特定对象为视点,在佛教“般若智慧”指导下的思维观察活动,即佛教中“止观”的“观”(Vipasyanā)。故其深刻性和完整性始终是同时代人和后继者所竭力赞赏、咏叹和深思的。而没有这种宗教规范的体验,是不可能复制和再现其山水文学的。这也就是谢灵运在宗教思维的范式里又创造出与宗教思维相距甚远的、新的美学和艺术的环境和境界。
四
这种宗教与审美的巧妙结合,一方面使人把自己融化在宗教意识的神学体系中,另一方面又让人向着拯救个性探索方向发展下去,就是说,人在宗教意识里不再表现为个体和个性,而是超越一切单个人的观念去寻求人类共同的存在本质。谢灵运的山水文学创作就体现了这个特点:它们更加关注着超越个体和个性,把佛教的心性论与人生之哀乐的咏叹联系于一起,探索着人生的更为深层的东西。
欢去易惨,悲至难铄。击节当歌,对酒当酌。……善哉达士,滔滔处乐。(《善哉行》)
短生旅长世,恒觉白日欹。览镜睨颓容,华颜岂久期。苟无回戈术,坐观落崦嵫。(《豫章行》)
空对尺素迁,独视寸阴灭。……桑茅迭生运,语默寄前哲。(《折杨柳行》)
余生不欢娱,何以竟暮归。……所秉自天性,贫富岂相讥。(《君子有所思行》)
心欢赏兮岁易沦,隐玉藏彩畴识真。(《鞠歌行》)
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七里濑》)
得性非外求,自己为谁纂。不怨秋夕长,常苦夏日短。殷勤诉危柱,慷慨命促管。(《道路忆山中》)
殷忧不能寐,苦此夜难颓。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运往无淹物,年逝觉易催。(《岁暮》)[10]在谢灵运的这些诗作中,时间与生命,成为每一意象深层的结构形式。从哲学上来说,时间(time)是永恒的、无限的、必然的,而个体的生命(life)则是短暂的、有限的、偶然的。二者的同时共境,本身即构成了突出的对立与矛盾。然而,就个体的生命来说,其时间与生命存在则是一致的。海德格尔(M.Heidegger)认为,西方的时间观念从亚里士多德到柏格森(H.Bergson)都是处于流俗的时间概念之中,即他们的时间概念所意指的时间乃是空间。他认为,人们习惯于把时间作为存在者状态上的标准,喜欢把“时间性的”存在者(空间关系与数学关系)划分开来,把道出命题的“时间性的”过程同命题的“无时间的”意义区别开来,还喜欢在“时间性的”存在者与“超时间的”永恒者之间划一条“鸿沟”。其实,如果真正从时间来理解存在,“时间性的”就不再可能只等于说“在时间中存在着的”。“非时间的东西”与“超时间的东西”就其存在来看也是“时间性”(temporality)的。因此, 海德格尔主张把时间性与此在(dasein)联系起来,从此在的时间性上探求此在“存在在世界之中”[18](P17)的本质。卡西尔(E.Cassier)认为,此在的人“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过程——一个永不停歇的持续的事件之流。……在它的生命中,时间的三种样态——过去,现在,未来——形成了一个不能被分割成若干个别要素的整体。……我们不能在描述一个有机物的瞬间状态时,不把这个有机物的整个历史考虑进去,不把这种状态与其未来状态相关联。对后者来说,前者只不过是线段的一个点而已。”[19](P63-64)莱布尼茨(G.W.Leibniz )指出:“现在包含着过去,而又充满了未来。”[19](P64)这样,现实此在的人,即不会再为面对线性时间的流逝而哀叹、苦恼,也不会为个体生命的短暂、无常而烦恼,他对这一切就会处之泰然。在谢灵运的诗中,我们感受到有这么一种时间观念:时间是流动着的,春去秋来,时光荏苒,倏烁星流,寸阴飞逝。在这种飞速流动的时间内,具有短暂生命的每一个体都无法控制自己生命的衰竭,“朽貌改鲜色,悴容变柔颜”,“览镜睨颓容,华颜岂久期”,所以,人们总是对时间的易逝和生命的短暂发出强烈的哀叹:“短生旅常世,恒觉白日欹”,“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人们在时间面前显得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故而咏叹、伤感、彷徨、绝望。这是一般人的时间观。而谢灵运的时间与生命观并未到此为止,他不同常人的是,他把时间和生命都看成是流动着的。因此,当他在生命与时间的对立和矛盾面前时,就既不苦闷、消沉,也不浮躁、轻飘,而是以一个豁达、明朗、坦然的心态而处之:“善哉达士,滔滔处乐”,“幸赊道念戚,且取长歌欢”,“苟无回戈术,坐观落崦嵫”,“桑茅迭生运,语默寄前哲”。涅槃并不仅仅就是死亡,它同时包含着新生。因此,短暂、偶然、有限的生命在这种涅槃佛性思想的赋予下也就具有了永恒、必然、无限的意义。这种“击节当歌,对酒当酌”、重生而不畏死的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更增加了现实生命的密度和质量。谢灵运时间观和生命观虽然没有海德格尔、卡西尔等的系统、深刻、思辨,但我们从中也可看出一些超越现实的生命观的气息。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时间和生命观的基础上,谢灵运把人的生命赋予自然界的一切,连自然界中的山水、草木都具有了人的生命、人的气息、人的哀乐。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池上楼》)
泽兰渐被径,芙蓉始发池。(《游南亭》)
白芷竞新苕,绿苹齐初叶。(《等上戍石鼓山》)
荠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袅袅秋风过,萋萋春草返。(《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
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10]
这些形态各殊、异彩纷呈的春草、泽兰、芙蓉、白芷、绿苹、荠荷、蒲稗、初篁、园柳等物色,虽渺小却无不洋溢着生命的光彩,然其形象之背后或深层结构,则无不是佛性之体现。草木如此,自然界的一切物色皆复如此。所以后人无名氏在《静居绪言》中评论道:“有灵运然后有山水,山水之蕴不穷,灵运之诗弥旨。山水之奇,不能自发,而灵运发之。”[20](P448)朱庭珍在《筱园诗话》卷1 中亦说:“即于写山水中,由景生情立意,以求造语合符理境,又由情起一波澜,以求语有风趣,亦非难事。……夫文贵有内心,诗家亦然,而山水诗尤要。盖有内心,则不惟写山水之形胜,并传山水之性情,兼得山水之精神。”[20](P449)这些评论虽未能直接点明谢灵运山水诗与佛性论的关系,但也指出了自然山水乃由人发,发之得其性情、精神的诗理。正是如此,谢灵运才能以玩、赏的心态和审美趣味来对待事物:“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15](《拟魏太子邺中序》);“情用赏为美,事昧竟谁辩”[10](《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妙物莫为赏,芳醑谁与伐”[10](《石门岩上宿》);“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10](《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景夕群物清,对玩咸可喜”[10](《初往新安至桐庐口》);“弄波不辍手,玩景岂停目”[10](《登石门最高顶》)。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读谢灵运诗》中写道:“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岂惟玩景物,亦欲摅心素。”[21](《全唐诗》卷430)白居易十分清楚地指出了谢诗对自然山水的“玩”、“赏”特征。由此可见,谢灵运的山水诗作所探索的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生命意趣,而是已经超越了个体和个性的审美意蕴而包容了宇宙整体生命的生存价值。
海德格尔认为,一件艺术品,必须是大地、天空、神圣者和短暂者四者的统一。大地(earth)指大地上的一切实物,“是承担者, 开花结果,伸展成石头和水,产生了植物和动物”。天空(sky )指一切天文气象,“是太阳的天穹轨道,是月亮变化的道途,有星星漫游闪烁,一年四季更替,有白昼的光明和暮霭,夜晚的黑暗与闪光,有天气的温和与险恶,浮云与湛蓝幽深的太空”。神圣者(divinities),指超自然的神圣的东西,“是神性召唤的信使。”短暂者(mortals )是指世俗的有生死的人,“去死意味着能够作为死亡而死亡。只有人去死,而且是不断地去死,只要人保持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诸神之前”。[22](P135)这四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单一整体。谢灵运的山水诗作,同样具有上述四者的统一存在,诗的意蕴就是在这四者的聚合体中敞开,此在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在这里现身、到时,我与物、人与世界均处于纯然而然的一元境界之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宋元嘉时期之所以能产生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的文学流派,其重要原因乃在于佛教的迅速发展,并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尤其是涅槃佛性学说对谢灵运的深刻影响,它使得谢诗中的物、情、理的融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佛教哲学的渗透。当然,宗教对艺术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限制或阻碍了艺术审美情思的自由抒展,它的范式化的框框,它的过分追求理性化的倾向,都对艺术的发展是不利的。从谢灵运的诗作中,我们也可看到这种副作用,这是我们应当指出的。然而,谢诗中的缺点,也不能全由佛教来承担,这里还有诗歌自身发展的问题,山水诗在宋元嘉时期只是作为一种新的题材体式而刚刚兴起,还未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不可能完美无缺。另外,还与文人自身的素质、才气、胆识、审美感受、语言表达等等诸多因素有关,这里就不再探讨了。
收稿日期:2000—0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