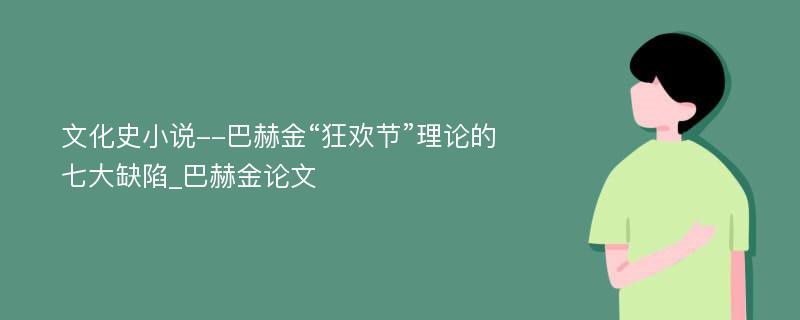
文化史的虚构——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七大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文化史论文,缺失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6)12-0052-09
我对巴赫金狂欢理论的质疑①,得到了夏忠宪教授的回应和批评,她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的创见》一文②(以下简称《创见》)。批评促使我对问题进行更全面、更深入的思考,也激发了我学术研究的热情。《创见》批评我“基本概念把握不准”、“不可思议”,以至“实在荒谬”,提示我“先要弄懂该理论”。但反复读了《创见》后,我还是没有在该文的提示下“弄懂”狂欢理论,反而产生了更多的疑惑和更尖锐的问题。这使我不得不以更鲜明也更尖锐的方式将自己的疑惑提出,求教于学界同仁,特别是那些没有先入为主之见,不将巴赫金狂欢理论视为最高权威和既定真理的朋友。
一、布克哈特和巴赫金,谁的描述更真实?
巴赫金用四个“范畴”来描述狂欢节:第一,“人们之间随便而亲昵的接触”,“在生活中为不可逾越的等级屏障分割开来的人们,在狂欢广场上发生了随便而亲昵地接触”,意义在于“取消的就是等级制”。第二,“插科打诨”,其意义在于“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级、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第三,“俯就”,“随便而亲昵的态度,应用于一切方面,无论是对待价值、思想、现象和事物”,其意义在于“使神圣同粗俗,崇高同卑下,伟大同渺小,明智同愚蠢等等接近起来。”第四,“粗鄙”,“即狂欢式的冒渎不敬,一整套降低格调,转向平实的作法”,意义在于“对神圣文字和箴言的摹仿讥讽等等。”另外,还有“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这是“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意义为“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③。巴赫金正是在这种描述和意义阐发的基础上,得出了“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狂欢节世界观”、“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的“可能性”等一系列重大而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文化史结论的。
如果我们不看别的文献,我们会倾向于相信这就是狂欢节真实客观的存在状态,认为这就是史实,从而接受了巴赫金那一系列文化史结论。但如果我们又读了布克哈特等人的著作,就不可避免地对巴赫金描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产生疑虑,进而对那一系列重大结论产生质疑。
在布克哈特笔下,狂欢节是“以游行本身为主要特征的节日庆典”,而“凯旋车”是游行的主要仪式。布克哈特多次描述了这些游行的状况,其中有很多次有具体的年代和事件背景。除了游行,狂欢节的其它内容还有赛马、赛驴,有教皇保罗二世招待群众,等等。但没有对“随便而亲昵的接触”,“加冕和随后脱冕”等场面的描写,一个字都没有④。
布克哈特描述的狂欢节与巴赫金的描述差距如此遥远,几乎没有重合之处。如果不是同在狂欢节这样一个题目之下,人们很难看出他们是在描述同一事件。布克哈特的描述惟一印证了巴赫金那几个范畴的,是人们“在歌声中竞相诽谤”这一句话,这大致可以归纳于“粗鄙”的范畴。这里特别要提出讨论的是两人对狂欢节的“主要的仪式”的不同理解,因为,主要仪式体现着事物的本质意义和内涵。巴赫金说:“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⑤而在布克哈特笔下,这个“主要的仪式”根本就没有出现,而对凯旋车游行的描述则达数十次之多。二者描述的反差实在太大了。谁更客观而真实地表现了狂欢节的基本存在状态呢?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基本状态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内涵和文化功能。虽然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基本状态可能有不同的描述,而且事物一旦转化为文字,也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形,但毕竟事实只有一个,基本状态只有一种,它不能因为视角的差异而随意描述,否则历史就没有客观性可言。历史学如果还是一门科学,那它就应该有自身的整体性。否则,任何人都可能从某个局部引发出自身所需要不同的以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历史则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打扮她,毫无例外,是为了占有她。我倾向于接受布克哈特的描述,原因有二:其一,他对每一个事件的描述都详尽地注明了史实的来源,史料的引证占了文章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这种史料的严谨性也是其著作历经一百多年而仍被公认为学术经典的主要原因。其二,布克哈特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描述历史,并不是试图导向任何结论,即没有“使命感”,这也为其描述的客观性提供了保证。而巴赫金的描述首先没有说明其资料来源,是从什么资料中概括出狂欢节的四个“范畴”以及“主要的仪式”,并将其当作狂欢节的基本存在状态?在此我要特别指出,也郑重提请有关研究者特别关注,这种不注明史料依据的描述,在学理意义上,是一个明显的缺失,一种学术性的硬伤,其客观性、全面性和公正性是没有任何保证的,甚至可能是对文化史的想象性虚构。而这正是整个狂欢理论大厦的基础工程。其次,巴赫金是为了自己的理论目的而进行描述的,为了把史实纳入自己的思维轨道,对狂欢节的存在状态进行了倾向性十分明显的选择性(同时也可以表述为扭曲性)描述,这是一种极为明显的“使命性”描述。但有了“使命感”之后,客观公正性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证呢?这种选择使巴赫金笔下的狂欢节的存在状态与史实相去甚远,一些边缘性的非核心的东西被置于中心地位。最明显的,就是对“主要的仪式”的描述。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有什么较权威的史料能够印证这种描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这种执此一端的描述完全改变了狂欢节的基本状态和文化性质。这是狂欢理论的第一个也是基础性的致命缺失。由于整个狂欢理论大厦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它决定了狂欢理论系统性缺失的必然性。
布克哈特的描述让巴赫金的追随者感到了极度的难堪。作为巴赫金的崇奉者,《创见》的作者借西方批评者之口,试图摧毁布克哈特的描述在史料意义上的经典性和权威性⑥,否则,这将会成为巴赫金狂欢理论的滑铁卢。历史上,任何经典著作(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到马克思)都有激烈的否定者,这不奇怪。但如果没有能力指出布克哈特描述的史实性错误,这种否定就会显得浮泛而苍白,学术风险极大,置自己于极为难堪的境地。
令巴赫金狂欢理论崇奉者难堪的还有威尔·杜兰近三十卷的文化史巨著《世界文明史》。当巴赫金把狂欢节提到中世纪人们的“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的时候,威尔·杜兰笔下竟找不到“狂欢节”三个字。是这位文明史大家的疏忽吗?也许。但他连每个时代的乐器、沐浴和游乐方式都没有疏忽,也详细地描述了威尼斯(这是狂欢节的重镇)等城市的节日庆典,难道却偏偏忽略了狂欢节⑦?为了避免这种难堪,《创见》中说,“此书并非无视狂欢节”,依据是此书写到与狂欢节类似的节日如“五塑节”、“驴子节”、“愚人节”等等。在这部近三十卷的文化史著作中,连“狂欢节”三个字都没有,这还不是“无视”,那还要怎样的无视才是“无视”呢?而《创见》提出的依据岂不正好反过来证明了,狂欢节在文明史中并不像巴赫金描述的那样具有核心地位,也不具有超越其它节日的文化重量吗?同时,我们也看到,布克哈特并没有置狂欢节于“节日庆典”的核心地位,而与奇迹剧、世俗演出和哑剧等并列描述。其实,不只是布克哈特和威尔·杜兰的著作,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人出版于1955年的《世界文明史》、《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等都对狂欢节只字未提。无限度地夸大狂欢节在社会生活中的分量和文化史中的地位,这是狂欢理论的第二个致命缺失。
由此可以得出,第一,巴赫金对狂欢节进行了选择(扭曲)性的描述,这种描述与其理论完全对应,却完全不能真实、客观和公正地表现狂欢节的基本存在状态,也扭曲了狂欢节真实的文化品格,使理论建立在一个失真的史实基础之上。第二,狂欢节远不像巴赫金描述的那样,在社会生活与文化史上占有那么重要的甚至核心的地位。既然狂欢节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远不如巴赫金描述的那么重要,又既然不那么重要的狂欢节的基本存在状态远不是巴赫金所描述的,那巴赫金赖以做出文化史结论的基础就太狭隘、太贫弱了,这种狭隘、贫弱与重大宏观形成了极为巨大的惊人的反差。在这里,逻辑的链条也许没有完全断裂,但已经极度脆弱,如同独木支撑巍峨大厦。
二、“民间”能否为狂欢理论突围?
为了摆脱史实基础薄弱的困境,巴赫金提出了“民间”这一概念,其理论的崇奉者更是把这一概念提到狂欢理论的核心来看待,《创见》这样来概括巴赫金的观点:“在他看来,文化是分层的,即可以分为‘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文化往往是以官方的价值标准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在这一体系中,边缘化的非官方文化(民间文化)或被排斥、湮没无闻,或经过‘他者编码’后,被扭曲变形……”⑧这段话无非是想证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没有得到主流史料的印证,是因为这些史料是非民间文化(官方文化),是“他者编码”,使狂欢节的民间内容被排斥,被边缘化,被扭曲变形,所以湮没无闻。
但是,布克哈特、威尔·杜兰等学者的著作从未排斥民间,反而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民间生活状况。布克哈特《节日庆典》一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讨论这一时期的社交生活当中,我们转向研究构成民间节日庆典一部分的游行和演出情况……”⑨。威尔·杜兰更是对每个时代的民间风俗和生活细节给予了极为详尽的描述,政治经济的内容反而只占较少篇幅。这两位学者的民间视角和描述立场是相当明显的。因此,试图以引入“民间”视角来否定这些著作的客观性和权威性,以使巴赫金完全不同的描述和评价得以成立,拓展狂欢理论的史实基础,是完全不符合真实情况的。
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再次指出,巴赫金是出于特定的理论需要,站在特定的立场上去描述狂欢节的,这使他的描述偏离了狂欢节的基本面貌,进而改变了狂欢节的文化性质。如果采用巴赫金这样一种态度,我们甚至可以将狂欢节描述为一个宗教节日,因为狂欢节有太多的宗教内容,如“背负十字架的基督”,“教士们的化装游行”,“司命运的女神”,更有教皇(保罗二世)接见和招待群众的场景,而凯旋车作为狂欢节最主要的表征,装载最多的就是表现宗教题材的内容⑩。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愿把狂欢节描述为一个宗教节日。如果没有一种整体观是无法对事物做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的,而巴赫金缺少的就是这种整体观。《创见》不正面回答我提出的那些实质性问题,如巴赫金对狂欢节的描述是否客观公正?狂欢节是否真正具有反官方、反教会的文化异质性?却以“民间”为核心概念对我进行批评,也给我一种自说自话的感觉,因为我并没采取一种“非民间”的姿态,我所引证的学者也没有这种姿态。对我的质疑大谈“民间”,是向想象中虚构的靶心射击,这不是一种认真的对话态度,也给人留下了理论乏力的印象。
三、狂欢节是反官方、反教会的?
这是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重要、最本质的问题,关系到我们对狂欢文化本质的认识。巴赫金对狂欢节的全部描述和论述,就是要证明狂欢节是一种异质文化,具有反抗或者解构官方文化、教会文化的内涵。他关于狂欢节的四个“范畴”和“主要的仪式”的描述,都归结到这一个核心点上来。在这里,我们要问,狂欢节是否具有这样一种文化异端性?
还是让我们回到史实:第一,狂欢节起源于基督教的谢肉节,英文的“carnival”一词,就源自拉丁文“carne vale”(意为“与肉告别”)。这是狂欢节与宗教的文化渊源。第二,狂欢节有大量宗教内容,僧侣是重要的参与者,教皇本人更是最重要的参与者。第三,在中世纪的千年黑暗中,狂欢节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宗教文化和平共处。第四,狂欢节在中世纪漫长的岁月中,年复一年,却没有从中产生新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力量,为历史的进步提供动力。
这些史实会不会让狂欢理论的崇奉者感到难堪?巴赫金说:“这种真正的节庆性是无法遏止的,所以官方不得不予以容忍,甚至在节日的官方部分之外,部分地把它合法化,把民间广场让给它。”(11)“容忍”一词暗示了狂欢节的文化异端性。但真实的情况是,教会不是“容忍”者,而是重要的参与者。为什么教会“容忍”并且参与狂欢节,还与之和平共处千年?是因为狂欢节其实并没有文化上的异端性,还是因为教会没有意识到其异端性?这个问题决定着我们对狂欢文化品格的定性。如果狂欢节真如巴赫金所论述的那样,具有“第二种生活”、“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狂欢节世界观”以至“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等如此重大的异端性的文化功能的话,那它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宗教内容?为什么僧侣和教皇也会参与,难道他们迟钝到上千年里都察觉不出狂欢节的文化异质性,或者察觉到了还要参与反抗自己的活动?为什么狂欢节能与教会长期和平相处,是因为教会对异端文化的容忍吗?为什么狂欢节在中世纪千年岁月中,都没有新的观念产生于其中?
史实如此清晰,逻辑如此简单。寻寻觅觅地搜罗只言片语,然后从中推出某种与之完全不对称的宏大结论,改变不了基本的史实和简单的逻辑。史实证明了狂欢节的文化品质是平庸的、保守的、游戏的、非异端性的,这才是“容忍”的真实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它存在千年却在文化更新上无所作为。教会如果能够容忍“第二种生活”,“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狂欢节世界观”,以及“大型对话”,并参与具有这些文化内涵的活动,那教会岂不是很宽容、很仁慈,甚至在否定自身吗?而中世纪那么多对异端的迫害又怎么解释,难道中世纪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年代?
巴赫金对狂欢理论文化异端性的论述是一个文化史的虚构。这是狂欢理论的崇奉者面临的理论困境,甚至可以说是绝境,要走出来实在是太艰难了。面对这种困境,《创见》是这样解释的:“在现实生活中对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或公开或潜在,消解力亦有大有小。如农民起义、农奴造反是一种对抗状态,利用节庆的合法性极尽戏谑调侃之能事、艺术狂欢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抗。”“潜在的对抗与公开的对抗相比,其冲击力不在外在形式的激烈,它往往在无形中就能起到抵制和消解的作用。”(12)于是我们又要追问,难道僧侣甚至教皇不但“容忍”,甚至还会参与到一种“往往在无形中”对抗和消解自己的活动中去,何况这种对抗和消解具有那么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最高层次(世界观)的意义?中世纪存在这种文化宽容吗?
退一步说,狂欢节真的具有这种“潜在的对抗和消解”的异端性,它又要潜多深才能被容忍呢?潜到教会都意识不到其异端性,因而被蒙骗成为重要的参与者那么深之后,它又能有多大的反抗和消解能量呢?我不知道这里的“某种程度”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一种过于暧昧的非量化的叙述,具有论证意义上的偷梁换柱的功能,抹杀了微弱和强烈之间的本质界线。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狂欢节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潜在对抗和消解的意义,这种对抗和消解的“程度”也是极其微弱的。这么微弱的一点“程度”,又怎么能够“往往在无形中”起到抵制和消解的作用,能够形成“第二种生活”和“两种思维体系”,能够升华到“狂欢节世界观”和与独白意识展开“大型对话”的高度去认识呢?巴赫金对狂欢节的文化异质性的论述,根本就没有史实的印证,也经不起最简单的形式逻辑的追问。这是狂欢理论的第三个致命缺失。
事实上,对于教会文化、官方文化而言,狂欢节基本没有文化上的异端性,也并非如巴赫金所论述的那样,具有反等级、反教条、反权威的自由平等精神和渎神意义,更不可能从中产生真正的自由平等观念和变更出新生精神。狂欢节现场的平等性、反等级性,只能在游戏的意义上认识,而绝对不可能作出那么重大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论升华。理论升华,特别是有全局性意义的理论升华,需要基本的史实支撑,而不能建构在一种狭小贫弱的基础之上。
四、为什么狂欢节没有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一面旗帜?
按照巴赫金的论述,狂欢节具有取消等级制、形成人们之间的新型关系,使神圣与粗俗接近,讥讽神圣文字、产生交替与变更精神,以感性的形式表现平等、自由等文化内涵,而这也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巨人们追求的基本目标。从最简单的形式逻辑来说,在那个上下求索,寻找思想资源的年代,这些文化巨人应该将狂欢节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精神富矿加以开掘,高举其旗帜,阐发其意义,弘扬其精神,挖掘其深度,使狂欢节的文化功能喷发潜能、发扬光大,为正在进行中的历史性文化转型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可是,非常遗憾,这种辉煌的景象并没有产生。
还是让我们回到史实中。无论在但丁、佩脱拉克、薄伽丘、乔叟等人的作品中,在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提香等人的绘画和雕塑中,还是在莫尔、蒙田等人的理论著作中,都看不到狂欢节的思想资源意义,甚至看不到狂欢节的踪影。拉伯雷曾提及狂欢节,但不是正面论述,更没有任何举其为旗帜的意思。为了防止那种具有诡辩意味的论证方式(这种方式习惯于在极其狭小的基础上得出极大的理论结论),我将他提到狂欢节的原话引述在这里。这是对一个木头雕刻人像的描述:“在里昂的狂欢节,大家把它叫做‘啃面包皮的’,在这里,它的名字是‘饿死鬼’。这是一个丑恶、难看,小孩子看了害怕的雕像……”(13)这也许就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文化巨人的代表作品中惟一提及狂欢节的。在这样一个小小的枝条上(独木算不上,说枝条也勉强,一片树叶吧),又能建构出多大的理论体系来呢?
文艺复兴长达数百年,其中涌现出大批文化巨人。难道那么多文化巨人在长达数百年的岁月中集体性地失聪失明,对狂欢节的文化意义和伟大思想内涵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没有人对狂欢节表现出特别的重视,连拉伯雷也没有(他如重视就会正面大篇幅描写,而不会在一部长篇中仅仅只是侧面地提一句)?这种史实让狂欢理论的崇奉者和辩护者如此难堪。这究竟是因为狂欢节本身就不具有反等级、反教会自由平等的文化内涵,还是因为那些巨人们迟钝愚蠢而没有发现这种思想资源呢?这个问题决定着我们对狂欢节文化品格的定性,决定着巴赫金对其伟大文化意义的认定能否成立。狂欢节不但在中世纪,而且在文艺复兴时期没有任何闪亮的表现,说明它的文化平庸性,没有思想资源的意义。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能用什么方式来改变这个结论,这是狂欢理论的崇奉者面对的又一个绕不过去的理论绝境。如果狂欢节作为狂欢式(按巴赫金的定义是所有狂欢节式的庆贺活动的总和)的核心,在文艺复兴时期以至整个中世纪都几乎没有表现出多少思想能量,那么,狂欢节那些伟大的文化内涵和思想意义,又从何说起呢?在这里,史实和逻辑都证明着巴赫金对狂欢节伟大文化意义的论述是一个文化史的虚构。这是狂欢理论的第四个致命缺失。
五、狂欢化到底有多少历史依据和文化能量?
狂欢化是巴赫金创造的学术概念,在狂欢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是暧昧而模糊的,这种暧昧性和模糊性掩盖了其历史依据贫弱而文化能量被无限夸大之间令人震惊的反差。在这里,我想对这个概念进行透视梳理,以剥离附于其上的暧昧性和模糊性,使其在学术的视野中变得通透明朗。
让我们从巴赫金的定义开始。他说:“狂欢式转为文学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14)这是它的定义。“狂欢化的渊源,就是狂欢节本身”(15),这是它的来源。“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16),这是它的功能。按照巴赫金的论述,狂欢化渊源于狂欢节,那么,只有那些渊源于狂欢节的文学作品,才符合狂欢化的定义。但是,当我们回到史实中,这种渊源于狂欢节的作品,从“狂欢式转为文学语言”的作品,又在哪里呢?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之中,中世纪又有哪些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体现了这种转化呢?按照巴赫金的说法:“文艺复兴时期,狂欢节的潮流可以说打破了许多壁垒而闯入了常规生活和常规世界的许多领域。首先这股潮流就席卷了正宗文学的几乎一切体裁,并给它们带来了重要的变化。整个文学都实现了十分深刻而又无所不包的狂欢化。”(17)这么说来,狂欢节功莫大焉,不但“打破”了壁垒,“席卷”了一切文学体裁,还带来了“无所不包的狂欢化”。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第一,文艺复兴时期思想解放的文艺潮流,跟狂欢节有什么关系?把这么大的历史功绩归于狂欢节,有多少历史依据?狂欢节在文艺复兴之前平庸了上千年,突然就获得了这么巨大的精神能量吗?那些精神的壁垒,是狂欢节“打破”的吗?一个看不到狂欢节踪影的文艺思潮,却被狂欢节的潮流“席卷”,这种强迫性的描述,按照怎样的逻辑才能够成立呢?第二,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文艺作品,在什么意义上可以用“狂欢化”来描述?按巴赫金的论述,只有渊源于“狂欢节本身”的文艺作品,才能被描述为“狂欢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哪一部作品,又是渊源于狂欢节呢?如果一部作品,连“狂欢节”三个字都没有,我们能说它渊源于狂欢节吗?即使拉伯雷的作品提及这三个字,也是一种极其细节性的描写,同样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巨人传》中有“狂欢节”三字,就能得出它渊源于狂欢节,因而是“狂欢化”作品的结论吗?我倒愿意提供一个例子,那就是歌德的《意大利游记》。歌德在这本书中相当详细地描述了罗马狂欢节的情况。可是,这本书写于18世纪末,文艺复兴已告完成,教会的绝对权威已经沦落,而且,按照巴赫金本人的说法,“自17世纪起,民间狂欢生活趋于没落,几乎失去了那种全民性质,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急剧下降。它的表现形式变得贫乏、浅显、简单了”(18)。《创见》引证歌德来说明狂欢节的文化史意义,既明显地违背了巴赫金本人的论述,也不能对文艺复兴时期狂欢节在文学作品中的存在提供依据(引证伏尔泰也是如此)。宏观地看,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狂欢节基本上没有进入那些文化巨人的价值视野,更不用说举为旗帜,那狂欢化又从何说起呢?又怎么能够把那些伟大作品归于“狂欢化”的旗下?在那些文化巨人的小说、诗歌、戏剧、绘画、雕塑和理论著作中,看不见狂欢节的踪影,却被认定为渊源于狂欢节的“狂欢化”,从最简单的逻辑上来说,也是不能成立的。只有在那种不讲史实的强迫性逻辑之中,才能把这些作家的作品以至整个文艺复兴,归功于狂欢节名下。“狂欢化”作为一个理论概念,得不到文学史实的支撑,这是狂欢理论的第五个致命缺失。至于今天有人用“狂欢化”来描述当时的文艺思潮,那是另外一回事,根本就不意味着当时的文学思潮和作品与狂欢节有什么渊源关系。将两者混为一谈,就会把历史的清澈之水搅浑。在巴赫金笔下,他自己定义的,源于狂欢节的“狂欢化”与文艺复兴时期“十分深刻而又无所不包的狂欢化”已经不是同一个“狂欢化”,前者渊源于狂欢节,而后者与狂欢节没有关系,不符合他自己的定义。在这里,概念已经发生了偷换。偷换的理论功能,就是试图强行在狂欢节与文艺复兴之间建立起史实中并不存在的联系。这种意义的转移,是狂欢理论关键性的一环,却又是丧失了内在规定性和逻辑性的一环。
六、狂欢节以及狂欢化是否具有对话的文化品格和精神能量?
巴赫金说:“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这里说的“对话”,按巴赫金本人的意思,是在“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与“独白意识”的对话;既然是在“高级领域”与“独白意识”的对话,而且是“大型对话”,它必然有相当的规模,并有相当的对抗性,尽管形式可能多样化。
让我们再一次不厌其烦地回到史实。首先,狂欢式转化为文学语言形成狂欢化,这一状态如我们前一节所论证,是缺乏文学史的史实支撑的,我们很难在文学史中找到这种转化的例证,不论在中世纪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都是如此。因此,源于狂欢节的狂欢化,是一个精神能量非常有限几乎找不到史实支撑的词。这种非常有限的能量,能够建立起“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吗?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如果不是逻辑线索的中断,至少也是极度的脆弱,这是典型的小词大用。而且,这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在中世纪没建立起来,也不可能被宗教文化允许建立起来。如果允许了,那就是多元化社会了,还谈什么“独白意识”呢?如果一种“可能性”在长达千年的岁月中还没有转化为现实性,这种“可能性”就是一种纯理论的虚设,没有任何历史依据。把这种虚设的“可能性”当作论证依据,不是以想象催生理论神话吗?大型对话结构在文艺复兴时期逐步建立起来了,独白意识被打破了,但如前所述,这种建立的力量不是来自狂欢节,也不是来自所谓的狂欢化。在任何一种论证之中(除了强迫性论证),这一历史进步的功绩都不能归功于狂欢节,狂欢节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没有扮演什么角色,既不能说重要角色,更不能说决定性的角色。
为了替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辩护,《创见》举了一些例子,如文学作品中的“小丑”、“傻瓜”、“骗子”形象,认为这是“讽刺性模拟”,也属于对话范畴。但是,我们要问的是,第一,它们与狂欢节有什么渊源关系?第二,这种“讽刺性模拟”有多大的规模,又有多强的力度,具有与独白意识的对抗性,并建立起“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在这里,作者又一次利用了人文科学的语言非量化性,用一种模糊的暧昧的逻辑,从一种局部的狭小的事实中推论出一个重大的文化史结论。其逻辑线索似乎是清晰的,但在一种学术性的视野中,又是暧昧而脆弱的。《创见》批评我“不相信‘狂欢’和‘对话’两者能够结合”,这种表述不够准确。准确地说,我不相信的是源于狂欢节的所谓“狂欢化”具有“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的文化能量,这种文化景观根本没有在历史进程中产生。
由狂欢节产生狂欢化,进而建立“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是一种由想象催生的神话。巴赫金关于狂欢节和狂欢化的“大型对话”意义的描述,是对文化史的又一次虚构。这是狂欢理论的第六个致命缺失。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巴赫金狂欢理论及其崇奉者之论证方式的根本缺陷。这种缺陷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在历史的层面,他们将局部的甚至极为边缘化的史实描述为整体的核心的史实,把独木当作钢筋水泥基石,以建构理论大厦。在逻辑层面,他们利用人文科学语言难以量化(“可能性”、“某种程度”、“往往”,这些词都具有把事物模糊化以改变其基本状态和性质的功能)的特征,以一种具有暧昧性的推理方式,从一种局部的边缘化的史实中,推论出整体的全局性的重大结论。在一种表面严谨的逻辑过程中,史实与结论的联系已经十分脆弱,这种脆弱性在对狂欢节“主要的仪式”的描述中,在“狂欢节——狂欢化——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这种推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他们来说,史料支撑系统性贫弱匮乏,不论是在狂欢节的基本存在状态、狂欢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狂欢节文化功能的异质性与反抗性方面,还是在文艺复兴中的作用、狂欢式转化为文学语言,即狂欢化、狂欢化所具有的对话功能方面,史料都远远不足以建构一座理论大厦。如果说,我曾以“想象催生的神话”来表述狂欢理论的非学理性过于绝对的话,那么“独木难撑大厦”,就更加准确地描述了狂欢理论在方法论方面的全局性缺失。这是狂欢理论的第七大致命缺失,是一系列缺失中最根本的缺失。
我想细心的读者一定会看出,我在对以上各个问题的论述中提供的史料,除了局部准确性之外,还是一个相互印证相互支撑的整体,因而结论也具有相互印证相互支撑的整体性。这种从诸多方面导向同一结论的整体性揭示出:狂欢理论各个局部、各个环节从史实描述到论证升华,其牵强性脆弱性也是相互印证的,其理论缺失是基于各个局部缺失之上的系统性、全局性缺失。
结语
八十多年前,鲁迅曾对中国文化做出了极端的表态:“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19)类似的表态很多。这种将中国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的价值姿态,显然是经不起学理性审视的。但八十多年来,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与鲁迅进行学理性纠缠。为什么?因为将鲁迅的这些表态置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就可以看到其“片面的深刻”,及其历史合理性。在当时,为了推动新文化的思想进程,轰毁旧文化的强大堡垒,那种非学理的、极端的和矫枉过正的姿态,才是最得力最有效的。这就是片面性和极端性的意义,应该得到理解。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对于《创见》所论述的它的多方面意义,我不想作什么回答。我承认“意义”(虽然不无保留),但还是要说,这种对“意义”的论述无法拯救狂欢理论在学理层面的缺失。“意义”不能超越史实和逻辑,不能扭曲学理。学理的支点只能是历史和逻辑,而不能是“意义”。历史不能因为“意义”的需要而变成一种可以随意选择描述视角和切入方式的功能性存在,否则,“历史”就不成其为历史,就将失去自身的尊严和客观性,而成为“意义”史了。而“意义”,我们知道,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利益背景、理论背景的人那里,是在不断流动的。
在“意义”的意义上,我对巴赫金的理解是语境性的理解。巴赫金的学术活动是在一种文化封闭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的,为了挑战这种封闭性,他在学术的外衣下表达自由平等、反抗敬畏、尊崇对话和反对独白的价值观。为了完成这种意识形态使命,他采用了“片面的深刻”的学术姿态。这可以理解,但这只能是一种语境性理解。一旦回到严谨的学术视野之中,回到历史和逻辑之中,我们的质疑立即全部生效。
注释:
①参见拙文《想象催生的神话——巴赫金狂欢理论质疑》,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②⑥⑧(12)夏忠宪:《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的创见》,载《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③⑤(14)(15)(16)(17)(18)巴赫金:《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75-178页,第177页,第175页,第186页,第247页,第185页,第185页。
④⑨⑩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7-420页,第397页,第397-420页。
⑦参见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幼狮文化公司译,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11)巴赫金:《拉伯雷研究》,李兆林、夏忠宪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13)拉伯雷:《巨人传》,成钰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882页。
(14)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