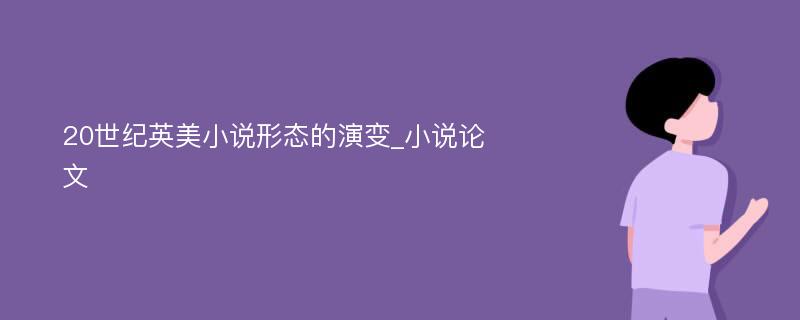
20世纪英美小说形式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美论文,形式论文,世纪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 本文追溯了20世纪英美主要作家在长篇小说的表现形式方面所做的不懈探索。文章重点分析了乔依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托妮·莫里森的《心爱》和B·S·约翰逊的《不幸者》等4部现当代小说的叙事技巧, 大致勾勒了一幅英美小说家致力于文学意识和文体意识革新的演变图。作者认为,小说形式革新不仅是作家个人创作特点的个性追求,而且是小说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 小说 形式 叙事 文学意识 文体意识 传统
20世纪英美现代小说的兴起,标志着古典小说的衰微。古典小说通过自身特有的结构所追求的恢宏的故事背景,所表现的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和个人命运与社会大众命运的息息相通,以及其维妙维肖的状物描写,对生活的人为模仿,对严明的理性精神和英语文化中特有的人伦理念的揭示,渐渐地被弥漫于字里行间的挫败感、无可名状的沮丧与悲凉、沉痛而富于诗意的落寞与孤寂、甚或许多非传统小说的“技巧”(如梦幻、呓语、无意识的自由联想、词语包括段落的任意组合、病态和疯狂的漫谈等)所取代。在这场传统与反传统的搏斗中,传统小说节节败退,以至于有作家认为,今天仍然用19世纪的小说形式进行创作就是“犯时代错误”。时至今日,小说所关心的已不再是“什么”,而是“如何”;不是“内容”,而是“手段”;从而使小说在主题上,从“中心论”走向“分散论”;在思想上,从“对深度的挖掘”走向对“平面的扩展”;在人物塑造上,从“英雄”走向“反英雄”;在情节的安排上,从“完整”走向“零散”,甚至使小说的结尾也变得要么模棱两可,似了非了,要么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了。
这就是英美小说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轨迹。尽管如此,现当代小说的价值却也不能忽视。如果我们不再抱残守缺,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看待英美现当代小说,就会发现在浩如烟海的现当代小说中,妙品佳构同样比比皆是。它们要么试图反映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如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要么概括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如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要么抉微烛幽,挖掘个性意识的觉醒,如乔依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要么以荒诞的形式“致力于文体和文学意识的革新”,如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要么追求表现客观世界的悲剧性和主观自我的渺茫性,如伍尔芙的《海浪》;要么致力于小说形式的“暴力革命”,如英国当代作家B·S·约翰逊的《不幸者》;要么以新奇叙事手法表现生存的荒诞和虚无,如托妮·莫里森的《心爱》……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小说既是内容的产物,又是技巧的产物,因此,小说分析既可以从内容入手,也可以从技巧入手。坚持内容分析的批评家一般认为,小说具有反映现实的功用,能给人以道德启迪作用,而坚持形式分析的批评家则信奉小说是艺术的产物,揭示其艺术规律,发现并研究特定作品的技巧,在这类批评家看来,才是对小说“唯一真诚”的分析,又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本文试图通过对几部重要小说的艺术分析,勾勒出本世纪英美小说追求形式变化的概貌。
一般地讲,英美现当代小说作者对形式——所有艺术技巧的总和——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内容——可以复述出来的故事的关注,这既是作者试图在艺术手法上超过前人的强烈的竞争欲望产生的结果,亦是文学批评引导创作的结果。被誉为现代文学批评大师的英国现代派诗人T·S·艾略特在《批评的功能》一文中指出:“我不否认为艺术可以有本身以外的目的,但艺术并不一定要注意那些目的……艺术在发挥作用的时候,不论它们是什么样的作用,越不注意那些目的就越好。”艺术本身的目的无疑是艺术自身,亦即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小说作者一旦视自己为艺术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或者什么哗众取宠的不负责任的文痞,他必然要不断革新对题材的表现手法,使他所表现出来的都是艺术性的,犹若视建筑为艺术的建筑师,主要关心的是建筑的风格和艺术个性,而不是对建筑材料的过分关注。自从王尔德喊出“生活模仿艺术”那震耳欲聋的口号后,对艺术手法的自觉关注像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流,时刻冲击着维多利亚时代对文学那种道貌岸然的评判标准。小说家不再以充当传统道德秩序的卫士(如简·奥斯汀、哈代等)而自豪,而首先对题材的表现手法进行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探讨(如詹姆斯·乔依斯、菲茨杰拉德等),将文学的触角从外倾转向内倾,将视野从对社会生活的关注转到对个人命运的关切,苦心塑造的主人公不再是社会普遍价值标准的传声筒,而是置身于社会现实之外、在孤独中走向觉醒或灭亡的反英雄。正如乔依斯所说,现代作家把孤独当成“艺术精炼的首要原则”来处理,于是,他们笔下的主人公总是从孤独和困惑开始他们的人生历程,经过长期的理性认识和思索,最后陷入更高层次的孤独和困惑,如《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的斯蒂芬·德达露斯。艾略特在《形而上的诗人》中说:“意义不过是窃贼手中的肉包子,目的在于分散读者的注意力。这样,诗才能通过他的感官,以不知不觉的方式抓住读者的大脑皮层,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对他悄悄地产生影响。”另一位美国文学批评家马克·肖勒在《探讨技巧》中也犀利地指出:“评论内容本身根本就不是评论艺术,而是谈论经验。只有当我们评论实现了内容,即形式,也就是说,只有把艺术品当作艺术品对待的时候,我们才是作为批评家在说话。内容(或经验)与实现了的内容(或艺术)之间的区别在于技巧……因此,当我们谈论技巧时,我们就几乎涉及到了一切方面。”诸如此类过分强调形式和技巧的呼声近一个世纪以来,可以说不绝于耳,它们对英美小说创作实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冲击。毋庸置疑,对小说形式特征的强调也并非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挑战。利维斯、特里林等批评家坚持认为,小说区别其他文类的正在于它的内容和题材,免于形式约束恰恰是小说的规定性特征。阐述这种争论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我只想以乔依斯那震古烁今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托妮·莫里森的《心爱》和B·S·约翰逊的《不幸者》为例,历时地说明本世纪英美小说在形式探讨方面走了多远。
《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1916)描写的是带有自传性的主人公斯蒂芬·德达露斯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他的人生观所发生的剧变以及他在自己个性意识觉醒过程中所经历的思想矛盾。斯蒂芬随着生活阅历的不断丰富,屏弃了宗教信仰,终于脱离了祖国,因为他的祖国“爱尔兰是一头老母猪,连自己的崽子都吞掉了”,最后决定“在某种形式的生活中或艺术中充分而自由地表现自己”,而为了保护自己,“决心使用唯一可用的武器:沉默、流亡和技艺”,一句话,小说表现的是个人与环境的尖锐冲突和矛盾。乔依斯这部意识流小说引起我们浓厚兴趣的除了它所表现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主题外,更主要是由于作者在对素材的犀利分析以及对经验的价值和性质的确定中所采取的迥然不同的技巧。乔依斯之前的大多数作家在确定经验的价值时,总会情不自禁地进行直接或间接的道德评判(如奥斯汀、萨克雷、霍桑、哈代等)。乔依斯则另辟蹊径,将他冷峻的分析和价值判断完全融入小说的内在结构之中,换句话说,斯蒂芬与环境的尖锐的冲突正是靠小说的内在结构来表现的。小说写了斯蒂芬幼年、少年和青年三个成长时期与环境的“格格不入”,作者相应地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对主人公的性格和意识觉醒过程进行分析和整合。打开小说,扑面而来的是作者用意识流手法描述的梦幻般的奇妙世界,以及周围环境对蒙昧无知的幼年斯蒂芬尚未发达的意识的无情撞击。作者在这一部分有意地,同时也是靠内在的文体结构,将环境与主人公并置在一起,以奇幻的手法描述幼童眼里的世界,犹若将一个尚不能作出选择和判断的幼童放置在迷宫和恐怖城一样,一切光怪陆离的、奇谲怪诞的、熟识的、陌生的、恐怖的,像决提的洪水奔腾而来,又如乐盲置身于现代音乐厅,无论如何也分不出鼓点和琴韵、噪音和主旋律。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容不得斯蒂芬质疑或作出判断。这一部分接连不断的情景描写和事件并置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而这正是乔依斯的匠心所在,因为斯蒂芬身边发生的一切在他的意识中也是没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仅仅是不同的事件而已。在小说的第二部分,随着主人公年龄的渐长,阅历的不断丰富,对外部世界感性认知能力的逐步提高,他开始对自己的经验进行理性判断和分析,作品的风格和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叙事节奏的明显加快。作者对斯蒂芬的经验世界进行剔除,对描述的经验的细节逐步充实(如他参与的关于宗教、政治、社会道德、祖国前途等的争论)。斯蒂芬几近成人时,他的浪漫激情也日渐饱满,但对爱情的憧憬敌不过理性的辩白,他终于沿着理性的弧线不断升高,直至达到理性认识的一个高潮——对宗教信仰的断然抛弃。他这时对自己的人生价值也作出了重新判断,逐步明确了成年以后所必须肩负的艺术使命。这一部分的叙事风格具有鲜明的特点:老辣,冷峻,语调激越,节奏明快,与主人公的内心活动绝妙地糅合在一块。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即当斯蒂芬认识到唯有艺术方能拯救自身灵魂之后,他与环境的冲突在表面上渐趋平缓,小说的叙述节奏也随之平缓。然而,斯蒂芬的认知活动并没有终止,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缓慢流动,乔依斯精心构思的句子,在舒缓质朴的外表下,处处透着犀利的分析和尖刻的讽刺,正如表面上平静的河面,在深处汹涌着潜流。统观整部小说,乔依斯的叙事技巧与主人公缓慢的意识觉醒过程以及主人公意识的有序和无序的流动水乳交融,相映成趣,完美地揭示了主题,终于诞生了使当时的读者望而生畏的反英雄斯蒂芬——一个以个人欲望代替社会意志,视传统道德如草芥,将生命的直觉和思维的悟性集于一身并企图主宰个人命运的人物。
詹姆斯·乔依斯生命不得志,自走出爱尔兰后一直贫病交加,最后双目失明,不到60岁时客死瑞士苏黎士。他早年曲高和寡,鲜有知音。他于1905年写成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曾被8家出版社拒绝, 后在美国现代派诗人庞德的帮助下,于1914年得以问世。该书遭拒绝的原因是由于它怪诞的文体,然而自20年代起,恰恰是他的这种文体始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B·S·约翰逊在《小说——形式与手段》一文中说:“仅就风格而言,《尤利西斯》就是一次革命。”福克纳在接受《巴黎评论》记者斯泰恩采访时说:“我那个时代仅有两位大作家,他们是托马斯·曼和乔依斯。看乔依斯的《尤利西斯》,应当像识字不多的浸礼会传教士看《旧约》一样,要心怀一片至诚”〔1〕。据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福克纳从乔伊斯的意识流手法中受益匪浅,并使这一手法在美国大放异彩,同时也使他跻身于伟大作家的行列。乔依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及其续篇《尤利西斯》一直被西方评论界誉为意识流的百科全书。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完整的故事和贯通一致的情节,事件之间没有明确的时序和逻辑关系,整个叙述风格似乎受变幻莫测的意识流程的制约。乔依斯在表现达德露斯对他的经验进行分析时,大量使用内心独白手法。为了强调其杂乱无章,作者常常抛弃标点和句头字母大写的习惯,大量采用拟声词和外来语,甚至自造新词,独创文法。乔依斯的语言仿佛是在流动,借以表现人物的思想进程,中间夹杂着大量的间歇、跳跃和停顿,充满了联想、类比、暗示和象征。这些在当时令读者尴尬、令批评家愤慨的新奇手法经伍尔芙、海明威、福克纳、普鲁斯特等大师的继承和发展,如今已如明日黄花,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和荣耀,但回顾近一个世纪英美小说在形式探索方面所作的不懈努力,乔依斯和他的意识流手法以及用小说的内在文体结构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的尝试,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
无独有偶,本文要分析的另一部“致力于文体和文学意识革新”的小说——《北回归线》,也是在庞德的帮助下,才于1934年在巴黎出版。它的作者亨利·米勒属于美国“迷惘的一代”,与海明威、斯泰恩女士、菲茨杰拉德等美国旅欧现代派作家关系密切,思想认识也比较接近。米勒对现代生存和欧洲文明感到极度失望,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现代社会现存的一切人伦理念和人际关系。如果说海明威笔下的人物脱离社会,走向丛林,积极投身于狩猎等冒险活动来表现现代生存的悲剧性以及个人在走向悲剧的过程中所残留的个性尊严,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人物在强烈的个性意识的觉醒中不断走向茫然,更多地表现现代生存的渺茫性和个人的挫败感,那么,米勒笔下的人物则是以在现代都市中极端的个人放纵,强烈的反叛意识来排解苦闷和空虚。钱钟书先生曾说:“恋爱是闲人的忙事。”以此来观照米勒的人物亦是无比熨贴:耽于酒色恰恰是百无聊赖之时寻求的意识麻痹。当然,《北回归线》中不仅仅是赤裸裸的性描写和不可遏制的欲望,它还有连篇累牍的冷潮热讽、俯拾皆是的痴人说梦、汪洋恣肆的议论剖析、荒诞怪异的自由联想、震耳欲聋的破口谩骂,总之,什么都有,唯独没有与传统小说丝毫的相似和雷同之处。
《北回归线》在巴黎出版后,即遭英美两国的查禁,直到60年代初才得以在大西洋两岸先后刊印。查禁的原因是由于“过分的色情描写”,而开禁是因为有色情而“无挑逗”。其实,它遭禁的真正原因恐怕是它那喷涌不止的反叛意识,它犹若爆发的火山,若不及时制止,一切现存的都将被摧毁。《北回归线》正是以它独特的文体革新意识、肆无忌惮的漫评、对人物灵与肉的各种体验的坦率暴露等令检察官们感到尴尬和气愤。那么,这部“最有争议”的小说开禁后令无数作家和读者为之喝彩的原因到底何在?
美国著名的黑色幽默作家诺曼·梅勒认为《北回归线》“同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一样……致力于文体和文学意识的革新,你只要读上20页便知道一个文学奇迹正在出现——以前从未有人这样写过,以后也不会有人以这种文体写得这么好”〔2〕。可见, 这是一部迥然不同的小说,其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它的“文体”和形式,也就是肖勒所说的“实现了的内容”。这部小说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情节,甚至没有连贯的故事,没有时间,没有高潮,有的只是米勒在巴黎生活期间无数个“片断”。美国当代后现代派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曾断言:“片断是我唯一相信的(文学)形式。〔3〕”文学批评家施奇克尔更加绝对,他说:“我们在片断中感知,在片断中生存,也必然要在片断中死去。奇怪的、残缺不全的状态、甚至奇怪的并置和重叠,恰恰是现代经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难道不应该描写这些片断、突出这些片断吗?”〔4〕问题是将生活片断按照时间顺序或者随意排列后的文体还是小说吗?当“新批评”成为英美评论界的时尚时,著名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赖在《批评的解剖》一文中,将小说分为4种:长篇故事、 自白、剖析和传奇。根据这种分类,《北回归线》无疑属于小说的范畴,但不是以故事和完整的情节取胜,而是以自白和剖析见长,正如袁洪庚在译序中指出的那样,本书“叙述的并非处于常规因果关系中的人物的活动,而是混沌般乱哄哄的背景下一群不受寻常社会规范制约的叛逆者有悖常理的破坏性言化和行动”。这个概括是比较准确的。《北回归线》洋洋洒洒25万字,除了个别地方有数千字长的严肃思考和对人类的各种经验进行的无情剖析外,其余则基本上是用数字叙述成的“疯子行径”、“疾人说梦”和随意叠加的生活片断。说它们是“疯子行径”,因为绝大部分事件都是始于疯狂而又终于疯狂,说它们是“疾人说梦”,因为所有人物过的都是醉生梦死的生活,除了喝得酩酊大醉就是无休止的嫖妓,正如米勒在书中承认的那样,“在我与未来之间形成障碍的唯一东西就是一餐饭”,而吃饱饭意味着“可以踏踏实实地继续干几个钟头,或许还能使我再勃起一回呢。”
裸露灵魂是对现代生存置疑的必然结果,而自我怀疑则源于对生存意义的探索。在米勒这类对人类文明极度失望的作家的意识中,世界是荒诞不经的,毫无意义的,因而,个人生存只是、也只能是在空虚中追求世俗化和本能性,在玩世不恭中寻求暂时的欢乐,在性的宣泄中证明自己作为男性的尊严和力量,并以此逃离这粗砺的世界。将一个坠入万劫不复境地的生灵和一颗正在蒙难的灵魂,用诗一样的语言和盘托出,让读者审视并剖析,这大概就是梅勒所说的“文学意识的革析”。那么,他所说的“文体意识的革新”又是什么呢?我以为作者用了三种方式实现了这种“革新”,那就是自白性、基调性和形式性。
自白性的本质是指灵魂的漂泊不定感的具体外化,是苦闷和空虚的外部显现。在《北回归线》中,米勒的具体作法就是在沉沦中诅咒沉沦,制造苦闷而又在苦闷中排解苦闷,不断地营造空虚而又在空虚中打发空虚,一句话,无休止地裸露灵魂的哀苦无路。小说中一次次的独白、沉思、漫评、忧虑等,都是自白性的具体外化。问题是这种无休止地裸露,炼狱般的生活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吗?回答是肯定的。借用洛德威在《后现代主义景观》中的话说,这种具有自我毁灭意味的自白“最能引起共鸣,因为在现代世界里能证明产生这种绝望情绪的事不胜枚举。”
与以苦闷和焦虑为特征的自白性密切相关的是基调性。演奏需要定调,自白亦然,否则则是艺术上的失败。《北回归线》自始至终笼罩在对生存意义的消失和价值枯竭后的“无言”之中。不论是诗意的描写还是多角度对痛苦和孤独的热切玩味,其目的均是要表现自己的愤世嫉俗和无奈情绪。在这种基调之下,读者看到的是对人类文明全方位的冷嘲热讽,感到的是一颗敏感的灵魂在蒙难。这正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文学的基调,米勒不过调得更准罢了。
形式性是米勒表现挫败感和精神萎顿的艺术手段。他对长篇小说的传统叙事成规的破坏最彻底,最无情,使他成了新形式的创造者。米勒将他在巴黎的生活经历浓缩成茫然无奈的情绪,犹如这种情绪的产生没有直接原因和具体时间一样,小说的任何一章都没有明确的时间,读者可以从任何一页阅读。称这部小说是一堆未标日期的“日记”倒更贴切,但它却不是“日记体小说”,后者与传统小说在情节的一致性方面更多的是认同而非偏离。米勒自60年代起声名日隆,根本的原因是被公认为后现代派小说认祖归根的源头之一。后现代派作家普遍追求形式性,用巴塞尔姆的话说,“因为形式是唯一值得关注的对象”。在美国超现实主义诗歌中,“垮掉的一代”的作品中,在“黑色幽默派”以及当代的先锋作品中均能找到米勒的影子。米勒与他们的区别仅是后现代派作家连情绪的统一也抛弃了,作品在形式上更加开放。
在这场对小说形式一次次破坏和重建的接力中,就本文而言,第三位出场的是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从文学意识和文体意识的革新角度考察莫里森的几部小说,它们均不具备《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北回归线》的开拓性和创造性,但在对传统小说叙事成规某些方面的“破坏”而言,莫里森的代表作《心爱》的贡献却同样是“登峰造奇”的。《心爱》是一部令人肝肠寸断的小说,是“反映美国历史上黑人生活经历的里程碑式的小说”,是对奴隶制的控诉和无情鞭笞。小说的主人翁塞丝不堪忍受奴隶主的压迫和欺凌,决定逃离魔窟,但功败垂成。为了不使年仅两岁的女儿沦为奴隶,她毅然用手锯锯断女儿的喉管。从此,她们居住的房子日日闹鬼,夜夜不宁,成了鬼怪肆虐的“地狱”。一天她家门口出现了一个自称叫“心爱”的姑娘,她会唱塞丝仅仅唱给她的女儿“心爱”的儿歌,认识塞丝的耳环,了解整套房子的结构。新来的陌生姑娘无疑被塞丝和她的二女儿当成了“心爱”的复活。大女儿的阴魂转世打破了塞丝平静的生活,给她带来欢欣和惬意的同时,也提供了赎罪的机会。“心爱”觉得塞丝亏欠了她,因而心安理得地接受塞丝对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呵护。塞丝最后干脆辞职在家,专门伺候这个半人半鬼的“女儿”,“心爱”成为完全的寄生物。家里的积蓄很快告罄,迫于生计,塞丝的二女儿丹佛勇敢地走出与世隔绝的家,请求邻居的帮助。30名妇女组成了一支十字军似的队伍开进塞丝的家,在几名男人的帮助下,一举赶走了饿鬼。但是,塞丝并未因“鬼”的消失而恢复正常的生活,反而更加萎顿,最后卧床不起,等待死神的降临。
如果《心爱》的情节安排如上所述,它充其量不过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当代翻版,不可能成为杰作。一如不同的题材能够表现相同的主题,相同的题材可以有无数种表达方式。按照肖勒的说法,评论题材不是在搞文学评论,那么,引起我们浓厚兴趣的只能是作者的艺术手法,即形式。不可否认,《心爱》对奴隶制进行了无情揭露和谴责,反映了塞丝一家三代女人的心路历程,但小说的艺术魅力是靠作者新颖的叙事技巧实现的。
如前所述,乔依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第一部分,将一切进入幼年斯蒂芬眼中的事物不加分析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开现代小说叙事之先,莫里森则对他的方法进行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她采用的主要方法是让主要事件不断“复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镜像结构,而在揭示主要事件与小说情节的关系时则采用的是“拼板式叙事”。
所谓“镜像结构”是指小说的主要故事线索,抑或一种声响、一个物体、一件事或者一句话,每隔一定的间距就要再度显现。每次复映都经过作者的精心加工,是对前一次复映的补充和延伸。复映与复映之间互相补充、互相印证,零散而有机地揭示着叙事的内涵。仅以小说中幽灵的出现为例。小说的第一句话是“124 号房子充满了恶意和一个幼儿的怨恨”,但接下来的却不是对房子结构的详细描述,也不是对“幼儿怨恨”的原因的交待,相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受害者的感受和房子闹鬼的各种情形以及塞丝的婆婆死时的状况。在前几页,重要的人物先后登场,事件接连发生,小说的叙事节奏极快。由于所有事件均是偶然发生,人物关系缺乏必要的交待,小说显得非常零乱。等我们读过数十页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小说的第一句话中就隐含着“幽灵”。所谓的“恶意”和“怨恨”,即是被杀死的女婴阴魂转世后对塞丝一家人的折磨。书中的人物对此一清二楚,只是不愿提及罢了。幽灵以及“杀婴事件”是小说的关键情节,不论是作者还是书中的人物均无法回避。尽管每隔几页或数十页,这个话题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但每次的叙述都是浅尝辄止,似乎作者要尽其所能中断叙事的连续性。杀婴事件既是《心爱》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理应大肆渲染,作者却恰恰在这个关键情节上惜墨如金,甚至有点故弄玄虚。不可否认,莫里森对这个事也是耿耿于怀,不放过任何能够暗示的机会,甚至不惜在叙述其他事情时戛然而止,强行在“信息链”中插入这个“象征”——一个雪球般越滚越大的象征,却在需要精雕细刻之处,轻笔带过。莫里森之所以这样安排恐怕还是要在形式上模仿塞丝的生活。塞丝杀死女儿这件事不仅给她,而且给所有与她有关的人物都造成心理重负。然而像所有沉淀于潜意识中的恶梦一样,它们总要不时地挣脱意识的锁链,影响一个人的言行。塞丝生活的“任何层面都在闹鬼”,这样,她的现实生活中不断浮现出过去的恶梦就成了真实可信的事了。通过“镜像结构”,作者便将塞丝等人的过去完全融汇于“现在”,营造了一种令人惊诧的真实感。
换一个角度看散漫于书中“死婴复活”事件,若将小说当作一个整体考察,我们又可以将莫里森的技巧称为“拼板式叙事”。假如莫里森是用绘画表现这件事,然后将“画”撕成10片,那么,就可能性而言,这10个色团会在书中的任何地方出现。事实也正是如此。又如塞丝的婆婆在第二页就写道死于病魔,但她过去的生活却没有出现太多的空白。作者用的显然不是倒叙法,因为她们仍然不时地出现于塞丝的生活中,并经常用现在时说出极富哲理的话(如“世界上没有不幸,只有白人”)。还有塞丝的情人保罗·D,虽然与塞丝分别18年之久, 其间漂泊流浪,居无定所,靠打零工度日,曾一度坐牢,但他的言行始终贯穿全书,我们只是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坐牢的时间和原因罢了。
将主要人物的生活经历经过作者一番重新排列,其结果是整部小说在叙事上呈不连贯性。作者抹去所有人物的年龄和故事的时间背景后,《心爱》出现了许多时空的空白和跳跃,这也许正是莫里森追求的形式效果。一连串不断变换的场景与相互交错的叙述将发生在几代人身上的悲惨事件交汇于感情的座标之上,这正是这部在表现上显得散乱而在本质上又显得统一的小说的艺术特点。莫里森在《心爱》中追求的不是叙述逻辑的统一,而是感情强度的统一。互不关联的段落在读者心中唤起类似的情感,就效果而言,已构成了一个统一的印象。
从叙事的角度衡量,《心爱》无疑是一个艺术宝库,现当代一切有影响的表现手法一应俱全。象征意义、荒诞派、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手法交相映辉,使这部反映黑人悲惨遭遇的小说具有了更深刻的普遍性,进而揭示了人类生存的荒诞和困惑。
逼近或者还原生活不仅仅是哲学家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无数艺术家和文学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剥去伪装、厘清真伪、拒绝平庸、走向生活似乎成了英美当代作家自觉肩负的“文学义务”。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文学离不开生活,但怎样才能更真实地反映生活却最能体现作家个人的天赋。不同的作家对小说形式的理解完全不同,因此,可以说小说的形式从来就是开放的,是时刻都在变化的。当形式变化是不自觉地进行时,它还不会引起批评界的过分关注,但当一个作家将文学创作当作“纯粹形式上的享受”时,我们就不得不予以重视和研究了。英国当代作家B·S·约翰逊就是这样一位致力于小说“文体暴力革命”的小说家。
约翰逊出生于1933年,于1973年自杀身亡。创作生涯不过十数年,但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在几乎所有关于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中都少不了他的大名。在《小说——形式与手段》一文中,他阐述了他对生活和艺术的关系的看法,他写道:“生活并不讲故事。生活是混乱的、易变的、随意的……作家从生活中仔细地抽出一个故事,把他讲出来,这必然意味着撒谎……我对在我的小说中撒谎不感兴趣……一个作家,不论他是多么才华横溢,他现在使用这种形式(19世纪的小说形式),就是犯时代性错误,是徒劳的,离题的和反常的。”正是基于这种激进的认识,约翰逊在他出版的几部小说中,在小说形式的创新方面作了肆无忌惮的实验。《旅行的人们》共分9章,他共使用了8种风格,其中包括意识流、内心独白、日记体、书信体和一个类似电影剧本的文本。各章之间的铺陈和过渡被所谓的“插曲”取代,目的是让作家借插曲的机会,与读者讨论前面的章节,甚至与假想的反对者展开激烈争论。约翰逊认为只有这样写才能使“读者相信他正在读一本小说”。考察一下小说的起源——英美文学界认为300多年前的迪福等人创立了小说, 而欧洲大陆则认为塞万提斯开了小说创作的先河——我们不难发现,当代“实验小说”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劳伦斯·斯泰恩(1713~1768)是致力于小说文体革新的鼻祖,他的《商第传》,借用W·W·罗布森的话说,“就文体的怪诞性而言,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小说可以与之匹敌”。《商第传》中有插图,有空页,有突然中止的段落,有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与遗落段落的衔接有一套绝妙的文字游戏。《商第传》彪炳史册在于它的形式的怪诞,或者说在于它在形式上更加逼近生活的真实。本世纪英、美、法等国的先锋作家一致认为表现一个人的死亡及意识空白的最有效办法莫过于留下几页空白,而不是自以为是的虚伪描写。斯泰恩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乏狂热的崇拜者和模仿者。约翰逊受《商第传》中空页的启发,在《旅行的人们》中用灰页表示人物的睡眼状态和恢复意识知觉的前奏,用黑页表示人物死亡。他在《标准的女管家》中,将基本相同的故事让书中的9个人物各自讲述一遍,且不使读者感到腻味, 我们不得不佩服他驾驭文字的天才。福克纳在《喧嚣与骚动》中让3 个人物讲述相同的故事后,还不满意,干脆自己站出来再讲一遍。小说发表16年后,他仍然意犹未尽,索性又讲了一遍,作为附录附在另一部小说之后。由此也可以看出,英美作家在小说形式革新方面真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了。
约翰逊的《不幸者》发表于1969年,讲述的是他的好友托妮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事,属于回忆性质。从小说看,他与托尼友情甚笃,经常在一起讨论包括文学的发展和文学批评的作用在内的各种问题。这本小说引起评论界重视的并不是所谓的内容,而是它独特的形式。作者将对好友的回忆完全融入到一场足球比赛中,时而回忆,时而是激烈的球赛,过去与现在完全重叠,似乎真有一条“时间隧道”任人自由穿梭。小说中的一切都是混乱的、任意的、非理性的,甚至是“非小说的”,但却是实在的。看球的亢奋和激动与回忆的痛苦和悲伤交织在一起,读来令人百感交集。《不幸者》不是以“书”的形式出现在读者手里,因为它没有页码顺序,而是分成24份,放在一个盒子里。如果读者认为印刷者已选择了一个特别的顺序,就可以像洗朴克牌一样建立一个任意的顺序。我们姑且将之称为活页小说。
形式的随意性必然起源于意义和信仰的消解。一个作家失去了探求生存意义的兴趣后,表现自己与这个已无意义的世界的联系时就仅剩下不断变幻形式的冲动了。如果连形式也消失了,作家还会剩下些什么?如果说小说形式的变化与主题的揭示之间出现了断裂,一味追求形式的标新立异,将小说这门艺术庸俗化,是一种艺术自戕行为,那么,这完全是因为生存意义与世界意义的消失,正如约翰逊以杀死自己的方式表明他信仰的枯竭一样,小说也要以自戕的方式宣告现今世界的荒诞和晦暗!
注释:
〔1〕崔道怡等:《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册, 工人出版社,第102页。
〔2〕袁洪庚译《北回归线》,敦煌文艺出版社,1993版封底。
〔3〕〔4〕Zeitlin,Michael,The Post—Freudian Alleg olriesof Donald Barthelme,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93,No.2
标签:小说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学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艺术论文; 人物分析论文; 文化论文; 尤利西斯论文; 北回归线论文; 斯蒂芬论文; 心爱论文; 文体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