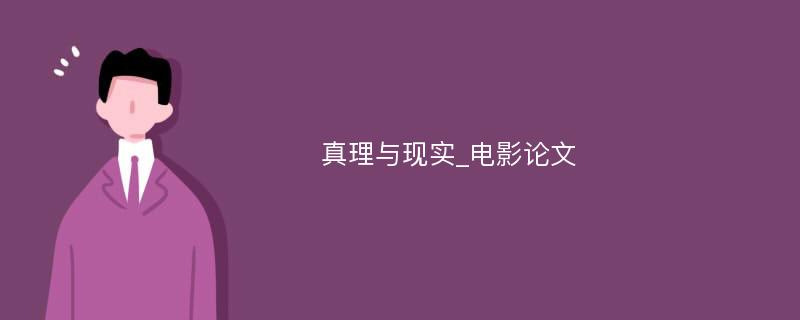
真实与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论文,真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津的电影我知道年轻人会觉得“很难看的”。因为我年轻时第一次看小津的片子是在拍《风柜来的人》的时候,我的副导给我两盒Beta录像带,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再换第二盒,怎么都一样,就放弃了,太年轻——看不进去。一直待我到了法国,《童年往事》拍完后那年,碰到马克·穆勒,他跟我说有两部片子一定要看,有小津的电影,我就去看。在戏院里面,看了《我出生了,但……》——小津早期的一部影片,非常好看,而且意义深刻。自那时起,我对他的片子才发生兴趣,后来陆续又看了—些。他的片子我比较喜欢的是《我出生了,但……》、《父亲在世时》、《晚春》、《东京物语》,分别代表他早、中、晚期的创作。以前有很多人说我的电影很像小津,在这里,借小津的形式来说说我自己的经验。
真实的表里
写实是再造真实,跟实质上的真实是一个等同的关系,它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这句话是卡尔维诺在谈到小说的形式时提及的。在谈小说的深度时他还说过,深度就在表面,深度是隐藏的。表面是文字,但我们可以从文字的结构里面看到它透露出来的蛛丝马迹,透露出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法诉清,只有身处事件中才能明白的事情。电影也一样,影像与声音呈现的是一种“表”。像小津的电影,譬如《晚春》,讲父女之间的关系,因为妈妈去世,只有父亲和女儿。父亲经人家介绍要娶另一个女人,女儿产生强烈的嫉妒,不但是嫉妒,还是一种反抗。有一场拍能剧,在观赏能剧的剧院里,女儿看她爸爸在看那个女人的时候,女儿的眼神简直要杀人了。嫁人之前女儿跟爸爸住在京都,父女住在一个房间,所以西方的解说都是父女间有一种暧昧,恋父情结。我认为不是,因为日本家庭生活里女不避男,家族里面洗澡都是一起的,和我们不一样,你不理解这个风俗你就不能理解这样的情感。西方可以是非常戏剧性的,可以一直深层到心理学的恋父情结。但小津安二郎呈现的是一个很简单的表象,所有的信息都是渐进和埋藏的。表面上很简单,让观众感觉没有什么重大的戏剧性,但是累积起来,底层便有个暗流,是惊涛骇浪的。表象所呈现的也许是相反的,就像交响乐中的赋格,音乐使用上的对位,几种乐器有不同的旋律,但是相关的,有强有弱。流行歌曲只有—个旋律,合旋是加强、渲染这个旋律,是主从的关系。赋格不是主从的关系,是平行的。在电影里就表现为表里,呈现出一种状态,在里面另有一种状态。所谓的表里,是我晚期才开始领悟到的。
我现在会喜欢某种人物关系,某种情境或某个事件,基本上它就包含了表里。我在表达上自然就做大了,而不是像编剧逻辑一样,表是呈现什么?里是呈现什么?但是布列松可能会比较清楚,难得有创作者这么清楚自己的创作意图,非常自觉,他算比较明确的。
小津的电影是反思的,看完会越想越多,因为它的底层有—个结构,是他影片的重点。譬如《东京物语》,基本上是战后整个日本的变化。人们的工作形态变了,子女进入都市工作,离父母远了,整个过程也不是小孩们不孝顺。小津呈现的其实很简单,但是看完后就会感觉很难过。在现代社会的情景之下,观众会感觉到父母和小孩之间关系的扭曲和变化,还有老夫妇战死的儿子和媳妇,媳妇就和子女之间产生一种对比,其实很复杂,但是表面上是很单纯的故事,所有的思考都在后面。小津电影的结构,看似好像都是生活片段,但其实都有非常严密的结构,就像工程师一样。比如小津的分镜表,每一个镜头,预计多长,会用多长底片,比如对白在时间里是30秒,或者1分钟,底片要用多少,都会清清楚楚地列出来,每一个镜头都是这样,在还没有开拍之前,到拍完后,这个电影有多长,和之前计算的都基本差不多。他的电影不是直接的戏剧性,不像西方的电影,看到最后都会直接告诉观众所要传达的意涵是什么,是直白的,观众可以感受到。东方的电影和小津的电影不是这样,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否则一片糊涂,也不会深邃地去想。
一般观众当然要看直截了当的电影。法国评论《海上花》说是永远发生在冲突的前面或者后面,绝对不直接描写冲突。在我看来,冲突没有什么好描写的,几下就可以拍完,但不直接,就可以拍出一种韵味。这一点,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与我的想法非常接近。换句话说,我们对电影都秉持相似的态度。这大抵也可以看成是东方人看事情的角度与习惯、表达情感的方式。
很多人说我的长镜头,就是镜头不动,然后很长。这很简单,谁都会,找到一个位置,把镜头放在那儿,让事情发生。一开始这样做,是因为当时在台湾其实没有所谓的专业演员,只有职业演员,他们那种固定的表演模式,让我很没办法。拍的时候你会发现,假使镜头太靠近,他们就会紧张;假使用轨道往前推,他们会更紧张。我只能选择这种方式,把镜头固定在一个最好的位置,如果在房间里,这个位置通常是信道,旁边有房间,可以看到窗子;也可能是客厅或者所谓的饭厅,因为有窗,景深不错,我对密闭的空间比较没兴趣。
当使用非职业演员拍摄时,就要遵照房间生活的真实动态,而不可以让演员远远地站在景深处按照剧本讲话。因此,“时间”在这种表演形态下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设定时间——上午、中午、下午……如果时间不清楚,便不可能安排演员。当导演有了一个清楚的、真实的时间观念后,便有了一个来自现实生活的依据,才能够判断影片中应该发生怎样的事情。如果违背了时间状态,就会发生所谓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基本上就是违背了现实时间的常理后,会发生什么。比方说一个小孩在本该上学的时间回家了,家中的妈妈就会很奇怪,明明是上课时间,你回来干嘛?于是妈妈就会冲过去问孩子,镜头便可以跟进房间去,有时声音还会变为画外音,那样想象空间就更大了。所以,导演要利用现实时间安排一个状态,当我在使用这种现实的真实生活状态作为依据的时候,我的电影就走向了另一个阶段。
导演一定要清楚地知道每一场戏的真实时间,如果不知道便无从依循。可以设想一下,在房间里有一场戏,某个时间,镜头一直固定在房间一角。接上一场戏,夫妻两个从外面回来,吵架的状态,这其中就会透露出一些角色的惯性与细节,比如他们在家里爱待在某个地方等,这些都是可以被使用的。所谓的戏剧性和冲突照样可以发生,但其魅力则接近现实生活。在拍片过程当中,一定要依循现实生活的逻辑。
再造的现实
我们通常是在模仿现实,再造现实。思考一场戏时,导演会有一个主观视点,就是导演自己的观点。导演会判断这样的戏和情境,它的意涵,它代表的象征意义是什么。西方电影的视点通常是全知的。全知视点其实很有力量——叙事的力量,那样的叙事等于是上帝的视点,这个人跟那个人有关系,另外那个人又跟这个人有关系,有对立两面的存在,并且有时还不止两面,有很多面,这样在叙事上是非常方便的。但我习惯的视点是跟着—个主要角色,比如跟着舒淇。我在《最好的时光》中间一段盯着女主角舒淇走,即结构和所有的场景,都不能跳开女主角,虽然很难做,但是很现实。很多电影都是运用客观的、全知的观点,而锁定—个人的视点则很少,因为限制很大,但如此的电影形式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表达形态也不一样。除了《海上花》是一个客观的全知叙事,我早期的很多片子都是盯着一个角色走的形式。虽然一部电影里角色有很多,但导演只有一个。将导演看到的、想到的结构起来,在影像的使用上其实并不难,而难点在于叙事观点。
就像我们在街上无意中听到一个声音“咔”——激烈的刹车声,你会回头看,但看到的不是撞车的那一刻,而是撞后的一系列状况,有人从里面出来,有人跑过来等,可能撞到一个小孩……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想这起车祸?只要是真实的状态,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最直接的就是表面的,你会想到一场车祸,这个司机真该死,没有人会想到背后是整个社会机制的问题。小津安二郎的电影基本上就是这样,他用的是生活中最简单的事件和元素。通常我们有个习惯,总想把这些戏剧化,冲突多一点,激烈一点,而恰恰忘了生活本身。
关于现实生活与电影真实,我们会有这种经验,比如拍吃饭。我的电影经常拍吃饭。《海上花》第一场是吃饭,我的做法是用真的酒,因为演员的水准参差不齐,有专业的、也有非专业的,所以用真酒最好。所有的菜都是主演之一高捷(饰罗老爷)做的,他曾经是一个厨师。开拍的时候菜上来都是热的,吃、划拳、喝酒……这些都可以称做是底色,要在这些之上雕琢导演要的戏。酒、饭菜都是真的,如此一来气氛便可以活起来,假使不这样做,就很难抓到吃饭的气氛。通常情况下,实拍时,气氛很容易被导演忽略。“底色”是什么?所谓底色就是一个与写实相当接近的概念。如今很多电影都“飞上天”了,写实就显得很落伍了,但其实“飞上天”,最终还是写实,写实是所有戏剧性的源头。如果违背了生活规范、社会结构,或者人们习以为常的风俗、人伦,就会跟正轨发生冲突。创作者越理解生活的底层、结构、规律和标准程序,就越容易看到戏剧性。
对我来说,最有趣的是复杂的人际关系。我的片子里大都是探讨人。至于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的批判,我不太重视,如果你要的话,只要设定角色本身的时空背景,自然就会有批判,甚至比直接批判的力量还要大。我的焦点是描述角色,让角色活起来。布列松把演员当做他的道具,来谈社会结构,或者他认为的什么。虽然我的电影很多是讲人生的苍凉,但那不意味我的人生观就是“痛苦即人生”。人生最有味道的时刻是人困难的时候,这也是人生最有力量的时候。所以我的片子基本上都是给自己找困难,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这不是痛苦,我一点也不痛苦。在那儿对抗,我才感觉是活着的,才是过瘾的。这就是我喜欢研究人的原因。
所以角色是最重要的,我可以拍各种各样的人,只要我有兴趣,只要我看到一个人有意思,就会好好研究这个人,然后把他/她变成角色。只要角色是活的,那么演员说什么都没有问题,因为他/她扩散出来的能量是很大的。演员跟导演合作,导演有责任把演员带上一个新的阶段,即便那个演员是一个自觉的创作者,导演都应该帮演员把他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在现场拍戏,演员最大,做导演的绝对不可以骂演员,骂了也是导演自己倒霉,因为导演的想法、感觉是要靠演员来传达的,所以挑选演员很重要,挑错了,就要自己扛下来。
从小津或是我的电影来看,我们处理演员的方式不太一样。一般情况,大家习惯是抓住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戏剧性很强,但仔细一看,其实不对,一点也不真实,角色没办法活起来。角色要活是不容易的。在对白使用上,我绝对不要传达强烈戏剧性的对白,我使用的是生活中的对白,所以我让演员不要对白,在规定情境中自由发挥。对白一定要符合真实性,所谓真实性就是时间。你要这个演员说对白,你需要帮他挑时间,要安排一个情境。拍之前,我一般不会要他们怎么准备,那是演员自己的事。舒淇拍《千禧曼波》的时候,我知道她压力很大,因为戏的张力很大,我通常都是下午才开工,让她可以有时间运动,绝对不会超过晚上11点就让她收工了。所以,她每天都是精神饱满地来拍,要不她没有那个能量来对抗。梁朝伟喜欢看书,只要丢本书给他,让他看就可以了。梁朝伟怎样演《阿飞正传》?他每次就是别的戏收工,到这个现场来睡,王家卫等他睡不理他,起来以后化妆开始。他演的是赌徒,他请教过赌徒。赌徒的手都很漂亮,常常都要修。他醒来后,化妆就修指甲,通过修指甲的形式开始进入这个角色。
我计较的、在乎的基本上都是以上这些东西。
在小津的电影里面,演员永远是那些演员,相互之间调换一下,并且大概拍来拍去都是家庭。比如出嫁,演爸爸的永远是那个人,他从年轻一直演到老,从爸爸在世一直演到老死。就是固定的那几个人……永远不变,为什么?演爸爸的演员也出去演过别的导演的戏,但没有在小津的电影里演得那么好,因为他在小津电影里,父亲就是那个样子的,完全符合他心目中父亲的形象。还有,他绝对不会乱演,也没有什么表情的。在小津看来,表情多的是动物园里面的猴子。因为在电影画面里,有演员的每一个画面,其表情、神情太多会干扰到其他,会干扰叙事的脉络,所以演员的表情是比日常生活中更少的。布列松电影里演员的表情就更少了,甚至少到没有。所以布列松说人是道具、人模。小津如此做,是因为那其实是某种真实,写实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我要告诉你们的其实是我自己的某种经验,这也是所谓的电影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但是,我劝你们以后还是从戏剧叙事结构开始,不要一下子就学我这样,我也是慢慢来的。
(整理:郑慧懿 罗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