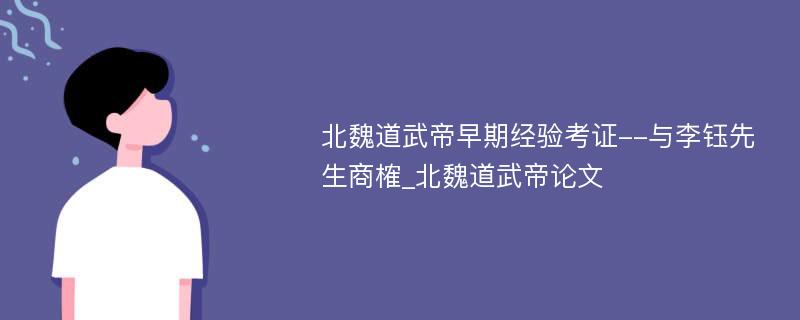
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辨——与李凭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魏论文,早年论文,武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武帝拓跋珪是北魏王朝的创始者,对于北魏王朝的建立与发展可谓居功至伟,但其早年经历因文献记载的阙略而显得扑朔迷离。近来,李凭先生推出了《北魏平城时代》一书,该书用相当大的篇幅对道武帝拓跋珪的早年经历作了十分详尽的考述,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与解释。(注:参见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一章第一节《道武帝早期经历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李凭先生早在《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就发表了《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考》一文,内容与《北魏平城时代》所述完全一致。不过,本文所引用的李凭先生的观点依然以《北魏平城时代》一书为准。)笔者喜读《魏书》,对北朝史事兴趣很浓,然细读过李凭先生此书后却认为,他关于上述问题的讨论与判断存在明显的缺陷,立论难以让人信服,不仅没能在前人论述基础上有所突破和补正,反而有可能引起更多的误解。故略抒管见,以就教于李凭先生与学界同好。
一、代国覆亡真相与什翼犍之死
拓跋珪为拓跋什翼犍之子拓跋寔的遗腹子,生于代国建国三十四年(371)七月七日,《魏书》纪传记载十分明确, 研究者对此也无丝毫的疑问。学者们的分歧开始于对代国亡国史实的认定。因此,欲彻底理清道武帝拓跋珪的早期经历,必须从其幼年所遭遇的代国覆亡事件说起。拓跋什翼犍无疑是代国最重要的君王,在位将近40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代国的历史也就是拓跋什翼犍统治的历史。根据《魏书》纪传的记载,代国亡国的史实应当是相当清楚的,并没有多少悬念存在。如《魏书·序纪》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建国)三十九年,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冬十一月,白部、独孤部御之,败绩。南部大人刘库仁走云中。帝复遣库仁率骑十万逆战于石子岭,王师不利。帝时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复度漠南。坚军稍退,乃还,十二月,至云中,旬有二日,帝崩,时年五十七。”
表面看来,代国的历史随着什翼犍之死戛然而止,什翼犍的猝死成为代国灭亡的关键因素。其实,导致什翼犍猝死及代国覆灭的罪魁祸首,应为在国难之时发动叛乱的拓跋寔君。寔君是什翼犍的庶长子,《魏书·昭成子孙列传·寔君传》十分清晰地记述了这次叛乱的经过:当时,“太祖(拓跋珪)年六岁,昭成(什翼犍)不豫,慕容后子阏婆等虽长,而国统未定”。在拓跋斤的挑唆下,寔君发动叛乱,“乃率其属尽害诸皇子,昭成亦暴崩”。当时苻坚的军队并未退走,驻扎在君子津(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黄河边)附近。叛乱爆发后,“诸皇子妇及宫人奔告苻洛军,坚将李柔、张蚝勒兵内逼,部众离散”。代国就此宣告彻底灭亡。寔君与拓跋斤的图谋终究也没有得逞,最后被苻坚处决于长安。《魏书》卷14载:高凉王拓跋孤之子拓跋斤“失职怀怒,构寔君为逆,死于长安”。可见,什翼犍死于寔君叛乱,代国亡于寔君叛乱,应该是言之有据的。
但南朝史籍如《宋书》、《南齐书》等对代国灭亡史实的记载却与《魏书》有很大的出入。如《宋书·索虏传》称:什翼犍“其后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鞬(同犍)死,子开字涉珪代立”。《南齐书·魏虏传》则云:“太元元年,苻坚遣伪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龙庭,禽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将这两段记载与《魏书》纪传内容相比较,不难发现彼此最明显的差别有两点:一是两部史书均认定什翼犍在代国灭亡时没有死在塞北,而是被俘进入长安。至于后事就不得而知了。二是两部史书均指明拓跋珪为什翼犍之子。而在这两点分歧上,无疑都以《魏书》的记载为正确无误,如王仲荦先生就在中华书局版《宋书》校勘记中明确指出:“按据《魏书·序纪》,什翼鞬为苻坚将苻洛所破后,旋为其庶长子寔君所杀,未尝执送长安。拓跋珪为什翼鞬之孙,亦非什翼鞬子。”(注:《宋书》卷95校勘记。本文所用正史及《资治通鉴》均用中华书局校勘本。)
但是,成书于唐代众史官之手的《晋书》非但没有纠正上述两处失误,而进一步引发了新的分歧。如《晋书·苻坚载记》载:“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洛等振旅而还,封赏有差。坚以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紧接着,《晋书·苻坚载记》还生动地记录了苻坚与什翼犍在太学中的一段对话。正如王仲荦先生已指出的那样,如果不能提出强有力的理由反驳《魏书》的记载,我们就应该承认什翼犍死于寔君之手,没有前往长安。此外,如果说《宋书》与《南齐书》将拓跋珪当做什翼犍之子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晋书》继续将拓跋珪称为什翼犍之子,实在荒唐可笑。不过,《晋书·苻坚载记》最荒唐之处表现在编造出“翼圭缚父请降”的情节,须知,各种史料毫无疑义地证明,拓跋珪当时年仅6岁。
然而,李凭先生在复原代国亡国史实时,却轻视《魏书》纪传系统而明确的记载,对寔君叛乱事件轻描淡写,专用上述《宋书》、《南齐书》、《晋书》等三部史书中抵牾丛生的记述。面对这些记载中的荒唐之处,李先生尽力为之辩解。如在解释所谓拓跋珪 “缚父请降”的问题上,李先生虽反复强调其有悖常理,但仍不肯放弃,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代人受过的观点。李先生在书中指出:“从三个方面来看,只有(皇太后)贺氏才应该是以道武帝的名义去绑缚什翼犍投降前秦的‘罪人’。”这三个方面是:其一,贺氏是道武帝的生母;其二,贺氏已上嫁什翼犍,能够找到发难的机会;其三,贺氏身后有一支可以发难的力量,即贺兰部。(注:参见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141—149页。)而对于贺氏发难的原因,发难的过程以及为什么要以道武帝的名义去发难,发难以后如何绑缚什翼犍投降前秦等等最关键最根本的问题,李先生却因史料阙如而无法回答。这种解释因此显得未免过于牵强。让笔者感到费解的是,李先生在书中也曾专门引述《魏书·昭成子孙列传·寔君传》的内容,却对其中“昭成(即什翼犍)亦暴崩”的记载视而不见。
另外,代国亡国后,前秦确曾强徙代国皇族人员及大臣进入长安。唐李延寿曾指明:“昭成皇帝九子:庶长曰寔君,次曰献明帝,次曰秦王翰,次曰阏婆,次曰寿鸠,次曰纥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注:《北史》卷15《魏诸宗室传》。)献明帝与秦王翰早死,阏婆、寿鸠、纥根、地干、力真等人极有可能死于寔君叛乱中,而寔君是被苻坚迁入长安后处决的。因此,笔者以为,在什翼犍诸子中,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幼子窟咄的行踪。窟咄在寔君叛乱中幸免于难,但被强徙进入长安。“昭成崩后,苻洛以其年长,逼徙长安,苻坚礼之,教以书学。”(注:《魏书》卷15《昭成子孙列传·窟咄传》。关于窟咄迁往长安的记载,还见同书《莫题传》以及《北史》卷15《魏诸宗室传》。)如果说拓跋氏皇族中有人进入长安太学习礼攻读的话,那么就非窟咄莫属。司马光推绎出的正是这种观点,《资治通鉴》卷104 《晋纪二十六》孝武帝太元元年云:“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长,迁之长安。坚使窟咄入太学读书。”
然而,李凭先生坚信《晋书》的记载,坚信什翼犍没有被寔君所杀,而是被俘进入长安,并进入长安太学进修。他在书中指出:“苻坚将什翼犍送进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中去学习,使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位‘荒俗’的君主倒也没有辜负苻坚,在学习文化上表现了积极的进取之心。可惜,他没等回到代北就去世了。”(注: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33—34页。)这可以说完全是依据《晋书》记载所发挥的想象。我们且不说这种想象根本没有其他资料的佐证,单就当时什翼犍本人的实际情况来说,也属子虚乌有之事。一方面,什翼犍在位近40年,代国灭亡之时,他已有57岁。在“漠北人噉牛羊而人不寿”(苻坚语)的时代,这样的年龄无疑是子孙成群的爷爷辈的老者了,让这样一位年近花甲的老者进入太学重新学习,是难以想象的。况且,代国当时的节节败退与什翼犍不良的健康状况有很大关系,寔君等人也正是乘什翼犍身体“不豫”的机会发动叛乱的。著名学者蒋福亚先生在《苻坚灭代》一文中也否认什翼犍被执的说法,精辟地指出:“苻坚虽然崇尚儒学,但把重病染身,年近六十的老翁送入太学习礼,之后还有问学等事,方之情理,实难讲通。苻坚灭代后,被当作人质留居长安并入太学的倒确有其人,这就是大乱之后什翼犍诸子中仅存的少子窟咄。”(注:《北朝研究》1990年下半年刊(总第3期)。 )也许是因为蒋先生的论列过于简约,没有引起其他学者(包括李凭先生)的注意。
另一方面,什翼犍绝非是《晋书·苻坚载记》所云“未参仁义”的“荒俗”之人。理解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我们了解一下什翼犍本人的早年经历便可明白。在拓跋鲜卑早期发展史上,诸部的斗争非常激烈。为取得后赵国石勒的支持,什翼犍曾作为质子,居留于后赵襄国(今河北邢台市)及邺(今河北临漳县临漳镇)等地,时间长达10年之久。襄国与邺都是后赵国非常重要的中心城市,什翼犍在此深受中原汉文化的熏陶。后来他在拓跋孤等人迎请下,回代国即位,时年19岁。笔者以为,在后赵国的10年时间,才应该是什翼犍学习中原汉族文化的好时机。他即位后不久便着手汉化改革,如始置百官,商议定都灅源川等等。在什翼犍重用的官吏中,燕凤与许谦是最出名的。更值得注意的是,什翼犍还命燕凤与许谦共同教授献明帝(即拓跋珪之父)学习汉文经籍。这当然都是富有远见的举措,与日后北魏皇族接受汉文化的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代国的文化水准与前秦相比肯定有较大的差距,不过,将什翼犍这样颇有作为的“雄杰之主”简单斥之为“荒俗”,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注:关于什翼犍的评价,可参看何德章:《鲜卑代国成长与拓跋鲜卑初期汉化》,《北朝研究》1993年第2期。)
二、拓跋珪是否到过蜀地
代国败亡后,苻坚等人曾有意将拓跋珪也迁往长安,但在燕凤的机智化解下,才侥幸逃脱。这一点在《魏书》中的《太祖纪》、《燕凤传》中都有清楚的记述。道武帝能侥幸逃过此劫,与前秦对代国遗众的安置策略有着直接的关系。攻灭代国后,如何管辖代国遗众及塞北地区,是前秦统治者面临的一个棘手难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防止该地区出现新的割据势力。为此,苻坚与苻洛等人经过深思熟虑,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主要采纳了代国旧臣燕凤的计策。燕凤建议的核心便是分而治之,即把代国所辖部众分成两部,让刘库仁与刘卫辰各领一部。“两人素有深仇,其势莫敢先发。此御边之良策。”然而,两部争斗之余,终有彼消此长的趋势,任何一方强大起来,对于前秦来说都非常不利,为此,燕凤计策中更妙的一着还在于保留年幼的拓跋珪。这样便在两方分立中,加入了第三种势力。拓跋珪作为已故代王什翼犍的嫡孙,具有刘库仁与刘卫辰都无法具备的血统优势。“俟其孙稍长,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继绝之德于代,使其子子孙孙永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边之良策也。”(注:《资治通鉴》卷104 《晋纪二十六》孝武帝太元元年。笔者以为《资治通鉴》在转述燕凤之言时,较之《魏书·燕凤传》有所引申,有画龙点睛之效。)
扶立幼主,历来是控制附庸国的重要手段,虽然有意一统天下的苻坚不希望这样做,不过,为牵制二刘势力,也不得不采纳这样的策略。平心而论,燕凤提出的建议虽有袒护拓跋珪的嫌疑,但不失为当时稳定塞北地区的上策——苻坚等人绝不是愚昧可欺之辈。很显然,在短时间内,冲幼而无实力的拓跋珪根本无法对前秦统治构成威胁。不过,前秦统治者在容忍拓跋珪留在塞外的同时,仍然毫不犹豫地将什翼犍的幼子窟咄及代国旧臣燕凤、许谦等人迁入长安。事实证明,苻坚等人采取的措施确实为拓跋珪的复国行动设置了重重困难,拓跋珪为此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
根据《魏书》、《北史》等文献的记载,道武帝拓跋珪在即位之前,并没有离开过塞北,先后在独孤部与贺兰部避难。当时有不少代国旧臣始终跟随拓跋珪,如《魏书·李栗传》载:“初随太祖幸贺兰部,在元从二十一人中。”(注:张金龙先生曾对“元从二十一人”进行了详细的考订,见其《拓跋珪 “元从二十一人”考》一文,《北朝研究》1995年第1期。 )又同书《长孙肥传》载:“太祖之在独孤及贺兰部,肥常侍从,御侮左右,太祖深信仗之。”《穆崇传》又载:“太祖之居独孤部,崇常往来奉给,时人无及者。”《叔孙建传》也载:“建少以智勇著称。太祖之幸贺兰部,建常从左右。”经过10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拓跋珪于登国元年(386 )正月于牛川(今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境内塔布河)即代王位。拓跋珪即位之初,曾有两个人对其王位构成严重的威胁,他们就是刘库仁之子刘显与拓跋珪本人的叔父窟咄。
在二刘(即刘库仁与刘卫辰)的较量中,刘库仁部逐步占据了上风。在一场决定胜负的大战中,刘库仁挥师“追至阴山西北千余里,获其妻子,尽收其众”。(注:《魏书》卷23《刘库仁传》。)到刘库仁子刘显统领部众时,“地广兵强,跨有朔裔”,(注:《魏书》卷24《张兖传》。)成为拓跋珪即代王位后最有力的竞争对手。对拓跋珪王位的又一个致命威胁,便是那位长期居留于长安的季父窟咄。窟咄在苻坚的关照下,入长安太学学习,前秦灭亡后,窟咄随慕容永率领的西燕军队离开长安。慕容永定都长子,而窟咄被任为新兴(治今山西忻州市)太守。刘显与拓跋珪争战失利后,便派人迎请窟咄回到塞北。这一举动在当时塞北引起极大震动,史称“窟咄之难”。论年龄与辈分,窟咄都比拓跋珪更有资格就代王之位。莫题等人甚至讥拓跋珪 “三岁犊岂胜重载”。(注:《魏书》卷28《莫题传》。)当时人心浮动,内乱一触即发。拓跋珪在万般无奈之下,又匆忙北逾阴山,奔至贺兰部避难,同时派使者求救于慕容垂部。
《南齐书·魏虏传》载:“坚败,子珪,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后稍强盛。”拓跋珪与慕容氏后燕的关系非同寻常,故有专门讨论的必要。高湖曾对慕容垂说:“魏,燕之与国。彼有内难,此遣赴之;此有所求,彼无违者。和好多年,行人相继。”(注:《魏书》卷32《高湖传》。)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因同文同种的关系,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频繁的通婚便是他们加强彼此联系的重要手段。如什翼犍便两度纳前燕慕容皝之女为妃。而什翼犍也以其兄翳槐之女嫁与皝。慕容儁、慕容玮在位之时,也与代国往来密切。早在代国败亡之前,前秦就出兵攻灭了前燕,慕容氏王族及数量惊人的鲜卑人被强徙入关中。而早在前燕覆灭之前,慕容垂已投靠了苻坚。慕容垂于太元十一年(386)于中山即燕王位,建立后燕。 而正在同一年,拓跋珪也在旧臣的拥戴下,即代王位。不可否认的是,在拓跋珪即位后,慕容垂确为保住其王位出力不少。如“窟咄之难”中,正是慕容垂派慕容贺驎率兵相救,后来,也正是在慕容垂军队的协助下,拓跋珪才最终打垮了他的死敌刘显。
不过,代国与后燕之间的特殊关系并不能作为证明拓跋珪曾依附于慕容垂的证据。下面两桩事例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佐证。拓跋仪于登国三年出使后燕。慕容垂曾责问拓跋珪不亲自前来的原因,拓跋仪回答说:“先人以来,世据北土,子孙相承,不失其旧。乃祖受晋正朔,爵称代王,东与燕世为兄弟。仪之奉命,理谓非失。”(注:《魏书》卷15《昭成子孙列传·仪传》。)继拓跋仪之后,拓跋觚也曾出使燕国,不幸被强制扣留下来,被软禁长达六七年,直到皇始二年(397)被慕容普驎杀害。拓跋觚在后燕国内拥有很高的声望。 在长期软禁期间,“觚因留心学业,诵读经书数十万言,垂之国人咸称重之”。(注:《魏书》卷15《昭成子孙列传·觚传》。关于拓跋觚的身份,唐长儒先生认为“当时献明太子拓跋寔死后,贺氏收继为(拓跋)翰妻所生”。见中华书局版《魏书》卷15校勘记。笔者认为唐先生的考定是十分精当的。)《魏书·叔孙建传》也载:“随秦王觚使慕容垂,历六载而还。”在塞北部族争战中,慕容垂支持鲜卑族兄弟拓跋氏,但慕容垂也不可能容忍代国的壮大,如果拓跋珪落入慕容垂之手,定会“奇货可居”,恐怕不会轻易逃脱其控制。另外,容易引起误会的还有窟咄等人的行迹。前秦覆灭后,窟咄跟随慕容永离开长安,后被任命为新兴太守。慕容永西燕政权最后被慕容垂消灭,国内鲜卑部众也由此被迁往河北。
李凭先生依据《晋书·苻坚载记》的一条记载,认定拓跋珪曾被迁至长安,后又被迁往蜀地;又根据《南齐书·魏虏传》的说法,认定拓跋珪曾经跟随慕容垂居留于中山。其实,李凭先生的论证途径是相当冒险的,因为他在为某一条记载苦苦寻找旁证的时候,却忽视了这条记载与其他多种记载之间的矛盾冲突,如果不能解释这些矛盾冲突,他的立论就无法站住脚。拓跋珪先后在刘库仁部(包含独孤部)以及贺兰部避难的经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魏书》纪传中找到多条相互衔接,互为印证的资料。除前面引述的资料外,又如《魏书·刘库仁传》载:当时,“自河以西属卫辰,自河以东属库仁。于是献明皇后携太祖及卫、秦二王自贺兰部来居焉。”《贺讷传》载:“昭成崩,诸部乖乱,献明后与太祖及卫、秦二王依讷。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于是太祖还居独孤部。”《安同传》载:苻坚曾将公孙眷之妹赐给刘库仁,“(安)同因随眷商贩,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我们当然不能轻易地将这些记载全数认定为魏收的编造。
李凭先生在书中想方设法地将所谓拓跋珪 “迁长安”与“迁蜀”的经历填补在记载阙略的时间段上。其实,这种努力也是行不通的。关于道武帝这段经历,李先生考定的结论是:拓跋珪等人在淝水之战前即从蜀地返回长安,依附于慕容垂。太元八年十二月后随慕容垂到中山,而重返代北的时间不早于太元十年八月。(注:详见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28—31页的论证。)笔者认为,确定拓跋珪是否迁往蜀地的一个关键,就在于确定他是否到过长安。假定拓跋珪曾迁居长安,那么,就必须拿出有力的证据与合乎情理的推论,并为其找到返回塞北的时机与途径。如果无法证明拓跋珪有曾在长安居留的迹象,或返回塞外的合理途径与机遇,那么“迁蜀”之事便成了无根之谈。
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治局势的一个转变发生在前秦军队在淝水之战惨败之后。而在此之前,前秦国势处于鼎盛时期,假如拓跋珪曾因罪被强制迁往蜀地,苻坚等人为何会让其随意返回长安,并依附于慕容垂的麾下?观《晋书·慕容垂载记》,慕容垂在投奔前秦后,屡屡受到王猛等前秦大臣的猜忌与排挤,如果慕容垂有扶持羽翼的野心,王猛等人岂能轻易放过?故而李凭先生提出拓跋珪等人淝水之战前就到长安投奔慕容垂的推断实在令人费解。在太元八年淝水之战后,慕容垂起初仍抱观望态度,但即使是将手下军队交付苻坚后,仍遭到苻坚君臣的猜忌。苻坚虽然违心地允其返回河北,但对他并不放心,“遣将军李蛮、闵亮、尹固帅众三千送垂。又遣骁骑将军石越帅精卒三千戍邺,骠骑将军张蚝帅羽林五千戍并州,镇军将军毛当帅众四千戍洛阳”。(注:《资治通鉴》卷105《晋纪二十七》。)很明显, 在慕容垂返回河北之初,整个长安及河北的控制权仍暂时掌握在苻坚与苻丕父子手中。又如苻丕派遣慕容垂平定翟斌叛乱时,便大有渔翁得利之意,仅“以赢兵二千及铠仗之弊者给垂”,还使苻飞龙率领一千名氐族骑士随从监视。(注:参见《资治通鉴》卷105《晋纪二十七》。 李凭先生在《北魏平城时代》一书中强调慕容垂在淝水之战失败后的当月就摆脱苻坚控制(第28页),不知有何根据。)在苻坚父子及群臣的猜忌与监视下,与慕容垂有姻亲关系的拓跋珪及其随从能与慕容垂始终同行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当时塞外的刘库仁部倾向于苻坚,站在慕容垂的对立面。在慕容垂围攻邺城之时,刘库仁在军事进攻取得初步胜利后,又招集雁门、上谷、代郡等三郡兵马向河北进发,支援河北地区的前秦军队,结果,在繁畤(治今山西浑源县西南)被寄居在当地的慕容文等人杀死。如果拓跋珪一直跟随慕容垂,并由慕容垂派回塞北,刘库仁岂不成为欺君犯上的罪臣与死敌,但《魏书·刘库仁传》却称赞他“尽忠奉事,不以兴废易节,抚纳离散,恩信甚彰”。
拓跋珪 “迁蜀说”的又一个有力反证,便是拓跋珪等与其叔父窟咄的关系。长安局面的完全失控是在慕容泓与慕容冲分别率领鲜卑族众起兵反秦之后。鲜卑人围攻长安,双方僵持长达一年之久。最终慕容冲取得主动权,在长安建立西燕政权。随后,鲜卑族众在慕容永等人的率领下离开长安东迁进入山西境内。就族类及戚属关系而言,如果拓跋珪此时身在关中,理应参加慕容鲜卑反叛的行列。其叔父窟咄就是在这时依附于慕容永并随之离开长安的。无论拓跋珪等人当时迁居蜀地,还是返回长安,理应与其叔父窟咄患难与共。而事实上,我们在文献中难以找到任何证明这对叔侄共赴危难的蛛丝马迹,反之,当窟咄随慕容永等人离开长安之时,拓跋珪已在牛川即代王位了。
拓跋珪不曾迁居长安的另一明证是他反感“羌俗”。李凭先生在书中指出:拓跋珪 “特别是居留于长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受到了汉文化的浓厚熏染,并结识像慕容垂这样汉化程度很深的鲜卑贵族,所以才会对汉文化相当倾慕,相当熟悉”。(注: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36页。)事实并非如此简单。道武帝即位之初,并不特别欣赏儒家文化。如贺狄干本是拓跋珪即位时的重要支持者。拓跋珪曾派遣贺狄干前往长安,有意与姚苌联姻,结果正遇姚苌去世,姚兴将贺狄干强留下来。“狄干在长安幽闭,因习读书史,通《论语》、《尚书》诸经,举止风流,有似儒者。”这本来是积极汉化的典范,没想到却招来杀身大祸。“及狄干至,太祖见其言语衣服,有类羌俗,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注:《魏书》卷28《贺狄干传》。)如果拓跋珪曾在长安长期居留,并喜好汉文化,那么,他对贺狄干的转变应该称赏有加,何以如此厌恶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呢?
拓跋珪早期对于官制的态度,也颇能说明问题。拓跋珪即位之初,代国仍沿袭游牧部落制度,一直到皇始元年,才“始建曹省,备置百官”,而这已是他即位10年之后的事了。另外,在官位名号上,拓跋珪力求质朴之风。“初,帝欲法古纯质,每于制定官号,多不依周、汉旧名,或取诸身,或取诸物,或以民事,皆拟远古云鸟之义。诸曹走使谓之凫鸭,取飞之迅疾;以伺察者为候官,谓之白鹭,取其延颈远望。自余之官,义皆类此,咸有比况。”(注:《魏书》卷113《官氏志》。)这难道不是长期在塞北生活的影响吗?
三、《魏书》之价值应予肯定
李凭先生关于道武帝早年经历的论述,其核心观点并不是他本人的发明,而主要是受到周一良先生观点的启发,或者是为周一良先生的观点作进一步的阐发与论证。周一良先生是公认的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权威学者,其观点理应受到重视,但尊重前辈学者观点与实事求是地论证学术问题并不矛盾。笔者以为,周一良先生对道武帝的早年经历并没有作过详细的论证,只是在讨论崔浩国史案问题时作了一个极具探索性的推断。但通过李凭先生的反复论证后,恰恰证明这种推断最终是难以成立的。其症结便在于这种推断对《魏书》的史料价值没有充分予以重视与肯定。
这一推断的逻辑关系是这样的:周先生认为崔浩被杀是因为其负责修撰的《国史》“备而不典”,暴露了拓跋氏皇族早年的“丑事”与“耻辱”。而什翼犍被俘至长安及拓跋珪迁蜀等史实,“对于拓跋氏而言,则为屈辱可耻之记录”。崔浩被杀后,北朝史书均被删改过,魏收在撰修《魏书》时,基本因袭这些史书内容,同样抹去了昭成被擒入长安及道武帝流放至蜀等事。(注: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书〉札记》之“崔浩国史之狱”,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6页。)基于周先生的这一推断,李凭先生在书中进一步解释道:“由于国史之狱的缘故,史臣不敢直书,致使北魏前期的历史记载之中疑窦丛生,《魏书》中有关代国灭亡前后的历史更是颇多讹舛。因而,《晋书》等南朝史籍中的敌国传闻反较《魏书》可信。周先生并以《晋书》为据,补以《宋书》、《南齐书》等史籍,揭示了拓跋部败亡以后什翼犍被迫内徙长安,道武帝因执父不孝而被流徙蜀地……从而,廓清了代国历史上的一团迷雾。”(注: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22页。)
在这里,有必要申明两点:首先,关于崔浩国史之狱问题的讨论目前在学术界仍见仁见智,尚无最终定论。(注:参见刘国石:《近20年来崔浩之死研究概观》,《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9期。 )例如有关魏收与《魏书》的评价,当属周一良先生所著《魏收之史学》一文最为详备。笔者认为,这篇先生自谦写于燕园学生宿舍的长篇论文,迄今为止仍是关于魏收及《魏书》研究最全面、最公允的经典性成果。不过,周先生的部分观点前后有较大的转变。如周先生曾指出:“且诛戮(崔浩)之后,不闻有命禁浩书或毁所刊石,是以知崔浩之史固未尝废,魏收得根据之,而浩之获罪别有故,亦不以修史也。”(注:周一良:《魏收之史学》,《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此书时,这篇文章并没有任何的更正与注释。)这与李凭先生所引述的周先生的看法是存在矛盾的。笔者恰恰以为周先生的早期观点是审慎而极为精辟的。在没有取得确实的证据之前,贸然判断《魏书》关于代国灭亡前后的历史不可靠,显然是难以服人的。因为崔浩国史之狱的发生,就对《魏书》中明确的记载满腹狐疑,进而将《宋书》、《南齐书》、《晋书》的零星记述奉为圭臬,甚至竭力为其中错谬与荒唐之处寻找根据,作为反驳《魏书》记载的依据,这本身就有矫枉过正之嫌。
其次谈谈“敌国传闻”。“敌国传闻更加可信”,这种观点乍听之下,似乎有些道理,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李凭先生也承认:“敌国传闻,粗略与歧异之处是难免的。”(注: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第24页。)如果说《魏书》与“敌国传闻”都有不足之处,就应等量观之,以公允的态度加以客观分析,而不应厚此薄彼,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魏书》。在代国史问题上,能称得上“敌国传闻”的南方史籍,只有《宋书》与《南齐书》。而这两部史书的有关记述极为简约,尤以《宋书》为甚。应该承认,严肃的史家在无从查考的情况下,将传闻写入史书,一般都经过较为仔细的斟酌与比较,因此,记载中“敌国传闻”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子虚乌有的捏造。但我们对其固有的缺陷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口耳相传的结果必然会使传闻的内容产生一些讹误与变异。我们在传闻中可以看到某些事件的踪影,但其中的地点、人物就往往张冠李戴了。南方史籍关于代国历史的传闻正是如此。前秦军队攻灭代国之时,什翼犍被其庶长子寔君杀害,又有一批代国人被迁往长安,包括什翼犍幼子窟咄。窟咄还被送入太学读书。南方人士并不清楚当时这些事变的细节,然而这方面的零星消息仍不断地传入南方人士的耳中,但这些消息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异与杂糅。于是在以后史官的笔下,本已花甲之年的什翼犍不但没有死于叛乱,反而代替窟咄进入长安太学学习,年仅6 岁的拓跋珪又取代寔君成为“缚父请降”的罪人。明明是窟咄先入长安,后依附慕容永,并想重返代北争夺王位,在传闻中,这些事迹的主人又变成了拓跋珪。
诸部史籍记载中,引起误解最多、内容最为失真的是《晋书·苻坚载记》,而其作者的失误也是最难以宽恕的。很显然,《晋书》根本不是什么“南朝史籍”,它的修撰时间在贞观二十年到二十二年(646—648)之间,是唐朝一统天下之后,其距《宋书》、《南齐书》以及《魏书》的撰修,至少也有上百年的时间。当时南北朝史籍及文献留存相当丰富,《晋书》撰著者大有比较选择、去伪存真的客观条件。可是,《苻坚载记》的作者竟根本无视《魏书》等北朝史籍的存在,完全信从南方文人所记下的传闻之说,连“拓跋珪为什翼犍之子”这样的错误都不能更正与说明,更记下了拓跋珪 “缚父请降”的荒唐传闻。这也许正应了当时人对《晋书》的批评意见:“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注:转引自中华书局编辑部:《晋书·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74年版。)
与《晋书》记载形成鲜明比照的,便是《南史》、《北史》及《资治通鉴》等典籍作者们的态度。李延寿完成《南史》、《北史》的时间要晚于《晋书》,但在代国史的记载上,却完全依据《魏书》的记载。周一良先生曾十分精辟地指出:“《北史》事实论赞大抵全取《魏书》,惟略有删削,极少改易增添。固是延寿年代稍晚,文献难征,然《南史》与宋、齐诸书颇有出入,苟收书芜秽太甚,延寿必大有改易。乃《北史》删《魏书》者十之一,袭《魏书》者十之九。于以知魏收之书详略得当,近于实录,而《北史》之删削翻有过简,致令史实不明者焉。”(注:周一良:《魏收之史学》,《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269—270页。)当时李延寿所能利用的北朝史方面的参考文献,并不止魏收《魏书》一种,也肯定看到了《晋书》这部同朝史官撰写、太宗李世民御撰史论的史书,也肯定了解不少代国历史的“传闻”,但这一切都没有丝毫影响到他利用《魏书》的成果。李延寿如此,一代史学巨匠司马光也是如此。在《资治通鉴》关于代国历史的记载中,司马光叙述的依据也主要来源于魏收的《魏书》。司马光也不可能没有看到《宋书》、《南齐书》及《晋书》与《魏书》相歧异的记载,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司马光判断的眼光与取舍的正确性。
毫无疑问,学术的进步在于创新,但新观点必须建立在更加详实的证据与更加缜密的推理之上。笔者以为,在道武帝早年经历问题上,《魏书》的相关记载指认明确,论列系统,并不存在过多悬念及抵牾之处。李凭先生提出的证据与所作的论证尚不足以推翻《魏书》纪传记载的可靠性,他提出的观点作为基本人的推测与假设似乎无可厚非,但面对众多与之相矛盾抵触的例证,要想成为一种全新的结论,尚不足让人信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推敲。
标签:北魏道武帝论文; 晋书论文; 北魏论文; 武帝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宋书论文; 北史论文; 魏书论文; 慕容垂论文; 慕容冲论文; 魏晋南北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