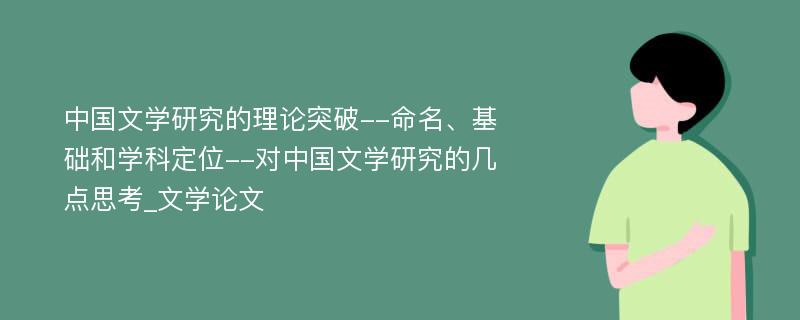
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突围——命名、依据和学科定位——关于华文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学科论文,几点思考论文,理论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肯定和质疑
学术自审是一个学科走向成熟的必经途径。
如果我们把1982年6月,由广东和福建七个单位联合发起在暨南大学召开的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注:最初联合发起召开第一届香港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的七个单位是:暨南大学中文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华南师院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台港文学研究会、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看作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由个人行为走向学科建设的开始,那么,20年后,我们重返暨南园,来举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成立大会,则意味着这一学科经过20年的努力,已经初具规模并正逐步为社会和学界所接受。较之20年前,我们看到,这一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包括老中青不同年龄层次和知识背景的学术梯队;对学科所涵括的“空间”(范畴)的差异性,及其性质和特征,有了基本的认识、限定和规范;对这一领域繁富的相关资料,有了初步的积累和梳理;在这一基础上,推出了一批从作家、作品、思潮、流派的专题研究,到带有整合性的文学史书写的学术成果。没有20年来这一不止一代人的学术积累,世界华文学作为一个新的学科为社会所接受,将是不可能的。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华文文学研究比较于其他传统学科,还只是初步的,幼稚和不成熟的。一个值得研味的偶合是,当人们在肯认华文文学的同时,一篇由汕头大学四位学者连署的全面质疑20年来华文文学研究的长文,在《文艺报》华馨版上加了按语发表,(注:文艺报2月26日吴奕錡、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的文章《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它几乎成为20年来没有多少争论热点的华文学界反响最为强烈的一个学术事件。尽管对该文的许多判断和立论,我难以苟同(注:参阅文艺报5月14日华馨版笔者与刘小新合写的文章《都是“语种”惹的祸?》。),但我仍然认为:肯认与质疑,这两件看似偶然,却又同步发生的事情,背后有其必然的因素。它确实反映了目前华文文学研究面临的某些困境,和人们争欲突破的躁动心情。20年来,华文文学研究从无到有,从最基础的资料搜集到研究的展开,其成果主要体现在“空间”的拓展方面。这对于一个尚处于草创阶段的新的学科,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但既然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仅仅止步于平面“空间”的展开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必须有自己学科的理论建构,从学科的范畴(内涵、外延)、性质、特征的介定,到反映学科特质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的确立,才能开拓学科研究的深度“空间”,获得学科独具的“专业性”。对理论的长期忽视——或者说对本学科理论建构的无暇顾及,是窒碍华文文学研究突破和提高的关键。即如企望从理论上为华文文学研究打破困局的汕头大学四位学者的文章,也同样在理论上存在许多混乱。他们对过往20年华文文学研究指责最烈的是文化民族主义。然而他们却对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民族性、民族意识等等概念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发展变化与影响作用,并没有做出合乎实际的界定与区分,而只是笼统地把语种写作等同于文化的民族主义,从而将20年来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都一概否定。其粗暴和简单化的背后,不仅是学术态度的失慎,更是理论观念的失范。意在从理论上打破困局,却更深地陷入理论的困局,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它从另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加强华文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已是当务之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学术自审的重要和必要。肯定是一种自审,而质疑也是一种自审。不能因为某些不恰当的、过激的批评,就放弃这种自审。在肯定与质疑的辩证认识中,寻找突破口,我们将走出幼稚,迈向成熟。
命名的意义和尴尬
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有着曲折的背景和过程。最初是随着中国历史的巨大转折,人们发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并不仅只有一种大陆的形态和模式,还存在着同样属于中国文学范畴的台湾和香港的文学形态和模式。“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的命名,便由此而来。这是第一届暨大会议(1982年)和第二届厦门会议(1984年)讨论的主题。由于最初向大陆介绍台港文学的,主要是由台港移居海外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便也被放在台港文学之中进行讨论。但到第三届深圳会议(1986年),人们已经感到,仅只台湾和香港,还难以包容世界上诸多同样用汉语写作的文学现象。一方面是那些被放在台港文学框架中讨论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他们的国家认同大多已经改变,再把他们放在作为中国文学之一部分的台港文学中来讨论,显然不妥;另一方面,80年代以来,东南亚历史悠长的华文创作的复苏和活跃,逐渐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他们由“华侨”到“华人”的身份变化,使他们较之欧美华文作家更为敏感的国家认同问题,在文学研究中同样必须慎重地处置,以免引起误解。于是从深圳会议开始,包括第四届的上海会议(1989年),第五届的中山会议(1991年)都在台港澳文学(澳门是中山会议新增加上去)之后,并置了一个“海外华文文学”,作为对中国以外各个国家华文文学创作的总称。至此,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空间”,都被包容进来了。但问题是中国本土以外—或称境外的华文文学存在,实际上具有两种不同性质,即作为中国文学的台港澳文学,和作为非中国文学的海外华文文学。前者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是一致的,后者则是互相分离的。把不同性质与归属的两种文学放在一起讨论,仍然不免发生某种尴尬。于是到第六届庐山会议(1993年),便打出了世界华文文学的会标,企图在一个更为中性的语种的旗帜下,来整合无论是中国还是海外所有用汉语写作的文学现象,超越国家和政治的边界,形成一个以汉语为形态、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文学的大家族。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由此诞生,并为后来历届的学术会议所接受。
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命名,显然提升了以往对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意义。它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置诸于全球多极和多元的文化语境之中,使“台港澳”暨“海外”的华文文学,不再只是地域的圈定,而同时是一种文化的圈定,作为全球多元文化之一维,纳入在世界一体的共同结构之中,使这一命名同时包含了文化的迁移、扩散、冲突、融合、新变、同构等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发展的可能性。以这样更为开阔的立场和视野,重新审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便更适于发现和把握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置身复杂的文化冲突前沿的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体现了鲜明的学科意识,和对这一学科本质特征的认识。
当然,新的概念一经提出,新的问题便也随之而来。首先是“对话”关系的改变。原来的台港澳文学,与之相对应的是祖国大陆文学,二者“对话”所要解决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多元的发展形态问题:而海外华文文学,其相对应的是“海内”的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作家所在国的非华文的文学,它们构成两种不同的“对话”关系,处理的是移民族群的文化建构与文化参与等等问题。而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世界性的语种文学,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样作为世界性语种的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等。它们形成的多元的“对话”关系,将更多地关注不同文化之间审美方式的差异,和各种异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的多重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接近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对话”关系的改变,实质也是研究重心和性质的改变,它必然带来诠释范式的变化。其次,作为世界性语种的华文文学,毫无疑问应当包括使用华语人口最多、作家队伍最为庞大、读者市场最为广阔、历史也最为悠久的中国大陆地区文学。然而在实际操作之中,由于祖国大陆文学已有一个庞大的研究群体而自成体系,而华文文学研究范畴的形成,又有自己特定的背景和过程,它往往不把祖国大陆文学包括其中。这就使“世界华文文学”的命名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只是狭义地专指台港澳和海外两个部分。而台港澳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不同的性质,使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些普遍性的理论命题难以形成,也不能互通。例如分析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形态的分流与整合的模式,并不适用于海外华文文学;而海外华文文学面临的族群建构的文化问题,也不完全适用于台港澳文学研究。把台港澳与海外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学并列一起进行命名,是特定历史原因造成的,带有某种权宜性。对它们深入进行理论追问,便会发现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命名与实际操作之间的脱节所带来的尴尬。以致在论者的文章中,往往会出现在共同的命名下,具体的对象却是游移不定的,或者专指台港澳文学,或者专指海外华文文学。已被我们所接受和肯定的“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命名,是否也应当在重新审视中,使之“名”“实”更为一致呢?在此一问题尚未妥善解决之前,我倾向于在具体讨论中将研究对象明确化。本文下面所将谈及的,主要针对海外华文文学。
学科的背景和依据
中国的海外移民史,中国海外移民的发展史,以及中国海外移民生存的文化方式和精神方式,是海外华文文学发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学科得以成立的客观依据。研究海外华文文学,不能无视或忽视海外华人的生存状况。在这个意义上,以海外华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在近年获得显著成果的华人学研究,理当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同样,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精神和文化的层面,也在丰富着华人学的研究,二者的相因相承,对深化华人学和华文文学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20世纪中国的海外移民,就其身份认同而言,大致经历了华侨——华人——华裔三个互相交错的发展阶段,它们相应地介定了不同历史时期海外华文文学的性质、特征和文化主题的变迁。早期的中国海外移民,大多没有放弃原乡的国籍,或实行双重国籍。他们因之被称为华侨,准此,华侨的文学创作,可以视作是中国文学的海外延伸。但当中国的海外移民,在取消双重国籍认同,而选择了所在国家的国籍之后,他们国家认同的政治身份已由华侨变为所在国公民的华人(或称华族),其用汉语写作的文学,虽然在文化认同上不一定出现根本的变化,但已经不能再认为是“中国文学的海外延伸”了,而成为所在国多元文学构成的一部分。早期的华侨和后来的华人,在其移居的国家或地区,绝大多数都是少数族群。他们以文学叙述的方式参与弱势族群族性记忆的建构,使二者在文学的文化主题上,有基本一致的一面,例如强调对于原乡文化的承袭,普遍抒写着怀乡思亲的文化情绪,等等。这些题材和主题的普遍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不能把所有海外华文文学抗拒族性失忆的自我历史建构,都当作文化的民族主义进行批判,二者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从华侨到华人,还面临着另一个在国家认同之后更深入的文化适应和新变问题,即华人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融涵化,这是海外华人文化生存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同时也呈现为进入“华人”时期的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化主题上与华侨文学不同的变化与发展。而对于华裔,即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移民的后代,几乎已经完全适应或被“本土化”了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无论用华文,或用当地语言写作的文学,较多地表现为站在异文化的立场上,重新消解、利用自己固有的族性文化,在移植、误读和重构中,作为少数族群自身的一种文化资源,参与到所在国多元的文学建构之中,表现出不尽相同于“华人”时期新的文化精神与文学特征。
上述对于华侨、华人和华裔作历时性的划分,只是就其大致的发展趋势而言。事实上,三者之间身份的并存和转换,是无时都在发生。随着新移民的不断出现,他们互相交错、重叠。在这个意义上,华侨、华人和华裔,还是一种共时性的现象。
近年华人学的研究,十分关注华人身份的这种变化。战后以来,围绕中国海外移民的身份问题,曾经出现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潮的转换。从战后初期的“华侨不变论”,到六十年代的“华人同化论”,走向八十年代以王赓武为代表的“华人多重认同论”,理论思潮的更迭,从另一方面反映半个多世纪来中国海外移民生存状态的急剧变化;同时也说明了华人学研究重心已由原来立足于中国、研究中国海外移民社会与母社会之间存在的原形与变形的文化关系,转向将海外华人族群放置于居住国的历史脉络之中,来探讨海外华人与所在地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结构关系(注:参阅朱立立的文章《华人学的知识视野与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反映当下海外华人生存境况变化的华人学研究的转型,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应当有所启示。过往那种专注于寻找海外华文文学与原乡文化之间薪传性和延续性的研究,只是海外华文文学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从文化身份的自我建构,到以自己的身份文化对所在国的积极参与,是当下海外华人生存状态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也是海外华文文学一个新的文化主题。从固守唐人街,到走出唐人街,海外华文文学无论创作还是研究,都应当敏锐地抓住当下华人生存的新境况,作出新的回应。借鉴华人学的研究,运用华人学研究实证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重视田野调查,重视考察海外华人社会和华人生存境况的变化,考察海外华人多重认同对华文文学的影响,考察海外华文文学的族性文化想象与族群建构的功能及其变化,等等,这一切都将极大地丰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文化内涵,使华文文学研究取得新的突破。
文化研究和学科定位
20年来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经历了两次研究场域(对象)的转移。第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此之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台港澳文学方面;但随着90年代初期最早进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有关台港澳文学史著述的完成,90年代以后的研究重心便转向海外华文文学方面,这一变化可从历届研讨会出版的论文集中看出端倪。第五届中山会议之前的论文选题,还以台港澳文学占多数,出席会议的境外作家、学者,也以来自台港澳的居多。而此后的几届研讨会论文选题,则逐渐转向海外,与会的嘉宾中也以海外作家、学者为多数。不过这里所说的“海外”,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另一次研究场域的转移正在发生,随着80年代以来新移民浪潮的出现,新移民文学成为一个新的关注热点。新移民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东亚的日本。对新移民文学现象的关注,相应地也带动了对这些地区华文文学发展的整体关注。它使得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重心,又逐渐地倾向了北美等一些新的地区。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这两次转移,都只是一种空间性的研究对象的转移,在方法论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承袭自传统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审美批评和历史批评的研究范式。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近10年来华文文学研究队伍出现的某些结构性调整,即一些原来从事文艺学、比较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更多地参加到华文文学研究中来,而每年都有一批经过比较严格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毕业生,成为华文文学研究的新生力量。他们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为华文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风气。不过,整体说来,华文文学研究尚未改变它过多偏重于鉴赏式的审美批评的局限。而过度与研究对象的不相一致的审美诠释,其所带来的审美的尴尬,便成为学界对华文文学研究最大的诟病之一。频繁的研究空间的平面转移,虽有着新建学科拓展研究范畴的必然性,但也说明华文文学研究存在着难以深入的理论稀薄和方法单一的问题。
打破陈旧、单一的研究模式,寻求新的理论资源,建构符合华文文学自身特质的理论体系,便成为突破华文文学研究困境的强烈呼唤。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文化研究从理论到方法,重新成为华文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热点。
本来,从文本学的观点分析,海外华文文学的文本价值就是多重的,对海外华文文学也可以有多种读法。一方面可以把它作为历史文本来读,一部分海外华文文学记载了中国海外移民的艰辛历程,极大地弥补了早期移民历史文献的不足。例如反映20世纪初期华人移民美国所受到的不公遭遇的《埃仑岛诗抄》,不一定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却成为那一时期移民经历和心声的反映。其次是可以把它作为文化文本来读,海外华文文学所参与的海外移民族群拒绝历史失忆的自我文化建构,和反映的复杂多层的文化关系,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的许多理论和方法,从文化人类学理论、族群文化建构理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多元化理论,到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等,都可能是我们深入拓展华文文学研究深度空间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方法。人们寄希望于文化研究能够把华文文学研究从平面空间的拓展,引向理论的深入和突破,也在于此。当然,海外华文文学首先是作为文学文本存在的,许多优秀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所有的华文文学都能达到可供分析的审美高度。如果因为海外华人作家坚持华文写作的艰辛,就盲目赞赏,使华文文学批评变成不负责任的“赞美修辞学”,或者因为其审美价值不高,而轻率否定,这都会给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带来损失。海外华文文学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本同一性,和其价值含量的不一致性,是一个悖论式的客观存在。当然最理想的结果是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都建立在审美价值的基础之上,是通过审美认识而获得的,确实有一部分华文文学作品达到了这一高度。虽然并非所有的作品都能做到这样,但其透过文学文本所传达出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仍然应当为我们所重视。对它们价值的充分认识和互相补充,将是充分发挥华文文学文本价值的一个有益而有效的工作。
当然,我们重视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并不认为要以文化研究来代替华文文学研究,把文学折零打散,变成文化研究的材料。有一种观点认为:“那种华文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转换,对‘文化的华文文学’而言,不过是修修补补式的小打小闹,与‘文化的华文文学’的宗旨是大相径庭的。”因为,这种“小打小闹”的“对华文文学进行文化批评”,是“跟‘文化的华文文学’分属两种不同的范畴。也就是说,语种的华文文学是属于学科内部方法论转换的范畴。‘文化的华文文学’则属于‘文化研究’中某种新学科建立的范畴。”(注:参见《华文文学》2002年第2期《浮出地表的“文化的华文文学”》。)这里已经说的很明白,所谓“文化的华文文学”将不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它的学科定位在“文化研究中某种新学科”。这是一种华文文学取消论。在我看来,引入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正是为了更好地确立华文文学研究的文学定位,说它是方法论上的修修补补小打小闹也好,期待它给困境中的华文文学研究带来某种突破也好,华文文学研究的学科定位都不会改变,它的定位就在文学。文化批评是我们深入进行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并不能因为我们重视了手段和工具,就以手段和工具取代了本体。这是一个本来并不复杂、但仍须深入辩析清楚的问题。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移民论文; 海外华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