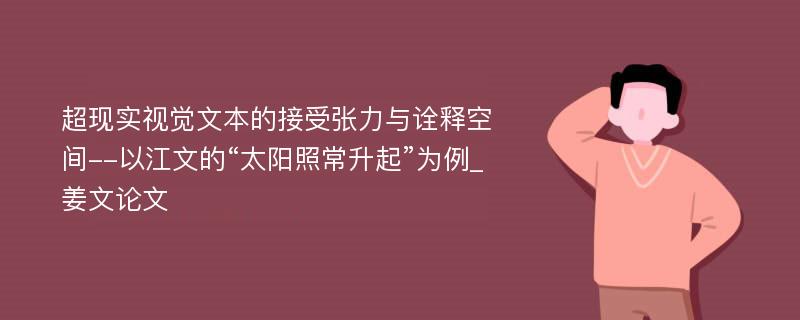
超现实视觉文本的接受张力和解释学空间——以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学论文,为例论文,文本论文,视觉论文,太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许多观众看完姜文的新片《太阳照常升起》的第一反应是“看不懂”。确实,《太阳照常升起》(以下简称《太阳》)对中国观众的接受习惯和期待视野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一般来讲,对新鲜事物的出现是绝不能因为看不懂、不习惯就一棍子打倒,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姜文曾经为自己辩解道:“确切地说,这电影不是看不懂,是难归纳,我妈就这么说,不习惯。”① 尽管影片难以归纳,我们还是从《太阳》中看到了一种可贵的原创精神和勇于实验的先锋品格,这无疑是值得赞许的。姜文的《太阳》一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线性叙事结构和情节片的写实风格,大量的意象隐喻和非逻辑的跳切镜头自然让我们想起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于法国的超现实主义电影浪潮。“超现实主义电影之父”路易斯·布努艾尔的杰作《一条安达鲁狗》和《黄金时代》中的符号和结构,使我们可以暂且将与之风格近似的《太阳》归纳为一部超现实的先锋实验文本。从形式的定性再回到内容的考量,我们同样可以赞许的是,由于《太阳》反映了1958年至1976年这段中国人不应忘记的特殊日子,对那个疯狂的年代,能够直面并表现理想的幻灭和宏大叙事的解构,仅此一点,足以让我们再次感动。这种题材在姜文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20世纪90年代初也许并不显得特别和可贵,但相对于新世纪以来开始泛滥的《英雄》、《十面埋伏》、《无极》、《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国产大片对历史的荒诞演绎态度和商业娱乐片的疯狂搞笑浪潮,《太阳》在电影审查制度所带来的有限表达空间中曲折地运用超现实的艺术手法来激起一点反思,表现一份真诚,其办法之聪明,其用心之良苦,能多少抚慰一下我们因为“看不懂”而引起的烦恼。
然而,本文的写作主旨并不在于对影片形式和内容的分析与探讨,而是想在解释学的学术层面上,从观众的理解和阐释的视域出发,充分揭示这种超现实视觉文本所具备的充沛的接受张力和巨大的解释学空间,以此来彰显《太阳》的先锋意义和实验内涵。实际上,以解释学的学理来观照,造成“看不懂”的首要原因在于接受者而不是视觉文本的制作者。显而易见,比较视觉文本对外在物象直观而真实的复制与文字文本对读者“二度加工”的依赖,观众更能轻易地理解到导演在视觉文本中灌输的意图与主题。换言之,直白的图像接受已经使观众习惯于捕捉制作者通过影视文本表达的原意,观众只有领会到那个固定不变的预设的主题时,才能说“我看懂了”。这样一来,“作品的意义就是埋藏于作品中的矿藏或文物,等待考古式的挖掘,或者作为潜在的谜团,等待我们去揭秘”②。西方普遍解释学的创立者施莱尔马赫就是这种“原意观”的信仰者,他认为理解的本质是“更好的理解”,即不断地趋近和复制作者的唯一意图。“按照这种态度,作品的意义只是作者的意图,我们解释作品的意义,只是发现作者的意图。作品的意义是一义性,因为作者的意图是固定不变的和唯一的。”③ 但是,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看来,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文本本身之中,而是依赖于对它的理解和解释,作品的意义往往随着不同时代和不同人的理解而发生改变。因此,理解的本质不是“更好的理解”,而是“不同的理解”。伽达默尔说:“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我们只消说,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这就够了。”④
遗憾的是,就像姜文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所说的:“电影的功能是什么呢?人们为什么要看电影啊?因为中国人生活在这个正在发展中的社会里,常常都要被格式化。但人的心灵是不应该被格式化的。”的确,观众的观看习惯已经被众多的情节片、商业片“格式化”了。这次姜文尝试着改变了一下叙事方式,观众就普遍以“看不懂”为由对此作,出否定的评价。《太阳》中那些变换的形式和隐晦的意象让观众不知道导演在说什么,长期形成的“原意理解”就这样突然失效了!其实,观众忘了自己有主动参与理解的权利和能力,更不知道在这部影片中,导演有意让他们去生成属于自己的多元解读。姜文说得很明白:“我见过几拨人在为这个片子吵,有画图的、猜测的、打架的……电影不过就是刺激了他们的想象力,把每个人的储备、精力、世界观都调动起来。调动起来了就有强劲的想象,强劲的说服人的愿望,要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所有的表达实际上都在表达自己。”⑤ 尽管许多观众反映“看不懂”《太阳》,但姜文的实验目的还是被明眼人看出来了。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对《太阳》评价说:“这部电影有非常多的解密的快感,几乎像《达·芬奇密码》般繁复,一旦找到关键,就觉得此片非常清晰和令人震惊。”⑥ 一言以蔽之,整部《太阳》就像影片中那个重要的隐喻——那张合影照上空洞缺失的李不空的头像,等待观众根据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去填补内容和意义。
一、作为超现实视觉文本的《太阳》的接受张力
众所周知,图像传递信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视觉接受的直观性和同步性。因此,视觉文本与生俱来的简单直观的优势对受众构成了巨大的诱惑,那种让人身临其境的当下感使观看变得如此不可抗拒。由此,不难理解图像叙事何以会迅速成为这个时代最显著的表征,更不难理解视觉文本何以能轻易地将文学文本放逐到边缘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话语霸权。相形之下,传统的文本阅读对主体的接受能力则有一定的要求,除了必须接受基本的文化教育等后天的思维训练,在实际的阅读过程中还需要读者充分调动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形象思维将语言文字转换为艺术形象。可以说,文学文本在接受上所具有的这种内视性、内运性和能力性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使受众获得更为深刻和丰富的审美体验,又无形地给读者构筑了一道接受障碍。所以,当声光色形组合的图像向我们直白地扑来时,人类天性中潜藏的畏难心理终于得到彻底的释放,“观看甚至成了观看者最好的休息方式”⑦。一闪而过的电影流容不得我们深入思索,我们的脑子成了视觉文本制作者的“跑马场”。就这样,长期形成的被动的浅层次观看培养了我们在接受上的惰性和慵懒。“在黑暗的包围中,观众的自我意识逐步被削弱,以至忘却了自我。另一方面,观众的注意力被充分调动起来,心醉神迷地紧盯着银幕上流动变化的画面影像,整个身心都沉没在声光色的变幻中,仿佛进入似睡非睡的梦幻状态,在做一场被人事先编排好的梦。自然,观影过程中观众的自我意识有时也会跳出,但更多的时候是不由自主地沉迷在影像世界之中,不知不觉地与其认同。”⑧ 也许,这就是杰姆逊所说的在与图像零距离接触中所导致的“主体的消失”。不仅如此,在当代大众审美文化潮流中制作的大量商业娱乐片和情节片,更加助长了受众的思维惰性和消遣心态。
毫无疑问,姜文的超现实视觉文本《太阳》,是一次对图像接受的直白性、被动性、惰性和消遣性的发难与挑战。首先,分段式的叙事结构要求观众对“疯”、“恋”、“枪”、“梦”四个部分的次序进行重新排列才能厘清影片的基本叙事逻辑。由“疯”到“恋”的过渡中那漂动的衣服、缓缓流淌的河水与梁老师所唱的《美丽的梭罗河》之间的诗意衔接,由“恋”到“枪”的过渡中明显的时间重叠式的衔接,由“枪”到“梦”的过渡中色彩的重合和正反对比式的衔接,所有这些非逻辑的组合都迫使观众必须动脑子去连接其中的某种诗意、情绪或意义,才能完成对影片内容最基本的理解。其次,影片开始时疯妈在树上对远处呼喊“阿辽沙,别害怕……”与最后她在火车上对太阳的呼喊之间的关系,李不空下雨天去找年青时的疯妈时所说的“我知道,我知道”与后来疯妈听见鹦鹉叫“我知道,我知道”之间的意味,影片开头的鱼鞋、鲜花和铁轨与最后那些鲜花、婴儿和铁轨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枪带与自杀、李铁梅画像与小李铁梅,等等,所有这些关系都像一个个等待解密的符号组合,催促观众调动自己的理解力和各种经验储备去主动地深度追求方能建构属于自己的意义序列。像其他实验电影一样,《太阳》尽可能地省掉了许多故事背景的交代和人物关系的叙述,很多场景和台词之间的关系需要观众绞尽脑汁地连缀。这不仅增加了接受的张力,同时也增加了接受的难度。
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学文本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对读者而言是间接的,它必须依赖受众的想象和再创造才能呈现在人的意识里。受众个体间的千差万别和语言本身的模糊性与含蓄性,自然导致文本接受上的未定性。这正如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所言:“因其的确无自身的存在,并因为我们正在想象它、生产它,所以我们的想象存在于它的存在之中,而它也就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中。”⑨ 但是,以图像为载体的视觉文本由于其对客观物象的真实复制而给接受和理解带来了无以复加的确定性,演员的逼真表演以及影片对生活原生态的呈现更是将一切都定型化。因此,图像叙事的确定性不需要受众主观想象的介入和“二度创作”,同时,动态呈现的画面也将观众的视线牢牢吸附在快速更替的电影流中。为了不放过下一个镜头的内容,观众没有时间去想象和思考,也不愿和不需忙里偷闲地参与再创造。这显然有别于绘画、雕塑的静态造型给观看者的思考和想象以“自由发挥的余地”⑩。基如此,一些反传统手法的实验电影制作者总是想减缓情节的节奏,降低情节的魅力,运用大量隐喻性的意象和违反生活逻辑的情景来制造观众接受上的困惑和空白,从而增加意义理解的不确定因素,刺激观众参与解读的兴趣和积极想象的动力。同样,在《太阳》中,那双莫名其妙的鱼鞋,那座神秘的石屋,那个写着“尽头非尽头”的路标,还有那张被剪掉头像的合影照以及老唐与智者谈话时背后耸立的宫殿,等等,都构成了一组组富有象征意味的符码。此外,那顺流而下的衣服和鞋,那毫无惊险地诞生在铁道上的婴儿,那双手插在裤兜里的吊死者的形象,都在背离生活常识的情况下建构起丰厚的理解张力。
戏剧表演是一种假定性的艺术,正所谓“三五人千军万马,六七步五湖四海”。舞台上那些虚拟化和象征化的表演必须依靠观众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运用生活经验来加以补充和丰富。而影视艺术却凭借图像的功能,先天地具备了与生活等同的真实感。这种强烈的真实感一方面增加了视觉文本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强化了观众对影像内容的认同,造成了理解的单一性和以寻求导演的意图为目的的“原意”观。但是在《太阳》里,姜文似乎在有意破坏图像叙事的真实性,故意表现自己的叙事好像没有任何预设的主题,和观众玩起了捕捉意义的迷藏。除了疯妈那些不知所云的话语,剧中人物反逻辑的行为和突兀的举动,姜文还特意用苍茫的大漠群山、空中飞舞的燃烧的帐篷、美丽的鲜花、石屋、小河、动听的歌声、吟诗声以及整部影片浓烈的色调等,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亦真亦幻、似傻如狂的诗意世界。在这个极富张力和诗性的视觉文本里,我们完全可以不考虑制作者的原意何在,只依据自己的想象自由地流连徜徉。
二、作为超现实视觉文本的《太阳》的解释学空间
姜文曾说:“电影先天不足,它太实,啪一照,想要的不想要的都在里面了。……我的非分之想就是,怎么能让电影在写实的基础上多一点想象力。国产电影……写实。写实的东西保险,观众容易接受,但也会付出代价,就是大家太容易接受了,紧接着就自信了,自信就踩你了。”(11) 看来,姜文非常清楚自己这次形式探索上的冒险性和视觉接受上的革新性。难得的是,他还是大胆地向前迈出了实验的步伐。正是这种大写意的开放性的视觉文本,给我们提供了多元理解和阐释的可能,也让我们罕见地感受到中国电影的先锋品格。但需要注意的是,《太阳》在接受上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也必须受到理解的历史性和客观性的制约。“这种客观性不但保证历史不受主观的随意曲解,同时也是衡量解释是否客观的标准。”(12) 显然,影片字幕上的1958年和1976年就注定了文本的历史内涵以及理解与阐释的客观性。事实上,那个年代的特殊的背景和特征已经渗透进许多镜头和台词。浪漫的爱情、对英雄的崇拜、扭曲的情欲乃至“阿辽沙”、《红色娘子军》和军装等,无不向我们暗示所有的理解与阐释都必须从这些特定的历史蕴涵出发,否则我们将无法明白剧中人物突兀或疯癫的行为背后所隐喻的时代信息,也无法理解普遍人性与历史个性的交互感通的关系。解释的空间和理解的自由常常就出现在微观意象的未定性与宏观历史的确定性之间。疯妈对“最可爱的人”的倾慕以及将儿子的照片与代表英雄主义的李铁梅头像合在一起的举动,梁老师对爱情失望后的自杀与那个时代的禁欲主义,带着理想和激情回国参加建设的老唐与他后来的颓废和玩世不恭,都需要我们在有限的历史内涵中生成无限的属于自己的意义诠释。
从接受的视域看,反常搭配和陌生化处理能够对读者既定的阅读习惯构成冲击,极大地激发受众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从而最大程度地调动人的想象能力。在《太阳》这部诗性特质浓郁的视觉文本里,我们可以随处发现视觉意象的反常搭配和陌生化处理。譬如婴儿出生在鲜花和铁道中,梁老师用枪带自杀,衣服和鞋能够在水中像船一样漂行,用圆滑的石头盖房子,女人和温顺的羊上树,小号的音乐声招来肉欲的偷情,等等。这些违背物理与情理的反常组合,一方面在给观众制造陌生化效果,从而引起人们审美的新颖性和奇特性感觉;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加强了意义理解的含混与朦胧,扩张了影片的解释学空间。因为反常搭配和陌生化重组完全解构了人们既往的观看经验,形成了新的接受空白。从逻辑上讲,既是空白和含混“赋予接受者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13),也是它增加了观众理解与阐释的高度和难度。
狄尔泰说:“一部作品的整体要通过局部来了解,局部又须在整体联系中才能理解,这就是一种解释的循环。”(14) 或从局部去解释整体,或从整体去理解局部,任何意义的建构总是在二者的互动互生中完成的。同样,对于采用分段式的圆形叙事结构的《太阳》,“疯”、“恋”、“枪”、“梦”四个部分对解读影片整体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不仅如此,即使是对许多很小的局部意象的深度理解也能帮助我们开掘导演的整体意图。譬如,影片最后孩子的出生和太阳的升起作为一组形象显然象征着未来和希望;而将孩子又放在铁道上,就更加暗示了时间的飞驰和世界的更新,这不由得让我们想起片名和导演对电影的总体意向。姜文这样解释说:“片名的来源是从《圣经》里来的。《圣经》里有这么几句话,特别符合这个故事:一代人来,一代人又走。大地永存。日头升起又落回到它升起的地方,太阳照常升起。非常有意思。不但把故事内容全部概括,而且定位在目前状态认同的一种自然和人的关系。关系就在于一代人走,一代人来,大地永存。”(15)由此看来,孩子、鲜花、铁道、太阳与影片的整体意向、意境是协调一致的,形象的解释就是一代人来,一代人走,大地永存。我们从这个整体意绪再去看那块写着“尽头与非尽头”的路标,就会发掘出更深的寓意:一个女人奔着幸福的爱情来,一个女人朝着绝望的爱情走,但是谁又能知道那幸福的爱情不是就此走到了“尽头”?那绝望的爱情不是一个“没有尽头”的旅程呢?是的,只有大地永存!
三、对《太阳》的多元理解与阐释
疯妈教训儿子说:“只能说你不懂,不能说你没看见。”这其实也是导演企图再三提醒观众的话。从解释学的视域观照,对《太阳》的“懂”与“不懂”都不是针对领会导演的意图或作品的原意而言的。影片中大量非逻辑的情景连缀和反常的意象组合本身就颠覆了单一主题式的传统,赋予了观众多元理解与阐释的可行性。大致说来,观众的意义解读和构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观众能够从影片中强烈地体会到一种理想的幻灭感。两个女人——疯妈和唐妻、两个男人——梁老师和老唐,最终都从理想和激情走向幻灭和绝望。这里交叉着梁老师、疯妈和唐妻的爱情的幻灭,老唐和梁老师从南洋回国参加建设到后来的颓废所表现出的激情的幻灭,疯妈对军人的崇拜和唐妻年轻时对男子汉的崇拜到最后的英雄主义的幻灭。其次,当我们在影片中看到这些宏大叙事渐次解构时,我们似乎又能真切地感受到一种诗意的生存及其隐喻的永恒和希望。太阳、鲜花、小河、森林、群山、大漠、歌声、古诗、鱼鞋……在影片中,姜文尽可能地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唯美的诗性图画,就连自杀也显得那么优雅和洒脱。尤其是疯妈在树上对着远方和在火车上对着太阳的叫喊,使人仿佛挣脱了苦难和幻灭,感觉到一股饱含希望的向上的力量。姜文说得有道理:“人类夸张自己的感情没有错,但问题是这感情是不是天地为你而感动,是不是天地为你而改变的。显然不是。所以,太阳照常升起。”(16)在自然的永恒面前,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诗意的栖居和永远向前!当然,我们还能从《太阳》中隐约领会到影片对那个特殊年代的诸多反讽意味。从李不空下雨天去求爱到遗物中的三根大辫子,从求爱时不停地重复“我知道,我知道”到后来鹦鹉的学舌,从山顶上老唐说“你的肚子像天鹅绒”时的粉饰到后来的“那就是他妈的一块布”,当然还有作为英雄主义化身的小李铁梅对上海来的唐妻的羡慕,无论是政治层面的还是情感层面的反讽,都可以让我们在反复回味中阐释出更多的意蕴。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心理和潜意识等视角去解读《太阳》蕴含的多种理解。毫无疑问,所有的意义生成都来自观众的视界和文本的视界的相互融合,来自影像的客观内容和观众的主观理解的对话与交流。
不可否认,作为先锋探索的超现实文本,《太阳》还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缺憾。一言以蔽之,《太阳》给我们的总体感觉是诗性审美富余而思想力度不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影片与原小说的对比中看得很清楚。原小说《天鹅绒》讲的是,母亲因为穷得连袜子都穿不上而常常遭人取笑,苦恼的她决心用儿子的学费给自己买双袜子。可到买的时候,她又突然改变主意,买了一块“珍贵”的猪肉想让全家享受一顿。但上个厕所的时间,猪肉却不翼而飞了。于是,母亲疯了!显然,小说所表现的现实性和批判性是真实而深刻的,具有特定内涵的“猪肉”要比影片中那双导致母亲发疯的唯美而多义的“鱼鞋”更有思想力度。姜文对死亡的处理也过于脱离观众的生活经验。影片中对梁老师自杀的诗性处理显然与那个年代无数痛苦不堪的自杀是相悖逆的,它扭曲并得罪了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情感。此外,影片中对梁老师自杀动机的交代、疯妈突然失踪的伏笔准备、老唐和未婚妻在荒山顶上的“神遇”等,都由于姜文的大写意手笔和大“减法”处理而显得过分跳跃和突兀,在将一切理解和阐释交给观众之余,也确实大大超出了他们的观看经验和期待视野。
但姜文在《太阳》上的努力和尝试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无论如何,这是一部极富原创价值的视觉文本,因为“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电影,在看过之后,我们往往在它的形式或者内容上,能找到一个渊源。也就是普通观众说的,这个片子像某个片子。但是看过整部影片之后,我们发现《太阳》似乎找不到一个渊源——也就是所谓的前无古人”(17)。对这样一部“前无古人”的先锋之作,仅用票房收入和观众“看不懂”的第一反应去衡量和评价是有失公允的。质言之,能否宽容并接受姜文的实验和探索,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电影的艺术发展。
注释:
①⑤⑥(11) 姜文:《我一直说我是个业余导演》,《南方周末》2007年9月27日。
② 金元浦:《文学解释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08页。
③ 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④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01页。
⑦ 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⑧ 修倜:《论电影艺术接受的被动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
⑨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金元浦、周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67页。
⑩ [德]莱辛:《拉奥孔》,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63页。
(12) 殷鼎:《理解的命运》,三联书店,1988年,第291页。
(13) 金元浦:《范式与阐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页。
(14) [德]狄尔泰:《解释学的形成》,转引自张首映著《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
(15)(16)(17) 姜文:《它是我心中的太阳》,《大众电影》2007年第18期。
